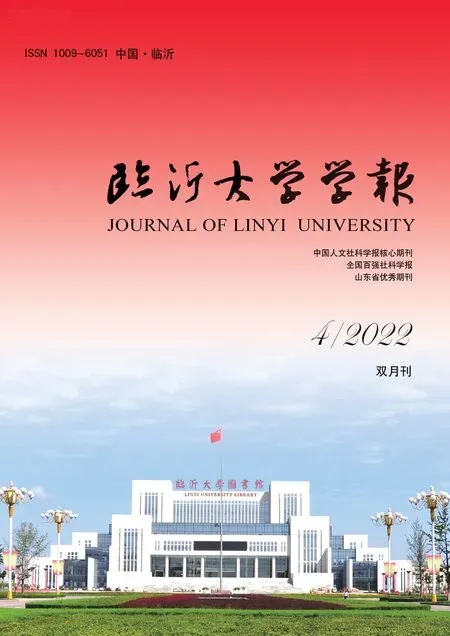我们为何不知自己正在做梦?
——论走神与梦境活动的现象学特征
2022-11-24陈亚立
陈亚立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在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中,一位棋手正在与国际象棋大师对弈,苦恼于对方不断进行长考的下棋风格,他暗暗在自己的内心中下起了另一盘棋。而等到大师终于落下一子时,他兴奋异常,迅速地拿起棋子走向一格空位,并说道“将军”。然而,当他面对对手及旁观众人的不解神情时才恍然大悟:他拿起的是现实中的棋子,走的却是心中的那一盘棋。
所谓的想象或幻觉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以不同的面目接近我们,而我们却总是在它们离去的后知后觉中才真正将它们识别。作为开始,当我们真正开始追问“我们为何不知自己正在做梦”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和审视一下“走神”这一同样常见的现象。在其中,我们能够发现它与做梦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毕竟我们有时会称它为“白日梦”,并且同做梦一样,没有人当下会立即意识到自己是“正在走神”的。
一、走神:直观与想象的原初性地位
胡塞尔将现象学这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定位为一种认识批判。现象学处理现象如何呈现、如何构造起自身的问题,这即是说,现象学探讨的是某一已然在我们眼前的事物是以何种方式及样态显现自身,并在何种条件和意义下被我们所把握的。胡塞尔将这种我们对现象进行把握的原始过程或行为叙述为直观(intuition)。对胡塞尔来说,直观即是“一切原则的原则”(principle of all principles):“每一个原初呈现的直观都是认知的合法来源,对于任何一个在‘直观’中被原初呈递的事物,我们都应单纯地以它们作为存在而呈现的那个样子接受下来,但也只是在它们借以呈现的这个界限之中。”[1]44直观作为事物借以呈现的原初场景和界限,其本身直接与感知或感性素材相关,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直观的本质依据于意识的一种意向性(intentionality)结构,即“意识总是关于……的意识”。感知或感性素材参与直观过程,但并不从根本上决定最终的直观内容。
比如,此刻教室里有一把椅子,从我座位所在的角度只能看见这把椅子侧面的样貌,就此而言我所获得的感性素材只有椅子的侧面这样一幅画面,但出于我对这间教室(连同对整个世界)的了解,在我看着这把椅子时,我的意识所真正把握的对象就是教室里“活生生”出现的这把椅子本身——它是在空间中存在的,三维立体的事物,而不是只有一个侧面。这其中就刻画着空间物作为显现者(that which appears)与其显现(appearing)之间的关联与差别。[2]12再比如,当我被分派了一项“清点教室中椅子数量”的任务时,我再向教室里的这把椅子看过去,我眼前看到的画面并没有改变,但我所意向的内容却已不再是教室里个别的“这把椅子”,而是一般性的“一把椅子”。此时,它具体的外观、颜色、材质等虽然同时被我看见,但其中只有它作为“椅子”的本质成为了我当下所直观到的东西,这即是本质直观(eidetic intuition)。“就像个别直观或经验直观的素材是一个个别对象一样,本质直观的素材是一个纯粹本质。”[1]9因而,我们的直观内容或意向对象绝不单纯由感官所接收到的感性素材所决定,相反,它取决于“看”的方式,取决于一件事物以什么样的形式、在什么样的意义之中让我们看到。
对于一位棋手来说,当他面对黑白格内的整盘棋子时,他既不是在看那些立体棋子的外观样貌,也不是在看它们各自所对应的“马”“卒”之棋子含义,而是在整盘棋局的动态演绎中不断直观它们可能的功能、效用。这意味着他要不断忽视并越过他所实际获得的感性素材,将目光投向那些在旁人看来是虚幻的对象。对于这位身处其中的棋手来说,只有他在运用着正确的方式“看”着这些棋子,并且以这种方式使棋子得以在最原本的意义中呈现自身。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棋手即是“把存在者从晦蔽状态中取出来而让人在其无蔽(揭示状态)中来看”[3]252,因而,他也以这种方式朝向真理:“真理的本质揭示自身为自由。自由乃是绽出的、解蔽着的让存在者存在。”[4]221但是,对于不观棋的旁人来说,这位棋手仅仅只是双眼发呆、目不见物地出神而已——他们看得见棋手所接收并已越过的画面景象,但“看”不见棋手在此之上所获得的直观内容。
然而,以上的例子还不能完全说明常见的“走神”情况是怎样的,因为棋手下棋时的出神与我们思考数学问题时类似,都是我们在以一种主动的姿态进入到极为专题性的观察之中,而“走神”则是不知不觉地、漫无目的的,因此我们仍需在一种更常见的情况中说明它的特性。
回到之前关于椅子的例子当中。倘若我已从这所学校毕业,却在多年以后再回到这个曾经的教室,面对毫无改变的这把椅子时,我首先所看到的既不是单纯的“这把椅子”,也不是任何一般的椅子,而是不可避免地被带到当初曾坐在这里的回忆中。此时我的眼睛可能正对视着这把椅子,也可能在整间教室里环顾扫视,但我从来都不是真正想看见它们当下的模样。或者,可能我并没有亲自来到这间曾经的教室,而只是看到了它的照片,于是我就在目不转睛地盯着照片中的每一个细节时走了神。在这一过程中,回忆的呈现比当下的感知更为强烈,这正是我走神的原因。而无论这种回忆是似真还是模糊,它都处于我们的幻想或想象之中。
想象并不意味着脑海中浮现着虚幻的事物——相反,至少对于胡塞尔所阐释的想象(phantasy)概念来说,它更多地意味着我们把某件事物从完全的虚幻中带到近前。比如,当我在凝视一幅老照片时,曾经的人和事物便再次进入到我的视野之中,但这并不是说我从这幅照片上看到了印在相片中的细节样貌,而是通过看照片这一过程,“曾经的它们”被再次带到了我的面前。也就是说,想象是非当下之物以当下化的方式被带到近前来的过程。倪梁康教授指出:“‘想象’的对应概念不是‘现实’,而是‘感知’;它们一同构成现象学意义上的‘直观’……‘想象’在胡塞尔那里归根结底首先意味着当下化(或再造、再现、想象变异等等)。”[5]383-386因此,想象意味着直观对象的“非当下”,即不以此时此地的感知素材所构造,但想象的本质并不在于它朝向或构造着某种意义上的“非现实”。想象的对象在当下化与再现的过程中被意向性把握,同样成为直观(“认知的合法来源”)。
回忆则是想象的一种形式,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想象的对象可以是虚构的,不具现实存在性的(如抽象的几何图形,或某些我不曾所见之物),但回忆或回忆的对象则是我曾经经历过的,它曾经是某种当下的感知,并且我在回忆时仍确认着这种存在性。Dermot Moran与Joseph Cohen在合著的《胡塞尔词典》中认为:
当我们回忆一客体时,其意思是我们并不真地具有该客体之直接的、实际的、躯体性的以及时间性的现存。在记忆中我们甚至肯定该客体并非当下存在着,但仍然存在有对其存在的某种关涉,它仍然以特殊的方式被设定着(作为过去)。……换言之,在一回忆行为中,被回忆的经验被呈现为一原初被我经验者,但现在具有着一时间性距离,后者使其与我当前经验相分离。[6]161
因而,回忆作为想象的一种形式,其本质在于其中被当下化的直观对象是我曾经经历者,并且在这一当下化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且确认着这种性质。比如,当我离开这间教室时,我为了回想起那把椅子最后有没有被放回原位,我需要让我离开教室之前的经历呈现在直观之中,并且,我必须在这种直观之中同时明确这是那个“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我所亲身经历过”的,它才能真正作为回忆呈现。但是,如果回忆的这一性质未被明确或者丧失,那么对于回想者来说,他所意向和直观到的内容就并不意味着“回忆”。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直观作为“一切原则的原则”,它的具体内容及其构成可能会有不同形式或来源,但意识所直接面对和指向的对象在其绝对被给予的意义上是地位等同的。“在进行任何智性的体验和任何一般的体验的同时,它们可以被当作一种纯粹的直观和把握的对象,并且在这种直观之中,它是绝对的被给予性。它是作为一种存在之物,作为一个‘这里的这个’被给予的,而对这个此物的存在进行怀疑是根本无意义的。”[2]27胡塞尔不仅在以上这段话中着重指出感知的现象学意义,同时接着强调想象在此处的同等地位:“这对一切特殊的思维形态都有效,只要它们是被给予的。但是所有这些特殊的思维形态在想象中也都能够是被给予性,它们能够‘仿佛’在眼前一般出现,但却不是作为现实的现在性……即使这样,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被给予性,它们直观地出现在这里……”[2]28
所以,当我们初步审视“走神”这种状态后应得出如下的结论。无论是何种原因导致了我的出神,它的最主要特征是我在某种程度上忽视当下的感知(或者说对可能的感知视而不见),将注意力转向想象中的内容。在此过程中,由于想象的对象同样可能具有绝对的被给予性,因而从直观内容上讲,我们前后所“看”的东西并没有层次上的不同,仅仅只是不同性质的意向物的替换。而我们对这些内容的性质辨认依赖于更加复杂的派生性认知活动,如对其存在性的一般判定、与我过去经历的关联等等,它们并不总是持续而直接地被我们所把握。
从现象学的意义上讲,“走神”正是直观行为在认知过程中的原初性、持续性和奠基性的显著体现,在其之中还隐隐透露着意识对于各种意义上的超越的原初渴求。正是因为它直接还原着直观行为(与直观中的想象行为)的这种原初特征及过程,我们才对它从不感到陌生和怪异,也更谈不上有所“怀疑”(因为无意义)。我们本就一直处于这样的状态中,“走神”只是以最专注且纯粹的方式让我们有了更强烈的体验。只有当我们最后“回过神来”,即重新建立起所有更高级的认知架构时(如对当下所处的时间—空间序列的建立),我们才会依照这一清醒时的标准将刚才的状态判断为是“走神”的——“走神”按其字面意义来讲也只存在于这一唯一的标准之中。
二、梦境:世界与在世存在的源始境域
实际上,做梦与走神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正是以上部分论述的内容。康德就在谈到做梦时说道,它的主要特征是(相对于清醒时)“逐渐地产生一种表象的混乱……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即想象力的一种不自觉的活动”[7]101。叔本华也曾说道:“用以区别梦和现实的唯一可靠标准事实上不是别的,而是醒时那纯经验的标准。由于这一标准,然后梦中的经历和醒时生活中的经历两者之间,因果联系的中断才鲜明,才可感觉。……人生和梦境都是同一本书的页子,依次联贯阅读就叫做现实生活。”[8]44-45康德用简短的语句说明了梦境活动的主要特征,如表象的混乱、想象力的不自觉运用,而叔本华则精准地指出了梦境与现实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在清醒时能准确地判断梦境并不属于现实的一部分。这些都与我们走神时的状态存在相似之处,因而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已能够弄清一些问题。
然而我们在走神时的体验与做梦又是不同的,正是这些不同造成了梦境的独特和强烈感,我们只有将其揭示出来才能回答那个最主要的问题。我们为何不知自己正在做梦?实际上,我在此处的回答已在前面的部分有所提及,即与“我们为何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走神”的情况类似——我们之所以不知自己正在做梦,是因为我们在梦里体验着最纯粹的原初状态,这种状态同样不显露地存在于清醒时。我们之所以不“怀疑”梦中的体验,是因为只要我们存在着,我们就必然以这种姿态获取着任何可能的体验,而我们不去怀疑梦中场景和事物的实际存在性,恰恰证明了这一层面的认知是要晚于它而建立和进行。这种原初的存在状态,海德格尔将其揭示为此在(Dasein)的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
与我们体验走神时不同,梦境之所以能为我们带来强烈的感受,是因为我们在其中“亲身”面对着各种事情,遭遇着各种场景,泛起着各种情绪。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场景,在梦中也是极为“真实”的。比如,在我清醒时,我有可能凝视着偶然遇见的一件工艺品出神,此时它直接被我的直观所捕捉,牢牢占据着我的注意力,其他的一切则视而不见,甚至连我自己都已消失;而在梦里,这件工艺品出现的方式绝不可能是“从天而降”、凭空而来,我一定是梦到我走在某个地方,或是在哪个房间里碰到了它,于是我凑上前,或是拿起它,甚至打碎了它。与我清醒时的那种观察状态不同,在梦里我与这个事物的遭遇一定是“亲身”的,并且是在一定的意蕴关联中有所根据的——这意味着它必然是在某个具体的场景中(无论这个场景是否荒谬),通过与我的遭遇呈现出来。这种整体背景域的必然涉入关联着海德格尔所阐释的“世界之为世界”的世界性(worldhood)概念。
对于胡塞尔来说,意向内容与意识活动之不可分割的意向性结构是一切认识发生和事物得以呈现的前提,在这种结构中,世界也可以作为一种意向对象(不充分地)呈现于意识之中,但它仅仅是呈现在意识中的无限可能多对象中的一种。从本质上讲,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先验自我是无“世界”的,它是一种超然的存在。而对于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此在(Dasein)来说,“世界”就是它的根本存在地、存在域,熟悉地栖居之场所,此在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世界性’是一个存在论概念,它指代着‘在世存在’的其中一个构成性环节的结构。……从存在论上来讲,‘世界’一词不是用来对此在所本质上不是的那些事物的特征加以描述,它恰恰描述的是此在自身的特征。”[9]92
海德格尔用在世来形容此在的这种“向来已在……之中”的根本存在状态,而这种“在……之中”也显然不是单纯三维空间性的“置于……之内”。“在……之中”(Being-in)意味着向来与不可避免地与各种事物遭遇,意味着此在在自身的展开状态(disclosedness)中与事物总在产生涉及一个意蕴整体的关联(involvement),事物总以这种方式闯进此在的视野并显现自身。而面对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闯入视野之中的事物,此在也并非以一种孤立、超然的观察者身份进行观看和认知——由于此在的存在是一种生存(existence),即总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其自身的存在有所作为[9]67,因而它首先且总是处于同上手之物(ready-tohand)打交道的操劳(concern)之中。[9]97
操劳,意味着此在同事物的最源始联系并非胡塞尔现象学中观察意义上的意向性关系,不是被给予性在直观中的单纯被把握,而是蕴含于在此之前就已必然存在的以使用与应对为代表的过程。对于此在来说,事物的最源始显现不是可以静观的现成在手状态(present-at-hand)[9]68,而是随时要将其置入使用之中的上手(ready-to-hand)状态。“上手”并不一定意味着此在对其主动地使用,那些此在需要躲避和害怕的事物同样是以上手之物的状态显现自身。事物之所以首先以上手的方式源始地显现,是因为此在以生存的方式存在着;这即是说,此在总是在不断领会着自身的存在,维护并听从着这种存在,并在各种筹划中对这种存在进行着作为。此在总是以自身的生存面对着其他存在者的存在,因此任何事物的本真显现首先基于此在对自身存在状态的透彻可见。当此在对某个(以现成在手式呈现的)事物进行纯粹地观察时,此在实际上短暂地遗忘并遮蔽了自身的生存,并且只有在这种短暂的遗忘与遮蔽中,事物才有可能以如此孤立(indifferent)和纯粹(pure)的方式呈现出来。
实际上,海德格尔并不反对意向性的根本地位,相反他是在一种更为源始的结构中拓展和揭示着它的内涵。“生存者与现成者之间的差异恰恰在于意向性……一扇窗户、一把椅子、任何广义上的现成者决不生存,因为它无法以意向的‘朝之所向’的方式向现成者而为。”[10]87此在的意向性即是以生存的方式朝向现成者而有所作为,它通常体现在各种行为之中,而纯粹的“看”只是其中一种形式。而此在有所朝向,并同时被动遭遇着的众多存在者,又在一种广泛的关联整体中构成了环围着此在的根本场域——此在以这样的方式生存于其中,存在于世界之中(Being-in-the-world)。这个“世界”才构成了源始意义上的此在的“现实”。这个现实与“实在性”不同,实在性是认知的产物,它的形成依赖于一系列复杂的内容构建,而现实在源始的意义上,于认知的架构还未完整形成时就必然存在和发生着。
弗洛伊德曾写道:“人从梦中醒来后,会天真地以为,梦即使不是另一个世界来的,至少也将睡眠者带入了另一个世界。”[11]6但实际上,我们永远只能拥有一个“世界”,存在于一个“世界”之中——即世界性和世界现象本身。此在的世界性就是此在所面对的现实。与其说我们在梦中不知那些是不“现实”的,不如说我们在梦中不知那些是不具有“实在性”的。我们自始至终都必然地知道和熟悉什么是现实,只是并不在所有条件下都懂得如何将眼前的所有体验都识别为是不是具有“实在性”的。对“存在于世界之中”的必然领会就包含着我们对现实的源始熟知。通常,即清醒时,我们在实在性的意义上运用“现实”这个词(作为那个唯一的现实),这其实有两层含义:一,我们生存于当下的这个“世界”中;二,这个“世界”是具有实在性的。不难看出,前者是必然的,也是更为源始的,而后者则是有条件的,它涉及更为广泛和系统性的判断。
例如,当我们沉浸于一款游戏中时,我们同样会忘我地对游戏中的遭遇作出反应和筹划,在我们认真地为其中每一次躲避和伤害牵动心神时,并不会时刻提醒自己这些都是假的。相反,我们还时常在遭遇突发情况时反应不及,想与游戏中的角色作出同样的动作,并同时感到紧张和害怕。这些都是因为当时的我们是暂时作为游戏角色生存于他们的那个世界之中的,而这种体验的转换和持续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生存于一个世界之中”这一结构是源始且必然的(对应上一段现实的第一层含义),而“我们生存于一个具有实在性的世界之中”这一条件和认识则是派生的、可变的(对应第二层含义)。
所以,最后回到梦境的问题中,我们便能看出其中的关键之处。梦境之所以被人们认为是虚幻的,是因为它在我们清醒时被认作是非现实。而在清醒时,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一部分来自于源始且必然的在世结构,一部分来自于系统性的关于实在性的认知。在梦里,前者依然存在(并且只要我们存在它就必然会存在),而后者是缺失的。这造成的结果是我们依然如一地生存于现实,但不去(或者说没有去)“识别”这种现实。当我们怀疑一个事物是否存在于现实之中时,我们怀疑的是它的实在性,这意味着:我们首先识别并认定了一个“世界”的实在性,并参照它的标准,判断这个事物是否被包含于这个世界之中——这无疑误解了世界的源始含义。而在梦里,我们不去识别世界的实在性,因为对世界之实在性的需求既不存在于世界的源始含义之中,也不存在于此在的本真之存在方式之中。相反,我们对于实在性的理解和追求却都是基于它们而来。
在梦里,我们纯粹地体验着这种源始的存在状态,生存于世界和现实的本真意义之中。在其中,此在再次回到原点处醒来——就像我们从梦中醒来后恍然间知晓我们的所在一样,置身于梦中的我们也是在瞬间被抛入那样的境地。此在总是必然地于“某时某地”中“醒”来,这种原初意义上的觉醒意味着此在进入、领会并听从了它自身的存在,即存在(Sein)于此(Da)——此在(Dasein)。
每一次的梦境都是此在的重新觉醒,因而它总营造着一种源始状态的纯粹保留。我们不会在梦中发呆和无聊,不会让自己完全地消散在一件被观察之物中。我们只在梦中经历一件件事情,置身说不清的众多情景,面对一个又一个问题。在梦中常有设身处地的危险,也常有扑面而来的爱与悲伤,面对这些我们无处可避、无可后退——这构成了我们用以形容“现实”的最原本意义。而我们的审视及反思只有在我们对其拥有某种程度的抽身与远离时才可能发生,这恰是梦境所不具备的条件,它背离了梦境的特征。因此,只有在清醒时,我们才能如此思考,而当我们能如此思考时,我们就已经(或即将)醒来。我们对梦境的思考本质上要求着我们从梦境中抽身,而我们对梦境的怀疑要求着我们与梦境之本质的隔离——这就是我们无法在做梦时有所自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