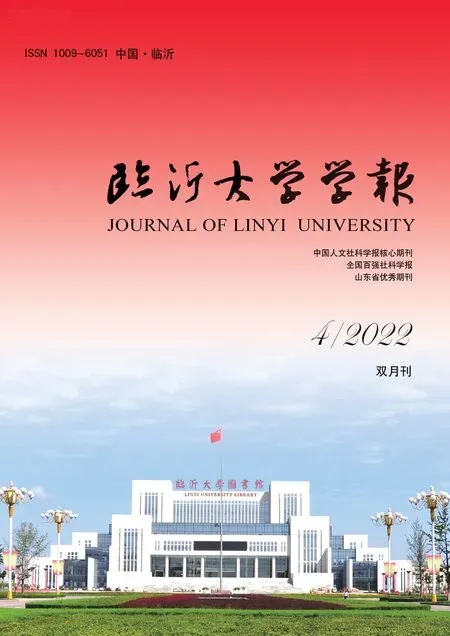北方文学家族与元代文学
2022-11-24张建伟
张建伟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元代处于古代社会家族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建立了统一政权,大量蒙古、色目人内迁,并以家族的形式定居内地,逐步汉化;另一方面,由于科举长期中断,汉族士人家族面临着如何延续发展的局面,他们或者积极参与新政权,或者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蒙古、色目家族的汉化是主流,也有汉族蒙古化倾向,比如真定史氏[1]。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北方各民族融入了华夏民族。
元代北方文学家族既具有古代文学家族共有的特点,又具有与其他朝代不同的特质,值得深入研究。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蒙古、色目家族,蒙古逊都思氏(月鲁不花、笃烈图)、康里部不忽木家族(不忽木、回回、巎巎)、北庭廉氏(廉惇、廉惠山海牙)、贯氏(贯云石、贯子素)、汪古马氏(马祖常、马世德)就是其中典型的汉化家族。除蒙古、色目家族外,汉人家族仍值得重视。蒙元时期的汉人包括汉族、契丹、女真等民族,耶律楚材家族、孛术鲁翀家族成为文坛不可或缺的力量。北方汉人世侯逐步实现了由军功到文化的转变,比如保定张柔家族(张弘范、张珪)与真定史天泽家族(史天泽、史樟)。北方文学家族逐步适应蒙古族政权,柳城姚氏(姚枢、姚燧)、猗氏陈氏(陈赓、陈庾)、东平王公渊家族(王构、王士熙、王士点)与济阴商氏(商挺、商琥)成为其中的代表。大都宋氏(宋本、宋褧)与汤阴许氏(许有壬、许有孚、许桢)借助元代科举而兴起。
目前对元代家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蒙古、色目家族,比如张沛之的《元代色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究》、赵一兵的《元代巩昌汪世显家族墓葬出土墓志校释五则》(《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2期)、马娟的《对元代色目人家族的考察——以乌伯都刺家族为例》(《回族研究》2003年第3期)等。对汉族家族的探讨更多在政治方面,比如吴海涛的《元代京兆贺氏与其他汉人官僚家族仕宦之比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符海朝的《元代汉人世侯群体研究》等。学术界对北方文学家族关注不够,研究较多的是文学家族的代表人物耶律楚材、郝经等人。杨镰先生在《西域诗人群体研究》中已关注到北庭廉氏与贯氏、雍古马氏、乃蛮答禄氏、康里不忽木等家族。他在《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中探讨了元代来自北庭而在江苏落地生根的双语文学家族。这些工作为进一步全面研究元代北方文学家族打下了基础。那么,北方文学家族有何特点与价值?与元代文学的关系如何?
一、北方文学家族与多族文人雅集
元代为蒙古族统治下的多民族王朝,蒙古人、色目人,以及列入汉人的契丹、女真等族出现了众多人物。清人王士禛在其《池北偶谈》(卷七)“元人”条说:“元名臣文士,如移刺(耶律)楚材,东丹王突欲孙也;廉希宪、贯云石,畏吾人也;赵世延、马祖常,雍古部人也;孛鲁术翀,女直人也;迺贤,葛逻禄人也;萨都剌,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鲁别族也;余阙,唐兀氏也;颜宗道,哈喇鲁氏也;瞻思,大食国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节义,文章,彬彬极盛,虽齐鲁吴越衣冠士胄,何以过之?”王士禛所举都为元代汉化的蒙古、色目,以及契丹、女真族人士,他们在政治、文学等方面成就斐然。即以文学而论,元代拥有历史上民族成分最为复杂的文人群体,除汉族外,还有蒙古、畏吾、克烈、塔塔儿、西夏、唐兀等数十个民族,甚至有来自拂林(大秦)、天竺(印度)的诗人,列入汉人的契丹、女真等族实际上也属北方少数民族。
各民族文人之间文化活动频繁,形式多样,包括赠答唱和、雅集聚会、同题集咏、书画欣赏与题跋、游赏赋诗等。北方文学家族成员为元代多族士人圈的主体,促进了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文学创作。
张之翰、王博文、霍肃、耶律希逸、李昂等人举行过雅集。张之翰《沁园春·序》记载,至元二十三年(1286)冬,他北归时金陵,告别行台幕诸公。《西岩集》(卷十二)记载词序曰:“适西溪、柳溪拜中丞,遵晦擢侍御,颐轩、恕斋授治书。越二十有五日,会饮颐轩寓第。时风雨间作,以助清兴。西溪草书风雨会饮之句,柳溪复出燕脂井阑之制,遵晦、恕斋道古今之事,颐轩歌乐府之章,某虽不才,亦尝浮钟举白,鼓噪其傍,一谈一笑,不觉竟醉。尝谓人生同僚为难,同僚相知为难,相知久敬为尤难。今欢会若此,可谓一台盛事,因作沁园春歌之。”词曰:
四海交亲,别离尽多,会合最难。见西溪老子,情怀乐易,柳溪公子,风度高闲。铁石心肠,风霜面目,更着中朝霍与韩。知音者,有颐轩待御,收拾清欢。 不才自顾何颜。也置在诸公酬酢间。似蒹葭倚依,琼林玉树,萧蒿隐映,春蕙秋兰。南北乌台,当时年少,双鬓而今半欲斑。明朝去,向德星多处,遥望钟山。
张之翰词序中提到的西溪为王博文,柳溪指契丹人耶律希逸,遵晦即韩遵晦,颐轩为李昂,恕斋为霍肃,词序曰:“尝谓人生同僚为难,同僚相知为难,相知久敬为尤难。”可见文人之间对诗酒聚会的珍惜。这次雅集的参加者耶律柳溪出自辽金元文学世家东丹王耶律氏,为耶律楚材家族成员,其他文人均为汉族,雅集的内容涵盖了宴饮、谈论、诗词、书法等,诸人各自展示了自己的才能与性情,已经与元末玉山雅集等极为相似了。
元代后期为李节妇题诗作文,是当时文坛的重要事件。据揭傒斯的《李节妇传》,李节妇姓冯,名淑安,字静君,大名(今属河北)人。山东亷访使冯时之孙,湖州录事冯汝弼之女,山阴令东平李如忠之继室。李如忠去世时继室冯氏才二十二岁,她抚养教育二子成人,“迁二丧反丧汶上”。冯氏成为当时闻名的节妇,礼部尚书孛术鲁翀与中书参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马祖常、翰林学士吴澄、集贤学士袁桷、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国子司业李端、太常博士柳贯等人争为文章颂扬李节妇。此次同题为文的参与者吴澄、袁桷、虞集、柳贯为南方文学家族重要成员,孛术鲁翀、王士熙、马祖常分属北方不同民族的文学家族。
北方民族组织参与多民族文学活动具有代表性的是高昌廉氏组织的文人雅集。蒙古蒙哥汗四年到五年间(1254-1255),廉希宪在陕西组织了廉相泉园聚会,参加的文人有姚枢、许衡、杨奂、商挺、来献臣、郭镐、陈邃、李庭、邳大用、张君美等,拉开了元代多族雅集文人的序幕。廉氏主持的大都(今北京)廉园唱和影响更大,在廉希宪、廉右丞、廉野云等人的组织下,廉园的诗歌沙龙荟萃了南北各族文人,包括袁桷、陈孚、王恽、姚燧、张养浩、贡奎、赵孟頫、卢挚、许有壬、贯云石等人。其中贯云石为高昌贯氏的代表人物,姚燧、许有壬等人为北方文学家族的重要成员,袁桷、贡奎、赵孟頫则属南方文学家族。廉园雅集荟萃了南北各族文人,成为大都的文坛沙龙与享誉天下的盛会。元代后期,廉希宪侄儿廉惠山海牙与贡师泰、答禄与权等人的玄沙香岩寺雅集汇集了乃蛮人答禄与权、畏吾人廉惠山海牙以及汉族人贡师泰等人,甚至还包括僧人藏石师,是一场典型的多民族的盛会。廉惠山海牙等人举行雅集之时,正值四方动乱,他们在诗酒欢会的时候,并未忘记时政艰难,但是,时政并非他们能左右,因此只能“遣其羁旅怫郁之怀”,“更深层面上体现的是文人追求独立品格”[2]。
北方民族参与的雅集活动范围极为广泛,遍及南方和北方,涵盖了京师与地方。元初南北刚刚统一之时,还存在隔阂,据董复礼的《宋蛮传》,河间(今属河北)人宋某从伯颜平宋而留江南,他操朔音,南方人莫能辨,称他为宋蛮。张之翰在《书吴帝弼饯行诗册后》中说:“江南士人囊尝谓淮以北便不识字,间有一诗一文自中州来者,又多为之雌黄,盖南北分裂,耳目褊狭故也。”[3]这一送别诗册肩负着展示北方诗人创作水平的使命,用以回应南方文人轻视北方文人的偏见。南北间的交流还是不可阻挡地开始了,而且越来越普遍,北方文学家族成员也加入到了入南的洪流中,白朴是较早南下的北方文人,姚燧、宋本、宋褧兄弟、孛术鲁翀等人也有纵贯南北的经历,无论是赠答唱和,还是同题集咏,这些诗歌活动都促进了南北文学的交流融合,体现了元代文学的特点。
元代北方文学家族包括了女真、契丹、蒙古、维吾尔等北方各民族,他们对元代文学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杨义先生指出:“北方文学对整个中国文学的作用和功能,起码可以概括成四个方面:1.它拓展了和重构了中国文学的总体结构;2.它丰富和改善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3.它改变了和引导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4.它参与了和营造了中国文学的时代风气。”[4]87经过南北多民族的共同努力,历经长时间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博大精深、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4]82。
元代的多民族士人雅集不分地域、种族,甚至身份地位,完全是尽情表现自我、才情与个性充分表达的舞台,体现了文人的独立品格。[5]文人雅集源远流长,但元代之前的雅集多为官员之间的诗词唱和,元代是个关键的转折期,北方文学家族成员成为雅集的重要参与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发展至清代,文人雅集更为兴盛,尤其是江南地区,文化家族成为主体,但其规模主要局限于当地府县,民族也仅限于汉族,逐步成为地方性的诗歌盛会。[6]
二、北方文学家族与域外交流
元代地域广阔,开放性强,与域外的交流极为广泛。北方文学家族积极参与其中,并在创作中有所体现。元代不仅域内民族众多,与域外的交流也极为频繁。通过使者往来,北方文学家族与高丽、安南等国的文人用汉语写诗,进行赠答唱和。
耶律楚材家族与高丽使臣有过多次文化交流。早在蒙古蒙哥汗时期,耶律楚材就参与了蒙元对高丽关系的决策,他促使蒙古由征伐变为和平相处,即保持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楚材曾与高丽出使蒙古的使者有过交往,他在蒙古汗廷见到的高丽使者为池义深,作《和高丽使三首》,其一曰:“神武有威元不杀,宽仁常愧数兴戎。仁绥武震诚无敌,重译来王四海同。”神武,指的是太祖成吉思汗。耶律楚材此诗传递给高丽国王一个信息,蒙古已经改变了对高丽的战争政策,“武震”已经被“仁绥”所代替,要求高丽称藩内附。到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蒙古与高丽终于成为藩属关系。高丽李奎报致耶律楚材的两封书信,反映了耶律楚材倡导的仁政绥靖政策在其间所起的作用。[7]
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同样与高丽使臣有过诗歌唱和,他作有《春日席上次高丽国使新安公诗韵二首》。耶律铸还写过《早春宴上次高丽入国使诗韵》,诗曰:“白玉堂前一树梅,为谁零落为谁开。人生颜色不长好,且尽生前有限杯。”[8]卷五劝使臣珍惜大好时光,多饮几杯。从诗题可知,这些诗都是高丽使臣先作,耶律铸次其韵而作。
除了耶律楚材家族,北方文学家族其他成员也与高丽君臣有过交游。据《元史》(卷一七四)《姚燧传》,姚燧曾赠高丽沈阳王父子诗文。高丽人李穀(1298-1351),著有《稼亭集》二十一卷,末卷附元人欧阳玄、谢端、余阙、黄溍、宋本、宋褧、王士点、苏天爵、贡师泰等二十多人的诗文。[9]这些参与域外文化交流的人多为北方文学家族成员,他们与域外文士有诗歌赠答,进行文学切磋。宋褧的《题稼亭》曰:“敦本崇礼教,有年可立致。负耒非无心,乘桴或有志。”[10]321称赞李穀崇尚礼教,其以归隐耕种标榜自己隐含深意。东平王士点在题诗中说李穀“束发读经史,入仕习华言”[11]78,李穀的学习与仕宦经历与元朝文士极为类似。
不只是高丽王室与士人,来元朝访问交流的还有高丽僧人。高丽僧式上人,号无外,他在元朝居留期间,结识了不少文人。至正元年(1341),无外云游到江浙时,与黄溍、张雨等人相会,黄溍作七律一首。[12]无外到京城后,以黄溍诗卷出示吴师道,吴师道同样次韵一首,[13]陈旅也有《次韵黄晋卿与张伯雨道士高丽式上人会于杭州开元宫》。有好事者绘为《文会图》,宋褧题诗,次黄溍诗韵,诗曰:“文章释老谁争雄,昔人三语将无同。巳公茅屋见新句,匡庐莲社追随风。名胜绝怜留翰墨,笑谈莫谓变虚空。鸡林到日传相诧,杖锦归来未是穷。”[14]宋褧认为,由于有共同爱好的文艺,不论是僧人还是道士,都没有什么区别,大家看重的是谈论与诗文书画,无外的这次经历定会在他归国后成为一段佳话而流传。这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宗教信仰的文人之间的交流,他们之间的纽带就是中国博大而包容性强的文化。
北方文学家族成员还与安南国人员交往频繁。宋本、宋褧兄弟都曾馆伴安南使者,汤阴许有壬曾作《琳宫词次安南王韵十首》。整个元代,安南与元朝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出使安南成为当时政坛的大事,不担使者撰写了大量安南纪行诗[15],送行的文士也有很多诗作[16]。至元十八年(1281),柴椿出使安南时,东平王构有《送柴椿使安南》。藁城董文用曾作《送李两山二绝》《送萧郎中方崖奉使安南》,姚燧有《送梁贡父尚书使安南诗并引》《满江红·送李景山使交趾》,这些安南送行诗词普遍坚持元朝官方立场,预祝使者完成外交使命,令安南称臣纳贡。
由于元代和域外的接触与交流极为广泛而频繁,元代歌咏域外风物的诗篇并不少见。来自东南亚的大象进入诗人的视野。宋褧《燕石集》卷九有《过海子观浴象》,诗曰:“四蹄如柱鼻垂云,踏碎春泥乱水纹。鸂鷘鵁鶄好风景,一时惊散不成群。”描绘了中原少见的大象,体态庞大的大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魏初的《青崖集》(卷一)也有《观象诗》,描写更为细致,他说:“中国传闻未尝见,一日争睹轰霹雳。巨鼻引地六七尺,左卷右舒为口役。耳项垂垂倍数牛,皮毛苍苍艾豭黑。目竖青荧镜有光,背阔隐嶙山之脊。”人们争相观赏这一庞然大物,称大象为“轰霹雳”,大象的巨鼻、大耳和阔背引发人们的关注。陈高的《不系舟渔集》(卷九)有《题献狻猊图》,诗人眼中的这一奇兽为“西域狻猊百兽豪,照人闪闪紫金毛。”记述了来自西域的狻猊(狮子)给世人的穿越历史时空的印象。冯承钧先生认为:“中国古昔或有狮子,然绝迹者已有千百余年,断可言也。……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朝廷所见者,如确是狮子,则必是外国国王入贡之物,非土产也。”[17]
至正二年(1342),佛朗国贡天马,成为诗坛歌咏的盛事。叶懋、宋无、陆仁、秦约、杨维桢等人,都曾写过《天马歌》。北方文学家族成员也参与了歌咏天马的诗歌活动,许有壬作有《应制天马歌》,诗曰:
臣闻圣元水德在朔方,物产雄伟马最良。川原饮齕几万万,不以数计以谷量。承平云布十二闲,华山百草春风香。又闻有骏在西极,权奇俶傥钟乾刚。茂陵千金不能致,直以兵戈劳广利。当时纪述虽有歌,侈心一启何由制。吾皇慎德迈前古,不宝远物物自至。佛郎国在月窟西,八尺真龙入维絷。七逾大海四阅年,滦京今日才朝天。不烦翦拂光夺目,正色呈瑞符吾玄。凤鬐龙臆渴乌首,四蹄玉后其前。九重喜见远人格,一时便勅良工传。玉鞍锦鞯黄金勒,瞬息殊恩备华饰。天成异质难自藏,志在君知不在物。方今天下有道时,绝尘讵敢称其力。臣才罢驽亦自知,共服安舆无覂轶。
诗人认为,汉武帝为求良马而劳师远征,不及元顺帝时天马自来。由遥远的佛郎国来元朝的上京,历经四年,七次过大海才到达。天马“鳯鬐龙臆渴乌首,四蹄玉后其前”,一派英姿飒爽。元朝真正实现了儒家重视的远人来服的政治理想。《天马歌》反映了元朝幅员广阔,与海外交流频仍的特点,诗人借助进贡天马之事,歌咏元朝的盛世品格。马祖常的《石田文集》(卷四)《骏马图》也写到天马,可见当时有不少以天马为题材的绘画。天马歌是元代同题集咏的主题之一。[18]
除了天马,来自西域的葡萄酒也引起了许有壬的注意。他的《谢贺右丞寄蒲萄酒》说:“几年西域蓄清醇,万里鸱夷贡紫宸。仙露甘分红玉液,天风香透白衣尘。”称赞西域葡萄酒的甘甜醇厚。《和明初蒲萄酒韵》将葡萄酒称之为“殊方尤物”[19]卷二十。
骆驼鸡、花驴、天马……,这些内容是元代诗歌中特有的。杨镰先生在《元诗叙事纪实特征研究》中指出,这些珍禽异兽再造了元人的知识结构,开阔了元人的视野。
三、北方文学家族与西域诗及上京纪行诗
元代有三类地域性突出的诗歌,即安南诗、西域诗与上京纪行诗。北方文学家族除了参与安南诗的创作,还是西域诗与上京纪行诗的倡导者和写作者。
荣新江先生说:“中国古代广义的‘西域’是指敦煌西北玉门关以西的广阔地域,而狭义的‘西域’则指今新疆南疆地区,也包括东疆的吐鲁番和哈密。”[20]和唐宋等其他朝代不同,在元人心目中,西域早就不是秘境。耶律楚材、耶律铸、丘处机、尹志平等人都有自成卷帙的西域诗,“无论诗歌史或文化史,这都是前所未见的奇迹。《西域河中十咏》等篇什是纪实的经典。经耶律楚材倡导,中亚出现了华夏诗文的社区,河中府——撒马尔罕成为华夏诗坛的西极。”[21]贾秀云在《耶律楚材与西域的第一个汉语诗歌沙龙》中认为,契丹族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既是西域诗的主要创作者,又是西域诗歌沙龙的组织者,起到了主导者的作用。这些都是对广义的西域的描绘,涉及到域外。
西域和上京纪行诗包括了中国的北部边疆,耶律铸的诗歌中多次写到西域和漠北的气候、物产和风土人情。比如北方特有的醍醐、驼蹏羹、驼鹿唇等八珍美味。[8]卷六耶律铸对漠北的和林多有描绘,《和林春日书事》:“冻折池塘百草芽,断鸿低雪怨凝笳。晴窗一曲春风咏,开彻满山桃杏花。”写出了和林初春的景色,尽管天气尚寒,但是满山已经开遍桃杏花。《和林雨大雹有如鸡卵者》叙述和林的冰雹竟然大如鸡卵。《戊申己酉北中大风》曰:“冲风回白日,飞砾洒青天。富贵城西畔,珍珠河北边。阳冰元不冶,阴火更潜然。直彻龙荒外,萧条是野烟。”“冲风”“飞砾”“野烟”,这些都是漠北特有的景象。
耶律铸很多诗篇对西域的描绘是结合战争来写的,《雪岭》《阳关》《阴河》等诗,简洁地叙述了蒙古军队的一系列胜仗,《雪岭》曰:“抑扬霆电决雌雄,霆激狂锋电扫空。如席片飞何处雪,扑林声振海天风。”[8]卷五
北方文学家族成员参与到上京纪行诗的写作中,这是最能体现元代文学特点的诗歌题材之一。上京即上都,元世祖忽必烈在此营建城郭,名为上都。每年四月到九月,元朝皇帝都要到此巡幸,朝臣扈从。以塞上草原开平地区建立的上京为歌咏内容,是元诗乃至整个中国诗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22]较早写作上京纪行诗的为耶律铸和张弘范,宋本、马祖常、王士熙、许有壬等人也都写过上京纪行诗。
金莲川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和河北沽源县滦河上源闪电河地区,为辽金元三代帝王的避暑胜地,元上都就建于此地。耶律铸多次描绘过该地的风景,比如《金莲川》:“金莲川上水云间,营卫清沈探骑闲。镇西虎旅临青海,追北龙骧过黑山。”诗题下注曰:“驾还幸所也。”[8]卷二写出了忽必烈带领蒙古军队行军迅速、气势逼人。再如《金莲花甸》:“金莲花甸涌金河,流绕金沙漾锦波。何意盛时游宴地,抗戈来俯视龙涡。”自注:“和林西百余里,有金莲花甸。金河界其中,东汇为龙涡。阴崖千尺,松石骞叠,俯拥龙涡,环绕平野,是仆平时往来渔猎游息之地也。”[8]卷五因为长期居留塞外,对这里的景色充满感情,这与中原乃至江南人士的感受不大相同。
宋本有《上京杂诗》七绝组诗,今存十七首,其三曰:“穹庐画毡绕周遭,五月燕语天窗高。草尽泉枯营帐去,来年何处定新巢。”写出了草原的高远广阔和游牧部族迁徙不定的生活习俗。其五曰:“平原细草绿迢迢,十脚穹庐二丈高。羊角风来忽掀去,干霄直上似盘雕。”渲染了草原风势之猛。“种出碛中新粟卖,晨炊顿顿饭连沙”(其四),表明此地农业之发展,然而,在猛烈的风沙之下,每顿饭里都和着沙子。“鹰房晚奏驾鹅过,清晓銮舆出禁廷。三百海青千骑马,一时随扈向凉陉。”(其十六)写出了元朝皇帝出行打猎的盛大场面,体现出北方民族的特色。“金脊殿洒马乳酒,铁幡竿送羊头神”(其十七)[23]97-98,充满了蒙古族的习俗风貌。
许有壬的上京纪行诗更为丰富,他曾作《和闲闲宗师至上京韵二首》,其一曰:“建瓴天下奠皇都,圣祖神功旷世无。滦水清浮金阙动,蹛林晴射锦云铺。”其二曰:“夷夏襟喉控两都,两都形势汉唐无。……香殿昼闲云气合,琼楼天迥月轮孤。”[19]卷十六两首诗都是歌颂蒙元国力的强盛,赞颂了上京特殊的地势与恢宏的宫殿。许有壬的另一组七律组诗对上京有更全面的描绘。《和谢敬德学士入关至上都杂诗十二首》其四曰:“逐兔弓良不用蹄,种荞坡峻马能犁。土山无树远如近,沙路有风髙又低。”该诗写上京的土山没有树木生长,沙路高低不平,其农业别具特点,坡地用马犁田。其九曰:“雁落长空迹篆沙,鸣嚆惊起一行斜。小车细马醉时路,丰草甘泉到处家。已解皮囊倾马湩,更搘银铫试龙茶。玉脂响泣炰羊熟,鼻观风香野韭花。”描绘遍地的草野与水泉,长空的大雁排开飞行,如同沙土上写的篆字。上京的景色与中原不同,饮食也有差异,用皮囊装的马乳酒,带毛烧烤的羊肉,给许有壬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上京的地理环境与生活习俗,许有壬还描写了上京的宫廷宴会。该诗其五:“庖羞水陆八珍聚,琛贡梯航万国通。”写到上京的宴会食物丰盛,都是各国各地进贡的珍馐。其八:“圣德如天万汇新,远柔穷漠会宗亲。锦鞲掣紲苍鹰健,玉辂鸣銮白象驯。”[19]卷十八铺陈了元朝诸王来会的盛大场景,其中还有进贡的供打猎用的苍鹰和供乘坐的白象。
安南诗、西域诗和上京纪行诗是元代最有特色的三类纪行诗,属于文学地理学中的文人流动引发的创作。这三个地区给元人带来了新奇的体验,无论是气候、山水,还是物产、风俗,都迥异于中原与江南。北方文学家族创作的西域纪行诗和上京纪行诗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这种由于文人流动引发的诗歌创作,极大地丰富了元代文学。
四、北方文学家族与元曲
北方文学家族不仅写作传统诗词,更对元代的新兴文体元曲卓有贡献。
北方文学家族不少是由金代延续发展而来,例如猗氏陈氏、陵川郝氏、隩州白氏、稷山段氏、济阴商氏、东平王公渊家族,他们成为金元文学之间的纽带。在金亡蒙兴之际,延续了文学的发展,使得元代文学拥有一个较高的起点。除了创作传统文学样式诗文词,北方文学家族还是新兴文体——元曲的最早创作者。虞集认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其所谓杂剧者,虽曰本于梨园之戏,中间多以古史编成,包含讽谏,无中生有,有深意焉。是亦不失为美刺之一端也。”[24]作为诗坛领袖,虞集对元代盛行的散曲与杂剧赞赏有加,与汉代的文章、唐代的律诗、宋代的理学相提并论,可见元曲对于元代文学的重要性。
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说,金代后期作家的创作已经有了一定的俗化倾向,他们推崇自然与平易的风格,采用俗语入诗文,“认识到了曲的价值甚至加入到俗文学的写作队伍中去”[25]。散曲这种文学体裁与金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有着很大的关系,明人王世贞在《曲藻序》中说:“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26]王世贞从音乐的角度说明散曲的产生是为了适应金元少数民族的乐曲。李昌集先生根据徐渭、王骥德的论述,指出“北曲在音乐体系上是以辽金时北方流行的音乐为基础的”[27]。因此,无论是重视俗文学的观念,还是散曲的写作,都是金元时期北方文化的产物。
根据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全元戏曲》做曲家地理分布统计,前五名之中只有浙江为南方省份,其余的北京、山西、河北、山东都属于北方,《全元散曲》的曲家统计也呈现出类似的局面,说明元曲具有鲜明的北方特色。浙江占据一席之地是因为元代后期元曲南移。[28]
早期的杂剧和散曲作家都是北方人,北方文学家族成员在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济阴商氏(商挺与其叔父商衟)、真定史氏(史天泽、史樟父子)、渔阳鲜于氏(鲜于枢、鲜于必仁父子)、大都费氏(费君祥、费唐臣父子)、洛阳姚氏(姚燧与其侄儿姚守中),都是长于元曲创作的家族,元好问、刘秉忠、魏初、白朴、张弘范等人也属北方文学家族成员。色目人不忽木、贯云石等人带着自己特有的民族特色加入了散曲的创作队伍。总之,北方文学家族促进了金元各体文学的发展。
元代前期的杂剧中心大都、东平、真定、平阳都在北方,这几个杂剧圈聚集了大量曲家,创作繁荣,又各具特色。元代杂剧创作体现出一定的地域文化色彩,东平(今山东泰安)以水浒戏著称,神仙道化剧的作者主要集中于燕齐之地。
五、结语:元代北方文学家族的特点和价值
作为唐宋到明清家族发展史上的转折期,元代家族具有重要的意义,北方文学家族为元代家族的代表。从家族史的视域下看,元代家族的发展比北宋有所退步。张兴武的《两宋望族与文学》第一章《唐宋“望族”之转型》指出,宋代望族往往数世之后便告萧条。“正因为缺少世袭式的制度保护,宋代文学家族乃至整个宋代家族又常表现出起落迅速、盛衰无常的特点。”[29]相较唐宋而言,元代贵族式的家族极为兴盛。除了蒙古博尔忽、木华黎、博尔术和赤老温的四大家族[30],其他色目、汉人勋贵之家同样历代簪缨,在仕宦方面享有特权。比如藁城董氏,家族六代官位崇高、仕宦持久。文学家族中,汉人世侯真定史氏与保定张氏在仕宦方面同样享有特权。[31]其他家族的仕进道路就比较曲折,比如大都宋本沉抑下僚,升迁困难,后来考中进士才得以入朝为官。
因为与元代政治关系密切,北方文学家族的命运与元朝的命运休戚相关。他们中的很多家族是伴随着蒙元的勃兴而崛起的,如北庭廉氏、贯氏、真定史氏、姚枢家族等,有些家族也随着元朝的灭亡而衰落,甚至覆灭,比如东平王公渊家族、洛阳姚氏、耶律楚材、孛术鲁翀等家族。除了政治方面,北方文学家族对元代的文化事业也有贡献,他们参与修撰了很多典籍,包括法规、文化典籍和史书。北方文学家族对元代儒学的传播也起了很大作用。
从文学家族的数量和成就来看,北方远远不及南方[32],这种现象是延续着宋代的趋势,元代南北文学家族的差异反映出这一趋势在不断加强。然而,从民族融合方面看,元代北方文学家族具有特殊的价值,新兴的蒙古、色目家族,以其原始性和开放性给濒于僵化的中原传统文化带来了新的活力[33],为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新鲜血液,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学。具体到文学,蒙古、色目文学家族,作为文坛的新面孔,为元代文坛带来了活力,丰富了元代文坛的组成,成为中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北方文学家族在历史上起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有些家族为宋金旧族的延续与发展,更多的是新兴家族,尤其是蒙古、色目家族。这些蒙古、色目各族,以及列入汉人的契丹、女真等民族,其家族在长期与汉族混居与通婚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中华民族。蒙古人聂镛、高昌三大家族廉氏、贯氏、偰氏以及鲁明善家族[34],雍古部赵世延、马祖常、回回丁鹤年、茀林金元素等人[35],因为起了汉姓,其后裔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无法区分。明朝初年,由于蒙古、色目人受忌讳,很多家族改姓,女真族孛术鲁翀的后裔改姓鲁,其家族一直延续到清代。马祖常后裔一直生活在潢川县回回营,其二十八代孙马启荷还有新编的《家谱》。[36]虽然大多数蒙古、色目、契丹、女真等民族的后裔不甚明了,但是他们融入中华民族,一起创造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由于地域的广博、政治与社会的特殊、作家身份的复杂等原因,元代文学呈现出不同于唐宋与明清的特点。北方文学家族与元之前的文学家族、与南方文学家族均有不同,通过探讨北方文学家族的特点与价值,有利于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元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