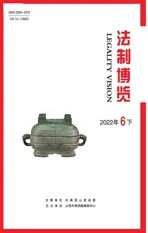以实质正义为中心的行政赔偿案件举证责任的转移与再分配
2022-11-24周欣
周 欣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上海 201100
一、问题聚焦:对举证责任转移的忽略造成同案不同判
行政赔偿是基于行政侵权行为而产生的行政法意义上的侵权之债,以“谁主张谁举证”为基本规则,包含的基本内容为原告对被告主体资格、损害事实的存在、损害数额的计算以及被告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被告对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承担举证责任。同时,在基本规则之外,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以及法院推定的情形。
目前法律、司法解释中对于行政赔偿举证责任的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形式正义,但是规定得过于原则且为初始分配,未考虑举证责任的转移,无法满足行政赔偿案件的复杂性要求,机械适用易造成个案不公,有违实质正义的要求。例如,若因行政机关未履行公示义务,致使原告未能证明行政赔偿主体而直接驳回起诉或驳回原告诉请,造成原告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同时,若以被告未履行公示催告义务,未进行财产移交、公证等为由,将原告提出的所有赔偿请求的举证责任全部转嫁给被告,亦容易造成原告滥用请求权。为平衡这种现象,审判实践中随着待证事实的深入,部分法官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对案件举证责任重新分配。这种再次分配举证责任从实质上维护了公平公正,是一种有力的探索,但同时因这些举证责任的再次分配缺乏统一标准,依赖于法官个人的经验等,易导致同案判决结果迥异的现象。
二、实证考察:转移规则缺失造成审判实践面临多重困境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已决案件中,以原告举证责任为观察角度,因举证责任转移规则缺失造成原告举证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赔偿主体锁定困难。赔偿主体的确定由原告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也会因被告原因造成原告赔偿主体难以确定。例如,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未出具法律文书,也未向当事人进行表明身份;行政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中有多个单位盖章;行政行为的实施系连续过程,依次涉及多个行政机关等情况,若由原告承担相应举证不利带来的法律后果,会使原告被侵害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从而蚕食政府公信力,不利于法治政府建设。
(二)损害结果证明困难。基于行政行为的强制效力,行政强制法规定了保护公民权益的诸多程序规定,例如公示、催告、制作财产清单、公证等,虽然相关的程序规范已经较为完备,但执法中违反法定程序的现象并不少见[1]。特别是在财产灭失的情况下,当赔偿请求人系生活场所或者小规模经营场所时,其通常主张的财产损失名目繁多且数额难以清晰记录;而当赔偿请求人当主张赔偿的物品过于贵重,例如古董名画等物品,财产价值较大且稀有,原告的举证责任也常陷入困境。虽然在最高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汇总规定了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完全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并不多见。尤其是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包含有贵重物品的情况,若贸然依据举证责任倒置来进行举证不利后果分配,将会对原被告的权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难以得到法院支持。
(三)损害数额举证困难。损害数额是赔偿请求人诉请的核心组成部分,当事人对于数额举证的常用手段是市场价格比对以及申请评估鉴定。但是,这两种举证手段在司法实践中都面临着局限性:一是对于灭失的物品,物品不复存在,价值鉴定条件不成熟,当事人又未保存购买发票,原告对于其价值的主张只能通过市场价格比对方式,但这种举证方式会被行政机关否认举证的关联性;二是对于尚存但有一定程度损坏的财物,要求当事人对财产的毁坏损失数额进行举证,即便可以通过鉴定方式估算出物品的残存价值或者可以通过支付维修费用使财物恢复使用,但由于物品在行政机关执法时的原始状态无法确定,且是否存在赔偿请求人的过错产生扩大损失的情况,也使得原告的举证陷入僵局。
(四)因果关系认定困难。因果关系的认定,是相对抽象的活动,应归属于法官自由心证领域。因果关系认定的复杂性,在民事侵权领域,尤其是环境污染、动物致害、医患纠纷等特殊侵权案件,规定了诸多因果关系举证倒置情形。但纵观行政赔偿相关法条,并未对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做出全面的规定,仅对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因果关系的证明,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应当由赔偿义务机关提供证据证明。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相对人常被排除在执法现场之外,或者处于被支配的情形下,对于因果关系的证明只能从外围予以证明,故此,在行政赔偿领域,对于因果关系的证明,难以独立存在,常蕴含于违法行为和损害结果的证明之中,依照法官的内心确信对于因果关系作出判断,存在着诸多因果关系难以认定的情形。
三、追根溯源:举证责任分配因素的再考量
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若法律适用存在异议或者适用结果显失公平,需考量制度背后蕴含的价值理念。原告证明的过程也是法官心证的过程,就其内容和范围而言是通过逻辑推理来评价证据的价值和对待证事实是否成立进行判断认定[2]。就举证责任的分配理论来看,影响举证责任分配的因素主要有当事人的证明标准的确定、举证能力的强弱、距离证据的远近(举证便利原则)、公平正义的需求等。
(一)证明标准的确定。证明标准是指举证一方对于待证事实进行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证明标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承担举证责任一方胜诉的可能性的大小[3]。证明标准包含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双重属性,客观性要求当事人对于证据进行充分举证,主观性要求法官结合经验进行判断和认定是否能够达到证明目的。证明标准的主观属性,决定了对其规则化表述。行政赔偿案件特殊性,决定了其证明标准认定存在着价值取向多元化、认定标准动态化、审查对象的特殊性等特点,因而要求行政法官在分配证明责任、订立证明标准时,树立动态变化意识。目前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上述标准是针对被告承担证明责任而言。民事证据采用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对于行政赔偿案件的原告举证则具有借鉴意义[3]。基于行政机关占有的绝对优势,对于原告证明标准应更为宽松甚至于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标准。
(二)举证能力的强弱。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但举证能力存在着天然差别。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在举证能力方面享有明显优势。在举证责任再次分配过程中,对于当事人收集证据能力的强弱相比于初次分配应有更为严肃的考量。当通过初次举证责任的分配,未达到查清待证事实的目的,应合理调整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弥补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弱势的举证地位,实现双方当事人在能够“武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诉讼。
(三)距离证据的远近(举证便利原则)。所谓举证便利即证据处于一方控制或者距离一方当事人较近时,应当由其承担相关证据的举证责任原则,也称作证据偏在。当证据处于一方当事人掌控或者一方当事人获取证据具有明显优势时,若一律按照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作出判决,不利于待证事实真相的查明,将造成个案不公。在审理行政赔偿案件中,证据偏在的情况可能更加突出,因此当事人之间分配证明责任时,应该综合考虑距离证据的远近等举证能力等因素,决定证明责任的归属。
(四)正义的需求。初始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由法律司法解释框定,系静态过程,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安定稳定性。但是,从个案观察,审理结果可能有违公平正义。法官在面对显失公平的个案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时,选择适用价值衡量等原则来进行平衡无可厚非。尤其在行政赔偿案件的因果关系等认定方面,当事人在举证证明其他赔偿审理要素后,再对因果关系举证已经浑身乏力,法官亦可通过正义需求对举证责任分配做出适当调整。
四、锦囊拆解:构建举证责任动态分配制度
举证责任的分配背后蕴藏着人权、秩序、公正、效率等一系列诉讼价值观,渗透于证明标准、举证能力和距离证据远近等因素的判断过程中,影响着导致举证责任分配的变化。在司法实践中,为保证法官能够形成内心确信,需秉持多元化价值理念对举证责任作出再次分配,形成动态的举证过程,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转变。在举证责任动态分配过程中,结合行政赔偿案件审理逻辑,笔者尝试提出如下建议:
(一)构建举证责任分配的分类排除规则。行政赔偿案件的诉讼请求主要由赔偿范围及赔偿数额组成。国家赔偿范围限定于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损失、直接利益损失及人身损害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在诸多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诉请中的部分主张可以直接排除于审理焦点之外,无需当事人进行举证,例如,因财产损失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当事人为维护权益引发的误工费、租金损失、交通费、律师费用请求以及基于不属于原告合法财产的请求。上述损失诉请,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将其剔除于审理重点之外,无需对相关待证事实进行举证责任的分配和再分配。
(二)扩充证明手段,压缩真伪不明空间。当事人穷尽举证手段仍不能查清的待证事实,即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法官通常通过调取或者鉴定、现场勘查等方式或者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方式,查明待证事实或者通过举证责任分配,推定待证事实真伪,分配法律后果,发挥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作用。第一种选择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能够压缩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空间,但有违背人民法院作为诉讼的居中裁判者地位;第二种选择更符合当事人对诉的利益的支配原则,因为当事人是诉讼利益的追求者,有义务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并承担相应的举证不能风险,但是这种选择可能不利于客观事实的查明,使当事人的损失得不到赔偿,造成个案不公。笔者更主张从实质正义出发,通过扩充证明方式,压缩真伪不明状态存在,尽力做到案件事实清楚明确,减少举证不能责任分配。
(三)坚持以成文规则为主,转移分配为辅。行政机关履职过程中侵害当事人权益的必须进行赔偿。法律司法解释对于行政赔偿案件的初始分配系成文法的规定,是对举证责任的基本安排,应充分尊重。而在涉及原告举证困境方面,应当采用多元化动态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需要注意的是,举证责任再次分配实际上是法官基于对个案实质正义的一种价值追求,属于法官造法范畴[4],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只有在适用成文法分配规则得出显失公平结论的情况下,才可重新分配举证责任。
(四)考量举证分配因素,调节举证分配。就行政赔偿案件而言,在举证分配过程中,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较重,应当充分考量举证责任分配影响因素,伴随待证事实的审查深入予以适当调节。在行政主体方面,对于原告举证责任的证明标准应当降低,当行政机关未履行公示义务时,只需要原告提供可能由被告实施的初步依据即可认定其完成了对赔偿主体的举证责任;在损害事实方面,对于损害事实方面的举证不能,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既不能单纯适用原告举证初始规则,亦不能采用一刀切的被告举证责任倒置,否则均有违实质正义要求,应结合物品损失价值及其在生活、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合理程度综合评判;在损害数额方面,法官需要更多借助于鉴定手段或者由法官进行酌情考量,对于损坏或者灭失的物品,原告能够证明物品价值的,结合物品折旧率等情况予以直接认定;对于不能认定价值的,由法官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在因果关系认定方面,只要不存在违背常理的情形,原告只需举证证明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初步联系或相当因果关系即可,更多的由被告来承担因果关系阻断的证明责任,才能更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