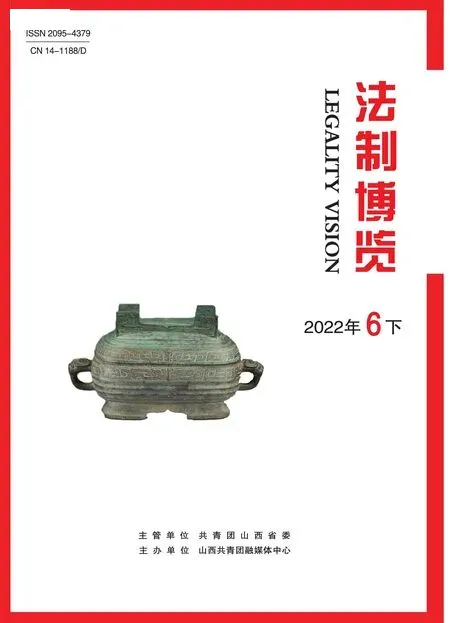《民法典》二元效力瑕疵体系下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之浅析
2022-11-24魏琳
魏 琳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上海 201612
《民法典》的编纂与出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关于婚姻制度所建立的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二元效力瑕疵体系,是在原《婚姻法》立法基础上的承继与完善,充分体现了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一、婚姻二元效力瑕疵体系
法律行为是民法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一般被定义为当事人旨在根据意思表示的内容获得相应法律效果的行为。[1]我国《民法典》在立法精神上确立了法律行为贯彻始终的体系,婚姻家庭编作为《民法典》体系的一部分,其自然也应适用《民法典》关于法律行为的一般性规定。
(一)法定形式是婚姻缔结的必要条件
法律行为分为财产法律行为和身份法律行为,婚姻缔结行为属于其中的身份法律行为,其是以最终在身份上产生一定法律效果为目的,所形成的是亲属的身份关系。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史尚宽认为:亲属法之亲属身份行为,即于亲属的身份关系发生效力之法律行为。我国学者张作华在其著述中认为:身份行为指自然人旨在创设或消解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行为。与债权行为一样,身份行为仍然要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同样是追求司法效果的表意行为。[2]婚姻缔结需要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即结婚应当遵从私法自治原则。因此,自治是婚姻缔结的法律基础,但是婚姻缔结又并非由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完全自主决定,因考虑到婚姻的道德伦理性、社会公益性等,法律又会做出强制性的干涉,因此婚姻缔结行为区别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一般民事行为是合同的双方在形成意思表示一致时,即产生了约束双方的法律效力,没有法定形式的要求,而以婚姻缔结为代表的身份法律行为即使做出了意思表示,也并不产生直接法律效果,还需要完成必要的法定形式,才发生法律效力。如果欠缺法定形式则不发生法律效力,即婚姻缔结行为存在瑕疵,构成存在缔结瑕疵的婚姻。
(二)关于我国婚姻效力瑕疵体系与德国相关规定的对比
我国自原《婚姻法》就已确立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二元效力瑕疵体系,现行《德国民法典》只规定了一种缔结婚姻的瑕疵类型,即可废止婚姻。根据《德国民法典》第一千三百一十四条规定,对于不具有婚姻缔结行为能力的情形,存在重婚、同性婚姻或者具有直系血亲关系的近亲婚姻的情形,或者是婚姻缔结一方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以及因为婚姻缔结一方存在意思表示瑕疵而导致婚姻缔结存在瑕疵,都会产生婚姻可以废止的法律后果,这种一元效力瑕疵体系是德国1998年《婚姻缔结法的新规定》的产物。[3]德国民法认为虽然法律规定无效婚姻并不产生溯及既往的无效的法律后果,但是也存在一些特别规定。例如,不当得利并不适用在离婚诉讼中对于财产问题的处理,在无效婚姻中所生育的子女的权利保障仍然适用婚生子女的法律规定,这些例外规定都意味着德国民法中关于无效婚姻制度的法律效果实际是对将来予以规制,这实际改变了无效制度的核心——法律行为无效产生溯及既往的无效的法律后果。实际德国立法者还是将可废止婚姻制度中根据涉及公共利益和只涉及当事人个人利益进行了区分,从有权申请废止婚姻的权利主体来看,如因为违背婚姻的禁止性规定而最终产生了婚姻被废止的法律后果,如违背了禁止重婚或具有直系血亲关系而结婚的规定,不仅婚姻缔结的双方当事人有权申请对婚姻予以废止,具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同样可以申请予以废止;而对于婚姻缔结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因为只涉及当事人个人利益,因此只有存在婚姻缔结意思瑕疵的一方才有权申请对婚姻予以废止。对于德国民法规定的可废止婚姻的除斥期间,仅对于婚姻缔结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的情形,即因为不具有缔结婚姻的真实意思、存在错误认知、受到非法胁迫和受到恶意欺诈而缔结婚姻的情形,主张废止婚姻的权利受到期间限制,而对于因为违背婚姻禁止性规定所导致的婚姻可废止,只要没有相反事由出现,法律并不限制相关权利人可以申请对婚姻予以废止的期限。
我国《民法典》确立的二元效力瑕疵体系认定的婚姻无效事由更多的是涉及公共利益,而认定婚姻可撤销的事由是涉及当事人个人利益。对于可撤销婚姻的权利主体明确规定是婚姻的另一方,虽然没有明确无效婚姻的权利主体,但我国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九条明确规定有权主张婚姻的权利主体是婚姻双方当事人及与其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其中婚姻当事人的近亲属及重婚情形下的所在基层组织都属于利害关系人。
二、与《民法典》合同编的价值体系对比
(一)婚姻缔结性质包含对个人自由价值的限制
我国《民法典》关于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立法体系确实是参照了关于合同无效与合同可撤销相关规定,但却也并非是简单的整合关于人身与财产的法律规定,而是在其法理的基础上予以了进一步抽象总结。自由价值是《民法典》合同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性价值,其余如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仅是作为与之对抗性的参照而存在,且自由价值是多数《民法典》合同编存在的基础与依据。在合同无效制度中,主要表现形式是通过自由等价值体系对部分合同效力予以否定,使得作为个人意志载体的意思表示得到保障,从而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志,达到维护个人自由价值的目的,主要规则包括对虚假、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等合同效力的否认;以实现维护公平、公共利益、诚实信用等对抗性价值为目的,限制自由价值的无限扩张,进而否定部分合同的效力,主要规则是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违反公序良俗等合同效力的否认。[4]在婚姻家庭中存在着个人主义为内核与以集体主义为内核的价值冲突,现代法律虽然是以个人主义价值为基石建立,但是在婚姻家庭法律体系中仍然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意志的范围予以限制,通过鼓励婚姻双方能够让渡出自己的部分权利、自我牺牲等行为模式来维系婚姻关系。婚姻缔结行为的价值体系中存在个人意志、家庭共同体意志、社会意志三个相互独立的价值维度,三项中缺乏任何一项都无法独立建立起完整合法的婚姻关系。民事主体仅具有自愿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并不会产生婚姻建立的法律效果,需要国家意志来予以认定。国家意志在婚姻家庭法律体系中既要做到让个人意志得到充分实现,又要防止过度利己导致对社会伦理的破坏,在国家对家庭的管控与防止公权力对私权过度干涉之间寻找价值平衡。综上所述,《民法典》合同编中的合同无效与可撤销制度属于财产法律关系,其是以个人自由价值为核心,除非有更强的理由,其他价值一般不能否定自由价值;虽然《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也是以个人自由价值为基础,但是作为身份法律关系决定了其价值实现要受到公共利益、社会伦理等价值的限制。
(二)婚姻二元效力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存在差异
1.关于无效婚姻的论述
无效婚姻中的重婚、未达到法定婚龄可以参照《民法典》合同编中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而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是基于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既然是基于社会公序良俗原则的考量,该亲属关系不应该仅仅是指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关系,还应该包括法律拟制亲属关系。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三条关于婚姻无效的第五项规定“第一项直系血亲及直系姻亲结婚之限制,于因收养而成立之直系亲属间,在收养关系终止后,亦适用之”。亲属关系应该是指法律上认定的亲属关系,不仅包括血缘亲属也包括拟制亲属。
2.关于可撤销婚姻的论述
对于受到非法胁迫而缔结的婚姻,因违背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属于可撤销婚姻,受胁迫一方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婚姻,且除斥期间为一年。患有重大疾病没有如实告知导致婚姻撤销属于受欺诈缔结婚姻的情形,这里的欺诈方应该仅是指婚姻的另一方,不包括第三人的欺诈,考虑的是婚姻双方之间应该尽到诚实信用的义务,并且对于自身的疾病也只有自己更清楚。对于个人财产状况、道德品质、不良行为等内容的欺诈缔结的婚姻,则并不能认定为可撤销婚姻,可以通过离婚诉讼解决。关于以伪造、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婚姻登记的情形,婚姻双方对缔结婚姻是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婚姻缔结主体也并未与事实不一致,只是登记形式与实际主体的身份信息不一致,不能因此而认定婚姻无效或婚姻可撤销。现行司法解释认为该种情形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解决,但因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诉讼时效较短,无法保证当事人的诉权。因此,建议应该在民事诉讼中予以解决。《民法典》合同编中的重大误解与显失公平制度并不适用于婚姻缔结行为,双方当事人均在场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很难会对另一方的身份关系产生认识错误;在身份法律关系中人格权平等,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而因婚姻涉及财产赠与也不成立婚姻的显失公平。
三、确认婚姻无效与撤销婚姻的认定机关与程序
(一)确认婚姻无效与撤销婚姻的认定机关
我国《民法典》规定确认婚姻无效或者申请撤销婚姻的情形均须经人民法院,一方面婚姻登记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对于已经成立的婚姻关系是否符合法定婚姻要件是否可以进行确认缺乏法律判断力;另一方面婚姻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并非行政法律关系,故应由司法机关对于民事法律效力予以判断,而非行政机关的权限,且确认婚姻无效与撤销婚姻并非仅是单纯的就双方的婚姻关系作出认定,而且还会涉及到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子女抚养问题、损害赔偿等其他民事权益事项。如果允许行政机关对婚姻关系作出撤销,难免会造成行政权力过分干预私人生活的不利法律后果,不利于保障婚姻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我国婚姻登记机关仅是对公民办理结婚或离婚登记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只有司法机关才能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予以实质的审查,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对婚姻效力作出判断,并对相应法律后果作出判决。
(二)确认婚姻无效与撤销婚姻的法定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五种适用特别程序的情形,并没有将婚姻无效与撤销婚姻规定在内。一种观点认为,确认婚姻无效或撤销婚姻案件属于非讼案件,应该比照民事诉讼特别程序进行审理。非讼程序主要是为了确认当事人所享有的民事权益、法律事实或法律状态,以解决民事法律关系的不稳定状态,保证社会关系的正常发展,非讼程序往往与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特定利益或不特定利益,实际是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因而在立法中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依职权进行干预的作用,要在一定范围内对当事人在诉讼程序过程中的权利予以限制,其是以达成简易迅速、经济、合目的性与创设性的裁判为目的。[5]确认婚姻无效与撤销婚姻案件应适用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的观点认为:既然《民事诉讼法》没有将宣告婚姻无效与可撤销案件列入特别程序范围,因此对于该类案件适用特别程序进行审理缺乏法律依据;不仅该类型案件并不能体现非讼案件的性质,而且通常存在原、被告及法院三方,由原告对存在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事实予以举证,被告对此予以质证,具有明显的对抗性。笔者结合司法实践倾向认为确认婚姻无效与撤销婚姻案件应该适用简易或普通程序审理。首先,该类型案件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在处理婚姻存续期间涉及婚姻效力、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一方当事人或者近亲属之间因为存在争议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可见该类案件不仅要处理婚姻的效力问题,还要处理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损害赔偿等问题;其次,该类型案件存在诉、辩、裁三方,是典型的民事诉讼构造,这与特别程序案件只有诉、裁两方的民事诉讼构造不同。在特别程序案件中法院只是审理事实问题,而该类型案件不仅要审理事实问题,还需要确定法律的适用。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主要是为了处理财产纠纷而设计,对于确认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等有关身份关系的案件,所体现的公益性并没有体现,而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对身份关系的案件都适用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希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在对诉讼制度进行更合理化改革的制度设计中能够将婚姻无效与可撤销案件纳入特别程序的范围内。
总之,我国《民法典》所确立的二元效力瑕疵体系下的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关注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立法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