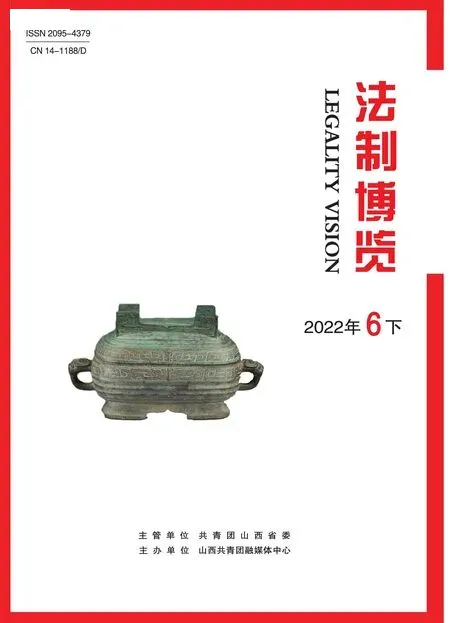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在《民法典》中的适用
2022-11-24林花
林 花
福建闽律律师事务所,福建 福州 350300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1月1日,我国《民法典》正式施行,其中人格权编中第九百九十六条的规定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再次引发关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讨论。而对该法条的解读,学者也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民法典》在第一百八十六条已经规定了违约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择一请求,那么第九百九十六条再作出特别的规定,就应该将该条解读为违约行为在“损害他人人格权”情况下,如果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那么可以直接在违约的诉讼中提起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应该说这是我国在立法层面上首次肯定了在违约的诉讼中可以直接适用该赔偿的规定。而此前,关于合同法领域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一问题,我国法律层面上的规定是十分模糊的,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而在司法解释层面上,也大多数是在合同法领域中禁止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救济。[1]最典型的就是2010年《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的规定》的第二十一条规定②《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旅游者提起违约之诉,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变更为侵权之诉;旅游者仍坚持提起违约之诉的,对于其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明确表态排除了旅游合同中精神赔偿的适用,实在令人唏嘘。
《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虽然提及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但我们也从条文中明确看出了该条文对其适用限定了“损害对方人格权”的前提,该法条限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使得其适用的范围过于狭窄,也无法解决包含精神利益的合同因单纯的违约行为而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例如我们所熟知的旅游合同、婚礼服务合同等等,这种特定类型的合同单纯违约行为,很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形出现,而这类的合同违约行为大部分是不存在损害他人的具体人格权的,显然该种违约情形是不能直接援引适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规定的,况且该法条本身的内容来看也是无法直接解决该类合同存在的精神赔偿问题的。
二、学说梳理:我国学界对合同领域内的违约能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有不同的看法
(一)第一种观点认为,违约不得请求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否定说”一直是我国的通说。王家福教授认为,合同中的违约责任依法只能赔偿违约所造成的财产方面的损失,而这种赔偿是不应该包括非财产上的损失。[2]王利明教授也是持“否定说”的代表人之一,其理由如下:1.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二元救济的区分;2.不符合合同的性质和特点,且与合同的等价交换原则不符;3.违背了我国合同法上的可预见性规则;4.认为即使是在一些以精神利益为目的的特殊合同中,也是属于不能适用的情形;5.认为衡量精神损害赔偿难度大,这将给法官们带来太多不合适的裁量权;6.适用该赔偿会增加风险,这也将进一步给交易市场带来消极的因素。
(二)第二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肯定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认为合同中的损害赔偿,是包括财产性损害赔偿和非财产性损害赔偿(精神损害),应在《民法典》合同编中确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如韩世远教授认为应当“勇敢突破原有成见”,对于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可以在原则之外规定例外。[3]程啸教授认为非财产损害不应该只限定在传统意义的侵权责任的范畴之中,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判例中得到很多的印证,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上的变更也体现了这一趋势。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完全有必要在一定的情形下给予当事人进行救济赔偿。[4]李永军教授认为,对于精神享受等目的性合同是可以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5]崔建远教授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持“肯定说”的立场,并针对王利明教授的“否定说”理由进行了详尽的逐一的反驳,简单归纳如下:1.在违约之诉中可否主张此类赔偿,是属立法政策的问题;2.合同未必都遵循等价交换原则;3.一些特定种类的合同,精神损害是符合可预见性规则;4.在发生违约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下,通过以违约为理由的诉讼来主张该请求,对当事人来说是更为简便和节约成本的做法;5.精神损害赔偿给法官带来的裁量权过大,这一问题在侵权中也同样客观存在。[6]
三、比较法上的考察
在英国,法院能允许当事人提起该赔偿的范围,通过判例不断得到延伸,概括起来主要涵盖在以下类型之中:(一)合同的目的就是要提供安宁和快乐的享受;(二)合同的目的就是要解除痛苦或麻烦;(三)违反合同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直接造成精神痛苦[7]。在美国,通过两次合同法重述,已经突破了此前的传统理念的否认态度,而对于合同领域中的精神赔偿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态度转变,至此也基本确定了美国对该问题的“原则+例外”的模式。并且这种例外随着日新月异的实践判例,不断得到发展和延伸。[8]
大陆法系的国家,在不断地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来确认一定情况下对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支持。在德国,其早期的民法中并没有明确地承认该问题,此后通过《德国民法典》上的债法改革将该赔偿的适用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并由法律来明确列明具体适用场合。在法国,现在宽泛态势只要构成精神损害,都可以不特别区分违约还是侵权直接进行相应的赔偿,可以说,法国法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方面表现得“非常宽宏大度”,其认为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根据是合同之诉还是侵权之诉而作不同处理,没有正当理由不会进行特别处理。[9]可见法国法对此问题的全面保护的力度。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典”也是与时俱进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进行了增设,并不断地完善特别法中可以适用慰抚金的规定。例如在侵权行为中将慰抚金请求权的基础由侵害人格权扩大到侵害人格法益和身份法益。在债务不履行中增设了包括“旅客时间浪费的金钱赔偿”的债务不履行引起的非财产上损害的金钱赔偿的规定。在我国台湾地区陆续制定的特别法也体现了非财产上损害赔偿的发展。
由此可见,合同领域的违约造成的精神损害是客观存在的,也有赔偿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所以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不断地发展和有限地承认合同法领域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并在不断探索能够适用该赔偿的合同范围。
四、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民法典》中的适用
通过我国学说上的梳理以及比较法上关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分析,可以说一定范围内承认合同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已经是大势所趋。有限地承认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我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后,也与时俱进地首次在法律层面上提及了违约责任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已经说明了我国在立法上的突破,肯定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但该法条处于人格权编,也仅只是在侵害人格权的前提下,在违约与侵权竞合时才支持该赔偿,具有局限性。笔者认为,我国也应顺应时代的趋势,有限承认合同领域内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我们要对《民法典》中相关的条文做出合理的法律解释,才能更好地在《民法典》中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
笔者认为,我们应对《民法典》合同编中第五百七十七条违约责任中的“赔偿损失”扩张解释为包含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在内的损失,从而为关乎精神损害赔偿的合同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提供法律依据。同时我们应将《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的“侵害人格权”做扩张解释,并将其理解为侵害人格权益和身份权益等具有人格属性的人格法益。[10]在侵权和违约竞合之中也在一定范围内扩大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当然我们也要通过进一步的总结概括相关合同类型,从而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限制在合同的适用范围之中。正如李永军教授指出:“这种区分是一个重要的和必要的限制规则,如果在纯粹的商业合同中也被允许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则任何情感和不愉快都会得到赔偿,最终将使合同这一交易工具不堪重负而死亡”。[5]对合同领域内特殊合同的违约导致的严重精神损害可以获得赔偿,这类特殊合同的类型结合我国实践的情况和比较法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粗略了解。
笔者结合我国一些学者提出的观点,将我国司法实践中能够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进行限定,提出如下四种适用合同的类型:(一)合同的违约侵害他人具有人身属性的法益。如实践中合同的加害给付,违约行为导致侵害他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格利益或者医院过错致错抱孩子的亲子关系的身份权益的侵害,应当都是属于可以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二)合同的标的物承载着精神利益。此类合同如骨灰、宠物狗等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保管合同或者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加工合同。(三)合同目的即为获得精神利益的合同。此类型合同主要有旅游服务合同、观看演出类合同、婚礼庆典服务合同、殡葬服务合同、养老服务合同等。(四)合同的履行关系着当事人的精神安宁。此类型合同主要有运输服务合同、酒店住宿相关合同等。
五、结语
合同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是一种法律制度的进步趋势,通过归纳总结适用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四种合同类型,将其适用限定在一定的合同范围内,以期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能够在《民法典》中得到更好的适用,为我国民法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