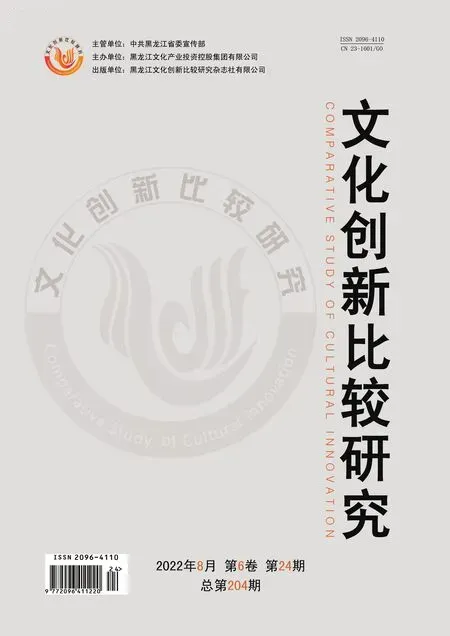西方价值观视角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影视展现研究
——以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为例
2022-11-24李欣玥张敏
李欣玥,张敏
(西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 710000)
“花木兰”人物最早出自我国南北朝《乐府诗集》中的《木兰辞》,该诗以北魏时期中原与柔然的战争为背景创作,1 000 多年来,花木兰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巾帼英雄”的代表,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正是以此为蓝本而进行的再创作。 该影片曾在制作之初就备受关注,但在上映后,在中国票房和口碑双双失利,标志着它在中国市场的最终失败。这部跨文化改编电影在国内表现不尽人意的原因,在于制作者对于电影和原文本之间文化冲突的不恰当处理,本质上,则在于其错误的“东方主义”思想及西方文化霸权的蔓延。
1 《花木兰》电影改编中体现的中西文化交融与冲突
1.1 中国传统花木兰人物形象
作为后世二次创作的原本,《木兰辞》 是中国传统认知中花木兰形象的来源。开篇,花木兰以普通传统女性和顺温良的形象出现。父亲年迈,家中又无长兄,对父亲的担忧成为花木兰“男扮女装替父从军”的动机。在个人和家庭的矛盾中,花木兰突破了社会性别观念及伦理观念的制约, 承担起家中长女的责任,从而做出不同寻常的举动。“将军百战死”数句则令花木兰在军旅生涯中英勇报国、 能征善战的形象深入人心。由此,花木兰是传统文化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忠孝” 常被用来描述这一女性历史人物的核心精神, 中国传统家国情怀在花木兰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和抒发。
然而, 花木兰始终是在传统社会道德框架之内的存在。到最后,她荣归故里,重新回归家庭及“为女为妻为母”的传统女性身份,也就是说,她虽有英雄气概,但始终秉持“温柔敦厚”的女性原则,实质上并未对“中国传统妇女观”形成冲击,而是达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且不以现代视角评判,花木兰这一角色正因这一平衡, 才能以积极的形象在封建父权制社会1 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不断被传颂至今。 直到今天,花木兰在国人认知中,仍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范畴之内的一个文化符号。
1.2 电影中塑造的花木兰形象与价值观冲突
在迪士尼电影《花木兰》中,其形象被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写。影片中的花木兰自小便天赋异禀、活泼张扬,也因此遭受邻居的指摘;成年之后又遇结亲失败便更让她在所处的社群中显得格格不入。 影片通过有意营造,蓄意呈现出一个“不适应自身性别身份,难以被周围认同”的特殊女性角色。 而这一迪士尼的“主角光环” 风格很明显是要为后续叙事作铺垫,并且向观众旁敲侧击地传达“邻人平庸迂腐,而花木兰必要冲破桎梏”的含义,其中未免暗含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丑化处理。
影片中,“为家族带来荣耀”的观念被反复提及,并与花木兰的每一个行动紧密相关。 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替父从军是家国情怀的代表,“家国一体”包含东方文化下集体主义的意蕴, 而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伦理观念。“西方人价值取向是重个人利益, 形成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1],在西方语境内,“家族荣耀”更偏向于个人主义的范畴,并且其中包含着功利性色彩,与其传统的“功利主义”更为契合。不难理解,虽然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两种表述在表面上大致对等, 但这和整部电影中鲜明的英雄主义一样, 都是对中国忠孝文化所进行的一种符合自己文化的“归化式”替换,本质上传达的仍是西方价值观。
“气”,是一个贯穿全片的要素。“气”元素不仅出现在《花木兰》中,也曾在《功夫熊猫》等好莱坞中国元素电影中有所提及。在中国,这一术语源于老庄哲学与中医思想,蕴含天人合一思想,被看作参与到人生命活动之中的一个自然元素。但在电影中,迪士尼进行故弄玄虚化的应用,直接用它对花木兰内在的精神力量进行描述,这样的运用并未对其进行真正理解,而是更多发挥了自我想象,本质上,是将它用作为满足西方观众对“神秘东方”好奇心的一个名词而已。
从人物发展的角度看,编剧也借“气”来代表花木兰的自我意识,她对“气”态度的转变也是自我觉醒、承认女性自身力量的节点。女性独立与觉醒是电影价值导向的另一着重点, 影片也在花木兰身上赋予了“女权主义”的当代新含义。然而,为极力渲染主角光环, 以父母为代表的身边人再次被进行了过于消极的刻画, 电影基于主观想象给观众刻意营造出了冷漠迂腐的中国大众形象, 花木兰也进而被刻意塑造成一个打破“旧思想”束缚的女性。 “女权思想”作为现代文化中的重要潮流之一, 在社会中有相当高热度。电影或许是尝试对当今时代发展做出呼应,但不得不指出, 其主观意识的强加使得电影在对原文本的解读上出现了相当大的偏差, 甚至有对中国形象的刻意污化之嫌。
1.3 电影对中国文化的粗糙展现
电影《花木兰》中对中国文化的敷衍展现也令国内观众感到不适。 花木兰是北魏时期的人物,《木兰辞》中提及的“黄河”“黑山”等都指明其活动范围应是我国北方一带, 然而电影却将福建地区的土楼描述为其家族所在地。 成书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的《重修虔台志》是有关土楼的最早记载,也与北魏相差千年[2]。 为使中国特色明显,电影中出现了不少象征性物品,如花家的传家宝,刻着“孝”和凤凰的玉饼。然而,简易堆砌的中国符号没有对剧情的发展起到任何作用,反倒更令人感到突兀。
如此种种, 在时空观上所犯的低级错误及对于中国元素的象征性套用使得电影评价大幅缩水。
2 西方消极改编及其原因:傲慢的“东方主义”和传统市场的消极引导
虽然讲述的是中国故事, 但电影迪士尼的风格十分突出,似乎电影只是借用了中国的外壳,而核心却是西方价值观的野蛮输出。究其原因,正在于西方世界“东方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及其所塑造的传统电影市场导向的局限性。
2.1 “东方主义”的窠臼
“东方主义”, 是西方立足于自身对东方各类学科认识和研究的总称, 包含着西方为强调自身的优越和支配地位而将东方世界作为对立面所进行的有意误读化认知。在这一思维下,西方与东方文化间存在一种主体与客体、控制与被控制的不平等关系。以西方思维认识的东方文化成为西方视角下的 “他者”,失去本身,成为西方重塑的去真实化的主观创作产物。其中,不免有刻意的丑化及对东方文化内核的西式代替。
好莱坞电影自早期就体现出“东方主义” 的趋势。 20 世纪初,“奸诈丑恶的傅满洲”成为对于东方形象污蔑性描绘的代表。冷战时期,随世界形势的变化,“‘东方主义’的论调常用来形容美国的东方‘朋友或敌人’”, 而东方人的身份人格仍是劣于西方人的存在。进入经济全球化后,好莱坞大片火热输出让“东方主义”持续发展,同时也将西方价值观向全球强势输送。 在中国,更是发展出了“自我东方化”趋势,如21 世纪初的《卧虎藏龙》等武侠电影,华人的导演虽一定程度上不再让东方被继续污名化, 但其中仍存在刻意粘贴中国元素以迎合西方喜好的嫌疑[3]。
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中多次出现对中国文化的不合理描述。影片制作方以西方思维理解中国故事,缺少对东方的耐心了解,过于主观臆断,从而不免落入“东方主义”窠臼。
2.2 西方电影产业的称雄及其多年塑造下的传统电影市场导向
现代影视源于西方, 以西方为立足点的电影产业及其理论在其100 多年的发展中逐步趋向成熟。在1930年代,美国好莱坞电影开始逐渐取得了全球影坛的霸主地位, 在其完备的制片厂制度下诞生了大量经典,并逐渐确立了其电影创作的基本特征。蓬勃发展的好莱坞电影在西方主导的现代社会引起巨大潮流,电影产业开始进入“经典好莱坞”时期[4]。 与此同时, 西方受众对东方的猎奇心态催生了早期好莱坞“东方主义”电影的诞生。
电影, 让刻板化的东方印象在全世界更加根深蒂固,其稳定的受众群体也逐渐在市场上发展,又反向促进了影片的继续生产。 在利益驱使下,“东方主义”趋向化的传统电影市场导向逐渐形成,并变得积重难返, 同时也让该类型影片在东方文化电影市场的霸权地位得以成就。 电影制作方缺失探索真正中国文化的动力, 简单拼贴和主观想象成了其创作的主要方式。
3 破除西方话语屏障,立足时代,主动推动中国影视文化的良性发展
经济全球化让文化交流愈加频繁深入,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 如何促进中国文化的有效“走出去”、 讲好中国故事成为近年来我国在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进程中的重要议题。
面对影视文化交流中的困境,我们应立足自身,通过多种方式主动发声来传播真正的中国文化,从而推动他国视角下我国本土文化影视展现的正常化。
3.1 增强自身文化自信,在自信心态中进行交流
5 000年历史培养出了灿烂的中国文化, 深厚的底蕴给予我们自信的底气。然而自近代起,文化自负、文化自卑的不良心态曾成为影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因素[5],自我抛弃不仅限制自身文化积极发展,助长崇洋媚外不正之风,也造成了他国对中国文化的偏见性理解。
文化,作为软实力,是民族复兴和自我发展的重要支撑。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在文化上处于被动状态、丧失独立性,那么制度、主权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6]。 在今天,我们应该秉持更加自信、理性的心态, 主动了解热爱自我文化。 坚持文化自信,才能守住本民族特色和主心骨,不会在文化交流中迷失自我、丧失主体性和生命力,也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本民族文化的正向发展,有力对抗“东方主义”等偏见性认识在世界文化舞台的霸权地位。
3.2 降低“文化折扣”,提升话语能力,增强他国理解
跨文化交流中,“文化折扣” 由于文化间的差异产生,并影响文化交流效果。 要降低“文化折扣”,需要了解差异,也要注重跨文化沟通的策略,力求增进他国对中国文化的正向理解。
不同文化由于历史发展背景不同有着不同特点。西方思维偏理性、重视个人,而东方偏感性、重视集体。在认识中国文化时,以西方思维来理解不免会产生误差, 这就需要在交流中运用合适的话语来缩小误差,促进文化的理解和接纳。 从形式上来看,良好沟通需良好的翻译来减少语言上的障碍, 在翻译时,不仅要尽力保留中国文化特点,也要兼顾受众的思维和接受能力,合理简化并注重解释。从内容上来看,对外传播应关注选材的重要性,先要贴合生活、契合时代发展,再从“他者”的角度出发,侧重选取接受门槛较低的大众文化及符合人类文化共识的话题[7],注重共鸣的引发,从而循序渐进地破除偏见,破除“东方主义”迷信。
3.3 审视自身文化类影视创作,重视优质本土影视成品输出
当前, 我们应意识到电影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跨文化类优质影视成品输出是更广泛直接传播中国文化、打破“东方主义”影片霸权地位的有力方式。然而,国内电影在这一方面的表现仍有欠缺。 好莱坞大片往往以其高质量的内容和技术令人印象深刻, 以科幻片和动作片为代表的美国大片将其国内价值观输送全球。但反观中国文化类电影,在制作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上还存在不足。
第一, 电影产业总体展现中国文化的能力仍有待加强,电影类型较少,以搞笑片、战争片为主。 “一些电影以搞笑或者武打为重点, 忽略了对传统文化的呈现,致使电影丧失了应有的文化传播作用。 ”并且,国内电影情节往往俗套,缺乏创新,更未恰当把握时代热点和展现中国当代文化[8]。
第二,好莱坞长期居于制作水平的领先地位,尤其在科幻片方面, 而中国电影的技术发展则仍任重道远。
第三,国内产业缺乏国际化的视野和营销体系,译介水平也有不足。 中国电影应立足国内而放眼全球,借鉴好莱坞模式发展国际化的营销,同时注重内容与全球文化接轨的能力。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国外反响平平, 主要原因就在于其鲜明的文化特色由于前期角色宣传、影片字幕翻译等方面的不足,未能避免文化隔阂, 从而使观众的观影体验和意愿受到很大影响。
在自我反思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对自己抱有信心。 中国电影在海外虽有不足,但逐渐地取得成绩。例如,《流浪地球》 在展现中国担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同时也引发了全球观众共鸣, 得到广泛认可,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一步。其成果也为中国文化的影视输出提供了模板[9]。
4 结语
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是当今我国传统文学作品在西方视角下影视化的一个样品, 制作方对中西文化差异进行的失当处理最终令整部电影呈现出不协调的效果, 其中蕴含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主观想象与肤浅理解,体现着西化的内涵价值,同时也丢失了中国原本的文化语言,显示出西方对中国文化认识的不足与偏差,而根源则在于其“东方主义”的错误思想。 这一思想被融入好莱坞电影的发展,令西方电影界的东方文化类电影长期具有“东方主义化”的色彩。
面对困境, 我们应主动破局, 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在过程中,应树立自信、立足实际,同时合理借鉴他国经验,通过运用多种形式,构建更加科学化、体系化的话语结构来进行中国文化的讲述,从而有力地破除西方刻板印象, 并推动西方视角下中国文化影视作品的良性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