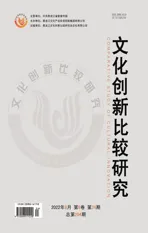《一九八四》歌谣中的概念隐喻
——董乐山、刘绍明的汉译本对比研究
2022-11-24巢圣安
巢圣安
(华东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7)
《一九八四》 是由英国作家George Orwell 撰写的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于1949年出版,描绘了极权统治下的虚构英国,书中名为“Oceania”。 该作在世界范围引起了轰动, 在1989年已有65 种语言的译本,数量为当时英语小说中最多[1]。
自20 世纪中叶开始,就已经有学者认为语言能够塑造个体的认知、影响非言语行为,而作者在《一九八四》中创造的虚构语言Newspeak,也是书中极权政党实施思想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2-3]。 因此,Newspeak 是众多语言学学者的研究对象,也已有学者研究了它对儿童认知系统发展的影响, 甚至有学者找到它与量子概率理论的共性, 试图用其解释人类的认知[4-5]。
《一九八四》中有四段贯穿全文、多次重复的歌谣,对剧情发展和情感渲染均起到了一定作用,而目前,针对《一九八四》中语言的研究很少触及这些歌谣。由于语言对认知的影响和塑造是本书的一大特点,歌谣的翻译质量及处理方式将影响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因此,本研究将从概念隐喻视角对董乐山和刘绍明的汉译本中的歌谣进行对比分析。
1 文献综述
1.1 概念隐喻
目前, 学界广泛采用的隐喻定义来自Lakoff 和Johnson,是“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的手段”[6]。与修辞学所关注的“隐喻”不同,这一定义下的隐喻(即“概念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除日常生活外,也渗透于语言和思维活动中的方方面面。他们认为,隐喻“是人类用来组织其概念系统的不可缺少的认知工具”,即隐喻认知观[7]。
概念隐喻中的两个主要要素是始发域和目标域,前者来源于人类在生活中所积累的经验,往往是非隐喻概念,即由其本身建构,通过其自身被理解;后者往往是人类难以直接理解的抽象概念, 需要通过映射,借助其他的概念域来理解[8]。 前者的结构映射到后者,便是概念隐喻[9]。其中,映射是概念隐喻形成的对应过程,具有系统性、部分性以及方向性。 映射过程也会保留始发域的拓扑结构,即“不变原则”。
1.2 概念隐喻的翻译研究
由于概念隐喻的形成受到文化因素影响, 在翻译等跨文化交际活动过程中, 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认知体验不同所造成的交际效果差异。 加上语言间词汇的不完全对应, 翻译过后的概念隐喻往往会与原文出现大小不等的差异。因此,隐喻翻译关乎作品在译入语语境内能否得到正确的理解, 是一个重要课题[10]。
在前文所述的隐喻认知观受到广泛认可后,译文再现原文修辞功能与否不再是人们评判概念隐喻翻译质量的主要标准。最初,隐喻翻译的主要策略是补偿[11],而其后数十年,隐喻的翻译策略也被精炼为相同、不同、非隐喻化,以及零译四种[12]。 后来,也有学者认为其翻译策略包括三种,即替代为目的语、转换为意义以及省略[13]。 随着对概念隐喻认识加深,文学功能、 构成基础以及语境因素均被纳入考虑。 因此,提高概念隐喻翻译质量,需要在充分解读原文隐喻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作者的创作意图、源语和目的语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异同,才能做到恰当的再现。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首先需要将原文的语言符号匹配至译者脑中的概念,组合为思想,再进化为联想、评价、想象等复杂的思维活动[14],因此译者对原文含义及写作意图的正确理解,起着基础性的关键作用。同时, 概念隐喻具有文化依赖性, 如果忽视文化的差异,对隐喻的始发域或目标域处理的不恰当,使译文中出现的概念与原文带来的文化体验不符, 会导致翻译的质量降低。同时,由于译者隐喻与作品本身也具有依存关系,其理解与再现受制于文学语境,此处处理不当,也会使译文效果打折扣。
2 分析与讨论
小说中总共出现了三段歌词、一段童谣,每段均出现多于一次。 由于童谣Oranges and Lemons 中并未出现隐喻,本研究将省略该段的分析。
2.1 第一段歌谣分析
原文:Under the spreading chestnut tree
I sold you and you sold me:
There lie they, and here lie we
Under the spreading chestnut tree.
董译:在遮荫的栗树下,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
在遮荫的栗树下。
刘译:栗树荫下
我出卖你,你出卖我。
他们躺在那边,我们躺在这边
栗树荫下。
这段歌谣属于书中的靡靡之音,由谱曲器编成,是专供无产者消费的音乐作品。 本段歌词音节数分别为8、7、7、8,均为句尾押韵。 除工整外,这四句歌词在词汇和结构上均没有特别出彩之处, 并不能称作是值得欣赏的作品, 因此两段译文在结构和韵律上的区别不会对概念隐喻的传达产生较大影响。
在文化效果上,sell 的直接对应表达在汉语中可以完整传达相应效果。 Merriam-Webster 词典中,sell 作为及物动词的第一个义项即为 “to deliver or give up in violation of duty, trust, or loyalty and especially for personal gain”。 根据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sell 的本义为 “to give, furnish, supply, lend;surrender, give up; deliver to; promise”,不包含“违反职责、信任或忠诚而交出或放弃”的含义。 汉典中,“卖”的本义为“拿东西换钱,与‘买’相对”,第二义项为“叛卖,出卖国家、民族或别人的利益”。 sell 的betray 义,及“卖”的“出卖”义均属于死隐喻,始发域为本义的物物交换, 目标域则为以他人的信任为代价换取私人利益。英语的sell 可作betray 用,汉语同理,因此“出卖”可以完整传达相应效果,使两段译文处理相同。
在文学语境中,它与故事背景及剧情中的两个核心要素有关。 其一,指小说中统治党精心控制语言,淡化,甚至消除sell 这一义项的负面意义,将其编入歌词供人消遣,让读者看来滑稽与恐怖兼具。其二,指这段歌词两次出现:第一次在第二部第七章,主角温斯顿想到3 个供认重罪的前高层在栗树咖啡馆因听到此曲而几欲泪下,其中二人有伤,恐为逼供所致,后来3 人便再次被捕、认罪、处决;第二次出现,是在全书最后一章,听到此曲触景生情、潸然泪下的,是已被捕并与朱丽亚互相出卖的温斯顿。此处文学语境将温斯顿的命运与3 位前高层匹配, 引导读者发现两段剧情的相似性, 暗示温斯顿接下来的悲惨结局, 并促使读者对小说中极权政党的统治和监视进行深思。二位译者在此处处理一致,均保留了小说核心要素的文学语境。
2.2 第二段歌谣分析
原文:It was only an'opeless fancy.
It passed like an Ipril dye,
But a look an'a word an'the dreams they stirred!
They'ave stolen my'eart awye!
董译:这只不过是没有希望的痴想,
消失起来像春天一样快,
可是一句话,一个眼色
却教我胡思乱想,失魂落魄!
刘译:本来不存希望,
心事化作春泥。
谁人巧言令色,
使我意马难收?
这段歌谣同样由versificator 编成, 四句音节数分别为9、7、11、8。 原文中的“(April) day”含义为快速流逝的春天,是“fancy”的比喻喻体,并非隐喻,因此不在本研究的分析范围内。
第三句“ (stir) the dreams”是隐喻,汉语中的字面对应为”搅动(我)的梦”,实际上指“激活(我)的思绪”,以及“让(我)开始幻想”。 dream 的本义指睡眠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思考、画面或感情,是一个抽象概念, 而非物体, 无法直接被搅动。 因此, 此处dreams 是被投射于物体域,为其赋予了实体。 类似地,第三句中的“a look”和“a word”也投射于物体域,与“dreams 产生物理互动,引人遐想。
此处,董译保留了“a look and a word”的字面形式,但将stir 非隐喻化,译为“教”,保留了其对客体施加影响、产生扰动的含义,同时也将“dreams”非隐喻化,保留“思”的含义,形成“胡思乱想”的译文。 这具有一定负面色彩,与原文所传达的情感有所不符,但其程度轻于刘译;刘译也将其非隐喻化,使用了成语“巧言令色”,但“巧”和“令”不存在于原文,有所偏离。 在文化效果上,原文较为中性,但该成语具有虚伪讨好的负面含义。
第四句“ (steal) my heart away”同样是隐喻,汉语中的字面对应为“偷走了(我)的心”,实际上指“令(我)着迷”,或“使(我)陷入爱河”。此处的heart 被隐喻为人体外的物体(“HEART AS AN OBJECT”),能够像一般的物件那样被他人盗走[15]。 steal 同时也可分类为动作域投射于人体域[16]。 二位译者在此处均未保留原有形式。
董译使用了汉语中的类似隐喻替换, 将其转换为“失魂落魄”。这一表达同属于隐喻,将魂魄这个难以理解的概念实体化、物理化,指人的精神和思想,形容人心神不定,同时也与前半句“胡思乱想”形成韵律上的对应。 同时,“胡思乱想” 也是原文第三句“dreams (stirred)”的非隐喻化表达,过程类似heart的物体化,投射于动作域。董译将原文第三句后半部分的内容整合到第四句中,避免了第三句过长,同时让两个特性及效果相似的隐喻相互靠近, 共享认知成本,从而减小读者的理解负担,同时保留一定原文韵味。
刘译也将“heart (stolen) ”与“dreams (stirred) ”整合,转换为不同的隐喻,到汉语中的“意马难收”。该谚语前半句为“心猿既放”,形容内心思想像放开的猿猴、 脱缰的野马一样难以收回。 这一表达是将“意”投射于“马”,特征为“难收”。采用这一表达能产生与原文类似的文化体验, 文学语境也契合小说情节:温斯顿对朱丽亚产生情愫,心中不服极权统治的火苗也逐渐燃起。 刘译工整的结构也符合汉语传统诗赋歌词的审美习惯,虽删改,但整体上刘译将原文的含义还原得比较完整。 刘译的主要缺憾在于引入负面色彩,使其产生了不准确的文化效果,也不完全契合文学语境。
2.3 第三段歌谣分析
原文:They sye that time'eals all things,
They sye you can always forget;
But the smiles an'the tears across the years,
They twist my'eart-strings yet!
董译: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
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
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
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刘译:谁说时光最能疗创,
谁说旧仇转眼遗忘,
旧时笑声泪影,
历历在我心上。
本段也由versificator 生成, 属于 “废话连篇”(drivelling 的董译)的歌词,隐喻共有三处。
第一处为 “time heals all things”, 属于拟人隐喻,始发域为人,目标域为time。 时间是一个抽象概念,本没有医师的疗伤能力,但人的悲痛可能随着时间淡化, 因此减轻痛苦这一现象被投射于heal。 此处,董译和刘译均保留了隐喻,采用了与原文相同的表达,二者的区别仅在保留all(一切)或将其译为“最能疗创”。
第二处为“the smiles and the tears”。 此处始发域为微笑和泪水,目的域是令人快乐和悲伤的经历。董译和刘译也均保留了隐喻, 因为笑容、 笑声及泪痕、泪影在汉语中均能隐喻“使人产生笑容”或“使人留下泪痕”的经历,因此保留隐喻能够产生足够接近的文化效果,同时契合文学语境,即温斯顿看到窗外的无产者女性忙碌家务杂活, 唤起了温斯顿儿时对家庭和母亲的回忆, 激发了其内心渴望他人关心疼爱,以及缺失安全感的深层情感。二位译者的处理均能使读者以类似的思考量联想到这一层含义, 因此效果相似。
第三处为第四句中的 “twist my heart-strings”。此处始发域为心弦,可以认为是心的一部分,而心此时兼具本身的物体属性和投射到的情感域。 针对其物体属性,“心弦”能被扭绞,即外部力量使其产生形变,而“心”作为人体器官,会产生痛觉;这种痛觉投射到情感域,代表人的感情悲痛。董译将其转换成死隐喻 “心痛”; 刘译采取零翻译, 删除twist, 并将heart-strings 还原为“心”。董译相对更为直白,“心痛如刀割”也符合汉语表达,效果与原文相似;刘译淡化伤痛,相对更含蓄。
本段歌词的前两项隐喻在英语和汉语中均存在基本对等的表达,文化效果相似,可近似匹配文学语境。二位译者在第三项隐喻上的处理有所不同:董译保留,刘译省略。其原因可能在于刘译的单句长度更小, 且注重形式的工整, 使得译文无法容纳原文隐喻,且“历历在我心上”的表达也能传达出温斯顿回忆过往的心境,相对含蓄地传达出悲痛和怀旧。
3 结语
本研究共分析了《一九八四》中三段由versificator 编写的歌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译者在处理歌谣中的隐喻时, 并非是简单地寻找译入语中最接近的对应隐喻, 而是综合考虑了文化效果和文学语境两方面。
在文化效果中, 译者首先考虑了原文的汉语对应是否能在读者脑海中唤起相近的文化认知体验。如果原文中的表达与译入语中的对应接近, 那么译者会偏向于直接选择该表达的译入语对应 (如sell译为“出卖”); 如果该对应不能很好地契合原文意图,或受到文学语境的制约,译者可能替换隐喻,选用译入语中带有相近文化效果的表达(如“(steal) my heart away”一处)。
在文学语境中, 译者不仅会考虑内容在剧情和人物形象刻画中的作用, 还会将形式纳入考量的范围,有时形式甚至是主要因素。 如第二段歌谣中,董译和刘译均采取了非隐喻化的方法,重组原文信息,利用汉语成语调整形式, 使该段符合汉语读者对抒情歌赋的认知。第三段歌谣类似,董译使用了直接对应,而刘译选择删除,将原文中的痛感交由读者自行体会,从而保持译文结构工整。
综上所述,在处理原文隐喻时,如果原文的隐喻在译入语中可以带来相近的文化效果, 且契合文学语境,译者可以优先保留原文;如果二者有任意一项效果不尽如人意,则译者可以尝试替换隐喻、非隐喻化、省略删减等方法。 此外,在诗词歌赋这类形式较为重要的情况下, 文化效果和文学语境均可做出一定程度让步。
《一九八四》是一部含有大量概念隐喻的小说作品,本文所研究的歌谣仅仅是其中的冰山一角。如果后续研究可以对全书及其译本进行概念隐喻翻译的定量研究, 总结出如此一部重隐喻的作品中隐喻翻译处理的影响因素、权重及各种条件下的处理偏好,将会为概念隐喻翻译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并指引后续翻译作品质量的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