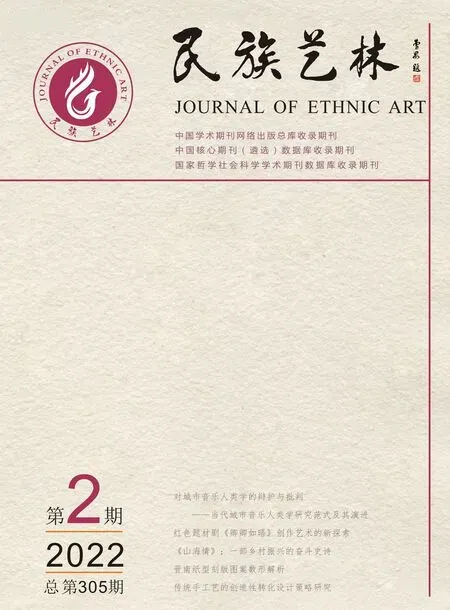《宋之小说杂戏》之补遗综论
2022-11-23马英超姜铭铭
马英超,姜铭铭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宋之小说杂戏》这一章是王国维先生探寻所谓“真戏剧”的源流的重要章节之一,王国维先生在该章先后论述了小说、傀儡戏、影戏、三教、讶鼓、舞队的发展情况及其与戏曲之间的关系。笔者在细读王国维先生《宋元戏曲史》的基础上,引后代众学者的考证材料,对《宋之小说杂戏》进行补遗综论。
一、王国维先生《宋之小说杂戏》之见
王国维认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他还提出“真戏剧”的概念,“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意义之始全。”[1]在王国维先生看来,戏曲的基本要素包含言语、动作、歌唱、舞蹈,同时以表演故事为目的。他在《宋元戏曲史》的前二章他论述了中国戏剧的起源、宋代滑稽戏的发展。虽然滑稽戏已有不少戏曲的要素,但是“固纯以诙谐为主,与唐之滑稽剧无异。但其中脚色较为著明,而布置亦稍复杂;然不能被以歌舞,其去真正戏剧尚远。”[2]而且王国维在第三章开头就论述,“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故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至其变为演事实之戏剧,则当时之小说,实有力焉。”[3]可见,在王国维先生眼中,“演故事”是戏曲的基本内涵。所以,第三章在《宋之小说杂戏》中,王国维进而论述宋代表演事实的小说、杂戏等对戏曲发展的促进作用。
王国维先生所讲的“小说”,特别是宋代的“小说”,多指说话艺术,“宋之小说,则不以著述为事,而以讲演为事”,且引证列举其分类,“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谓说话有四种:一小说,一说经,一说参请,一说史书”。[4]至于演史与小说可以自成一类,而且演史与小说体例大致相同。演史与小说至宋代发展得相当繁荣,“《东坡志林》(卷六):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云云。《东京梦华录》(卷五)所载京瓦伎艺,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至南渡以后,有敷衍《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者,见于《梦粱录》,此皆演史之类也。”;“其无关史事者,则谓之小说。《梦粱录》云:“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泰等事。”[5]王国维认为这种说话艺术到了宋代已经十分发达,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受众量大。基于此,说话艺术对于戏曲的发展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特别是题材与结构上,“此种说话,以叙事为主,与滑稽剧之但托故事者迥异。其发达之迹,虽略与戏曲平行;而后世戏剧之题目,多取诸此,其结构亦多依仿为之,所以资戏剧之发达者,实不少也。”[6]
除了小说以外,以演事实为主,与戏剧更为相近的则是傀儡戏。王国维先生先对傀儡戏的起源发展做了论述,他认为傀儡戏发展至宋代最为繁盛,且种类繁多,“至宋而傀儡最盛,种类亦最盛:有悬丝傀儡,走线傀儡,杖头傀儡,药发傀儡,肉傀儡,水傀儡各种”;傀儡戏的表演内容与说话、讲史等相关,并以讲故事为主,“凡傀儡,敷衍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中略)大抵弄此,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等也。”[7]王国维先生认为这种表演故事的木偶戏的发展,是戏剧进步的表现,“则宋时此戏,实与戏剧同时发达,其以敷衍故事为主,且较胜于滑稽剧。此于戏剧之进步上,不能不注意者也。”[8]
傀儡以外,还有演故事为主且近似于戏剧的影戏。其形式上以纸、羊皮等材料雕琢成形,其内容与说话、讲史也类同,“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以彩色装饰,不致损坏。(中略)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盖亦寓褒贬于其间耳。”[9]这种专演故事的影戏,也是有助于戏剧进步的。
除小说、傀儡、影戏以外,还有三教、讶鼓、舞队等戏剧的支流,也是需要注意的。三教俗称“打野胡”,源于古代傩仪驱祟,宋时发展为一种表演艺术。讶鼓戏已经开始分角色,扮演各种情态。宋代舞队剧目颇多,王国维先生列举了《武林旧事》记载的70 种剧目。王国维先生认为舞队与戏剧的差别是戏剧有固定场所演出,而舞队则是巡回演出。这三种杂戏皆是人来表演简单的故事内容,但比起傀儡和影戏,其故事性要粗劣简单得多。
小说、傀儡戏、影戏、三教、讶鼓、舞队等都以演故事为主的,说话艺术以口来讲唱故事,傀儡戏、影戏以借助道具的形体来表演故事,三教、讶鼓、舞队以人的舞蹈来表演故事。在王国维先生看来,他们对真正戏曲的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后代学者之补遗
(一)宋代说话艺术研究
关于宋代说话艺术的发展,对《都城记胜》所记录的说话情况,在王国维之后马美信在《宋元戏曲史疏证》里补充了后来学界主要的三种观点:第一种以鲁迅和孙楷第为代表。鲁迅认为宋代说话四家,分别是小说(银字儿、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说参请、说诨经,讲史书,合生;孙楷第又对鲁迅的四科纲目进行了补充:“一、小说,即银字儿——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说铁骑儿。二、说经——说参请、说诨经、弹唱因缘。三、讲史书。四、合生、商谜(附说诨话)。”第二种以陈汝衡和李啸仓为代表,认为宋代说话有小说、说经、讲史书三家,其中小说包含银字儿、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说铁骑。第三种以王古鲁为代表,认为宋代说话四家:“一、小说。二、说铁骑儿。三、说经、说参请、说诨经。四、讲史书。”[10]
后来学者对此问题亦多有研究,田冬梅、张颖夫在《论鲁迅先生关于“宋代说话”分类之误》中质疑合生、商迷的分类,他们认为《梦粱录》对说话艺术的记载比《都城纪胜》要更为详细,《梦粱录》把“合生”二字删掉了,并不是《梦粱录》的作者对《都城纪胜》存在误解之处,而是有意为之,鲁迅先生对宋代说话艺术的分类是《梦粱录》存在误解而导致的,不应该把“合生”和“商迷”列入一类或者把“商迷”排除在“说话家数之外”,“宋代说话”四家应为小说、谈经、讲史书、商迷四类,“合生”是“小说”中之一种。[11]2002 年,冯保善在《宋人说话家数考辨》一文中认为宋人的说话应当不下十家之数,并列举有小说、讲史、说经说参请说诨经、说三分、说五代史、合生、商迷、说浑话、诸宫调、唱赚覆赚、弹唱因缘。[12]2007 年,冯保善《宋人说话家数再辨》一文中又补充了说铁骑儿和学乡谈。并且他认为说铁骑儿是以民族战争中的英雄为主体而不是以一朝一代为主体的,学乡谈的内容“盖学各方方音,以说某事,而以诙谐取胜”。[13]2017 年,王齐洲、陈利娟在《宋代“说话”家数再探》提出了新的宋代说话技艺的划分方法,即以经、史、子、集四大类来划分“说话”类别。他们认为说经、说参请、说浑经等类于“经”,演史、说三分、说五代史等类于“史”,小说、铁骑儿等类于“子”,合生、商迷、说诨话等类于“集”。[14]至于如何分类,各家各派多有分法,但现在公认无疑义的为说经、讲史、参请,有疑义的为合生。小说又名银字儿。银字在唐代是一种乐器,由此可见小说与说唱、戏曲有密切的关系,包括婚姻爱情、神仙灵异、传奇异闻、公案、发泰、市井武侠等。说史,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宋代又称说铁骑儿为专门讲说宋代民族战争的故事。说经,演说佛书,说参请当与参禅有关,更有以语言配合动作,一棒一喝警醒世人者,常带有戏剧性和喜剧性。[15]
台湾地区的曾永义教授在其《曾永义学术论文集》一书中将两宋勾栏瓦舍中的说唱技艺做了更详细的概括,分讲史(说三分、五代史)、小说、诸宫调、合生(合笙)、浑话、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说参请、学乡谈、弹唱因缘、唱京词、唱耍令、唱拨不断、说药、缠达、赚、覆赚、崖词等二十种。[16]
(二)宋代说话艺术对于戏曲发展的作用研究
马美信先生在《宋元戏曲史疏证》中论述了说话对戏曲的影响,共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说话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宋人话本和官本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彼此袭用的题材,据可考者,约三十多种。如官本杂剧《莺莺六幺》,当演崔莺莺与张生情事,宋话本有《莺莺传》,它们都来源于元稹的《会真记》。小说与戏曲题材的互相袭用,其影响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既有戏剧据小说而改编,也有小说据戏曲而改编。总的来说小说对戏曲的影响比较大。
第二,戏曲的体制受到说话的影响。中国小说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开篇往往先把主要人物的姓名、籍贯、经历以及家庭情况等作一番介绍,话本也是如此。元杂剧末尾有“题目正名”,用四句诗来概括全剧的主要情节,如王实甫《西厢记》:“(题目)小琴童传捷报,崔莺莺寄汗衫。(正名)郑伯常干舍命,张君瑞庆团圆。”这种形式也是从话本中吸取来的。话本小说有入话、头回,开头或用几首诗词发表议论,叙述背景以引入正话;或用一段小故事,从正面或反面映衬正话。入话、头回,相当于《醉翁谈录》所说的“小说引子”,明人也称之为“引首”“请客”“摊头”,其作用是在正话开始前招引听众,安静场子。宋杂剧有“艳段”,“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其性质与头回相似。金院本专有“冲撞引首”一类,也是在正戏开始前的简短表演。
第三,在叙述方法上,戏曲也有借鉴说话之处。戏曲和小说虽同是叙事文学(艺),但在叙事方法上有明显的区别。说话一般采取第三人称全知式叙述,戏曲则是采用代言体的表演方法。然而中国传统戏曲经常采用第三者的叙述来介绍剧情和人物以弥补舞台演出的不足。《琵琶记》第三出开场,通过“末”扮的牛太师府中院子之口,详细地描述了牛府的富丽堂皇,牛小姐的美貌娇艳,带有明显的说话色彩。这些内容是舞台上无法表现的。在元杂剧中,写到两军交战的场景,也不是在舞台上正面表现,而是通过探子之口叙述出来,这也是小说的表达方法。[17]
解玉峰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今读》一文中对说话技艺对戏曲发展的影响有着更深一步的理解,他认为中国戏曲真正形成的标志是角色“体制与讲唱故事的结合”,说话艺术以讲唱方式去表演故事的普及是戏曲形成的基本条件。[18]
2019 年,吕茹老师在《叙事时间的一致与转化:话本小说与戏曲的互动》对相关问题做了比较新的探索和研究。[19]她从叙事的角度出发,认为话本小说与戏曲的叙事时间具有共通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话本小说和戏曲作品普遍采用直线叙事的方式;第二,话本小说与戏曲作品的题材相互借鉴,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呈现相似的内容。究其原因,一是受史传文学叙事模式的影响;二是在话本小说与戏曲发展的过程中,二者在“叙事源流、文化语境、审美趣味”方面具有相互渗透性。
台湾大学曾永义教授在《曾永义学术论文集》一书中概括了两宋勾栏瓦舍中的乐舞、歌唱、杂技、说唱、戏曲、偶戏六类技艺,并认为这些技艺在两宋时期发达到自组班社共襄盛举切磋技艺的境地了;而这许多发达的技艺,可以说都是构成南戏北剧重要的因素,尤其大型说唱文学和艺术诸宫调、覆赚的成立,更提供了南戏北剧丰富的题材和音乐的滋养,如果没有它们在瓦舍勾栏里相互结合孕育,南北戏剧也就无法成立。[20]曾永义教授还在《戏曲源流论》一书中认为,中国地方戏曲的形成与发展的路径除了“由小戏发展而形成”一条最为主要外,尚有“由大型说唱一变而形成”与“偶戏为基础而形成”两条路径;他考察了我国历代剧种,其符合“大戏”规模,标示“戏曲形成”的“南戏北剧”,莫不经由小戏吸收说唱文学壮大而成。[21]姚民治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同源互补论》一文中认为:“说唱文学中丰富多彩的说唱技艺、绘声绘色的语言描摹也都给予正在形成中的戏曲以极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讲唱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故事,曲辞则为戏曲提供了歌唱的形式。”[22]
(三)傀儡戏的起源及其与戏剧的关系问题研究
关于傀儡戏的起源,现代学者刘琳琳在《傀儡戏起源辨》中对傀儡戏起源问题做了相关论述,她对学界的众多论述比较严谨的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源于傩仪中的方相之舞,此观点的代表学者如孙楷第先生;第二种认为它的前身是由陪葬之俑发展而来的丧家乐;第三种则认为中国的傀儡戏根本是源自印度、韩国。但刘琳琳从傀儡的功能与出现时间、美学特征、民间记载三方面反驳这些观点,丧家乐的说法也与后来演滑稽内容相矛盾,丧家乐应只是傀儡戏的表演内容之一,来自印度更无材料支持,印度的佛教思想和内容丰富了傀儡戏的内容罢了。[23]
至于宋代傀儡戏与戏剧的关系问题,马美信认为宋代的傀儡戏已经能演较为复杂的故事,其题材大多数来源于说话,具有很强的戏剧性;从表演来说,傀儡戏“或作杂剧”,有各种技艺性的演出,“或如崖词”,具有音乐、说唱的成分,这都说明傀儡戏与戏剧十分接近,两者的关系很密切。马美信还举出孙楷第《傀儡戏考原》中的观点,孙楷第认为宋元以前无戏剧,而宋元以来的戏文、杂剧出于傀儡戏和影戏,孙楷第的这种说法未能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24]叶明生先生在《傀儡戏与地方戏关系考探》一文中认为“傀儡戏为歌舞百戏之先声”,当然这并不是认为一切地方戏都是傀儡戏派生出来的,叶明生认为傀儡戏与地方戏的关系是“共时态发展”,是竞争又互补的关系。[25]江玉祥在《皮影、木偶戏的传承与保护》一文中引孙楷第先生的观点,认为木偶戏与皮影戏同属于傀儡戏,从影像上看,木偶是立体的,皮影是平面的。[26]曾永义先生在其《曾永义学术论文集》一书中将两宋瓦舍勾栏的技艺分类概括为乐舞、歌唱、杂技、说唱、戏曲、偶戏六大类,其中戏曲指杂剧(包括艳段、正杂剧二段、散段杂班),偶戏中包括悬丝傀儡、杖头傀儡、药发傀儡、肉傀儡、水傀儡、影戏、乔影戏、手影戏等八种。[27]可见,曾永义老师将傀儡戏、影戏合称为“偶戏”,又把它们和宋代杂剧区分开来。曾永义先生在其《戏曲源流新论》一书中认为近代“大戏”形成的路径中很重要一条就是“以偶戏为基础而形成”。[28]曾永义老师的这种观点,肯定了偶戏产生以来对戏曲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且更进一步论证近代的一些大戏是由偶戏发展而来的。
(四)影戏的相关问题研究
王国维先生把影戏单独作为一个因素来论述其对戏曲发展的影响,而上文已经谈到孙楷第先生认为影戏属于傀儡戏。刘琳琳女士在《宋代傀儡戏研究》中认为影戏从物理特征上来看为“平面傀儡”,属于傀儡戏的一种,而且宋代是影戏的发明期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但是影戏又是一个特例,其历史渊源、发展轨迹和艺术美学特征是完全自成一体的,所以影戏是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因此她认为在谈傀儡戏对戏曲的发展时,如孙楷第先生认为的傀儡戏与影戏起相同或相似的作用是不恰当的。[29]前文已经提到了台湾大学曾永义教授的观点,曾永义先生在其《曾永义学术论文集》一书中将影戏、乔影戏、手影戏纳入“偶戏”中,曾老师将傀儡戏、影戏合称为“偶戏”,又把它们和宋代杂剧区分开来,这是对傀儡戏与影戏关系问题研究上的一大进步。[30]
马美信认为影戏演剧的底本也称之为“话本”,且与说话中的“讲史”同,说明影戏受说话影响已不是简单的歌舞杂技表演,而以故事比较复杂的讲史作为主要内容。[31]2020 年,朱恒夫发表的《中国皮影戏的历史、现状与剧目特征》一文,认为北宋时影戏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这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演唱不再随意,而是遵照着脚本的内容。第二,已经形成了一批专业的艺人队伍,还分为“影戏”与“乔影戏”两个品种。第三,有了人物的脸谱,并按照性格、品性饰以图案色彩。第四,演出水平极高,能使观众忘乎所以,以假当真。到了南宋时期,影戏更是进入“前所未有的辉煌时代”,常常表演宋金对峙的故事。[32]此时的影响十分广泛,已经近似于戏剧了。李跃忠在《宋代影戏剧本探微》中认为,宋代影戏演出有说有唱,而且要“摆布”影人,影戏是把唱功放在第一位的,影人的动作表演则是放在第二位的。[33]
(五)舞队与戏曲的关系问题研究
马美信在《宋元戏曲史疏证》中认为王国维先生对舞队与戏曲关系的认识尚有偏颇,他认为舞队与戏剧的差别并不在是否有固定场所演出,南戏和北杂剧多有穿州撞府作巡回演出者,然不能说南戏和北杂剧不是真正的戏剧,而且舞队虽有演出故事者,但其所演故事十分简单,虽有角色的装扮,却不是用代言体演出,故尚未脱离歌舞戏的范畴。[34]
杨子在《宋代队舞演出场合及其用乐初探》中认为:“宋代宫廷队舞已有固定的表演程式,其结构可概括为三段式,宋代队舞的音乐基本沿袭唐代歌舞大曲,乐队配置以节奏热烈的吹管乐和打击乐为主要伴奏乐器。同时,宋代队舞表演加入戏剧性成分,为‘以歌舞演故事’的明清戏曲艺术奠定基础。”[35]
三、小说杂戏与戏曲关系之我见
在《宋之小说杂戏》一章中,王国维先生从“真戏剧”的概念及其要素入手,对小说杂戏与戏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在《宋之小说杂戏》这一章里,王国维先生主要是从演故事的要素入手的。王国维先生所说小说、傀儡戏、影戏、三教、讶鼓、舞队都是以“演事实为主”,小说为讲唱文学是口演,傀儡戏与影戏已形演,三教、讶鼓、舞队以人演。本章就是从“演事实”这条路径上探寻真戏剧产生的源流的。
至于宋代小说杂戏及其与戏曲的关系问题,后代鲁迅、孙楷第、马美信等学者皆有补充论证,而中国台湾学者曾永义老师是目前做得最详细严谨的。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曾永义老师提出的“大戏”和“小戏”的概念,要站在宏观方面了解曾永义老师对戏曲学的构建,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宋代小说杂戏及其与戏曲的关系问题。关于“小戏”与“大戏”的概念,我们可以参照曾永义老师《戏曲学》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所谓“小戏”就是演员合歌舞以代言演故事,包括傩仪小戏、唐参军戏、宋杂剧院本、民间乡土小戏等。“大戏”是对“小戏”而言的,就是演员足以充任各门角色扮演各种类型人物,情节复杂曲折足以反映社会人生,艺术形式已属综合完整的大型戏曲之总称。曾永义认为中国戏曲大戏是在搬演故事,以诗歌为本质,密切融合音乐和舞蹈,加上杂技,而以讲唱文学的叙述方式,通过演员充任角色扮饰人物,运用代言体,在狭隘的剧场上所表现出来的综合文学和艺术。可见综合文学和艺术的大戏是由故事、诗歌、音乐、舞蹈、杂技、讲唱文学叙述方式、演员充任角色扮饰人物、代言体、狭隘剧场等九个元素构成的。至于“大戏”与“小戏”的关系,曾永义老师认为“小戏”是“大戏”的雏形,“大戏”是戏曲艺术的完成。[36]通过比对王国维先生对“真戏剧”的定义与曾永义老师“小戏”“大戏”的概念,可知曾永义老师在戏曲学的建构上要更加清晰严谨。基于宏观概念的了解,我们再依次叙说关于宋代的说话、傀儡戏、影戏等问题。
(一)宋代说话艺术与戏曲的关系
宋代的说话艺术情况,王国维先生认为分小说、说经、说参请、说史书四类。马美信先生在《宋元戏曲史疏证》中对宋代说话艺术的情况作了补充,论述了鲁迅和孙楷第、陈汝衡和李啸仓、王古鲁这三家的观点。后来学者也多有补充论证,包括田冬梅、张颖夫、冯保善等人;王齐洲、陈利娟提出了“经史子集”四分法比较耳目一新。关于这个问题论述最全面的还是曾永义先生。曾永义不仅分析了两宋的说话艺术,而且把两宋勾栏瓦舍中各种技艺进行了分类,详细地呈现给我们。上文已经对其观点进行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至于说话艺术与戏曲发展的关系问题,王国维先生认为讲史和小说对戏剧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题材与结构上的。马美信先生在此基础上认为说话艺术对戏曲的影响分为三方面,即说话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说话艺术影响了戏曲的体制、戏曲借鉴了说话艺术的叙述方式。解玉峰先生则认为讲唱故事的流行和普及是戏剧形成的前提。吕茹老师进一步分析了说话艺术与戏曲叙事方面的影响。以上观点皆是围绕题材、结构、叙事方面来论证的。除了这些以外,曾老师则更加重视戏曲的音乐性,他认为讲唱文学对戏曲的发展,还包含了更多的音乐滋养,而且特别强调了大型说唱文学、艺术诸宫调、覆赚对戏曲形成的促进作用。
(二)傀儡戏、影戏、戏曲的关系
王国维先生在论述傀儡戏与影戏时是分开论述的,认为傀儡戏与影戏都是以演故事为事,但是傀儡戏比影戏更近似于真戏剧。后代学者对这种观点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傀儡戏,孙楷第认为在宋元以前无戏剧,而宋元以来的戏文、杂剧出自傀儡戏和影戏;马美信认为宋代的傀儡戏从内容上与表演上与戏剧十分接近,两者关系密切;叶明生认为傀儡戏与地方戏的关系是“共时态发展”,是竞争又互补的关系。
对于影戏,马美信、朱恒夫、李跃忠论述了宋代影戏的繁荣状况。孙楷第先生认为傀儡戏与影戏对戏曲的影响起相同或相似的作用;刘琳琳认为影戏从物理特征上来看为“平面傀儡”,属于傀儡戏的一种,但是影戏又是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所以她认为在谈傀儡戏对戏曲的发展作用时,如孙楷第先生认为的傀儡戏与影戏起相同或相似的作用是不恰当的。至于傀儡戏与影戏的关系、两者在两宋勾栏瓦舍中的地位以及两者对戏曲发展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论证最系统的是曾永义老师。
曾永义认为傀儡戏与影戏(包括影戏、乔影戏、手影戏)都属于“偶戏”,但是“偶戏”与杂剧戏曲是区分开来的。偶戏系统属于勾栏瓦舍中六大技艺的一种,而且曾永义进而考证认为这些民间技艺极为发达。偶戏与乐舞、歌唱、杂技、说唱、戏曲六类技艺,他们之间相互结合孕育,对南戏北剧的滋养是具有前提性的作用的。
(三)宋代小说杂戏余论
王国维先生可能受限于当时的研究材料不足,对宋代小说杂戏与戏曲的关系问题还不够详细,难免会有疏漏之处。台湾大学曾永义先生凭借自己的博学与严谨治学的精神,构建了较为系统性的戏曲学。对于宋代小说杂戏方面,曾永义还举例论证了勾栏瓦舍中的乐户艺人数量庞大、各派皆有不少名家,在技艺方面甚至无所不能;南宋的书会亦是相当普遍,为民间表演艺术家亦即乐户技人编写大量的演出底本,诸如剧本、话本、曲词、隐话等。[37]这是在小说杂戏方面更加系统性的认识,除了说话杂戏等技艺的发展,我们还需要关注到人才的培养和剧本来源的问题。当然,曾永义老师也告诫我们还要认识到其他技艺对戏曲发展的影响,即前文所引论曾永义老师概括的勾栏瓦舍中的六大技艺。因为说话艺术、傀儡戏、影戏等在社会中不是孤立发展的,他们存在于两宋众多技艺之中。众多的技艺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孕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小说杂戏对戏曲的发展影响较大,但绝不能忽视其他技艺的影响,这也是曾永义老师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