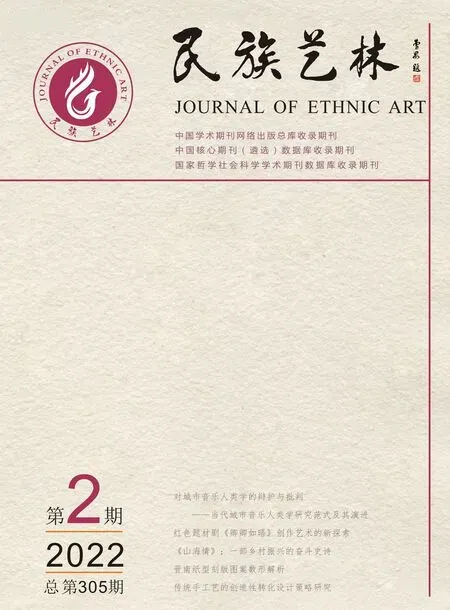重读“孤岛电影”《木兰从军》:一种互文性视角
2022-11-23何东煜
何东煜
(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 海淀 100875)
作为舶来品的电影,在抗战之前的渐进探索中摸到了扎根中国本土发展的自我肌理。随着全民族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电影产业也受到了强烈冲击,这一时期上海租界地区形成了“孤岛电影”景观,其中,1939 年上映的古装片《木兰从军》因其巧妙的叙事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本文试从“互文性”角度重读该片。
一、互文性理论与电影研究
“互文性”概念由法国文学理论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20 世纪60 年代最先提出,亦称为“文本间性”。其原述为:“任何一个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1]换言之,任何一个文本都与其他文本可以发生关系,文本之间相互关联、参照、渗透,并形成一个开放的网络结构。文本意义的产生由互文性概念理论的提出而打破了封闭格局和自足阐述,文本与其他文本主动关联而生产意义、与文本之外的社会环境等相互关联,由此文本意义变得流动而多元。真正将互文性理论更进一步推向可实践与操作研究的人是热拉尔·热奈特,在已有互文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跨文本关系”学说。“热耐特的理论建构以其清晰性和可操作性极大推动了后来的互文性研究,这个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受到他的启发,每一种专题都可以作为一个局部纳入他设定的这个理论框架。”[2]其跨文本性学说构成的五种形式是:文本互涉、后设文本性、近文本性、主文本性、超文本性,为研究具体文本提供了强烈的实践性支持。
今天电影研究中的互文性分析也愈发引人关注。网络发展和信息爆炸的当下,电影因视听综合的本体特征而产生了异乎于文学作品等传统文本的传播效果。“对电影研究者而言,如何通过分析一部具体影片与整个电影文本世界的关系来分析电影、把握电影的表达策略也特别具有启迪意义。”[3]绝大多数的电影文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互文,“电影文本与文字文本(文学、戏剧、戏曲)的互文性、同一类型或题材的影视作品之间的互文性、同一导演或演员的作品之间的互文性”[4]等,都是互文性理论应用在电影分析与批评中的常见角度。
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与文学产生最亲密转换生产关系的当数第四、五代导演的诸多作品,但实际上,20 世纪80 年代伊始第三代导演的创作就已经开始将重心转向文学名著的改编。这一事实与西方互文理论的发展和传入我国在时间进程上脚步基本趋同,我国电影互文性角度研究的诸成果多数关注的焦点也在现当代文学与电影作品改编上。一种学术理论的提出、成熟并成为一种研究范式进而传播普及,反证着其适时性、科学合理性。而用后来的理论研究先前的文本,则会对同一文本发掘出更多的解读,也能更有说服力地印证该理论的实用性。对中国早期电影的研究中少有从今时互文性角度出发的热切关注,但中国早期电影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孤岛电影”古装片则属文本与文本外界互文的典型代表。从互文性角度出发,重读此类影片中的代表作品,可以更加清晰认识该类影片在电影史上的位置和特别之处,也可以对当下电影的现实创作产生一定思考和启发。
二、“孤岛电影”与古装片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本土民族电影产业受到了强烈冲击,最明显的变化是电影创作与产业格局的改变。抗战前期,中国电影产业主要集中于上海地区,上海也因为电影的发展被世人称为“东方好莱坞”。抗战爆发后随着政权控制的地区分化,中国电影格局也随之变成三个区域多个中心,其中以上海租界电影为代表。全面抗战开始时,欧美诸国并未对日宣战,多持中立态度,因此日军于1937 年12 月侵占上海之后,碍于外交原因,并未进入法属租界及公共租界,上海租界地区周边已被日军侵占,沦陷区如汪洋大海,租界置于其中暂得安宁,就像一座孤岛,直到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在上海租界地区集中创作、生产、放映的电影,又被称为“孤岛电影”。
战争的爆发、时局的艰难等因素,让上海地区的诸多电影人选择离开,事实上留在租界在日军包围之中的电影人数量并不乐观,但他们依然选择坚守电影阵地继续斗争,并在重重困境中寻找到了属于这一特殊时期特殊处境中电影创作和发展的道路,创作出了一批反映观众现实诉求、实现救亡图存憧憬的佳作。
在此时期的诸多影片中,古装片占有较大比重并取得了一定成就。整个“孤岛”时期电影产量中古装片约占三分之一,共80 余部,尤其到20 世纪30 年代末,古装片的创作热度达到峰值,其中代表作品有《貂蝉》《明末遗恨》《木兰从军》《李香君》《关公》《孔夫子》等。20 世纪20 年代末曾流行一时的古装片重新风靡,当然,“孤岛”时期的古装片热潮,是多方因素共同影响促成的。“在‘孤岛’的电影公司不能拍指名道姓的抗日片,而只能在‘古装片’名目下,借古喻今,抒发爱国情感和国破之痛。”[5]上海被日军侵入之后,虽然电影生产集中在租界之内,但受到高压电影检查管控的束缚。伴着审查和剪刀政策的还有对爱国影人的绑架暗杀等生命威胁,所以此特殊时期上海电影人们借用古代故事和商业电影的外表,隐含爱国救亡的现实意识,鼓舞观众对战争胜利的希望,坚定观众抗击外敌的信念,灵活巧妙、含蓄地表达和传递抗日思想。
除了时局需要以外,此时古装片的流行兴盛也是市场消费和审美层面的观众诉求。20 世纪20年代末大量古装片、武侠片以及神怪片竞相摄制,发展到顶峰时实际成为了一种恶性的商业竞争:一方面古装片多以历史为壳,实则“来演绎‘才子与佳人’或‘英雄与美人’这样一种传统叙事母体”[6],并无教育社会、观照现实的价值;另一方面,武侠片和神怪片的过分夸大,使得观众不乏少数沉迷其中,成了麻醉和逃避现实的幻剂。同时由于商业竞争的主导,电影质量良莠不齐,甚至拼凑炮制之品都不少。那“孤岛”时期为何古装片兴盛也被说是市场消费和观众审美的诉求呢?租界地区与外围日军占领区隔离,面对战争的焦虑惶恐心理需要宣泄,人们没有其他娱乐活动和消费之地可去,加上战时一系列宵禁政策和上海市民的文化娱乐传统,多种因素都指向了电影消费,戏院成为这一时期市民文化娱乐的中心。“孤岛”前期民众的家国意识空前强烈,爱国情感和对敌愤慨需要作为文化产品的电影在银幕上相互呼应,借古喻今的古装片(尤其是那些改编自耳熟能详的中华历史故事的影片)可以满足观众的这种观影期待。再者,租界被日军包围,外国电影无法销入,客观上市场空间为民族电影尤其是受创作者与观众共同青睐的古装片提供了充分的孕育土壤。综上所述,古装片可谓是“孤岛电影”的主力军。
三、影片《木兰从军》互文性分析
《木兰从军》是“孤岛”时期上海华成影业出品的古装片,1939 年公映,由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执导、“南国影后”陈云裳主演,该片上映后轰动一时,“连映85 天,创下新纪录”[7]。影片讲述了边关因外敌番兵入侵战火涌起,老军人花世荣被朝廷召回参军,花家大儿已故、小儿童龄,孝女花木兰不忍看年老体衰的父亲受此苦罪,毅然主动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从军途中与刘元度逐渐熟络,在战场上共同杀敌,深入番兵腹地刺探敌情,回营铲除叛国军师、歼灭番兵。后婉拒朝廷奖赏只求回家省亲,荣归故里的木兰换上女装众人吃惊,最终与刘元度喜结连理。
时至今日,提及“孤岛电影”和民国电影古装片研究,以及民国电影批评史观、战时电影“家国意象”研究等,都无法绕过这部电影,可见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位置。导演卜万苍、主演陈云裳后期从影之路的变迁,也让他们相较同期其他影人略显黯淡,甚至有研究提及本片,将作为导演的卜万苍对本片的贡献忽略,将影片成就皆归功于编剧欧阳予倩之身。笔者将从互文性视角切入,重读这部“不可忽视的传世经典”[8]。
(一)改编:故事与时代
热奈特提出的“超文本性”可以用于文字文本与电影文本的互文性分析上,即“在文学文本作为素材文本向影视文本转换时,我们可以将其纳入到比较研究的范畴中来,将重点放在因改编而引起的两篇文本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转变过程之中”。[9]其中,内容即故事,形式即话语。
“木兰从军”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个典故,花木兰也是中国民间传说中最脍炙人口的女性英雄形象之一。最早文学文本出自“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中的北魏民歌《木兰诗》”[10],“至晚到唐代,木兰的故事已广为流传”[11]。电影传入中国后,该故事被多次搬上银幕,创作时间上从20 世纪20 年代跨度至今,空间上上海、香港、北京,以及美国等不同地区、国家均有涉及。卜万苍版本的《木兰从军》能如此耀眼影史,基于互文性分析应该先从故事讲述的年代与讲述故事的年代说起。
文学文本《木兰诗》出现于北魏年间,即五代十国——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不足四百字的叙事诗从当时众多民歌中留存,侧面可以看出人们对战争的抵触和对安宁的呼唤。《木兰诗》中写道:“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战争之残酷寥寥几句已然显示,万里跋涉,边疆严寒,衣食不饱,奔波不停。如此动荡的大背景大时代,如此漫长的十年征战,聚焦于花木兰一个女性角色身上,浪漫之余,实则更显悲壮。故事讲述的年代因文学修辞的必要,对残酷的展示并不直观,但可以联想若今日我们换位角色成为木兰,如此经历是否以几句浪漫悲壮之诗就能全部呈现?电影《木兰从军》上映之时,正值侵华日军攻陷南京、上海(除租界),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百姓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加之此前几十年诸多不平等条约下的列强蚕食,中国的国家前途像黑暗中摇曳的微弱火光一样岌岌可危,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区,浮萍一般没有生机。《木兰从军》虽然没有今天电影拍摄时的精致置景可以让观众一眼将故事时代归于历史的准确坐标,但仍然可以通过画面、服饰、道具、台词、字幕等明确其故事讲述的年代与此时讲述故事的年代(1939 年)如此相像——战火涌起、外敌入侵、国家危亡之际。两个时代时间不同,处境却如此相同契合产生互文,加之对文本的预先熟悉和期待心理,成就了观众对该片当时极大的认同。
编剧“欧阳予倩提出,当时上海沦为‘孤岛’,不宜摄制明显地宣传抗日的片子,应该采取借古喻今的手法,含蓄地表现花木兰智勇双全、杀敌卫国的故事”[12],于是在遵照原故事的前提下,对照抗战社会现实语境进行了改编。并且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孝”文化做了文章,将花木兰的“忠”置于“孝”实现的先期语境之中,达成实现国家责任与家庭责任的统一,“影片中木兰‘忠孝两全’的美德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13],使得“孝”具有了超越家庭伦理范围的更深刻的价值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个人的终极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构成国家的基本细胞,英雄的故事在银幕上起点于承担家的责任,在观众心中可以引发强烈的共鸣,家国意识得以同时构建。将国家民族命运回归到现实中与每个个体家庭的命运息息相关,观众所获得的冲击和感触才越直观、深刻。
借古喻今的转换性叙事策略除了整体上故事背景观照现实,细节方面也可以一一对应。电影中外敌番兵其实隐喻的是日军,番兵入侵边境实则比喻日军入侵中国。除了国家敌人,花木兰周边人物的特征也可与抗战现实背景下租界的各类人群对应,例如卖国军师影射着汉奸,刚毅的军队元帅隐喻抗战前线的军队将领、李家村为难花木兰的“混混”是现实里部分不关心国家命运的麻木民众等。去掉时间空间以及人物名字的限制,故事主题的时效解读就是指抗战背景下需要民众“快把功夫练好它,强盗贼来都不怕,一起送他们回老家”(片中民谣唱词),全民挺起胸膛保家卫国。同时,本片除了爱国民族意识表达外,在电影结尾处,以敌军诈降为重点情节呼应现实,让民众警醒侵华日军的东亚共荣圈谎言,不要被日伪奴化教育所毒害。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除典故原型之外,《木兰从军》较之《木兰诗》这一文学文本有了较大的改编,这是编剧欧阳予倩的贡献。原文学文本的故事主线木兰从军、建功立业、回家团圆,并没有涉及爱情情节。在电影《木兰从军》中,编剧加入了刘元度这一男性角色,最终与花木兰在一起获得圆满结局。“孤岛”时期之前的上海,属中国最前沿民风开化的地方,“摩登”成为上海和上海人现代生活体验的代名词,才子佳人、鸳鸯蝴蝶的爱情故事曾在银幕上盛极一时,成为观众欲望投射的产品。尽管此时(1939 年)的上海已成“孤岛”,但在战争中个人建功立业这一原文学文本母题之下,加入爱情故事,更与彼时观众长期形成的观影心理、审美习惯相契合——要想安居幸福必先平定战乱驱除外敌。这是内容情节上,电影较原文学文本的改编之处,其合理性在于与当时观众长期的审美志趣相契合。
同时,除了故事与时代的互文性外,就上海影人这一大的集体来说,本片也产生了互文关系。前文关于“孤岛电影”的概况中已述,日军占领上海后对上海影界实施了极为高压的检查管控政策,爱国影人甚至会因为电影中的政治表达而受绑架迫害,和战争中的普通民众一样,影界也急需《木兰从军》这样一部作品促成自我意识的唤醒、表达和坚守,它凸显着“30 年代初以来所形成的关于时代呐喊的主流通俗剧范式的中国电影转换成借古人的言行而浇国人当时‘爱国情怀’的块垒”[14]。所以,《木兰从军》内容情节与原文学文本、社会现实、影界状态、平民呼声等均有互文性关联,造就了其“旧酒装新瓶”依旧能芬芳引人的效果。
(二)话语:意义的生产
同样的故事,话语方式的改变,生产出新的意义。简单来说,话语即怎么讲故事,关注其表达形式和意义生产。文学文本尤其是中国早期文学文本,多数以叙述为主,作者将主人公所做所经历之事转述给读者,读者无法获得所有的细节。《木兰诗》从诗歌体量来看为长篇叙事诗,但和后来其他文体相比,字数还是极为有限,将跨度十年的木兰从军故事放在几百字内,能呈现的细节则少之又少。电影本体的特征是视听性,即与文字叙述最大的不同之处——演示。通过出场人物的行动表现,尽可能多地直观展现给观众大量的细节,使观众观感眼见为实、耳听为实。同时,电影叙事机制下又会生成新的意义,与其他文本产生互文性。
电影叙事话语体系主要包括取景构图(拍摄)、场面调度(表演)、画面连接(蒙太奇)等,其中场面调度和取景构图是更具演示性的重要形式。本片导演卜万苍,并非文人转行从事电影导演,20 世纪20 年代卜万苍最早“师从美籍摄影师哈里·哥儿金学习摄影,其间作为摄影拍摄了《饭桶》”[15],此外“则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向家庭伦理剧靠拢,同时在影片中发挥出摄影的优势,注重影片画面的意境美”[16]。摄影出身的卜万苍在后来的所有作品中都非常重视以电影本体即画面为基础的叙事能力。电影《木兰从军》与早期古装片不同,在“孤岛”与外界绝缘、无法充分展现战争外景的条件下,尽管大部分镜头均于室内摄影棚拍摄,却利用摄影机机位的调整、景深镜头、构图变化等技巧,让故事呈现更具观赏性,同时产生互文意义。
例如影片展现花木兰与敌对关系人物对抗情节时,分切给花木兰的镜头不少采用仰拍机位,表现其勇敢机智;分切给敌对关系人物的镜头——故事开头李家村几个故意刁难花木兰的村痞、从军路上两个意图调戏花木兰的兵痞、故事中后贼眉鼠眼的叛国军师等多采用俯拍机位以显示其猥琐渺小。而木兰准备离家从军告别父母之前、木兰在军营里参见元帅、战胜敌人后受君王召见、安定后回家省亲见到父母等伦理化、仪式化场景中,构图多采用均分、对称、稳定的形式。一则传统的故事,其伦理主题上的“孝”与“忠”等都在构图的话语形式中生成互文意义,让观众明了家国一体,与时局互文。在摄影棚有限空间内的置景,则利用房屋门窗框、城墙边沿、卫兵等来区隔空间层次,进行景深效果的营造,并通过此类场景中的人物运动、位置变化,在镜头内完成焦点的转换,给观众不同于传统戏曲舞台的视觉感受。观看感受的真,促使观众形成故事代入感,即在场接受。
一位导演在一部电影作品中的话语方式、意义生产也和其个人的其他作品相互文。早期的卜万苍电影受欧化影响轻松明快,而后关注传统家庭伦理,现实批判意识渐显。日军侵华之后,卜万苍开始向左翼电影运动靠拢,其间代表作品《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都把“民众的苦难和不幸作为聚焦的中心”[17]。卜万苍导演对传统和现实的关系有着敏锐的认知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处理,如在电影《木兰从军》中,在呈现花木兰与刘元度的爱情发展暗线时采用一些喜剧手法,契合着观众的审美习惯,使影片上座率高、观众认同感强。而更为重要的家国意识和现实责任,在其撰写的《我导演电影的经验》一文中便可知晓:“一部优良的电影应该要明确地把握住正确的中心意识的……光是技巧而没有正确的主题固然不成其为艺术,但表现方法的拙劣显然也是艺术的死敌……技巧(形式)和意识(内容)是分不开的……我们要创造一种‘中国型’的电影……我们不能一味学人家,而且学人家的电影,在中国是没有前途的。”[18]
本片饰演花木兰的女演员是有“南国影后”之称的陈云裳,《木兰从军》是她北上上海出演的第一部影片,对花木兰形象的塑造可圈可点,成功的表演使她俘获了上海观众的心。陈云裳精准地塑造出了相较文学文本中花木兰最不同的突出之处:尽孝的前提是尽忠,国家安定小家才能安居,这是与抗战时局最为紧密呼应之处。彼时有评:“她的木兰,开始时的小女儿之态,活泼可爱,替父从军时之正义,及改换军装后的英俊,言谈举止、对话的姿态都达于臻化之境界。”[19]
本质上,文学和电影对人物塑造的方式有根本的不同。陈云裳生于广州,拍摄《木兰从军》时正值18 岁芳华,少女时期她曾“学习昆曲、京戏、粤剧,以及歌舞,还学会了游泳、骑马、网球、绘画以及各种礼仪,堪称全面发展。”[20]在前文讲到,《木兰诗》文学文本是源于北朝民歌的,原文描写和文学的地域性想象可以让我们脑海中对花木兰形象有一个轮廓勾勒:她高风亮节、身怀武艺,深入敌后、有勇有谋,外貌、行动以及性格一定具有北方人的英气和洒脱。但这一想象的人物轮廓无法落实更多细节,陈云裳的扮演满足了我们的想象,这依旧得益于电影的叙事话语机制。歌舞戏曲的功底让她在片中展示舞剑、骑马、狩猎等多个场景时英姿飒爽一气呵成;姣好的面容亦满足了观众对女英雄的外貌想象。这些影像的呈现都与原文学文本互相指涉,利于观众接受。陈云裳出生成长于广州,虽然学习过普通话,但片中饰演花木兰时所说台词今日听来依旧南方口音浓重,这与文学文本《木兰诗》中花木兰的人物地域归属设定不同,但却与当时观影现实互涉——上海话亦称吴侬软语,上海本地女性说起普通话想来必然和陈云裳一样有南方口音,和观众的地缘互涉增进着观众对影片人物形象的认同。
在《木兰从军》中,编剧欧阳予倩、导演卜万苍难得设置了国家与个人两条交织的线索。个人情感方面,陈云裳将20 世纪30 年代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追求独立自主的时代新女性气质赋予银幕上的花木兰。片中花木兰对刘元度明明也有好感,但却在战争结束之前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不依附刘元度解决各种遇到的挫折困难,尽全力动用智慧自己解决,这样一个消解了对英雄固有的男性性别认知限定的女性形象,在战时的上海更有现实意义。而同时换上女装的花木兰又是如此美丽动人,和上海的摩登、上海女性的摩登、观众心中对女性的摩登想象相互指涉,使本片虽是古装片却依旧有着浓浓的时代气息。影片结尾木兰省亲,母亲说提亲下聘的人已经好多了,问木兰嫁哪家时,花木兰说我已经定下来了,母亲见刘元度后欣然同意,未加任何反对,最后二人终成眷属。中国古代的伦理观念中父母之命不可违,怎会有与片中一样的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呢?这一情节和陈云裳塑造的独立自主的花木兰形象一样,是改编后的结果,同样与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思想解放、婚恋自由这一观念互相指涉。20 世纪30 年代中国的进步观念,无论大到国家民族大义,还是小到个人恋爱观念,都在片中由陈云裳扮演的花木兰一一表演展现,“她积极进入公共空间,要‘一来尽孝,二来尽忠,得胜回来让人知道,女孩子也能光大门楣’的现代女性意识”[21],形成强烈的现实互文性,花木兰这一形象“既令人仰慕,又归于平凡,成为政治宣传与社会动员的女性英雄符号”[22]。
总之,借助传统历史故事,对文化观念中适应时局的部分加以互文性改造和放大,并从电影艺术角度对视听语言、仪式性场面、情感因素等加以用心塑造,让《木兰从军》获得了观众一致的口碑认同。
四、结语
“孤岛时期”结束后,上海全部沦陷,民族电影随着战争的紧张和市场的竞争,失去了“孤岛”前期的旺盛生命力和巨大影响,但是,以《木兰从军》为代表的一批与现实互文的优秀作品依旧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意义的构建生产,可以从不同时空维度来简单小结:对“孤岛时期”来说,首先,以《木兰从军》为代表的古装片成熟的互文性叙事规避了当时电影审查的政治风险,正是因为叙事策略的巧妙性,才得以支持数量庞大的作品问世,并以媒介文化产品特有的传播速度和力量最大限度调动着民众的爱国热情。其次,该片“成功引起了一系列历史上中华民族抵御外敌入侵的古典作品改编,使得‘孤岛’产生出一批在娱乐的外衣下伸张民族大义的电影”[23],持续繁荣了电影市场,从产业和消费角度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民族电影产业的基本力量,也促使电影艺术与技术实践不断收获创新。另外,尽管最终上海全部沦陷,但是“孤岛电影”时期古装片形成的特点——与现实互文,对抗战结束以后1945—1949 年间的中国电影创作和生产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为战后电影创作的起步提供了一个较高水准的参考坐标;同时电影作为文化的先锋力量在“孤岛时期”得以发挥,其观照现实教育改良社会民众的自觉和自20 世纪20 年代民族电影初盛时烙入影人、影史骨髓的电影艺术观一脉相承,并延续到战后,诞生了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直面灰暗、反映民众诉求的佳作。
到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谈论中国电影的现实创作时,都应该注意到历史中以《木兰从军》为代表的“孤岛电影”古装片这颗珍珠。当动辄有人争议——电影的社会现实意义在哪里、为何在今天诸多中国电影中作为文化角色的电影似乎是缺位的,或者谈论今日电影为何讲故事的策略技巧依旧生硬等诸如此类问题时,其实我们可以重回影史翻开文本去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