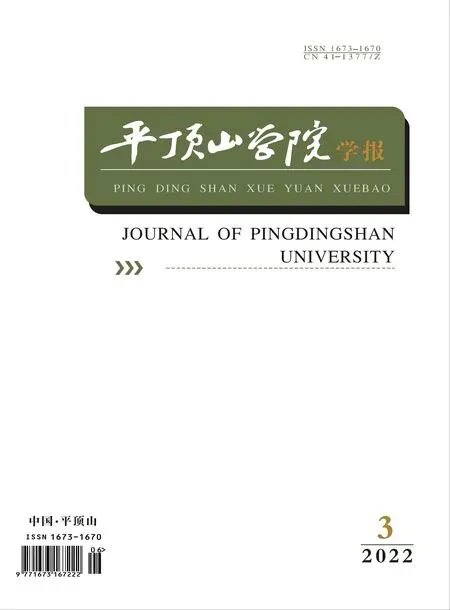封建之义的解构与重构
——以柳宗元和张载为中心
2022-11-23陈佩辉
陈佩辉
(浙江大学 哲学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封建郡县之辨在秦以后历代都有展开,是关乎政治体制选择的关键问题(1)“封建”一词的含义在近现代发生重要变迁,本文所采用的“封建”之义是未经西方概念影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所理解的“封建”。详参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1、69—73页。。柳宗元与张载之辩是封建郡县之辨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抛弃了圣人立制的传统观念,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探究封建制的起源,并在制度设计和制度价值上论证了郡县制优于封建制,全面否定了封建制作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制度载体的意义,解构了封建之义。面对这一挑战,张载调整封建制的具体设计并在新的理论基础上重构了封建之义,有力地为封建制作了辩护。然而,目前学界的研究大都聚焦于柳宗元的解构,对于张载之重建的研究远未充分,更未展开对这一解构和重构过程的考察。因此本文尝试侧重从张载的角度考察封建之义的解构与重构:首先,我们探讨柳宗元对经典中的封建之义的解构及其影响;其次,我们讨论张载如何回应柳氏的挑战以为封建制辩护;最后,我们讨论张载如何通过《西铭》为封建制重建理论根基。
一、柳宗元对封建之义的解构
学界对柳宗元《封建论》的研究汗牛充栋,本节仅就柳氏对封建之义的解构作一简明分析。在展开具体分析之前,我们先借助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来理解经典世界中的“封建”。王国维认为,西周制度的目的在于“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1]454。王国维所言的道德团体,事实上是政治宗法化的天下共同体。其强调封建制以亲亲尊尊贤贤为原则,其中宗法是封建制的核心[1]474,井田和分封也即狭义的封建则是另外两个重要因素。但在西周封建制下,无论是在伦理上还是在政治上庶民都未得到恰当的对待,即使是庶人之贤者也无入仕之途。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这一制度必然会被认为是不公的。注重“至公”的柳宗元对封建制提出了最为深刻的质疑,其《封建论》力图取消封建制的神圣性,并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制是儒家政治理想的载体。
在《封建论》中,柳宗元首先透过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论证了国家在起源阶段必然采用封建制,否定圣人创设封建制。他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2]70柳宗元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出于自我保存的需要人与人之间必然联合成群,而群与群之间为了获得更多自我保存的物质基础就必然相互争夺。在不断争斗中,有智有德者胜出,兼并诸群,从而形成包括里胥、县大夫、诸侯、方伯、连帅和天子在内的共同体层级,这就是封建制形成的过程。但有智有德者并不能改变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共同体的内部结构,是以群与群之间又相互妥协而难以相互消灭。在共同体层级结构形成后,经由血缘继承而传递到后世,即使圣人也只能因之而不能去之。因此,封建制是社会历史发展必然产生的制度,而非圣人有意创立的制度。
柳宗元从人类社会起源的角度论证封建制非圣人所创,虽然破除了封建制的神秘面纱,但并没有否定封建制是理想制度。要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还要从制度本身去寻找更多论据。柳氏首先从制度设计之优劣上寻求证据[2]71-72。基于周秦兴衰和汉初分封之弊的历史经验,柳氏认为封建制的权力配置容易造成诸侯尾大不掉的局面,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支配性,不利于维持天下一统的局面。周之所以亡即在于诸侯盛于下而分其权,汉初郡国制的实践也再次证明了封国容易叛乱,威胁国家稳定。而秦之郡县制则能够保障中央管摄天下,统一支配郡县之权,消除地方叛乱的根源。柳氏这一论断之所以得到后世诸多儒者认同,正是因为其透过历史兴衰洞察到了地方分权过重导致的“其专在下”和地方叛乱问题。
而比制度设计之弊更为严重的是隐藏在制度背后的价值取向之弊。柳氏说:“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2]74柳氏一反先儒封建为公的论断,认为郡县为公。他认为汤、武获得各地诸侯的依附才拥有了革命和延续社稷的力量,同时分封诸侯也可以保证其继续坐拥天下,因此,封建诸侯事实上是自私而非大公。郡县制虽然是秦始皇为了一家之私而设,但却在制度上消除了众多封国,在客观上保证了公平。要理解郡县制之所以为公,还需要结合接下来一段文字:“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2]74-75柳宗元极其强调尊贤的重要性,即它关乎政治治理的成败,贤人在上则天下安,小人在上则天下乱。柳宗元认为,因为世袭制的缘故封建制无法保障在上位者皆贤,只能按照一定比率保证其为贤者。可能这一比率因为贵族家庭教育得当而高于整体的贤人比率,但周代的制度实践证明这一比率并不能保障贤人在位从而延续周之社稷。在此情况下,政治治乱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而这与圣人为公之意是相悖的。同时,由于世禄的缘故,贵族占据了大量的公共职位和公共品,贤人入仕的空间被大大削减,虽有圣贤之人也无法立于上位。这就必然导致贤愚不能上下分,降低施政效率,从而降低国家治理能力,最终导致天下乱多而治少。显然,这不是圣人设立制度的初衷。与此相反,郡县制却开放了几乎所有的公共职位给予贤人,更利于实现公天下。两相比较,封建制劣于郡县制。因此,封建制不仅不是圣人所创,也并不符合圣人之意。必须指出,柳宗元尊贤的背后是其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以及追求公义的政治价值,在亲亲贤贤之间,柳宗元更重视贤贤的优先性(2)在《六逆论》中,柳宗元进一步否定了“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的观念,强调圣贤可以超越贵贱亲疏。详参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5—97页。。这与西周封建制重视亲亲迥然不同。
总之,柳氏之分析抛弃了封建制的政治哲学意义,纯粹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论述封建的起源,能讲述其历史之理,而不能究经典之深意。其从制度设计出发认为诸侯尾大不掉,容易形成叛乱,但也否定了地方分权的积极意义;从公义价值出发否定封建为公,但也忽略了封建制作为道德共同体的价值。同时,柳氏对作为封建制三要素之义的井田制避而不谈,最终使封建制变为一种尾大不掉的区域行政制度,且妨碍贤人居位和导致地方叛乱。
柳宗元《封建论》颇具说服力的洞见借助其文笔在宋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苏轼认为“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3]。程颐认为“封建之法,本出于不得已。柳子厚有论,亦窥测得分数”[4]。志在三代的张载却不同意柳论,接下来一节我们分析张载对柳论的反驳。
二、张载对柳宗元《封建论》的反驳
针对柳宗元从制度起源、制度设计以及政治价值三个方面对封建制的质疑,张载必须做出回应。前文已经指出,柳宗元从人类社会起源的角度分析封建制之形成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的价值,从制度设计和政治价值的角度否定封建制则彻底消除了封建制所寓的圣人之意,因此,张载只需从制度设计和政治价值的角度重新肯定封建制即可证明封建制乃圣人创设的理想制度。
首先看在制度设计上张载如何反驳柳宗元。张载说:“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简则治之精,不简则不精,故圣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则事无不治者。圣人立法,必计后世子孙,使周公当轴,虽揽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后世安得如此!且为天下者,奚为纷纷必亲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复逐之,有何害?岂有以天下之势不能正一百里之国,使诸侯得以交结以乱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后世乃谓秦不封建为得策,此不知圣人之意也。”[5]251在制度设计上,张载从两个方面反驳柳宗元所指出的权力配置问题。第一,权力配置与治理效率有着密切关联,事权越简越有利于治理效率的提高。在封建制下,圣人通过分封诸侯和授田于民而将天下事分于天下人,天下人皆有其具体的职分并可自由发挥而不受上下层级结构的制约,是以封建制能尽天下之力以成天下之事。与此相反,在郡县制下,天子或中央总揽天下之事,事权过于集中且人与事间隔层级过多,除非圣人在位,否则天子要么无法一一处理天下事,要么在位者忽略具体事务的地方性和特殊性,从而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因此,从行政效率的角度看,封建制之分权优于郡县制之过度集权。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是张载观察宋代中央集权之弊而得出的洞见,可谓从正面反驳郡县制优于封建制[6]。第二,针对柳氏所提出的诸侯分权造成地方叛乱的问题,张载从权力制约的角度为封建制辩护。他认为,封建制下天子亦可罢黜或讨伐不肖之诸侯,且天子王畿之地远大于百里之国,诸侯叛乱只能发生在天子无德且中央政府治理极其败坏的极端情况下,因此,诸侯分权之弊并不影响封建制本身的卓越设计。不过张载也改变了诸侯世袭的条件,同时缩小了诸侯封地面积,在此情况下,诸侯无力构成对中央的威胁。这应是其吸收柳论而做出的调整,后世不少儒者继承了这一思想以反驳“封建制引起叛乱”的观点。
其次,柳宗元还从政治价值的角度认为郡县制为公而封建制为私,其重要依据是封建制之亲亲妨贤入仕。针对这一点,张载说:“古者诸侯之建,继世以立,此象贤也,虽有不贤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国,彼不得暴其民,如舜封象是不得已。”[5]296圣人设计诸侯世袭制度的原因在于“象贤”,即使贤人之子弟有不贤者,也要给予其世袭之位,以此作为贤人的象征,凸显贤人之德的意义。允许不肖子弟在位并非任其蹂躏百姓,而是由天子派遣贤人代其治理,舜封象而剥夺治权就是如此。简言之,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共同体朝向道德之维。张载在《策问》中说:“世禄之荣,王者所以录有功,尊有德,爱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穷也。为人后者,所宜乐职劝功以服勤事任,长廉远利以嗣述世风。而近世公卿子孙,方且下比布衣……盖孤秦以战力窃攘,灭学法,坏田制,使儒者风义浸弊不传……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为利矣。求口实而朵其颐,为身谋而屈其道,习久风变,固不知求仕非义,而反羞循理为不能,不知荫袭为荣,而反以虚名为善继。”[5]355-356张载观察到在郡县制和科举制下的士人日渐沉沦,降志以求利,屈道以谋身,士人群体逐渐丧失了道德共同体的面向。这是北宋士人的真实写照。其实唐代高门和寒门之间就有关于进士与门荫孰高孰低的争论,高门认为其优良的家庭教育能够培养经明修行之士[7]41-43,而寒门则认为高超的文学技艺表明自身也具有传承斯文和佐佑王化的能力[7]49。张载的策问就是针对这一现象而延续其讨论的。
张载认为,郡县制由于缺乏三代学法和田制不利于培养和选拔经明行修之士,是以郡县制和以功名为导向的科举制并非修身进德的理想制度;封建制则能给予诸侯和公卿大夫士一定的爵禄,为其道德修养的展开提供保障。世袭之家的子孙后代并非仅仅以承袭爵位为荣,更重要的是以承袭贤德之风为荣,以传承父祖之德为己任。由于具有了基本的物质保障,世禄之家更容易做到以廉自居、重义轻利。此外,要保障子弟修德,还需要一套家法,也即张载非常重视的宗子法。总之,在世禄和宗法下,士人形成以家族为单位并相互联结的道德共同体,传承父祖之德,兢兢业业,服勤事任,自修为贤,化及其民,这才是“象贤”真正的指向所在。而郡县制虽然更有利于贤人入仕,但在培养贤人上缺乏相应的价值指引和制度设计,表面上进贤而事实上则是妨贤。因此,封建制相较于郡县制更有利于圣贤的养成。这是用贤的前提,即两相比较,郡县制更为妨贤。由此,张载从道德共同体的角度为“封建为公”做了很有说服力的辩护。
同时,张载也不同意封建制妨贤。前文已经指出,天子可以罢黜不肖之诸侯,也可以任命贤人为官吏制约不肖之诸侯,从而在政治治理上保证贤人居位。因此,世袭制度虽然增加了治理成本,但并未显著降低治理效率。再加上世禄对于养贤以教万民的作用,世袭制度的优势是明显的。不特此也,受柳论的影响,张载还力图平衡亲亲贤贤,将贤贤的优先性提升到与亲亲几乎相等的地位,为封建制下庶民之贤者入仕奠定了价值基础。他说:“‘亲亲尊尊’,又曰‘亲亲尊贤’……若尊贤之等,则于亲尊之杀必有权而后行。急亲贤为尧舜之道,然则亲之贤者先得之于疏之贤者为必然。‘克明俊德’于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于百姓而万邦协,黎民雍,皋陶亦以惇叙九族、庶明励翼为迩可远之道,则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后远者可次叙而及。”[5]58张载认为在亲亲与贤贤之间的冲突中,不能不顾亲亲的因素而只考虑贤贤,也不能只循亲亲而忽视贤贤的重要性。前者与实践中选贤由近及远的渐进原则相违,后者则与儒家选贤治国的原则相悖。因此,王者在贤贤的同时要兼顾亲亲。他以尧为例说明如何做到“权”。尧舜皆先选亲族之贤者,然后再选百官亲族之贤者,最后挑选庶民之贤者。质言之,在贤均的情况下要以亲亲尊尊来定用贤之序。张载的这一创见既有伦理价值的考虑,也有实践效果的考量:由亲及疏的选贤原则在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共同体中一方面照顾到了亲亲的伦理价值,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选贤实践的不断推进。那么当亲亲和贤贤出现冲突时怎么处理呢?前文已经指出,张载认为应当罢黜不贤者,从而保障贤者居位。
总之,张载从权力配置、养贤用贤等方面反驳了柳氏的立论之基,从道德共同体的角度论证了封建制是理想的政治制度。此外,张载还重视封建与井田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只有通过封建才能最终保证井田的贯彻[5]251,并从根本上消除悬殊的贫富差距[5]248,384,从而为万民的基本生活提供根本保障。
肯定封建是圣人之意,并不意味着作为圣人之迹的封建制可以在当代复活。张载则不仅肯定封建制作为圣人之迹具有永恒性,同时又怀着极大的热情复原封建制,并为其可行性作论证。《经学理窟·自道》言:“上曰:‘慕尧舜者不必慕尧舜之迹。’有是心则有是迹,如是则岂可无其迹!”[5]290与宋神宗观点不同,张载认为体现天道的圣人之心与圣人之迹是不可分离的,复三代不仅是精神上的复归,也需要具体物质形态上的复归作为基础。在三代之制的可行性上,张载认为井田制得万民之心是以甚易行。他认为要实行井田制需要君相有德有才,同时在制度设计上多考虑兼并之家的利益[8]。他还认为通过“以地换权”的方式可以解决大地产所有者的抗阻[9]107-108,他们在获得一定的封地、采地或者“田官”职位作为补偿后自然会减少对实行井田制的阻挠。在官本位的古代中国,这一举措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也反映出张载制度思考的创新性。
驳斥柳论只是张载重构封建理想的第一步,要焕发封建制的生命力,还必须为其提供新的理论根基。这是张载撰写《西铭》诸多目的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接下来我们分析《西铭》如何为封建制立基。
三、《西铭》:新封建制的理论根基
正如前文所言,张载重塑了经典意义中的“封建”。前文已经指出,封建(分封)、宗法和井田是经典意义中封建制的三要素,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道德共同体的制度基础。在三要素中,宗法是最为核心的因素,张载也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对其有很大的推进。张载认为,“井田而不封建,犹能养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犹能教而不能养”[5]297。井田制为共同体成员的基本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是谓“能养”。分封诸侯、大夫世禄则为士人修身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解除了其后顾之忧。这看似属于“能养”的层次,但正如前文所说,隐藏在封建背后的是亲亲贤贤的原则,世袭之子孙必须以绍述先人之德为己任,从而为封国内的子民提供效法的道德楷模,因此“封建”是“能教”。“能养”“能教”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儒家的人伦价值,是以“能养”“能教”的井田与封建必须围绕宗法这一核心要素来构建道德共同体。张载通过“能教”反驳了柳宗元封建妨贤的观点,给予了贤贤更多的优先性,同时又通过新宗法思想增加了封建论的理论厚度。
宗法并非如一些批评者指出的那样一定会破坏公正、否定民主[10],宗法不仅仅是家族规范,其背后也寓居着更为根本的道德原则,在古代中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我们先看《西铭》在宗法思想上的突破,然后分析新宗法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如何为封建制立基。
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5]62针对张载宗法思想,学界多有研究,我们结合时贤的研究梳理《西铭》在宗法思想上的新突破。第一,在道德价值上,《西铭》基于宇宙家庭共同体提倡“民胞物与”的仁爱观。《西铭》的平等仁爱观与张载在他处对爱有差等的肯定有一定张力,但对差等之爱的肯定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平等之爱。平等之爱的仁爱观对差等之爱的实践具有范导作用,能够促进仁爱范围的不断扩大[11]108。第二,在形上学上,张载通过宇宙生成论论证了天地乃人与万物之父母,为“民胞物与”的仁爱观奠定了形上学基础。因此,人不仅要对生身父母尽孝,也要存心养性、穷神知化、成己成物以对天地父母尽孝,这也就扩大了孝的范围[11]109。同时,由于每一个个体都直接禀赋了天地之性,也都拥有独立修德以尽孝事天的能力,这就弱化了在上位者的教化作用,突出了每个个体的道德主体意识[9]161-169。第三,在宗法结构上,天地成为万民之父母,天子从民之父母变而为宗子。这就使得宗法大家庭囊括了天下万物,最大化了宗法的适用范围,不再如西周宗法那样主要为贵族而设。宗法适用范围的扩大,不仅意味着道德共同体的扩大,也意味着庶民之贤者被纳入某种亲亲序列之中,从而获得了更多的任用机会。以上几点,学界或多或少皆有所论述,但对《西铭》何以成为封建制之基础这一逻辑环节尚未分析。我们接下来结合张载的其他论述,尝试揭示这一环节的内在逻辑。
首先,《西铭》为封建制奠定了价值方向。封建制所构筑的共同体与《西铭》中所设想的宇宙共同体都是道德共同体,都以共同体成员的德性修成为第一目的。正如前文所言,张载认为相较于郡县制以功利为导向、助长求利求仕之心,封建制则以道德为依归,更有利于共同体成员德性的实现。任何一个共同体都有政治、经济、道德等诸多面向,不可否认郡县制在调动资源以发展经济、增加财富上有其显著优势,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上也更为有力。但郡县制之目的外在于道德,容易导致财富集中于皇权之下等诸多问题,这是其不可能被张载视为理想制度的根本原因。而封建制在制度设置上将财富分配固化,并附属在道德之下,共同体成员在修德之外难以获得更多财富,凸显了道德在封建制中的优先性和支配性。因此,在制度设置的目的上,比之于郡县制,封建制更符合《西铭》的内在要求。同时,《西铭》也引领了封建制的价值方向,将封建制共同体从道德境界提升到天地境界。
其次,《西铭》为封建制确立了价值序列。《西铭》的宇宙共同体是拟家庭式的宗法共同体,宗法居于核心支撑地位,因此,其制度落实也必然选择以宗法为核心框架的封建制。众所周知,郡县制在制度设计上剥离了亲亲原则,宗法几乎丧失了其在政治上的影响,无力在孝悌之道上为万民示范,是以郡县制不是实现宗法共同体的理想形式。但如果封建制完全以亲亲为原则,也与《西铭》的精神相背离。正如前文所言,张载以亲亲贤贤为原则构建的封建制与经典意义上的封建制有很大不同,他提升了贤贤的优先性,使其几乎与亲亲相抗,这是对以往封建制过于重视亲亲的重大调整。事实上,这种调整恰恰是《西铭》仁爱观的内在要求,虽然宗法依然是宇宙共同体的核心支撑框架,但寓居于其中的价值原则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西铭》“民胞物与”的仁爱观必然要求对基于血缘的亲亲原则加以限制,防止仁爱局于私家之中。而要平衡公私,必须使贤人居位。唯有圣贤方可穷神知化以继天之志,方可爱必兼爱,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因此,在价值序列上,《西铭》为封建制的亲亲贤贤奠定了基础。
最后,《西铭》为封建制中各级共同体勾勒了具体形式。第一,“民胞物与”的仁爱观并不否定差等之爱,无论是对天地、大君、大臣之爱还是对鳏寡孤独者之爱都是通过拟家庭的方式实现的,这就决定了亲亲是最根本的爱。因此,博爱落实到实践中,也必然按照爱由亲始的差序展开。同时,张载肯定私亲为公,他说“虽货色之欲,亲长之私,达诸天下而后已”[5]32,而为亲亲提供物质保障的制度自然是井田、世禄和世位。第二,《西铭》同样强调每个个体自立的道德主体意识,穷神知化以实现其天命之性的自然流行。由此,在制度设计上,张载必然强调分权,从而保障每个共同体基于自立的自我实现。郡县制强调上下统属关系,显然不适合《西铭》要求,而封建制中家、比、闾、族、党、州、乡、大小诸侯和天子各自拥有与其相适应的自主权,与《西铭》对道德自主性的强调相适应。第三,如果大小共同体只有自立而无合作是无法联结为天下或宇宙共同体的,因此张载还强调公私相济。张载说:“后世不制其产,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贵专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为计。”[5]249郡县制下君主以其势专天下之利,役百姓之力以供其需,放弃了养民教民的责任,上下之间不相为计。封建制的各共同体之间则相互成就:庶民养公田以奉公;乡里也有相互救助的制度安排;诸侯对下要养民、教民,对上要上贡天子;天子要成为天下的道德楷模。总之,封建制内部各共同体之间形成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以相养相成的道德共同体,与《西铭》之仁爱精神相表里。
终上所述,《西铭》规定了封建制宗法共同体的道德境界,预设了封建制亲亲贤贤的价值序列,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其井田、封建等具体的形式。因此,《西铭》必然以封建制为依归,同时封建制也只有在《西铭》的范导下才能重新焕发生命力。
四、结语
柳宗元从制度设计和制度价值等诸多层面否定了封建乃神圣理想政治制度,消解了封建制的政治哲学内涵,使封建制沦为一种“坏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张载则认为柳宗元不识圣人之意,并从制度设计和制度价值层面论证作为道德共同体的封建制优于郡县制,有力地驳斥了柳论,扭转了柳宗元对封建制的解构。张载在反驳柳论的过程中也改造了封建制的具体设计,提升了贤贤在封建制中的地位,同时也改变了诸侯世袭的条件以及封国的大小,显现出其思考的深度和创造力。更为重要的是,张载通过《西铭》为封建制提供了本体论基础和新的价值根基,使封建制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也为后世儒者坚守封建政治理想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