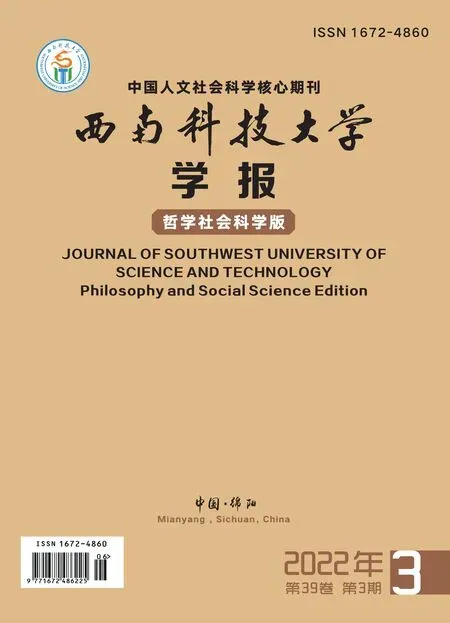“模仿”与“代偿式转换”
——论纳兰词英译中的审美再现手段
2022-11-23张白桦杨剑桐
张白桦 杨剑桐
(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010000)
纳兰性德(1655-1685 年),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生于清顺治11 年,被誉为清初第一词人,其主要作品有《通志堂经解》《侧帽集》《饮水集》等。纳兰性德与阳羡派代表陈维崧、浙西派掌门朱彝尊鼎足并立,并称“清词三大家”[1]72。清末著名学者王国维对纳兰性德评价甚高,《人间词话》中有言,“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1]71,称其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1]71。纳兰性德的诗词涉及边塞、爱情、悼亡等题材,风格以清新婉约、哀感顽艳著称,是中国词坛中当之无愧的瑰宝。
从20 世纪30 年代开始,国内的一些学者和翻译家、西方汉学家和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英译了一定数量的纳兰词。然而,这些译者各自翻译的纳兰词在数量上非常有限,且比较零散地出现在各种介绍中国诗歌的作品选中[2]6。目前,鲜有译者将纳兰词的译作编著成册,而深入研究纳兰词英译的国内学者也只有寥寥数人。纳兰性德作为极具影响力的词坛翘楚,其作品的英译现状与其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并不匹配,因而对纳兰词展开进一步译介和研究理应成为国内译者和学者关注的方向。
一、翻译美学和翻译的审美再现
翻译和美学自古就有着深厚的渊源。古希腊哲人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43 年)在修辞教育中强调“合适”的概念,所谓“合适”的词汇是指“最高雅的” (most elegant) 语词[3]7-10。西塞罗关注了翻译中蕴含的审美信息,将翻译扩展到美学领域。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Tytler,1747-1814 年)将他的译文审美要旨阐释为“成功的译作应能体现原作的风采,洞察原作的全部推理,最终表现出原文之美”[4]204-205。我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以“文”和“质”作为评价译经行文特点的标准,其中就蕴含着文本评价和美学批评的概念[5]67。在近代,严复提出翻译的“信达雅”原则,并把“雅”作为其翻译理论的主要特征。可见无论东西,人们对于美都有着执着的追求。
刘宓庆于1986 年提出了翻译美学的基本理论构想,并在之后编写了《翻译美学导论》,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翻译美学的理论框架。刘宓庆指出,翻译美学的理论和任务就是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包括对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语言审美和翻译接受方面的研究,对翻译中审美心理活动(如意象、情感等)一般规律研究,对翻译中审美再现手段及对翻译美学价值观的探讨[6]210。
一般来说,翻译审美的客体是原文文本,翻译的审美主体是译者。翻译的审美再现指的是用译文再现原文的审美信息,这与审美者的审美理想和对审美客体的关照情况有关。审美理想可以看作是翻译家对待翻译艺术实践的原则主张,是翻译家对如何体现原作美的一种理性和感性认识的统一[7]254。翻译审美者对审美客体的关照就是译者对原作的“观”“品”“悟”,把握原语的形式要素和非形式要素,审美者如果不能做到对审美客体全面的关照,其再现审美信息的过程也会受到影响。
二、翻译审美再现的手段:“模仿”与“代偿式转换”
刘宓庆认为模仿(imitation)是翻译中审美再现的基本手段。模仿的概念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提出。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公元前460-370年)认为艺术起源于模仿。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 年)肯定模仿的艺术价值,认为模仿是人类的天性。亚里士多德的见解是模仿是根据可然和必然的原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它带有一种普遍性[8]81。人们在模仿中采用不同的媒介,取用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方式来展示事物的形象,包括对色彩、形态、声音等方面的模仿,并从模仿的成就中获得快感[8]27-28。诗人是以语言为媒介进行模仿的,人们对音调和节奏天然的敏感性促成了诗歌的诞生。
刘宓庆将模仿分为三类,分别是以原语为依据的模仿、以译语为依据的模仿和动态模仿。
以原语为依据的模仿注重原文形式和气质的还原,强调原文信息的“复制”,使译语读者产生和原语读者相同的审美体验。译者需要忠实于原文,还需要精通原语和译语文化,拥有匠石运金之功力,才能最终呈现完美的翻译作品。然而,因为原语文化具有异质性特征(heterological features)[7]252,对原语审美信息的转换有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特别是双语在民族文化和心理素质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时,刻意的模仿常使效果适得其反[5]220。因此,以原语为依据的模仿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以译语为依据的模仿为解决原语信息不可译的问题开辟了新的道路。刘宓庆在《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中提到的“对应”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并且他在《翻译美学导论》中也把“对应”归为模仿的范畴。以译语为依据,与目的论中的语内连贯原则不谋而合。译者应顾及目标文本的可读性及其在目标读者群中的接受程度,而且译本在译语读者看来是连贯的、可接受的。以译语为依据的模仿意味着顾及并跳跃了民族文化、心理素质、语言特征等方面的障碍,发扬了译文优势[6]220,用译语的审美信息替代原语无法复制的信息。译者要对目的语有较强的审美意识,能在目的语当中找到与原文的美相对应的表达方式,做到对应式审美[6]220。
动态模仿基于动态对等理论(dynamic equivalence),取以上二者之长,是一种综合式的模仿。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1914-2011 年)认为动态对等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和源语信息最接近的、最自然的对等话语,首先是重视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才是风格语言形式上的对等”[9]166。动态对等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出发,目的是使译语读者得到和原语读者相同的阅读感受,消除译语读者对原语表达的陌生感,并强调语言功能和读者接受的对等。动态模仿要求译者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将模仿视为一种变通化手段[7]265,在以原语为依据的模仿和以译语为依据的模仿中择善而从,选择最优方案。
由此可见,模仿是一个灵活的概念,既包括原文信息的复制,又包括表达方式的变通。而这种变通即是代偿论的核心思想。
“变通”的理念早在《周易》中就已经出现。《周易》中涉及变通的表述有“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等,并提倡切合时宜的变通[10]7。代偿是翻译方法论中的变通手段,也是翻译中审美再现的手段。刘宓庆用代偿的概念来定义模仿的性质。以原语为依据的模仿”属于“非代偿式转换”,是完全忠实的翻译;“以译语为依据的模仿”和“动态模仿”属于“部分代偿式转换”,其中已经能看到变通的影子;而完全意义上的“代偿式转换”是对原文的重建与改写,是最高形式的变通。译者选择代偿式转换有主动原因也有被动原因。首先,不同译者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态度各异,一些译者不会注重还原原语的形式,而是偏向于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的再创作。另外,由于原语的语言文化异质性特征的限制,一些文本无法实现语言层面的模仿,译者只能更多地谋求对应功效的重建[6]220。
刘宓庆认为,代偿是积极意义上的“权宜之计”[7]256。这其中传递了三层含义。第一,代偿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手段,是在无法还原原语形式时的不得已之下策。最理想的翻译方法依然是恰当的直译。第二,代偿是积极的变通,而非消极的趋易避难。虽然原语有时存在一定的不可译性,但译者的职责是对如何翻译进行积极的思考,不是“宁顺而不信”地去大刀阔斧地改译或编译。第三,代偿虽是一种变通,但终归万变不离其宗,在做到语言层面叛逆的同时应实现“叛逆性忠实”,将译文的创造性和叛逆性把握在有限的空间内。否则,这种创造性就会演变为误译、错译,给原作带来破坏性,造成“破坏性叛逆”[11]151。
从“非代偿式转换”到“部分代偿式转换”,再到“代偿式转换”的过程,可以看作是“直译——直译与意译结合——编译”的过程,同时也是翻译由“忠实”走向“叛逆”的过程。翻译的审美再现和翻译策略具有某种同一性,这不免又涉及到了翻译研究的基本主题: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从翻译美学角度来看,译者对原语文本进行鉴赏和分析后,以译者主体性思维为驱动,将掌握的审美信息寓于自身的文学创造性中,最终做出语言的转换。作为翻译和翻译审美的主体,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有着天然的支配地位。英国翻译理论家赫曼斯(Hermans,1948-)指出,“翻译从来就不是透明的”“翻译告诉我们的更多的是译者的情况,而不是所译作品的情况”[12]12-13。但正是因为这种不透明性,译者的权力必须加以约束。就好比是驰骋在有限疆域的骑士,得体的主体性可以让他游刃有余,规矩方圆之中自有其广阔天地[13]46。
三、纳兰词英译中审美再现手段探析
本文以四首国内译者的纳兰词译本为例,探讨纳兰词英译中审美再现手段的具体运用。以下的译本示例选自国内四位最具代表性的译家,包括吴松林、许渊冲、朱曼华和翁显良。在对纳兰词进行译介的国内译者中,许、朱、翁三人译介的纳兰作品数量较少,其中许译本为1 篇,朱译本和翁译本各2 篇,许对翁译本的改译1 篇。吴译的纳兰词数量较多,共200 首,收录在《清代满族诗词(双语)·纳兰性德卷》中。在纳兰词的译介中,纳兰词的形式、风格、意象、意境和文化负载信息都成为译者再现的对象。四位译者在翻译中对不同审美信息各有侧重,译者的风格也体现得比较明显。从翻译美学的层面来看,译文呈现的样态是由译者运用的审美再现手段所决定的,不同的审美再现手段表现为侧重于原文形式因素的再现或非原文形式因素的再现,抑或是两者兼顾。而无论译者使用何种手段,其最终目的都是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让双语读者拥有相同的审美体验,使译文达到“化境”之效果。接下来,本文将从以原语为依据的模仿、以译语为依据的模仿、动态模仿和重建四个方面探讨纳兰词英译的审美再现手段。
(一)非代偿式转换——以原语为依据的模仿再现
以原语为模仿原型的再现(SL-oriented representation)旨在以原语的审美信息特征和结构复制译语美的信息[7]256。由于原语和译语在词语、语法、审美偏好等方面的差异,对原语审美信息的复制需要特别考虑形式上的复刻,诗词翻译中尤其如此,因为诗歌的形式美本身就是读者审美体验中重要的一环。译语读者通过对形式和的审美来感受原文的神采,其中形式审美包括对诗歌的观感和读感的审美。下文以吴松林的《采桑子》译本为例进行分析[14]15。
采桑子
谁翻乐府凄凉曲,
风也萧萧,
雨也萧萧,
瘦尽灯花又一宵。
不知何事萦怀抱,
醒也无聊,
醉也无聊,
梦也何曾到谢桥。
Picking Mulberries
Who′d like to play the melody of desolation?
The wind rustled,
The rain bustled,
The wicks burned out though my heart bustled.
Puzzled by what entangled,
I felt listless, soberly,
I felt senseless, drunkenly.
Did I meet my girl enchantingly?
吴松林主要从音韵和句式层面对这首词进行了以原语为依据的模仿。
1.音韵层面
本词为三平韵,上片押阴平韵,下片押阳平韵。译文在上下片的后三句分别押了两种尾韵,上片押了辅音韵/d/,下片押了元音韵/I/,以体现原文前后两片所押平韵的阴阳之差。这种完全依据原语特征的模仿是十分精妙的,充分体现了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间的可转换性(convertability)。此外,译者先压辅、后押元的手法制造了先急后缓的阅读感受。首段中,风和雨的意象具有一种力度感,每行适合以短促有力的辅音结尾;而尾段的“醒”“醉”“无聊”传递了舒缓的状态,以元音结尾能达到朗诵时的拖音效果,让音韵变得舒缓,表现了纳兰在雨夜失眠时百无聊赖的心境。
2.句式层面
译文基本体现了原文的结构和句式特征。吴译的首末行词数均多于二三行,词的观感继续保持上下长、中间短的形态,保留了原文词牌的格式特点。
吴松林模仿纳兰在上下片的二三行中运用对仗和叠韵达到的复沓效果,将“风也萧萧,雨也萧萧”译为“The wind rustled, the rain bustled”,用rustled和bustled两个观感和读音极为相近的词模仿了原文中的反复和叠韵,同时也避免了英语中重复的大忌。在下片中,吴译将“醒也无聊,醉也无聊”中的两处“无聊”分别译为“listless”和“senseless”,将表达“醒”和“醉”的“soberly”和“drunkenly”单独放在句末,同时增补了主语和系动词“I felt”置于句首,达到了两句都以“I felt”开头,以词缀为less 的形容词为表语,以词缀为ly 的副词结尾的对应效果,使结构规整有序。原文中附着在这些规整表达之上的审美信息也能同样表现在译文中。
诗词的神韵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蕴含在其独特的形式之上,保留原文的形式因素是减少翻译过程中审美信息折损的一种方法,如此也能使译语读者享受一种新颖的审美体验。除此之外,译者在复刻原文形式美的同时还可以对部分细节做灵活处理,使译文和原文整体相似却又求同存异,从而更能凸显出翻译中审美再现的哲学性与艺术性。下面再来看纳兰词英译中以译语为依据的模仿再现。
(二)部分代偿式转换——以译语为依据的模仿再现
以译语为依据的模仿再现(TL-oriented representation)旨在以译语的语言结构特征、表现法传统和社会的接受倾向为依据,调整原语审美信息的类型和结构,将其表现在译语中[7]261,“译文优势”在此时发挥了作用。需要注意的两点:第一、译文应该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以译语特征为再现依据;第二、译文只是将难以模仿的部分加以代偿[7]261,而不能随意改变原语的基本特征。下面以许渊冲的《秣陵怀古》译本为例进行分析[15]284。
七绝·秣陵怀古
山色江声共寂寥,
十三陵树晚萧萧。
中原事业如江左,
芳草何须怨六朝。
On the Capital of Yore
Both mountain hue and river song are sad and drear;
Showers of leaves on Thirteen Tombs ruffle the ear.
The Northern Kings sought pleasure on the southern shore;
The bygone dynasties need no grass to deplore.
Nanjing was the capital of the Six Dynasties(211-280;317-589)and of the early Ming, whose thirteen emperors were buried in the Thirteen Tombs and whose last emperor sought pleasure on the southern shore and was overthrown.(译者注)
许渊冲从音韵和内容两个层面做了以译语为依据的模仿。
1.音韵层面
许译将译文的押韵格式改为AABB 式,前两句以“drear”和“ear”结尾,尾韵压/ɪə/,后两句以“shore”和“deplore”结尾,尾韵压/ɔ: /,替换了原文七言绝句的押韵规则。对音韵的替换是一种以译语诗歌形式为依据的模仿,这样的模仿是“以诗译诗”的原则在音韵层面的诠释,能使译语读者也产生阅读诗歌的审美感受。
2.内容层面
首联“山色江声共寂寥”的译文为“Both mountain hue and river song are sad and drear”。“山”指南京的钟山,“江”指长江,纳兰正是面对着见证无数王朝更迭的“江山”之景写下的这首怀古绝句。这里的“山色”译为了“mountain hue”而不是“mountain color”,hue 有“色度、色调”之意,可以增添译文的艺术色彩和画面感,而使用color则过于平实。句尾的“sad and drear”改自英语中的习惯表达“sad and dreary”,意为“凄惨,悲凉”。drear 是dreary 的文学化表达,增强了译文的文学色彩。译者的选词渲染了一幅低饱和度的画面,如同山水画一般显出古意,凸显了阴沉的氛围和作者悲伤的情绪。
在颔联中,作者借南京的钟山和长江之景联想到了北京的十三陵,写下了跨越时空之景。译文使用借代修辞,以“leaves”代指原文的“树”,并把“Showers of leaves”作为主语,突出了十三陵晚风吹过,树叶簌簌落下的画面;同时,译者增译了“ruffle the ear”作为谓语和宾语,动词“ruffle”表达出了风吹树叶之声扰人心绪的感受,将抒情的隐性变为显性,使读者的感知更为真切,仿佛身临其境。
如果说首联是从视觉维度传情,颔联则是以听觉维度达意:画面为实,声音为虚,虚实结合,似真似幻。许译将作者描写的情景具体化、抒发的情感立体化,增加了诗歌情趣的同时也扩大了诗歌的意境。
颈联是译者改动较大的部分。“中原事业”意为迁都北京后的明王朝,“江左”意为建都南京的南方政权,这句话意为迁都后的明王朝和江左政权一样腐朽。这句话非常难译,如果直译,译者需要表述“迁都到北方的明王朝”,可能要用到定语从句,“江左”也要指出是“建都南京的六个政权”。这在有限的句子空间内是无法做到的。许渊冲先生对这一句做了大胆的意译,译成了“北方的皇帝总是去江南寻欢作乐”,同时省略了“江左”,使用借代手法以“The Northern Kings”代指定都北方的王朝,以君主的昏庸影射国家的腐朽。许先生还特意在注释中增加了明朝末代皇帝到江南享乐的细节作为对原文的补充。通过意译,译文的表达变得更加生动而且通俗易懂,读者对政权更迭也有了更形象的理解。
在尾联的翻译中,译者把原文中作宾语的“六朝”在译文中用作主语,并将其意译为“The bygone dynasties”,表示这些朝代已经湮灭在了历史中,而这些朝代的名称已经不再重要,它们不过是历史上无数政权腐朽而亡的缩影,可见译者对“六朝”进行模糊处理关照了诗歌整体的情境,同时也关照了读者的阅读接受。本句的意思是“芳草何必为六朝的旧事而感伤呢”,其中“芳草”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意象。“芳草”在诗歌中总是用于咏叹六朝的衰亡,如韦庄《台城》中的“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和王安石《桂枝香》中的“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许译将其译为“grass”不能算错,但笔者认为可以在文后对其做出注释,否则读者读到这一句可能会产生“为什么要用草来哀叹覆亡的朝代”的疑惑,因为他们不了解“芳草”在中文的文化负载含义,而减少读者在理解译文时的障碍也是对译文社会接受倾向的照顾。下面来看纳兰词英译中的动态模仿。
(三)部分代偿式转换——动态模仿
动态模仿又叫优选模仿(optimized imitation),是一种灵活的变通手段,即在可以原语为依据时选择原语进行模仿,在以译语为依据更佳时选择译语进行模仿[7]265。动态模仿的特征主要有四点:不违背原文的主旨性原义,灵活处理原文的外在形式美,执著于译语的最佳可读性,以及努力寻求在高层级上对原文美的模仿[7]265。下面以朱曼华的《木兰花令》译本为例进行分析[16]193。
木兰花令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
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
泪雨霖铃/终不怨。
何如薄幸/锦衣郎,
比翼连枝/当日愿。
To the Melody “Magnolia-Flower-Short-Verse”
If the first love is to last /in human whole life,
Why Autumn-Fan sighed herself /a disfavored wife?
Nowadays a sweetheart so lightly /changing her mind,
That such a frivolous attitude still /considered as a style.
Once at midnight, an imperial couple /sworn a love vow,
The concubine was tearful in whisper /without sorrow.
Even if the heartless emperor /was such a fickle guy,
Still he would swear a love oath /“‘wing-to-wing’ to fly”.
Usually, Autumn-fan used as an analogy of disfavored beautiful lady.(译者注)
朱曼华对这首词的形式和节奏做了以原语为依据的模仿,而在音韵、句法和文化层面做了以译语为依据的模仿。
1.以原语为依据的模仿
朱译本在形式上做了灵活处理。相比于原文的每行七字,译者把译文每行的词数控制在十个左右,虽然译文在观感上略显臃肿,但每行的长度还是基本保持一致,每行的朗读的时长也基本相等,停顿也更具规律性,基本符合原文工整精炼的风格。此外,译文在节奏的划分上也有着原文的影子,节奏的划分见示例。原文每行七字,节奏上四下三,既工整地划分了字数,同时也划分了每一行的意群。译文的节奏则是单纯以意群来划分,划分节奏的位置在每小句的最后一个意群之前,和原文一样保持在每行中间靠后的位置,使译文在朗读时有着和原文相似的节奏感。
2.以译语为依据的模仿
译者在音韵、句法和文化三个层面对原文进行了以译语为依据的模仿。
1)音韵层面
朱译重新处理了押韵格式和韵脚。本词的押韵格式可看作是AAAABBAA 格式,译文的前四行和七八行押了/aɪ/,第五行押了/aʊ/,而第六行却押了/əʊ/。译文的五六行并没有押同样的韵,而在朱曼华看来,这种押韵方法属于“大体整齐押韵”。他认为把读起来口型相似,听起来有韵律实感,但写起来并非同韵的两个词也视为近似押韵的一种形式[16]6。这种押韵的效果算是差强人意,不过从用词来看,第五行的“vow”和第六行的“sorrow”都是以“ow”为结尾的单词,以观感的整齐增添了视觉上的美感。
2)句法层面
译者在本词的翻译以增补主语为主。
本词中有多处主语被省略。在上片的第二句,原文并没有表述变心的人是谁,而朱译增补了主语“a sweetheart”,表明容易变心的是心上人。但需要注意的是,是本词是以女方的口吻所作来控诉男方的薄情,所以此处可突出是男方变心,因此把主语替换为“beau”来突出男方“花花公子”的形象可能更为贴切。在下片第一句,原文并没有表述“语罢”和“不怨”的主语,译者在翻译时增补了“an imperial couple”和“The concubine”作为主语,使译文的逻辑更加清晰。下片第二句的意思是“你(男方)怎么比得上明皇,他(唐明皇)还是和杨玉环有过比翼鸟、连理枝的誓愿”,表达了男方的负心绝情。其中两个主语“你(男方)”和“他(唐明皇)”在原文中都被省略。译者在翻译时做了调整,把薄情男与明皇的比较的部分改为让步状语从句“即使皇帝是个薄情的人”,并在主句部分增补了主语“he”,把名词“愿”改为动词“swear”,使译文符合英语的语法。
3)文化层面
首句中的“秋风悲画扇”的典故出自班婕妤的故事,后人借“妾身似秋扇”来比喻女子失宠。“何事秋风悲画扇”的译文为“Why Autumn-Fan sighed herself a disfavored wife”,译者没有完全遵从原文来直译,而是把秋风和扇子两个意象合并成了“Autumn-Fan”,又运用拟人手法,化“妾身似秋扇”为“秋扇即妾身”。为方便译语读者理解,译者还在文后添加了注释“失宠的美丽女子通常被比作秋扇”来说明秋扇一词的文化负载含义。
在诗歌翻译中,选择直译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需要添加注释来向译语读者介绍原语的相关文化。但有的诗歌中文化负载词过多,如果全部通过直译和添加注释的方法来翻译,不但会使注释过于冗长,也会牺牲译语读者阅读的流畅性。因此,省译与意译就显得很必要。例如本词下片中又出现了三个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典故,在翻译时均有变通。朱译用“an imperial couple”代替了李杨二人,又对“雨霖铃”做了省译。译者在翻译这处典故时化隐为显,把含义融入典故,放弃了对原文美的刻意效法。这样可以做到充分地移情,实现对原文高层级的模仿。在“比翼连枝当日愿”中,“比翼鸟”和“连理枝”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因此译者省译了“连理枝”的意象,把“比翼”译成了“‘wing-to-wing’to fly”,同样体现了李杨二人的缠绵情意,没有折损原文传递的意境。
综上所述,以原语为依据的模仿和以译语为依据的模仿既是一体两面,同时也相辅相成。朱译依照英语的表达习惯对译文做了变通,而这种变通在最终的呈现也使译文每行的节奏做到了与原文相近;同时,译者模仿原文的工整形式把每行译文控制在相近的长度,并在这个框架内实现对译文的变通。朱译既取了两种模仿手段之长,又使两种手段相互交织、互为体现,令人叹服其译技精湛。最后来看纳兰词英译中的重建。
(四)代偿式转换——重建(recast)或改写(rewrite)
重建(或改写rewrite)属于创作(artistic creation)手法,是一种最高形式的变通,也是翻译原创的一种代偿形式[7]269。完全的代偿式转换是一种“得意忘形”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摆脱原文的束缚,按目的来安排体式,以达译者预期的最大优化[7]269。这与翁显良先生的“散体译诗”理念不谋而合。下面以翁显良的《如梦令·万帐穹庐人醉》译本为例进行分析[17]106。
如梦令
万帐穹庐人醉,
星影摇摇欲坠。
归梦隔狼河,
又被河声搅碎。
还睡,还睡,
解道醒来无味。
Better Sleep
Silence settles over this wilderness of tents.
Many a cup have I drained.
Ah! The stars are flickering, perilously reeling.
I am off, headed for home.
But that Wolf River bars my way.
It howls——my dream is shattered!
Sleep, better go back to sleep,
For the waking hours are dreary.
翁显良先生的翻译风格是“得作者之志、取汉语之长、求近似之效”。“得作者之志”是理解和诠释作者的情志、灵魂和神韵;“取汉语之长”是指重新构思后,突破原文表层结构约束,以译文语言之长向读者介绍原作;“求近似之效”是指在语言、文化、历史等因素之下,使译文的艺术效果贴近原作[18]113。可见翁显良在翻译时主要运用重建手段进行审美要素的再现,将原文的意蕴进行重构。实际上,原文中的某些审美信息并不依赖语言文字这些表层因素,它们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实现转换。翁显良在本词中的具体重建做法如下:
在第一句中,翁译把原文分成了“万帐穹庐”和“人醉”两句,先写景,后写人。第一句使用抽象名词“Silence”做主语,在后面接着使用“wilderness of tents”,突出了环境的安静和荒芜,第二句使用倒装增强语气,着重译出纳兰借酒浇愁之愁。
第二句“星影摇摇欲坠”使用了夸张手法,翁译添加了语气词“Ah!”,写出了纳兰在醉酒后看到星光摇曳时的内心真实的感叹与惊惶,仿佛星星真的要飞坠而下。此外,“flickering”后面加了逗号,增加了阅读时的停顿,体现了从“摇摇”到“欲坠”的递进感。
在三四句中,纳兰描写了自己的梦境。翁译使用了“that Wolf River”“bars my way”和“It howls——”“my dream is shattered”,以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表达身居边塞的现实与思乡情感之间的矛盾,破折号的使用也增加了梦境的真实感。
在五六七句中,翁译将“还睡,还睡”的重复改为“Sleep, better go back to sleep”,使情感再次递进,传递无奈醒来,不如睡去的惆怅心情,又把动词“醒来”处理为名词短语“waking hours”,突出了纳兰清醒时百无聊赖的感受。
由于重建彻底抛弃了形式因素的再现,译文的意义的再现尤其是意境的再现就变得十分重要,这也是译者进行重建的首要目的。对形式的模仿可能会使译文“因韵失义”或“因形失义”,而重建的意义就在于摆脱原文形式对译文意蕴重现的干扰,译者通过形式上的再创作,使原文模糊的审美信息更有效地融入译文之中。翁译本通过使用抽象名词、语气词、破折号、倒装等手法对原文进行改写,使译文形散而神聚,更加传神地呈现了原文的情感和意境,使纳兰在军营之夜的寂寥与不安跃然于字里行间。翁译本把《如梦令》创造性地由一首词变为一篇散文,让译文读者在全新的形式中品味原文的神韵,感受着由译者创造的纳兰词的第二次生命。这种以形式的代偿来继承和发扬原文精神的做法为文学作品的推陈出新注入了新的动力。
结语
通过对以上几首纳兰词译本的分析可以看出,四位译者在翻译纳兰词时分别使用了不同类型的审美再现手段。本文以刘宓庆的模仿论和代偿论为理论支撑,在研究视角上呈现从以原语为依据和以译语为依据的模仿到二者的动态结合,最后到对原文本美学信息重建的演进方向。随着“模仿——重建”研究视角的变化,译者越来越注重其主体性的发挥,译者关注的重点也呈现出由形式因素向非形式因素转变的特征,即从注重再现纳兰词的形式美到注重再现其意境美。译者如何再现原作的美是其作为审美主体所做出的主观选择,影响因素有译者自身的风格因素、译者对原文的挖掘以及译者希望实现的美学效果。翁显良的“散体译诗”风格就体现在《如梦令》译本中形式因素的零还原,许渊冲一向注重诗歌翻译中的押韵形式,而许译《秣陵怀古》中就实现了对尾韵的重新处理。吴松林认为《采桑子》词牌的句式需要体现在译文中,于是他在翻译中使译本的形式与原文本保持极大贴合;而朱曼华认为《木兰花令》中过多的文化符号阻碍了译语读者的理解,所以对词中的部分内容做了省译和意译。四位译者赋予了纳兰词译本多样化的美学特征,也赋予了纳兰词更高的传承价值,使纳兰词化为多彩的样貌,在英语世界中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