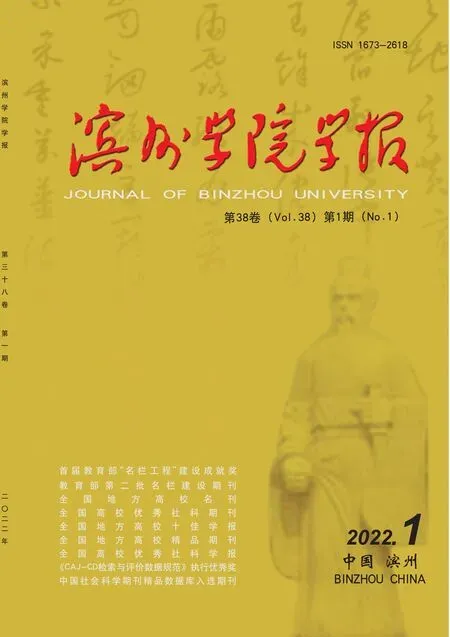南宋夏贵军事谋略评析
2022-11-22熊梅,张典
熊 梅,张 典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夏贵(1197-1279),淮西安丰军(今安徽寿县)人,南宋重要抗蒙将领,颇负军事才能,史称“资精悍,能夜视,工劫寨,累有战功”[1]36。他立足晚宋江左,在南北对峙的历史环境下,没有东晋桓温拓地河南的功绩,亦无宋武刘裕问鼎长安的壮举,不以战绩闻名天下;他犯科配隶,不识之无,未能效仿南宋文臣武将著作兵书传世,不以军事理论享誉四海;他由宋入元,声名狼藉,受到后世学人诟病,不以忠君护主流芳千古。然晚宋深陷战争泥潭、国运垂危之际,夏贵结发从军,折冲千里,年逾六旬方开阃,“晚取节钺致使相”[2]278,“崎岖戎马,东奔西走,补救于末造者”,先后庇护巴蜀、捍蔽鄂渚、屏藩两淮,为挽救赵宋危亡殚精竭虑,“使其能保危疆,支撑半壁”[3]523。过往儒家士人基于封建伦理纲常的出发点,着重讨论夏贵的叛臣身份,冠以贪生怕死、卖国求荣的名号,自20世纪初起,逐渐有学者开始重新客观审视夏贵,集中于对其生平事迹的整理与研究(1)屠寄《蒙兀儿史记》(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697页)、柯劭忞《新元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9-2831页)中为夏贵立传,矫宋、元二史之不公;孙克宽《入元宋将夏贵事辑》(《大陆杂志》第27卷第2期,1963年,第1-8页)整理各古籍文献中夏贵事迹;方震华《近四十年南宋末政治史中文论著研究》中认为夏贵“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0期,1992年,第207-218页);段玉明《论夏贵》(《钓鱼城与南宋后期历史中国钓鱼城暨南宋后期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407-424页)考证夏贵生平事迹,并对夏贵与吕氏军事集团的关系,鄂州、丁家洲战败责任进行了辨析。,然疏于对夏贵军事谋略的系统研究,未改变夏贵怯懦、庸将的传统形象。本文拟利用夏贵军事实践对其军事谋略得失进行反思(通常而言,军事思想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军事哲学层次上,主要有战争观、军事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二是军事实践层次上,主要包括国防建军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军防主张)、指导军事斗争的基本方针和原则(战略战术)。(参见贺幸平主编:《高校军事理论教程》,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段玉明先生指出:“由于夏贵主要是一个出入沙场的战将,在军事理论与治军方略方面无多建树我们不应苛求。”(段玉明:《论夏贵》,《钓鱼城与南宋后期历史中国钓鱼城暨南宋后期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故本文讨论夏贵军事谋略主要从军事实践层次出发,集中于其军防主张与战略战术),重新评价夏贵在晚宋军事领域的历史地位。
一、夏贵的军防主张
北宋军事学家何去非认为:“兵于人之国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4]8国防事业是国家安身立命的重要保障,虽不可穷兵黩武,也不可荒废忘战,张弛有度方可长治久安。《百战奇法》指出:“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圣人之深戒也。”[5]2489从统治者到边关将领,只有安不忘忧、常备不懈才能应对变幻莫测的边疆形势所带来的威胁与挑战。细绎夏贵加强边疆防御能力的行动,可归结为以下两点。
(一)筑城结寨
宋季以来,因河套养马地丧失与马政不举,宋军以步兵为主体。南渡后,再失陕西,使得骑兵愈加羸弱,南宋名臣虞允文道:“敌以多马为强,我以无马为弱。强弱之所以异,三尺之童皆知之”[6]3204,一语道破南北战力差距。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下,军事学家们提出诸多以步兵对抗骑兵的良策,仅战略而言,则是依托险要地形限制骑兵而发挥宋军强弩优势,即“用地阵而设险,以水泉而作固。”[7]9330故利用筑城结寨的方式与蒙军对抗成为宋军的首选。
史称夏贵“工劫寨”[1]36,善于袭扰敌军城寨据点,从侧面反映出夏贵对城寨的选址、构造以及城防建置等方面了若指掌,对利用山城水寨进行战略攻防轻车熟路。咸淳二年(1266),夏贵任四川制置使,为应对蒙军“据夔灭蜀”战略,保卫四川的生命孔道,其认真分析东川军力格局与地形地势,于枢纽三台山筑城,“城三台山,立为涪州”[2]277,加强东川抵御力量。咸淳三年(1267),“城叙州北岸登高山”[2]277,加强岷江与长江交汇处的防务,避免蒙军绕道川南进入长江,暗度陈仓。咸淳九年(1273),夏贵任淮西制置使,借鉴四川山城防御体系,“依山筑城”[2]277,强化淮西军事防御能力。另有怀远县“西北八里”[8]1005筑边军城的记载。上述记载均体现出夏贵善筑城的特点,惜对夏氏的筑城理论、设防思想没有详细阐释。宝祐五年(1257),枢密使贾似道携夏贵视察淮西荆山地势,询问守御良策。夏贵道:“荆山在涡河口,与涂山对峙,流淮贯其中而入海,两山束之如人咽喉,一有鲠则安丰、寿春断,则淮危矣。”[2]275精辟论证荆山筑城与两淮安危的密切关系。不久,蒙军亦“欲城荆山”,兵贵神速,夏贵放弃大型筑城器械,仅率轻兵前往,就地取材,“得石燧于才岩下,得古井二十有四于榛莽中,石可凿水可食”,艰苦作业,“不数月而城成”,立刻显示出重要战略价值,“后至者以数百艘载畚钟具而无所施”[2]275。胡昭曦先生给予高度评价:“在未来的战争中,荆山城在阻挡蒙军对两淮的进攻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9]189可见,夏贵不仅对城寨选址极具眼光,筑城技术亦可称道。
(二)人尽其才
北宋军事学家许洞认为,天、地、人是取得战斗胜利的关键,而其关系则是“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10]4故战争中应网罗一切人才,“但负有一能,军中皆有以用之,不可弃也”[11]48。若裨益战事,则“士无贵贱高下,有一德而可用”[12]2257。宋室南渡后,军事冲突成为常态,迫使南宋政府动用一切力量维系战争,学者陈亮认为应尽发天下“雄伟豪杰之士以共济大业”[13]21,反映了南宋社会的普遍观念。夏贵十分清楚广大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其用兵择将特点如下。
其一,不问出处。洪福本为“夏贵家僮”,虽身份低微,却负有军事才能,随军征战,“从贵积劳为镇巢雄江左军统制”[7]13269,德祐元年(1275)四月,在淮西大部沦陷的情况下,仍“复镇巢军”[7]929,尤显韬略。又辟黄介为广济簿尉,黄氏“平反死囚,尹不能抗”[7]13310,颇有才干。北界“许、蔡间有巨盗”,遭到蒙廷镇压后“逃入宋境”[14]3941,这些“归正人”虽为草茅贱士,但洞悉蒙军情机宜,夏贵悉数接纳,投入战争中(史载:“许、蔡间有巨盗,聚众劫掠,(陈)祐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随制置夏贵过汴,祐斥下马,挝杀之于市。”(宋濂等:《元史》卷168《陈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又载:“(宋亡夏贵北上)随行带领将佐三百余人。”(刘一清:《钱塘遗事》卷9《祈请使行程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综合两条史料,可知这些“巨盗”被夏贵委以将佐之职),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上述事例中不排除夏贵培植亲信的嫌疑,但毕竟发掘了一批可用的人才,“使在彼无弃材,在我无遗用”[15]263,继承了“广行招致,随材任用”[15]153的用人思想。
其二,军民联防。端平入洛后,南宋国土日蹙,人口益减,面对强大的蒙军,单凭军队的力量势必难支,故依靠民丁协同作战,有利于抗击侵略。早在北宋备御西夏时就曾采取过军民联防的方式,与夏贵同时期的名臣崔与之认为“选守将、集民兵为边防第一事”[7]12258,“七开大阃”李曾伯措置广西时亦“辑约溪峒,团结民丁。”[16]346夏贵任制阃四川时,除筑城结寨外,还“迁涪之军民以守之(三台山)”,“迁叙之军民”[2]277守叙州北岸登高山。一方面加强城寨防御能力,完善山城防御体系,保存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军民协同防守,闲时共劳作,战时齐御侮,提高城寨的战斗续航时间。
二、夏贵的战略战术
夏贵戎马倥偬,与蒙(元)进行军事斗争是其军旅生涯的主要部分,其中饱含夏氏指导全局的策略、作战具体部署以及克敌制胜的谋略。夏贵的战略战术可分为两个次级层面:其一,宏观的战略思维;其二,微观的战术指导。
(一)战略思维
景定元年(1260)四月,夏贵凭白鹿矶战功迁“知淮安州兼淮东安抚副使”[7]873,跻身阃帅,肩负战局的战略攻防,观其二十几年边关指挥经历,可大致窥见夏贵的战略谋划。
1.贵谋先备春秋时期孙武提出“兵者,诡道也”[17]2,高度概括了战争是谋略的艺术。及至宋代,军事学家们对谋略推崇备至,谓“经武之略,在于贵谋”[18]5010。《百战奇法》提出“凡用兵之道,以计为首”[5]2355,肯定计谋在战略筹划中的重要地位。除对传统军事谋略的阐发外,宋代军事学家们创造性地将“谋”的含义从单纯的军事计策扩展至战前准备环节,“先料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险易,粮之虚实”[5]2355,抑或“欲谋行师,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阵,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10]18,是谓先备。
夏贵对用谋与战前准备十分重视。景定五年(1264),夏贵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入蜀作战。为完成理宗“克复成都”[2]276的重托,夏贵入蜀后即开始筹划进攻成都的作战计划。其时,利州至成都一线为蒙军占领,又设“四帅府”(2)即阆州大获城、果州青居城、广安军大良城、蓬州运山城。控嘉陵江、渠江,进逼川东忠、万、开、达等州,正面防守严密。故此,夏贵大胆设计从川南沿沱江北上的大迂回作战。
首先,夏贵以泸州神臂城为转运枢纽,聚集兵士,囤积粮草,养精蓄锐。其次,夺取沱江的控制权。咸淳元年(1265),遣都统昝万寿扫清沱江上游蒙古水军,获“云顶山、金堂峡之功”[7]894,牢牢把控沱江上游。稍后,夏贵亲率精兵自神臂城出发,“潜师溯资江而上”,突袭蒙将刘整部,“斩馘数千人,整败归”[19]2830,从而确保资江畅通无阻(3)资江,沱江下游资州至泸州段。史载:“雒江(沱江),出成都府汉州什邡县西北六十里之章山……又东经资县治南,而为珠江,亦曰资江……雒江之名,亦随境而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6《四川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14页。),保证士兵、军粮及物资能从川东沿长江运送至泸州,再进入沱江运往成都东北近郊。最后,夏贵率五万宋军溯流而上,绕过蒙军正面防线,顺利到达成都东北部展开作战。
虽然该场战役以失败告终,但就前期准备工作来看,环环相扣,有条不紊,无不见夏贵之良苦用心。令人慨然的是,两年前川军仅“闻赛存孝(刘整)至”即“遁去”[14]3786,经夏贵整顿,竟与刘整厮杀得胜,其中固有奇袭的优势,但夏贵对军心凝聚的作用亦不可小觑。仅此战例,可见夏贵策划战略进攻时,对兵力、军心、地势、粮草等方面较全面地进行考虑,其备至矣。
2.藏战于守宋朝因“将从中御”“冗兵”等问题,军队战斗力不尽人意,故长期保持守势,奉行“专力防守”的消极思想。然而,战略思想上的单纯防御使宋军失去灵活性,时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处境。面对这种状况,自北宋中期开始,军事学家们提出了“藏战于守”“守中有攻”的积极防御思想。曾公亮认为城邑防守中当“以战代守,以击解围”[11]653,以善守代死守。南宋思想家陈亮继承其说,谓“以攻为守,以守为攻,此兵之变也。攻专用攻法,守专用守法,其败也固宜然。守专用攻法,攻专用守法,亦焉得而不败哉?”[13]45将这种思想扩展于整个军事活动中。
景定三年(1262),蒙将杨大渊献取蜀之策,“取吴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据夔”[14]3778,是谓“据夔灭蜀”战略。蒙廷全权委任杨氏家族实施该战略,集中表现为攻打巴、忠、达、开、万等州,期冀绕开重镇重庆直接攻击夔州。[20]据宋蒙双方记载,该域战事颇为激烈,有赖于各将守御,未被蒙攻破。(4)史载:“(景定三年正月)甲戌,诏权知梁山军李鉴守城有功。”(脱脱等:《宋史》卷45《理宗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80页。)另有:“(中统)三年春,世祖命出开、达,与宋兵战于平田,复战于巴渠…乃遣其侄(杨)文安攻宋巴渠…复使文安相夔、达要冲,城蟠龙山,宋兵来争。”(宋濂等:《元史》卷161《杨大渊传》,第3777页。)夏贵任蜀帅后,清晰地认识到守御诸州固然重要,却是离本檄末,他意识到蒙军频繁袭扰诸州之基础在于对渠江的把控(5)蔡东洲先生认为:“渠江上接米仓道,下连钓鱼城,是宋蒙双方物资补给、兵士运送、战斗应援的大通道。”并将杨氏家族夺取渠江控制权作为“据夔”战略的准备工作。(蔡东洲:《杨大渊家族归降与宋蒙(元)东川战局》,《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48-55页。)。因此,夏贵一面加强川东诸州的防御力量,抵挡蒙军(6)以开州为例,咸淳元年(1265)蒙将杨文安攻而不得,咸淳二年(1266)千户王福“破其城”,咸淳三年(1267)十月宋军收复。(宋濂等:《元史》卷161《杨文安传》,第3780页。);另一面时刻关注渠江沿线蒙军据点动态,观衅待时。咸淳二年(1266)底,夏贵遣张珏等将乘蒙千户散竹酒醉之际,夜袭渠江下游重镇大良城,“大战城中,复其城。”[7]13281宋军借此契机,逐步清理广安内蒙军山城据点,于次年二月,“克复广安军”[7]897,收复全境,一举打破蒙军四帅府的壁垒,联合钓鱼城与礼义城,重新构建山城防御体系,并夺取了渠江的部分控制,根本上缓解了川东诸州的紧张态势。
川东诸州“专力防守”,抵御蒙军正面进攻,虽有成效,却是扬汤止沸,颇为被动,夏贵灵活布局,化消极防守为积极防御,牵制蒙军主力,捕捉蒙军破绽,遇有战机则转守为攻,打击蒙军赖以进攻的运输通道,使川东局势稍有缓解,可谓守中有攻、藏战于守。
3.积极江河防御长江自古以来便是贯通中国东西部的运输大动脉,白居易曾作诗“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来描述长江交通运输的繁盛景象。南宋时期,由于秦岭、淮河以北的国土沦丧,京城由开封迁往临安,宋朝交通运输趋势由南北走向转变为东西走向,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长江凸显出重要战略价值。张锦鹏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江、运河为快速运输军队及物资,为军队大规模集结、抗击及防御外敌进犯提供了快速转运通道和天然屏障。”[21]97故此,妥善利用江、淮天险关系着南宋政权的安全。
咸淳四年(1268)十二月后,夏贵先后担任沿江制置副使、淮西制置使,担负长江中游防御的重任,数次参与江面战斗、巩固江防。其中,最能体现夏贵战略思维的当属其作为主要负责人主持的鄂州之战。
咸淳十年(1274)七月,元丞伯颜自襄阳攻鄂,宋廷急调各阃增援前线,夏贵奉旨“上流应援”[2]277,率淮西舟师配合各部守军展开防守。其时,宋军分为三部,夏贵以战船万艘“分据要害”,是谓阻敌入江;京湖宣抚使朱禩孙“以游击军扼中流”[14]3101,是谓阻敌渡江;都统王达率精兵八千驻阳逻堡,是谓坚城固守。九月,伯颜“分军为三道并进”[14]3100,兵峰直指鄂州。
先是,元军欲夺汉口入江,夏贵率军“并力守御”[22]4,不得,复与宋军“战于柳子、鲁洑、新滩、沌口”[14]3256,皆不得入。元千户马福建言:“沦河口可通沙芜入江。”[14]3101宋军统制官王顺对沙芜口给予高度重视,他建议“栅沙武(芜)口及沌口”,然夏贵意图以沙芜口诱敌入武湖,“欲纵北船入口,然后与战。”[23]69夏贵的考虑在于,各入江口通道狭小,虽可阻敌入江,却无法有效杀伤敌军,而位于长江北面的武湖,烟波浩渺,自古即为操练水军之所(史载:“(武湖)在(黄陂)县南四十九里,黄祖阅武习战之所。”(李吉甫:《元和志》卷27《江南道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既适合大规模水军作战,亦与长江有一定缓冲,选取武湖作为战场,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南宋水军优势以大量杀伤敌军的有生力量,从根本上解除危机。然而,元军佯攻汉口打乱了夏贵的部署,其“移兵援汉阳”[14]3101,元军乘势“自汉口开坝引船入沦河,转沙芜口以达江”[24]4933。夏贵觉察后迅速反击,“帅汉鄂州师顺下流迎敌”[22]4,夜袭北营,却不慎被元总管张当发现踪迹,败归。稍后,元将阿术采用捣虚之计,突破宋军中流防御登陆长江南岸,架设浮桥供大军渡江,伯颜亦于阳逻堡败夏贵主力,鄂州之战以元军胜利落下帷幕。
是役虽败,然夏贵在实施江河防御时具有“大创尽歼”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其不以遏敌踟蹰敷衍塞责,反而创造战机,试图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一劳永逸地解除鄂州困局,不慎判断失误致敌入江,夏氏并未畏敌怯战,反而趁元军立足未稳,潜师夜袭,惜被元军察觉铩羽。客观地来说,相对于王顺等将领的固守战略,夏贵的积极江河防御战略思维无疑富有进取性与前瞻性。
(二)战术指导
夏贵在“积功到大阃”的过程中,长时期担任中下级军官,指挥少量精兵作战,在战术层面捷报频传,“绫诰叠若坻”[25]128,用兵如臂使指,归纳其战术运用主要有以下两类。
1.机动作战机动性是军队作战的重要部分,古语有云兵贵神速,高机动性往往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夏贵指挥精兵作战,对军队机动性报以极大热情,用兵神出鬼没,使敌军难以窥探行踪与目的,最终把握战机达成军事目的。
嘉熙二年(1238)正月,蒙军犯安丰,宋廷“诏史嵩之、赵葵应援黄州、安丰。”[7]815夏贵作为先锋率先抵达战场,见敌军势众,乃“树五色旗帜于废寺、林落中间”,复“以空寨设疑城于瓦步”[2]275,制造援军抵达的假象,主力则藏踪蹑迹,悄然临城。蒙军误以疑城为宋援,“空围城兵以攻瓦步,竟劫空圃”,复还安丰,而夏贵已入城,蒙军顿失军心,“始溃围去。”[2]275其后,宋将余玠、赵东等援军纷至,终解安丰危机。客观地说,夏贵入城不仅打击了蒙军士气,亦为援军争取了宝贵时间,而其制造信息差潜师入城正是成功的关键,充分发挥了军队的流动性和速决性。
前述咸淳元年(1265)资江突袭刘整之战例,亦是“出刘整不意”,败归元军皆曰:“蜀被兵以来未有此战”[2]277,这不仅体现了机动作战的突然性,更显示了夏贵对军队高机动性的追求与娴熟掌握。
2.奇正之道为了达成既定战略战役目的,动用少量精锐部队以特殊方式进行的非常规作战,谓之奇正之道。孙子认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17]69,首倡在战术中用奇的重要性。宋代军事学家们进一步阐发,认为攻守之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26]41,但曾公亮认为“故不虞以击,则谓之奇兵;匿形而发,则谓之伏兵。其实则一也。”[11]149各家的争鸣促进了奇道用兵理论的发展,得出“兵不奇则不胜”[11]149的结论。该军事思潮在夏贵的战术运用中多有体现。
淳祐六年(1246),蒙军围高邮,夏贵自告奋勇,“以百兵往赴之。”[2]275抵达前线后,夏贵部署百名步军夜伏于蒙军营寨外,另率十人伏于寨旁。时蒙军戍卫以口哨为号,夏贵“效其声而混之”,继发一响砲于寨中,蒙军“夜乱自相攻击”[2]275,夏贵趁机率伏军杀入,大破敌军。宝祐四年(1256),淮东重镇扬州陷入重围,夏贵“伏兵白马庙前”[2]275,大败蒙军,策应扬州。景定元年(1260)二月,元军驻扎白鹿矶两岸,以浮桥作为联系,“时南北两岸氈帐为满”,旌旗蔽日。宋军数攻失利,夏贵“乃部分其军”,以精兵自上流潜至浮桥下,“每夜五更一点至桥下”,每每引得蒙军出动,宋军却不战而退,如此反复,蒙军习以为常,数日后,夏贵精兵于一更至桥下,趁桥上防守空虚,发起突袭,“一鼓而桥尽断”[2]276,切断两岸蒙军联系,次日尽夺其船。同年,蒙将李松寿挑衅边境,夏贵“出奇兵潜伏南渡门”,舟师主力往来弥勒浦,蒙军兵至,夏氏以“伏兵掩袭鱼梁沟之哨骑”,遣舟师“夺犯刘伶台之战舟”,后水路并进,“松寿仅以身免”[2]276。
由上可见,夏贵善于奇正之道,常用少量精兵对敌薄弱环节实施精确打击,战法方式独特、出击隐蔽突然,果若“惊前掩后,冲东击西,使敌莫知其所备”[5]2415。
三、制约夏贵军事谋略的因素
夏贵的传统形象是怯懦、庸将,与前文所述的足智多谋大相径庭。从时间分布来看,开庆元年(1259)升阃前胜多败少,是年后败多胜少,特别是在决定南宋国运的鄂州之战、丁家洲之战中表现不佳,故夏贵战绩发生逆转与其角色转变关系密切。为了全面客观评价夏贵军谋特色,有必要对限制夏贵军事才华的因素进行探讨。
(一)军政积重难返
夏贵跻身封疆制帅后,其角色从单纯服从命令的执行者变为掌控一域攻防事宜的布局者,麾下部曲规模急剧扩大,使得夏贵的指挥愈受客观原因(即南宋军政优劣)的影响。
1.指挥体系叠床架屋如前所述,当兵员数量较少时,夏贵与士兵间的中间环节很少乃至没有,将卒山鸣谷应,在作战时能够发起精准打击,出现突发状况时能够及时做出调整,夏贵的指挥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当夏贵出临高位后,部队指挥层级增多,对其调遣部队产生负面影响。
其一,纵向信息传输缓慢。受古代通信技术的局限,军队规模的扩大,部队指挥层级的增多,无疑会对信息传递的时效性产生影响。尽管南宋设有完备的国家通信工程——邮传系统,但其“散漫混乱,机构重复设置,制度形同虚设”[21]228,效率低下。信息由某作战单元传往决策中枢,再由决策中枢加工后传递回原或其他作战单元的双向传递过程需要相当的时间,导致某些信息不能被及时利用,影响了各作战单元间实现良好的协同作战。其二,横向指挥体系增加。南宋后期军队系统比较复杂,组织形式多样,据王曾瑜先生研究,南宋后期有“各种番号新军的创设,都统制的滥授,部分总管、钤辖、都监等重新成为统兵官,加之一般由文臣担任的宣抚使、制置使等主持大军区,许多知州、知府和知军任节制屯戍军马”[27]245。十羊九牧的军事指挥体系不利于制帅的发号施令。
迟滞的通信系统与臃肿的军队体系导致夏贵在进行战略攻防时协调独立单元具有一定困难,信息容易在传递过程中失效与失真,进而造成军队运转呆板机械。咸淳十年(1274)夏,夏贵率军十万围正阳,攻势甚猛,“决淮水灌城几陷”[19]2283。面对宋军汹汹气势,元廷急诏元将塔出率军救援,取道颍州,设伏兵击溃颍州北关宋军后,“长驱直入正阳”,与元将阿塔海会师,渡淮河与宋军决战,“至中流,殊死战”[19]2283。各路元军纷至,元将怀都率步军沿淮河西岸行进,“至横河口,逆战退之”[14]3197;元将孟德从水路出击,“夺战舰数艘”[14]3903。夏贵纵有雄师十万,面对元军分道出击、灵活多变的攻势,最终溃师而去。
2.军官素质良莠不齐夏贵为中下级军官时,与底层士卒箪醪投川,有助于部队的良性发展。其一,士卒受夏贵的精心训导,保持强劲战斗力,前述夏贵百兵奇袭蒙军大营即是明证;其二,夏贵待兵和善,为小校时,部役必使军士“归饭”,左右纠正按例应言“送饭”。夏贵道:“送则各务夸美,必置鱼肉,皆出强为;归则老小团聚,随其有无。”[28]47亲密的将卒关系有利于激发士兵高昂的战斗热情。
当夏贵升为阃帅后,庞大的军队规模使其必须借助大量的中下级军官对全体士兵进行管理,其个人能力与魅力的影响减弱,各部实际战斗力因中下级军官的能力而变化。晚宋时期军官素质互有参差,虽然不乏军事才能优秀的将领,但普遍存在庸碌无能之辈。这些将领无退敌之勇,“方以败而为功,待其去而奏捷”[29]80,专力于役使士卒,“主兵官苦以劳役,日夜罔休”[7]4872,严重损害士兵战斗力与斗志。此外,部分贪生怕死的主兵官面对元军的进攻不战而降,如德祐二年(1276)丁家洲之战后,元军主力东下,淮西“知州孟之缙及知无为军刘权、知镇巢军曹旺、知和州王喜,俱以城降”[14]3105。这不仅破坏夏贵对淮西的整体布防,亦可能泄露军事机密。
由于军官素质良莠不齐,导致夏贵统帅的部队战斗力分配不均,强弱有差,特如上述孟之缙等拱手而降之徒,成了全军的安全漏洞与敌军的突破口,使得夏贵麾下看似人数颇众,然战斗力不如以往精兵。
(二)治军理政有瑕
通常而言,高级将领拥兵巨万,除出色的军事指挥技术外,统帅力亦是至关重要的能力,其表现在对麾下的节制与管理上,要求将领拥有杰出的行政管理能力。夏贵起自白丁,父母早亡,少时落草为寇,刺配入伍,戎马一身,文化水平十分有限。因此,尽管夏氏作战勇猛、南征北战,但对于如何治军理政,则不如孟珙、李曾伯等儒将,从而限制军队战斗力。
1.厚赏易力宋代承袭五代“厚赏养士”的措施,企图利用厚赏鼓舞士气、维持秩序、提高战斗力。在时局动荡、战争频发的时代,此举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夏贵是自底层擢升而上的战将,深知士卒爱利胜过言义,故常常用丰厚的物质财富换取将士们浴血奋战,而不是灌输爱国信念激发士兵的正义感与荣誉感。如景定元年(1260),夏贵任淮东安抚副使,奉命收复涟水,蒙将李璮出兵阻挠,大破之,得“赐钱百万”[30]2898,夏氏厚赐兵士,士气大涨,不仅顺利攻克涟水,竟逾蒙境连下七州四县[14]3477;咸淳七年(1271),沿江制置副使夏贵策应援襄大军,“以钱二百万随军给用”[7]908。夏贵激赏部曲,士卒皆用命,任围攻襄阳的元军“生兵日增,关隘日密”[23]174,夏贵部竟突破元军防线成功运送物资至襄阳,稍解燃眉之急。然而,这种方式虽然可以短暂提高军队战斗力,但非长久之策,当士兵对赏赐不满时,十分容易导致兵变与消极作战。开庆之役后,南宋财匮力绌,贾似道行公田法多方括敛,然收效甚微,至咸淳末,南宋经济濒临崩溃,宋廷不得不减少对前线将士的赏赐。咸淳九年(1273),夏贵任淮西安抚制置使,麾下较任淮东安抚副使及沿江制置副使时更众,宋廷仅“赐钱百万激犒备御”[7]917,其无奈削减赏赐,极大打击士卒的积极性,厚赏易力模式产生反作用,后续作战多遭败绩。可见,夏贵采取经济手段提升军队战斗力的方式必须建立在雄厚资金的基础上,较岳家军等以爱国主义为信念的部队有很大局限。
2.招募无法咸淳间,战事频仍,军队缺员严重,又因主兵官随意压榨剥削士兵,“榜掠之酷,兵不堪命”[7]4872,造成逃兵众多、百姓避征的现象。夏贵作为一方制帅,肩负护卫一域之重任,为维持军队规模,常强捕平民为兵(7)史载:“咸淳间,招兵无虚日,科降等下钱以万计。奈何任非其人,白捕平民为兵,召募无法,拣选云乎哉!”(脱脱等:《宋史》卷194《兵志八》,第4840页。)未明言孰为“非人”,又载:“至咸淳中,大将若吕文德、夏贵、孙虎臣、范文虎辈,矜功怙宠,慢上残下,行伍功赏,视为己物,私其族姻故旧,俾战士身膏于草莽,而奸人坐窃其勋爵矣。”(脱脱等:《宋史》卷196《兵志十》,第4894页。)比对两条史料,时间吻合,则夏贵似为其一。,“召募无法,拣选云乎哉”[7]4840。胡乱强征导致军队鱼龙混杂,“有老弱者,有投巧者,有供官吏厮役者,有为将帅营运者,精锐不能十一”,实乃乌合之众,既缺乏战斗信念,“一有调发往往涕泣,不以胜敌自期,先以败衄自处”[31]2120,亦难以接受专业的军事训练,“涅刺之后,更不教阅”[7]4872。时人要而论之,谓“简汰不严,教阅不习”[31]2120,这无疑降低军队职业化程度,严重削弱军队战斗力,临战时,“前锋未接,后骑已遁”[31]2120,气馁若此,何以任战?丁家洲之战中,号称“诸路精兵”[7]13785的13万宋军与敌一触即溃,夏贵叹曰:“诸军已胆落,吾何以战!”[7]13786夏贵不加筛选的补充兵员,是导致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夏贵戎马经年,通过丰富的军事实践,形成富有实践性的特色军事谋略,主要包含军防主张、战略思维和战术指导三个层面。其中,军防主张的重点是扼襟控咽及任人唯能,着眼于实用性。其战略思维侧重于绸缪牖户、以屈求伸及积极江河防御,特别是善于创造利己作战时空,谋求消灭敌军有生力量,抽薪止沸,暗合“大创尽歼”思想。战术指导侧重于军队机动性与奇正之道,在敌众我寡的客观条件下,针对敌军薄弱环节,避实击虚,险中取胜。
夏贵晚年战绩不佳,究其原因,是职位迁升导致夏氏军事才华愈受晚宋腐败军政与个人统帅力欠缺的限制。前者表现在晚宋军政不举引发号令阻塞:指挥体系尾大不掉掣肘将领调兵遣将的时效性,军官素质参差有别梗阻主帅运筹部署的可靠性。后者体现在夏氏个人行政管理才能缺陷导致治军无方:厚赏易力,短期可激励士卒用命,赏阙则士气低迷乃至反噬;招募无法,暂时能保持军队规模,实则降低军队职业化程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夏贵的看法偏向负面,经过对夏贵军事谋略及不足的评析,其或许称不上旋乾转坤的旷世名将,但绝不是欣生恶死的怯懦庸将。客观论之,夏贵确难以媲美高斯得、文天祥等才华横溢、挥斥方遒、流芳百世的万古“名臣”,亦无法比肩史弥远、贾似道等势倾朝野、杖节把钺、呼风唤雨的不世“权臣”,然其奋起于赵宋危如累卵、苦苦挣扎之际,飞刍挽粟,赴汤蹈火,数逢偾战而不挠,屡受挫衄而不屈,含辛茹苦,“国亡始降”[3]524,诚可谓兢兢业业、扶危救困、劳而不怨的苦功“劳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