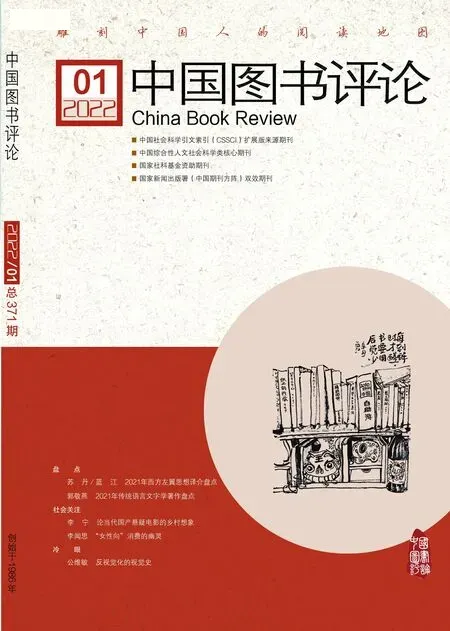国产悬疑剧的社会寓言与叙事伦理
2022-11-22□杨毅
□杨 毅
【导 读】在数量众多的悬疑剧中,偏重社会现实题材而非仅仅依靠推理的作品引起了观众更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社会反响。本文认为,悬疑剧对于社会现实的想象是寓言式的,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处于敞开与隐匿之间的叙事伦理。悬疑剧正是通过对肉眼可见的“主观暴力”的凸显,而巧妙地隐匿起支配社会根本性矛盾的系统暴力,而达到对社会问题的“敞开式遮蔽”。
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悬疑剧的热播成为中国影视行业乃至整个大众文化领域值得关注的现象。各大网络平台几乎同时推出了各自的产品,从而引发了悬疑剧的大量涌现:爱奇艺打造的“迷雾剧场”推出包括《隐秘的角落》 《沉默的真相》在内的6部高质量悬疑剧,优酷的“悬疑剧场”则以 “悬疑+”的模式尝试类型突破,腾讯也推出了《摩天大楼》等多部 “女性向”的“她悬疑”。有趣的是,与此前流行的穿越玄幻、都市职场、爱情甜宠等国产类型剧被频频吐槽或口碑两极分化的状况不同,这一波悬疑剧的热播得到了绝大多数网友的追捧,甚至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仅有的为数不多的质疑,也仅仅是针对某些剧情逻辑的疏漏或个别细节的处理表示不满,而很少有人从作品的艺术性或思想性的层面予以否定。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数量众多的悬疑剧中,偏重社会现实题材而非仅仅依靠推理的作品引起了观众更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社会反响。《隐秘的角落》连日霸占微博热搜,引发广大网友对剧情的又一轮解读,剧中某些经典的台词和歌曲迅速成为流行语;《沉默的真相》的豆瓣评分达到国产网络剧几乎从未有过的9.2的高分,白宇饰演的男主角江阳深入人心。种种事实表明,当前悬疑剧特别是社会现实类的悬疑剧的蹿红,隐含了社会文化的诸多症候,因此值得关注和思考。问题在于,为何偏偏是这两部剧从众多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爆款?它们体现出什么样的文化症候与社会心理?还有就是在它们纷纷以现实题材著称的背后,又是如何展现出社会问题的呢?
一、作为寓言的悬疑剧:从犯罪推理剧到社会问题剧
如果我们把悬疑作为一种类型元素来看待,那么这一文类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侦探小说。按照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观点,侦探小说的出现与工业革命带来的大城市的布局和熟人社会的解体有关:“侦探小说所特有的社会内容就是个人踪迹在大城市人群中的隐没。”[1]由于大城市的人们处于陌生人社会的环境之中,因此他们在城市行走的过程中很难遇到熟人,只能作为“人群中的人”而行色匆匆,直到不留痕迹地消失。这种陌生人社会表现出极大的“匿名性”:既是人们过往经历的匿名,也是个体当下身份的破碎、片面和游移。人们彼此讳莫如深,各自的内心晦暗模糊,不仅无法了解对方所做的一切,甚至无法表达自身的感受。这也是以爱伦·坡(Allan Poe)为代表的作家创作的一系列侦探小说所表现的主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匿名性和破碎感,犯罪的前提就难以形成,侦探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不过,齐泽克(SlavojŽižek)将这一时期的侦探小说称为“侦探故事”(detective story),因为他们的小说只是扩展而成的短篇故事,即“以探险故事的形式写成的冗长倒叙”。只有到了20世纪20年代,通俗文化领域的侦探故事开始向侦探小说 (detective novel)转移,这导致了侦探故事很快销声匿迹。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在《血腥的谋杀》(Bloody Murder)一书中也认为20世纪20年代是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他发现在此之前,“人们没有在评价侦探小说时考虑过它有一定的规则,没有意识到不仅需要制定严格的规则,同样需要严肃地遵守规则。不过,到了20年代末,出现了一些文学理论,它们试图制定一系列规则,要求侦探小说作家都必须遵守”[2]。这些规则包括侦探的角色、案件调查的手法、罪犯的身份、人物和情感的互动,等等。它们的出现对应了侦探小说文体及其功能的变化,即从供人消遣的猜谜游戏,转变为可供阅读的作品。
而与之同时发生的,则是现代小说最终战胜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齐泽克对此解释道:“现代小说和侦探小说均以同样的形式问题(formal problem)为中心。这形式问题就是非可能性 (the impossibility)的问题:以线性、一致的方式讲述故事,是不可能的;显现(render)事件的 ‘现实主义’式的连续性,是不可能的。……要在意味深长的生活故事的整体性中锁定某个创伤性事件(谋杀),也是不可能的。”[3]尽管齐泽克很快把问题引向了精神分析的维度,但这也提醒我们,源于侦探小说的悬疑类型在文体上不仅与现代社会和文学艺术自身的转型密切相关,还意味着它始终在社会现实与文体类型的互文叙事中发挥着潜在而重要的作用。简言之,正是瞬息万变的风险社会所特有的“复杂叙事”,才促成了这一文类自身的转型发展。
不妨以推理题材最为盛行的日本为例。作为推理小说奠基人的江户川乱步,根据日本独特的居住空间创作出密室杀人小说,展现的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东京的新都市地景。[4]“二战”后的日本出现了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推理。此类作品着重挖掘犯罪的深层原因特别是社会根源,而不再仅仅依靠逻辑推理或营造恐怖气氛来吸引读者。这同样与战后日本在经济重建过程中的社会思潮密切相关。日本战后经济的崛起建立在因战败而造成的社会巨大断裂的基础上,由此暴露出的种种社会问题成为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现实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在传统的现实主义逐渐让位于现代主义之后不久,现实主义的卷土重来成为一个有趣的悖论:一方面,悬疑作品正是基于现代社会动荡不安的状态而发生发展,因此“天然地”带有某种现实品格;另一方面,悬疑作品自身的文体类型又决定了它是一种与传统现实主义手法难以协调的叙事艺术。所以,悬疑剧对于社会现实的想象就只能是寓言式的。悬疑剧以悬念的制造为核心,但悬疑剧中的悬念乃是基于不可靠的叙述者而产生的一种限制性视角,它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对事件本身的否定和质疑,反而恰恰是一种认可和强化。因为只有在预先承认一切事件都可以经由理性的推演而得到解决的前提下,悬疑剧制造的悬念才不仅是令人恐惧的,更会显示出令人信服乃至反思性的一面。这也正是悬疑剧作为社会寓言所表现出的品格。
按照这个思路,中国当代悬疑剧的发展同样是以寓言的方式回应当下变化发展的现实,大致经历了犯罪推理剧到社会问题剧的转变。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电视剧行业并没有“悬疑剧”的类型,只有大量公安题材剧的播出,如21世纪前后的《永不瞑目》《重案六组》《玉观音》等。2004年以后,公安剧由于政策导向等大幅缩减,古装探案剧成为荧屏新宠,如 《少年包青天》《神探狄仁杰》 《大宋提刑官》系列电视剧。这些古装探案剧大多以历史上的清官作为原型,着力展现他们在断案过程中的过人本领。这些作品通过塑造无所不能又为民请命的清官形象,建构了一个与庙堂或官方“对立”的民间,从而尽可能地让他们在民间除暴安良、惩戒贪官。但由于无法摆脱 “清官政治”的民众想象,它们仍然是对封建帝王政治的变相认同。另一种带有悬疑色彩的类型是谍战剧的热播,如《暗算》《潜伏》《黎明之前》。这些以谍战的形式重述国共历史的作品,同样符合当代人的价值观和心理需求。——谍报人员铤而走险的任务和命悬一线的处境投射了不稳定的中产阶级的自我想象,不少谍战剧更成为现代职场的教科书。2017年,网剧《白夜追凶》和 《无证之罪》的播出颇受观众好评,从而一改此前现实题材悬疑剧乏善可陈乃至粗制滥造的局面。这两部剧集尽管被网友分别看作“本格派”和“社会派”这两种不同的推理类型,但主要表现的还是犯罪作案的动机和过程,以及由此牵扯出的人物心理乃至人性的问题,而远没有当前悬疑剧直面社会问题的程度之深,因此不妨称之为犯罪推理剧。
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悬疑剧拥有较大的受众和相对广阔的市场,但中国的悬疑剧一直成就不高。主创人员仅仅看到了这种类型剧的商业价值,却意识不到作为社会寓言的悬疑剧所具备的文体政治,因此无法有效地植根于社会现实的具体问题而做出有力的回应和反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20年大火的《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掀起国产悬疑剧的新一轮热潮,尤其是在社会关切的现实问题上开拓了国产悬疑剧的新格局。《隐秘的角落》展现了三个“坏小孩”在无意间拍下张东升杀人的视频后,如何在与他周旋的过程中一步步地走上 “黑化”之路。尤其是绝顶聪明又无比腹黑的朱朝阳,更是借刀杀人地实施了“完美的犯罪”,长大后不啻另一个张东升。这些细思极恐的情节不得不令人反思家庭、社会、教育所隐藏的种种问题。《沉默的真相》则以探案剧的形式讲述了一个有关司法正义的故事:年轻的检察官江阳接手多年前的侯贵平案,但由于此案牵扯高层官员的丑闻,导致江阳在查案的过程中百般受阻,但他从未放弃,直至付出了事业、家庭乃至生命的代价。该剧涉及了乡村性侵、贪污腐败、冤假错案等诸多敏感的社会议题,因此极大突破了悬疑剧介入现实的力度。简言之,社会问题的直接呈现不仅是此次热播剧的重要特点,也是它们引发观众共鸣并迅速成为爆款的原因所在。
也就是说,在这一波悬疑剧蹿红的背后,其实都含有大量表现社会现实或者干脆说是社会问题的揭露,而并不主要揭示案件本身的前因后果。这与此前悬疑剧主要通过逻辑推理来解密犯罪过程的探案剧形成了较大差异。《隐秘的角落》在剧情开始的前几分钟就把张东升杀人的全过程如实展示出来,这就将谜底直接呈现给观众,进而揭示案件背后的动机,以及人物扭曲的心理和复杂的社会关系。该剧虽然在技术层面上营造了悬疑紧张的气氛,但真正打动人的不是惊悚或灵异的镜头处理,而是蛰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某种莫名的焦灼与恐惧,那种南方小镇夏日里特有的潮湿黏腻和人物内心的惶惶不安,仿佛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巨大的深渊,都有不为人知的隐秘的角落。 《沉默的真相》虽然以“地铁抛尸案”为起因,但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也不难猜测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意味着该剧同样是以案件本身为契机,重点转向对司法正义、社会公平等诸多公共议题的呈现。
二、“极端的叙事”与“反爽剧的爽剧”:《沉默的真相》的新快感机制
既然这一波悬疑剧的爆款与社会问题的揭露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如何处理这些敏感的社会议题就成了颇为棘手且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进一步思考悬疑剧作为社会寓言的关键所在。
有趣的是,这两部大火的悬疑剧均改编自紫金陈的 “推理之王”系列小说。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剧版如何成功地改编原著小说,而是紫金陈推理小说本身带有的社会暗黑的属性。暂且不论紫金陈的文笔如何,因为作为通俗小说的紫金陈的作品原本就是依靠故事本身的情节取胜。奠定他在推理界地位的“谋杀官员”系列小说,显然是当前通俗文学的典型代表。被剥夺者底层人物的复仇,不仅有着自身暴力的内在合理性,还夹杂着挑战公权力的快感。这些想象出来的大快人心的桥段,与其说是迎合了人们对权力体制权谋化或腹黑化的想象,不如说是暴露了底层无权者的极度焦虑,甚至隐藏了他们对权力的暗中崇拜,是“用反霸权的方式充分体会霸权的快乐的一种写作伦理”[5]。
不过,这种写作伦理在几年后出版的《长夜难明》中,体现出从内部尝试突破的情形。这充分体现在主人公江阳的人设上。原本前途一片大好的检察官江阳自从接手侯贵平案后“一路向下”:先是怕连累家人而不得以离婚,接着是蒙受不白之冤而锒铛入狱,出狱后只得靠维修手机谋生,再之后是查出肺癌,最后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引起社会关注,只为了侯贵平案能继续查下去,还他本人乃至司法一个尊严。剧版《沉默的真相》延续了这一设定,就像江阳自杀前面对镜头说的:“这个案件我调查了七年。在这些年里,不断地受排挤、被打压,最后几乎家破人亡,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
如此说来,《沉默的真相》似乎完全不同于大众文化产品所遵循的“爽伦理”的原则,因为该剧塑造的主角江阳,乃是一个为了社会正义而献身的“殉道者”的形象,而全然没有通俗文学中主人公可以随时翻盘的“金手指”,或者通常电视剧里的 “主角光环”——事实上,这正是近来热播悬疑剧不同以往的“现实品格”,也是令观众感到振奋人心的原因所在。但是,江阳这个角色在本质上是理想化或者干脆说是极端化的,因为在现实中恐怕不会有人像江阳这样为了翻案而放弃一切,也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故事。这倒不是说艺术作品要遵循生活本来的面目来塑造人物,而是说由于投入了过多预设的观念,而丧失了作品应有的可信度。事实上,不仅是江阳,也包括屈死的侯贵平,誓死捍卫公平正义的“平康三杰”,其实都难以摆脱这种极端化的人设(剧版的这种人设比原著更加突出,显然也是有意为之),反倒是李建国、孙传福等众多反派的恶行看上去更显“真实”。不妨说, 《沉默的真相》正是通过“极端人物”的塑造来达到“极端目的”的“极端的叙事”——为了预设的目的,将人物的某一特性放大到极端的状态,并将剧情故事的逻辑推演至极端。“极端的叙事”在叙事上能够将剧情变得荡气回肠、引人入胜乃至催人泪下,甚至也可将社会问题暴露出来,但也因为不顾现实本身的逻辑,反而无法将更深层次的矛盾揭示出来。
显然,只有通过塑造江阳这种极端理想化和道德化的人设,才能够完成作品想要传达的主题。这无意间暴露出悬疑剧的悖论:一方面,作为社会寓言的悬疑剧总是要通过社会问题的直接呈现,来获得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另一方面,悬疑剧在呈现社会问题的同时却不得不借助理想化和道德化的 “极端人物”来实现。原因不难想见,只有搁置现实中人的利益交换和明哲保身的生存法则,才可能实现于情于理都无法完成的任务。反过来说,如果不是塑造“极端人物”的性格和行动,悬疑剧就无法推动叙事的展开,也就难以实现它对现实问题的呈现、创造和拯救。
换言之,当社会本身的现实逻辑无法直接对应作品自身的叙事规则之时,悬疑剧就只好再度开启“爽剧模式”来完成主题的升华。只不过,这里的“爽剧”不同于此前单纯“为爽而爽”的快感模式,而是通过将主角不断贬损而后赎回其名誉的方式,使正义再度回归人心。所以,主人公“一路向下”的人设,与其说是对爽剧伦理的颠覆,不如说是以“反爽剧”的方式实现了新的快感机制,也改写了爽剧的打开方式,因此不妨称之为“反爽剧的爽剧”。这种新的快感机制基于上述叙事手法而构成了该剧的叙事伦理。《沉默的真相》通过为无名英雄正名的方式,赎回了被历史掩埋的人质,但这种救赎并非发生在创造之后,而是先于创造而出现:“救赎作为对修复的一种迫切要求而出现,而在被创造出来的世界上,它先于任何恶行而出现,没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好地表达了救赎之于创造的优先性。”如果抛开阿甘本对伊斯兰教传统的发现,“救赎不是对堕落的造物的一种拯救,而是使创造变得更易理解,它赋予创造以意义”[6]5。尽管剧中人物寻找真相的行为困难重重,但他们显然被赋予拯救者的角色,这种拯救不惜以受难的结局而促成了行为和生产的合法性。
由于全剧完全站在江阳的立场上展开叙事,也就是将主角置于崇高客体的位置上,这使得我们必须对其产生伦理和情感上的双重认同,尽管这只是一种欲望的投射。《沉默的真相》由此预设了一个隐含的观众:我们一边为正义的迟到而感到愤愤不平,另一边又高喊着正义不会缺席!事实上,该剧通过讲述江阳苦苦追凶的悲情故事,与其说是旨在探讨司法公正的问题,不如说是为了抚慰那些枉死的冤魂,从而想象性地解决社会矛盾。如果说《长夜难明》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多少还带有一些反思和批判的属性,那么《沉默的真相》则改写了小说的意图:那些漫漫长夜里的黑暗,是为了迎来黎明前的曙光;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命,是美好世界里的小瑕疵。《沉默的真相》有选择性地忽视了整个案件背后复杂的权力—资本体制的巨大难题,也搁置了正义的实现方式和权力的运行机制在根本上源于何处的真正问题。不妨说,《沉默的真相》在看似揭露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巧妙地将真正的社会问题转化为道德和情感的叙事,就像剧中江阳和朱伟只得靠信念来支撑自己的行为一样,因为他们除了信念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实现正义的有效途径。这无疑再次印证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执着只能诉诸一种抽象的道德。
三、权力的边界:两种“暴力”与悬置的可能
在这些暴露社会问题的悬疑剧中,社会问题的处理成为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一方面,悬疑剧借助悬疑外壳讲述社会现实存在的诸多议题,这至少在表面上已经触及了问题所在;但另一方面,悬疑剧在介入社会问题的同时,总是事先剥离问题的复杂性,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拒绝追问其内在根源。从这个角度说,《隐秘的角落》脱离了理想道德化的人设,也尤其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悬疑剧。如果说,《沉默的真相》清晰地划定了正义/邪恶的边界,从而在此基础上展开道德叙事,那么《隐秘的角落》中的人设则显得暧昧模糊,因为我们很难认同剧中的某个角色。他们也不再有着善恶的明确划分,只有生活重压之下的蝇营狗苟,似乎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隐秘的角落》不是在漫漫长夜里苦苦等待天明,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展现人的自私、冷漠和算计,以至于有人认为这是“对恶的极度渲染”而表示批评。[7]
不过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性揭露中的价值导向,而是如何看待人性本身的复杂维度,也就是如何将人性问题置于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中去呈现。事实上,《隐秘的角落》已经尽可能地挖掘出人性的幽暗和复杂。无论是心理极度黑化扭曲的三个“坏小孩”,还是想要回到平静生活但实则已经坠入无底深渊的张东升,以及朱朝阳表面上平常但内心极度不安的父母,他们挣扎在家庭与社会的旋涡中,看似身不由己的背后都有着深层的社会根源。《隐秘的角落》将视角下沉到家庭,但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从来就不是真空的,而是与社会有着直接的联系。尽管我们可以将三个“坏小孩”的“坏”归结为最近流行的原生家庭问题,但如果把问题仅停留在家庭层面,无疑遮蔽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的权力关系。正因为如此, 《隐秘的角落》将社会问题的呈现主要停留在家庭层面的微观权力上(比如,周春红对朱朝阳压抑般的控制、父爱缺失导致的心理扭曲等),但忽视了社会中更带有压迫性的权力关系,比如,校园和职场中的权力对人的压制。试想,像朱朝阳和张东升这种天才般的人物,何以会沦为如此腹黑可怕的“杀人犯”?!这恐怕不仅是家庭和人性所能解释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但是,无论是否深度展现了社会权力对人的形塑,悬疑剧的发生都源于权力加之于人的后果。简单地说,如果没有暴力事件的发生就不会有悬疑剧的探案和解密。事实上,悬疑剧总会令人联想到现实中发生的那些暴力凶案。这些暴力凶案一旦上升为社会公共事件,就不再是个人或团体的仇怨,而变成发生在两个世界临界点上的暴力。张慧瑜敏锐地指出这种暴力事件有着明确的界限:“对于这些边界之外的人来说,他们采取自残或残害别人的方式,只是为了让边界内部的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也就是引起关注,暴力的象征、符号意义大于实际的破坏效果。”这完全适用于《沉默的真相》中江阳的自杀,因为江阳的自杀只有被策划为一起谋杀案件,并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侯贵平案及其背后的利益链条才能得以公开揭露。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尽管他们用极端的方式证明自身的存在,也客观上呈现出社会等级森严的壁垒,但实际上“经常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或许,问题还要稍微复杂一些。在齐泽克的论述中,这种“发生在临界点上的暴力”,被视为一种对事物“正常”状态(和平)进行扰乱的“主观暴力”(subjective violence),表现为社会上时有发生的暴力冲突和恐怖袭击。但与此同时,齐泽克提醒我们还需要辨识另一种暴力,即内在于事物“正常”状态的“客观暴力”(objective violence):“客观暴力是无形的,因为它支撑着我们用以感知某种与之相对立的主观暴力的那个零层面(zero level)标准。因此,系统暴力就像物理学的‘暗物质’(dark matter),它是所有突出可见的主观暴力的对立物。我们的肉眼或许难以看见客观暴力。然而,如果我们要理解那些看似主观暴力的‘非理性’爆发的事物时,我们就必须要考察这种客观暴力。”[8]2所谓“客观暴力”,是指潜藏在肉眼可见的“主观暴力”背后的东西,因为它不仅支配了“主观暴力”的出现,还巧妙地将自身隐藏起来,使人难以察觉。正如齐泽克说的:“在这里,暴力指的是系统的先天暴力:不单是直接的物理暴力,还包括更含蓄的压迫形式,这些压迫维持着统治和剥削关系,当中包括了暴力威胁。”[8]10
如前所述,由于人为设置了边界,悬疑剧在表现权力关系的过程中,只能在客观上认同并加固边界存在的合理性,而无法有效地反思这种权力关系,因为从根本上讲,边界正是为权力而划定的界限。因此,只有对原有边界的悬置,才有可能打开突破的可能性。这正是阿甘本所说的悬置与去功用化。在荣耀的身体中,“器官或工具与其功能区别开来,从而处于某种悬置状态,它们因此获得了一种明示的功能;展现了与这种悬置的功能相对应的善”[6]178。正如黄晓武指出: “这一悬置是一种敞开,它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停止了原有的行为或对立模式,使其失去效力,因而开启了新的可能性。”[9]18“阿甘本所提出的悬置、去功用化和停歇是指通过有意为之的停顿,使之前发生作用的机制展现出来,从而使这一机制失去作用。”[9]23所以,悬疑剧在展现原有机制的同时,不妨尝试暂且搁置边界的存在,将人为划定的清晰的边界悬置起来,回到问题的源头上进入过去并揭示出某种机制发生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从促使原先机制失效的角度,重新选取事件进行考量。这样,悬疑剧在揭露社会问题的同时就成为考古式的对问题起源的追踪调查,进而总体性地揭示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权力,而不仅仅诉诸家庭或者个人层面的伦理。
这种回到起源式的追踪调查,意味着一种行动和一种独特能力,即“能够瞥见那些光中的阴影,能够瞥见光中隐秘的晦暗”[6]26。事实上,作为社会寓言的悬疑剧,最有可能成为感知到时代光芒中的阴影和晦暗的艺术,甚至最有可能成为不被时代之光所蒙蔽的“同时代的艺术”。悬疑剧通过发现那些“隐秘的角落”,从而中和时代之光,以便发现其晦暗,仿佛它们与时代之光同样密不可分。那些被时代遮蔽的被凌辱者和被损害者,经由社会问题式的呈现与创造而讲述个体的经验,进而上升为所谓“结构性问题”后,又回到这种个体生存的艰难。这种社会问题的循环论证,尽管令我们看到了时代的晦暗,却很难让人感受到其中的紊乱和断裂。客观地说,这些爆款悬疑剧的制作不可谓不考究,其细节处理也值得称赞,但由于总体上基于欲望和情绪的满足,悬疑剧对一些主导观念进行了抵抗,却在另外的层面重复着这些主导的价值。
[本文为2021年北京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北京历史文化题材文艺作品创作研究”(21WXA002)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德]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M].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08.
[2][英]朱利安·西蒙斯.血腥的谋杀——西方侦探小说史[M].崔萍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95.
[3][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M].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85.
[4]陈国伟.都市感性与历史谜境:当代华文小说中的推理叙事与转化[J].华文文学,2012(4):85-97.
[5]周志强.寓言论批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论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256.
[6][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M].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7]郑焕钊.屡屡破圈之后,国产悬疑剧需守住价值观[N].文汇报,2020-10-20(12).
[8][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M].唐健,张嘉荣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9]黄晓武.悬置与去功用化:阿甘本的分析策略及其来源[M]//.[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