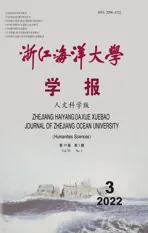多丽丝·莱辛笔下英裔帝国流散者大海情结研究
2022-11-22刘玉环
刘玉环
(长春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200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是战后英国文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女作家。莱辛出生于波斯,在南罗德西亚长大,二战后回到英国,属于典型的流散者。尽管莱辛反对殖民统治,反对种族歧视,但作为英国殖民者的后代,莱辛在南部非洲度过了青少年时期,所以属于帝国流散者,即“为了殖民而离开故国的流散者”[1]。
受个人经历影响,莱辛视野开阔,其作品数量众多,主题包罗万象。自1950 年凭处女作《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 初登文坛,莱辛的非洲题材小说便唤起西方社会对南非殖民地种族歧视的关注。此外,莱辛于1962 年发表的《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引领了西方女权运动第二波,其女性题材小说引发了战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高潮。在后期空间小说创作中,莱辛在广阔宇宙时空中探索人类的历史,想象世界末日人类毁灭的场景,推动了战后西方科幻文学的发展。作为“历史记录者”,莱辛在创作中再现了20 世纪人类历史的风云变幻、气象万千。
一、英国文学中的海洋书写概览
学界对莱辛的研究几乎与莱辛创作同步,且成果丰硕、视角丰富。目前学界多从女性主义、政治书写、精神分析、殖民和后殖民主义、身份认同、苏菲主义、分裂整合主题、伦理主题、认知主题、流散主题、空间书写等角度对莱辛展开研究,同时也有学者研究莱辛创作的叙事艺术。但截至目前,学界尚未关注莱辛创作中的海洋书写。实际上,海洋是莱辛创作中的重要意象,这与莱辛作为英裔帝国流散者的流散经历有关。莱辛笔下的英裔帝国流散者多怀有大海情结。究其原因,首先,英国是岛国,“海在英国人的生活中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与海洋有关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都是不列颠人的至宝”[2]。其次,对于英裔帝国流散者来说,大海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殖民与航海密不可分。正是从取得海上霸权开始,英国拉开了海外殖民的序幕;反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航海事业的衰落也推动了大英帝国的分崩离析。
英国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文学。5 世纪中期出现的民族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展现了英国早期的航海事业。16—17 世纪出现了三部以海外移民为主题的海洋乌托邦作品,即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的《乌托邦》(Utopia,1516)、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1626)和詹姆士·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1611—1677)的《大洋国》(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1656)。18 世纪出现了《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1719)、《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1726)等海外探险小说,体现出殖民思想的萌芽。19 世纪是英国海洋文学繁荣期,很多浪漫主义诗人和维多利亚小说家歌颂海外扩张,抒发身为大英帝国子民的自豪感。20 世纪英国海洋文学在变革中发展,关注的重点转为“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性善恶”。[3]
英裔帝国流散者是英国海洋文学创作的主体及描写的主要对象,莱辛关于英裔帝国流散者大海情结的书写属于英国海洋文学的一部分。张德明[4]提出海洋文化的四大要素是“人、海、船、岛”,并根据四种要素的不同组合方式提出五种海洋文化模式:殖民—探险模式、海盗—劫掠模式、移民—难民模式、奴隶—囚犯模式和传教—布道模式。莱辛笔下殖民前期英裔帝国流散者的海洋情结基本体现出“殖民—探险”模式;到了二战前后大英殖民帝国即将谢幕之际,其笔下英裔帝国流散者的海洋情结则表现出“回归故土—逆向征服”模式。所以,莱辛关于英裔帝国流散者大海情结的书写既与英国海洋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又体现出大英帝国殖民末期英裔帝国流散者海洋情结的独特之处。对莱辛的海洋书写进行研究,既能丰富莱辛研究视角,也有助于发现英裔帝国流散作家海洋书写的共性,彰显大英帝国殖民末期英裔帝国流散文学的时代特色。
二、莱辛笔下殖民前期英裔帝国流散者的大海情结:征服异邦
莱辛笔下殖民前期英裔帝国流散者的大海情结体现出“殖民—冒险”模式,这代表了当时英国海洋文学的主流。在殖民前期,英国“这个16 世纪时还在牧羊的民族摇身一变,成了海的女儿”[5]。当偏安一隅的牧羊女放眼世界,成为野心勃勃的水手,英国社会在大海情结推动下拉开了海外殖民的序幕。此时扩张与冒险是英国社会的主旋律,“英国涉海文学认同国家海外扩张和冒险事业”[6]137,成为“帝国殖民事业的宣传工具”[6]138。所以,此时英国流散文学中英裔帝国流散者大海情结的主要内涵是“征服异邦”。
首先,早期英国殖民者的大海情结主要表现为渴望征服大海彼岸,实现一夜暴富,“殖民第一人”鲁滨孙便是典型代表。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堪称真正意义上的英国第一部海洋小说”[7]。在小说中,鲁滨孙“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只是想航海”[8]3,主要目的是发财致富,为此他悄悄离开家,踏上开往伦敦的航船。第一次出海就遇到风暴,侥幸死里逃生。然而,在财富诱惑下,鲁滨孙对海难灾祸的记忆逐渐淡化,再次登上航船,赴非洲经商。尝到甜头后,鲁滨孙第三次出海,但途中被摩尔人(Moors)俘获。两年后,他划着主人的船逃跑,被一艘葡萄牙货船救起。即使在命悬一线的紧迫形势下,鲁滨孙念念不忘的还是挣钱,他把小船上的东西卖给船长,带着这笔钱,“踏上了巴西海岸”[8]27。依靠获得的利润,鲁滨孙在巴西购买了庄园,但很快又厌弃了庄园生活,选择第四次出海,到非洲贩卖黑奴。不幸的是,他在中途遭遇海难,独自生还,滞留荒岛。在荒岛独自生活二十八年,鲁滨孙仍没有放弃发财梦,他把船上一切能用的东西统统运上小岛,还学会了很多手艺,积累了大量财富。获救时,鲁滨孙已经拥有一座小岛,他的“新殖民地”[8]234。回英国结婚生子后,短暂的陆地生活并没有让鲁滨孙放弃出海的念头。妻子去世后,看到侄子带着巨额利润航海归来,鲁滨孙禁不住诱惑,再次出海经商。
鲁滨孙的故事从出海开始,又以出海结束。从航海经历可以看出,鲁滨孙怀着强烈的大海情结,主要表现为对征服异邦、一夜暴富的渴望,是早期英国殖民者的代表。从鲁滨孙开始,英国殖民者相继踏上殖民航船,主要目的是发财致富。莱辛的父母来非洲正是为了寻求财富,莱辛提到“我的父母在伦敦展会上看到宣传单上说,‘在南非靠种玉米五年内就可以发家致富’”[9]。他们向往大海尽头那片神奇的土地及其许诺的大笔财富,因此踏上了开往非洲的航船。
其次,早期英国殖民者的大海情结还表现为对英国航海事业和海外殖民活动深感自豪。比如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帝国号手”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在诗集《七海》(The Seven Seas,1896)中歌颂了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吉卜林认为上帝赐予英国人一条海上通道,英国殖民者可以沿着这条通道驶往天涯海角,为帝国带回无尽的财富。因此,其笔下的英国殖民者崇尚大海英雄主义,满怀豪情踏上海外殖民之路。在《最后的水手歌》中,“兴冲冲的水手们的灵魂高声歌唱,‘我们要去开阔的海上奋斗’”[10]6。尽管大海无比凶险,但英裔帝国流散者能够战胜大海,因为“上帝把海赶往虚无之岸”[10]5。在另一首诗《海夫人》中,海夫人不断派出儿子们“去耕作潮汐”,“她养育了一群男人,一个漂泊的种族,/将他们托付于海的幽深”[11]12。海夫人就是英格兰的化身,虽然一些子民葬身大海,但英格兰仍不断向海外派遣自己的儿子,“男人们的传奇,传遍那些崭新的、赤裸的土地”[11]13。吉卜林歌颂这些帝国流散者,因为他们的出海行为成就了英国的帝国伟业。
此外,大英帝国殖民盛期的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也对英国航海事业充满自豪。康拉德生于波兰,1878 年到英国商船当水手,1886 年成为船长,1898 年定居英国。康拉德见证了英国航海及海外殖民的巅峰时刻,在作品中表达了对英国航海事业的崇敬。康拉德认为泰晤士河是英国航海实力的象征,在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1902)中这样赞美泰晤士河:
宽敞的航道中的古老河流,在这白日将尽时,水波不兴地安息着,它世世代代为两岸聚居的种族做过多少好事情,如今,这条可以通往天涯海角的水上通途,端庄静穆地舒展在眼前。我们在观赏这条令人崇敬的河流,不是靠一个短暂的来而复往、去而不返的鲜艳白昼的闪亮,而是靠一种永志不忘的记忆所发出的庄严光辉。[12]3
在康拉德看来,泰晤士河之所以荣耀,是因为见证了英国航海事业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进出港口的船威名赫赫,它们从泰晤士河出发,驶往世界各地,建起横跨全球的殖民帝国,带回琳琅满目的金银财宝。“它曾载浮过所有那些名字如同宝石一般在时代的暗夜中熠熠发光的船只,从‘金鹿号’开始——它圆滚滚的两侧船舱中装满金银财宝归来时,女王陛下曾亲临拜访。”[12]3在康拉德看来,船上的人不管是离家远征,还是得胜归来,都无限荣耀。
其中有冒险家和移民;有贵族们的船和生意人的船;有船长们和海军将领们;有专做东方生意的隐秘的“私贩”们;还有在东印度舰队服现役的“将军们”。黄金的猎取者或名誉的追逐者们,都是从那条河流上驶出的,他们手持利剑,往往还高举着火炬,他们是陆上强权的使者,是从圣火中取采火花的人们。[12]4
从上文可以看出,船上的人主要包括从事殖民贸易的商人和为殖民活动保驾护航的军人。所以,对泰晤士河的赞美也体现出对英国航海事业和海外殖民活动的自豪感。
再次,早期英国殖民者的大海情结也表现为对自身航海能力的骄傲,莱辛的母亲莫德(Maude)便是如此。莫德是“海的女儿”,她的母亲是伦敦泰晤士河上一位驳船船夫的女儿,所以“大海和河流流淌在她家族的血液中”[13]307。“她的记忆与言谈中处处是海洋,她生长于伦敦的大街小巷,但大海才是她心中的腹地。”[13]307
在英国的生活没多少乐趣可言,但有船可坐。她和船长的关系好得出了名。父亲在船舱里病倒了,但母亲适应航海的能力无人能比:她酷爱甲板上的游戏和舞会,任何场合都打扮得漂漂亮亮,那个德国船长明显很欣赏她。有了那只装满漂亮衣裙的箱子,她肯定是舞会上的美人吧。[14]160
在文中,“和船长关系好”体现的不仅仅是友谊,更是地位。在英国历史上,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船长和水手的地位逐渐提高。从18 世纪开始,水手开始受到人们尊重。“在人们眼中,船长们都是绅士。”[15]所以,与船长谈笑风生表明莫德适应航海的能力超强,体现出其高贵的社会地位,也表现出莫德对英国航海事业充满自豪。
这种对自身航海能力的自豪也体现为对船的深情。康拉德在散文集《大海如镜》中提出水手往往对船充满眷恋,“他们对自己的船爱护有加,船也保护着他们穿越这茫茫大海”[16]。在很多殖民者眼中,“船像一个可以移动的‘房子’”[4],而房子则是暂歇的船。比如即使到了干燥的非洲高原,莱辛的母亲莫德仿佛仍置身“漂泊的航船”。在非洲,“她让茅草屋前端向草原敞开,‘就像船头一样’”[17]119。正如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所说:
虽然他们生活在遥远的土地上,但却像她的水手一样,不因在遥远的海浪上漂泊就认为自己不属于祖国。从表面意义来看,殖民地就是漂泊的舰队;英国期待这些稳固的海军队伍(由世界基督之湖的水手所指挥的不动的教堂)……他们会因她的荣耀而荣耀,胜过热带天空下的骄阳。[18]
也就是说,即使到了殖民地,殖民者也应把自己当作帝国的水手。莫德终身“囚禁”在干旱的非洲高原,但却把非洲高原的茅草屋当作航船,一心征服大海彼岸。
最后,早期英国殖民者的大海情结也表现为对英国海军充满向往。海军对于英国海外殖民非常重要,所以从15 世纪末都铎王朝开始,英国历代君主都热衷于发展海军。到了19 世纪初,英国海军的强大已经成为神话,似乎可以称霸世界。有强大的海军作后盾,英国海外殖民迅速发展,成为称霸四方的日不落帝国,创造了“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的神话。中西辉政[19]认为,“‘不列颠治世’的‘三大支柱’包括优越的海军军力、广大的殖民地、工业革命与商业立国传统所培育出的经济力量。”由此可见海军对于英国、对于海外殖民的重要性。
莫德从小便对海军充满向往。莱辛提到,“我想母亲最嫉妒她的弟弟约翰(John),因为她更聪明伶俐,应该是她去海军,而不是他。她是那位聪明者,是她终日梦想着大海的一切,梦想着船只,从不晕船”[17]112。最终,约翰没能通过海军体检,于是选择去马来西亚(Malaysia)经营橡胶农场。不久,莫德也满怀期待地踏上了开往非洲的殖民航船。
三、莱辛笔下殖民末期英裔帝国流散者的大海情结:回归故土
二战前后大英殖民帝国即将谢幕之际,作为“鲁滨孙的子孙”[20]113-120,莱辛笔下英裔帝国流散者的海洋情结则表现出“回归故土—逆向征服模式”。
首先,莱辛笔下殖民末期南非英国殖民者的大海情结表现为将大海看作逃离殖民地困顿生活的世外桃源。如果说“殖民第一人”鲁滨孙向往大海的主要动机是想发财致富,那么殖民末期南非英国殖民者向往大海的主要原因是想忘掉贫穷。来到非洲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往往使南非英国殖民者深感失望,此时大海成为逃离壅域的理想之邦。比如在《野草在歌唱》中,南非白人主妇玛丽(Mary)因无法忍受非洲农场生活的贫穷而精神崩溃,她希望丈夫迪克(Dick)能够种植烟草发家致富,这样他们就可以离开农场,重新过上文明生活。在她所憎恨的非洲农场,“她的生活态度就像是在她讨厌的国家里短暂停留的旅人”[21]144。丈夫同意种植烟草后,玛丽心底又萌生出对生活的希望。“她关注山坡下烟草仓库的建造进度,就像留心一条正在建造中的船。那船会将她载往远方,脱离这种放逐生活。”[21]145
此时,大海象征着与令人失望的殖民地相对的理想家园,是南非殖民者难以企及的极乐之地。当时很多殖民者贫病交加,去海滨疗养是医生经常推荐的治疗方案。但对很多南非英国人来说,由于农场盈利有限,甚至入不敷出,海滨疗养远远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比如迪克患疟疾时,为迪克诊治的医生看出玛丽同样体质虚弱,很可能患上了贫血症和神经衰弱,建议玛丽至少到海滨疗养三个月。玛丽说没钱度假,医生很不理解。“他问玛丽多久没去海滨了,其实她一辈子也没见过海。”[21]119直到生命终结,玛丽都没到海滨疗养过。莱辛一家同样如此。莱辛的母亲莫德来到南非后,终日被困在高海拔的干旱地带。“她时刻怀念着大海,但负担不起那笔钱。她被困在了农场上。”[13]307此时大海象征着摆脱殖民地贫穷壅域的希望,象征着故国英格兰,是南非殖民者可望而不可即的梦。
其次,殖民末期南非英国殖民者的大海情结多表现为将大海看作通往故国家园的便捷之路。莱辛[22]提到“生活在高原的我一直渴望大海,这已成为一种狂热”。实际上,莱辛并非出生在海洋国度。她出生在波斯,成长于干旱的非洲高原,所以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关于大海的记忆。然而,她却从周围的南非白人那里感染了对大海的热爱。在半自传五部曲《玛莎·奎斯特》(“Martha Quest”,1952)系列小说中,玛莎经常梦见自己被困壅域,每天夜里都梦想着大海:
在这个把她困住,把他们统统困住的噩梦中,他们必须记住:外面某个地方存在着光明,能够听到拍击岩石的水声。世界的某个地方有海岸,海浪像奋勇争先的赛马日夜奔腾……总有一天,玛莎会从容地立于海岸之上,凝视着滚滚波涛奋力奔涌。[23]294
此时玛莎向往的大海是与干旱贫瘠的非洲相对的世外桃源,是与破败的殖民地相对的理想家园,大海象征着获得拯救的希望:
她梦见自己站在干燥的高原上,很多船只朝四面八方扬帆远航,离她而去。在这片把她困住的干旱高原上,所有东西都干燥易碎,根本原因在于干旱,只有遥远的地下才有水。夜复一夜,她梦想着水源,梦想着大海,梦想着如万马奔腾的急流。她一次次醒来,鼻孔里闻到海的气息,舌尖上留着盐的余味。[23]247
玛莎就是莱辛的化身。此时,莱辛梦中的大海逐渐明晰,成为英格兰的象征,其大海情结也表现为对“征服英格兰”的渴望。莱辛提到:
从狭义来讲,英格兰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圣杯。不久前,那些恰当的人——具有冒险精神、不惜一切代价的人——涉足殖民地。最近,一种逆向移民正在进行中。那些地平线征服者现在踏上航程,或展开翅膀,奔向英格兰——这里主要指伦敦——决定要用自己的方式征服伦敦。[24]
此时,莱辛[13]12承认“我想生活的地方是伦敦”,因为“非洲是一隅偏居之地,生活了无趣味”。每晚她都梦见大海,海浪随缓慢、忧伤的思乡节奏而起伏。
到了二战前后,英国殖民者眼中的英国航海事业逐渐失去绚丽的光环,大英殖民帝国也显出日暮穷途的衰弱趋势。此时他们不再向往大海彼岸,而是渴望回归英格兰。他们甚至畏惧通往海外的旅程,痛恨开往海外的航船。小说《爱之子》就是一个例子。在小说中,詹姆斯·里德(James Reid)是二战时期的英国士兵。为防范日本偷袭印度,詹姆斯所在部队被派往印度,乘坐运兵船出海的痛苦经历使他看清英国的航海事业已经辉煌不再,海外殖民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所以内心产生了对大海的痛恨和畏惧,期待返回故土、永不坐船。当时詹姆斯所在的军队乘坐一艘客轮经开普敦开往印度。为避免德国潜艇攻击,出发前大船进行了伪装,看起来像一片云,或是一团飞鱼,“反正是转瞬即逝的东西”[25]194,这也昭示着英国航海事业的辉煌转瞬即逝。
对于士兵来说,这是一次痛苦的旅行。一方面,船内条件非常恶劣,严重超员。大船设计可容纳780 名旅客与船员,当时却塞进5 000 名士兵及随行军官。大船分成很多层,最上面的A、B 两层条件最好,留给军官;越往下条件越差,依次挤满级别更低的士兵,这是“他们保卫的那个社会的生动象征”[25]194。詹姆斯等士兵住在E 层,在吃水线以下,非常拥挤。舱壁内挂满吊床,相互间只隔几英寸。剩余空间仅够十个人站立,彼此间隔也仅几英寸。他们还能听到下面传来尖叫声,这才意识到自己不在最深的痛苦之渊,下面还有更深的一层,同样挤满人类。
由于条件恶劣,士兵纷纷病倒。出发不久,栏杆边就站满呕吐的人,厕所也排起长队。由于气候炎热,很多人中暑,烧得浑身发烫,无法进食。此外,他们还面临淡水不足的威胁。由于口渴,一些士兵把垃圾桶吊下海取海水,喝过后很快病倒。淡水缺乏使他们只能用海水洗衣服,“换上海水里洗过的衣服,发现他们的汗,加上衣服里的盐,发出了臭味,短裤和衬衫硬邦邦的,磨得身上难受”[25]203。恶劣的条件使一些士兵再也无法忍受,因精神崩溃而被带走,加入发疯者的行列。詹姆斯的上级珀金斯中士(Sergeant Perkins)曾打算让混乱的场面恢复秩序,但看到很多人躺在呕吐物中痛苦地呻吟,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珀金斯中士鼓起勇气向上级报告:“要是把动物关在那种环境中,我们都会受到指控的。”[25]201然而,上级军官也没有办法。很快,整艘大船上的人都病了。大船到达开普敦时,当地人看到的是一群“活鬼一样的士兵”[25]215。“看起来不像士兵,更像病号。他们扶着栏杆,四周张望,一个个瘦骨嶙峋、一副病态”[25]215。
另一方面,尽管有两艘驱逐舰护卫,大船还是随时可能遭到德国潜艇攻击,这使他们的航行雪上加霜。当士兵们冒险离开底层,来到被禁止登上的甲板时,感觉好一些,但却更清楚地意识到大船面临的威胁。由于客轮船体巨大,很容易成为潜艇的攻击目标。在漆黑的甲板上,靠着漆黑的栏杆,望着漆黑的世界,他们体会到更深的恐惧。于是他们还是回到船底,“舱里有安全的假相,毕竟四周有墙围着”[25]197。大船刚到开普敦,负责接待的达芙妮(Daphne)便接到丈夫乔(Joe)的电话,称“一艘潜艇差点干掉了他们,不过他们自己还不知道”[25]214。可见大船幸存下来实属不易,这也反映出当时英国航海事业的衰弱。
詹姆斯在这次航行中认识到大海可怕的一面,从此不再向往大海彼岸的异邦圣土,而是向往“神圣的陆地”[25]208,渴望回归故土。小说中,在开普敦志愿接待运兵船的白人主妇达芙妮象征着詹姆斯所向往的神圣陆地。大船刚进入开普敦港,詹姆斯便看到一幅期待已久的陆上美景图:“桌山(Table Mountain)一处高坡上,两个年轻女人躺在游廊上的折叠椅里,俯瞰着大海。”[25]209这两个女人便是南非白人主妇达芙妮及其好友贝蒂(Betty)。经历了噩梦般的航海生活,此时詹姆斯感觉从没见过这么可爱的女人,“穿着晨袍的那两个女人,在花园的植物丛中,就是幻象。他瞪大眼睛,一直盯着她们,有意把这画面储存在大脑里,以后他能看,能保存,能抓住”[25]226。当达芙妮站到他身边时,这个饿得半死、流浪儿般的可怜小伙子以为是在做梦,称自己“到了天堂”[25]219。
此时,与对陆地的热爱相对,便是对大海的憎恨和恐惧。在开普敦停歇时,“年轻人一致认为,最好的享受就是坐在这儿,俯瞰着他们的敌人——大海”[25]221。在陆上隔着安全的距离来看,大海又展现出无穷魅力:“海水一望无垠,像孔雀的尾巴一样闪闪发亮,迥异于其本来的面目——潜艇出没的杀手。”[25]221然而,经过炼狱洗礼的士兵们早已认清大海的真面目,对大海充满恐惧。比如当达芙妮开车带詹姆斯去海边棚屋时,达芙妮眼中的大海美丽如画,但詹姆斯却说:“我讨厌它。海出来抓我们。会抓住我们的。”[25]228听到大海涨潮的声音,詹姆斯放声尖叫,无比恐惧,双手紧紧捂住耳朵。他表示,“我最好永远不再看到大海”,“等战争结束了,我绝不会走近任何一条船”[25]233。
詹姆斯对船和大海的恨实际上体现出他对英国航海事业、海外殖民的失望和愤恨。在他看来,海外殖民毫无意义,包括他自己在内的5 000 名士兵耗费几年时间、遭受无数痛苦来到印度,虽然把日本人赶出了印度洋,但不过是“保卫着坏的东西不被更坏的东西侵犯”[25]271。
此时,英国殖民者眼中的英国海军也风光不再。莱辛提到,二战初期,弟弟哈里(Harry)所在的英国战舰游弋在太平洋上,执行拦截日军的任务。当时英国海军军舰“反击号”(Repulse)和“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赫赫有名,被认为永不沉没,哈里就在“反击号”上。然而,不到二十分钟,两艘战舰就被日军击沉。哈里刚刚上了甲板游走,整个船就沉了。“当时海里漂着很多死人……还有人抱着漂浮物大喊救命。”[14]251海军是英国海外殖民的基石,战舰的沉没标志着英国海军的衰落,也暗示着英国航海事业、海外殖民事业的穷途末路。
总之,莱辛身处英国海洋文学传统之中,其笔下殖民前期英裔帝国流散者的大海情结体现出“殖民—冒险模式”,这代表了英国海洋文学中帝国流散书写的主流。同时,作为大英帝国殖民末期的英裔帝国流散作家,莱辛的海洋书写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莱辛见证了二战前后大英帝国航海事业和海外殖民由盛而衰的过程,亲身体会到殖民末期英裔帝国流散者渴望逃离殖民地、回归故土英格兰的流散意识,所以其笔下殖民末期英裔帝国流散者的大海情结表现出“回归故土—逆向征服模式”,这是莱辛海洋书写的重心所在,也是莱辛对英国海洋文学内涵的发展。
与殖民前期笛福、康拉德、吉卜林等作家对英国海外殖民扩张的歌颂不同,莱辛尽管也书写殖民前期英裔帝国流散者的大海情结,但对其“殖民—冒险”活动始终冷眼旁观。如果说“帝国号手”吉卜林等作家的海洋书写帮助构建了文本中的大英帝国,助推了英国的海外殖民活动,那么莱辛则是大英帝国的掘墓人,终生致力于解构大英帝国。对殖民末期英裔帝国流散者“回归故土—逆向征服模式”大海情结的书写,是莱辛解构“殖民—冒险神话”、解构大英帝国的重要途径,开启了战后英国海洋文学的帝国反思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