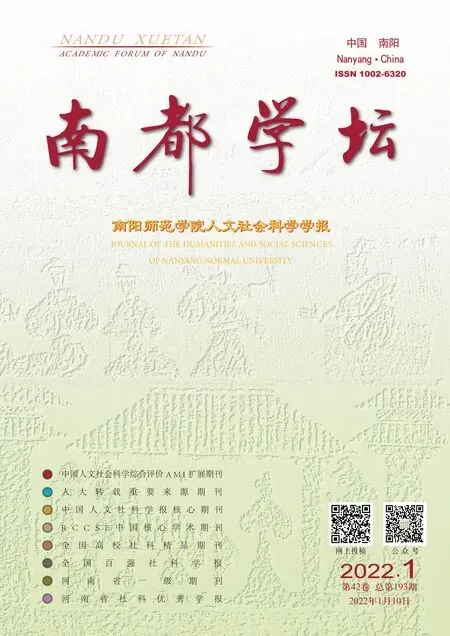清末的武侠启蒙与金庸武侠小说的新境界
2022-11-21陈岸峰
陈 岸 峰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一、清末的武侠启蒙
(一)启蒙话语之下的“武侠”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不少国人由昔日的妄自尊大而陷入自卑情结,郁达夫小说《沉沦》中的中国留日学生,由于感到祖国羸弱,备受日本人歧视,因而大受打击,最后选择自沉,而在其将沉前便发出“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1]53。与此同时,战败后的中国,却因救亡意识而侠风复炽。梁启超指出:
自甲午以前,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不知国危,则方且岸然自大,僵然高卧。[2]
此际已非“自强”,而是“救亡”。故此,“尊侠力,伸民权”[3]485成为一时风潮。章太炎在《儒侠》一文中指出:
且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过于除国之大害,捍国之大患者乎?[4]439
章太炎还在《变法箴言》中对日本的武侠作介绍:
至于书生剑客,慷慨国事,竞为诡激,横刀曰攘夷,擐绔曰脱藩,一言及尊攘,切齿扼腕,斥当轴为神奸,而笑悼老成宿儒之畏懦,悲歌舞剑,继以泣涕,展转相效,为一世风尚……卒使幕府归政,四邻不犯,变更法度,举错而定。[5]19
章太炎认为日本的侠者,力量很大,能干预政治,可为中国借鉴,这是对当时流于空谈的中国士大夫的鞭策。1897年,梁启超的《记东侠》盛赞“日本以区区三岛”而使列强“莫敢藐视”,强国秘密在于“当时侠者”成为社会民粹主流意志,“乃至僧而亦侠,医而亦侠,妇女而亦侠,荆聂肩比,朱郭斗量。攘夷之刀,纵横于腰间;脱藩之袴,络绎于足下”,“而以侠为国之用”[6]。梁启超高度赞扬侠成为日本民间的主流风气,他对侠有以下定义:
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7]20
谭嗣同在《仁学》中指出如果不能实现变法,应任侠以有作为:
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侠气,出而鼓更化之机也。[8]79
由于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的特殊地位,他们重侠的宣言与主张掀起了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的尚侠热潮。
(二)日本武侠对中国士人的影响
1902年日本青年押川春浪(1876—1914)写成《武侠之日本》,书写日本与美、俄两国的军事对峙,并将日本原有的“武士”升华为“武侠”。《武侠之日本》全书使用“武侠”一词达92次,书中诸如“武侠男儿”“武侠精神”“武侠团体”“武侠帝国”等话语,鼓吹武士道的复仇精神。曾避难至日本的梁启超深受押川春浪《武侠之日本》将“武侠”转换为具有现代启蒙意义的民族自救道路的影响,他在1904年出版的《中国之武士道》的序中指出:
虽然,吾以为必有赴公义之精神,而次之乃许其报私恩焉。不然,彼固日日欲赴公义,而适以所处之地位,有不能不报私恩之事,而后乃以报私恩名焉。要之所重乎武侠者,为大侠毋为小侠,为公武毋为私武。[7]2-3
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列举了16种武士道行为,一方面近一半是表彰赴国之难;另一方面是为民铲除不平。梁启超大力提倡“武侠”的“公武”精神,即泯除传统的莽夫的门户之见或私利恶斗,遂将传统侠义的附庸地位,提升至民族国家的启蒙现代性精神,以“中国之武士道”精神冲击陈腐的社会风气,高度体现了启蒙的现代性(1)关于梁启超流亡日本及接触西学的整体情况可参见Joseph R. 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Chapter3,Berkeley: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Chapter 5,Cambridge, Mass:Harvard UP,1971.。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即称:“中国民俗与欧西日本相反者一事,即欧日尚武,中国右文是也。”[7]24梁启超又将武士精神提升至国力层次而指出:
日本之武士道,垂千百年而愈久愈烈,至今不衰。其结果所成者:于内则致维新革命之功;于外则拒蒙古,胜中国,并朝鲜,仆强俄,赫然为世界一等国。[7]5
有署名“壮游”又在文中自称“金一”者,亦即金天翮(松岑,1874—1947),在《国民新灵魂》一文中称:
重然诺轻生死,一言不合拔剑而起,一发不中屠腹以谢,侠之相也;友难伤而国难愤,财权轻而国权重,侠之概也。是故朱家、郭解、王公、剧孟侠也,荆轲、聂政、要离、仓海亦侠也,李膺、杜密、范滂、顾宪成、高攀龙亦侠也,富兰克令、哲尔生、丹顿、罗伯斯比、玛志尼、加里波的、噶苏士、巴枯宁、西乡隆盛、宫崎寅藏尤侠也。(2)1903年,吴江金天翮发表《女界钟》一书,便署名“金一”,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金天翮也就是宫崎滔天(1871—1922)《三十三年落花梦》最早的中译者之一,诗歌、散文及小说均有成就。[9]574
此文将“武侠”的范围扩之古今中外,武夫与文人及政客以至于贩夫走卒,皆可为侠。
(三)近代武侠小说的勃兴
1915年12月,包天笑(朗孙,1876—1973)在《小说大观》第3期上首次对“武侠小说”进行类型命名,以当时已经盛名之下的林纾的文言短篇小说《傅眉史》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正式命名的“武侠小说”。1922年的一则广告声称:
吾国民气,萎靡不振,看侦探小说与侠义小说,有振起精神、浚瀹心胸之功用;吾国社会,奸诈谲伪,看侦探小说与侠义小说,有增进阅历、辨别邪正之功用;吾国外侮,纷至沓来,看侦探小说与侠义小说,有巩固民心、洗雪国耻之功用;吾国外债,日加无已,看侦探小说与侠义小说,有激发慷慨、将以救国之功用。[10]
1914年,平江不肖生(向恺然,1889—1957)在日本创作《留东外史》,特别插叙了“以武保国强种”的具有以武侠救国的津门大侠霍元甲故事。自1913年与1916年两次讨袁失败后,平江不肖生在上海专门从事写作,然而并未放弃武术事业。1922年,他应世界书局之邀而从事武侠小说创作,其《江湖奇侠传》以“长篇武侠小说”面世,其具有启蒙意识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开篇,便从“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殉难写起。除了《江湖奇侠传》与《近代侠义英雄传》之外,平江不肖生还撰有《江湖大侠传》《江湖小侠传》《江湖异人传》《现代奇人传》《半夜飞头记》《猎人偶记》《江湖怪异传》《烟花女侠》《双雏记》《艳塔记》《滴血神剑》共13部。此外,他还参与制作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神侠金罗汉》《飞仙剑侠大破谋人寺(上集)》《飞仙剑侠大破谋人寺(下集)》《江湖奇侠》。其将武侠小说改编为电影,应该对时在香港撰写武侠小说兼编剧的金庸有所启迪。
与平江不肖生齐名的另一武侠小说作家赵焕亭(赵绂章,1877—1951)的《奇侠精忠传》于1923年5月由上海益新书社初版发行,影响较大,其他作品包括《大侠殷一官轶事》《殷派三雄传》《英雄走国记》《惊人奇侠传》《双剑奇侠传》《北方奇侠传》《双鞭将》《蓝田女侠》《说剑谈奇录》《边荒大侠》《不堪回首》《江湖侠义英雄传》《白剑莲影记》《奇侠平妖录》《尹氏三雄传》《昆仑侠隐记》《侠骨红装》《剑低箫声》。
另一重要武侠小说作家还珠楼主(李寿民,1902—1961)一生着有武侠小说36部,多达4000余万字,他与“悲剧侠情派”王度庐(王葆翔,1909—1977)、“社会反讽派”宫白羽(宫竹心,1899—1966)、“帮会技击派”郑证因(郑汝霈,1900—1960)、“奇情推理派”朱贞木(朱桢,1895—1955)共称“北派五大家”。还珠楼主走出了一条与平江不肖生的启蒙现代性完全不同的道路,其“蜀山”系列,包括“蜀山剑侠正传”:《蜀山剑侠传》《蜀山剑侠后传》《峨眉七矮》;“蜀山剑侠前传”:《长眉真人传》《柳湖侠隐》《北海屠龙记》《大漠英雄》;“蜀山剑侠别传”:《青城十九侠》《武当七女》《武当异人传》;“蜀山剑侠新传”:《蜀山剑侠新传》《边塞英雄谱》《冷魂峪》;“蜀山剑侠外传”:《云海争奇记》《兵书峡》《天山飞侠》《侠丐木尊者》《青门十四侠》《大侠狄龙子》《蛮荒侠隐》《女侠夜明珠》《皋兰异人传》《龙山四友》《独手丐》《铁笛子》《黑孩儿》《白骷髅》《翼人影无双》。其余还有:《万里孤侠》《黑森林》《虎爪山王》《血滴子大侠甘凤池》《征轮侠影》《力》《拳王》《黑蚂蚁》《酒侠神医》。其作品融合神话、志怪、剑仙、武侠于一体,“奇幻想象与雄伟文体”相统一,对后世武侠作品影响巨大[11]253-254。
二、金庸武侠小说的新境界
(一)对侠的现代阐释
金庸武侠小说之所以风靡天下,实乃其在武侠境界上有所突破所致。有论者指出,清末以来武侠小说的桎梏在于“理性化倾向”:
清代是武侠小说鼎盛期,理性化倾向更为严重。《三侠五义》《施公案》中,侠客变成皇家鹰犬,立功名取代了超逸人格追求,武侠小说甚至蜕变为公案小说。历史经验证明,古典武侠小说循着偏重社会理性一途走到了尽头。[12]181
即是说,在清廷的高压下,侠客难以有所作为,甚至沦为官府的鹰犬,武侠小说的发展备受压抑,也是现实的反映。故此,民国初年的武侠偏向于情而非义:
民国初年开始了这种转向,情取代义成为侠客人格的主导方面;江湖成为侠客主要活动场景,不是替天行道,而是情仇恩怨成为主题。《江湖奇侠传》是这种转变的标志,它开辟了武侠小说的新天地,带来了本世纪上半叶武侠小说鼎盛期。[12]181
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突然“转变”,以至于“鼎盛”,亦属必然。杜心五(1869—1953)、王五(子斌,1844—1900)、霍元甲(俊卿,1868—1910)等大侠的出现,正是时代剧变的征兆(3)刘登翰先生将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2年为萌芽期;1923年至1931年为繁荣期;1932年至1949年为成熟期。关于派武侠小说的发展的论述,可参阅刘登翰:《香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在此关键时刻,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借易鼎之际的书写而令武侠摆脱沦为朝廷鹰犬,豪气重现。此中,《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及《鹿鼎记》等长篇的背景均属易鼎时代。《天龙八部》乃以北宋末年宋、辽争持的场域为背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及《倚天屠龙记》则从宋、金对峙写起,历元蒙勃兴以至于元末群雄并起,《碧血剑》写“甲申之变”(4)有关“甲申之变”的专著,可参阅陈岸峰:《甲申诗史:吴梅村书写的一六四四》,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鹿鼎记》与《书剑恩仇录》则述天地会之反清复明故事。故有论者指出金庸武侠小说之突破在于:
金庸以及他所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沿着民初武侠小说道路发展,并有所突破,它真正对侠进行了现代阐释,完成了古典武侠小说向现代武侠小说的转化。[12]181
所谓的侠的“现代阐释”,实即指金庸武侠小说传承了五四文学中“感时忧国”(5)严家炎先生指出新武侠小说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一脉相承,异曲同工。见严家炎:《新派武侠小说的现代精神》,载《明报月刊》1996年2月号。[13]的历史意识,在中华民族的各个转折时代均作出想象的书写,同时面对当代的政治人物以及历史事件如“文化大革命”,均成为其笔下的隐喻及批判所在。故此,有论者指出:
他写着武侠,写着政治,又不时透出对武侠愚昧的叹惋和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根本上的鄙弃。正因为这样,金庸的小说才拓出了武侠的新境界,成为二十世纪里真正有现代意义的作品之一。[12]346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均是武功盖世且心存天下苍生。例如,郭靖从蒙眛少年及至中原后便深受范仲淹、岳飞的心系天下苍生的思想所感召,从而投身于保家卫国之行列;杨过更是舍小我之仇恨,承传嵇康之“魏晋风度”,最终亦追随郭靖抗击蒙古大军;张无忌在张三丰的精神感召之下,负起抗击元蒙之重担,最终又顾全大局而甘愿飘然远去。即金庸既写武侠,又写政治,而主要的是突显侠之正义与忘我,实乃对侠魂之召唤,而非“武侠愚昧的叹惋”,至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亦不能做到“根本上的鄙弃”,只是让侠客在历史的时空中参与演出,却无法逆转既定的历史现实。
(二)对侠的历史诠释
金庸武侠小说的另一创造性突破更在于融入历史的诠释,有论者认为:
金庸小说“历史感”之强烈,往往使读者分辨不出究竟他是在写“历史小说”还是“武侠小说”。[12]162
事实上,只有将武侠置于历史环境之中,侠客才能绽放异彩。从司马迁《史记·侠客列传》中最早关于侠所记载的“侠以武犯禁”[14]开始,便写出了侠的使命,没有特定的历史时空,侠的“以武犯禁”亦必将落空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金庸的历史意识于晚年的修订本中益发深入,除了在有历史证据之处作出说明之外,甚至将具体的年代标示出来或增入史料,如《天龙八部》的《释名》中,旧版(1963年香港武史出版社)原无“据历史记载,大理国的皇帝中,圣德帝、孝德帝、保定帝、宣仁帝、正廉帝、神宗等都避位为僧”“本书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祐、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旧版的《射雕英雄传》原仅有“山外青山楼外楼”一诗引首,略叙其历史背景,而修订版中则改为“张十五说书”,以引出其时宋、金的局势。金庸在中国历史的各个转折点上均予以省思,实乃传承自鲁迅以降的对国民性的拷问,例如:《天龙八部》中的胡汉之分与萧峰的舍身喂鹰;《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抗议名教与抗击蒙古之后返回古墓隐居;《倚天屠龙记》中的复仇与宽恕;《笑傲江湖》中的正邪之辨。这一切,均是国民性的关键以至于哲学思考的重大命题,绝非坊间谈情说爱的俗套小说可以企及。
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在其批评者夏志清对现代小说所评价的“感时忧国”的思潮上走得更深更远,而在想象的空间上则拓展得更广更阔,诚如舒国治所言:
其文体早已卓然自立。今日我国人得以读此特殊文体,诚足珍惜。而金庸作品之涵于当代中国文学范畴,亦属理所当然。[15]140
由此而论,若将金庸武侠小说置于五四文学之中,亦是独树一帜,光芒万丈,不可忽视。治文学史者以陈见陋习而排斥武侠小说于文学史之外而声言寻求现当代文学杰作,何异于刻舟求剑?
(三)对武功描写的创造性突破
金庸武侠小说能在新派武侠小说的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其关键之一在于其对武功描写的创造性突破,武当派开山祖师张三丰的创造力则源于王羲之的“丧乱帖”、倚天屠龙歌诀以及龟蛇互搏而创造出太极拳、太极剑。金庸在张三丰的武功创造性上所花的心思不下于书写杨过的自创武功的过程:
二十四个字合在一起,分明是一套高明武功,每一字包含数招,便有数般变化。“龙”字和“锋”字笔划甚多,“刀”字和“下”字笔划甚少,但笔划多的不觉其繁,笔划少的不见其陋,其缩也凝重,似尺蠖之屈,其纵也险劲,如狡兔之脱,淋漓酣畅,雄浑刚健,俊逸处似风飘,似雪舞,厚重处如虎蹲,如象步。[16]131
此乃无意之书,乃浑然天成的武功创造:
张三丰情之所至,将二十四个字演为一套武功。他书写之初原无此意,而张翠山在柱后见到更属机缘巧合。师徒俩心注神会,沉浸在武功与书法相结合、物我两忘的境界之中。
这一套拳法,张三丰一遍又一遍的翻覆演展,足足打了两个多时辰,待到月临中天,他长啸一声,右掌直划下来,当真是星剑光芒,如矢应机,霆不暇发,电不及飞,这一直乃“锋”字最后一笔。[16]132
以上乃绝妙武功,亦是绝妙文字与想象。张三丰之武功实如诗学之神韵派,随兴之所至而抒写胸臆。24个字,215笔中的腾挪变化,此为“倚天屠龙功”[16]132-135。“情之所至”“无此意”“物我两忘”“长啸”,以上种种境界,皆乃“魏晋风度”,是金庸用以推崇一代宗师张三丰的最崇高修辞,以上之书写,乃绝妙文字,更是百年现代文学史上对武功的罕见描写。
在《神雕侠侣》中,郭靖则在襄阳城以“上天梯”的功力爬上城墙的惊险一幕突显其以武功应用于战场之智慧:
郭靖一觉绳索断截,暗暗吃惊,跌下城去虽然不致受伤,但在这千军万马包围之中,如何杀得出去?此时敌军逼近城门,我军若是开城接应,敌军定然乘机抢门。危急之中不及细想,左足在城墙上一点,身子陡然拔高丈余,右足跟着在城墙上一点,再升高了丈余。这路“上天梯”的高深武功当世会者极少,即令有人练就,每一步也只上升得二三尺而已,他这般在光溜溜的城墙上踏步而上,一步便跃上丈许,武功之高,的是惊世骇俗。霎时之间,城上城下寂静无声,数万道目光尽皆注视在他身上。[17]885
郭靖再以三箭大败忽必烈大军:
郭靖身在半空,心想连受这番僧袭击,未能还手,岂非输于他了?望见金轮法王又是一箭射来,左足一踏上城头,立即从守军手中抢过弓箭,猿臂伸屈,长箭飞出,对准金轮法王发来的那箭射去,半空中双箭相交,将法王来箭劈为两截。法王刚呆得一呆,突然疾风劲急,铮的一响,手中铁弓又已断折……他连珠三箭,第一箭劈箭,第二箭断弓,第三箭却对准了忽必烈的大纛射去。
这大纛迎风招展,在千军万马之中显得十分威武,猛地里一箭射来,旗索断绝,忽必烈的黄旗立时滑了下来。城上城下两军又是齐声发喊。
忽必烈见郭靖如此威武,己军士气已沮,当即传令退军。[17]886-887
郭靖的神威更在力斥忽必烈的招降以示忠贞不屈之后,身在千军万马之中,将“降龙十八掌”“九阴真经”及全真派天罡北斗阵法,融会贯通,在战场上施展开来:
郭靖此时所施展的正是武林绝学“降龙十八掌”。法王等三人紧紧围住,心想他内力便再深厚,掌力如此凌厉,必难持久。岂知郭靖近二十年来勤练“九阴真经”,初时真力还不显露,数十招后,降龙十八掌的劲力忽强忽弱,忽吞忽吐,从至刚之中竟生出至柔的妙用,那已是洪七公当年所领悟不到的神功,以此抵挡三大高手的兵刃,非但丝毫不落下风,而且乘隙反扑,越斗越是挥洒自如。……郭靖的降龙十八掌实在威力太强,兼之他在掌法之中杂以全真教天罡北斗阵的阵法,斗到分际,身形穿插来去,一个人竟似化身为七人一般。[17]905
以上以武功驾驭战场的两幕,浑然天成,郭靖作为中原武功第一的身手,于此展现,其博大精深与勇猛刚烈,举世无匹,万夫莫敌,乃萧峰之后,在战场上如天神般横扫千军的英雄(6)相关论述可参阅陈岸峰:《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功》,载《南都学坛》2021年第1期,第39-51页。。
柏杨(1920—2008)在《武侠的突破》中指出:
金庸先生武侠小说的兴起,使武侠小说以另一副崭新的面貌出现——它与众迥然不同,不仅与今人的武侠小说迥然不同,也与古人的武侠小说迥然不同。第一、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是真正的武侠小说,有“武”,尤其有“侠”。第二、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是完整的文学作品,像大仲马先生的《侠隐记》是完整的文学作品一样,它的结构和主题给你的冲击力,同等沉厚。[15]142-143
柏杨指出金庸武侠小说在古今武侠小说中的“迥然不同”,亦即其创造性,同时又肯定其武侠小说乃“文学作品”,甚至将其推崇至法国大仲马的地位(7)相关论述可参阅严家炎:《似与不似:金庸和大仲马小说的比较研究》,吴晓东、计璧瑞编:《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239页。。冯其庸先生则认为:
金庸的小说大大发展了侠义小说的传奇性。传奇性,这本来是侠义小说本身应有的不可或缺的特点,如侠义小说而不带某种传奇性,反倒令人不满足,甚或失去其特色。问题是在于这种奇峰天外飞来之笔的可信程度,前后情节连接的合理程度,也即是传奇性与可信性的一致,从这一点来说,金庸小说,常常又使你感到奇而不奇,甚至读而忘记其奇。[15]48
伟大作家之不同于平庸作家之处便在于想象力的神驰。金庸武侠小说的突破在于人物之奇、故事之奇及武功之奇,这一切均是其想象力的创造性所在。有论者指出:
回顾一下汉语文学史,特别是汉语叙事文学,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无论魏晋志怪、唐宋传奇、元明戏曲,或者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山海经》《太平广记》《阅微草堂笔记》这类准文学的笔记写作,符合写实原则的颇少,而“离奇荒诞”者居多:即使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的《红楼梦》《水浒传》其实也不乏“离奇荒诞”内容,甚至可以说,倘若没有那些“离奇荒诞”的成分,《水浒传》不成其为《水浒传》,《红楼梦》也不成其为《红楼梦》。[12]30
金庸武侠小说中主人公之种种奇遇,历险、获武功秘籍而练成绝世神功,其想象力真可谓上天入地,无奇不有,为五四文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文学之偏于写实主义作出补济。例如:萧峰于千军万马中伏于马腹之下奔杀南院大王并擒拿楚王,犹如天神之纵横天地;天山童姥与李秋水之决战,死而复生,生而复死,令人拍案称奇;丁春秋与虚竹之战,优美如道家美学的呈现;鸠摩智“火焰刀”的武功,震撼人心;小龙女以左右互搏使剑,犹如天女散花;黄药师与欧阳锋及洪七公以箫、筝及啸之较量,犹如八仙中的韩湘子与妖怪及铁拐李在海上搏斗;张三丰以“丧乱帖”创造武功,实乃“魏晋风度”与武功之结合的崇高境界;张无忌力战少林三高僧的“金刚伏魔圈”,其场景之恢宏,情节之扣人心弦,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令狐冲在华山之上中了圈套而生命悬于一线,凭借鬼火而打败左冷禅、林平之而化险为夷;韦小宝的种种奇遇及江湖手段,滑稽至极。
刘再复指出金庸武侠小说之突破更在于以下各方面:
金庸写作的自由精神,不仅使他的小说能够以自觉自创的文创把本属于俗文学的武侠小说提升到与新文学同等的严肃文学的水平,而且使他的小说在审美内涵上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单维现象(只有“国家”“社会”“历史”之维),增添了超验世界(神奇世界)和内自然世界(人性)的维度,使“涕泪飘零”(刘绍铭语)的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另一审美氛围,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缺少想象力的弱点。而在描写“国家”“社会”“历史”维度时,用现代意识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界限,消解汉族主义,质疑了通行的本质化了的“中国人”定义,使得金庸小说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梦想。[12]19
金庸武侠小说之想象奠基于现实,对武侠、奇遇以及人生际遇做了极致的发挥。因为金庸武侠小说之创造性的想象,使20世纪中国文学走出所谓“写实”的政治桎梏,在“超验”与“人性”的层面作出极大的发挥,并以多元民族思维,促进民族共和。
(四)对雅俗界限的超越
金庸武侠小说是五四以降的文学创作之中,不经任何的意识形态所刻意扶植而自然生成的重大文学成果。即是说,真正意义的白话文学的开花结果,始于金庸的武侠小说:
金庸对本土传统小说形式的继承和革新,既是用精英文化改造俗文学的成功,又是以俗文学的经验对新文学的偏见做了最切实的纠正。这确实具有“存亡继绝”的重大意义。[12]42
又:
历史上的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原本各有自己的读者,简直泾渭分明。但金庸小说却根本冲破了这种河水不犯井水的界限。[12]43
严家炎甚至称金庸武侠小说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18]276。故此,所谓的“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设置与论争(8)王剑丛在《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中便将金庸武侠小说列于“通俗文学”之中。[19]347,本身便十分可笑。有论者便指出:
由于社会变化和外来文学影响,中国文学已逐步分裂为两种不同的文学流向:一种是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的“五四”文学革命催生的“新文学”;一种是保留中国文学传统形式但富有新质的本土文学。[12]41
所谓的“雅俗对峙在二十世纪就成为小说内部的事”[12]35,“雅俗对峙”事实上是一种文化霸权,金庸的武侠小说就因为被标签为“通俗小说”而被摒除于文学史之外(9)王剑丛指出:“俗”并非庸俗,而是深入浅出、是大众化、民族化的需要。要真正地做到雅俗结合并非易事。这是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然而他却又认为“香港生活节奏快、香港社会的世俗化倾向”而导致武侠小说的崛起,似乎没有合乎逻辑的必然关系。见王剑丛:《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第348页。[19]348,或附于边缘位置。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无论在文字、人物、情节以至于思想上,均远远超越五四运动以来的所谓正统文学或严肃小说,其叙事、描摹、想象以及思想内涵,为百年之内所少有者。金庸自己说:
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15]71;[12]40
可见,金庸亦已被迫接受武侠小说作为通俗、娱乐的属性,但他又希望在既定的框架中有所作为,在《天龙八部·后记》中金庸便赞同陈世骧(子龙,1912—1971)先生的见解:
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的无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20]2210
而事实上其武侠小说中所谓的“娱乐性的东西”绝少,如老顽童周伯通与桃谷六仙的滑稽,亦只如戏剧中的插科打诨的元素而已,况且老顽童与桃谷六仙的诙谐亦有其深意,并非无聊与低俗。
(五)对理想的国语的实现
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功,除了对武侠境界上的创拓之外,其最成功之处更在于其以小说的方式创造了“新文学运动”中所谓的“理想的国语”,即从胡适以至于周作人等人所追求的理想的现代白话文。五四之后的白话文运动,分化成欧化白话与旧式白话两股潮流[12]32。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文字,亦有过渡的痕迹,即从欧化白话到糅合文言白话以及浙江方言的过程(10)关于金庸武侠小说在语言上的糅合古典与现代的论述,可参阅刘登翰:《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271页。。有论者指出:
金庸以他独特的语言面向了、倡导了另一种写作。说这种语言源自“五四”之后的旧式白话,这当然不错,但金庸的白话不仅与还珠楼主或张恨水的白话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明显又吸收了欧化的新式白话的种种语法和修辞。[12]32-33
金庸欧化白话的语法及修辞主要体现于《飞狐外传》中,例如以下描写南兰与马春花的文字:
终于有一天,她对他说:“你跟我丈夫的名字该当对调一下才配。他最好是归农种田,你才真正是人中的凤凰。”也不知是他早有存心,还是因为受到了这句话的讽喻,终于,在一个热情的夜晚,宾客侮辱了主人,妻子侮辱了丈夫,母亲侮辱了女儿。[21]56-57
在传统中文中,“夜晚”不会用“热情”作为形容词,而且更不会连用三个“侮辱”。又:
那时苗人凤在月下练剑,他们的女儿苗若兰甜甜地睡着……
南兰头上的金凤珠钗跌到了床前地下,田归农给她拾了起来,温柔地给她插在头上,凤钗的头轻柔地微微颤动……[21]56-57
连用两个“给她”,颇为生硬、累赘,而以凤钗之颤动作为性象征,亦源自西方文学技巧。福康安与马春花在后花园偷情一幕的文字更是明显的欧化白话风格:
福公子搁下了玉箫,伸出手去搂她的纤腰。马春花娇羞地避开了,第二次只微微让了一让。
但当他第三次伸手过去时,她已陶醉在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男子气息之中。夕阳将玫瑰花的枝叶照得撒在地下,变成斑驳陆离的影子。在花影旁边,一对青年男女的影子渐渐偎倚在一起(原版:终于不再分得出是他的还是她的影子)。太阳快落山了,影子变得很长,斜斜的很难看。
唉,青年男女的热情,不一定是美丽的。[21]101-102
最后一句的叹喟,很像巴金《家》《春》《秋》中的腔调。以上所引,均为金庸创作初期在文字上的探索。在后来一再的修订中,他已在几部长篇小说中建构起流畅而优美的现代白话文。故有论者指出金庸武侠小说在白话文上的价值,便在于以其所创造的现代白话文抗衡西潮之下欧化白话文的冲击:
新体白话文是新文学作家交出的一份答卷;金庸小说的白话文是金庸交出的另一份答卷,同时也是本土文学作家中交出的最好的一份答卷。两者的孰优孰劣恐怕还会有争论,但是无疑金庸的白话文比新体白话文负荷着更多的民族文化价值,假如我们要从语言观察、体认、学习汉语本身的文化价值,金庸的白话文肯定比新体白话文提供更多有益的启示。金庸透过写作,不但提高了白话文的表现水平,而且在西潮滚滚的时代,在中国文化价值备受挑战的时代,用他一以贯之的语言选择承担了重振民族文化价值的使命。[12]21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智慧的综合呈现,中国语言的现代化始于五四时期,其时一切均为尝试。五四时期的知名作家在语言方面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很多作家在作品中的文字都带有明显的地方方言以及文言文的痕迹。故此,胡适与周作人等人均曾做了多方面的探讨。周作人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所作的《导言》中指出:
民国六年以至八年文学革命的风潮勃兴,渐以奠定新文学的基础,白话被认为国语了,文学是应当“国语的”了……但是白话文自身的生长却还很有限。[22]666
细心玩味之下,周作人对当时所谓的白话文之成功已成事实的观点,颇有保留。首先,他指出白话文在清末与民国已有所不同:第一,现在白话,是“话怎样说便怎样写”。那时候却是由八股翻白话;第二,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23]51-52。周作人分辨白话文与古文之别在于“白话文的难处,是必须有感情或思想做内容”,而古文则“大抵在无可讲而又非讲不可时,古文是最有用的”[23]58。即是说,古文之书写颇为曲折,而用白话文则是因为其时“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23]58,要求的是直接、明快的表达方式。至于胡适,则为“白话”作出如下三种定义:清楚、直接、简单的语言,即其所谓的“白话”[24]8。为进一步说明“白话”的特征,胡适以“生”与“死”判别“白话”与“文言”的关系[25]57,认为国语的文法是“一种全世界最简易最有理的文法”[24]6。胡适又在《国语文法概论》一文中,从音韵、词汇以至于句子,均做了详细的论述(11)有关胡适《白话文学史》的论述,可参阅陈岸峰:《革命与重构:论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58-64页。[25]443-499。然而,胡适更多的关注则寄望于国语拼音的成功(12)周作人在《国语罗马字》一文中虽对罗马拼音存有质疑,但仍然表示支持。见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1-62页。[26]111-119。事实上,早在1922年,周作人便已对建设现代国语作出了具体的建议:采纳古语;采纳方言;采纳新名词[27]。周作人“理想的国语”的构思,乃从自己对语言的了解出发而作出更为深入的探讨及建议。他指出可以以口语为基本,糅合古文、方言以及欧化语,加以合宜的安排,知识与趣味并置,“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再加上自己的性情,从而造出雅致的现代汉语[28]123。他又进一步提倡“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的文章[29]221,即在锻炼文字中,将文人的优雅文字镕铸于市井俗语之中,中外兼采,古今并用,为传统古文与现代白话文的渗透,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13)相关论述可参阅钱理群:《周作人传》,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85-394页。。他又于1926年撰写《我学国文的经验》,仔细罗列了《四书》以及部分的经、史类,而更多的是白话小说,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琴南,1852—1924)翻译的《茶花女》、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最终,他建议博览以吸取众书之精华[30]7-11。
然而,胡适与周作人可能都没想过,理想国语之成功,并不在于语法之严密,或不同元素之配合,他们所建议的一切均只是悬浮于理念上的想象。理想国语之成功,在于一位可以集各项元素之大成而又能流行于所有华人地区的成功作家的出现,其成功的实践比一切的构思更有示范性与影响力。最终,成功地实践了胡适与周作人“理想的国语”之作家,便是金庸。自金庸作品面世以来,除了思想层面获得了普遍的认可之外,其语言之传播亦同时为普罗大众所接受,潜移默化,约定俗成,这就是五四以来所期待的“理想的国语”。有论者指出:
金庸小说的语言特点与成就有以下几点。一是“述事如出其口”,真正地做到了口语化,明白流畅,言文一体;二是语言丰富,且出神入化,将成语、方言、俗语等等都“化”入他的现代口语之中;三是语言优美,生动活泼,发掘了汉语特有的诗性特征(当然也继承了古典诗、词、曲、赋的优秀语言传统,并将之“化”入小说的叙事语言之中);四是机智幽默,随处发挥,极富创造性,至于语言的准确和鲜明,以及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等等。[12]87
作为一个作家,如不能“述事如出其口”,那便没有成功的希望,至于语言的丰富、优美、生动、活泼,都是成功作家的基本要求,而机智幽默则与语言没直接关系,只是回到第一点的“述事如出其口”,即与作家的个性有关。金庸在“理想的国语”方面的创造性,可见于《天龙八部》中萧峰在战场上的一段文字:
萧峰执了一张硬弓,十枝狼牙长箭,牵过一匹骏马,慢慢拉到山边,矮身转到马腹之下,身藏马下,双足钩住马背,手指一戳马腹,那马便冲了下去。山下叛军见一匹空马奔 将下来,马背上并无骑者,只道是军马断缰奔逸,此事甚为寻常,谁也没加留神。但不久叛军军士便见马腹之下有人,登时大呼起来。
萧峰以指尖戳马,纵马向楚王直冲过去,眼见离他约有二百步之遥,在马腹之下拉开强弓,发箭向他射去。楚王身旁卫士举起盾牌,将箭挡开。萧峰纵马疾驰,连珠箭发,第一箭射倒一名卫士,第二箭直射楚王胸膛。[20]1181-1183
再看《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与黄蓉在湖上约会的文字:
船尾一个女子持桨荡舟,长发披肩,全身白衣,头发上束了条金色细带,白雪映照下灿然生光。郭靖见这少女一身装束犹如仙女一般,不禁看得呆了。那船慢慢荡近,只见那女子方当韶龄,不过十五六岁年纪,肌肤胜雪,娇美无比,笑面迎人,容色绝丽。[31]333
所谓“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用以形容金庸以上两段分别描写战场上仿如天神的萧峰之神勇与湖上美如仙子的黄蓉的芳姿神态的文字,可谓恰如其分。这就是金庸作为一位伟大作家在文字上所综合与创造的阳刚与阴柔之美。
金庸的文字,除了欧化与文、白以至于方言的糅合外,其成功处主要还体现于以下几方面:武功的动作及动词的运用的准确与多姿;人物心理的描写的细腻入微;风景描写之到位,特别是江南风物;切合人物所处的朝代及身份的语言。至于方言方面,金庸在着手修订自己的作品之际,曾将《天龙八部》中的人物阿朱和阿碧的口语对话,改写为苏州白话。这说明他意识到方言的妙处,一番苏州白话,令整段书写妙趣横生,同时亦令读者随段誉走出大理,一下子置身于吴侬软语及苏杭风物之中。故此,在建构“理想的国语”的同时,金庸亦不忘适时发挥方言的功能,这便是语言之妙用无穷,当然亦属其巧思天成。
(六)对人的文学的召唤
武侠除暴安良、心系天下,这一切均乃人性的善良与正义的召唤。金庸自己便曾说过:“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绝大多数小说一样。”[32]1749人性的文学,即人的文学,亦即呼应了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号召,这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道路。更为重要的是,金庸武侠小说乃有意识地对五四以来的小说观念的偏颇作出补给:
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似乎出现了一种观念,以为只有外国的形式才是小说,中国的形式不是小说,例如一般人编写的文学史或小说史,都很少把武侠小说列入其中,或是给予任何肯定。我想这和武侠小说本身写得不好也有关。这也是情有可原。不过,一般知识分子排斥像张恨水那样的章回小说,而把巴金、鲁迅那些小说奉为正统,这个问题主要是基于政治因素甚于艺术因素。[12]114
武侠小说之被排斥与边缘化,既中断了侠义观念的承传,又灭绝了江湖的想象。故此,金庸武侠小说之崛起乃有意识地对传统小说作出创造性的改造及发展,以对现代文学补偏救弊。有论者指出:
中国传统小说自五四以后已一蹶不振,金庸不仅对之进行改造,而且大大发展,赋予新的人文关怀之精神,从语言、结构、情节、描写等方面革故鼎新,使中国传统小说重放异彩,这种改造犹如黄宾虹对中国山水画的改革、梅兰芳对京剧的“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小说有别于五四以后的新潮小说,为已成为历史的中国传统小说重获新生而开拓了成功之道。[12]161-181
换言之,金庸武侠小说乃划时代的创新,一如黄宾虹之于山水画、梅兰芳之于京剧。
金庸武侠小说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建伦理,召唤良知,讴歌侠客,肯定爱情,批判虚伪,驱逐黑暗,这一切均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发扬,均乃“人的文学”之最成功的实践。故此,金庸武侠小说乃对五四以来以激烈反传统以至于“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摧毁传统人伦、文化至于极致的救赎,可以说是在废墟上想象传统,重建价值。
武侠小说之被排斥与边缘化,既中断了侠义观念的承传,又灭绝了江湖的想象。金庸及其武侠小说自被陈世襄先生推崇为“无异于元曲之异军突起”“所不同者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20]2220。故此,金庸武侠小说之崛起乃有意识地对传统小说作出创造性的改造及发展,以对现代文学补偏救弊。
TheEnlightenmentofMartialFictionsintheLateQingDynastyandtheAchievementsofLouisCha
CHEN Anf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 530006, China)
Abstract:After the crushing defeat of the Qing Dynasty (1616—1911) i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 the Qing Empire faced internal rebellions and external invasions, under which circumstances a plethora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patriots rose to the occasion in a desperate move to salvage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being split asunder. Chinese scholars and political activists like Zhang Taiyan, Liang Qichao, and Tan Sitong argued that martial arts culture could be leveraged to enlighten the ignorant Chinese populace, drawing reference from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martial arts on politics.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people thus became high on the agenda of Chinese literary movements. The famous political reformist Liang Qichao published lots of articles in this regar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cept of “Swordsman” translated from Japan aroused the writing of martial fictions in China. Louis Cha, better known by his pen name Jin Yong was a renowned writer of martial fictions who had published lots of wonderful works. Chinese nationalism or patriotism is a strong theme in his works, many of which also emphasize the idea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identity. His works show a great amount of respect and approval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especially Confucian ideals such as the proper relationship between ruler and subject, parent and child, elder sibling and younger sibling, et cetera. The rising of Louis Cha in the mid-20th century had expanded the types and possibilities in martial fiction creation, especially regarding the main theme of saving the nation from extinction, which was viewed as a concrete response to Liang Qichao’s enlightening call.
Keywords:Liang Qichao; martial fiction; enlightenment; Louis Cha; cultural imag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