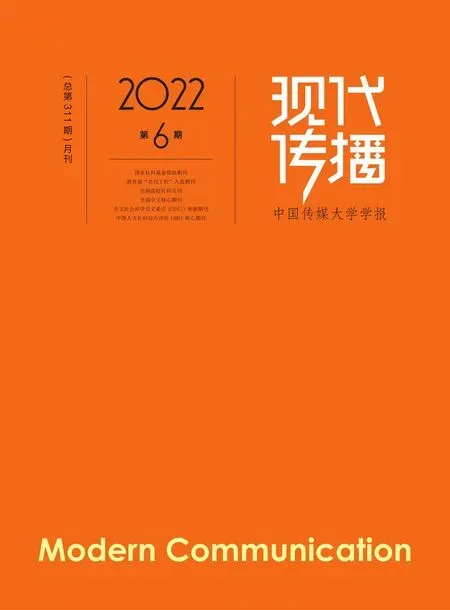全球计算宣传的趋势、影响及治理路径*
2022-11-21邹军刘敏
邹 军 刘 敏
一、引言
人们真正认识宣传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时各种宣传策略被广泛使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拉斯韦尔将宣传定义为“通过操纵表述以影响人类行为的技巧”①,揭示了宣传的本质就是符号操纵,是借助符号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手段。回顾宣传的历史不难发现,每当有新的传播媒介问世和普及,一股新的宣传浪潮就会随之而来——无论是报刊、电影、广播还是电视,都被充分地用于宣传。互联网自20世纪90年代商业化以来,经过短短30年的发展,已成为信息传播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是舆论呈现的绝佳之地,也是各种势力开展宣传的主阵地。近年来,伴随社交媒体的兴起,一种依托于社交媒体平台的新宣传方式——“计算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应运而生。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塞缪尔·伍利(Samuel Woolley)和英国牛津大学的菲利普·霍华德(Philip N.Howard)于2016年联合发表题为《政治传播、计算宣传和自主代理》的文章,将计算宣传界定为“社交媒体平台、自主代理、算法和旨在操纵舆论的大数据的组合”②。数据显示,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可能有超过1.5亿人受到俄罗斯宣传活动的影响③,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计算宣传和传播政治虚假信息的国家和政党数量逐年增长,计算宣传的工具和技术已经成为政治和公共外交等领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④。
计算宣传在政治传播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以至于要理解当代政治和社会传播,就必须研究计算宣传以及与之相关的算法、自动化政治等。国外关于计算宣传的研究往往以某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该国家计算宣传呈现的特征及带来的危害。⑤如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简称OII)关于世界各地计算宣传案例的研究报告认为,基于计算宣传的社交媒体操纵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主要表现为政府参与和组织的造谣活动。⑥就影响而言,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计算宣传在破坏民主的同时,会摧毁法治、选举自由和禁止操纵选民等公共价值观,全世界的政治话语也因此正在被改变。⑦诸多事实证实政治行动者利用算法技术和政治机器人试图操控公众舆论,但他们对这些工具的运作也不能完全控制。⑧
从国内研究情况看,计算宣传的影响最受关注,如欧亚、夏玥等指出计算宣传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得到普遍应用并显现出潜在威胁,国际传播遭遇新挑战⑨;罗昕、张梦等认为计算宣传在西方已成为操纵舆论的重要方式,政治人物利用它帮助实现自身政治目的⑩;史安斌、杨晨晞通过分析“信息疫情”与计算宣传的关联,发现计算宣传会加速“信息疫情”的蔓延。至于计算宣传的具体运作,多数研究将其与社交媒体操纵联系在一起。如骆正林、曹钺从主体性、主体间性与人机关系三个维度批判社交媒体机器人假新闻的“远距离操纵”、数字劳工以及交流中介角色;张洪忠等则指出政治机器人的舆论干预突出体现在政治选举、社会动员、政治干扰三种应用场景;卢林艳等借助社交媒体账号的元特征、网络特征、内容特征、时间特征等分析社交机器人的行为特征,发现社交机器人更接近喧哗的大众,发声的目的不是创造某种观点,而是让某种观点变得引人瞩目或者通过关注特定话题模糊视线。
梅罗维茨指出:“电子媒介打破了传统的情境定义,使得私人情境和公共场所的界限变得模糊,从而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角色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社交媒体的兴起进一步打破了公域和私域的界限,为计算宣传手段的更新迭代提供了合适的传播情境,其影响与日俱增。面对这一现象,我们有必要将目光投注到这一尚在发展的宣传实践,探讨全球计算宣传呈现的新态势,分析其多层面的影响,并提出治理之策。
二、计算宣传更新了社交媒体操纵的手段
社交媒体操纵是一系列相关操纵技术的集合,“监视”与“控制”是其主要形式,包括使用逻辑谬误、心理操纵、虚假信息、修辞和宣传技巧,通过排挤信息或对抗观点来压制对方意见,诱导他人或群体停止听取对方论点,将受众注意力转移到操纵者设置的议题上。相较于传统的社交媒体操纵,作为智能时代产物的计算宣传大大拓展了社交媒体操纵的边界和影响范围,对于信息传播的破坏和操纵更隐蔽、更复杂,也更具误导性和冲突性。计算宣传超越了以往任何一种媒体操纵方式,呈现出如下态势:
(一)信息操纵更加隐蔽与不可控
社交媒体匿名机制和网络平台取代了传统把关人,媒体操纵显得更为隐蔽。相较于单纯依靠社交机器人驱动的操纵方式而言,计算宣传更擅长使用算法技术、自动化加人工管理技术,有目的地在社交网络上散布误导性信息而非单纯的人际互动。一般而言,社交机器人的运行逻辑以社交关系为主,能够在短时间内依托真实用户的社交网络加速噪音信息的传播。但社交机器人只是计算宣传的一部分,且依然是对人类行为的模仿而非超越,而算法技术的超级计算能力和社交媒体中的海量信息结合在一起,可精准地向具体的人提供量身定制的信息。可以说,计算宣传的威力远超单纯依赖社交机器人的舆论操纵。由于普通用户对于算法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存在一定程度的知识盲区,因而在舆论发酵之初借助自动化信息为用户设置政治议题,就可以塑造一种虚假的社会共识和媒介真实,让用户误以为所有的信息都来自自己的个人网络,即家人、亲戚和朋友。例如,当大量的机器人被用来跟踪、转发或点赞某候选人的内容时,这位候选人就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容易得到广泛支持。这将带来所谓“媒介等同”(media equation)效果,即用户下意识地对社交媒体的自动化信息做出社会性反应——理性被压制,错误信息像病毒一样在网络社区中传播。计算宣传对社交媒体用户的操纵正是利用虚拟社区缺乏集中控制的特点,通过自动化的数据生成来传播充满偏见的信息。至于舆论大规模扩散时期,计算宣传基于协同过滤机制将“政治模因”(meme,类似中文的“梗”)推荐给宣传对象,再经过用户的大规模转发,其传播效率和影响力都很惊人。在整个操纵过程中,计算宣传不易被监测到,人们也无法简单地了解他们的范围和规模,这为有效预防和抵制计算宣传带来了挑战。
(二)欺骗和误导更快、更智能
社交媒体的兴起与通信技术的可供性激发了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也为进一步释放集体行动和话语表达的潜力提供了可能。深度学习和智能算法让社交机器人的速度变得更快,更能理解人类互动。正因如此,网络空间的决策权和选择权逐步让位于计算宣传主导下的社交机器人,人的主体性与权威性被大大降低。尽管假新闻、假账户等都可以成为计算宣传操纵的手段,但社交机器人仍是最常用的方式。当社交机器人逐渐以“类人化”的方式去制造虚拟账号并进行传播时,计算宣传就可以在无形之中渗透到虚拟空间的每一个角落,“机器水军”成为驱动社交网络的决定性力量。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机器人不仅生成的选举推文数量比其他类型的推文高得多,而且主要在操纵者所设定的政治框架内发布推文(左倾和右倾社区都超过80%)。这被视为计算宣传实施大规模欺骗的重大胜利,亦是社交媒体操纵使用计算宣传方式的分水岭。计算宣传在引导公众情绪、操纵舆论和规避法律程序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表现在数字民主和选举方面,由软件驱动的自动化系统掌握着政治交流和民主进程的命脉。除此之外,社交平台本身的开放性和低门槛让政治性媒介操纵更易成为误导其他国家的工具。有西方国家借助计算宣传在敌对国家的社交媒体大肆散播虚假信息,致使对方舆论环境复杂化。例如假借互联网自由的名义开展了包括“薮猫项目”(The Serval Project,即突破互联网防火墙的限制,在没有基础设施、无线发射塔、卫星、无线接入点及载波的情况下实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通讯,支持各种手机终端)在内的综合破网工程,在全球范围内借助社交机器人传播本国的价值观,通过网络虚拟机器人自动发帖倒灌政治谣言和情绪渗透,在社交媒体以最短时间聚集最多的参与者,再借助圈层传播的力量动员并串联集体行动来误导公众,为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服务。
(三)“巨魔部队”越来越组织化和政治化
“巨魔部队”(troll armies)最初被定义为“那些故意诱使人们产生情绪反应的人”。“巨魔部队”与“网络水军”的概念较为接近,意指受雇于政府、军队或政党,通过社交媒体操纵公众舆论,传播政治观点和干扰决策的类军事化组织。越来越多的“巨魔部队”利用计算宣传的高智能性,参与到重大政治事件的进程中。他们采用自动化和人机交互组合的方式躲避平台的限制和侦查,使得带有政治意图的操纵更为灵活和复杂。政治行动者通过“巨魔部队”能够大规模地生产出充满强烈怨恨和反对的信息,如欧盟研究发现由俄罗斯国家机构雇用的“巨魔部队”,一直在社交媒体上积极评论和张贴内容,服务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议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治情感的唤起并非基于理性,而是由发自内心的经验情感和想象中的对错意识形成的,这给了“巨魔部队”更多信心。近年来,大量“巨魔部队”从准军事单位转变为与政府签订合同的战略传播公司,对社交媒体的操纵也逐渐演变成越来越组织化、政治化的活动,“巨魔”俨然成为仇恨言论和骚扰的代名词。早在2015年,英国陆军第77旅就宣布将在社交网络上通过控制信息的叙事方式与敌人作战。一项研究表明,全球有30个政府(在该研究涵盖的65个政府中)雇佣“键盘军”(即巨魔部队)进行宣传和攻击批评者。“巨魔部队”通过强调悲情来唤起情感,从而加深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不仅如此,“巨魔”制造的虚假信息在危机时期得到迸发式增长,即便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也不例外。有研究者指出,信息需求的急剧增加和民粹主义的暗流涌动为计算宣传奠定了理想环境。在这种高风险情况下,信息景观操纵的下游效应可能表现为态度和行为,个体对他人的想法或群体的行为模式缺乏了解,网络空间的对立冲突时有发生,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四、计算宣传的多层面影响
尽管计算宣传亦可用于寻求建设性的公共服务、改善新闻业和产生公共知识,但计算宣传带来的更多是深刻的政治动荡和伦理问题。对网络信息进行战略性操纵以行使政治权力,已成为21世纪公众舆论形成的一个关键问题,相关文献也显示出多项政治活动与计算宣传有关。当虚假新闻内容得到自动化支持并通过不透明的算法以预先编程的方式来传播时,政治行动者便拥有一套强大的计算宣传工具。而这一操纵方式又常常与虚假新闻、后真相政治、社交媒体相勾连,让计算宣传的影响渗透到包括政治在内的多个领域。这些影响往往从控制个体的认知开始,进而扩展至网络舆论,然后产生对现实政治的影响。
(一)个人层面:引发“孤岛行动主义”
总部设在美国的咨询研究机构——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Future,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智囊团,旨在帮助组织规划长期未来,简称IFTF)数字智能实验室主任塞缪尔·伍利博士说:“计算宣传的目的不仅是让不受欢迎的意见在社交媒体对话中显得更受欢迎,它还使民主运作不可或缺的群体保持沉默和分裂。”长此以往,社交媒体在深化公民参与和改变民主方面的理想主义观点被计算宣传的恶意活动所重创。不仅如此,受“后真相”病灶影响,假新闻传播呈几何式增长,计算宣传与“后真相政治”交织后更显强大,而公民力量和对抗精神却越来越单薄。
1.虚假信息泛滥搭建思想“牢笼”
在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2012年的墨西哥选举、2013年的波士顿马拉松和2014年的土耳其选举期间,人工智能与计算宣传技术尚未成熟,社交媒体操纵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被监测。随着深度伪造(deep fake)技术的不断成熟,信息和视频更容易被篡改,计算宣传制造的虚假信息也更加隐蔽。心理学研究显示,人们在无法找到最佳解决方案或者在处理复杂数据时,倾向于放弃复杂分析过程,依赖思维捷径做快速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恶意行动者通过计算宣传控制社交媒体,创造围绕目标群体的媒体幻影,极易导向错误的结论,造成以讹传讹。与此同时,计算宣传借助平台匿名机制制造自动账号或虚假角色来传播的假新闻更能促成主流观点的形成,让受众产生“人为共识”的错觉。自从“深伪”开始用于计算宣传以来,社交机器人不仅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布最新报道,也能发送大量的阴谋论和宣传性内容,将伪造的信息与虚假的权威勾连,使其具有误导、误传和操纵信息的空前潜力。面对虚假信息的泛滥和算法推荐的广泛采用,民众容易陷入已有认知的“信息茧房”,无形中受困于思想牢笼。当某些事件触及到不同人群的认知分歧时,情绪就会被不断放大并通过圈层传播在网络空间回荡,最终出现群体极化效应。
2.民族主义“巨魔”压制个人言论
有研究显示,至少从2012年起,机器人就被用于在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骚扰记者和攻击持不同政见者。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热衷于在社交媒体展开政治行动。为了更好地推动舆论,设定政治或媒体议程,审查言论自由或控制在线信息流,操纵者依靠使用自动化技术、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的计算宣传,雇佣大量的“巨魔部队”有目的地分发虚假、误导、捏造的内容,影响或欺骗社交媒体用户,将计算宣传的政治属性发挥到极致。“巨魔部队”从事的计算宣传拥有大量资金和资源,能够通过高度协调的政府机构传播虚假信息并制造虚假共识。“巨魔部队”的强大威力不仅限制了言论自由,也帮助了党派极端分子、国家情报机构和恐怖分子提升自我宣传能力并攻击客观报道理念,削弱公众对媒体机构的信任,从而降低民主的质量。有研究者认为,在2016年菲律宾选举中,民粹主义领导人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的胜利正是得益于“巨魔部队”诱导下草根阶层的支持和虚假的媒介形象的营造。社交媒体的商业性使得影响意见的权力始终掌握在拥有最大传播权的个人或者组织手上。正如伯奈斯(Bernays) 所说:“在我们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行为中,无论是在政治或商业领域,在我们的社会行为或我们的伦理思想中,我们都被相对较少的人所支配……他们了解心理过程和社会运动的模式。正是他们拉动了控制公众思想的电线,他们利用旧的社会力量并设计出新的方式来约束和引导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只要能够控制“巨魔部队”,就能控制人们看到的信息。在计算宣传时代,正是少数操纵者利用社会裂痕和“巨魔部队”的话语扩散参与话题讨论和舆论发酵,从而挤压个人言论自由和话语表达的空间。
(二)群体层面:信息聚集下的舆论偏向
计算宣传对个人言论和思想的压制必然引发群体效应。表面上看,社交机器人和“巨魔部队”被部署从事传递信息和通信之类的合法工作,但受操控的信息大规模聚集便会成为加强计算宣传和仇恨运动的有效工具。一些政府使用政治机器人伪装成公民账号,发帖压制反对者的声音,尤其是在选举期间会采取更加广泛的部署,用虚假新闻报道、协调造谣运动和“巨魔”等计算宣传的关键要素,攻击人权捍卫者、民间社会团体和记者,试图左右选票或者诽谤批评者。这些自动化传播行为的影响常常难以察觉,经过社交媒体的放大,极易在群体层面带来情绪对立和舆论失焦的效果。
1.破坏性宣传削弱网络空间的公共性
互联网最初被视为一种推动民主化进程的设施,但是伴随社交媒体的兴起,去中心化的公共领域“乌托邦”被击碎。以平台为中介的计算宣传受到社交媒体运作的规训,商业目的和政治意图的操纵亦会干扰受众对真相的判断。“先入为主”的首因效应让计算宣传的观点和主张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加之议程设置的助推,操纵者主导的意见能够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使其在短时间内就能占领社交媒体阵地。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y)认为计算宣传不是简单地通过诉诸情感来结束理性辩论,也可以通过破坏性宣传来干扰理性辩论,而这种破坏性宣传需要通过另外一种理性的失败得以证明,即通过证伪来传播情绪,它更像是用“脱离他们思想的情感”来结束辩论。比如宣传人员会使用机器人对人类用户(如记者、维权人士和专家)进行大规模的攻击,并建构和他们观点相矛盾的竞争网络。换句话说,这种宣传策略是通过不同观点的数量而非质量来削减主流意见的可信度。计算宣传正是这样一步步侵蚀公众的正常认知基础,改变舆论形成和演变的正常轨迹,使网络空间的公共性进一步被削弱。
2.视频化运作和拟人化传播致使舆论失焦
社交媒体提供的海量信息导致人们对于环境的认识碎片化,公共事务想要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就需要具有较强的视觉要素,即形成聚光灯效应。这一需求与计算宣传的深度伪造趋势刚好吻合。牛津互联网研究所的计算宣传研究报告作者之一——萨曼莎·布拉德肖(Samantha Bradshaw)曾表示:“以视觉内容为目标的互联网用户将使科技巨头难以识别和禁止被操纵的内容。”不仅如此,社交机器人为了应对平台反垃圾信息的制约和算法识别,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内做某种观点的“扩音器”而非“发起者”。他们会选择另辟角度切入热点使其不易成为舆论焦点,让其行为表现得更像大众社会里孤立的个体而非机器人,从而躲避平台监管。视频化运作和拟人化传播使得计算宣传更不易被观测到,前者会分散受众的注意力,后者可加剧网络舆论情绪化、舆论话题多元化,并逐渐偏离事件的中心议题。这种情绪极化带来的认知趋同性还易招致利益泛化,增加了主流舆论演化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三)从国内到国际:溢出国界的政治风险
牛津互联网研究所发布的2020年媒体操纵调查显示,有61个国家(地区)的政党或政客使用计算宣传工具和技术作为其政治竞选活动的一部分。计算宣传从诞生之初就自带政治属性,因为对于政治人物而言,操纵舆论是实现政治目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据《纽约时报》报道,韩国国家检察官曾指控韩国国家情报局特工发布120多万条推特信息,旨在左右舆论并支持总统候选人朴槿惠。朴槿惠最终赢得了总统宝座,但负责机器人驱动的情报局长被判入狱。简言之,计算宣传能够成为左右国家选举、煽动公众抗议、开展国际攻击的有力武器。
1.“伪草根运动”淹没真实政治对话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格局的变迁造就了计算宣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党通过社交网络开展竞选,宣传自己的候选人或者特定的政治议题,制造“伪草根运动”(astroturfing):即让政治机器人通过点赞或者分享故事制造虚假的受欢迎感或支持感。这种方式最常见于社交媒体中,仅仅在推特上就大约有3000万活跃账户是机器人驱动的,它们模仿人类用户并生产丰富的内容实现社交媒体操纵。而政治机器人主要有三种类型:(1)关注者机器人——用于提高政治人物的关注者数量,被动地点赞或转发内容;(2)路障机器人——用来通过非传统通信渠道发送与活动分子或政治反对派相关的垃圾标签;(3)宣传机器人——用来模仿人类,发出支持或反对信息的机器人。这三类政治机器人都被用来人为地提高政客的知名度,排挤网络政治讨论的合法参与者,最终以压倒性规模淹没网上关于政治的真实对话。当政治机器人制造的虚假信息被大量支持时,“伪草根运动”现象便会产生——伪造成自发涌现的公共舆论,强化草根群体对某些政治行动者的刻板印象,通过“制造同意”产生“虚假民主”。不仅如此,一旦人工智能、自动语音系统、机器学习等工具被广泛运用于社交媒体操纵,计算宣传就拥有了对话性,政治机器人也会更加人性化,这时的操纵比任何时候都难以发现,真实的政治对话被淹没。
2.在线政治操纵制造网络主权风险
社交媒体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社交媒体的设计者们也一直遵循着这一自由愿景——思想自由、言论表达自由以及信息自由。但是随着操纵手段的隐蔽性和智能化,几乎所有社交平台都在与操纵、极端主义内容和不文明行为作斗争。计算宣传通过算法技术将新奇激进的主张、激动人心的新闻和断言转发给志同道合的小组成员加剧社会矛盾,“巨魔部队”凭借其军事化的统筹调度掀起“网络战”,用户的假设和偏见在得到回应和强化的同时降低了政治共识或妥协的可能性。有研究者指出,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在使用“巨魔部队”来影响其他国家的事务。2014年,俄罗斯“巨魔”在网络上发布大量亲俄和反乌克兰的帖子,进一步让乌克兰人口实现分裂,以此作为促进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一种手段。事实证明,利用计算宣传来改变围绕冲突的叙述可能有助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盟友有限的报复下获得这片领土。此外,“巨魔部队”主导下的极端意见可以强化错误信念:政治候选人、社会和政治话题、策略相关的虚假指控和阴谋论都被强化了。政治机器人与公民交流的“逐底竞赛”(race to the bottom)会降低人的尊严,改变以事实为基础的社会对话方式,使日趋主观的舆论环境得以形成。如果说政治操纵可以影响选民,针对他国的政治操纵就是对其网络主权的侵犯,进而威胁现实的国家安全。
3.全球网络空间失序改变地缘政治格局
随着逆全球化和国家间话语博弈的日益加剧,具备冲突性的计算宣传变成了政治博弈的重要手段。一些政治势力通过散布虚假信息试图改变世界传播格局,以掌控全球地缘政治的话语权。在信息地缘政治上,强国通过计算宣传破坏国际议程和外交政策,这一策略在社交媒体匿名机制的运作下更为隐蔽。当前全球的网络空间充满着民粹主义、性别主义等极端思潮,仅2020 年,法国极右翼和极左翼民粹主义者在社交媒体上就发布了大量的误导性信息,并将其变异成阴谋论和伪科学,目标直指政府和建制派。从空间维度上看,从事计算宣传的组织遍布世界,仅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就有数百个“巨魔部队”活跃在阴暗的网络中,充当网络攻击的武器。计算宣传与极端情绪的双重作用将政治焦虑不断放大,激发用户的非理性表达,导致全球网络空间失序。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地缘政治格局只会增加猜疑和分裂,致使“信息战”更为激烈。
五、计算宣传的治理路径
计算宣传与社交媒体“并驾齐驱”能够赋予舆论操纵新的机会和想象力。用于计算宣传的工具成为人类行为的脚手架,但它们的工作方式却无法预测和控制,由此引发的后果常常难以预料,有时甚至超过始作俑者的设想。对计算宣传的治理已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亟需开辟有效治理的新路径。
(一)构建跨国合作的全球治理模式
计算宣传是虚拟世界的“传染病”。网络传播速度快,需尽快干预以防止恶意活动蔓延,减少其对社会的危害。互联网是典型的全球性市场,只有跨国合作的全球治理模式才能应对计算宣传不可控的风险和危害。全球治理模式的形成首先需要加强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信息畅通,将网络空间的治理主体拓展到由企业、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等组成的跨国社会网络,通过战略互动,编织一个有效且稳固的跨国行动者合作网络。这首先要求国际协议和国际公约鼓励各国网络法律法规的协调,并寻求在应对计算宣传方面建立国家间的合作。早在三十多年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的《与计算机有关的犯罪:法律政策分析》就强调建立普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保护国际数据网络的重要性。如今,国家间的合作更显必要。其次,国际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要开展常态化的国际计算宣传治理交流活动。此外,鉴于从事计算宣传的网络部队已经从通常意义的军事单位转变为战略传播公司,这些企业作为计算宣传的主体,应按法律要求对计算宣传的风险进行专业评估,特别是关注如何保障社交媒体用户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这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一环,因为大多数公共和私营部门共享着同一个封闭代码软件。
(二)建立节点治理与长效治理的协调机制
由于全球博弈的复杂性,制定基于各国网络主权平等原则的、统一的计算宣传治理规则在短时间内尚难实现,因而有必要采取“节点治理”策略应对政治性操纵行动。节点可以是任何机构或组织,它们的界限可以是清楚的,也可以是模糊的;在组织上,它们可能是分散的或分等级的;它们可能包括个人、团体、组织或国家;它们可以是大的或小的,紧密的或松散的,包容的或排他性的;它们可能只是偶尔从事类似活动的业余人员,也可能是专业人士。当计算宣传破坏了正常的社交媒体秩序时,节点会按照国家治理的基本规划进行针对性改造,这种治理也被称为“协同治理”(coproduced governance)。它能够从不同角度处理和看待事物,以便能够在多利益相关方环境中进行制衡,并分担这项工作的集体责任。网络和节点集合构成了“实践的临时枢纽”,这种流动性极强的权力网络能够更好地应对计算宣传的动态化转向。节点治理特征越明显,在适当条件下能够对抗社交媒体操纵并以促进公正和民主的方式来改变网络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在节点治理的同时,应逐步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协调运行,以实现治理的常态化。
(三)实现线上线下联动的社交平台监管
网络技术的全面普及以及社交媒体规模的持续扩大为媒体操纵奠定了基础,而计算宣传恰好利用了感知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将用户对于社交媒体的信任转换为政治操纵。整个网络空间的计算宣传威胁日益严峻,计算宣传以其智能化、规模化、隐匿性、攻击性的特点,令社交媒体操纵的防御和应对面临更大挑战。考虑到社交媒体平台在其中扮演的中介角色,应采取激励策略,赋予平台更大责任,让平台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不给计算宣传以有乘之机。只要平台履行好把关人的角色,对数据流动和信息内容进行监测,及时鉴别、过滤并拦截非法信息,计算宣传的危害就会大大减轻。与此同时,法律法规的完善、行业组织和公众的监督等线下的监管也要跟上,实现线上线下的联动。
(四)提升破除群体沉默和压制的算法素养
在计算宣传主导下的社交媒体操纵中,“算法黑箱”“信息茧房”等问题屡见不鲜,传统媒体时期强调的媒介使用能力和素养已经不能应对“巨魔部队”对个人言论自由的压制,更不能应对计算宣传对正常的国际关系和民主进程的破坏。即便各大社交媒体已经在努力控制媒体操纵和虚假信息的传播,真相的最终仲裁始终还需要用户持续发力。因此,有必要将媒介素养替换成算法素养,即媒介使用者在面对算法时的认知、知识、想象和可能采取的策略。但现实并不容乐观,有研究表明只有37%的用户能够察觉到脸书网站的新闻推送页面背后有一套算法逻辑,因而各届亟需加大对算法素养的关注,通过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并举的方式培养人们评估在线内容的数字技能,同时提高对互联网信息流程和它的民主化潜力及结构限制的认知水平。从本质上讲,这种批判性的数字素养能够帮助公众对所见的内容及背后的生产有更好的理解,从而有助于对抗计算宣传的负面影响。
注释:
① Marková,Ivana.PersuasionandPropaganda.Diogenes,vol.55,no.1,2008.p.41.
② Woolley,Samuel C.,Philip N.Howard.PoliticalCommunication,ComputationalPropaganda,andAutonomousAgents:Introduc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0,2016.p.3.
③ Bjola,Corneliu.PropagandaintheDigitalAge.Global affairs,vol.3,no.3,2017.p.189.
④ Arnaudo D.ComputationalPropagandainBrazil:SocialBotsDuringElections.Oxford: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Project,Aguest,2017.p.1.
⑤ Bolsover,Gillian.ComputationalPropagandainChina:AnAlternativeModelofaWidespreadPractice.Oxford: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Project,April,2017.pp.1-2.
⑥ Bradshaw,Samantha,Philip N.Howard.ChallengingTruthandTrust:AGlobalInventoryofOrganizedSocialMediaManipulation.Oxford: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Project,January,2018.p.59.
⑦ Bayer,Judit,et al.DisinformationandPropaganda-ImpactontheFunctioningoftheRuleofLawintheEUanditsMemberStates.European Parliament,LIBE Committee,Policy Department for Citizens′ Rights and Constitutional Affairs,2019.p.111.
⑧ Howard,Philip N.,Bence Kollanyi.Bots,#Strongerin,and#Brexit:ComputationalPropagandaDuringtheUKEUReferendum.Available at SSRN 2798311,January,2016.p.5.
⑨ 欧亚、夏玥:《隐蔽的说服:计算式宣传及其对中国国际传播的挑战》,《对外传播》,2019年第12期,第40页。
⑩ 罗昕、张梦:《西方计算宣传的运作机制与全球治理》,《新闻记者》,2019年第10期,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