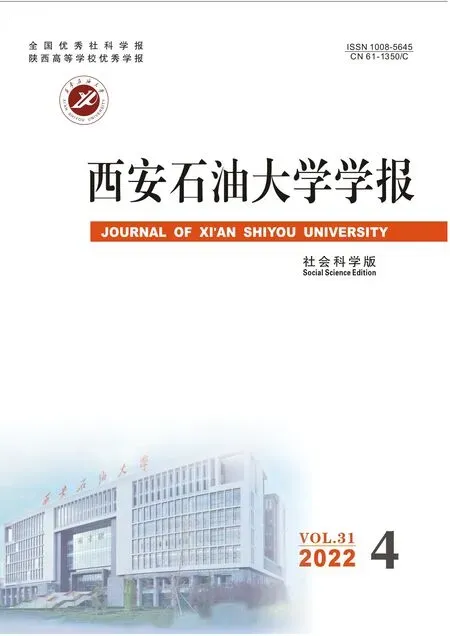从《战争日记》到《保卫延安》的文学建构
2022-11-21张曼
张 曼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0 引 言
《战争日记》记录了杜鹏程从撤离延安到跟随部队进入新疆喀什的三年(1947年3月1日—1949年12月31日)行程中的军旅见闻,《保卫延安》则是杜鹏程以这段革命实践中的真实见闻为素材而创作的一部革命战争小说,不仅汲取了《战争日记》中真实的战争数据和采访素材,也从下乡采访与亲历战争中重新审视了革命实践话语与艺术自律之间的复杂性。从战地记者到文学作家,杜鹏程的身份变化何以承载他的革命理想与文学追求?《战争日记》又何以呈现出《保卫延安》背后的文学建构过程?《保卫延安》为何要进行这种文学形式的变革与转化?目前,学界关于《保卫延安》的研究成果较多,如赵俊贤、潘旭澜等学者关注于小说的审美价值、人物形象以及相关史料的考察,但鲜有针对《战争日记》与《保卫延安》之间的文学建构关系的研究,仅有赵俊贤在阅读《保卫延安》创作手稿后进行了具体史料的钩沉,何浩分析了《战争日记》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间的关系以及《战争日记》的文学性,《战争日记》与《保卫延安》之间的文本间性仍存在可挖掘之处。因此,本文拟将《战争日记》与《保卫延安》置于互文性的阐释语境下,通过对作家创作主体心理和文本审美形式的价值考察,探讨长篇小说文体形式承载的表达功能及原因所在,意在重新审视十七年时期作家的个人记忆与主流历史话语表述之间的复杂关系。
1 从《战争日记》到《保卫延安》的生成维度
1.1 现实之维:对真实生活状况的反思
杜鹏程出生于农民家庭,幼年上过私塾和基督教学校,1938年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童年的苦难生活经历促使他在学习期间就主动从事抗日救国宣传,义不容辞地投身革命事业。1947年,他以随军记者的身份跟随西北野战军转战西北战场,经历了粉碎胡宗南进攻延安和解放西北的整个战斗过程。他在日记中多次强调,“我想尽力把战争中见过的人和事,内部的也好,敌人的也好,记录下来,不能放过生活所施与我的。”[1]28从他的生活行军记录来看,由于在随军途中历经多个省、市、县、镇、村,丰富的下乡经历让他对底层农民的生活和习性有了深入了解,也对毛泽东系列讲话中有关农民阶层的分析产生现实性的反思,并意识到战士和老百姓的现实生活状况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冲突。杜鹏程发现,在农村虽然有像白老汉全家那样愿意为革命和战争事业无私贡献的农民,他们相信战士,愿意把自己的粮食拿出来给战士,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带路,但大多数底层人民因为个体经济所造成的散漫和封建残余思想还依旧存在,有的百姓不愿意给战士提供食宿,在实际生活中缺乏阶级意识,对平时施以小恩小惠的地主容易产生同情心。同时,与战士们的相处让杜鹏程对战争有了深入的反思。他意识到,虽然大部分战士在《讲话》精神的指导和学习教育之下,有着为保卫圣地延安出生入死的决心和勇敢,但是,对陕甘宁边区的干部腐化问题他也时有耳闻,也亲眼看到军队中仍存在着组织纪律混乱问题以及贪生怕死逃跑的战士。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十年的和平生活已经让解放区的百姓和战士们失去了对战争生活的警惕性。
农村的真实状况让杜鹏程在下乡走访的过程中意识到《讲话》中所要求的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复杂性,但他在《战争日记》中对革命现实经历的个人记忆与表述显然只是着眼于个体生命在战争中的悲惨命运,还没有涉及到公共记忆与历史表述的规范化问题。因此,面对这样复杂的现实状况,《保卫延安》的创作显得尤为必要,因为他考虑的是如何将即将走入新中国的人民群众与“人民的文学”创作方向相结合的问题。
1.2 阅读之维:《战争日记》呈现的精神资源
一个作家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成长史,也是其获得间接经验的重要来源。杜鹏程在1982年曾写道:“像我这一辈中从事文学创作者,全是在《讲话》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执笔为文的。”[2]9从杜鹏程1947年至1949年期间的阅读史出发,可以发现其阅读资源大部分来源于《讲话》精神。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讲话》《整风文件》以及各种战时油印小报,这是作为战士必须接受学习的思想建设工作,也是作为知识分子进行文艺创作的指导方针。杜鹏程在1983年写道:“战争生活给予我什么,你由作品中可以看到。——但这小小收获的根源,还得到学习《讲话》的精神中去找。”[2]515《保卫延安》的主人公周大勇受阶级觉悟的启蒙从原始的农民身份中走出来,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并且以阶级性话语启发和教育士兵,成为军队士兵学习革命文化的引导者。以《讲话》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性、人民性、意志性、斗争性和集体性精神建构成周大勇、李诚等战士身上的英雄文化人格和集体主义文化精神。可以说,《讲话》的文艺创作方向塑造了杜鹏程革命实践与创作中的阶级文化意识,为《保卫延安》所确立的英雄理想信念提供了精神成长的内在动力。
二是阅读《讲话》中受到毛泽东称赞的文学作品。杜鹏程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接触到屠格涅夫、法捷耶夫、格拉特科夫、爱伦堡、克劳什维兹、西蒙诺夫等外国作家的作品,学习苏联和西方作家在通讯稿、小说中如何描写战争和战争中的人民。倘若将《讲话》与杜鹏程个人的阅读史相对照来看,其读过的大部分小说都是毛泽东在1942年《讲话》中给予高度评价的作品。例如,法捷耶夫的《毁灭》中展示了在革命烈火中锻炼成长的苏维埃人民英雄形象,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塑造了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英勇奋斗的人物形象,考涅楚克的《前线》被当作对干部进行教育的重要材料,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被称为人民解放军最喜爱的读物之一。对苏联文学作品的阅读让杜鹏程不仅学习到《讲话》中极力推崇的优秀战争文学作品,也感受到优秀的苏联文学革命者所承载的精神特质。因此,苏联文学的精神资源为杜鹏程积极参与中国革命建设提供了持续不断的革命斗志。
三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左翼文学传统以及解放区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接受。杜鹏程从12岁做学徒之时就接触到古典文学名著与鲁迅的小说,到14岁的时候,他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受进步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阅读左联作家的优秀作品,如巴金、蒋光慈以及未曾读懂的鲁迅。他在《战争日记》中提及,每次阅读鲁迅、洪灵菲、蒋光慈等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解放区短篇小说时,都会对国内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有深入的理解和反思。他在新文学作品塑造的底层民众的悲惨经历中看到了与解放区现实生活状况相似的贫苦大众的身影,这种精神共鸣让他在行军途中艰苦的环境下沉浸于新文学阅读资源中,新文学为他的学习创作提供了革命烈火般的精神斗志,也让他意识到文学对于救亡和启蒙大业的重要性。
经过长期的阅读滋养与写作训练,杜鹏程在行军途中创作了很多与战争有关的话剧、短篇小说,累计达到数百篇。他将《战争日记》中的个人记忆仅仅看做“私人的写作”和未来创作的文学素材,并开始思考如何将革命实践的个人记忆与《讲话》所确立的历史叙述方向相连接。他从1949年12月12日开始草拟将《战争日记》改编为长篇报告文学的提纲,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一百万字的报告文学初稿。但这篇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长篇报告文学并没有达到杜鹏程理想的文学效果,仍旧存在着文体的局限、人物形象塑造不够成熟以及流水账式的叙述拖沓等问题。在他看来,材料式的堆砌并不能够彰显这场战争中的人民意志,关于战士英勇冲锋的伟大事迹也并非日记或百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所能够容纳,究竟怎样的艺术形式才能够写出这段可歌可泣的人民英雄之歌,这是杜鹏程用了4年的时间反复思考的问题。
1.3 主体之维:革命与激情的内在感召
将日记修改为真实性叙述的报告文学后,杜鹏程并没有大功告成后的如释重负,而是意料之外的失落和难过。在他看来,战士们的丰功伟绩并没有得到充分呈现,其内心革命与激情的交织也并没有在主题基调中体现出来,这是作为战士与文人的杜鹏程内心深处的遗憾。因此,面对这段可贵的革命经历,他开始思考究竟是修改成斯诺《西行漫记》那样的长篇报告文学,抑或是以长篇小说的形式高唱新时代的伟大英雄赞歌。他在叙述方式的选择上进行了反复的修改与尝试,革命与激情的双重感召让他毅然选择了困难度更高的长篇小说。
一方面,童年生活与随军经历造就了杜鹏程为苦难民众与热血战士代言的诗意与激情。他曾在后记中描述了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后在严寒和风雪中行走数日回到故乡的内心历程,童年的苦难生活与母亲的悲惨经历是支撑着杜鹏程革命精神的内在动力。而杜鹏程不但是本质上的革命家,也是“本质上的诗人”[3]14,正如后来晓雷对他的评价:“老杜绝不是文人意义上的作家,他是战士意义上的作家,是革命家。”[3]652杜鹏程在《战争日记》中提到他对文学的热爱影响了他的爱情、事业与革命道路。他在1947年5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因为我觉得军人在文学上表现太贫乏,我要有意识的收集素材。”[1]52由此可见,“革命”对于杜鹏程而言,是他通往文学道路上的重要动力。
另一方面,长篇小说比纪实性的报告文学或日记更能融入诗意的激情。魏钢焰认为,杜鹏程作品的抒情体现在“作家主观评价的感情色彩很浓”[4]55-62。杜鹏程在《保卫延安》中以抒情的笔触描写了战士们艰苦的作战环境,冰冷严酷的客观环境与战士们豪情壮志的杀敌士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杜鹏程抒发革命情感号召的独特方式。《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等英雄人物对战争的视死如归如同一个具有高度宗教信仰情怀的圣徒,百姓们也将毛主席看作引导革命成功的精神信仰和大救星。对他们而言,这场保卫延安圣地的战争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性任务,而是一个具有神圣感的共同使命。
因此,集战士与知识分子双重身份于一身的杜鹏程,既能够在战士的精神中看到人民奋起反抗的集体性号召,也能够在一同奔赴延安圣地的知识分子身上看到震撼人心的抒情感召。源源不断的革命精神动力与生死相许的决心魄力将杜鹏程与《讲话》中豪情万丈的革命精神感召紧密联系,让其与胡风、冯雪峰等具有诗人与革命战士双重身份的左翼知识分子精神相承接,这也奠定了《保卫延安》在当代文学史与历史合法性建构中的史诗性品格。
2 《保卫延安》的文本形式与文学建构
2.1 长篇小说的意识形态功能
革命与诗意的内在感召是理解《保卫延安》“史诗性追求”的因素之一,但如果仅仅有激情和诗意,《保卫延安》也不会作为“红色经典”而长盛不衰。宏大的“号召之力”与“感召之情”究竟该如何叙述?初次完成后的报告文学以纪实的方式将真实生活与艺术生活融为一体,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缺乏明确性,叙述方式也是“按时间顺序把战争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5]494报告文学的叙述总体显得较为拖沓、冗长,原因既在于写作技巧之稚拙,更在于报告文学的文体功能已经不符合建国后的意识形态需求。
正如海登·怀特所言,“叙事不只是历史再现的一种可用或不可用的话语形式,他必然还包含着意识形态。叙事不仅传达意义,也创造意义。”[6]28回溯40年代的文学环境,战时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促成了“报告文学”成为最为热门的写作体裁,报告文学本身的意识形态性是对战争的及时反映,作品的新闻性、纪实性更为受到读者的欢迎。作为身在前线的进步作家,杜鹏程对这种写作形式较为熟悉,也深知报告文学如同革命者的“武器”一般锋芒。但值得注意的是,《保卫延安》是杜鹏程在1950年完成报告文学的初稿后开始反复修改的,共和国诞生之初的和平时代需要的文学作品已经由“革命性”转为“建设性”的时代潮流,在文学上也需要长篇小说的文体形式完成民族国家话语的集体性想象,报告文学的文体形式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此,杜鹏程下定决心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创作。他曾说:“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5]495长篇小说的形式选择也让杜鹏程与新时代的文艺要求贴合得更近,小说形式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特征更加完备。因为建国后的文学使命不在于描述战争本身,而在于通过战争叙事建构新国家中的人民主体意识。长篇小说的形式恰恰承载着共和国初期的国家和民族想象,也让叙事形式本身产生了内容和意义。
正如伊格尔顿所言:“艺术中的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的内容。”[7]28杜鹏程心目中的理想作品是具有史诗性的品格和纯熟的艺术造诣,这对作家处理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也对文体形式有所限制。因此,在《保卫延安》的文学建构过程中,杜鹏程必须首先处理小说的形式问题。他重新反思文学创作的叙述立场,将战争的亲历者立场转变为历史的见证者,将个人记忆的私人话语转变为历史建构的公共话语。《保卫延安》对报告文学文体形式的反叛着眼于文体形式与社会现实状况之间的关系调整,这是小说对革命社会现实及其意识形态话语的剥离。正如卢卡奇所说:“小说是成熟男性的艺术形式。”[8]63长篇小说在塑造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中的文体功能满足了杜鹏程对文学理想的追求。而卢卡奇认为小说处理的是心灵与形式的问题,也就是现实生命与真正生命的关系问题。杜鹏程也以战争中的英勇战士为原型塑造了周大勇、王老虎、李诚等典型英雄人物,以战士们从撤退延安到收复延安的作战过程为主要故事情节,讴歌了战士们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2.2 冯雪峰的“慧眼”与贡献
1954年6月,《保卫延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4年的反复修改与订正绝不仅仅只是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学形式叙述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个人记忆与新时代的文艺方向之间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处理个人的革命实践与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之间的关系问题。
从出版过程来看,《保卫延安》的生成离不开主编冯雪峰的“慧眼”。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新中国第一家专业的国家级文艺出版社,出版符合特定社会政治语境的重量级作品是其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杜鹏程将报告文学改为长篇小说的过程中,总政文化部将他从新疆调到北京专门修稿,并且将《保卫延安》在出版之时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之一”。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的楼适夷在回忆中提到在《保卫延安》封面上“被动”印上“丛书名字”的“曲折”插话,并且谈到冯雪峰对于《保卫延安》出版的重要性:“后来,如对杜鹏程《保卫延安》的投稿,(冯雪峰)则亲自审读以后,就与作者反复长谈,两个人并坐在写字台边,几乎是手把手地帮助作者作了很大的修改,70万字的稿子变成40多万字,才成为后来出版的样子。”[9]441牛汉也曾回忆:“杜鹏程把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寄给冯雪峰。他看了,很欣赏,交给我发稿,让我当责编,我写了出版说明。”[10]96杜鹏程在《回忆雪峰同志》[2]322-337中也曾提到,在《保卫延安》改完之后他首先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主编冯雪峰,与冯雪峰几次交流之后获得了极力的肯定和赞赏,也得到了大量宝贵的修改意见。除了在《保卫延安》的出版和修改问题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外,冯雪峰还在《保卫延安》出版一个月后,在《文艺报》发表了《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1)《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后收入《冯雪峰论文集·下》,改名为《论〈保卫延安〉》。,重在强调《保卫延安》的史诗性主题和作家战斗的创作精神,为《保卫延安》的阅读和接受提供了具有引导性的批评指引。因此,《保卫延安》经典性地位的确立离不开文坛领军人物冯雪峰的“慧眼”和贡献。
2.3 主流新文艺方向的助力
从《战争日记》到《保卫延安》的记忆重构,除了杜鹏程高度敏锐的思想觉悟和文坛领军人物冯雪峰的“贡献”之外,也离不开《讲话》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助力。杜鹏程在1947年4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是英雄们用他们的行为和血汗书写的时代伟大的史诗。我恨不得以东海之波涛,尽书这时代的全貌!”[1]32因此,杜鹏程自觉的创作意图与主流的文艺创作方向是相符合的。周扬在1949年7月曾说:“革命战争快要结束,反映人民解放战争,甚至反映抗日战争,是否已成为过去,不再需要了呢?不,时代的步子走得太快了,它已远远走在我们前头了,我们必须追上去……它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11]529由此可见,《讲话》中的文艺思想在建国后被充分地实践,特别是在文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宣传工具之后更为突出。周扬在1950—1953年间的讲话中也多次重申要遵循《讲话》的创作原则,强调作家应该如何创作,以什么样的叙述立场写什么样的革命故事。他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指出:“作家在观察和表现生活的时候必须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为指南。他对社会生活的任何现象都必须从政策的观点来加以估量。”[12]243他在会上不断重申《讲话》中“必须首先写光明,写正面人物”,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12]250的要求。至于作家如何写英雄人物的缺点问题,周扬也有所提及:“许多英雄的不重要的缺点在作品中是完全可以忽略或应当忽略的。”[12]252因此,《保卫延安》正是以二元对立的革命叙事方式建构了现代国家政权的民族精神与想象,重构了向往延安革命圣地的一代人对自身历史的集体记忆,作家与文化领导者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动下共同完成了新的文艺使命。
因此,当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作品被先验性的赋予民族国家想象的人格化表征时,我们可以发现,《战争日记》中的革命现实状况在反复的修改中逐渐得以净化与规训。实际上,解放军与民众之间的真实关系并非完全如《保卫延安》中所呈现出来的军民鱼水情,军队内部也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冲突。杜鹏程在1947年12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刚回农会,听说地主梁高升儿媳被人强奸,营长正在调查。”[1]172在5天后的日记中又写道:“今天开会将一个副教导员孙某捆起来,他畏缩逃跑。”[1]173赵俊贤在阅读《保卫延安》手稿时发现,杜鹏程在《保卫延安》的改动过程中删去了“赵德仁自伤”“某团长打骂战士”[13]29-40等表现我军内部矛盾或阴暗面的生活素材,压缩掉了军内富有生活情趣的艺术描写。与之相对的是,他将国民党的战士在这场战争中放置在反人道主义的立场,小说中描写的军队腐败问题、肆意强抢妇女和粮食等丧尽天良之事都是出自国民党士兵之手,对于我军的战士与百姓则进行了无声的净化。不过,他并非在创作之初就有净化战争和历史的创作意图,而是不自觉地受到了艺术自律的影响。张均曾考释《保卫延安》中对于战争本事的改写[14]26-33,例如将几场惨仗忽略掉,只记录了胜利的战争。人性的另一面和士兵对战争的抵触性在《保卫延安》中都被有意忽略,仅记录了战士对战争的忠诚度以及军人与百姓之间关系的融洽。不可否认,这样的战争场面并非战争生活的全部历史,而是杜鹏程根据新的文艺创作方向对个人的革命记忆进行了技巧性的重构和筛选。作为新中国初期的建国历史小说,《保卫延安》有责任和使命去通过战争和革命的宏大叙事完成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这样的叙述立场符合一个现代国家在兴起阶段的共同体想象,也符合新中国对于历史记忆重构的迫切需求。
因此,《保卫延安》的“快写慢改”恰当地处理了革命战争的个人记忆与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文学形式表现了我党领导下的解放军战士的英雄主义精神,成为激励人民参与新政权建设的重要媒介。
3 结 语
《保卫延安》《红岩》等“国家文学”文本的生产普遍面临着作品何以“炼成”的问题。《保卫延安》讲述的是现代民族国家何以建立的过程,回答的是延安圣地所确立的政治正确性如何被保卫的问题。杜鹏程处于和平年代的建设时期重新叙述这段战争和革命的历史,必须要思考的是如何站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政治立场上去反思这段革命历史。《保卫延安》的反思正是对失去生命的战士们致以人性的悲悯与生命的最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