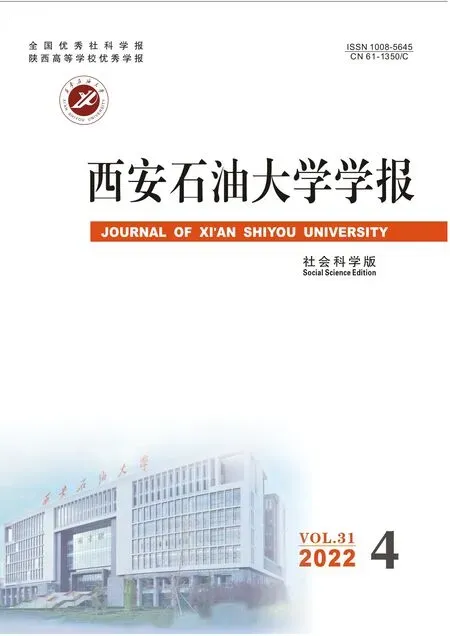从“以道观之”到“以事观之”
——论具体形上学展开的理论进路
2022-11-21徐煊
徐 煊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0 引 言
在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取向上,杨国荣将以往的哲学视域概括为三个阶段:“以物观之”更多指向本然世界和自在之物,肯定了世界本源于物,确认了世界的对象性,但是仅停留在对世界的理解和说明层面,没有涉及对世界的变革;“以心观之”将对世界的认识从实体的物转向为人自身的观念,其中涉及的对世界的变革流于抽象思辨,趋向于消解客观世界的实在性与真实性;“以言观之”以语言的描述和分析作为把握世界的方式,容易导致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将把握存在的方式曲解为存在本身。可以看到,上述三种视域都没有将说明世界和变革世界有机融合起来,而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是世界与人相互作用、共同整合而成。在人对世界的理解上,说明和变革表现为统一和动态的过程。在这种前提下,具体形上学开显出的“以道观之”和“以事观之”的理论视域,体现了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进一步理解与思考。
1 视域的推进与深化:从整体性到过程性
具体形上学作为“未济”形态的开放体系,从“以道观之”到“以事观之”的理论进路,首先可以理解为从整体性视域到过程性视域的深化。这种进路不是某种转变,而是一种推进,也可以说是具体形上学体系逻辑的自然顺延。“以道观之”原出自《庄子·秋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意思是从道的角度看,万物都是道的产物,没有贵贱之分。在《秋水》篇的具体语境中,“以道观之”主要与贵贱的判定相涉,相对而言只是一种纯粹的视野,没有被知识化。到冯契那里,“以道观之”被延伸定义为一种人们在认识事物时的立场或角度,注重的是道本身以及从道的观点看万物而得出的概念和命题,从而引出其形成的认识结果,即智慧[1]203。郭明俊在理解冯契视域下的“以道观之”时认为:“‘以道观之’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包含着平等的观照天地万物、尊重每一个存在者的个性的平等意识,它并不否定和抹煞事物之间的差异和区别,而是要人们在承认和尊重这些差异和区别的基础上,超越这些差异和区别,以一种更宏大的视野、博大的胸怀来看待天下万物。”[2]31承继冯契之学,杨国荣将具体形上学接续的“以道观之”在广义的层面定义为一种认知视域,内含辩证思维的趋向,这里的“以道观之”既保留了中国哲学中基于“道”注重的整体性,又关注到对象本身的关联性与过程性,从而站在道的立场考察世界之在与人之在,既回归了哲学的本然形态,又拒斥了抽象形上学和后形而上学趋向的分离和分化,进而关注到人内在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统一性,这也是存在的具体性与真实性的体现。
禽霍乱是一种多杀性巴氏杆菌引起的急性侵害多种禽类的接触性传染病,多发生于16周龄以上的鸡。温暖潮湿的环境和季节多发,通常发生于春末夏初,传播缓慢且有间隔,往往鸡群中有发病死亡后间隔数日再有病死鸡出现,或每日出现少数鸡死亡的情况。鸡群中一旦发生本病,往往不易在短期内控制疫情,尤其在茂密的树林,最容易发生。
《道论》原书名为《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易名原因在于杨国荣对中国哲学“道”这一范畴的重新思考。《道论》的二版后记中提到,“中国哲学很早已开始了对世界之在与人自身存在的形上之思,这种沉思往往凝结于‘道’这一范畴,并以‘道’为本而展开其多方面的内容。”[3]338这里明确了“道”这一范畴首先开显出的是以考察世界之在与人之在为指向的形上追问。“道”在中国哲学中可以理解为存在的一般原理,但其同时也包含着价值理想,后者既涉及天道与人道的沟通,也涉及对“性与天道”问题的探索,无论是“天道与人道”,还是“性与天道”,都表明了中国哲学对存在的追问展开于人与世界的相关性之中,以及二者最终超越分离而呈现统一的形态。陈赟在《“具体形上学”对传统儒家形上学的推进》中也肯定了杨国荣对于天道的重新理解:“天道并非超越实体,也并不能理解为脱离人的生存的存在本身,而必须理解为以道观之的一种视域。”[4]3
雅典是古希腊商贸最发达的城邦之一,完善的民主制度,磁铁一般吸引着各处人才,城邦经济也赋予他们思考的闲暇。相貌丑陋、衣冠不整的苏格拉底点化了柏拉图。柏拉图在市郊得到了一块休憩园林,后来就成了闻名于世的“雅典学院”。在那里学生无需交费,女性也可以驻足聆听。现代人把柏拉图的意念分为逻辑、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学等,但他的学说是杂糅在优美沉思的“对话录”中。
道,指向的是“通”。“通”不仅指各领域之间的汇通、由技进于道,而更强调一种扬弃割裂与分化的视野,以整体性与统一性的视域考察世界与人的存在及其关系。在这种视野下:第一,现实世界呈现为一个整体,既然是一个整体,就不能悬置人的存在而空谈抽象的自在之物。第二,有关形而上学的追问,都是由人提出的,因此就会不可避免地代入人的视域、与人的存在发生关联,相应地,在人对世界的存在提出各种追问的过程中,人自身也不可避免地与世界发生联系。第三,在《道论》中,“形而上学”指向的是有关“人与世界的存在及关系”问题,广义的世界之在,首先包含人的存在,如果要研究世界之在,就不能忽视人的存在于其中的作用,二者相互显现共同形成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
在“以道观之”的视域中,形上与形下的统一首先可以从中国哲学“道”与“器”的关系来看。如果引用中国哲学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辞上》),杨国荣认为西方传统形上学是离器言道,后形而上学是离道言器。[11]168前者导致了对世界抽象、静止、孤立的理解,后者则缺少对存在的整体性的把握,引起形下之域的碎片化与繁琐化。这里的“器”包含特定的事物或现象,指向具体性的存在,“‘道’既是存在的原理,又体现了存在的整体性、全面性;‘器’相对于道而言,则主要是指一个一个特定的对象。”[11]168无论是离器言道还是离道言器,造成的结果都是道器两离,即西方抽象形上学所呈现的本体与现象世界的两分或超验与经验世界的割裂,除此之外,还意味着存在本身与把握存在的方式都趋向于分化与分离。而具体形上学关注的视域,则指向道器不离、道器合一,“由‘技’进于‘道’、从单向度或分离的视域转换为‘以道观之’”,“以‘道’的隐退、‘技’的突显为背景,确认存在的具体性意味着走向视界的融合、回归统一的世界。”[11]168
其次,“以事观之”指向的过程性视域还可以在《杨国荣:从“道”到“事”——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这篇访谈中找到根据:将《存在之维》易名为《道论》得于对“道”这一中国哲学思想核心的重视,而杨国荣点出的“修道之谓教”则体现了修道、教化或者工夫的问题与“道”密切相关,工夫本身以成己与成物为指向,其展开过程就是具体的做事、处事过程。[5]18也就是说,按照“道”的原则修养自身、教化他物,是以成己与成物为指向,而修养教化的过程则可视为工夫,这一过程也就是“事”的具体展开。
在“以道观之”到“以事观之”的理论进路中,“具体性”既可以分别呈现不同的趋向,又最终以融合的形式指向人与现实世界的统一。由上述可以看到,具体形上学内含的已经不再是西方传统形上学的狭隘之义,而是既融合了中国哲学重视的人的存在,也关注到当代形而上学的转向问题,其视域最终指向在形上之域与形下之域的统一中理解人与现实世界。而扬弃以往只关注形上之域的思辨或抽象考察,回归到我们这个人与事物共同存在的现实世界则尤为重要。从形上与形下的关系看,以道观之是从形而上的角度切入,论述形而上的原理不离形而下之器,以事观之则是从形而下的角度切入,论述形而下之域的人之所作同时呈现形而上的面向。可见,作为中国哲学概念的“道”与“事”,都兼涉形上与形下。无论是“以道观之”还是“以事观之”,最终指向的都是形上与形下的统一。而形上与形下的统一所体现的,就是具体形上学的视域。
首先,“以事观之”指向的过程性视域体现在,人对现实世界生成过程的参与,是通过做事来展开的。在人不断做事的过程中,现实世界得以生成,由此,现实世界以“事”为本源。根据《人与世界:以“事”观之》的论述,广义的“事”突出的是人之所作,也就是人的现实活动及其行为结果。一方面,“事”表现为人的存在方式,从观念活动到现实践行,人自身都因事而在,与事同在;另一方面,“事”具体展现为人对世界的变革,人通过“事”参与世界变革的过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变革了本然自在的对象,展示了对象的实在性,同时也确证了人自身的存在,在做事的过程中与现实世界发生关联。相应地,在具体的做事过程中,事的具体性规定了人的具体性,人自身也在这种整合与统一的过程中不断走向真实和具体化,二者互涵互涉、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现实世界。
关于上述“道”与“事”的关系,《人与世界:以“事”观之》中也提到了“道本身则唯有通过‘事’才能把握”[6]11。这句话的根据来源于中国哲学的“日用即道”与“即事是道”。“即事是道”原出自明代哲学家王艮承继的王阳明思想,而日用即道则从中国先秦哲学孔孟荀那里就可以找到根据。杨国荣在《以事行道——基于泰州学派的考察》这篇论文中基于“日用即道”与“即事是道”延伸论述的“以事行道”[7]7-8,同样彰显了“事”的过程性视角。这里的事可以视为日用常行的具体化,而以事行道的旨趣则在于在平民化的生活中和人的日常行为中实现社会道德理想。反过来说,道遍润于万物,遍润于生活各处的日用常行,后者就属于广义的“事”。通过事实现道,无疑体现了“以事观之”的过程性视域。
现在回头看来,大可不必,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道”,我应该顺应我的“道”,演好我的角色,不应该把自己和别人对立起来。
2 形上学的“具体性”指向:从人的存在到人的行事
在具体形上学中,“具体性”的概念尤为重要,形上学的具体性归根结底是在论证“存在的具体性”。许苏民就曾指出,杨国荣哲学体系的第一原理就是从人的现实的知行过程敞开和澄明人与世界之“在”的具体性,概而言之就是“在的具体性”[8]29。所谓存在的具体性,指向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以已经进入人的知行之域的存在为研究对象,其中也包括人存在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这些存在与人的存在发生关联,具有实际意义,这才是真实具体的存在。这既是具体形上学之“具体”所在,也是“以道观之”与“以事观之”的理论进路得以展开之基。从“以道观之”着重论述“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在具体形上学中的合理性与重要性,到“以事观之”默认“关注人的存在”是具体形上学视域中大的前提,进而着重论述人的行为活动及其结果,这一理论进路显现的是对形上学“具体性”的接续与推进,进一步深化并落实了“具体性”的概念。
关于所谓的具体性是否会使形而上学流于形而下的经验等问题,在《人与世界:以“事”观之》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下述逻辑关系:作为人之所作的事,具有广泛的涵盖性,广义的事同时包含西方哲学的“实践”与中国哲学的“行”的双重面向。[6]11-12在西方哲学中,“实践”的涵义经历了多个阶段的转换,而最终指向于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一切客观物质的社会性活动。而经验,在哲学上指人们在同客观事物直接接触的过程中通过感觉器官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的认识,概而言之,经验多指通过实践得来的知识或技能。在中国哲学中,“行”多表现为社会领域的诸种活动,而“相形之下,生活世界中的日用常行,以及日常之行的个体之维,则似乎未能进入上述‘实践’的视野”[6]11。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1986年发表了“The Death of Author”(《作者之死》)一文,该文集中探讨了作者、读者及文本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带有反主体性质的“作者之死”这一略显极端的论断。巴特要表达的是作者并非优先于文本,任何以全知全能的视角试图控制文本写作的意图,最终将妨碍作品内涵的扩散。正是由于巴特这一对于作者权威地位的尝试性颠覆行为,最终使得文本创作的作者和文本意图的作者得以区分。
前面提到,形上学的“具体性”更多指向以人的视域考察存在,包括在《哲学的视域》中,杨国荣关注到了“以道观之”视域的主体——人的存在,即“人以道观之”[9]413。“以道观之”与“以人观之”相比,虽然更注重视域本身,要求从存在本身把握存在,但是就现实的层面看,“以道观之”仍然是一种人的视域,是人以“以道观之”的方式理解和把握世界。关于这一看法,在之前学者的探讨中存在两点争议:(1)如果说具体形上学的“具体性”是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那是否过于强调人在世界之中的主体作用以致于流于主观视域;(2)涉及到现实世界的真实具体的存在,是否还属于形而上学的领域,或者说是否会流于经验领域的“形而下学”[10]。上述争议的根本基点,就在于前面提到的“人的视域”。
在人文科学当中,依然存在着一种客观性,与自然科学中的绝对客观不同,作为主体的人与客体世界共同存在,这也是一种客观事实。这种客观性无法摒除人类的存在。人与世界相互影响,从而不能忽视人的存在对客体世界的说明和变革作用,这也是一种客观性。从人的存在出发并不意味着具体形上学片面偏向主观视域,而是关注到人的存在的双重特性:其本身既是一种存在,同时也是开显世界之在的方式,二者统一于这个现实世界。但是这里也包含着一个问题,关于人以道观之:一是人作为有限的存在,以之为主体真的能达到以道观之的境界吗?二是“人以道观之”这样的表述似乎包含着两个方向,一个是人以道观之的过程,一个是人以道观之的结果。从前者的角度看,“人以道观之”这一过程的确客观地存在着,但是从后者的角度看,人以道观之观到的结果则不可避免地包含主观性,包含人自身的判断、倾向、情感等。因此,具体形上学从人的存在出发有其合理性,但是将其限于人的视域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似乎还需进一步解决。
可以看到,无论是西方哲学注重的实践,还是中国哲学注重的行,在作为对“人类作用于世界的活动”的解释这一方面,都各有侧重但没有达到相对宽泛的涵盖面。而“事”则同时兼具实践与行的上述特性。由此,事的具体性体现在:“‘事’与人的不同需要以及多样的存在情境、特定的时空条件等相联系,包含具体的品格。”“实践和行在实质上乃是以做不同意义上的‘事’为指向,离开了多样之‘事’,其形态将呈现空泛性和抽象性,唯有关联不同之‘事’,这种抽象性才能被扬弃。”[6]12实践和行既指向事的不同方面,也指向多样之事的展开。经验或经验知识的确被包含于广义之“事”中,但是经验只是由作为事的具体展开的实践得来的,是事的具体性的体现之一,而不能将这种事的表现形式等同于或曲解为事本身。这种广义之事包含经验认识的关系,从另一层面也折射着形上与形下的相互兼涉与统一。由此,人之所作的实践活动本身和以实践为对象的认识过程,都涵盖于广义之事下,这样既避免了对具体形上学的论述流于形下之域,又进一步落实了对形上学“具体性”的论证。
根据杨国荣先生的观点,之前的形而上学研究没有把人的存在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作用和联系表达出来。而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在具体形上学中为什么合理,或者说人的视域何以在形而上学领域中合理存在,这就需要从“以道观之”的整体性出发,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现实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悬置人的存在及其与世界之在的相互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整体性与具体性并不是冲突的。“以道观之”注重的整体性与统一性更多是以多样性的整合拒斥抽象的同一,是一种形上与形下的沟通与融合,整体性视域意味着不能忽视存在的时间性与过程性,其所具有的现实性也构成了具体性的含义之一。在《道论》中,关于“存在的具体性”问题,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按其现实形态,存在的具体性既表现为它在过程中的历时性展开,也以过程中的自我统一为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统一性与过程性的融合,构成了存在真实、具体的形态。”[3]60
(2)soft5.5测试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口服鳕鱼皮胶原低聚肽后,受试组皮肤水分和弹力值上升,皮脂含量下降,与口服前对比差异显著(P<0.05),对照组统计差异不显著(P>0.05)。
相较于传统形上学所探寻的抽象的本然世界,事的发生并不存在于本然世界之中,本然世界也不涉及对事的考察。相对于自在之物,“以事观之”视域中的物,首先指向经过人作用的物,即前述的已经进入人的知行过程的存在对象,物在这里被赋予了现实性,这才是真实、具体的存在。从而,以“事”的角度考察才能呈现现实世界的实质意义。“事”的哲学概念不是推崇某种终极性,而是以之作为视域达到对人与世界更具体的理解。有关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问题,终究离不开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以“事”观之,才能突显人的存在及其行为活动对世界的影响与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这也是具体形上学的题中之义。在融合“以道观之”从人的存在出发注重世界之在与人之在的沟通与统一的基础上,“以事观之”进一步指向经过人参与变革而生成的现实世界,以此更具体地理解人及其存在处境。
3 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从形上到形下再回归到形上
通过调查问卷分析形成各类图书阅读不均的原因,跟读者的自身阅历、喜好、知识积累以及个人需求有关。通过分析宁夏图书馆读者的阅读喜好,有助于确定各类读者的图书采购量和控制副本量,使有限的购书经费得以充分发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也有助于平衡各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对图书馆的满意度。
从对世界的总体把握出发,人之在世,以其现实活动及行为结果为指向的“事”,具体地展开于人的整个存在过程。“以事观之”是《人与世界:以“事”观之》提出的具体形上学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新视域。相较于以道观之从整体性视角去考察存在,以事观之则更注重过程性的视角。换言之,如果说“以道观之”关注的是世界之在与人自身之在的统一,那么“以事观之”则关注的是实现这种统一的过程。
在《道论》中,杨国荣多次提到“存在的统一性首先在于只有这一个世界”,“只有这一个世界”是指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本身并没有所谓的形上与形下的分化,这种分化是因为人受到二分思维的影响而对这个世界所作的区分,而完全摒除形下之域追寻纯粹的形上之域则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纯粹的形上之域真的存在吗?即使存在,人通过人所作的区分而追寻到的本然世界,还真的是纯粹的本然世界吗?随着时代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形而上学再去试图追寻世界的本然形态或终极形态还现实吗?或者说,还具有意义吗?相对而言,关注现实性才恰是我们当下的时代所重视的。
西方的metaphysics受传统思维逻辑的影响,注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而以中国哲学的“形而上”翻译西方的metaphysics的恰当与不恰当之处,是形而上学领域历久弥新的问题,在此不作赘述。需要注意的是,具体形上学虽然回归了西方哲学形上学关于存在问题的关注,但是这里的“形上学”仍然不能忽视中国哲学视域中的“形而上”的原义(“形而上者谓之道”)。西方的“metaphysics表示物理学之后,它在逻辑上似乎蕴含着与经验世界形成某种界限的可能”[3]34,而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则不离于“形”,形上与形下的界定归根到底是以“形”作上下区分,离开了“形”,则流于空谈。“这里的‘形’,可以理解为实在的世界,‘形而上’非离开此实在的世界而另为一物,相反,有此实在的世界,才有上、下之分;形上与形下、道与器等等,无非是同一实在的不同表现形式,二者都内在于这一个实在的世界。”[3]46形上之域与形下之域的统一便可以理解为只有一个现实世界,事物的存在与人的存在皆内在于其中,道与器也不再是两种相分孤立的存在,而是这一个世界的不同呈现方式,二者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得以沟通和相融。换言之,若想探讨形而上学领域的问题,则无法完全隔绝形下之域,彼此互涵互涉,相即不离。这既是具体形上学的前提,也是具体形上学的指向。
前面提到,道作为中国哲学的独特范畴,既指向存在的一般原理,同时也包含着价值理想,因此“形而上者谓之道”表明形上之域已经包含价值理想所指向的具体性的存在,包括人的知行过程。而从前述道与事的关系可见,“道体现于其中的日用常行,本身即属广义之事”[6]11,“日用即道”“即事是道”既体现了作为存在原理的道无法疏离于形下层面人的日常活动,也体现了具体的做事过程内含着道指向的普遍存在原理的范畴。在“以事观之”的视域中,形上之域与形下之域、世界之在与人之在密切相关,事便可以视作二者的联结。
“以事观之”以人的活动及其结果为指向,在这一层面,首先表现出形而下的特质。“事”既可以指向人作用于物的现实活动(做事),也可以指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处事),另一意义上“事”还可以指向人成就自我的过程。首先以人与物的互动为形式的“事”具体展现为人对世界的变革,这可以看作是制天命而用之、赞天地之化育的具体化。[6]75参与世界变革的前提是所作之事基于对象的内在法则与人自身的合理需要,合乎实然、必然与当然,具有适宜性与正当性,这是事展开的合理方式。相应地,物也不会自发地满足人,唯有通过人作用于物的做事过程,物才能成为合乎人需要的对象。事作为人的活动,不仅基于人的现实需要,还以实现人的价值目的为指向。人与物互动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以后者为形式的事的展开,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使人的社会关系获得现实、多样的品格。在人与物的互动以及人与人的交往中,物与他人主要表现为对象性的存在。而以人自身的成就为指向,事同时关乎人与自我的关系,这里的自我既表现为主体,也表现为对象。如上关系体现了事从不同方面成就人并赋予人以多重存在规定。
伯虎终于说到正题。只见他们三人面前的空中,三维画面像一朵花瓣似地打开了,应用里出现了一个导航页。而就是这个导航页当中的“降维安全监测”六个字,使得安文浩一怔。
在上述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互动关系中,都可以体现出“无论是生活世界之中,还是生活世界之外,人所做之‘事’既展开于具体的时空之中,从而渗入形而下的品格,又具有建构现实世界以及成就人自身的形而上意义”[6]自序3。“以事观之”指向的是展开于具体时空中的现实世界,这个生成于“事”的现实世界已经呈现出本然世界经过人作用之后的形态。人通过做事使得本然世界转化为现实世界所以可能。在此意义上,形上与形下获得了统一。
有观点认为,具体形上学的视域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视域,是在纯粹的形而上学中界定何为具体,因而导致“具体”和“形而上学”概念范畴的冲突和矛盾出现。但是从“以道观之”和“以事观之”两种视域的最终指向来看,具体的形上学,已经不再是从纯粹的形而上学视域中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也不是单纯局限于讨论形上之域,而是已经扩大了内涵。无论是以道观之还是以事观之,最终关涉的都是形上与形下的统一,这也是这一理论进路从推进到融合的体现。《道论》作为具体形上学问世初期之作,是奠基也是总纲,需要向学界清晰阐明其理论观点及根据,而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核心观点及根据铺陈完成之后,便进一步深化“具体性”的概念所指,也就是“事的哲学”,从形而上到形而下,最终又回归到形而上,如果没有关注到具体形上学的理论进路,很有可能使得其前无根据、后无支撑,枝叶零散,从而受到诟病。当然,若想探讨其理论进路,自然不可以忽视具体形上学体系的其他著作——《伦理与存在》《成己与成物》《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这些著作前后有其在不断发展着的逻辑关系,有其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仅仅限于“道”与“事”探讨出的理论进路可能会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断裂性,而没有站在一个更加宽广、具有关联性的视角去考察具体形上学。
4 结 语
在具体形上学的开放体系中,“以道观之”作为体系开端提出的视域,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为指向,注重从对世界的总体把握考察存在与人的相互显现;“以事观之”作为体系逐步深化的视域,以人的现实活动及其结果为指向,二者关注的都是已经进入人的知行领域、与人发生关联的具体真实的存在,这种存在既具有本体论意义,又因与人自身共同存在于这一个世界而被赋予现实性的内涵,形上之域与形下之域在此获得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