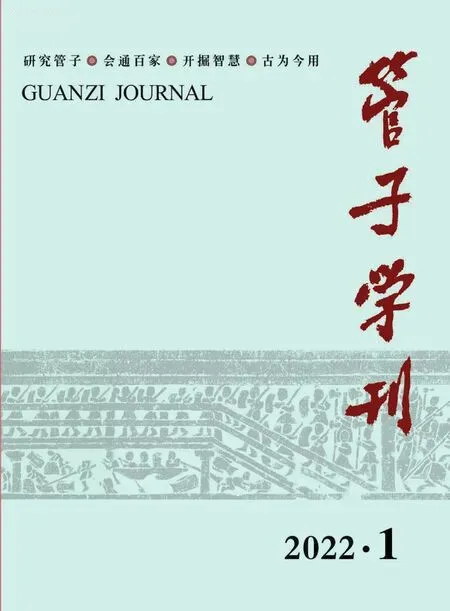差异教化观的理念、原则及指向
——基于啮缺在《庄子》中的五次出场而论
2022-11-21杨小婷
杨小婷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
《庄子》首篇《逍遥游》曾提到“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1)钟泰:《庄子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依全书来看,此“四子”实际指:许由、啮缺、王倪、被衣(蒲衣子),四子在首篇只是隐身性的出场。《天地》篇交代四子及尧的关系:“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啮缺,啮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2)钟泰:《庄子发微》,第254页。考察围绕五人而编织的故事链来看,《庄子》花费心血构思的人物是啮缺,而非熟知的许由(3)本文悬置《庄子》内、外、杂篇和作者归属争议,文中所谓庄子哲学是将《庄子》文本作为研究体系,而非历史上庄子本人的哲学。原因如下:《庄子》作为具有独特精神特征的经典文本,全书思想有其统一性,杨国荣指出,将《庄子》全书视为一个整体是更合理的一种理解路径;《庄子》各篇作者虽尚有争议,但各篇皆从庄子思想出发“具有自身主导的哲学观念和基本的学术立场,这一点又显然不应有疑问。作为先秦的重要哲学经典,《庄子》中的主导观念、基本立场内在地渗入于全书,并展示了庄子哲学之为庄子哲学的整体特征”。参见杨国荣:《庄子哲学及其内在主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1-8页。同时,外、杂篇对内篇极重视的人物形象啮缺所聚焦的差异教化观的续写,具有统一的精神指向。此外,本文首要关切在于,试将人类关注的问题及处理路径从《庄子》中导出,以重现《庄子》的当代价值,并以之作为进一步理论建设的背景。。许由共出场七次,啮缺出场五次,王倪、被衣各出场三次。许由出场虽多,但几乎都是同一故事,即许由逃尧——可见《庄子》并未在其身上耗费笔墨;而王倪、被衣的出场则皆是作为啮缺的对话者而出现的,身份皆为得道者,并无深意。而啮缺分别在《齐物论》《应帝王》《天地》《知北游》《徐无鬼》篇中一再出场,重要的是每次出场都有新的情节推进。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三次出场:《齐物论》—《应帝王》—《知北游》,呈现出一条啮缺问道、经道家式教化而得道之路,学界鲜有研究分析这一构思的深层意旨;其次,《徐无鬼》篇中,啮缺询问学生许由逃尧的理由,《天地》篇更出现了一段很“不合情理”的对话,即许由对老师啮缺的一番严肃批评。若顺着故事发展的情节链来看,应该是在许由逃尧后,尧试图请许由的老师啮缺做天子,因而询问许由“啮缺可以配天乎”,而啮缺的学生许由竟回答:啮缺若为天子,则天下就要岌岌可危了(“殆哉圾乎天下”),这一批评的用语是非常严重的。
对啮缺这一人物形象,学界已有关注,如陈赟曾指出,“《庄子》对政治生活的思考”是“以‘四问四不知’为起点”的,而“‘啮缺’这个人物在《应帝王》中”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而且,庄子这一政治思考通向的是“天地人三才贯通的帝王政治类型”(4)陈赟:《“不知之知”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贯通——对〈庄子·应帝王〉开端的理解》,《齐鲁学刊》2014年第6期,第5-15页。;张文江则分析了啮缺进入君王(尧)的视线的原因,即很有可能是因为过于擅长思辨活动,但幸运的是,得到了许由适时的掩护(5)张文江:《“四子”的隐显和出处:论〈庄子〉中一个师生组合》,《上海文化》2018年第9期,第129-135页。;郭美华则围绕许由批评其师啮缺的内容指出,这“并不一定切中啮缺本人的实情”,他最终将批评内容的深意指向“对于有德有智者治理世界的完全拒斥和彻底否定”(6)郭美华:《天地整体及其秩序之自在性与他者之差异性的让渡——〈庄子·天地〉第3-5节的哲学解读》,《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23-32页。;冯春晖则考察了“啮缺问乎王倪”一节,指出王倪三答“吾恶乎知之”,而“‘知’与‘言’相对”,庄子批判的是“人为之‘言’”对“本浑然为一”的世界的改变(7)冯春晖:《〈齐物论〉“啮缺问乎王倪”寓言发微》,《东南学术》2021年第2期,第191-198页。。以上成果对关涉啮缺的部分内容,给出了独到的理解。但是,围绕以上疑团对啮缺“问道”全程做全景透视与全面审视,以明晰《庄子》创作啮缺这一形象的深层用意,尚有待推进。本文在细致分析啮缺问道之路的深层意旨的同时尝试指出:啮缺的形象最初定位应是一个教化观居于儒、道间的道家内部人士,主要是在教化天下应以何种理念为本上的“辗转(突出‘摇摆不定’之意)”;《庄子》安排尧询问是否可将天下托付给啮缺时,借许由之口对此做出了严肃回应;此回应置入啮缺故事链内而理解,这一创作者深耕的故事链价值将得以充分彰显。
一、第一次问道:“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齐物论》是啮缺的首次显性出场,他是带着质疑的求教姿态出现的: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慄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且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鰌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辨?”啮缺曰:“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8)钟泰:《庄子发微》,第52-53页。
啮缺首次问道,急于从王倪那里获取他所谓的“知”:万物共同的评价标准、无所获取共同标准的原因、无法获取则如何理解万物。《庄子》借王倪之口,指出啮缺所谓的“知”并非“真知”,进一步强调啮缺的癔症是执着于“同”“正”,而执着于“同”“正”就不可能指向“真知”。王倪三次告之以:我怎么会知道呢(“吾恶乎知之”)!此回答从内容及形式上皆力图呈现一种“真知”,可惜啮缺并未理解。更准确地讲,他的知性追求使得他不甘心于此回答。在啮缺执着追问下,王倪决定“尝试言之”,他分别从居住、饮食、审美角度反问“正处”“正味”“正色”,以说明万物各有其嗜,各有其“正”,无法强求“同”。显然,这是在批评孟子“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9)朱熹:《朱子全书》(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01页。观点。《庄子》中常以动物喻人,这显然是对啮缺沉迷于以统一或单一的标准评价万物的思维的批评。
可惜,此次问道后,啮缺尚未觉悟,紧接着第四次追问:“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由前三问的“同”“正”到第四问的“利害”,显然已不只是在追问统一或单一标准,而是在更进一步追问是非、好坏、优劣,甚至高低、贵贱的细化的评判标准。对于啮缺此问,郭庆藩注曰:“未能妙其不知,故犹嫌至人当知之,斯悬之未解也。啮缺曰,未悟彼此之不知,更起利害之疑。”(10)郭庆藩:《庄子集释》(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6页。郭注的重点旨在指出啮缺未悟“彼此之不知”。教学过程至啮缺此追问进入死局,因为啮缺并未从王倪的教导中悟道,更陷于以是非二分来评价他者的一种“自我观之”的“我执”中。
对此,钟泰有着更值得注意的见解,他指出:“‘啮缺’、‘王倪’,皆假名。‘啮缺’喻知……‘王倪’喻德,言其侗侗如小儿也。老子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是也。三答‘吾恶乎知之!’承上‘知止其所不知’,言德不在知也。”(11)钟泰:《庄子发微》,第53页。钟泰认为,《庄子》借王倪教导啮缺的内容所要传达的是“德不在知”。结合此论,可进一步体悟《庄子》说:“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的意旨:“止”即强调对差异须有敬畏感,而“德不在知”的“知”,则指一种无视差异、分化而试图以“一”评判“万”的霸道思维;“知止”是达“德”的工夫,“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所传递的是对追求同一的这种知性冲动的两个否定面向:实然层面的不可能、应然层面的不应该。总之,“德不在知”是对《庄子》强调的德与知的张力的总结:追求“共同标准”的评价性知识的行为,一定会流向背离真正的“德”,导致对他物“真”的无视,如此,则既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德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智者。
可以看到,第一次问道所得的核心即“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其所传递出的是一种对差异的敬畏感。这种对差异的尊重,自然蕴含一种对界限的尊重。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荀子批评思孟学派以“尽心知性”来“知天”这一路径,并进而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中,亦可看到一种界限意识。在先秦儒学内部,荀子曾激烈批评思孟学派为“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12)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4页。。对此,李景林指出:《五行》《中庸》和《孟子》都强调圣者可知天道,但荀子对此显然不认可,正是基于此,荀子批评思孟为神秘主义(13)李景林:《教化视域中的儒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7页。。不过,荀子主要是强调天人有不同界限,但《庄子》中有着一种更极致的路线:一种“人不知人”“物不知物”及“人不知物”,并且人也不可能彻底搞清楚“自然”何以让万物呈现出“万”的特性的原因。然而,这样一种消极的认识论,却是要救治现实中的主体间交际的流弊的,如用当代科学术语讲,即对“基因密码”的奥秘性要持有敬畏感。据后现代主义来讲,即如德里达所论:“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首先是对他者(the other)的追求”“‘对他者的尊重’是‘唯一可能的伦理律令’。”(14)王治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17-24页。
二、第二次问道:“有虞氏不及泰氏”
《应帝王》一开篇便接着啮缺《齐物论》中首次出场的“四问而四不知”继续铺陈:
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15)钟泰:《庄子发微》,第167-168页。
啮缺“跃而大喜”,以此观之,可知啮缺在首次问道后终于开始觉悟“不知”与“真知”关系的妙处了,因为被衣曰:“而乃今知之乎?”钟泰亦指出,被衣“许其悟,而亦惜其晚也”(16)钟泰:《庄子发微》,第168页。。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惜啮缺晚悟的内容是“有虞氏不及泰氏”,这反过来正说明,啮缺之前对此不悟,而这则正是啮缺问道的出发点——国家层面的教化理念。有虞氏即舜,儒家的理想帝王;泰氏即太吴伏羲,道家的理想帝王,而“‘有虞氏不及泰氏’已含轻视儒家之治的意思,但是话很委婉,只是不及而已”(17)王孝鱼:《庄子内篇新解 庄子通疏证》,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46页。。对《庄子》的这一“良苦用心”,王孝鱼曾指出,《庄子》在内七篇之末特意作《应帝王》一篇,目的就是试图以道家思想横打诸子百家(18)王孝鱼:《庄子内篇新解 庄子通疏证》,第145页。。
首先,《庄子》借被衣来点化啮缺:有虞氏的教化观“未始出于非人”。此处“非人”指“天”,对此,钟泰曾指出:“注家有以非人释作物者,不知人与天对,不与物对。《庄子》全书皆如此,可检案也。”(19)钟泰:《庄子发微》,第169页。这是在批判有虞氏的教化观未遵循天自然化育万物的原则。质言之,这种路径其实是试图从宇宙论上来为万物之出生就显现为“万”,即通过对差异做出一种自然源起的事实描述,进而为差异的合理性做支撑。庄子进而赞泰氏“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此处“非人”则做动词用,即伤人,这是对一种以尊重特殊性为出发点来教化的理念的肯定。《庄子》极其警惕:试图以“一”化众,认为这是以某一群体的“一”而伤另一群体的“天(性)”。
其次,《庄子》批判有虞氏曰:“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所谓“藏”,即强调一种时间上的绵长。对此的理解,需要借助《天运》篇曾提到的内容:“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20)钟泰:《庄子发微》,第327页。钟泰指出:“‘藏仁’,则所谓(强行)久处者也。久处则滞矣。以是要人,则虽得人之道,而非如天之治浩也。”(21)钟泰:《庄子发微》,第168页。在钟泰对第二次问道的分析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字,即“滞”与“浩”。《庄子》批判有虞氏以仁爱来要结人心,虽也能暂时使人安顺,但此法不能成为教化之本,因而不能长期使用;强行长期使用,必然使社会走向停滞,关键的是,这里的“滞”的原因指向无法达到“天之治浩”。“浩”本身指向对多样性的追求,对多样性的否定则意味着对个体繁荣(individual flourishing)的压制与牺牲,并且最终导致对人类繁荣(human flourishing)的损伤。这里引用了“繁荣”一词来加以诠释,有必要对“繁荣”在当代哲学中的所指作出交代:“英文词‘Flourishing’描绘了事物本身的繁荣昌盛、欣欣向荣。它内指事物自身潜在功能的全面发展与充分展开,外涉事物发展的兴旺蓬勃、光彩华丽”“‘人类繁荣’(Human Flourishing)作为一个值得推荐的研究路径引入当代平等主义问题讨论”,并视其为与“‘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相呼应的一个政治哲学主题。”(22)[加拿大]克里斯汀·希普诺维奇撰,孙晓静译:《人类繁荣——平等问题研究的一种新路径》,《现代哲学》2020年第2期,第32-44页。而第二次问道所得的核心即“有虞氏不及泰氏”,其所传递出的则是:正义的“人类繁荣”应建基于“个体繁荣”上。很显然,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与《庄子》文本可达成一种相互诠释的效果。
那如何解决“滞”成就“浩”呢?对此,王船山在《庄子解》之《应帝王》篇题解中有一深刻的回答:“不自任以帝王,而独全其天,以命物之化而使自治,则天下莫能出吾宗,而天下无不治。非私智小材,辨是非、治乱、利害、吉凶者之所可测也。”(23)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三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76页。船山指出,《庄子》所护持的是一种“自化自治”,物“自化自治”的好处则在于:个性化的充分展开,将意味着向丰富且持续的可能性世界与意义的敞开,而建基于这种“个体繁荣”上的“人类繁荣”,才是人类高度文明真正要追寻的一种“正义的繁荣”。这正是《庄子》护持个体特殊性的深层关切所在。
三、第三次问道:“不以故自持”与“道通为一”
但是,强调尊重差异并不意味着个体就应“自贵而相贱”(24)钟泰:《庄子发微》,第370页。,据《庄子》构思的啮缺的最后一次出场,更可知这条故事链的意图。啮缺第三次问道是在《知北游》中,以一首“被衣为啮缺歌”来结尾,至此,《庄子》中再未出现啮缺问道的踪影,显已真正得道:
啮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女形,一女视,天和将至;摄女知,一女度,神将来舍。德将为女美,道将为女居,女瞳焉若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言未卒,啮缺睡寐。被衣大说,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彼何人哉!”(25)钟泰:《庄子发微》,第489页。
啮缺此次问道于被衣,被衣教其“无知无识”,结果“言未卒,啮缺睡寐”,被衣大悦,赞啮缺真正体悟了大道的精神实质,这是从王倪到被衣三次问道的教化终至的呈现“不以故自持”:内在与外在彻底地化“我执”,尤其是过去被“成心(故)”所支配的“我”。“成心”既指主流规范,亦含唯我主义。“不以故自持”,即要求“我”既不被流行的观点所制约,亦不只以自身嗜好所驱使,实现一种“无知无识”的境界。显然,此处对“知识”的否定,实质指向反对以一种统一或单一的标准来统“万”,而这才是“真知”“实知”。
至此,《庄子》借被衣之口指出,啮缺由思想的摇摆经教化后归于道家之“道”:“以道观之,物无贵贱。”(26)钟泰:《庄子发微》,第370页。同时,亦明确指出了道家式的教化目的——“丧我”,这一目的之精神指向进入“道通为一”的“齐”的境域。第三次问道所得的核心即“不以故自持”与“道通为一”,其所传递出的是差异原则与“齐”的境域的“共在”(together)。由此观之,《齐物论》名为“齐物”,然绝不能被误解为在追求所谓的“共同标准”。其一开篇就以“丧我”发端,继而强调摒弃“成心”而来的一种“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27)钟泰:《庄子发微》,第370页。的评价思维,从而才可“齐物”。这一经“无知无识”与“自我遗忘”而至的“齐”的境域,恰如荷尔德林在诗意而哲学的语境中描绘这种存在的美妙感受:“个体与一切生命同在,在陶醉的自我遗忘中回归自然万物,这是思想与欢愉的峰顶。”(28)[德]埃里希·蒂斯撰,马绎、刘媛译:《中国人的时间图像》,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页。
毋庸置疑,这种教化观有着不可抵抗的迷人魅力与价值:其反对构建一个单一的标准,而是考虑所有个体在行为中的个体性是否得到尊重、个体繁荣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性。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丧我”与“自我”的张力,也就是说,从事“丧我”工夫的主体“我”是不可能彻底消解的,“我”依然时时在场。那么,尊重个体性或差异性,在现实交互行为中,如何能保障避免滑入唯我论而不自知的危险呢?即交互行为中的“丧我”,如何得到更稳固的实现?
对此,应该说,《庄子》的差异教化观是以尊重个体性为基础的。但是,《庄子》并不是一种唯我主义的伦理观,不仅与那种每个个体仅对自己的舒适与苦痛负责的观念十分不同,且与之本质相异。强调“以道观之”的同时,《庄子》的这种差异教化观内含一种非“唯我论”的伦理气质,即沿袭《老子》所主张的一种“自爱,不自贵”(29)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0页。精神,个体尊重自己的特殊性的原因,源于其所持有的差异伦理观。个体“不自贵”的原因,亦源于其持有的差异伦理观,即因为意识到自我的特殊性,因而亦意识到每个个体都是“主体”,因而都具有特殊性。当同时认可“自爱”与“不自贵”,才能在享受差异伦理观优势的同时,保证有一只脚时刻踩在开向唯我主义歧途的刹车上。可以说,《庄子》中无论是“许由逃尧”,亦或啮缺经道家式的教化终达“无知无识”,都可看出“自爱”与“丧我”同等重要,缺少其中任何一方,另一方都难实现真正的意义。
但是,还需要指出,《庄子》的尊重论与流行的“移情”尊重论是不同的。移情尊重论的前提是理想化“共情”,这里有一个潜藏的意识,即认为人所“嗜”是相同的,这就易致使在实践中,将《孟子》“凡同类者,举相似也”(30)朱熹:《朱子全书》(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00页。的“相似”强化为一种实然“同”与应然“同”。如当代哲学家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就竭尽全力把尊重完全建立在“移情”上,认为“迫害”他者的人“傲慢地排除或者缺乏移情,无法从他人的视角看问题”。但这样一种移情论,常常陷于无法解释很多“迫害”是出于“共情”的,如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备受来自于“己所欲,施予人”的“好心”所带来的某些“迫害”。另一位美国哲学家安靖如(Stephen C.Angle)对斯洛特提出质疑,假如君王(即教化者)“非常痛苦地看到用这样痛苦的方式‘教导’受害者的必要性。假设他(君王或教化者)的眼睛中满含泪水,你能简单地说他此时缺乏同情心吗?”(31)[美]安靖如撰,吴伟万译:《圣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页。安靖如质疑迈克尔·斯洛特所提出的这种移情论时,所举例的君主是明太祖朱元璋。这当然不是说《庄子》否定人能够“共情”,相反,道家发自真心“疼”每一个存在(32)贡华南:《哲学视域中的疼》,《哲学分析》2021年第1期,第116-125页。。《老子》很早就讲:“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33)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71页。不过,《庄子》的尊重论,显然是以对他的时代的移情尊重论所暴露出的弊病的反思为背景的。因此,希冀警惕理想化主体与他者之间能真正“共情”的“度”,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去追求一种实质的尊重。
四、另外两次出场:“必以无为者主之于先”
啮缺在《庄子》中,还有两次出场,皆与许由有关,也都和尧要托付君主之职有关:
啮缺遇许由,曰:“子将奚之?”曰:“将逃尧。”曰:“奚谓邪?”曰:“夫尧畜畜然仁,吾恐其为天下笑。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散。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是以一人之断制天下,譬之犹一覕也。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34)钟泰:《庄子发微》,第581页。
尧问于许由曰:“啮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许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啮缺之为人也,聪明睿知,给数以敏,其性过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审乎禁过,而不知过之所由生。与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天。方且本身而异形,方且尊知而火驰,方且为绪使,方且为物絯,方且四顾而物应,方且应众宜,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虽然,有族有祖,可以为众父,而不可以为众父父。治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35)钟泰:《庄子发微》,第254-255页。
“教”的活动涉及教者与被教者,古典文本中,教者形象主要是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机器,教的内容往往是存在一种标准及以此为基础的评价体系。本文的“教化观”一词,主要是就一种社会教化观而言的,尤指一种自上而下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引导性活动,“就已有的社会属性而言,教化是人文讯息的代际传递,是‘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不间断的社会运动,并且具有某种强迫性和给予性。这样,自先而后、自上而下的推及,便和社会的政治运作及其制度安排紧密地接合在一起”(36)景海峰:《从诠释学看儒家哲学的教化观念》,《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5-11页。。这种教化观的内核是价值观的“引导”,所谓“引导”,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施予,二是导向。这两部分往往看起来是融合为一的,但是,如对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引导性活动的具体操作过程而言,二者往往有着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即“施予”是“导向”之前提与规划,“导向”则是“施予”目的之实现。《庄子》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多次出现对教者身份的拒斥,众所周知的事例即许由逃尧。许由逃尧时,一并批评了尧过往的教化理念:一种以单一的标准及评价体系(“一人之断”)来教化天下,是蔽于一瞥之见(“犹一覕”)。许由并不否定尧想要造福天下的动机,但担心以一化众,会产生扭曲人性、祸害天下的恶果(“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在《天地》篇中,《庄子》又借许由之口对啮缺不能为天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乘人而无天”,即啮缺持有一种执着于专凭教者的智术而轻视被教者的“自然”的教化理念。这种“有为”的热情将导致诸多“不堪”:“其性过人”则“人将不堪矣”“‘而又乃以人受天’,‘受’尤代也”(即以人代天)”则“物亦将不堪矣”“人不堪,物亦不堪,则过失必多矣。”(37)钟泰:《庄子发微》,第255页。质言之,《庄子》笔下的叙事,多次呈现出一种无欲做教化典范的姿态,这一姿态所传递的深层意旨,即对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论的警惕,以及对每个个体特殊性的护持,这就指向了一种“从下而上”的平等追求(38)关于平等的哲学讨论,如何实现一种真正平等,从下而上的路径,一直被视为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核心。。
许由还进一步指出啮缺“彼审乎禁过,而不知过之所由生”,即执着共同标准的啮缺能明白如何制止人家做错事,而无法理解人家做错事的根由。问题就出在教化者以己身为本而不与万物同行,将会顾盼四方而使万物来顺应他,将会追求每件事情都办得符合他所制定的统一标准。《庄子》认为,这些以一己标准为标准的教化,最终都会走向滞化。
接着,《庄子》总结道:这种“有为”的热情“可以为众父,而不可以为众父父”。所谓“‘可以为众父’,喻啮缺为臣道而有余。‘而不可以为众父父’,喻啮缺为君道则不足。”(39)钟泰:《庄子发微》,第256页。即许由认为啮缺未能做到从“无为”出发,观照万物之差异性,所以许由明确指出啮缺可以做“臣”的具体执行工作,以“仁义”爱人,但不可为“君”,其为君也,则虽表面“治”,却是“乱之率也,北面之祸也,南面之贼也”。质言之,《庄子》强调“仁义”举措的基础原则须是“无为”,他警惕一种对“仁义”的滥用:“己欲立而立人”时,无视己与他的差异,而强行以己之标准立他。《天地》篇后,《天道》篇紧接着就宣讲:“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40)钟泰:《庄子发微》,第288页。即强调本末不可颠倒。对此,《庄子》还进一步具体分述:
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赏罚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礼法数度,形名比详,治之末也;钟鼓之音,羽旄之容,乐之末也;哭泣衰绖,隆杀之服,哀之末也。(41)钟泰:《庄子发微》,第288页。
《庄子》在此连用五个“末也”来定位“有为”的王道教化,这显然流露出对《礼记》强调的王道教化系统,即“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42)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719页。思想流弊的警惕之意(43)儒家的教化观与道家的教化观,共同构成了古典中国“教化观”的圆圈。以“礼教”为核心的儒家教化观突出的是一种“类”的普遍性,在社会教化的规划层面强调一种个体对“群”的认同,这种认同自然不乏“服从”之义(需要指出,此处的“服从”尚是一个中性词,突出的是“规训”义);但由于对“服从”的滥用,可能导致对个人认同的漠视性压制。因而,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学界对儒家以“礼教”为核心的教化观弊端的自省或批判,但并不认同以一种群体认同与个体认同截然二分的框架来刻板化、标签化中国哲学各家各派,更不认同将儒家的教化观简单归于这类观点:“群体认同”凌驾于“个体认同”上。但限于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及篇幅限制,重点围绕《庄子》中啮缺相关的教化观的关切做讨论,因而只对儒、道教化观特点做简单叙述。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接受这样一种比较之下的观点,即道家教化观相较于儒家教化观,更关切个体的“个体认同”。还应该指出,《庄子》并不绝对否定“引导性活动”,但是其警惕一种过度的“引导”以及由之而来的对个人的本真性的遮蔽。。《庄子》认为,“倒道而言,迕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44)钟泰:《庄子发微》,第289页。。这是指出“王道”只能为“具(器)”,而不能成为“道”,安能治人!
《庄子》进而对理想教化观中的内容给出了具体排序: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45)钟泰:《庄子发微》,第289页。
此段描述,排篇布局颇有《大学》之感,然《庄子》首句“先明天,而道德次之”突出了《庄子》着意处:差异教化观所基于的是对个体特殊性原则的维护。如此,“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才是实现太平之治的大道。质言之,《庄子》极为警惕礼在产生、演变中的两面性:一方面,即凡规范之产生,就有一个非真即伪的“原罪”存在,而不可能对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个体皆有益或达到绝对公平;另一方面,规范往往会走向某种僵化。《庄子》恰是在规范产生的“原罪”上质疑规范的压迫性、牺牲性,在规范演变的流弊中警惕规范的形式化、虚伪化。《庄子》对礼的“伪(产生上的人为性与演变中的虚伪性)”的一面敲响了警钟,不过,消除礼的流弊对人的限定的积极方法并非否弃礼,重要的是如何警惕其易滋生的“伪”并持续予以修正。对此,《庄子》强调一种对“真知”及“真人”的追求,给出了一种以“贵真”为基底的教化理想:“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46)钟泰:《庄子发微》,第724页。
综上,《庄子》全书有着一种在“无为”与“有为”原则间的自觉调适,就国家层面的教化观而言,其原则为“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47)钟泰:《庄子发微》,第287页。。对此,刘凤苞在《南华雪心编》中指出,“用天下,归重无为;为天下用,责成有为。无为、有为,天下均不可离。看他分出上下界限,朗若列眉,为下文本末、先后伏跟也”(48)王先谦集解,方勇导读、整理:《庄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林云铭《庄子因》认为:“此言有为之事虽不可废,然必以无为者主之于先也。”(49)林云铭:《庄子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页。林氏的这一“必”字突出了《庄子》的用意,十分中肯。后两次出场所得的核心即“必以无为者主之于先”,其所传递出的正是差异教化观的基础原则。
依上所论,亟待指出的是,强调差异性原则是对既有社会规范的“一”的质疑与警惕,这往往被认为是以一种补充性原则而具有其价值的,正如过往研究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将道家看作是儒家教化观弊端的纠正者。而实际上,《庄子》认为“无为”原则为“本”而非“末”。
质言之,人类已经发展到越来越认识到特殊性、多样性及其价值的时代,在多元文化碰撞的今日,《庄子》对以某一种标准的“独尊”所提出的“不可能”已日渐成为现实,然《庄子》所强调的“不应该”却还缺乏实质层面的重视。首先,因单一价值观而带来的伤害,是对人与理性的伤害,统一的评价规范之专行其弊端甚矣。其次,要谨防一种道德热情,即对“仁义”的滥用——在倡导“己欲立而立人”时,无视己与他的差异,而强行以己之标准立他。换言之,用统一性原则碾压特殊性原则,必须被制约。在高举“人类繁荣”的社会整合论原则的同时,较为合理的做法是:应将尊重每个个体繁荣的原则视为平行原则,即尊重个体特殊性,而非只将个体视为社会结构中的“角色”而只具有“角色价值”(50)有关角色伦理学的研究,可参考[美]安乐哲,[美]孟巍隆译,田辰山等校译:《儒家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庄子》一书突显出其独特的伦理特质与价值资源。《庄子》所传递出的对个体特殊性的肯定,亟需在当代公共生活伦理困境中被重视,即对一种单向度的评价体系的不满与否,甚至反叛与解构。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啮缺问道”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庄子阐释其主要思想的过程:从否弃一种平面化的人为的“同”,到对差异性的关注,再到最终在其间实现“丧我”,以追求并实现一种在人间世的自在的逍遥游。同时,这一追求及实现,如无一种“道通为一”的自觉,则这种自在感与逍遥游也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实现。
结语
本文通过复原、再诠《庄子》中“啮缺问道”这一故事链,想要指出:首先,啮缺最初定位应是一个教化观居于儒、道间的道家内部人士,而《庄子》借许由之口批评啮缺的内容有着深刻蕴意;其次,《庄子》借许由、啮缺所传递的对统治者教化职位的推却姿态有其深层意旨,即强调一种差异教化观,其核心理念是质疑一种想要以一统万的社会整合论、要求警惕一种改造他者性的道德热情;再次,将《庄子》全书视为一个整体文本而观,《庄子》有着在无为与有为间的自觉调适,但原则是“必以无为者主之于先”。
那么,尊重差异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文基于啮缺在《庄子》中的五次出场所试图给出的回答是:就个体而言,尊重差异意味着个体应自觉探求并尊重主体特殊性;在群己关系上,则意味着要尊重他者性及多样性;而建基于“个体繁荣”基础上的“人类繁荣”才是一种“正义的繁荣”,因为这种繁荣是真正向丰富且持续的可能性世界与意义的敞开。在理论建设上,希冀个体化时代的社会整合论、社会决策及相关理论,应该以构建一个尊重个体权利、包容个体差异的共同体为方向。同时,持续修正不适宜的礼,以使其不断剥离“伪”的一面,而这就是《庄子》差异教化观的指向所在,其目的及警惕恰如罗素所言,“参差多样,对幸福来讲是命脉,在乌托邦中几乎丝毫见不到”(1)[美]罗素著,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0页。。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庄子》对于教者之职的拒斥在姿态上有重大意义,但在现实政治层面,如完全拒斥教化之职,则对公众实现这种差异伦理观缺少助益。从这一角度而观,当前学界一些研究成果认为庄子的自由观对现代公民自由追求的实现,益处颇少甚至有着阻碍之力,有其合理性。不过,如果以啮缺从问道到闻道之路而观,即道家式的教化是存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其说道家是拒斥教化和教化者之职,毋宁说拒斥的是以消解差异性原则为内容、目的的那类教化和教化者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