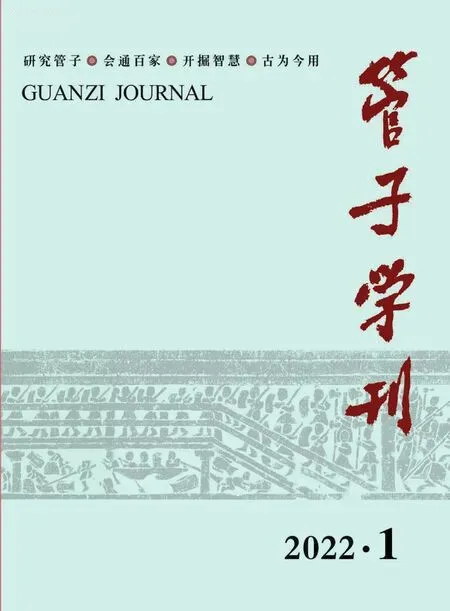试论儒家生态思想及实践
2022-11-21陈红兵
陈红兵
(山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儒家生态思想及实践本身有一个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儒家生态思想肇始于孔子,但其早期系统阐发则主要体现在《中庸》《孟子》《荀子》《易传》等先秦著述中。汉代,董仲舒等以天人感应理论阐释儒家生态思想。宋明理学则吸收融合佛教理论思辨,进一步阐发了《中庸》《易传》中的生态思想,形成儒家生态思想的又一高潮。本文主要以先秦儒学、宋明理学相关文献为主体,从生态存在论、生态价值论、生态实践三方面论述儒家生态思想及实践的基本内容。
一、“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态存在论
儒家、道家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根源,在存在论方面持类似的观念,均将世界视作天地创生万物的过程,而天地万物及社会秩序则在这一创生过程中形成。关于儒家生态存在论,我们突出两方面:一是天地创生万物的有机生成论,其中包括关于天地“生生之德”“诚者天之道”等的阐述;二是关于人与天地之间“继善成性”关系的思想。
(一)“生化万物”的生生之德
关于天地万物生成模式,《易传》将天地创生万物的过程描述为天地→万物→家庭→国家的生成序列:“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1)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99页。认为不仅自然万物生成于天地,而且人世间夫妇、父子、君臣等伦常关系同样根源于天地,有自身生成发展过程。宋明理学则更进一步将天地创生万物过程阐释为“无极→太极→动静→阴阳→五行→万物”序列,从而将我国古代太极、阴阳、五行学说中的相关思想整合为统一的有机生成论模式。
相对于道家突出“道法自然”特征而言,儒家生态存在论更强调天地“生生之德”。在这方面,《易传》的相关阐述最为典型。首先,我们看《易传·彖传》关于乾坤两卦的阐述。乾卦的《彖传》中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万物的产生有赖于天道变化。阳光雨露、四季变化是万物生成的基础,万物正是在天道变化过程中形成自身的生命。坤卦之《彖传》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大地是万物资生的基础,万物正是在广袤的大地上顺利成长。其次,《系辞》中也称颂天地生长化育万物的盛德大业:“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以天地生化万物的富有、生生不息(“日新”),阐明天地的“盛德大业”;从乾之“大生”、坤之“广生”,阐明天地生化万物的广大功用。此外,《易传》等经典还具体阐述了天地在生化万物中的不同功用。如《系辞上》说“乾知大始,坤作成物”(2)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第5、23、503-506、493页。,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中说“天生之,地养之”(3)董仲舒:《春秋繁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1页。,即是说,天始生万物,地长养万物。天地在生化万物过程中是共同发挥作用的。
在《易传》思想的基础上,儒家思想家对天地“生生之德”有进一步阐发,如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阐释说:“天地之盛德,在乎常生。……以其常生万物,故云‘大德’也。”“生生,不绝之辞。……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4)刘玉建:《〈周易正义〉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403-404、376页。着重从“常生”“恒生”阐释“天地之盛德”。所谓“常生”“恒生”,实际上强调的是天地生长万物的生生不息。张载《横渠易说·复卦》则从“天地之心”阐释“天地之大德曰生”:“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5)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13页。将天地生长万物阐释为“天地之心”,实际上是将生长万物视作天地造化的目的。朱熹《仁说》进一步将“天地以生物为心”与儒家“仁”的观念相关联:“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6)朱熹:《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9页。是说天地以生物为心(目的),人与万物产生后,也秉承了天地生物之心。因此,不管是“天地之心”还是人内在的本心,无不“以生物为心”。“以生物为心”即体现了对万物的“仁爱之心”。
蒙培元先生在讨论儒家生态哲学思想时,认为儒家“天地之心”观念体现了对自然目的性的探讨。在他看来,“心”就是目的。天地是以“生”为心。“心”本意是“木心”,象征生长,之后逐渐发展为儒家目的性学说。宋明理学所谓“天地以生物为心”“人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体现的即是这一内涵。他认为,天地本无所谓“心”,但天地生化万物,无形中体现出“生”的目的。人承继天地生物之心,则体现了心之自觉,体现为真正的目的性。在儒家看来,人心是对天地之心的承续,人的目的是对自然目的性的继承。因此,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体现了对天地之心的承续与实现。蒙培元先生认为,中国儒家所说“为天地立心”,与康德“人为自然立法”不同,它是通过自身的创造将自然目的性呈现出来,是“赞天地之化育”,是善(7)杜维明、蒙培元、郑家栋、李存山、卢风、雷毅:《儒家与生态》,《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1期,第9页。。由上可知,在儒家看来,宇宙创生万物的过程是一个创生生命的过程,人应秉承天地“生物之心”,辅助万物生长化育。就此而言,儒家的存在论是一种有机生成论。
儒家还将天地“生生之德”与“诚”之德相关联。《中庸》阐释“诚者,天地之道”的内涵,强调天道运行“至诚无息”,“天地之道,可壹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8)陈戍国:《四书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0页。。“诚”是相对于“贰”,相对于虚妄而言的,突出的是天地生化万物有自身固有的、真实无妄的规律。“诚”体现在天地创生万物上则是因为天道之“诚”,所以能够“生物不测”。儒家关于天地“生生之德”、“诚”之德的阐释,从根本上说,体现的是对人生意义的追寻,是从天地的本性探索人应具有的德性。“生生之德”落实到人的德性上,即是帮助他人、万物实现自身生命之“仁”。儒家主张人应自觉继承天地“生生之德”,体察、拓展内在本有的“仁”德。而要体察、拓展内在的仁德,则应秉持“至诚”德性。儒家认为,只有秉持至诚之德,才能体察、实现自身以及他人、万物内在的本性,才能“赞天地之化育”。
(二)“继善成性”的天人关系
“究天人之际”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主题,而儒家关于“天”的认识也始终是围绕人生的意义探寻的。人作为天地造化的产物,在天地万物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人在天地运化过程中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儒家没有脱离其生成论背景孤立地探讨这些问题,而主要是从“继善成性”的角度阐发天人关系思想的。一方面,人的性命源于天地造化;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身的主体性,在天地造化中具有自身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围绕这两方面,儒家天人关系论阐释了如下四层内涵:
其一,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相继关系,即人是天地生成的产物,人的本性是从天地生成的。《易传·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9)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第5、503页。。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即是说人与万物的性命均是天地造化的产物。伴随天地的变化,人与万物会相应调节自身性命系统;而所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是说人的本性是承继天地阴阳变化而来,是在天地阴阳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易传》肯定天地生化万物的“生生之德”,因此称之为“善”。《易传》“继善成性”思想后来在宋明儒学中得到继承和发挥。朱熹、王阳明等将“生生之德”阐释为人内在本有的仁德,认为人的“仁德”是对天地“生生之德”的继承和实现。
其二,人承继天地的本性,因此同天地一样具有相同的生生之德或仁德。周敦颐《太极图说》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10)李敖主编:《周子通书 张载集 二程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将生成万物视作天地的仁义之德,而圣人体察、效法天地生成万物的德性,以仁义养育万物,教化百姓。程颢将“仁”分为“天地之仁”与“人心之仁”,而“仁”的本质是“生意”,即生命活力,如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11)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0页。这是说万物的“生意”或生命活力,即是《易传》中所说的“元者善之长也”,即是“仁”。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阐明了“生生之德”或“仁德”是人与天地的共同本性。
其三,儒家阐述了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心”的观念。程颢说:“天地之间,非独人为至灵,自家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尔。”(12)程颢、程颐:《二程集》,第4页。一方面认为人心与草木鸟兽之心一般;另一方面又肯定人受“天地之中”(正性)而生。在此基础上,儒家肯定“万物皆备于我”(13)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孟子》,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25页。,肯定“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14)黄宗羲:《宋元学案》(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52-553页。,实际上即是肯定人禀受天地正性,因而具有天地万物的全息。以此,《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15)陈澔注,金晓东校点:《礼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61页。肯定人能够体现天地之心。关于人为“天地之心”的内涵,当代生态思想家罗尔斯顿的类似观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生物进化产生出人类是自然唤醒了心智;同样,从个体的发育看,个体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也是自然唤醒了心智……生态的刺激使人类的主体‘我’诞生了。大地的景物以我来对它进行沉思,我就是它的意识。”(16)[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著,刘耳、叶平译:《哲学走向荒野》,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9页。从一定意义上肯定了人的心智是自然运化到高级阶段的产物,肯定了人的心智能够更好地体察天地万物本质及规律。
其四,从天人关系角度考察人的责任、价值、地位,认为人秉承天地“生生之德”,理当承担起“成己成物”“参赞化育”的责任,实现天地生长化育万物的目的。《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7)陈戍国:《四书校注》,第38页。肯定人能继承发挥天命之性,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立为三。《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18)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孟子》,第224页。是说人能认识、长养内在禀赋的天地之性,则能侍奉天地,实现生长化育万物的目的。
儒家存在论突出天地生长化育万物的作用、德性,在天人关系上,从天地生长化育万物的高度考察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考察人自身的能力、价值、作用和地位,一方面肯定了人与天地万物的一体性、统一性,就此而言,儒家存在论是一种有机生成论、整体论,其关于天地生长化育万物、天人相继、天人共同的生生之德等观念,对于我们今天建构生态整体论世界观具有启发意义;另一方面,肯定了人的主体性价值、作用。从这方面而言,儒家没有抹杀人的主体性价值。但儒家是在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性基础上阐述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其关于人的地位、作用的论述,也没有将人与天地万物分离对立起来,没有单纯从人自身的生存利益出发,强调对自然万物的利用与改造,而是从天地高度阐述人对天地万物的责任,因此避免了西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僭妄。儒家天人关系论对于我们今天重新思考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二、“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生态价值观
生态价值观本身具有多方面内容。人在天地万物中的价值是生态价值观的重要方面。儒家注重从天人之际考察人生的意义及人应具有的德性,认为人的价值即在于承继天地“生生之德”,赞天地之化育,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人与自然万物的不同价值也是生态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儒家一方面追求“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另一方面又肯定人比其他万物更有价值,并认为人高于其他万物的地方即在于人具有德性。儒家以“仁民爱物”为自身价值追求,但在关爱人与万物上,又主张“爱有差等”,认为对人与万物的关爱程度应有差别。儒家对人之德性价值的高扬,及“爱有差等”观念,是否属于当代生态文化思潮批判的人类中心论?本部分将围绕以上方面阐述儒家生态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一)“与天地参”的主体价值
儒家注重从天人关系角度阐释人的价值,一方面肯定人产生于自然界,另一方面肯定人的产生是天地生长化育万物的重要环节,认为人的价值正在于能够继承天地“生生之德”,成己成物,协助实现天地生长化育万物的目的。
《易传》从“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阐明人对于天地万物的“财成辅相”作用。关于“财成辅相”的内涵,郑玄注释说:“财,节也。辅,相。左右,助也。以者,取其顺阴阳之节,为出内之政。春崇宽仁,夏以长养,秋教收敛,冬敕盖藏,皆可以成物助民也。”(19)李鼎祚:《周易集解》,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63页。“财成辅相”,是指人应通过顺应天地阴阳变化之道,春季崇尚宽和仁爱,夏季应当长养,秋季注重收敛,冬季理当盖藏,利用天地阴阳变化节律,成就万物,助益百姓。主张顺应自然变化节律组织生产生活,利用自然万物利益百姓。
《中庸》认为人的价值在于“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20)陈戍国:《四书校注》,第38页。。所谓“成物”即体察自然万物本性,帮助自然万物实现自身的价值。关于“赞天地之化育”,程颢阐释说:“至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赞者,参赞之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之谓也。”(21)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3-34页。当代学者刘文英亦阐释说:“‘赞’是一种有为的活动,‘赞’的前提是尊重天地自然本身的变化和飞潜动植的化育,而不是把人的意志强加于世界。换句话说,必须按照天道、物性的要求去影响和推动‘万物的化育’,以便使‘化育’的过程和结果避免灾祸和为人所宜。”(22)白奚:《论儒家的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论——从刘文英先生对儒家生态伦理观的研究说起》,《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7页。从中不难看出,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易传》中所说的“裁成辅相”内涵本质上相同,均强调的是人应顺应天地阴阳造化规律,促成“万物的化育”,达到利益百姓的目的。
儒家一般从天地人三才并立的高度阐释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如《荀子·富国》中说“天地生之,圣人成之”,《荀子·天论》中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23)章诗同:《荀子简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6、177页。。肯定天地产生万物,圣人辅助天地成就万物。万物在天地运化过程中生成,而人依靠社会治理成就万物,因此人具有与天地并立为三的地位;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立元神》《天地阴阳》篇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24)董仲舒:《春秋繁露》,第51,167页。也是肯定天地生成养育万物,人成就万物。人具有超越万物、长养万物、成就万物、参与天地的地位和作用。
儒家从天人关系高度阐释人自身的主体价值,这与道家偏重于强调人顺应自然造化是有差别的,突出了人自身的价值和地位。但是儒家的主体性思想,又与西方现代文明将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论不同。儒家并没有将人的价值与天地阴阳变化节律对立起来,而是强调人必须顺应天地阴阳变化节律,发挥自身成己成物、利益百姓的价值。
(二)“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价值理想
儒家“天人合一”“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价值理想,不仅体现了儒家人生价值追求,而且也体现了生态价值观的内涵。儒家关于生态价值理想的认识本身存在一个过程。
先秦儒家相对重视人与自然万物的现实繁荣和谐。如《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既是指君子的德性,也是指对待万物“无过与不及”的中庸态度。儒家强调“中和”,旨在促进天地的和谐有序,以及万物的生长发育。“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5)陈戍国:《四书校注》,第19,47页。等,描述的均是天地万物和谐有序、共生繁荣的理想状态。《荀子·王制》亦肯定以儒家礼义治理天下,能够达致“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的状态(26)章诗同:《荀子简注》,第86页。;孟子同样强调对待动植物,应根据其生长时节加以合理利用:“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合理利用事物,则万物都能得到长养。“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万物都能得到适宜的长养,百姓就能“谷不可胜食……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27)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孟子》,第196、5页。。从中可以看出,先秦儒家生态理想还是很现实的,主要强调的是人与万物共生繁荣的理想状态,关注的是百姓物质生活的富足。
先秦儒家也注重人自身的德性,但其对于德性的强调,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仍相对重视人对天地自然造化的顺应。如《易传》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神乎?”(28)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第19页。强调的是“大人”德性、智慧、行为对天地、日月、四时的顺应与契合。这与后来宋明理学所强调的“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29)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2014年版,第1066页。的理想境界有本质差别。显然,宋明理学更偏重于人自身的仁德及德性境界。
宋明理学在生态价值理想方面则突出主体对“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体认。程颢首先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本质上阐述的是主体对自身与天地万物同一体的体认,是一种精神修养境界。朱熹也认为“万物一体”并不是万物存在的本然状态,而是人应追求的理想状态,认为只有通过克制私欲,“公而后仁”,才能达到“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王阳明对“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30)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066-1067页。从中可以看出,其所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主要是从不同层面阐明人对天地万物的同情爱护之心,是从情感角度表达主体关于自身与草木鸟兽乃至瓦石的一体性的体认。
儒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一方面突出的是主体对天地万物的同情、爱惜之心,突出的是主体仁德的修养,这体现了儒家德性伦理的特征;另一方面,“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价值追求,又体现了儒家关于人与天地万物关系的体认。在儒家看来,“仁德”是对天地“生生之德”的继承和实现。从这方面而言,“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又是人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理想的实现。此外,儒家“仁民爱物”观念强调对百姓、万物的关爱之情;而所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则表明儒家将道德关爱拓展到天地万物。这又与当代生态文化思潮将伦理关怀拓展到其他生命、拓展到自然生态系统的观念相契合。而儒家将伦理关怀的拓展建立在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性、“生生之德”的体认基础上,对于我们今天建构生态价值观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三)“爱有差等”的仁爱序列
儒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思想建立在对血缘之爱的拓展基础上,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思想特质。陈炎认为:儒家的仁爱源于父子、兄弟之间的血缘关系。儒家学者又从“泛血缘”的立场出发,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31)杨柳岸导读:《论语》,长沙:岳麓书社,2018年版,第148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2)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孟子》,第13页。,将血缘情感拓展为“君君臣臣”的社会伦理。在此基础上,儒家更进一步将血缘之爱拓展为人与万物之间的拟血缘关系。从拟血缘关系出发,人与鸟兽草木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血缘关系,但我们依然可以将仁爱之心拓展到它们身上(33)陈炎、赵玉:《儒家的生态观与审美观》,《孔子研究》2006年第1期,第6页。。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见草木之摧折而有怜悯之心”“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
儒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一方面强调施仁爱于天地万物,另一方面又强调对人、对鸟兽、对草木瓦石应施以不同的爱,此即所谓“爱有差等”。《吕氏春秋·爱类》说:“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34)吕不韦撰,杨红伟译注:《吕氏春秋》,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537页。爱护其他事物,不关爱人,算不上仁;不爱护其他事物,只关爱人,还可以称之为仁。所谓仁,就是关爱其同类。王阳明《传习录》也说:“惟是道理自有厚薄……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35)王阳明著,迟双明解译:《传习录全鉴》,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页。对禽兽和草木都关爱,但是却又舍得用草木喂养禽兽;对人与禽兽都关爱,但却忍心宰杀禽兽奉养亲人,供奉祭祀,宴请宾客。在王阳明看来,爱有厚薄等差,这是道理应当。
儒家“爱有差等”观念建立在人与万物具有不同价值的观念基础上。儒家高扬人自身的价值,将人视作五行秀气所生,视作天地之心:“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36)陈澔注,金晓东校点:《礼记》,第259-261页。儒家区分人与万物的不同价值。《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7)章诗同:《荀子简注》,第85页。水火有能量但没有生命,草木有生命但没有知觉,禽兽有知觉但没有道义。人则有能量有生命有知觉有道义,因此在万物中最有价值。程颢、朱熹均肯定动物具有一定程度的“仁义”,而其与人的差别则在于动物“气昏”“推不得”,或者“偏而不全,浊气间隔”(3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册),武汉:崇文书局,2018年版,第42-43页。,也就是说动物虽有一定程度的仁义之性,但是对道德仁义缺少充分的自觉意识。在肯定人与万物不同价值的基础上,荀子、董仲舒甚而认为万物的价值就在于能够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如荀子强调“材官万物”,旨在“养人之欲,给人之求”(39)章诗同:《荀子简注》,第203页。。董仲舒认为天地产生万物的目的是为人所用,如说:“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40)董仲舒:《春秋繁露》,第46页。荀子、董仲舒的这些观点与西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观念颇为类似。
陈炎将儒家“爱有差等”思想概括为一种同心圆模式:“儒家的这套融人伦与自然于一体的生态观念,就像一块石头投入水中而引起层层涟漪一样,由宗亲到国人,由华夏到夷狄,由动物到植物,直至波及到无机物。越是接近圆心的部分,波纹越高,爱的能量也就越大;越是远离圆心的部分,波纹越小,爱的能量也就越小。……从理论上讲,儒家这种由内向外、推己及人的爱是没有止境的。但是,正像波的延伸距离有限一样,人的爱能也不是无限的。于是,在渐行渐远的扩散之中,水的波纹总会消失,人的爱意也总会消散的。从积极的方面说,儒家的生态观有着实用性、灵活性、全面性的特点。从消极的方面说,这套生态观又有着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特点。”(41)陈炎、赵玉:《儒家的生态观与审美观》,《孔子研究》2006年第1期,第7页。儒家“爱有差等”观念体现了儒家价值观的人本主义倾向,儒家虽然肯定关爱自然万物,但它更关注的是人自身利益的实现;同时,儒家“爱有差等”观念又体现了儒家价值观的宗族特征,这体现在它主张每个人对他人的关爱,应将自己的亲人放在优先位置。就此而言,陈炎谓儒家“爱有差等”观念具有实用性、灵活性、全面性,具有功利主义、机会主义特点,是切中肯綮的。
儒家高扬人自身的价值,在仁爱万物方面主张“爱有差等”,围绕这些观念,学术界有关于儒家是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而白奚所谓儒家生态伦理是一种“以道义为中心的人类中心论”的观念颇为学术界认同(42)白奚:《儒家的人类中心论及其生态学意义——兼与西方人类中心论比较》,《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2期,第22页。。不过,将儒家视为人类中心主义的说法,误解了当代生态文化思潮中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概念。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人与自然万物分离对立基础上的观念,它将人的价值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将自然万物视作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认为自然万物只具有满足人自身物质生活需求的工具价值。显然,儒家人本主义观念与人类中心主义有本质的区别:首先,儒家在肯定人自身价值的同时,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一体性,并没有将人与自然万物对立起来;其次,儒家虽然肯定对自然万物的利用,但又强调“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强调将仁爱之心拓展到天地万物乃至草木瓦石;再次,儒家高扬的人的主体性,不是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的主体性,而是继善成性,效法自然生生之德,赞天地之化育,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德性主体性,更强调的是实现自然万物价值,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正如蒙培元先生所说,儒家“所谓主体,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为目的的德性主体,不是以控制、征服自然为目的的知性主体,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然为‘非我’、‘他者’的价值主体”(43)杜维明、蒙培元、郑家栋、李存山、卢风、雷毅:《儒家与生态》,《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1期,第8页。。
三、“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实践
在儒家生态实践中,德性修养占据重要位置,《中庸》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44)陈戍国:《四书校注》,第38页。,实际上阐明了儒家通过德性修养实现其“赞天地之化育”生态理想的方式与路径,而与此相关的至诚、无私、识仁、感应、大清明等德性也因而具有生态实践意义;儒家生态实践在社会层面,又体现为一种生态治理实践。儒家生态实践主要是适应古代社会渔猎、农业生产的产物,因而儒家生态治理实践主要体现为对渔猎及农业生产的社会治理。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家生态治理法则主要是复述古代社会治理法规的相关内容,因此,《礼记》《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著作记载有大体类似的内容。儒家生态治理实践主要包括以礼义治理天下的生态治理,以及设置相关官职、制定相应制度等生态政治两方面。以下我们从生态修养实践、生态治理实践两方面具体论述。
(一)“存性事天”的生态修养实践
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实践关系上,儒家强调德性修养的重要性。如将天地生长化育万物视作“天地之德”,强调主体效法、培养天地的“仁德”,成就万物,赞天地之化育。《中庸》说:“仲尼……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45)陈戍国:《四书校注》,第47页。孔子顺应天地,具有“天无不覆,地无不载”之德性,能令万物和谐共生。二程从“忠恕”阐明圣人效法天地之德:“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变化草木蕃,不其恕乎!”(46)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92页。认为“忠”即是“诚”,即效法天地生物之德。“恕”即“将此放顿在万物上”,是将“忠”应用于万物,尽物之性,令万物繁茂。不管是《中庸》强调效法天地之德,还是二程强调诚于天地之道,施仁恕于万物,均体现了儒家生态实践突出德性修养的特征。
关于如何通过德性修养,实现自身的生态理想,《中庸》阐明了“至诚→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的德性修养路径。这里所说的“性”是指人与万物从天地禀受的真实无妄的本性。所谓“尽其性”,即借由“至诚”,体察、实现自身所禀受的天赋本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则是在“尽其性”基础上,体察、帮助他人、万物实现其本性。关于“能尽”,朱熹阐释说:“能尽之者,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47)朱熹撰,梁振杰注说:《大学中庸集注》,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页。即强调体察、明了和处置得当。关于“尽物之性”,朱熹阐释说:“鸟兽草木有多少般样,亦莫不有以全其性而遂其宜。”(48)朱熹:《朱子语类》(第4册),第1179页。即让鸟兽草木的自然本性和目的得到充分实现。可见,“尽物之性”蕴含有借由主体至诚无私的德性修养,令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生,令其本性得到真实而完整的实现的内涵。就此而言,“尽物之性”与当代生态伦理保障万物生长、发育、繁衍等生存权益的观念相一致。“赞天地之化育”则是在“尽物之性”“成物”的基础上,从天地的高度阐明主体德性修养的目标。朱熹认为天人各有自身的职分,“若以其分言之,则天之所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49)朱熹:《朱子全书》(第6册),第596页。,因此人可以通过自身的智慧、行为实践辅助天地化育万物。朱熹也将“赞”阐释为《易传》中所说的“财成辅相”,即“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所谓“财成辅相”即在体察天地之道的基础上,教导百姓耕耘灌溉,播种收获。而所谓“与天地参”,则突出了人与天地并立,与天地共同化育万物,促进万物和谐有序的地位和作用。
《中庸》所阐述的“至诚→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德性修养路径,突出德性修养对于实现辅助天地生长化育万物生态理想的重要性,其中蕴含有强调主体“至诚”德性、体察人与万物本性的智慧、恰当处理人与万物关系的“义”(“遂其宜”)之德性在生态实践中重要性的内涵。在生态理想实现的路径方面,儒家大体遵循由内修己身,到拓展自身伦理关怀到他人、万物、天地的理路。这里所说的“赞天地之化育”带有关注包含万物在内的整体生态系统的意味。这一理路大体上与《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拓展理路相一致,体现了儒家德性伦理以自身德行修养为根本的观念。儒家生态德性修养路径不断拓展自身伦理关怀范围的理路,也与当代生态文化思潮将伦理关怀范围由人自身,拓展到其他生命,再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历程相一致。这也体现了人类伦理自觉、关怀范围不断拓展的基本规律。
儒家诸多德性的培养与生态环保相关,除上文所述生态德性修养路径中蕴含的“至诚”、体察智慧、“义”等德性之外,儒家思想家还将“仁恕”“孝”“大清明”等德性与生态环保联系起来。儒家生态德性从不同角度划分,又大体上可以划分为超越的德性与具体的德性、偏重于道德的德性与偏重于智慧的德性等。超越的德性包括超越具体事物层面的天地之德,如至诚、无私,及“大清明”的整体性智慧;具体的德性是指直接面对万物的仁恕、义、孝、体察等德性。体察、“大清明”偏重于智慧,而至诚、无私、仁恕、义、孝偏重于道德伦理。
儒家生态德性具有多方面的生态环保意义:
第一,在儒家思想中,“至诚”是相对于“人欲之伪”,相对于人的自私、虚妄而言的,因此至诚与无私是相互关联的生态德性。在朱熹看来,只有“至诚”“尽性”而“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才能真正默契“天地之化育”(50)朱熹撰,梁振杰注说:《大学中庸集注》,第166页。。“至诚”是儒家生态德性中的根本德性,与天地之德相应,是对天地之德的效法,是对天地自然规律的顺应。“至诚”又是儒家其他生态德性的根本、基础。如上文所说,“唯天下之至诚”,方能“体察”人与万物的本性,方能恰当处理人与万物关系(“义”);至诚方能效法天地“生生之德”,方能“仁恕”天下万物……也正因为在“至诚”的基础上,才能顺应天地自然节律,才能体察人与天地万物的本性,恰当处理人与万物关系,才能帮助自然万物实现其本性,实现天地生长化育万物的目的,因此从中不难看出“至诚”德性的生态环保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至诚”是一种客观求实的精神,是一种尊重自然、尊重生命的精神。这也是我们今天生态文明建设所必需的根本精神。
第二,“仁恕”是儒家生态德性的重要方面。“仁恕”体现在生态环保上,即是关爱万物,让万物的本性得到充分实现。“仁恕”是“至诚”在对待自然万物态度上的具体体现。从前文所述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我们不难认识到“仁”在儒家生态德性中的地位,认识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中蕴含的对鸟兽的“不忍之心”、对草木的“怜悯之心”乃至瓦石的“顾惜之心”。“恕”则突出的是克制人的自私贪欲,尊重自然万物本性,让其本性得到充分实现。体现在行为实践上,则是在利用自然万物时,强调顺应自然万物生长的季节性规律。应该指出的是,儒家没有像佛教一样完全禁绝杀生,而是主张在动植物生长季节,禁绝砍伐、捕猎。“仁恕”德性中体现的关爱自然万物,尊重万物本性,让万物本性、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的观念,对于我们今天形成自觉爱护自然万物,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观念和风俗习惯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在儒家德性中,“仁义”常常连用。同样,“义”也是儒家生态德性的重要方面。“义”体现在生态环保上,即“处之无不当”“遂其宜”,即根据自然万物的本性,正确处理万物之间、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从正确处理万物之间的关系而言,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即实现万物的和谐有序、共生繁荣。从正确处理人与万物的关系而言,则是正确处理人的利益与万物生长、发育、繁衍等生存权益之间的矛盾。这要求我们一方面不应单纯从人自身的利益出发,无节制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另一方面也不应将人等同于万物,奉行生态中心主义。在这方面,儒家主张根据动植物生长季节利用自然资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51)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孟子》,第5页。。这是“义”之德性在生态环保方面的具体体现。显然,儒家“义”之德性对于我们正确处理人的利益和动植物生存权益,对于我们正确评判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观念有借鉴意义。
第四,“孝”在生态德性中,突出的是对自然万物的“诚敬”。如《礼记·祭义》中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52)陈澔注,金晓东校点:《礼记》,第544页。如果不按照动植物生长节律砍伐一棵树,捕杀一只野兽,都不能算作“孝”,实际上是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应秉持诚敬的心。如果说“恕”“义”突出的是让自然万物实现自身的本性,得到适宜的生长、发育、繁衍的话,“孝”强调的则是主体在利用并面对自然万物时,应秉持诚敬的心。从这方面来说,“孝”是保证自然万物本性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孝”之德有助于培养人们时时处处尊重万物、正确利用万物的诚敬心。
第五,“体察”在儒家思想中,是指主体对人与万物本性的体察。“体察”并不是儒家思想家所用的字词,但儒家思想家常用不同的词汇表达这一德性。乔清举教授将其称之为“生态良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感应’、张载的‘体’、程颢的‘觉’、程颐和朱熹的‘生’、王阳明的‘感应之几’、谭嗣同的‘通’,都是生态良知。”(53)乔清举:《儒家生态文化的思想与实践》,《孔子研究》2008年第6期,第15页。前面说过,《中庸》所谓“尽性”蕴含有对人与万物本性的体察,这里所说的“感应”“体”“觉”“感应之几”“通”等,说的均是主体对人与万物本性体察的智慧。“体察”与通常所谓认识不同,它是以自身生命感应他人万物的生命,是自身生命与他人万物生命的相通。“体察”是德性主体关爱人与万物的基础。只有体察到人与万物的本性,才谈得上仁爱万物,实现人与万物的本性。“体察”德性的培养,要求人的自身生命、直觉、情感的全身心投入和参与。儒家对“体察”德性的强调,对于我们今天培养主体的生态觉悟、生态情怀等具有多方面启迪意义。
第六,“大清明”则是儒家体察、治理天下万物的整体性智慧。“大清明”是《荀子·解蔽》在吸收融合道家“虚壹而静”思想基础上阐明的治理天下的整体性智慧:“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54)章诗同:《荀子简注》,第233页。认为治理天下必须建立在“大清明”的智慧基础上。荀子关于“虚壹而静”及“大清明”的阐释,主张将道家“虚壹而静”的修养法则与关于天地万物的认识及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整体性智慧。借由这种智慧,人们能够从天地整体考察事物,使万物发挥各自的功用;能够通晓自然及社会发展规律,进而经纬天地,治理万物(55)陈红兵:《儒家生态哲学思想要论》,《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44页。。儒家“大清明”的整体性智慧的生态意义主要体现在,它要求决策者应有清醒的头脑,整体考察“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的状态、规律、趋势,从生态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出发,协调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利益、矛盾,促进“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
(二)礼治天下的生态治理实践
儒家强调以礼义治理天下。而以礼义治理天下,其中也包括通过社会治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序的内容。《荀子·王制》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使下谓之君。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56)章诗同:《荀子简注》,第85-86页。肯定以礼义治理天下,不仅能够协调家庭及社会伦常秩序,而且能够使“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实现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有序。
儒家还从存在论意义上强调礼义源于天地,以论证礼治天下的合理性。《左传》载:“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57)左丘明撰,蒋冀骋标点:《左传》,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44页。“天之经,地之义”是礼的本质,是百姓应遵循的天地法则。圣王之所以制定礼仪规范,是为了维护天地的秩序,以免百姓丧失本性。《荀子·礼论》亦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58)章诗同:《荀子简注》,第205页。肯定天地是礼的重要根源,也因此要求礼治天下必须建立在“尊事”天地基础上,实际上即强调以礼义治理天下应当遵循天地自然规律。
祭礼是礼的重要方面。儒家从“报本反始”的角度阐释祭礼的产生及其意义。《礼记·郊特牲》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59)陈澔注,金晓东校点:《礼记》,第297页。《国语·鲁语》在阐释祭礼的来由时也阐述了“报本反始”的内容:“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60)左丘明撰,韦昭注:《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天地山川是人们衣食生活的来源,人们祭祀天地山川,是为了表达自身的崇敬、感恩之情。
儒家文化中包含祭祀山川动植物多方面的祭祀之礼。(1)祭祀土地山川。中国很早就有设坛祭祀土地的风俗。根据《礼记》的说法,立社是为了祭祀土地,教导百姓“报本反始”,报答天地。《尚书·舜典》提出“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61)冀昀主编:《尚书》,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10页。,这里所说的“六宗”是指天宗日、月、星,地宗岱山、河、海。这句话意思是说君主应当祭祀天地、山川,遍及群神。(2)祭祀动物。儒家文化肯定一些动物具有神性,如龟龙麟凤,应当祭祀;还有一些动物如猫、虎、虫对于农业生产非常重要,是蜡祀的对象。(3)对植物的祭祀。在儒家文化中,山林属于祭祀的对象。《周礼》中大宗伯主持的祭祀活动有一项是祭祀山林。根据《礼记》的说法,山林之所以应当祭祀,是因为:“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62)陈澔注,金晓东校点:《礼记》,第526页。实际上直观认识到山林、川谷等所具有的调节气候、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63)乔清举:《儒家生态哲学的基本原则与理论维度》,《哲学研究》2013年第6期,第65页。。儒家祭祀山川动植物的祭礼,体现的是对山川动植物的感恩、崇敬之情,这对于提醒、培养人们爱护自然万物的情感具有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除了祭祀山川动植物之外,与生态环保相关的礼仪,还有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籍田礼、蚕桑礼等。《礼记·月令》记载:“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64)陈澔注,金晓东校点:《礼记》,第173页。籍田礼即在孟春正月,春耕之前,天子率诸侯亲自耕田,以祈风调雨顺,年谷丰登的典礼。籍田礼渊源于远古时期部落首领带头耕种,然后才开始大规模春耕生产的古俗。蚕桑礼则是王与诸侯亲自参与祈蚕桑仪式,并由后妃夫人入蚕室,表示亲自从事蚕桑之事;亲自缫丝,表示亲织……以此号召民众重视蚕桑事业。籍田礼、蚕桑礼等礼仪对于提醒人们重视农业生产,感恩天地自然,按照季节时令从事农业生产,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礼治天下还包含以礼义节制人们的行为实践的内容。这方面内容往往带有禁制、制度的性质。以下我们从生态管理官职设置、相关生态环保禁令等方面具体阐述。
先秦时期,我国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生态管理官职设置。根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先秦设置的与生态环保相关的官职,有掌山之政令的“山虞”,掌管泽之禁令的“泽虞”,掌管林之禁令的“林衡”,掌管川之禁令的“川衡”,掌管田野狩猎之禁令的“迹人”,掌管矿之政令的“矿政”等等。其中,山虞的职责是:“掌山林之禁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抡材,不禁。凡窃木者,有刑罚。”山虞掌管有关山林的政令,为山中的各种物产设置藩界和禁令加以守护。规定不同季节砍伐不同方位的木材,百姓上山砍伐木材要按照一定的时节,政府工匠入山选择木材不受此限制,偷砍林木的则要受到刑事处罚。林衡的职责是“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计林麓而赏罚之”。林衡掌管巡视平地和山麓的林木而执行相关的禁令,合理安排守护林木的民众,按照他们守护林木的成绩进行赏罚。迹人的职责是:“掌邦田之地政,为之厉禁而守之。凡田猎者受令焉,禁麛卵者,与其毒矢射者。”迹人掌管王国田猎场所的政令,为之设置藩界和禁令加以守护,凡进行田猎均要接受迹人的安排。禁止猎杀幼兽和掏取鸟卵,禁止用毒箭射猎。其他关于川衡、矿人等官职的职责,《周礼·地官司徒》中均有介绍。从中可以看出,相关官职的设置,旨在根据山川动植物的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资源不被破坏。
先秦时期还形成了较完备的生态环保禁令,而这些禁令大多与“谨其时禁”相关。这是因为古代渔猎、农业社会的生活资源主要是来自自然界的动植物,而这些动植物资源有自身的自然生长节律。所谓“谨其时禁”,即要求砍伐树木、捕食渔猎、种植五谷等应根据动植物生长的季节规律,在动植物生长季节禁止砍伐、渔猎,按照植物生长季节从事农业生产(65)陈红兵:《儒家生态哲学思想要论》,《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43页。。《礼记·月令》对不同季节相关禁令有较具体的规定,如“(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即孟春时节禁止砍伐树木。不许捣毁鸟巢。不许杀害幼虫、幼兽、幼鸟、怀胎的母兽,不许捕捉小兽和掏取鸟卵。不得修建城郭。“(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仲春时节不要把川泽的水用光,不要使池塘干涸,不要焚烧山林。“(季春之月)田猎罝、罘、罗、网、毕、翳、喂兽之药,毋出九门……。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季春之月打猎用的捕兽的网、捕鸟的网、长柄小网、隐蔽自身的工具、为野兽准备的毒药,一概不准带出城门。……命令主管田野山林的官员禁止人们砍伐桑树柘树。“(孟夏之月)是月也,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 孟夏四月,草木更加茁壮高大,不要使它们有所毁坏。不要大兴土木,不要征发百姓,不要砍伐大树。……要驱赶野兽使其不危害庄稼,但是不要举行大规模田猎。“(季夏之月)是月也,树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不可以兴土功。”(66)陈澔注,金晓东校点:《礼记》,第174、177、180、183、190页。季夏六月,树木生长旺盛。应命令主管山林的官员入山巡视林木,严禁砍伐。不可以大兴土工。《荀子·王制》亦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67)章诗同:《荀子简注》,第86页。草木正在生长的时候,不能砍伐草木;鱼鳖之类怀孕产卵的时候,不能到湖泽中捕鱼、投毒药。春夏秋冬按照季节从事农业生产,池塘河流严格禁止在规定时期内捕捞,树木的砍伐与长养不错过季节,五谷、鱼鳖、山林才会得到充分的生长,百姓才会有充裕的生活资源。这突出的是在动植物生长季节禁止砍伐草木,捕捞鱼鳖,按照农作物的生长节律从事农业生产。传统社会注意适应不同季节动植物生长规律,制定相应的禁令,旨在保护动植物及山川土石等自然生态环境,维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四、儒家生态思想文化的意义与局限
儒家生态思想文化是一种前现代生态观念,它主要建立在农业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基础上。农业社会因生活资源、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如四季变化、土壤肥瘠等依赖性较强,因此较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内在生命关联,将人与天地万物视作相互关联的有机统一整体,要求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肯定其他生命存在的价值,在尊重其他生命生长发育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人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儒家生态思想文化对于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多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其一,儒家生态思想强调天地生长化育万物的过程是一个创生生命的过程,将人与天地万物视作统一的有机生命整体,是一种有机整体论的世界观。在此基础上,儒家强调人应继承天地自然的“生生之德”,担当起“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的责任,实现天地生长化育万物的目的,从而将生态伦理建立在甚深的存在论基础上。儒家有机整体论的世界观,以及将生态伦理建立在存在论基础上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建构生态整体论世界观具有深刻的启迪价值。
其二,儒家重视德性修养在生态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主张通过德性修养达致“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儒家一方面肯定人的主体性价值,肯定人与自然万物具有不同的价值,主张对人与万物应施以不同的关爱,但另一方面又将人的价值纳入天人一体性关系中考察,将“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视作道德伦理责任,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视作人应达致的理想境界,因而避免了西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迷误,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解决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争端具有借鉴意义。
其三,儒家重视生态德性修养实践,阐述了“至诚→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的德性修养路径,并注重至诚、仁恕、义、孝、体察、“大清明”等生态德性的培养与教化。儒家生态德性修养实践,对于我们今天重视生态伦理教育,重视培养人们生态道德,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儒家注重社会政治层面的生态治理实践,重视祭祀土地、山川、动植物的礼仪,为农业生产举行的籍田礼、蚕桑礼等,对于培养人们尊重自然、感恩自然、爱护自然万物的情感,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传统社会相关生态环保官职的设置,生态环保制度的建设,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相应的生态管理制度仍有启发价值。
儒家生态思想文化作为一种前现代生态思想文化,也存在自身的思想局限。这是因为,儒家生态思想文化主要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其思想观念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和个体自身的生命体验,对自然万物及其内在关联的认识有待于现代生态科学的充实和完善。此外,当代生态哲学的产生,根源于今天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在古代社会,生态环境危机远没有今天如此严重和紧迫,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并没有形成今天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思想文化,儒家生态思想文化主要还是从当时的社会治理实践和主体自身德性修养实践出发的推演。
儒家生态思想文化的思想局限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儒家生态思想将天地生长化育万物的过程视作创生生命的过程,将人与天地万物视作统一的生命整体,儒家生态思想对天地“生生之德”的关注,对“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理想境界的追求等等,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经验和人自身生命体验基础上的直观认识。这些认识停留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直观,对自然界创生生命的内在机制及具体过程等缺乏科学、明晰的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利科特认为古代生态整体论世界观根本不能像今天量子力学和生态学那样,解释自然整体内部的复杂深刻的有机联系,而只是一种直观思维的表象(68)J. B. Callicott, Earth’s Insi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69.。因此,儒家生态世界观要适应今天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应吸收融合生态科学、复杂性科学以及当代生态存在论的思想成果,充实自身关于存在关系性、过程性、整体性的认识。
其二,儒家生态思想偏重于从主体自身的德性修养,阐释人在天地万物中的作用、价值和地位,阐释生态理想,往往使德性修养主体忽视关注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寻求其现实解决途径。如儒家将生态理想阐释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精神境界,在生态实践上,突出主体内在道德伦理关怀范围的拓展,突出主体自身生态德性的修养对于生态环保实践的价值。儒家生态德性思想当然具有自身独特的生态意义,但是其思想局限也是明显的:过多关注主体自身的德性修养,容易忽视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客观上必然限制其影响社会的力度和范围。
其三,儒家生态实践注重社会政治层面的礼义治理方式,以及相关生态环保官职的设置、制度建设,相对偏重于发挥政府在生态环保中的作用,而发挥民间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的作用不够。生态环境建设本身包含多方面内容,而社会也有自身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它要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协同运作。在今天,发挥民间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通过种种方式对民众进行生态环保教育,正变得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