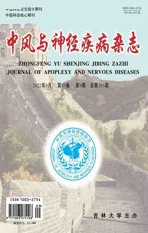微血管功能障碍与认知障碍
2022-11-19蒋春彦综述张清华杜怡峰2审校
蒋春彦综述, 张清华, 杜怡峰,2审校
微血管疾病是一组由多种病因引起的,可累及全身多个系统的血管疾病综合征。随着年龄增长,血管硬度增加,血管壁对脉冲压力的调节能力下降,导致动脉压力过度转移到微血管系统,微血管阻力增加,心、脑、肾和视网膜等高流量低阻力器官尤其容易被累及。认知功能障碍是老年人主要的健康问题之一,发病率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而增加。然而,认知功能障碍的机制尚不明确。研究发现,微血管功能障碍(microvascular dysfunction and damage,MVD)可能介导了血管性危险因素对认知功能的损害。研究两者关系对了解认知损害的病因和机制有重要作用。本文主要是对微血管功能障碍的定义、评价方法及其与认知障碍的关系进行综述,以期为认知功能障碍的研究提供新见解。
1 微血管功能障碍
微血管在解剖学上主要是指通连小动脉和小静脉间的细小血管,分支连接成网,又称为终末血管床。微循环在机体环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在调节或维持体内环境恒定、全身血流动力学和组织代谢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目前,关于MVD的定义和分类尚无统一定论。MVD主要是指一组由多种病因引起的,累及全身多个系统的,对小动脉、微动脉、微静脉和毛细血管造成损伤或者阻塞,进而影响组织灌注的血管疾病综合征[1]。MVD与基因、肥胖、衰老、高血压、糖尿病、心理压力和代谢综合征等多种因素有关[2]。不同器官的MVD病理机制不尽相同,但存在重叠性,研究认为MVD的发生是以内皮功能障碍为基础,炎症因子风暴、氧化应激反应以及细胞稳态失衡相互作用,造成微血管功能、管径和密度的改变,最终导致血管阻塞和组织灌注减少而产生的一系列病理变化过程[3]。
随着科技进步,现可使用多种无创技术评价各个脏器微循环功能和结构改变,如血浆生物标志物评估全身微血管损伤情况;磁共振成像技术评价脑小血管病(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CSVD);视网膜微血管动态和静态成像技术[4];尿白蛋白排泄率(urinary albumin excretion,UAE)和胱抑素C水平等评价肾微血管功能[5];经胸超声冠状动脉血流显像(transthoracic doppler echocardiography,TTDE)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等技术评价冠脉微血管功能;此外,还可以通过皮肤激光多普勒血流仪和皮肤毛细血管镜以及舌下微循环显微镜等技术评估微血管内皮功能情况[6]。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人体和动物实验模型中[7],血管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年龄相关的微血管稳态损害,包括肌源性自我调节机制的改变,使老年大脑更容易受到高血压等共病引起的损伤。MVD在认知障碍的进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充分认识血管与认知的关系的至关重要。
2 阿尔茨海默病
神经退行性病变是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最具代表性的疾病是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 disease,AD),多发生于老年和老年前期、以进行性认知功能障碍和行为损害为特征,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给社会和医疗卫生服务带来巨大负担[8]。阿尔茨海默病典型的病理改变是淀粉样蛋白沉积、神经元纤维缠结和神经元丢失,确切的病理机制迄今尚未阐明。众所周知,大血管缺血性疾病和脑出血可直接影响认知功能,然而,不仅仅是大血管疾病可能会对大脑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微血管功能障碍可能是AD早期病理事件之一,甚至早于脑内β淀粉样蛋白(β-amyloid,Aβ)沉积[9,10],是导致认知功能减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研究认为年龄相关的胰岛素样生长因-1缺乏会损害神经血管单元,损害星形胶质细胞、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的功能[11]。老年高血压患者(尤其是长期高血压患者),在衰老、氧化应激和炎症的作用下,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receptor for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RAGE)表达上调,加之,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受损,血管紧张素-Ⅱ1型受体激活增加会导致RAGE信使核糖核酸表达增加,过多地介导Aβ从血液转移到大脑;另外,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1(low-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 related protein-1,LRP-1)表达下调,维持血脑屏障(blood brain barrier,BBB)完整性的能力下降,Aβ从大脑运输到血管相对减少(与RAGE的方向相反);内皮细胞是血管功能和结构以及炎症的主要调节因子,也是BBB的细胞部位[7]。高血压损伤内皮功能表现为可溶性血管内皮粘附分子-1(soluble 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sVCAM-1)和可溶性细胞内皮粘附分子-1(soluble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sICAM-1)水平升高,直接或间接地促进Aβ生成增多,清除减少,导致神经元损伤和认知能力下降。另一方面,AD病理还会加重微血管的损伤,例如,糖尿病状态下胆固醇代谢异常可以通过增加Aβ的生成,Aβ在脑微血管壁上沉积而损失脑微血管。关于AD、神经血管单元功能障碍和其他血管危险因素之间的分子机制在其他文献中有深入的讨论[12]。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神经血管调节受损与认知的关联。
3 微血管功能障碍与认知
目前的研究认为在微血管功能障碍与认知的关系中,可能涉及的全身病理机制包括内皮功能障碍、炎症反应、氧化应激和凝血/血栓形成不平衡等多个方面[3,13]。
随着年龄的增加,血管内皮完整性的破坏会增加BBB的渗透性,导致直接的神经毒性,髓鞘受损和纤维蛋白沉积[14]。炎症因子,如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白细胞介素-6(interkleukin-6,IL-6)、白细胞介素-8(interkleukin-8,IL-8)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TNF-α)等可加重内皮功能障碍;粘附分子、免疫调节、氧化应激和凝血系统的激活,造成微血管的功能和结构损伤,脑微循环稳态失衡。另外,氧化应激与炎症因子和细胞因子水平相关,脑内皮细胞活性氧产生增加会刺激炎症因子和细胞因子的释放,导致神经炎症。神经炎症、胶状淋巴细胞功能障碍和/或脑微血管损害的加重与高血压等血管危险因素引起的认知障碍有因果关系。
由此可知,全身的MVD可能参与了神经血管单元、大脑自我调节、血脑屏障通透性和神经生成等许多大脑调节过程,这些过程的早期损伤可导致神经元功能障碍、缺血和细胞死亡,从而导致认知功能障碍。
两项大型的队列研究表明,微血管综合指标与较低的认知功能得分有关(特别是在精神运动速度和工作记忆方面)[15,16]。但目前对于MVD单一指标与认知功能相关性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所以,本文主要是对几个关键脏器血管床的微血管功能障碍与认知的关系进行总结,提高我们对两者的认识。
3.1 脑小血管病与认知 脑组织缺乏能量储备,微循环阻力的调节是维持脑部局部血流充足的关键,大脑的最佳功能依赖于健康的微血管系统。脑微血管内皮功能障碍主要包括BBB功能障碍、血管舒张受损、血流和间质液引流功能障碍、白质稀疏、缺血、炎症、髓鞘损伤和继发性神经变性[17]。
脑小血管病常见的病因学分类主要是小动脉硬化性、脑淀粉样血管病、遗传性脑小血管病(区别于脑淀粉样血管病)、炎症和免疫介导的小血管病、静脉胶原病和其他小血管病等[18]。由于脑部结构可视化的问题,脑小血管病是一个用来描述与脑微血管障碍相关的病理、神经影像学和临床特征的术语。脑MVD在影像学上可表现为典型CSVD的特征,包括近期皮质下小梗死、脑白质高信号(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y,WMH)、脑微出血、腔隙、血管周围间隙和脑萎缩[19]等能够间接反映微循环功能。
对289例记忆门诊患者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CSVD综合评分与蒙特利尔认知评估得分存在负相关。白质高信号、微梗死等与认知功能损害密切相关,与AD病理(尤其是侧脑室周围WMH、顶叶WMH、皮质微出血)显著相关,并且与AD风险增加显著相关[20]。另外,对1201例中老人的血浆Aβ水平和比率分析,表明较高水平血浆Aβ水平和比率与腔隙和微出血计数增加相关。在遗传性脑小血管病中,脑淀粉样血管病与APOE基因型和Aβ在皮层中的沉积相关;Notch 3突变导致皮质下梗死伴白质脑病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脑动脉病(cerebral autosomal dominant arteriopathy with sub-cortical infarct and leukoencephalopathy,CADASIL),符合原发性血管细胞缺陷伴随衰老引发的小血管疾病(脑血流灌注失调、细胞损伤和认知功能下降)[21],法布里病是一种心脏、肾脏、皮肤等多系统疾病,在脑组织与白质高信号相关,可以导致认知下降;遗传性胶原蛋白病,如Ⅳ型胶原突变可导致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微动脉病和白质脑病。
在瑞典的社区老年纵向人群研究中,调整混杂因素后做中介分析,发现WMH体积的变化对微血管病变负荷与认知功能下降(简易精神量表得分低)的介导作用是66.9%,这表明了脑微血管病变与随后的认知功能下降之间的联系可归因于脑微血管病变的进展[22]。研究发现WMH通常发生在白质中,而腔梗通常发生在深部灰质中。白质高信号和腔梗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可协同加剧认知功能的损害。总的CSVD负担评分可能比单独考虑1或2个个体特征更能反应CSVD对认知功能的影响。所以越来越多的研究提出了CSVD总评分/总负担的概念,以更加准确地捕捉来自脑小血管病的全部脑损伤。
3.2 眼底微血管与认知 由于视网膜与脑组织具有相似的组织起源,解剖结构、血液供应和调节机制,可以认为视网膜血管是研究脑血管的窗口[23]。随着眼底血管成像技术的发展,视网膜微血管系统被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相关性的研究。视网膜微血管的检测方法主要包括视网膜眼底照相、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ngiography,OCTA)和动态血管分析(dynamic vessel analyzer,DVA)等[4]。在Heringa等[24]总结中,视网膜微血管变化与痴呆、认知障碍和脑成像异常之间存在相关性。对于更严重的视网膜微血管病变,相关性最强。
既往的研究多采用眼底照相技术,比如,在社区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研究的12317例老年人群中,发现血管完整性的丧失(视网膜病变及其组分)与20 y认知能力下降速度加快有关[25]。但在北爱尔兰老龄化纵向研究队列的1431例(平均62岁)人群中,未发现视网膜血管定量指标(小动脉/小静脉比值,分形维数和弯曲度等)与认知的相关性[26]。
OCTA作为一种新兴的非侵入性成像技术,可以显示不同层面的视网膜和脉络膜微血管结构。Bulut等[27]发现与26例对照相比,26例AD患者的视网膜毛细血管密度显著减少,视网膜中央凹无血管区(foveal avascular zone,FAZ)面积明显增大,这在后来的研究中多次被证实。但另一项对976例非痴呆的社区老年人研究中,未发现分形维数和FAZ与认知能力下降或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和痴呆的发生风险的相关性[28]。这可能与眼底微血管病变的进程,痴呆的异质性以及潜在的混杂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眼球轴长)等有关。另外,采用DVA技术可评估视网膜血管的舒缩功能。Querques等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MCI组和AD组动脉舒张显著减少。另外一项研究对12例AD、12例MCI和 32例对照的分析,发现仅AD组视网膜小动脉的反应扩张显著减少,并且未观察到OCTA所测得的血管结构指标在各组间的差异[29]。这表明视网膜血管的功能可能改变先于其形态改变,但目前的研究结果仍是不确定的,需要更大样本量的研究进一步明确[30]。此外,一些利用OCTA深度开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来研究眼底血管与认知的关系,还在探索之中。
总之,因为研究对象、视网膜血管和认知功能评估方法等不同,目前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大样本队列研究进一步探讨视网膜微血管改变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
3.3 冠状动脉微血管功能障碍与认知 心脏与脑组织一样,缺少能量储备,冠脉微血管在调节冠状动脉血流量以响应心脏氧气需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冠状动脉微血管功能障碍(coronary microvascular dysfunction,CMD)是指血管舒张功能受损或冠状动脉微血管痉挛,导致血流储备的减少,引起CMD。CMD的诊断基于微循环的功能,可以通过冠脉血流储备和微血管阻力指数的测量或冠状动脉内乙酰胆碱输注诱发的心绞痛等有创的方法以及通过PET和心脏磁共振评估心肌灌注等无创的方法评估[31]。
既往研究证实CMD是涉及大脑和肾脏等多个器官的全身性微血管疾病的证据。CADASIL患者存在冠状动脉微血管功能受损,Notch 3突变携带者可能会增加早期急性心肌梗塞的风险,表明CADASIL可同时累及心脏和大脑[32]。另外,心脏功能的分级下降与脑老化有关,较低的心输出量与脑体积下降及认知功能损害显著相关,并且与MCI或痴呆的风险增加相关[33]。CMD患者更容易出现认知障碍,但CMD患者中认知障碍的患病率尚不清楚,需要进一步系统性研究小血管疾病的心脑联系[34]。
3.4 微血管功能障碍的血浆生物标记物与认知 内皮细胞可降低血管张力,维持血管通透性,抑制血小板粘附和聚集,限制凝血系统的激活,刺激纤维蛋白溶解等。所以,内皮细胞是保持微血管功能完整性的基础。当内皮细胞功能发生改变而对器官功能产生不利影响时,可以认为内皮细胞功能障碍[35]。
目前主要通过血浆中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on Willebrand Factor,vWF)、可溶性细胞粘附分子(cell adhesion molecules,CAMs)水平等来评价内皮功能。微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和炎症状态被认为是联系血管危险因素和痴呆的关键途径。有研究显示Aβ能够诱导CAMs介导的炎症级联反应,并通过损伤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引起BBB功能障碍。霍恩研究纳入377例非痴呆老年人,证明炎症指标和内皮功能障碍指标均与较差的认知功能评分(信息处理速度,注意力和执行功能)显著相关[36]。利用阿尔茨海默病神经成像计划数据的研究发现AD与sVCAM-1和sICAM-1水平升高显著相关;在临床痴呆评分总和模型中,sVCAM-1和脑脊液Aβ或Tau独立发挥作用,当添加到任何生物标志物时,有更强的加性效应[37]。在另外一项纳入110例AD患者和50例年龄匹配的对照的研究中,AD组sVCAM-1、sICAM-1、E-选择素(E-selectin)和P-选择素(P-selectin)均增加,但仅有sVCAM-1水平反映痴呆的严重程度。这说明虽然目前研究提示外周可溶性CAMs水平的升高与各种类型的痴呆显著相关,但在对痴呆预测价值方面,尚需研究进一步验证[38]。
在对心、脑、肾MVD血浆生物标记物的总结中还发现甘油三酯、CRP、胱抑素C、同型半胱氨酸、IL-6、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vWF和尿酸等均升高[3]。综上可知,多种MVD血液学指标相互交织,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更加关注作用于MVD不同机制的血浆标志物的综合指标,探讨其与认知的关系。
3.5 其他 此外,MVD还可累及其他脏器,如肾脏和皮肤等。与大脑一样,肾脏也是高流量低阻力的终末器官,对涉及不同机制的内皮功能障碍(氧化应激和炎症)敏感,血管容易受到损伤。肾脏MVD表现为肾小球损害,导致肾功能下降和蛋白尿,最终可导致肾功能衰竭。尿蛋白升高和肾小球滤过率降低与海马及灰质体积的下降有关,在认知障碍向痴呆的转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39]。马斯特里赫特研究发现尿蛋白水平与认知评分相关,年龄每增加10岁,UAE每增加一倍,总体认知评分下降3.1%,信息处理速度下降2.6%,执行功能下降3.4%[40]。血清胱抑素C浓度,也反应了肾微血管损害,研究发现血清胱抑素C水平与较低的神经心理评分相关[41]。
另外,皮肤被覆全身,位置表浅,其血管反应性变化常出现在某些疾病的早期阶段,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全身微血管功能,是评估微血管功能障碍的理想位点。目前可通过经皮氧分压、近红外光谱、热成像、激光多普勒、激光散斑对比成像、视频毛细血管镜等评估皮肤微血管内皮功能。但关于皮肤MVD与认知的相关性,目前研究结论尚不一致[42,43],可能与皮肤微血管病变进程、检测环境或检测部位有关,未来还需要更多大样本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两者的相关性。
4 总 结
综上所述,微血管功能障碍是一种全身性血管疾病综合征,多种机制和病理彼此交叉,相互作用,并且多个脏器MVD都与认知相关。所以,在未来的研究中,首先,应该关注微血管功能障碍综合指标的发展演变,建立一个更统一的MVD评价标准;其次,人群中的血管危险因素尚未得到很好的控制,涉及微血管机制的多种血管性疾病的与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抑郁、肥胖和痴呆等慢病密切相关,探讨微血管功能障碍对慢病的早期防治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最后,目前缺少微血管功能障碍与认知功能损害的纵向研究,纵向探索(纵向观察和干预研究)微血管功能与认知的关系,对揭示MVD如何促进AD的发展演变及寻找有效的AD干预靶点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