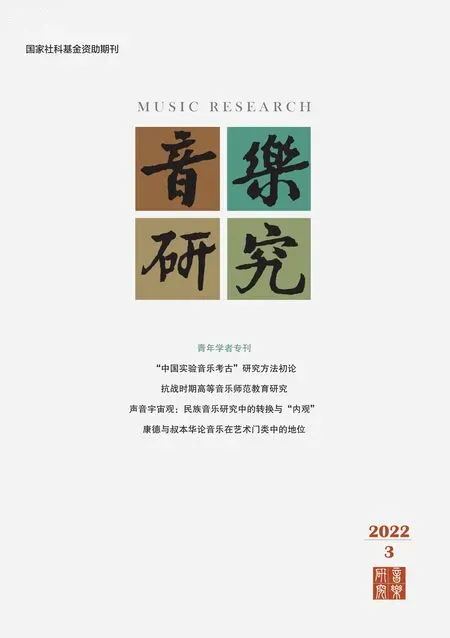声音宇宙观: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转换与“内观”
2022-11-18高贺杰
文◎高贺杰
引言:关于文化研究的声音“宇宙观”
所谓“宇宙观”,指的是一个文化群体对其自身所处世界(宇宙)的理解,以及自身与所处世界的关系与认识的总合。在现今的文化研究中,“宇宙观”常等同于“世界观”或称“宇宙论”(cosmology)等。在人文研究的论域中,更多的则是在文化学语境内阐述某一文化群体与自然及自身内外、部的关系与规律。
本文所讨论的声音“宇宙观”,①在本文语境中,声音(或音乐)“宇宙观”(Cosmology)等同于声音(或音乐)“世界观”,为行文之便,亦简化为“宇宙观”;与该术语平行的词汇还有universe,有时也译作“宇宙观”。是文化研究语境所讨论的某一特定民族(或族群、社区等)对于包括音乐在内的声音的文化观念————其核心是不同族群对于声音的感受。美国人类学家斯坦利·坦比亚(Stanley Tambiah)认为,一般而言,宇宙观“视天地万物或宇宙为一个有序的系统,根据空间、时间、物质,以及运动来对其描绘”②王爱和《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版,第2 页。。譬如,一般人们会将传统意义上中国人的宇宙观,归结为基于阴阳、五行等概念所关联构成的一整套包含自然与人文在内的文化系统。总的来说,宇宙观是一种从整体看个别,亦从个别观测整体的研究视角。在唯物论的认识立场中,任何关于自然的宇宙论问题同时也被哲学世界观所支配,没有单独存在的“宇宙论”。
一些学者在其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已不同程度地涉及音乐(或声音)宇宙观的问题。曹本冶在考量仪式音乐研究的基本架构时,就曾援引美国学者罗杰·基辛的表述指出:“宇宙观是一个民族对其所处之生态环境的构成……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的认知”③曹本冶《思想~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音乐艺术》2006 年第3 期,第92 页。。齐琨在对长江流域民间丧葬仪式音声的研究中,也对如何总结并定义“宇宙观”提出了相应的见解,她指出:由于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宇宙观又可被理解成一种“时空观”;同时,鉴于不同地理环境和自然面貌的差异与区别,宇宙观也呈现局内与地域性特征,“不同地方的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和观念存在差异,因此宇宙观为局内人所持有的。局内人的研究意义不在于证其真伪,而是理解为何局内人持有如此宇宙观。”④齐琨《音声表述的宇宙观————长江流域汉族聚居地丧葬仪式音声比较研究》,《音乐研究》2014 年第4 期,第84 页。在这里,研究者已探涉到宇宙观的内在实质,并对宇宙观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这两个底层维度有所考量;此外,研究者认识到,我们对于时间与空间的认识体系,以及对其的表达方式,也构成了我们的宇宙观表述。
声音宇宙观其含义是指:研究者尽可能不被自身既有的音乐及文化观念所“格式化”,并以符合研究对象自身文化逻辑的视野与认知体系,在除却“习以为常之弊”与本位文化逻辑影响的基础上,去感受并最终表达关于音乐文化内生事实的文化研究。
一、“分类”与“术语”————探寻“声音的观念”
如何探寻声音宇宙观?或者以怎样的步骤进入对声音观念的研究?这很难给出明确的标准答案。在研究不同文化体系中关于“即兴”这一音乐观念时,布鲁诺·内特尔曾这样总结自己的研究切入视角:“民族音乐学家们感兴趣的是世界各文化中音乐创作的分类法……他们同时希望能建立起自己的分类法作为比较研究的基础”⑤〔美〕布鲁诺·内特尔著,张明坚译,张娜整理《世界民族音乐中的即兴演奏观念》,《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 年第3 期,第3 页。。一般说来,对于音乐的分类问题,以及对相关音乐术语的解读,是研究者了解某一族群声音观念的一个好开端,同时,也是步入声音宇宙观最为便捷的途径之一。
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历程中,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已有许多研究者或从方法论层面,或以自身研究个案总结出发,提出了关于“声音的观念”的相应见解。例如,曼特尔·胡德关于“双重音乐能力”(bi-musicality)的概念,其本质就是希望研究者能够通过学习被研究对象的乐器,在演奏实践中体会“局内人”那些言传之外的音乐感受。民族音乐学所积极提倡的田野工作这一基本的学科作业方式与“方法论”,也是通过如局内人般的体会去感受他者的音乐文化,以达到理解与解释的研究目的。
需特别指出的是,“声音宇宙观”包含着不同的境界与层面,不能一概论之。一个族群对于声音的某种观念,也正是其“声音宇宙观”的组成部分。对于声音的感受方面的探索,斯蒂芬·菲尔德关于卡鲁里人的音乐人类学研究,或许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发。作者将自己的研究界定为“声音民族志”(ethnographic study of sound):“意在讨论卡鲁里社会有种种自然或人为的声音:鸟叫、哭泣、诗、歌曲等构成的象征系统……并揭示着卡鲁里人的民族精神(ethos)”⑥徐欣《声音·情感·世界观————评斯蒂芬·菲尔德〈声音与情感:卡鲁里人的鸟、哭泣、诗与歌〉》,《歌海》2011 年第3 期,第15 页。。
沈洽在《基诺族的音乐观念及他们的歌》一文指出:“‘歌’是‘音乐’的一个门类……但基诺人对于‘音乐’乃至‘声音’的理解和分类与‘主流文化’的分类观念不完全一致。”⑦沈洽、刘怡《基诺族的音乐观念及他们的歌》,《民族艺术研究》2001 年第3 期,第23 页。在经过一系列比对、探试、爬梳、分析之后,沈先生感慨,尽管很多在所谓的主流文化持有者的听觉判断中,基诺族对于不同动物、不同身份的人,以及巫师、“祖先”、神灵所沟通的具有表情功能与作用的声响,也符合我们一般认为的“音乐”,但基诺族对此却有着不同的分类标准与体系。安东尼·西格一直以一种学科视角,审视以往研究中将音乐与语言彼此分离的做法。在《苏亚人为什么歌唱》第二章,他专门论述了“苏亚人的口头艺术:从语言到歌唱”,开宗明义地指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应当从检视音乐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开始”⑧〔美〕安东尼·西格尔著,许硕文、高贺杰译《苏亚人的口头艺术:从言语到歌唱》,《大音》2010 年第1 期,第257——258 页。。这里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就是一种基于分类的类比性研究视角。作者详细论述了苏亚人是如何看待和区分“讲话”(speech)、“训导”、“歌谣”、“咒语”这些不同的“体裁”。由此使我们得以发现,在苏亚人的概念中,对于音乐的认识,哪些和我们相似,而哪些又极为不同。作者通过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研究模式予以解析,实现对苏亚人音乐文化的深层描述————这实际上也呈现了一种苏亚人的文化观念和音乐传统中的宇宙观。
毋庸置疑,分类研究在学术研究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涌现出了不少对于民族音乐研究对象分类观念进行研究的优秀案例,这些研究对我们进一步探究宇宙观有积极的启发意义。例如,何晓兵在对四川白马藏族民歌的考察中,通过国际音标注音与概念的辨析,探究了白马藏族的诸多音乐与文化观念。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关于音乐及文化的“宇宙观”。何晓兵强调,在包括对民歌等在内的各种相关音乐文化的研究中,“重要的是弄清‘为什么这样分类’,而不是去主观地或‘科学地’为其设计一套分类体系”。⑨何晓兵《四川白马藏族民歌的描述与解释》,《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9 年第4 期,第72 页。
在观察东干人关于民歌的概念及分类法时,赵塔里木结合历史文献、语言辨析,以及田野调查等多重维度,对东干人关于音乐和文学的整体概念“曲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对“曲子”与“唱”“歌”“牌子”,以及曲子中的“音与话”及东干人关于曲子的分类等问题,在一定程度揭示了研究对象内部的音乐观念。赵塔里木指出:“东干民歌的传统分类法是不成文的民间知识,它隐含在东干人有关民歌的传统观念和行为之中……在东干民间艺人看来,曲子是‘唱’的,牌子是‘耍’的,唱的成了耍的,曲子便成了牌子。”⑩赵塔里木《中亚东干人关于民歌的概念和分类法(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1 年第1 期,第48——49 页。
上述研究案例,通过概念的分类与辨析,探讨相关族群的音乐观念,进而涉及声音宇宙观的挖掘与呈现。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在进行“分类”研究的同时,我们能实现对一种文化综合观念的呈现呢?
事实上,所谓的“分类”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整理”与“归纳”,不存在“为分类而分类”。在分类的过程中,依照什么准则进行划分,如何对探究之“品类”予以不同的“定性”,其本身即包含着对依据、标准、性质的判定。也就是说,分类本身已包含着对事项的判定和认知,并由分类将这种认知进一步揭示出来。这正如沈洽在研究基诺族关于歌唱分类概念时所说,我们之所以对自身及研究对象有所体悟,是因为其背后都受到研究者自身所携带的某种“认知框架”的影响和制约,其本质是“某种特定的方法论和理念,也就是某种‘格式化了的(约定俗成了的)’特定符号系统”⑪沈洽主编《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序言”,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年版,第5 页。。同时,涵盖在分类过程中的,还有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的分类观念与研究者自身既有文化概念的对比,由此在比较中亦产生一种“文化间性”的领悟与解读。在这里,文化的理解将不再是传统主体与客体“二元性”关系,而是置于一种“共谋”关系————强调主客体彼此之间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所达成共识的一种可能性。因此,从一定程度而言,推及音乐研究中,就涉及对研究对象性质的界定,也就实现了一种关于某一文化“宇宙观”的具体体现。
与分类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则是关于音乐术语(或用语、习语等)问题的讨论,也同样涉及该术语所属族群对于音乐的文化观念。
在传统的人类学研究中,“通过语词”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解析范式。在音乐研究领域中,近年来学者也越来越认识到音乐术语的重要性。博特乐图在对蒙古族传统音乐中的一些概念在文化所有者本位表述与研究者的局外转述所发生的区别与偏差进行思考发现,在音乐文化所有者的使用层面,很多音乐术语并非是局外人理想化的“固定”不变,而往往具有多义性和多用途性,并且依附于相应的语境而发生意义的微妙变化,从而提出对于术语“灵动”性的思考。恰是这种灵动的特质,使我们得以探寻该术语背后深层的文化逻辑与文化观念。他指出:“术语及概念无法脱离语境而孤立地存在,它与运用他的主体和它所指的事物以及表述语境、表达习惯、指向目的粘连在一起”⑫博特乐图《“灵动”的术语————蒙古族传统音乐中的概念表述及其转述问题》,《音乐艺术》2018 年第2 期,第92 页。。这种对术语“灵动”性的把握,不仅强化了术语对“观念”解析的重要作用,也凸显了“术语”的运用语境,是对“术语”研究本身的进一步深入。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于通过音乐术语研究进而讨论相应音乐文化体系的重要作用,有较为明确的认识。萧梅对于通过“乐语”进而深度解读中国音乐传统与本质性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讨论。她认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历史传承中积累的习语(或乐语),为其当事人主体对音乐的认知和实践经验的升华。”⑬萧梅《中国传统音乐“乐语”系统研究》,《中国音乐》2016 年第3 期,第80 页。马克斯·皮特·鲍曼也曾明确指出:“音乐术语与宇宙观的关系是不容忽略的”⑭管建华《欧陆人文哲学语境的民族音乐学————马克斯·皮特·鲍曼讲座的解读》,《人民音乐》2018 年第3 期,第74 页。。
回溯当代民族音乐学发展历程便可知道,很多学者都曾关注到民间术语表述,并意识到对其解读不失为窥探一种文化观念的有效途径。⑮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术语的关注,先后有何昌林、程茹辛、张振涛等学者进行过系统性的研究。沈洽在《民族音乐志的架构》一文中,就专门将“有关音乐和音乐有关的各种辞语及其含义”作为第一条,列入音乐民族志架构的“常规志目”。
二、仪式音声与声音(音乐)民族志————基于文化内核与观念解构的声音宇宙观
当今民族音乐学对声音宇宙观的探寻,主要来源于两股学科动力:其一为仪式音乐研究,其二为音乐民族志。
(一)仪式音声研究与宇宙观
仪式音声的研究出发点,是将音乐视为一种文化行为的产物,而将思想作为文化行为深层的推动力;在此逻辑前提下,对音乐行为的关注,有助于我们推断其行为所有者背后的文化思想与观念。“仪式”作为一种文化行为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因而通过仪式音声的田野调查,“对被研究者的‘行为’进行观察、记录及描述,进而分析、解释或理解行为的深层动力————‘思想’。”⑯同注③,第83 页。这种表述与思路,一方面将“看不见、摸不着”的观念,附着于可以观察视听的外显性行为表象之中,从而使对“思想”的讨论有了物质性的“行为”依据;另一方面,在仪式音乐研究中,“音声”概念的引入,本身就涉及声音宇宙观。比如,“听不见”的声音,各种法器声、器物声、韵念声;由此都被纳入仪式音声境遇之中。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仪式音声的研究又何以成为宇宙观的探求路径呢?在通常情况下,研究者相信,外显仪式行为的内在因素是仪式音声所有者的思想观念,而思想的深层就是“宇宙观”。在仪式音声的研究范式中,研究者往往不厌其烦地对不同地区和民族的信仰体系、音乐传统,进行精细的个案研究,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甚至进行某种跨种类、跨地域性的比较研究;除音乐之外,还往往不放过其历史脉络的追溯、文化环境的考量,并将音乐的风格、结构形态,以及运行机制和功能,嵌入到仪式音声所依托的文化上下文语境中。因而,在仪式音声的研究中,无论是历史人文背景亦或自然地理现状,乃至风土人情风貌这些被以往研究所“一概而论”的背景性资料,还是仪式行为中几乎无处不在的巨大象征体系,都是探求声音宇宙观的基本要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很多以往并不被“学院派”所关注的民间音乐事项,却恰恰成为民族音乐学者所醉心挖掘的研究对象,因为当其融入原生的仪式行为,就成为“历史传统的言说,成为民族文化语境中的一种陈诉方式”⑰彭兆荣《仪式音乐叙事中的族群历史记忆————广西贺州地区瑶族“还盘王愿”仪式音乐分析》,载曹本冶主编《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南卷》(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年版,第320 页。。因此,通过仪式音声研究探求相应的声音宇宙观,便具备了逻辑与事实上的可能。
(二)音乐民族志与宇宙观
1.作为整体性观察的声音宇宙观
作为音乐文化的全方位、立体式的深度书写,音乐民族志以对观念的解构与地方性知识的探索,承载了对声音宇宙观尽可能全景式的呈现。一般认为,音乐民族志就是对一个民族(或族群、社群等)的音乐及与音乐有关的文化各个方面————包括其音乐所生成的历史人文脉络,以及音乐自身结构内外部特征,进行全面的描述与记录,以求尽可能真实、客观地反应该民族(或族群、社群等)的音乐现状和生活样貌。无论是研究还是写作,音乐民族志不仅汲取人类学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y)的诸种方法论与理论规范,也遵循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学科规律与基本要求。
音乐民族志在力图进行整体、全观研究的同时,仍将侧重于研究对象的某一个主要特色或重要方面,在所聚焦“问题意识”与兼顾研究对象音乐文化整体性之间,进行辩证的取舍与平衡。
2.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声音宇宙观
揭示研究对象自身的地方性知识体系,是音乐民族志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作为一种局内音乐文化与智慧系统的地方性知识,也可被视为一种具有地方属性的“生存性智慧”⑱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主要指“在实践中应对各种生存型挑战而形成的、否弃传统唯知识导向的研究,强调智慧导向的自信”,此概念由邓正来基于推进中国经验的研究而提出,可参见其《中国模式的精髓————生存性智慧》《“生存型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等相关文论。。例如,对印度传统音乐与其教育体系进行深入研究,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印度的音乐文化,不能仅从音调、旋律、节奏等表面形态进行分析和认识,而是要与“作乐者”所成长的自然时空与历史环境,以及印度特有的宗教文化和道德追求乃至天人关系等方面,进行融合性的思考与观察。民族音乐学秉承“音乐即文化”或将音乐“置于文化上下文语境”的研究理念,在音乐民族志中揭示地方性知识,实际上就是在呈现研究对象关于音乐的宇宙观。
3.族群内观与观念转换————音乐宇宙观的本质
格尔茨在《地方性知识》第三章用了较多笔墨来描述“理解”这个概念,在他看来,人类学研究的某种境界追求,就是一种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这种“内部的眼界”,亦即民族音乐学研究常常提及的文化或族群“内观”。
安东尼·西格对苏亚人的歌唱进行民族志研究后认识到,苏亚人观念中对时间的理解或许与其自身的时间概念有所不同,因为如果处在苏亚人族群内观的视角来看,该族群恰恰是通过仪式及音声行为,体现其社会的时序观念和宇宙观。事实上,对声音世界观探寻的本质,也常体现为一种族群内观的研究视角,也就是人类学研究一直强调的————以局内人(或局内-局外“双视角”融合)的视角进行观察与研究。在音乐研究中,这也常常体现在诸如突破以往研究中对歌曲旋律、歌词(包括衬词)的认识,以及音乐分类观念的评价与分析。上文提及的斯蒂芬·菲尔德关于卡鲁里人研究中的那句著名表述“对你来说它们是鸟,对我来说是森林里的声音(voices)”,也属于典型的族群内观。
赵塔里木对新疆额鲁特蒙古族民歌进行考察与研究时,就曾专门围绕“音乐观”及其相应的分类等问题展开讨论,实现了对所调查对象“声音宇宙观”的呈现,可谓是族群内观性研究的典型案例。作者以额鲁特妇女哄诱母羊的歌为例,指出在研究者看来形态上属于音乐的“歌”,但额鲁特人(除了受过学校教育的一些人)却不认为这是一首歌。这种观点在牧民中多次被证实。”⑲赵塔里木《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中国音乐》2012 年第4 期,第16 页。而当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人与骆驼的交流时,却被该族群看作是歌唱。为什么同样是对牲灵所唱,给骆驼唱“劝奶歌”却发生了变化?作者指出,在艰难的自然生存条件与漫长的历史发展历程中,骆驼对于传统额鲁特人的生活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一定程度上骆驼已具备“人格”意义而成为额鲁特人的伙伴。正因如此,我们便可对额鲁特人“给骆驼取名字”、“忌讳别人用手摸驼糕”等生活行为有了更深入的文化性理解。此外,作者以此进一步深化了额鲁特人关于歌唱性质的认定:“同许多文化中的传统观念相比,额鲁特人并没有把‘歌’本身具有的形态特征作为区别性标志,而是从实用的方面————特定的沟通对象来界定什么是‘歌’”⑳同注⑲,第17 页。。
笔者以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层面,是对研究者自身的要求————研究者需要具备以研究对象的文化逻辑,来呈现、阐述研究对象文化事项的能力,这就是笔者所谓研究者须树立的“族群内观”。上述案例中对于族群内观的展现,以及对该族群深层文化观念的表述,需要研究者长期并细腻的观察与思考。
民族志研究是以一种族群内观的方式尽量接近并呈现该族群的宇宙观。笔者在研究鄂伦春族音乐的过程中,最初遇到的困惑是,作为一个基于森林狩猎文化且人口极少的“无文字民族”,其传统形态概念下的民族音乐或“民歌”已经屈指可数,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次民歌普查、个案调查的运动式研究中,其音乐本体形态范畴内的音乐(作品)调查对象及分析空间已非常有限,那么,这样一个似乎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贫矿”,如何承载一份音乐民族志的讨论与撰写?面对此情形,业师萧梅建议笔者在解构自己音乐前见的同时,通过了解鄂伦春族关于声音与自然的“感受”以及相关的表达方式,去体察他们的音乐观。这里,无论是笔者解构自身的音乐“前见”,还是试图以鄂伦春族的方式感受森林音响生态与词汇表达系统,其本质都指向一种声音宇宙观体系。由此,笔者对原本作为歌曲“附属性”结构的衬词进行重新检视,发现其大量存在于作为行为的民间歌唱(这里的“行为”更强调歌唱的动态而非静态的“作品”概念)之中,所蕴含着的即兴歌唱中填补声韵的修辞性意义,以及作为历史脉络所浮现的部落标志(如姓氏或族徽标识);同时,探讨建立在其表面大量曲调(或曲调框架)重复现象背后的即兴演唱所带来的唱词所具有的“书写性”意义,以及支撑这一“偶然”书写性行为背后在唱词,(侧重语音)并进而经由语音与曲调旋律“化合”作用,以说明该民族民间歌唱活动之所以以即兴方式得以源源不断生成的运行机制,即笔者所提出的“音韵关联”。还涉及鄂伦春族赖以生存的天地自然、山林万物,以及传统狩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马匹等自然生灵,是如何以一个族群的声音感受,以及历史经验与生存性知识技能体系,进入其歌唱行为之中。㉑㉑ 参见高贺杰《论语音在鄂伦春人歌唱建构中的作用》,《中国音乐学》2011 年第1 期;《马·鱼·小孩————生态视角下的鄂伦春歌唱》,《音乐研究》2011 年第4 期;《音乐·文化·信仰————中国萨满音乐研究述评》,《大音》2009 年第2 期;《音声视角下的萨满服研究————以两次鄂伦春萨满仪式音声个案为例》,载萧梅编《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东北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 年版。这样一份关于鄂伦春族的声音民族志的书写及其所呈现的声音宇宙观,其最重要的启发,则来自于在体认和思考其声音宇宙观的过程中首先力图能实现的“观念解构”。
这里的观念解构,除形成对研究对象宇宙观的了解与认知之外,还兼有对研究者自身的反躬自省,这种反躬自省一样促进了他者宇宙观的理解。这种反躬自省的视角,在深入研究对象的文化逻辑过程中,亦加深了研究者对自我文化体系的了解。诚如赵塔里木对额鲁特民歌的研究,就是通过研究对象进而对自身文化体系产生的理解来完成的。
民族音乐学通过深度的音乐撰写呈现一个社群的宇宙观,已不是一件新鲜的事。许多优秀的音乐民族志研究,通过社会、历史、自然信息深刻全面展现族群的音乐文化,同时研究者也通过对音乐的了解和认识,进而达成对该族群社会的深刻理解。例如,《苏亚人为什么歌唱》的民族志研究,作者“从音乐表演(行为)的角度研究社会,而不是简单地把人类学方法和关注应用于音乐”㉒㉒ 〔美〕安东尼·西格尔著,赵雪萍、陈铭道译《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年版,原序第xiii 页。㉓ 尹翔《议题的空间拓展与深化————21 世纪以来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世界大会回顾》,《中国音乐》2021 年第3 期,第188 页。㉔ 巴奈·母路《灵路上的音乐————阿美族时漏社祭师岁时祭仪音乐》,福建师范大学2002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 页。,这就是声音宇宙观的价值与意义。
三、声音宇宙观————难以言说的存在
2004——2017 年,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有五次年会将议题关注于“音乐、宗教、仪式与宇宙观”㉓㉒ 〔美〕安东尼·西格尔著,赵雪萍、陈铭道译《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年版,原序第xiii 页。㉓ 尹翔《议题的空间拓展与深化————21 世纪以来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世界大会回顾》,《中国音乐》2021 年第3 期,第188 页。㉔ 巴奈·母路《灵路上的音乐————阿美族时漏社祭师岁时祭仪音乐》,福建师范大学2002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 页。,可见“宇宙观”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关注程度。
事实上,无论是在仪式音声研究,还是对于音乐民族志的讨论,抑或其他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个案,对声音世界观的探寻,研究者须尽量革除一种“看不见”的文化遮蔽,并实现居于族群内观的观念转换。如对于民间歌唱的研究,民间歌唱一般是各个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行为与内容,甚至歌唱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仪式。但是既有的一些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个案,对于歌唱(或音乐)这种原本在各民族传统中都非常“显著”的文化行为却常常视而不见,或者熟视无睹(因缺乏足够的观念认识与分析技术与能力)。这可理解为一种文化世界观的“负作用”。巴奈·母路梳理历史上对台湾“阿美”部落祭祀团体的研究后指出:“(除了)描述祭仪现况及几首歌曲的记谱外,其他文献都是以人类学的范畴为主,并没有特别针对音乐本体做探讨。”㉔㉒ 〔美〕安东尼·西格尔著,赵雪萍、陈铭道译《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年版,原序第xiii 页。㉓ 尹翔《议题的空间拓展与深化————21 世纪以来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世界大会回顾》,《中国音乐》2021 年第3 期,第188 页。㉔ 巴奈·母路《灵路上的音乐————阿美族时漏社祭师岁时祭仪音乐》,福建师范大学2002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 页。这既有音乐学者“熟视无睹”之因,也有因受到宇宙观的影响,很多音乐行为不能轻易为人们所视、所闻。此外,他还指出:一方面,与仪式紧密相连的歌舞,不能够脱离仪式语境而随时随地进行表演;另一方面,当这些歌曲与“民间信仰”融为一体时,更需要有特定的对象和特殊的目的,甚至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时空情境”才可以呈现。因而,尽管“阿美”人的生活中有丰富且大量的音乐文化行为活动,但是外界除了对其“丰年祭音乐”和一般性的歌谣有所了解外,其传统社群中与祭仪相关的其他诸多音乐事项则鲜为人所道。
如若揭开文化视野的“遮蔽”,民族音乐学将为人文学科领域呈现出不一样的文化研究图景。如沈洽通过“术语”研究与“分类”观念的分析,对无文字民族的基诺族的歌唱文化及其歌唱的意义,产生了完全颠覆性的认识:“把‘歌’中的‘词’活剥出来视为‘文学’的一种分类观念是‘主流文化’意识过强的表现……正是因为基诺人没有书写传统,把‘语词’编进‘歌’里,就等于是把‘字’(音节)‘刻写’在‘歌调’这样一种特殊的纸上”㉕㉕ 同注⑦,第30 页。㉖ 王铭铭《局部作为整体————从一个案例看社区研究的视野拓展》,《社会学研究》2016 年第4 期,第98 页。。革除避障、呈现“真理”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其作用正如英国民族音乐学者马丁·斯托克斯所说,因为一些优秀的音乐民族志的出现,使得以往音乐人类学家在“似乎音盲”的人类学家群体中,努力使人们“聆听自己的声音”这种窘境慢慢退散。从这个层面来说,评判一份音乐民族志的重要标准之一,取决于其是否意识到声音宇宙观的存在,以及对声音宇宙观的发现、呈现与表达。
民族音乐学以个案研究为根基,但绝不仅仅满足于个案研究————无论个案的表述有多么精彩,仍然是“树木”而非“森林”,是术而非道。这正如王铭铭在讨论呈现宇宙观的意义时所说:“延伸有关文化的物质性、社会性与精神性讨论……还包含超出社区边界并与之形成不同形式的关联性的半自然和自然界、‘精神世界’,即通过研究宇宙观与现实社会之间关系可以认识到的‘抽象世界’。”㉖㉕ 同注⑦,第30 页。㉖ 王铭铭《局部作为整体————从一个案例看社区研究的视野拓展》,《社会学研究》2016 年第4 期,第98 页。对宇宙观的揭示,需要通过一个个精彩的个案表述,实现对个案的学术方法论跨越,并以此而形成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理想学科愿景。民族音乐学如果有所谓学术的“企图”,当以自身研究推动整体人文社科的研究境遇,研究自己、理解他人,并通过研究自己与研究他人,最终实现对自我的理解与超越。
结 语
上文通过对声音宇宙观概念的阐述,以及通过研究对象的分类与术语来探究声音宇宙观,进而在仪式音声与“音乐民族志”的研究中努力呈现声音宇宙观。事实上,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其“声音宇宙观”本质,是一种对研究者的观念转换与研究对象的族群内观的呈现。但是在讨论声音宇宙观这一个问题时,笔者仍感到一种“言说困境”:一方面,声音宇宙观无处不在,附着于每一种文化形态表征背后最深层的观念之中;另一方面,它又似乎“无处安放”,也难以被言说。因为当我们将其附着于某一个研究个案的表象时,所谓“宇宙观”的终极性方法论意义,就常常被矮化,甚至被消解,成为某些具体的文化象征或符号解读。一直以来,民族音乐学都以研究音乐文化为己任,当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时,“宇宙观”就是文化的最深层内核与元概念,那么,是否意识到声音宇宙观的存在,以及对声音宇宙观的发现、呈现与表达,是品评音乐民族志的标准维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