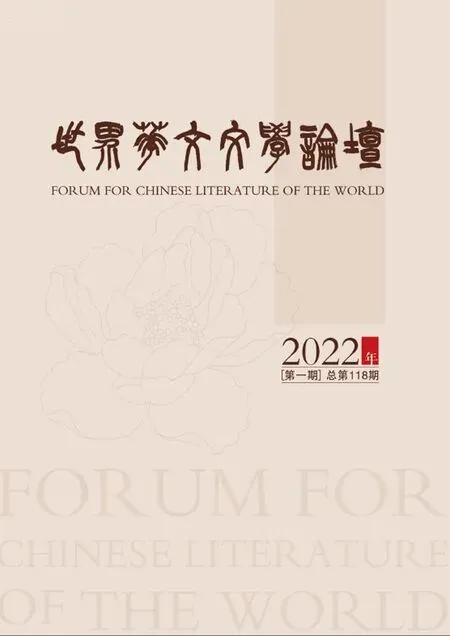困境与突围:於梨华的华人女性书写
2022-11-18顾思思
顾思思
内容提要 於梨华被誉为“留学生文学鼻祖”,其作品中除详尽展开了留美知识分子的生存经验外,更聚焦留美女性的现实困境与可能出路,这些经典作品不仅是对异域空间华人女性的困境书写,也寓指人类世界普遍的性别悖论与难题。於梨华对女性困境的书写提供了一种关于男女两性关系的理性思考,这是於梨华为华文文学做出的不可忽视的独特贡献。
在於梨华五十多年笔耕不辍的创作生涯中,以“牟天磊”为代表的“无根”一代青年的迷惘与困惑为代表,将留学生文学带进大众的视野,对20世纪60年代华文文学具有突出贡献。於梨华的作品除了描绘中国知识分子旅美生活之外,更是把形色各异的女性放在中心位置,从未停止对女性困境的揭示与书写。她的短篇小说集《秋山又几重》,处处可见留美女性遭受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抑,既谋生艰辛,又谋爱无望。将目光聚集于於梨华笔下的女性人物,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女性多以悲剧收尾,这些悲剧的成因不仅是由于现实处境的“被困”。於梨华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此,她并未将一切都归因于异域环境和男性群体,而是进一步把审视的目光投向女性自身,女性本身具有的弱点难以得到根本性克服。在男权文化的压抑之下,女性的心灵发生异化,自我主体意识逐渐丧失,成为於梨华笔下的可怜女性,既没有梦也没有家,逐渐走向自我压抑、自我围困的精神“围城”。於梨华将个人的情感经验倾注于笔下的女性人物,积极思考女性困境的出路,探索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并寻求男女两性的和谐。
一、以坦率笔墨直面留美华人女性的双重艰难
在於梨华的大部分作品中,留美华人女性是最常见的群体。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台湾掀起了赴美留学的热潮。这群人为渴求更好的生存空间而前往美国。然而实现这种美好愿望的只有少数,大多数人的处境则是於梨华作品中描述的那般艰辛——为了生存已使出浑身解数。尤其是留美女性,她们不仅要在异域文化下求学求生存,更因为女性自身的身体与生理弱点,导致她们处于一个相对的物质低位,有着比男性更为迫切的爱情与婚姻等方面的情感需求。
(一)令人焦头烂额的物质窘境
很多带着美好愿望只身赴美的人,来到美国后的现实落差导致生存困境。这一类题材的表现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於梨华对女性困境的书写,多是其自身生活经验和心绪的忠实记录。李子云评论於梨华及其作品时坦言:“於梨华基本上属于经验型的作家,她作品的取材大抵与她的生活经历有关,基于她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她不属于那种侧重想象善于营造空中楼阁或侧重思辨的作家。”①《小琳达》开始的多篇经典篇目再现了孤身留美女性的生存不易,於梨华也由此展开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女性世界”。《小琳达》中的吴燕心刚到洛杉矶时,身上一共只有35元美金,她刚到学校就快速找了一份帮助照顾一个叫小琳达的6岁小女孩的工作,她自以为这是件“不学自会”的事。但是小琳达却十分狡黠,她喜怒无常,常常骂燕心“笨猪”,燕心屡屡受气但为了生存不得不处处讨她的欢心,向这个异域小女孩乞讨友情。她如此委曲求全最终还是失去了这份赖以生存的廉价工作。《友谊》中的孙依莼,她一心随着其男友汪怀耿到美国去,终于来到美国以后,第一件要面对的事就是他们经济的困窘。依莼住在一个月只需付30美元的合租房里,很快就找了一个打字员的工作,然而她与怀耿的休息时间刚好错开了,两个人很少碰在一起,长此以往,她渐渐掉入了无限的空虚:“平时还好,晚上早早上床,一到周末,媛媛她们都出去了,她像只被摔出网外的蜘蛛,在空中乱晃,找不到一个落脚处。”②
生存问题是留美后第一要紧的难题,在美国谋生,远远没有想象中的容易。这就如同《秋山又几重》中赵恬对吴直吐露的一番肺腑之言:“你在家乡,不知道我们海外华人在各行各业挣扎求存的艰难”③,这句话既概括了於梨华本人的过往经历,又写尽了海外华人的求存现状。在这陌生冷漠的异域他乡,为了生存,她们不得不夜以继日工作,不仅要忍受物质的匮乏,甚至还要忍受种族的歧视。她们从一个把梦顶在头上的女大学生,到一个把梦捧在手里的女留学生,再到一个把梦踩在脚下的女人。女性人生黑暗面的揭露也给於梨华带来一些责难之声,她坚持认为:“一个作家不应该为迎合读者或讨好某些人而写,否则是出卖自己。这是一个写作的人的道德问题。不管它流行不流行,畅销不畅销,我要诚实,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作家,我要写使我感受最深的,我确信的,我要写来。”④
(二)女性无法逃避的情感困境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在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情感方面的需求。事实上,物质与情感是所有女性生命中最重要的两部分。缺少任何一部分,对于女性来说都是不够圆满的生存状态。对于留美女性来说,情感生活的困境比物质生活的困境更为痛苦与致命。因为“一个人在海外,挣扎了两三年累了,泄了气,更也许,一个人太孤单了,需要个依靠”⑤,不可否认,一些女性到海外并不像男性一样豪情壮志闯天下,或是抱着找一个好丈夫的目的,漂洋过海从台湾地区前往美国,她们渴求找到一个依靠与归属,来建立自己的安全感。她们大多可以忍受生活的困窘,为衣食住行奔波劳累有时反而充实了在异国他乡的孤单生活。於梨华的大部分小说也正将重点放在了留美女性的情感困境上——爱情的幻灭、婚姻的琐碎以及灵与肉的冲突与困惑等等。这些女性情感困境的真实再现,在於梨华的笔下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雪地上的星星》中罗梅卜两次真心寻爱都遭遇打击之后,那种悲凉与痛惜引人深思。梅卜初到美国时,对这里的生活充满美好的热忱。六年之后,她对生活低了头,她想找个人,找个家,找个归宿。这唯一的愿望,最终也落了空。梅卜先认识了王大卫,王大卫舍得为她花钱,却并不打算跟她结婚,不过是想欺骗她的感情,玩弄她的身体。梅卜认清王大卫的嘴脸后,一直对爱情保持着警惕。一直到梅卜25岁时,经人介绍她才开始和李定国通信,靠信纸互传情愫建立感情。令罗梅卜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建立在纸上的三年爱情一触到现实的寒冬即宣告了它的死亡。梅卜为这次破碎的梦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三年的青春,而她已是快30岁的老处女。那些“比星星还小,比星星还亮,比星星还多的星粒,像无数个璀璨的希望。可是当她蹲下去伸手去抓,抓的是一把冰冷的雪,冷得直透她的骨髓。希望破灭时,不也是这种感觉吗?”⑥在於梨华的小说中,像梅卜一样在寻觅真爱的道路上无助绝望的女性不止她一个,还有《雪夜》《江小慧》等都属此类。这不仅是罗梅卜个人的特殊爱情悲剧,也是海外年轻华人女性普遍的情感遭遇,正因如此,小说才有较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孤身海外却找不到爱人固然令人烦恼,但结婚也未必一定能获得幸福。留美华人女性想要寻得依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婚姻,在走进婚姻的“围城”之前,她们对婚姻,对男性充满的是美好幻想,一旦踏入婚姻,就会即刻醒悟过来婚姻是座“围城”,“婚姻的悲剧性并不在于它无法保障向女人许诺过的幸福(保障幸福这种事本来就不存在),而在于它摧残了她;它使她注定要过着周而复始的千篇一律的生活。”⑦《林曼》中的林曼很年轻便自主地与一个菲律宾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生下一个女儿后没多久就离婚了。后来“我”向她表述心意并求婚时,林曼是这样回答“我”的:“我老实对你说,我已结过一次婚,这一辈子再没有兴趣结第二次了。”⑧字里行间流露的分明是对婚姻的失望与抗拒。林曼最终的确没有再婚,选择与人草草同居。在《秋山又几重》中,赵恬的婚姻也是一塌糊涂,她坦白承认:“但是我不爱他,不用说没有魂飞魄散的爱,连亲近他抚摸他的柔情蜜意都没有。但是我嫁了他。”⑨在短暂的无爱婚姻过后,最终二人还是分道扬镳,“两人都浪费了生命中最灿烂的一段的遗憾”⑩。婚姻的残酷性就在于此,它打破了女性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使女人从虚构的婚姻童话中走回现实。

二、触及女性内观自省的性别与文化冲突命题
无论处在何种环境下的女性,都一直面临着种种困境。不同时代的作家也持续关注着女性问题。於梨华的小说中,我们不得不加以考虑的一点正是小说中的人物所处的背景环境,海外华人女性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她们在西方世界,在男权社会,都毫无意外地被迫处于“边缘地位”。女性自身又具有难以克服的弱点,这就更加剧了女性的“边缘化”。
(一)异域环境给女性带来的身份苦恼

(二)男权社会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吞噬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女性依赖男性,妻子作为丈夫的附属物而存在,她们需对丈夫绝对服从,宽容忍让。在这种社会观念的长期浸淫下,女性渐渐失去自我意识和自立能力,一些女性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惯性与惰性,从而自觉地选择对男性完全依附。从中到西,时空迥异,然而不变的是男女两性不平等的地位。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就对这种不平等地位提出了强烈反对。在父权社会中,男人将男性定义为“自我”,将女性定义为“他者”,从而确立男性的本体地位。尤其是男女平等观念未普遍之前,女性自小对男性霸权司空见惯,在成长过程中她们也未必觉得有何不妥,甚至极大多数已经深受男权文化的荼毒,成为男权文化的牺牲者与守护者,把男性社会施以的外在规定内化为“应当”遵守的女性准则,自然而然地扮演男权社会分配给女性的各种角色。女性的自我意识一步一步被吞噬,女性渐渐自觉成为人类群体的第二性。严重的性别歧视导致女性被“他者”的身份约束,她们是真正的失语者。华人留美女性更是如此,她们不得不在东西方男权文化的共同夹击下求生存空间。

(三)女性自囿的精神“围城”
女性的物质困境、精神困境、情爱困境、婚姻困境等等,都时刻萦绕在女性身旁提醒着女性寻找出路。这出路并非简单强硬地与男权做斗争,因为女性不得不承认女性并非完全的受害者。性别天平的严重倾斜,既有男性原因,也有女性自身的缘由。
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提到的:


不能单怪别人,於梨华还对女性群体进行了自我审视。在留美环境与男权社会之外,留美女性还有着女性群体自身固有的劣根性,女性自身的弱点也时时刻刻在束缚着女性的生存与发展。在於梨华的小说中,她委婉揭露了女性的弱点,这种弱点也给女性造就了一座自囿的精神“围城”。《意想不到的结局》中,於梨华这样描写小琥:


三、对女性突围的可能性设想兼容中西

(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二)男女两性的和谐

於梨华通过几十年来的人生感悟的积淀与中西方文化观念的融合,形成了融合中西、兼容自立的女性意识。她的这种两性观念不但会为女性争取自由和尊严,而且也给予男性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从而避免了两性之间的冲突和抵触,表现出和谐健康的两性平等的精神。这是一种美好的畅想,如今看来也更符合社会两性关系的需求。
文学虽然是不同思想和观点的碰撞,是温饱之后追求的上层建筑,但文学最终一定会落地生根。当它被读者阅读,在读者心中泛起涟漪,它会像滚雪球一样影响到人们的现实生活。本文所探讨的於梨华小说中的女性困境,何尝不是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境遇和命运。作家要在短篇幅的小说文字里写完某些有深意的事件甚至是某些人某个家族的一生,这考验的是作家讲故事的基本功。作家能否让自己写的作品在现实社会中掷地有声,甚至为某种社会观念的驻足和流行鸣锣开道,这考验的是作家关注现实的精确度与敏感度。於梨华对女性生存困境的书写体现出她在挖掘女性内心深度时丰沛的想象力,将女性群体聚焦于留美女性更贴合她的生存经验,对现实的关注度越高,文字更加有血有肉,这在男权社会的大环境中,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人文关怀。

①李子云:《於梨华和她的〈屏风后的女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8年第1期。

⑥於梨华:《雪地上的星星》,《当代》1980年第2期。
⑦[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