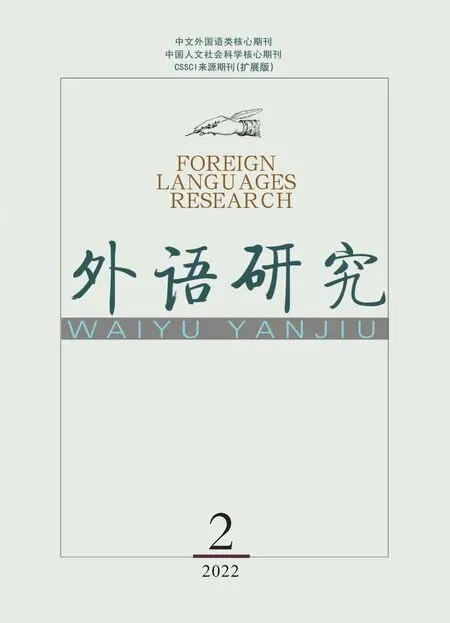《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中的身份焦虑与伦理混乱*
2022-11-17袁英哲田俊武
袁英哲 田俊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0.引言
犹太裔作家霍华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1942—)是当代英国备受瞩目的喜剧创作大师。为缅怀莎翁逝世四百周年,雅各布森与霍加斯出版社联合推出《夏洛克是我的名字》(Shylock Is My Name,2016)一书,将《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这部经典莎剧改写成长篇小说。该书一经出版便受到各方关注,引起评论家们的广泛讨论。蒂姆·马丁(Tim Martin)在《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中直言这部小说的影响力惊人,“雅各布森的‘商人’与其说是对莎翁的复述,不如说是对这位剧作家的逆向工程(reverse-engineered)”(Martin 2016)。《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埃里卡·瓦格纳(Erica Wagner)却认为《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中反复出现的“犹太”字眼不过是老生常谈,书中“角色无一鲜活:他们都是作者与自己和我们辩论的喉舌”(Wagner 2016)。尽管大众对这部改编新作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雅各布森在书中确实打开了一扇通往与原作截然不同世界的大门。
自诩为“犹太裔简·奥斯汀”的雅各布森被公认是书写当代犹太群体生存现状的行家里手,擅长以风趣的笔触描绘犹太人在异国的种种困境与焦虑。但是笔者认为这些并不是他创作的全部内涵,在其作品中还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词,那就是伦理。不论是《芬克勒问题》(The Finkler Question,2010)中萨姆·芬克勒(Sam Finkle)对自己犹太身份的避之若浼,还是《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中西蒙·斯特鲁洛维奇(Simon Strulovitch)对自身犹太作风的言不由衷,其实质都是个人在复杂的伦理环境中产生的伦理身份困惑和伦理意识混乱。在雅氏幽默的叙事和细腻的表达背后,是他对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的深切关注。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探析《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中斯特鲁洛维奇与夏洛克面临的身份困惑与伦理混乱,剖释他们在理性与非理性意志主导下做出各种伦理选择并最终殊途同归的过程,以期揭示雅各布森在喜剧帘幕之下精心编制的伦理之帷。
1.认同困惑与身份焦虑
瑞贝卡·华雷斯坦纳(Rebecca Wallersteiner)曾评论说:“在新书《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中,雅各布森以其犀利、辛辣、北方式的幽默审视了当代犹太身份问题”(Wallersteiner 2016)。事实上,她只说对了一半。雅各布森确实在这部作品中探讨了犹太人的身份问题,但是并不局限于当代,而是将整整四个世纪的时间全都纳入考虑。与“新瓶装旧酒”或“换汤不换药”等传统改编模式不同,雅各布森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将原作的主要情节与核心人物置换到现代;另一方面大胆创新,将原作中本来仅占一角的夏洛克一分为二,开创性地在新作中塑造了两位“夏洛克”——一位是从原剧穿越而来的“灵魂人物”夏洛克,另一位是他的现代复刻版斯特鲁洛维奇。这两位“夏洛克”非但外形各异,内里也是千差万别,这在一定意义上暗示了标题“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不单单是对莎翁原作的致敬,同时也包含了雅氏对“我是谁”和“夏洛克是谁的名字”这两个身份命题的伦理追问。
萨罗·巴伦(Salo Baron)认为,犹太人身份问题肇始于犹太解放运动(1979:33),似乎是近代才发现的问题。然而,这颗巨型“地雷”从埋线布局到全球爆发并非朝夕之功,其产生源头最远可追溯到公元四世纪的欧洲。自基督教接管罗马起,“一种恶毒的意识形态就如同不详的风暴云般”笼罩在了犹太人的身上(Meyer 1967:11)。起初,犹太人以“神之选民”的身份与他族相安共处。可是,在明确表示“耶稣是人不是神”之后,犹太人便遭到了基督教旷日持久的排挤和打压,不仅被当成“神之弃民”,丧失了土地、工作和社会地位,变得只能在规定的聚居地生存或他乡流浪,而且被打上“杀害基督凶手”的标签,成为与恶魔结盟的异端,承受来自各方的宗教钳制。随着欧洲“反犹主义”(anti-Judaism)和“种族排犹主义”(anti-Semitism)愈演愈烈,犹太人的处境越发艰难,最后甚至成为纳粹“种族灭绝”(Genocide)的对象。在长期的奔波和逃难中,流散成为犹太人民的生存常态,种族、区域与文化的割裂令其在多元伦理环境下倍感困惑和焦虑,成为他们身份构建的主要障碍。
作为英国犹太裔,斯特鲁洛维奇的认同困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他对自我伦理身份的矛盾认知,二是外界对其犹太身份的边缘定位。小说中,斯特鲁洛维奇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犹太家庭中,父母都是犹太人,经营着一份汽车零件生意。初时,他以犹太身份为傲,甚至“早熟地蓄起小胡子”(雅各布森2017:6;以下此书引文仅标注页码),以彰显自身的犹太特质。然而,眼见家族事业渐入佳境,斯特鲁洛维奇逐渐对自己的犹太身份产生动摇,继而向英国社会的主流文化靠拢。在举家搬入柴郡黄金三角的领主豪宅后,斯特鲁洛维奇周遭的伦理环境随之一变,令其拥有了“社会新贵”这一新的伦理身份。财富资本的累积与新贵身份的获取并没有令他感到满足,因为“比起新贵,他更欣赏世家”(56)。所谓世家,多指有着悠久历史和多代传承的显贵之家。英国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一部英国贵族史,宫廷权贵和世家名流不仅决定着英国政体的本质内核,上层阶级对主流意识的把控更是其主导社会文化发展与伦理机制构建的重要手段之一。社会地位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文化立场的优劣。文化作为多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斗场,历来便是各方势力争战不休的舞台。不同文化之间的较量通常会以宣扬本土文化和打压他者文化的方式展开,以此塑造自己高人一等的文化身份。斯特鲁洛维奇对世家地位的欣赏不仅折射出其意识深处对英国阶级文化和伦理秩序的认可,同时还暴露出他在英国强势文化输出下所衍生出的对本族文化的不确定和不自信。这种不自信直接动摇了其文化身份的根基,造成文化归属感的丧失和伦理身份的焦虑。而内部犹太文化与外部英国文化在斯特鲁洛维奇身上所呈现出的交融对抗之势,也令其在个人文化身份及社会伦理身份认同上挣扎彷徨。
除了斯特鲁洛维奇在伦理身份认知上的偏差之外,外界对他的犹太身份也大多报以异样的凝视。作为有名的艺术慈善家,斯特鲁洛维奇曾试图以父母之名在柴郡设立一座犹太美术馆,并表示愿意向公众免费捐出自己的艺术藏品,以求得郊区一栋废旧老宅的使用权。不料,此方案遭到了以德·安东(D’Anton)为代表的本土势力的集体反对,理由是其艺术藏品“不符合本地区的文化内涵”(109)。对于世代流离的犹太人民来说,拥有一个安全稳定的栖息之地是他们一生的夙愿。继承这一志向的斯特鲁洛维奇选择在柴郡开设犹太画廊,不单单是为了开拓自己的艺术事业,更是为了将祖辈的名字刻在这片土地上,以获得精神上的归属感。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al and Imperialism)一书中,萨义德强调,“领土和占有是地理与权力的问题”(2003:6),占有土地就意味着拥有权力。斯特鲁洛维奇想要为英式建筑烙上犹太印记的行为,在柴郡人民眼中无异于是对其本族领地的闯入和侵占。无论他的艺术藏品价值几何,都配不上那栋英式老宅分毫,因为在以欧洲文化为主导的伦理环境中,“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萨义德1999:10)。画廊事件不仅揭示了斯特鲁洛维奇边缘化的社会身份困境,还显露出犹太人与西方人之间难以调和的文化冲突。
与斯特鲁洛维奇一样,书中的另一位犹太人也承受着多元文化冲击带来的伦理身份困惑,但是他的矛盾和焦虑更为复杂。作为莎翁作品中最经典的犹太角色,“夏洛克”(Shylock)这个词本身便是一个蕴含着巨大能量的特殊符号,在四百年间持续地影响着世界对犹太人的看法,甚至一度被视作整个犹太民族的代名词。历经百年冲刷,夏洛克的形象非但没有黯然失色,反而呈现出鲜活的多面化特征:他可以是莎翁笔下阴险狡诈的无良商人,也可以是德国用来肃清犹太人的反面典型,还可以是反犹主义者眼中的“加害者”与亲犹主义者心中的“被害者”。从表面上看,夏洛克在全世界的文化圈都得到了普遍认同,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但是从根本上看,只能被动接受他人指摘的夏洛克,却是一个在多方势力操控下失去自我的纸片人,身份的杂糅性抹杀了他自身的特质。正如斯特鲁洛维奇虽然心里觉得他很了解夏洛克,可在真正与之相处后,才发现自己对他其实一无所知。小说中,夏洛克本人有一句颇为精辟的总结:“他人眼中的我,才是真正的我”(65)。结合上下文来看,这很显然是一句反语,其本意一方面是要表达雅各布森对人们藉着私心为夏洛克套上多重伦理身份这一乱象的辛辣嘲讽,另一方面,也由此点明雅氏对犹太人历史身份遗留命题的伦理追思:如果“我”的身份全权交由他人定夺,那么真正的“我”究竟是谁?
事实上,除了书中出现的两位新旧夏洛克之外,还有第三位隐含的夏洛克,即雅各布森本人。换个角度来想,若将小说的标题看成是作者与读者的第一次交谈,那这句简单明了的“自我介绍”何尝不是雅各布森的内心自白。显然,不管是穿越而来的夏洛克,还是其现代复刻版斯特鲁洛维奇,抑或是雅氏本人及其他犹太人,在世人眼中,他们所共有的名字都是“犹太人夏洛克”。哪怕时光推进四百年,犹太群体面临的伦理困境依旧如故。
2.伦理混乱与身份危机
小说伊始,斯特鲁洛维奇这位“富有、暴躁、敏感的慈善家”(3)便在一个二月的墓地偶遇那位“易怒又暴躁的犹太人”(5)夏洛克。雅各布森缘何选择墓地作为这场世纪会晤的发生现场呢?概因其特殊的空间意义和文化价值。就空间层面来说,墓地作为人们进行殡葬事业的社会性场所,除了为亡者创造安息之地,还能为生者提供哀悼之所。在这个独特的灰色区域里,生死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共存于世,墓内亡者与墓外生者同时在场,令当下和过去冲破现实的禁锢,实现短暂的阴阳交汇,时空的概念也由此被模糊甚至消解。可以说,墓地特有的空间属性对生死之间二元对立的淡化,削弱了“灵魂人物”夏洛克出现时的突兀感。就文化层面来说,墓祭行为本身就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文化活动。人们通过修建墓地来缅怀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或者对个人及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显要人物,此举不仅衍生出祖先崇拜、神鬼信奉等社会文化风俗,而且奠定了以血缘羁绊、道德教诲等为基础的社会伦理意识。墓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深深嵌入到人们的思维模式之中。特别是在文学作品里,墓地常常被视为连接现世和冥府的桥梁,亡者通过墓地重回人间或是人类通过墓地唤回亡者。但是,生死屏障的破除带来的往往不是幸福结局,而是现实社会的动荡和伦理秩序的混乱。因此,雅各布森安排两位夏洛克在墓地相会,某种程度上暗示二人身处的混乱伦理环境。
站在历史的维度来看,“受难文化并未导致犹太人接受建立在大屠杀基础上的受难者身份……摇摇欲坠的犹太身份使他们在犹太生存问题上产生了诸多焦虑”(Novick 1999:190)。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政治并立,多元文化共存,世界文明的交融和对抗形势愈演愈烈,四处流散的犹太民族首当其冲被推到台前,成为以西方文化为首的主流意识凝视下的“他者”。为了在外邦世界得以存续,犹太人不可避免地经历族裔身份与社会身份的二元对立,从而陷入身份危机的漩涡之中。这种身份危机往往伴随着“人们试图给犹太人套上一个种族、一个民族或一种宗教的外套”时出现(Solomon 1997:6),而想给他们穿上这件外套的,除了非犹太人,还有犹太人自己。
对于斯特鲁洛维奇来说,与族群和信仰相关的主要伦理冲突不在外,而在内。斯特鲁洛维奇家里存在着一个微妙的现象:尽管男人们平时都在口头上否认自己信教,却会在某个特殊时刻化身虔诚的信徒,将犹太教义贯彻到底。这个特殊时刻多与家庭和子女有关。在很多方面“都堪称异教徒”(36)的犹太父亲莫里斯·斯特鲁洛维奇(Morris Strulovitch)尤为如此。听闻儿子要娶一名基督徒为妻,暴跳如雷的莫里斯不惜在婚礼前夜宣称逆子已死,并“口头埋葬了他”(12);而在与第一任妻子不欢而散、继而另娶一位同族妻子后,莫里斯却即刻收回前言,与儿子和好如初。从社会学上讲,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与婚姻家庭应该是共生关系,而非敌对关系。斯特鲁洛维奇的父亲以信仰为刃,在儿子与外邦人步入婚姻家庭时,单方面割裂与其在原生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强行剥夺斯特鲁洛维奇作为“儿子”的伦理身份,导致家庭伦理的缺失和家庭成员的疏离。正如聂珍钊所言,“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2010:21)。这段“起死回生”的经历不只引发斯特鲁洛维奇伦理意识的混乱,还直接改变他的家庭伦理观,造成他对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扭曲认知。
遵照父亲旨意与凯(Kay)结婚的斯特鲁洛维奇对这段婚姻并不热衷,拥有间歇性“犹太癫狂”的他与“没有信仰”的妻子在很多观念上背道而驰,难达共识。随着妻子中风倒地,斯特鲁洛维奇“再无心去扮演丈夫的角色”(9),这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他自愿放弃“丈夫”的伦理身份。为了留住“父亲”身份这一根最后的稻草,他选择将全部的情感寄托在女儿比阿特丽斯(Beatrice)身上。然而,从混乱的伦理意识中脱胎而来的亲子关系无疑是病态的。他无视女儿的个人意愿,强行在其出生时代为立下“将来得嫁个犹太丈夫”(39)的神圣誓言;他监视并跟踪女儿多年,只为将她牢牢把控在自己手中,肆意释放自己近乎变态的占有欲。他之所以这么做,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扭曲的家庭伦理观:在这个不完整的犹太家庭中,女儿既是女儿,也是妻子,因而要对父亲和丈夫效忠。正如李尔王要求所有女儿都爱戴他的背后蕴藏着某种与俄狄浦斯情结正好相反的“成人情欲”(adult libido)(Pauncz 1952:58)一样,斯特鲁洛维奇对比阿特丽斯也怀着类似“恋女情结”(Lear Complex)的非理性情感。错误的伦理观念自然无法带来称心如意的结果,比阿特丽斯非但没有如其父所愿领回一位跟他一样的犹太丈夫,反而选择与公开行纳粹礼的足球运动员葛兰顿·豪瑟姆(Gratan Howsome)交往,以示对父亲和犹太身份的拒绝与反抗。在相继失去“儿子”和“丈夫”的伦理身份后,斯特鲁洛维奇连“父亲”的伦理身份也一并丧失,这就将他置身于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机之中。就家庭伦理而言,斯特鲁洛维奇与比阿特丽斯都是家庭伦理缺失和亲子关系异化的受害者。一个家庭中妻子与母亲身份的同时缺位,势必让其他家庭成员的伦理身份也相应发生异化,这种非正常的转变必然将本就岌岌可危的犹太家庭推向更深的伦理旋涡。
面对所有家人全部离场的窘境,“举目无亲”的斯特鲁洛维奇转而向家庭之外的夏洛克寻求帮助。同样失去女儿杰西卡(Jessica)的夏洛克在此隐晦地提出一个想法,那就是为豪瑟姆举行割礼仪式(circumcision)。“割礼”是自亚伯拉罕时代起就流传在犹太民间的传统宗教仪式,根据《圣经》,犹太男孩出生后第八天就要行割礼,以示与上帝之间的契约成立。它为犹太民族印上特有的身份标识,在犹太人的民族身份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外邦人可以通过割礼仪式成为以色列人或犹太人”(Thiessen 2011:5-6)。夏洛克认为,让豪瑟姆举行割礼仪式既可以考验他对比阿特丽斯的真心,又可以让他为曾经冒犯犹太人的行为付出代价,还可以满足斯特鲁洛维奇想找一个犹太女婿的心愿,可谓一举多得。
原剧《威尼斯商人》中也有割肉履约的情节,俗称“一磅肉”事件。虽然夏洛克直到最后也没能割下安东尼奥心口的那磅肉,在世人眼里却已经将其身份定义为残酷的刽子手,加诸其身的百年唾骂也由此展开。可以说,原剧里夏洛克身份危机的爆发点就集中在“一磅肉”上。而新作中斯特鲁洛维奇能否顺利应对自己的身份危机也取决于“一磅肉”计划的实施结果。通过再现这一经典情节,雅各布森让夏洛克直接参与到斯特鲁洛维奇的伦理选择之中,目的是为其在后文发出自己的声音埋下伏笔。雅氏此举既不是刻意猎奇,也不为强行辩护,而仅仅为了让读者明白,此时的夏洛克已经跳出禁锢他四百年的牢笼,不再局限于世人对他的刻板印象,也不再以一个虚无缥缈的纸片人身份旁观他人故事,而是成为一个与斯特鲁洛维奇一样拥有主体意识的人,“一种伦理的存在”(聂珍钊2011:6)。
3.伦理选择与自我和解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比阿特丽斯与豪瑟姆为了逃避割礼,携手私奔威尼斯。于是,行割礼的任务落到斯特鲁洛维奇的老对手德·安东的头上。此时,割礼的性质已经从“考验豪瑟姆的真心”“对其冒犯行为进行惩戒”和“找个犹太女婿”的合理诉求变成“向敌人复仇”的私人恩怨。经过普鲁拉贝尔(Plurabelle)等人的刻意渲染,这个本该是私下解决的家庭内部矛盾直接升格为犹太族群与外邦族群之间的种族纠葛。一时间,斯特鲁洛维奇的面前出现三个伦理问题:行不行割礼?谁来行割礼?以及怎么行割礼?
针对这一突发状况,斯特鲁洛维奇与夏洛克产生明显的意见分歧。夏洛克三次指出斯特鲁洛维奇太过沉迷于“个人恩怨”,直言此事不可为,建议其不如放弃割礼仪式,与外邦女婿握手言和。可是,困于局中的斯特鲁洛维奇远没有身在局外的夏洛克这般冷静透彻,在他心里,德·安东既是阻挠他为父母寻求归属的罪魁祸首,还是引诱比阿特丽斯离家出走的始作俑者。新仇旧恨齐上心头,斯特鲁洛维奇坚定地做出让德·安东公开执行割礼的伦理选择。这也意味着在唤回女儿与惩戒德·安东之间,斯特鲁洛维奇选择了后者。诚然,如果单纯从斯特鲁洛维奇与德·安东的私怨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折辱对方的好机会,不单可以令其付出血的代价,同时还能实施宗教制裁。就像鲍西娅让夏洛克改信基督教的本意不在招安而在羞辱一样,执行犹太割礼的德·安东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将成为有别于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异类。然而,从斯特鲁洛维奇面临的伦理危机来看,这却是一场必输的战役。就算坚持割礼,斯特鲁洛维奇也无法重整自己支离破碎的犹太家庭,甚至可能永远失去女儿,加上此番他高调与德·安东作对,无异于坐实外界对犹太人“残暴冷血”的评价,显然会对自己社会身份的塑造产生不利影响。但是,被愤怒、偏执等非理性情感冲昏头脑的斯特鲁洛维奇只看到眼下一时的痛快,看不到之后的种种弊端,因此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而这一错误也导致后续一系列闹剧的发生。
小说的第五幕是全书最后一章,也是整个故事的高潮所在。在这一章里,雅各布森一改之前用数字标记章节的现代排版模式,将原本应该写作“二十四”的章节标题更名为“第五幕”。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威尼斯商人》中原版报幕格式的仿拟,而在致敬之余,雅氏似乎还有意与莎翁一较高下。原剧中,夏洛克在第四幕的审判结束后便黯然离场,根本没有机会出现在第五幕中,雅各布森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让两位夏洛克同时现身于最后一章,这种对既定故事格局的打破,势必将结局引向未知。
在这出荒诞的割礼闹剧中,新作的每个人物都对应原剧的某位角色,只不过角色的分配是错位的——斯特鲁洛维奇扮演夏洛克,德·安东扮演安东尼奥,普鲁拉贝尔扮演法官,观众扮演评审团,夏洛克扮演鲍西娅。对于熟读莎剧的读者来说,这一幕一定显得格外古怪,夏洛克居然成了“仇敌”鲍西娅的代言人,这是否表示夏洛克从一开始就是鲍西娅的化身呢?实则不然,通过故意营造这种出人意表的角色反差,雅氏在为大众带来强烈感官冲击的同时,意在引导读者对夏洛克和鲍西娅的演讲进行比较,以此展开进一步的思考:
慈悲不是出于勉强……慈悲待人,理当不求回报,只为它的真谛——因为慈悲不是用来交易的。……悲悯不屈从于利益或奖惩,也不屈从于自我陶醉……去宽恕那些不配得到宽恕的人……展现你的同情心(rachmones)无损公正。具备同情心的人认可公正的裁决,但做起事来,却会遵循那缔结了我们的法则。也即遵从上帝。(251-252)
对照原剧不难发现,夏洛克的发言看起来“鲍西娅味”十足。然而,事实却是除了第一句与原文有所重合以外,其余的话都是夏洛克,或者说雅各布森本人的二创。闻此发言,在场观众争相报以热烈的掌声以示赞同。讽刺的是,夏洛克的这席话并非出自基督教所熟知的《圣经》,其中的慈悲、宽恕、同情心(意第绪语中的“rachmones”)等概念全部源自犹太教理。夏洛克选在此刻发表演说,一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主体身份,二是为了嘲讽基督徒对自己教义的一知半解,三是为了告诫世人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说完这番犹太式的箴言,夏洛克在书中的全部戏份尘埃落定,接着便如同他迷雾般的登场一样悄无声息地退场了。
另一边,斯特鲁洛维奇终于等到割礼仪式的结果:德·安东在出生时已接受过包皮环切手术,所以无法完成割礼。对此,斯特鲁洛维奇并不惊讶,因为他早已意识到“这件事里没有赢家”,对双方而言,“输赢都同样荒谬”(258)。于是,他在不合时宜的满足中做出最后一个伦理选择: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的落败,并为德·安东送上战利品。平心而论,对于德·安东和普鲁拉贝尔的存心戏弄,斯特鲁洛维奇完全有权利提出申诉,请求更换割礼执行人,以确保契约的顺利完成。然而,他却选择直接让步。这一伦理选择集中反映斯特鲁洛维奇在利己与利他、情感与理性之间的深度思考。促使他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有二:其一,德·安东在公众面前坦白自己与犹太人拥有相同身体构造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斯特鲁洛维奇的预期目标:让德·安东也体尝一下被他轻视的犹太人民的感受。其二,从情感上说,斯特鲁洛维奇希望德·安东代表他所在的西方阵营向犹太人低头且“血债血偿”;但从理性上说,德·安东行不行割礼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犹太人在西方世界的艰难处境,除了可以获取一时畅快,于己于他并无更多好处。尽管这场割礼闹剧以荒谬开篇,以诡诈收场,却给了犹太人向外邦人证明自己的机会,“被真实地看见”对于当代犹太人而言同样意义重大。所以,斯特鲁洛维奇决定放下私人恩怨,以包容的心态与社会、民族和自我达成和解。这是理性意志恢复后的斯特鲁洛维奇,作为社会和族群中的独立主体,做出的正确伦理选择,象征着他伦理意识的升华。小说以比阿特丽斯返家与父母重聚作结,也明示理性意志对犹太家庭回归伦理正轨的重要作用。
4.结语
虽然雅各布森在《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中借用了莎翁喜剧的外衣,但这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喜剧小说。正如雅氏自己所言,犹太人的想象力在本质上是严肃的,“非常有趣就是非常严肃”(Manus 2009)。从这点上来看,《夏洛克是我的名字》其实是一部相当严肃的伦理寓言。透过斯特鲁洛维奇和夏洛克的双重视角,雅各布森以一种犹太式的内聚焦笔触对西方世界的犹太刻板形象进行重构,从文学的角度为犹太人在多元文化中遭遇的多重身份焦虑与混乱提供一种伦理的解读。第五幕里夏洛克的临别箴言与斯特鲁洛维奇的最终和解都勾勒出雅氏对当下社会伦理、种族伦理和家庭伦理的深入考量,彰显现代犹太人对族裔与公民、自我与他者、仇恨与宽恕等对立体系的多元伦理思考,以及由此做出的理性伦理选择。通过将原剧大团圆结局的主角置换成犹太人,雅氏不仅表达了对犹太族群和谐未来的美好愿景,而且以此告诫世人:唯有跟随正确伦理观的指引,才能有效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价值,实现自我与自我、自我与世界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