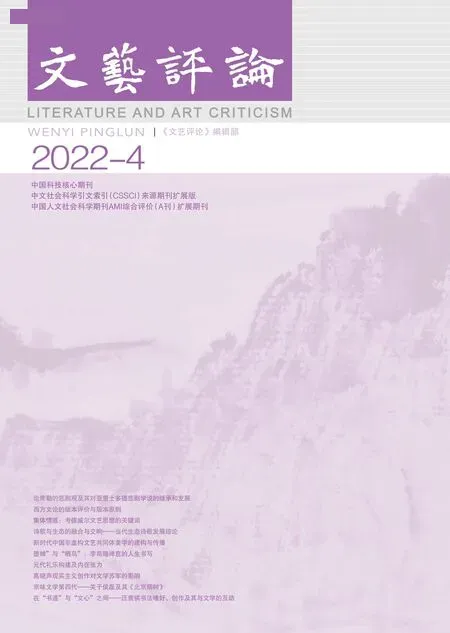以小说的方式为文化赋形立传
——关于葛芳长篇小说《云步》
2022-11-15陈敏王春林
○陈敏 王春林
面对葛芳的长篇小说《云步》,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就是它的文体归属问题。一方面,已经承认它是长篇小说,另一方面却又要专门来讨论文体归属问题,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云步》肯定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我注意到,其实,一方面,早在2018年,葛芳就出版过一部名为《六如偈》(中国书籍出版社)的小说集,其中不仅收入了《六如偈》这部中篇小说,而且还把它移用来做了书名。另一方面,《云步》中的卷一《六如偈》,卷二《云步》,卷三《山月照》,卷四《垂钓声音》,卷五《归去来》这五个部分,在组构为长篇小说之前,也都曾经以中篇小说的形式分别发表于《花城》《钟山》《上海文学》《天涯》《芙蓉》等文学杂志。尽管无法从葛芳那里得到证实,但从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来判断,极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就是,在写作当初,葛芳或许并没有创作一部大体量长篇小说的艺术自觉。一种合乎艺术逻辑,也合乎创作实际的判断,恐怕就是,只有在完成了以上五个部分,并且也已经以中篇小说的形式分别发表之后,葛芳方才突然意识到这五个部分其实完全可以整合成为一部结构相对松散的长篇小说。既如此,《云步》究竟能不能被看作是一部长篇小说,自然也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根据自己多年来的阅读经验,我所给出的是一个肯定性的答案。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云步》肯定不是一部合乎艺术常规的长篇小说。既缺乏贯穿文本始终的整一(更不用说跌宕起伏或者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任何一个始终处于文本核心地位的主人公形象,所以总体的艺术结构就必然是枝蔓而松散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又应该看到,不仅只有卷五的故事游离了同玄镇这个特定的地域,前面四个部分的主体故事全都发生在同玄镇,而且五个部分出现的人物形象也还彼此互有交叉勾连。卷一《六如偈》中活跃的人物形象,主要有评弹艺人司文育、桂月、萧岚,书店老板陈家洛,原先的镇长、后来被提拔的马市长,擅长于装神弄鬼的汪道士,以及司文育那个不成气候的浪荡儿子司斌等。卷二《云步》的核心人物虽然变成了昆剧演员林平山,还有他那个名叫程心佑的妻子,但与卷一交叉的人物,却也有司文育、萧岚、以及那个浪荡子司斌。卷三《山月照》虽然增加了陈良运、何君华、潘总等人物形象,但居于中心位置的,却毫无疑问是前两部分都曾经出现过的萧岚。卷四《垂钓声音》中的故事虽然围绕甄岭与鸣芝这一夫妻而展开,但引发矛盾的焦点人物之一,却仍然是已经在同玄镇开了小店的萧岚。卷五《归去来》的故事地点由同玄镇转移至太湖里一个名为迁山岛的小岛,主要人物是渔民作家芹菱,相对次要的一个女性人物就是萧岚。如上所述,既然五个部分之间存在着人物形象的彼此交叉与勾连,那么,尽管的确显得比较松散,但一部长篇小说所要求的总体意义上的整一性也还是具备的。
换个角度说,虽然葛芳的《云步》缺少能够贯彻始终的主人公形象,很是有一点五部分各有其主人公各自为战的感觉,但只要我们不再拘泥于传统意义上要求主人公只能是小说中的某一个具体人物形象的狭义理解,解放或者说打破习惯性的思维方式,那么,《云步》中就同样是有主人公形象存在的。这个主人公不是别的,正是那种看似抽象无比实则触目处皆是的“文化”。其他且不说,单只要我们细细地端详揣摩一下五个部分的标题,就能够强烈感觉到其中所蕴含的那种文化意味。且让我们来一一加以分解。首先是“六如偈”。六如偈是一个来自于佛教经典《金刚经》中那个其实已经广为人知的说法。那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其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人生在世,一定要想方设法摆脱欲望漩涡的困扰,这样才可能不再苦恼无边,才有望真正通达大道。只有把一切都看明白之后,才能够做到既可以拿起,也可以放下。然后是“云步”。所谓“云步”,是戏曲表演中的一个专有名词,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时走路的一种基本程式:双脚并拢,先脚跟分开,脚尖相对,再脚尖再分开,足跟相对,如此连续反复,使身体向左右横向移动。向左时,右脚为着力点,向右时,左脚为着力点。卷二之所以要命名为“云步”,与身为核心人物的昆剧演员林平山紧密相关。这一部分快要结尾时,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种描写:“挥手之间,他走起了云步,甩起了水袖,‘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一番吟唱之后,似乎所有的离愁别恨,所有的哀怨情思,都在天地之间一笔勾销了。”从一种象征的意义上说,云步所传达出的应该是一种舒缓自在的精神姿态。接下来是“山月照”。“山月照”语出王维的诗歌《酬张少府》中的“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一句。所谓迎着吹来的松林之风解开衣带,在山间明月的映照下独坐弹琴,所传达出的,乃是摆脱俗务的羁绊之后精神所抵达的一种自由自在状态。紧接着是“垂钓声音”。“垂钓声音”这一标题具体来源于日本一位名叫坂本龙一的作曲家。用萧岚的说法就是:“想不到吧,坂本龙一坐在冰山的边缘,牵着一根绳,将录音设备沉入冰原。那是北极圈的某一天,冰原之下传来汩汩水流声。‘我正在垂钓声音啊。’他小声说,说完笑了。是的,他在收集冰川死去时的呻吟声。比起弹奏完毕就会随着时间消逝的琴音,坂本龙一一直以来都钦慕长久、不灭的声音,大概就像是江河流淌、海浪击岸、树叶被吹动的声音吧。”最后就是“归去来”。所谓“归去来”的具体出处,肯定是陶渊明那堪称杰作的《归去来辞》。其中传诵最为广泛的一个段落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既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为物所役,已经以今天的正确衡量出了昨天的错误,那为什么还不赶快采取相应回归田园、回归大自然的行动呢?!虽然不能说其他作家在为小说命名的时候就不考虑文化内涵的问题,但相比较而言,如同葛芳这样五个部分的标题全都很讲究,有来历,典有所出的状况,其实是非常少见的。也因此,如果我们把这种真正耗费了一番心思的标题,与小说中那种悉心呵护以评弹、昆剧、古琴、茶道、美食等器物为代表的江南吴地文化,以及如同陶渊明那样一种回归田园向往大自然的生活与精神态度结合在一起,断言葛芳这部结构的确略显松散(这里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松散的艺术结构本身是不是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江南吴地文化的一种外化表征)的《云步》,乃是一部以“文化”为潜在主人公的,试图以小说的形式为“文化”赋形立传的长篇小说,就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一种说法。从文体的角度来说,也正因为有“文化”这一主人公统摄全篇,所以,我们才更有理由把《云步》界定为一部长篇小说。
事实上,《云步》的五个部分,作家所聚焦的可以说全都是围绕某种文化器物而生发出的矛盾冲突。《六如偈》中,是评弹。首先是现代性强势冲击下评弹艺术的整体低迷状态:“评弹团越来越不景气,这倒是的。这么好的演员不好好珍惜,实在是作孽。有个性的人早早跳槽,凭嘴上功夫去当司仪,公司开业小型演出啦,有人家做寿啦,结婚啦,都用得着。”司文育的女徒弟桂月,之所以要经常性地跑到师傅的评弹书院来和师傅一起搭档演出,便是迫于这种整体情势的缘故。某种意义上,如果我们可以把桂月看作是评弹艺术的象征载体,那么,葛芳通过她的不幸命运遭际所试图传达出的,就是在评弹艺术总体走衰的情势下,权力对评弹艺术的强势凌辱。当然,如此一种象征性表达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马市长甫一上任,就立马进行了古戏台的搬迁:“马市长就是当年同玄镇的马镇长,自从他被汪道士点化官运亨通,成为分管旅游的副市长后,第一目标就是全力打造千年古镇同玄镇,把原本在运河边上的古戏台搬到胭脂街,说这里资源集中,好开发。”就这样,“领导一声令下,三百多年的古戏台就挪了地方”。如此一种貌似扶持文化实则在戕害文化的行为,自然会令司文育这样的文化人倍觉齿寒。所谓象征性表达,就是指桂月有一次专门给司文育打电话请假,说自己要随团去上海演出半个多月,要师傅另外请个搭档,以免耽误生意。没想到,等到桂月从上海回来之后,却差点因为宫外孕而丢了命。尽管葛芳采用了非常含蓄的处理方法,但根据若干带有暗示性的细节来判断,那位致使桂月不幸宫外孕的作恶者,也就是这位马市长。其一,“桂月从上海回来时乘着一辆黑得锃亮的高级轿车。人从车上下来,还没来得及站稳,汽车喷了几口尾气,‘唰’地消失了”。其二,“那人曾给她许下什么诺言,什么花好月圆,什么良辰美景,全都是戏文里唱的,假的”。其三,“马市长派专车来接司文育和萧岚,说省里文化厅的领导来了,点名要听评弹《钗头凤》。马市长的高级轿车黑得锃亮,司文育觉得眼熟,一时也想不起来哪里见过。和萧岚坐在后排座,只闻到一股股香味,也不知是萧岚身上的香,还是轿车里本身就有的,还未开唱司文育就有点犯迷糊”。将以上三个细节整合在一起,如果马市长可以被看作是政治权力的一种象征,那么,葛芳所试图形象表达的,恐怕正是政治权力对评弹艺术,对文化的一种“强奸”。
《云步》里,是由林平山所代表的昆剧艺术。虽然出生于普通的乡村人家,但林平山却有着十足的昆剧艺术天赋:“林平山的扮相实在是堪称惊艳。”“长得俊,再加上化妆师笔墨点染,在舞台上水袖一闪,别说女人心动,连男人看了也会爱煞。昆曲里的曲词又是雅致,光听那曲牌名,就让人浮想联翩,什么玉山颓、醉扶归、霜天晓角、桂花锁南枝,一个个场景让人恍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方面是出于天性,另一方面肯定也与后天的长期浸染紧密相关,林平山简直就变成了昆曲的优美化身。如果说《六如偈》更多关注政治权力与文化、艺术的冲突,那么,到了《云步》中,作家所集中思考表现的,便是文化、艺术与经济的矛盾。这一点,突出不过地体现在林平山和他的妻子程心佑之间。爸爸在省政府大院里办公的程心佑,原本是林平山戏曲学院的同学,也曾经酷爱昆曲艺术,但后来,由于时代浪潮习染影响的缘故,她竟然越来越看重世俗的经济利益:“程心佑多年前就改行了,她开服装公司,开化妆品店,她的观点要赚就赚女人和孩子的钱,赚得合情合理。”一个固执地心仪文化、艺术,另一个则早已经随波逐流地向往拥有更多的金钱,林平山和程心佑矛盾冲突的发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避免。既然如此这般地“同床异梦”,那曾经一度志同道合的他们夫妻俩最后的分道扬镳,也就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到了《山月照》里,文化的载体,变成了那张古琴,以及萧岚那位不仅极善于弹琴而且还能够斫琴的师弟何君华。首先是那张战国时代的古琴:“古琴没有名字,孤独似在湖里任意飘荡的一艘船,要去向何方,谁也不知道。暗沉的漆面,像满腹的心事要倾诉。”尽管现实生活中的为人着实有不堪之处,但小说中人物陈良运对古琴那样一种“独琴于室,无人无响,正所谓大音希声”的评价,却还是颇值得一听。尽管并非全然都与情爱有关,但萧岚所面对的,却是在陈良运与何君华之间的一种艰难选择。陈良运,从日本来到同玄镇,不仅不断地游走于上海和同玄镇之间,而且看上去较堂兄陈家洛更有飘逸之气,更见神采。如此一种情形,再加上看似不俗的谈吐,以及他一度的疯狂追逐,自然会令萧岚不由得着迷。但此后的一系列事实,包括他不仅四处兜售日本房产投资一站式服务,而且很快就和一个被称为邢总的女性打得火热,都充分证明着他的做人无底线与不可信任。与陈良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恰好是萧岚那位月朗风清的师弟何君华。“君华弹琴,着玄色上衣,千层底布鞋,正襟危坐,神色悯然。指尖铿然有力,右手弹拨,左手抚弦,疾速之处快而不乱,徐缓之处慢而不断。《流水》。《渔樵问答》。似在山林野外徘徊,又疑在潺潺溪涧逗留。拂过清风,风呈波浪之相。越过阡陌,明月相照。”别的且不说,单只是葛芳这一段绝对称得上妙笔生花的文字所勾勒出的何君华形象,其精神之超拔之状,就足以令人印象深刻。说到这里,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提及的就是,葛芳整体行文时文字与姿态的优雅与蕴藉。如果不是长期接受着以评弹、昆曲为代表的姑苏文化的滋养与熏染,这样的文字与姿态,恐怕既很难写出,更很难做出。不管怎么说,陈良运与何君华,两相对比,真正可谓精神境界高下立现。既如此,一直心慕能够借助于文化与自然获得某种精神自我提升的萧岚之弃陈良运而择何君华,也就自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萧岚揉揉眼睛伸个懒腰,皓月当空。她想起李白的诗,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写得真好,时至今日,她才体味出真正含义。”
到了《垂钓声音》中,文化的承载体变成了萧岚店里的那一杯苏式玄米茶。与苏式玄米茶紧密相关的一个核心人物,是那位自身前后有着截然不同变化的甄岭:“店里没有其他人,甄岭得了折扇,喝了玄米茶,神清气爽,仿佛做了半天神仙。其实之前他也是忙得要命,开店,做生意,接待一茬一茬的人,宾朋满座。现在一下子人生转了个弯。朋友评价说他简直是前后判若两人。的确,他对物质生活要求越来越简单,人却越来越清瘦,有奕奕神采。”如果说《山月照》中面临抉择的人物是萧岚,那么,到了《垂钓声音》中,需要作出抉择者,就是这位前后判若两人的甄岭。甄岭面对的,一方面是那位长期在官场打拼,只是一味想着怎么样购房赚钱的妻子鸣芝。鸣芝“炒股炒房,买基金理财,忙得不亦乐乎,平时办公室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她盯着股市潮涨潮落,心情也随之起伏不定。”除了钱财上的贪婪之外,鸣芝一直隐瞒着丈夫的一个小九九,就是那一次去香港游玩时,在维多利亚港曾经差一点失身于一个萍水相逢的男子。另一方面,则是那个冰清玉洁似乎一尘都不染的脱俗女子萧岚。很大程度上,正因为萧岚的超凡脱俗,所以他们俩才能够彼此间惺惺相惜:“萧岚是特别随性的人。或者说,他们俩之间互相随对方的性格,你想喝茶就喝茶,你想写字画画就写字画画,你不说话就不说话,发你的呆想你的事,你想海阔天空聊生活,可以!有机锋有内容。”毫无疑问,正是彼此间如此一种高度的精神契合,才使得甄岭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唐代的王维与裴迪:“甄岭想到王维在辋川和裴迪的山居岁月,真是好啊,古槐树的白花开得粉嘟嘟的,压满了枝梢,群蜂嗡嗡响,像刮风。王维和秀才裴迪有一搭没一搭聊,对诗,喝酒,饮茶。”当然,葛芳的艺术处理方式也还是相当克制的,到最后,作家并没有让甄岭简单地放弃鸣芝,而且安排甄岭携带鸣芝一起去北欧旅游,让他们一起去坂本龙一曾经“垂钓声音”的北极圈做一种亲身体验,尝试着以如此一种方式召唤已经迷失了自我的鸣芝精神世界的魂兮归来。
最后一部分《归去来》,可以说通篇都在围绕陶渊明那种向往、回归大自然的世外桃源的精神理想做文章。某种意义上,那座孤悬在太湖之上的迁山岛,就可以被看作是世外桃源的一种现实镜像。除了那个带有贯穿性质的人物萧岚之外,最主要的人物形象,是那个尽管没有考上大学,只能作一个普通农妇,但却依然有自己精神追求的芹菱。芹菱那种向往追求精神自由的独立意志,在她的这样一段话语中表现得特别淋漓尽致:“你知道吗?我在学生时代就特别痴迷写作,可是很倒霉,高考的时候因为数学发挥不利,和大学失之交臂,永远错过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女儿也上大学了,我忽然意识到——我自由了,这很重要!可以随心所欲干我喜欢干的事情,我可以暂时离开他们,就像你现在一样,去一个想去的地方!没有人能干涉我!就像我的祖母金枝一样,任性,有主见,我知道她最后跑了,扔下丈夫和五个孩子,在那个时代她多有勇气啊!”饶有趣味的一点是,小说中有着文学写作梦想的芹菱,也在写作完成着一部名为《乘着月色逃离》的以祖母金枝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现实中芹菱的故事,与作品中祖母金枝的故事,二者相互交织推动着故事情节的演进。到最后,尽管芹菱的努力一再遭受来自于大自然的打击,但意志坚定的她却始终“回也不改其乐”地坚持着自己所选择认定的人生方式。请一定不要忽略临近结尾处芹菱想象中祖母对自己说的那段话:“芹菱,人生什么都不重要,忘不掉的可能还是故乡啊!你从小出生在这里,是地地道道渔民的孩子,那就守着这片湖,这个岛,这样,你的心会特别舒服!”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千万不能简单地把这里的故乡仅仅理解为芹菱她们所在的这个迁山岛。从一种象征的意义上说,葛芳所意指的,其实是所有能够如同陶渊明世外桃源一样的理想精神居所。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带有江南一带东吴地域特色鲜明的一些文化器物,比如评弹、昆曲、古琴、茶道,甚至类似于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的精神方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云步》这一长篇小说的核心事物或者说“主人公”形象。以这些器物为突出标志的一种精致的传统文化,在当下这样一个日益世俗、功利、粗鄙化的,现代性已然弥漫一切的时代,其颓败与衰亡,似乎也是合乎逻辑的必然命运。但所有的这一切,却并不妨碍饱受江南文化浸淫的葛芳,以她那虽然温婉但却从不退让的小说笔触来为这种看似无形的文化赋形立传。在一个文化必然会颓败衰亡的时代,虽然貌似没有那么剑拔弩张,那么慷慨激烈,但如同葛芳这样坚韧的书写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日益世俗、功利、粗鄙化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强烈反抗。正是在这样的意义层面上,对葛芳的长篇小说《云步》,我所持有的就是一种无条件的认同与肯定姿态。
总而言之,在认真地读过葛芳的长篇小说《云步》之后,的确感到有话要说。于是也就有了以上这些或许根本就搔不到痒处的拙劣文字。不揣简陋地写在这里,愿以此与葛芳,与广大读者共勉,希望葛芳在今后能够创作出更加优秀作品,能够在文学道路走得更远也更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