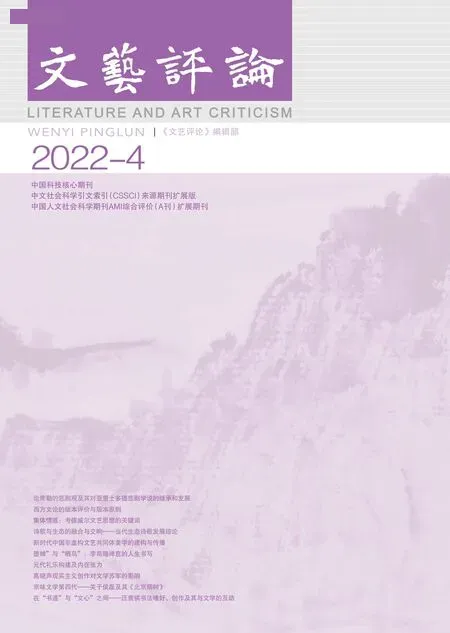诗歌与生态的融合与交响
——当代生态诗歌发展综论
2022-11-15汪树东
○汪树东
中国作家中,诗人对大自然尤为敏感,尤为热爱。大部分当代诗人都亲近自然,热爱自然,具有或自觉或不自觉的生态意识。他们对身边的生态问题颇为关注,当江河湖海被污染时,他们会奋力疾呼;当森林被伐童山濯濯时,他们会拍案而起;当百兽凋零飞鸟遁迹时,他们会长歌当哭;当雾霾弥漫蓝天沦陷时,他们会冷嘲热讽。当然,他们也颇能够感知大自然的神秘节律,能够超越现代人自然冷漠症,浓墨重彩地描绘自然之美,为早已被祛魅的大自然再次复魅。因此本文所论的生态诗歌,是指诗人能够自觉感受到现代生态危机,超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建立起亲近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态整体观,致力于书写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歌。1978年以来,大部分诗人都曾创作过若干首生态诗歌,甚至出现了于坚、吉狄马加、雷平阳、李少君等这样长期持续创作生态诗歌的著名诗人,而华海、侯良学、沈河、哨兵、徐俊国等诗人更是专注于生态诗歌的创作,《悼念一棵枫树》《避雨之树》《哀滇池》《拒绝末日》《我,雪豹……》《寻找一棵大树》《水立方》等生态诗歌堪称当代诗歌的经典篇章。整体上看,题材多样、艺术风格繁复的生态诗歌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发展史中的重头戏之一,赋予了当代新诗全新的生态风景。同时,生态诗歌也为中国新诗重塑了生态维度、地方维度,重新接通了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历史文脉,对生态文明的建设也颇有助益。
一
整体通观1978年以来近四十年的生态诗歌发展史,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各有特点又前后相续的历史阶段,即1978-1989年的发生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阶段、20世纪头20年较为繁荣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的生态危机主要是历史上的大破坏和当时日益加速发展的经济造成的。历史上的大破坏,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在极左思潮下全国各地罔顾生态规律大肆砍伐原始森林、开垦草原和湿地、围海围湖造田、猎杀野生动物以及无节制的矿产开发和道路建设等造成的生态破坏,例如大炼钢铁就对全国森林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而改革开放以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经济状况,大力发展经济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为了发展经济,各地往往不顾生态规律,也不顾及环境保护,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环境的快速恶化相伴而生,生态危机比比皆是。在此阶段,徐刚、沙青、岳非丘等人的生态报告文学率先崛起,极力揭露生态危机的现状,但是当代生态诗歌尚处于萌芽发生阶段,创作了较重要的生态诗歌的诗人有牛汉、昌耀、海子、于坚等,较有代表性的生态诗歌有牛汉的《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昌耀的《鹿的角枝》、于坚的《南高原》《避雨的树》、海子《活在珍贵的人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
改革开放初期,当代诗坛上活跃着的是一大批当初被打成“右派”而后归来的诗人,重要的有艾青、牛汉、曾卓、绿原、公刘、邵燕祥、流沙河等人,这些诗人多关注较为宏大的社会历史,具有较为强烈的历史反思精神,同时也葆有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精神,但是他们普遍缺乏诗意歌咏大自然的持久兴趣,生态意识也处于朦胧之中。当然也有例外,例如牛汉、昌耀就写出了颇有生态意识的诗歌。牛汉在1970年曾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从事极为艰苦的农业劳动,身心均受到较大的摧残,但是他同时也看到了大自然生命的创伤,每每感同身受,从而滋生出强烈同情自然生命的生态悲悯意识。例如他的《华南虎》一诗写桂林动物园被囚的华南虎,写它的绝望和反抗,写对自然生命的同情,感人至深,也促使每个人反思自己对待其他自然生命的残暴态度。他的诗歌《悼念一棵枫树》在那个时代里也是绝无仅有的生态文学的华美篇章,诗句中弥漫着诗人对另一种自然生命的深切理解、赏识和热爱,以及为它的遭遇而滋生的悲怆。他的诗歌《麂子》则写出诗人为麂子这样的自然生命担忧的生态情感。至于他的《鹰的诞生》《半棵树》《巨大的根块》《毛竹的根》《奇迹——庐山好汉坡所见》《车前草》等诗歌均能够呈现自然生命的内在性和自在性,赞美它们的顽强生命,弥漫着慷慨激荡的生态强音。到了20世纪80年代,牛汉还关注到了华南虎灭绝等生态问题,例如他的诗歌《虎啸的回声》就写到广东一个自然保护区由于滥伐森林导致华南虎远走他山的生态悲剧。
昌耀也曾于20世纪50-70年代被流放于青海边缘藏区,与那些藏族牧民为伍,朝夕与大自然相对,慢慢地滋生出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例如他在诗歌《莽原》中写道:“远处,蜃气飘摇的地表,/崛起了渴望啸吟的笋尖,/——是羚羊沉默的弯角。//在最后的莽原,/这群被文明追逐的种属,/终不改他们达观的天性:/或如松鼠痛饮于光明之枝。/或如河鱼嬉游于波状之物。/捕捉那迷人的幻梦,/他们结成箭形的航队/在劲草之上纵横奔突,/温柔得如流火、金梭……/莽原,宠爱自己的娇儿。//正是为了大自然的回归,/我才要多情地眷顾/这块被偏见冷落了的荒土?”[1]昌耀摆脱了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看法,并不把那些游牧的藏族人视为落后、不文明,相反,他发现藏族人在游牧中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是真正令人眷恋的种族。昌耀正是深受藏族人众生平等、敬畏生命的传统生态文化的影响,他才重新发现了青藏高原上自然生命的神圣性,因此他产生了一种惜生护生的生态意识,例如他在诗歌《寓言》中曾为自己误杀一只蜜蜂而惭愧。他也非常崇敬自然生命,例如诗歌《一百头雄牛》就赞美青藏高原上的牦牛,崇敬它们那种遗世独立的悲壮精神。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诗人中很少具有生态意识。对于北岛、顾城、舒婷、杨炼等诗人而言,真正重要的是现实社会,是人、人性、人道、人的命运,是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对理想爱情的追寻。即使对于崇尚童心的顾城而言,大自然也没有成为兴趣的中心,更不要说生态意识的启蒙了。但到了第三代诗人那里,开始出现了两位有代表性的具有生态意识的诗人,即于坚和海子。于坚漫游于云南大地,深受云南少数民族万物有灵、敬畏自然的生态智慧的滋润,在大自然中脱胎换骨,灵性重生,因此他的许多诗歌都是歌咏云南山川大地之壮美的,著名的有《南高原》《避雨之树》等。尤其是《避雨之树》讴歌了那株像大自然母亲一样的亚热带榕树,堪称当时生态诗歌的最美篇章。而他的《那人站在河岸》等诗歌则较早表现了河流污染问题,也是当时生态批判的诗歌力作。至于海子创作出了生态诗歌,则与他的乡村生活经验和梭罗的影响有关。他出生于安徽怀宁乡村,从小与大自然生活在一起,从内心里亲近自然、热爱自然,他对现代城市文明、工业文明怀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倾向。此外他非常喜欢荷尔德林、梭罗、叶赛宁等作家,也受到他们的生态思想的影响。他在诗歌《活在珍贵的人间》中曾写道:“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一层层白云覆盖着/我/踩在青草上/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泥土高溅/扑打面颊/活在这珍贵的人间/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2]。海子喜欢的人间,不是喧嚣的城市,而是乡村,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人间;幸福也是来自与大自然融合为一。至于他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更是歌咏一种与大自然相融为一的诗意栖居的生态理想。
当然除了上述这些较为重要的诗人诗作之外,20世纪80年代还有不少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创作过一些生态诗歌,例如艾青的诗歌《盆景》反对现代人强制扭曲植物的形状以满足人的畸形审美趣味,叶文福的诗歌《天鹅之死》批判俗人猎杀天鹅的罪行,白桦的《雪山杜鹃——过白马雪山所见》讴歌云南白马雪山上的凌寒而开的高山杜鹃花等等,不一而足。此外,诗人渭水的几首生态诗歌也值得关注。渭水曾写过不少社会抒情诗,主要有《1986:阿兹特克世界大战场》《1988:奥运会启示录》等,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他对重大社会问题反应及时,抒情姿态激烈,当他关注生态问题时,他就写出了生态批判意味浓郁的生态诗歌。例如他的诗歌《大难之后:中国的沉思——大兴安岭火灾一周年祭》写了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火灾,严厉批判了导致火灾蔓延、酿成人祸的官僚主义体制,提醒森林的消失会造成的人类灾难。他的长诗《挑战》则写人类生存面临的各方面挑战,尤其是生态危机的挑战,呼唤现代人的生态意识的觉醒,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状态。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渭水处理这些生态题材时,虽然表达了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不过概念化痕迹过于明显,个人的生命体验尚未有效地注入其中,因此艺术魅力大打折扣。
我们必须承认,20世纪80年代没有出现更为专注、艺术成就更好的生态诗人,也没有出现较为集中的生态诗集,生态诗歌的概念还没有被提出,生态意识也只是混杂在诗人对大自然的亲近、对环境污染的敏感中。徐刚凭借《伐木者,醒来》这样的生态报告文学震撼了国人麻木的神经,呼唤国人重视保护森林,甚至影响了我国的林业政策;高行健凭借《野人》这样的生态戏剧在当代实验戏剧中引起极大的轰动,“救救森林”的呐喊响彻剧坛;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树王》、张炜的《三想》等生态小说则深入历史、反思现代化,树立了极为自觉的生态意识,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此阶段的生态诗歌还没有出现真正的经典之作,社会影响力也颇为有限。
二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加速,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更为突出;空气污染加剧,酸雨、雾霾、沙尘暴对于许多地方而言都成了见惯不惊的常态;江河湖海污染加剧,河流消失、湖泊萎缩、湿地锐减,沿海地区赤潮频见,水生态全面恶化;森林进一步减少,野生动物锐减,草原沙化日渐加重;垃圾泛滥,垃圾围城日益严重,随着农药、除草剂和化肥的大量使用,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也日益明显……当然,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风起云涌,尤其是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巨大影响,中国作家的生态意识进一步觉醒,对生态的书写更为自觉,当代生态诗歌的发展明显进入了更为自觉的发展阶段。更多的诗人加入生态诗歌创作队伍,建立了更为自觉的生态意识。除了于坚之外,李瑛、韩作荣、李松涛、沈苇、吉狄马加、倮伍拉且等诗人都创作了富有个人特色的生态诗歌。更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生态诗歌作品开始频繁出现,例如于坚的《哀滇池》、李松涛的《拒绝末日》、韩作荣的《寻找一棵大树》等。而且生态诗歌的题材也出现了较大的拓展,举凡江河湖海污染、森林被伐、野生动物遭猎、洪水泛滥、江河断流等生态问题,都有诗人及时准确地书写。诗歌刊物、文学刊物也在推动生态诗歌的创作,例如《诗刊》就曾多次举办“大地之歌”“土地与未来”“绿色地球杯”等诗歌征集活动,《绿叶》《生态文化》《中国绿色时报》《中国环境报》等报刊也频繁地刊登生态诗歌。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于坚、李松涛、渭水的生态诗歌创作。于坚到了20世纪90年代相继推出几首重磅的生态诗歌,如《哀滇池》《棕榈之死》等。长诗《哀滇池》控诉了云南昆明滇池的水污染,写出了诗人故乡沦陷的悲哀和恐惧,个人经验和时代经验汇合,生活细节和历史现象交织,深刻的生态哲思和丰沛的艺术想象相融,巍然屹立于当代生态诗歌史上,构成标志性的存在。而李松涛的长诗《拒绝末日》曾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以其对华夏大地上的土地沙化退化、水污染、森林遭毁、野生动物濒危、人口爆炸等生态问题的全面揭露而震惊世人。虽然该长诗存在着较为鲜明的概念化倾向,但是它的生态忧患意识弥足珍贵。渭水则依然坚持着20世纪80年代政治抒情诗式的进路,不过把关注点再次投向了生态问题,因此创作了长诗《水的哭泣——献给世界“地球日”二十周年暨新世纪的开拓者》(《诗刊》1992年8月号),指出现代人需要注意水对于文明和生命的重要性,并为现代文明却造成可怕的水危机而感到震惊。诗人具有非常恢弘的眼光,把往古今来、宇宙八方都纳入视野之内,最终呼吁“为了整个地球整个人类更加干净/我们该重新/擦亮这同样泛着粼粼水波的眼睛/重新/走向文明”。不过,该诗依然存在概念化严重的弊病,缺乏独特的意象,缺乏动人的想象,缺乏春风化雨的细腻诗意。
其次,值得关注的是出现了非常典型的专注于生态诗歌创作的诗人江天和他的生态诗集《楚人忧天》。江天的诗集《楚人忧天》于2001年获得第九届中国人口文化奖诗歌类一等奖,被视为“有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江天具有较为敏锐的生态意识,对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都极为关注,例如他的诗歌《杜鹃之啼血》写森林被伐、鸟儿丧失栖息地的生态悲剧,《云雀的请愿》写农民过多使用农药导致云雀也无法生存的环境问题,《海狗》写人类因为要吃海狗鞭而虐杀海狗,《鲸鱼》写鲸鱼集体自杀,《都市垃圾》写城市垃圾泛滥,《造纸厂》写造纸厂排放污水,等等。应该说,江天的生态诗歌的生态视野较为开阔,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各类生态环境问题都有所涉及,而且具有一种较为宏大的全球性视野,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发展史较早聚焦于生态诗歌,试图以诗歌的力量来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但是江天的生态诗歌也存在着较为鲜明的问题,关键在于这些诗歌过于拘泥于切实的生态环境问题,缺乏必要的诗意提炼和想象力的飞扬,也缺乏具体生动的生活经验的充实与支撑,对生态意识的理解流于常识,无法达成对生态问题的殊异化、个体化的理解,从而出现鲜明的艺术局限。
再次,韩作荣此阶段创作的生态诗歌的生态视野较为开阔,艺术魅力独具,值得关注。韩作荣是当代著名诗人,他的诗集《韩作荣自选诗》曾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他具有较为自觉的生态意识,许多诗歌堪称典型的生态诗歌,《野生动物园》和《寻找一棵大树》都是当代生态诗歌史中的重要篇章。他的《杀鱼》反思日常生活中对待鸡、鱼这样家养动物的杀食暴力问题,《一条水沟的改造》写城市里的环境治理问题,《裘皮店》反思对野生毛皮动物的猎杀问题,《麻雀》写一只偶然闯入诗人家里的麻雀的极度恐慌,进而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遥远距离。除了短诗之外,韩作荣的《野生动物园》《寻找一株大树》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两首生态长诗。前者反思了现代人对待野生动物的野蛮态度。后者则反思了华夏大地上森林消失、大树消失的生态困境,诗人写道:“是谁,是哪一双罪恶的手/用文明的钢牙噬杀了一株伟大的生命/当巨树轰然倒下/树的痉挛与震颤,会使一座大山崩溃/与根的分离,使巨树成为尸体/它白色的血浆还没有流尽/一群食虫鸟便雾一样飞来寻找食物/山林里失去一株大树/枝桠间的云彩已化为雨滴/将林地涂抹成酣畅淋漓的水墨/可树的影子已深深地沉入泥土/让土地更为沉重/林地间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空白/和我的心灵一起,因缺失而虚妄/在森林,一株过于高大的树是孤独的/群树因失去大树会更加孤独/甚至风再也不能在最高处喧哗/只能在树丛中呜咽”。[3]诗人亲近大树,崇拜大树,从大树那里获得一种心灵的抚慰,因此当大树死去,他才长歌当哭。韩作荣的《寻找一棵大树》和牛汉的《悼念一棵枫树》在当代生态诗歌史中遥相呼应,高标出尘,独领风骚。
此外,诗人沈苇也创作了不少生态诗歌。他大学毕业后到新疆乌鲁木齐工作,在新疆大地上四处漫游时也产生了较为自觉的生态意识。他的诗歌《开都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写新疆开都河畔的一只蚂蚁,洋溢着众生平等的生态思想,“我俯下身,与蚂蚁交谈/并且倾听它对世界的看法/这是开都河畔我与蚂蚁共度的一个下午/太阳向每一个生灵公正地分配阳光”[4]。的确,人总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自以为是万物之灵长,傲视其他所有自然生命;但是从太阳角度来看,人与自然万物都是平等的,太阳向每一个生灵公正地分配阳光,这种太阳般的公正也就是生态正义。在诗歌《鳄鱼》中,沈苇更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立场和伦理立场,去发现鳄鱼这样的自然生命的美与善。沈苇的诗歌《鳄鱼》和于坚的诗歌《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样,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桎梏,体现出对自然生命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从而发现了自然生命的内在本性和丰沛诗意。
当然除了上述的诗人诗作之外,20世纪90年代还涌现了一大批生态诗歌佳作。例如著名诗人郑敏的诗歌《谁征服谁?飞鱼与云团的对话》写出了诗人在万里高空上对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生态思考。在诗人看来,面对天地日月这样的生命之源,人类不能傲慢地想着征服,“沉默是人类最高的智慧,/静聆自然的声音/静观星辰们的旋转/人终于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再问道:/谁征服谁?”[5]人类不能妄想征服大自然,而只能承认自我的渺小,谦卑而感恩地踏实生活。著名诗人李瑛也创作了不少生态诗歌,例如他的诗歌《羚羊》赞美藏羚羊的矫健与野性,诗歌《一只山鹰的死》赞美山鹰的庄严与英武,诗歌《生命》怜惜那些远离大海、被晾晒在绳子上的死鱼,诗歌《一只死去的藏羚羊》则为一只被猎杀的藏羚羊而悲伤,对人类污染西北高原表达了愤怒的批判。著名诗人雷抒雁的诗歌《断流》则写黄河断流,感叹世道沦丧、生态退化。四川诗人哑石的《青城诗章》也是这个阶段生态诗歌的重要收获。哑石在20世纪90年代曾短暂隐居四川青城山,师法王维,深入自然,感悟自然大道的运行规律,体悟天人合一的佳妙境界,发而为诗,便成了《青城诗章》中那些生气弥漫、妙悟自然的生态诗篇。此外,还出现了若干位少数民族诗人开始进行较为自觉的生态诗歌写作,例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倮伍拉且,他们多信奉本民族的万物有灵论,致力于发现万物的内在灵性。《吉狄马加诗选》《诗歌图腾》两部诗集中的生态诗歌所在多有,极为生动地呈现凉山彝族人的生态智慧观。
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生态诗歌的确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生态诗人日见增多,生态诗作日渐繁盛。《哀滇池》《拒绝末日》等生态诗歌无论是在诗坛上还是在社会上影响力都很大。更重要的是,诗人们的生态意识更为成熟,越来越多的诗人能够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偏见,以生态整体主义视角审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例如于坚的《哀滇池》就明确地在生态整体主义立场上提出敬畏自然的生态主张。此阶段诗人们的生态视野也更为开阔,生态忧患意识更为显豁,例如江天、渭水、李松涛等诗人的生态诗歌创作就极大地拓展了当代诗歌的生态视野,让所有生态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时的诗歌观照。于坚、哑石等诗人主动地开始承接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生态智慧,吉狄马加、倮伍拉且等少数民族诗人则主动去寻觅本民族的传统生态智慧,从而使得当代生态诗歌出现了较为鲜明的本土化特色。
三
相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生态问题成为新世纪头20年代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SARS病毒爆发、汶川大地震、南方冰雪灾害、舟曲地震和泥石流灾害、玉树地震、几乎覆盖全国的雾霾、年年频见的洪灾和旱灾再加上2019年以来的新冠疫情,来自大自然的各种灾害横扫人类社会。更兼网络的普及,人们更容易获得各种资讯,因此绝大部分人都开始觉察到了生态危机的全球性爆发。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也积极地宣传生态文明建设,强有力地把生态文明确定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之一。因此,生态诗歌也像其他生态文学体裁一样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阶段。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华海非常专注于生态诗歌的创作,并带领许多志同道合的广东清远诗人组成了清远生态诗歌群落。华海已经出版了《华海生态诗抄》《静福山》《华海微诗集》《蓝之岛》等生态诗集和生态散文诗集《红胸鸟》,还编辑了两部生态诗评论集《当代生态诗歌》《生态诗境》,还主编有《庚子生态诗歌选本》等生态诗集。他的“静福山”系列组诗在当代生态诗歌中占有较重要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他借助“清远诗歌节”的平台,继续鼎力推进当代生态诗歌的创作和研究,例如2015年第二届清远诗歌节就以“山水田园诗歌的变革与走向”为主题,2018年第五届清远诗歌节则以“诗歌中的生态焦虑和梦想”为主题,2019年第六届清远诗歌节暨国际生态诗歌笔会聚焦“山水清音 澄明之境”,邀请国内多位知名诗人、学者参与研讨、对话,极大促进了当代诗人生态意识的觉醒和深化。在华海的倡导和示范下,有不少清远诗人越来越关注生态诗歌,例如唐德亮、唐小桃、汤惠群、李衔夏、梁晶晶、温建文等。他们对清远的笔架山、静福山、北江、江心岛等地域的生态较为关注,他们的生态诗歌写作具有鲜明的在地性,他们也普遍具有较为自觉的生态意识。应该说,清远生态诗歌群落渐渐显示了生态诗歌的地方化、流派化的倾向。这是目前国内第一个流派性质的生态诗歌团体。
其次,吉狄马加倡导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也极大地促进了新世纪诗人生态意识的觉醒。2007年8月,由中国诗歌学会与青海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青海举行,以“人与自然和谐世界”为主题举行了诗歌高峰论坛。吉狄马加在《青海湖诗歌宣言》中说:“现在,我们站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向全世界的诗人们呼唤:在当今全球语境下,我们将致力于恢复自然伦理的完整性,我们将致力于达成文化的沟通和理解,我们将致力于维护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念……我们永远也不会停止对诗歌女神的呼唤,我们在这里,面对圣洁的青海湖承诺:我们将以诗的名义,把敬畏还给自然,把自由还给生命,把尊严还给文明,把爱与美还给世界,让诗歌照亮人类生活!”[6]吉狄马加在诗歌宣言里非常强调自然伦理的完整性,强调敬畏自然,这无疑与新时代生态诗歌的伦理旨趣不谋而合,因此对于敦促中国诗人的生态意识的觉醒而言具有振臂高呼的重要意义。
再次,出现了集团式的中国生态诗歌团队。2009年8月16日在北京大学燕园宾馆2219房间,中国生态诗歌团队宣布成立,主要成员有华海、侯良学、红豆、姜长荣。他们提出要用生态的视角打量世界,用诗歌发出生态的警报,呼吁人们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反思现代文明。中国生态诗歌团队随后注册了生态诗歌的博客,不断吸引全国各地的生态诗人加入,不时更新生态诗歌博客。团队成员华海、侯良学都成为了中国当代生态诗歌的代表性诗人,出版了多部生态诗歌集,红豆也出版了生态诗集《液体的树》,为中国当代生态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又次,许多重要诗人在新世纪都倾力于生态诗歌创作,并创作了许多富有艺术魅力、社会影响较大的力作,例如吉狄马加、雷平阳、李少君、李琦、李元胜、阎安、宗鄂等。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裂开的星球》把彝族神话传说与现代生活熔于一炉,批判了现代人对待大自然的急功近利的恶劣态度,构筑了一种气魄宏大、视野开阔、众生平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态整体观,堪称当代生态诗歌的新经典。雷平阳从第一部诗集《雷平阳诗选》开始就非常关注生态问题,他的诗歌《杀狗的过程》把人类对待其他自然生命的暴虐态度写得令人毛骨悚然,从而呼唤人与自然生命的和谐相处。至于雷平阳的《大江东去帖》《昭鲁大河记》等诗歌对云南自然生态的诗意展现,气象雄浑,境界壮丽。雷平阳在他的生态诗歌中有意复活云南大地的万物有灵论,抵御现代化的钢铁步履,捍卫大地伦理的完整性。而著名诗人李少君也是具有自觉生态意识的诗人,他的《我是有背景的人》《神降临的小站》等诗作极好地把握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合适位置,跳脱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生态诗意。李少君有意接通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历史文脉,多以山水诗歌致敬诗仙李白,把山水自然视为精神的教堂。著名诗人李琦的生态意识勃然生成于四处漫游之际,她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礼赞自然,《一棵树的修行》赞美那些能够傲寒而立的北方之树,《大海苍茫如幕》赞美大海浩瀚的厚重和无与伦比的魅力,《那拉提》赞美新疆那拉提草原的出尘之绝美。李元胜则借助对昆虫之美的探访深深地楔入大自然,他的诗集《无限事》中生态诗歌比比皆是,例如《青龙湖的黄昏》写诗人融入自然的高峰体验,《散步》写人与大自然的交互影响,《紫色喇叭花》写喇叭花的美,《喀纳斯镇的独自散步》写新疆喀纳斯的巧夺天工的美,《雨林笔记》写诗人对热带雨林的热爱,这些生态诗歌就像晨光中的粒粒露珠一样晶莹剔透,沁人心脾。而阎安的诗集《自然主义者的庄园》中散布着不少构思精巧、生态意识鲜明的生态诗歌,例如《有鹤的悬崖》写风景区中的垃圾污染,《砍树的人》批判那些砍树破坏生态的人,《我想去的地方》则表达了诗人归隐自然的生态理想。宗鄂也颇具有生态意识,他的诗歌《悼念一片桑树》写桑树被伐让故乡裸露游子痛心的生态悲剧,《干涸的河流》写河流断流的生态悲剧,《发菜》写过度搂发菜造成草原沙化的生态悲剧,《早市》则从菜市场中被宰杀的鸡鸭看到家养动物的生存悲剧。从这些诗人诗作可以看出,到了新世纪,生态诗歌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已经成熟,诗人能够驾轻就熟地掌握生态题材,选取的视角也极具个人化特色,因此避免了大而化之的概念化弊病。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开始出现了若干非常专注于生态诗歌创作的诗人,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就。除了上述的华海、侯良学、红豆之外,还有比较典型的生态诗人,如敕勒川、沈河、哨兵、徐俊国、津渡、张二棍等。敕勒川长期在内蒙古生活,颇受蒙古族敬畏天地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的诗集《细微的热爱》中生态诗歌较多,多描绘诗人敬畏自然、热爱生命的生态情感。沈河长期生活在福建三明,从事林业工作,他的诗集《也是一种飞翔》《相遇》中多关注福建三明的生态,构建了一个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青印溪,在当代生态诗歌发展史中占有一定地位。哨兵长期在湖北洪湖生活,非常关注洪湖的生态问题,他的《江湖志》《清水堡》《蓑羽鹤》《在自然这边》等诗集中大部分诗歌都是地方感鲜明、富有生态关怀、艺术魅力较高的生态诗歌,他的长诗《水立方》主要展示了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期洪湖的生态恶化问题,可以与于坚的长诗《哀滇池》遥相呼应,堪为当代生态诗歌的典范之作。徐俊国曾长期在山东平度农村生活,延续了陶渊明、王维、孟浩然式的山水田园诗风,不过他更关注的是当前乡村的生态问题,是如何与大地上的自然万物重修旧好,因此他的诗歌《鹅塘村纪事》《燕子歇脚的地方》《自然碑》中也出现了大量同情弱小的自然生命、讴歌大自然的生态诗歌,《道歉》写诗人对万千自然生命的愧疚之情,《小学生守则》颁布要尊敬自然生命的新守则,《自然碑》则写珍稀动物灭绝的生态问题。津渡则长期生活在杭州湾地区,喜好观鸟,热爱自然,他的诗集《山隅集》《穿过沼泽地》《湖山里》中也颇多生态诗歌,多描绘诗人观鸟、旅行时的生态体验,具有自觉的生态整体观。诗歌《穿过沼泽地》可以视为津渡的代表性生态诗歌,主要描述诗人在沼泽地观鸟时的体验,行文流畅,若行云流水。津渡在诗歌《穿过沼泽地》中写道:“我与万物之间的相互磨损/我借助了你们,在尘世间站立/在高高的天穹下,沼泽/一只硕大的眼球上不停地游走/孤苦地徘徊,漂泊,终于/全部转换为无尽的喜悦”。[7]由此可见,诗人津渡在大自然中才体验到生命真正的喜悦。张二棍是近年迅速崛起于诗坛的青年诗人,他的诗集《旷野》《入林记》《搬山寄》中也颇多生态诗歌,这与他来自乡村、从事地质工作有关。他写生态诗歌也多关注那些备受人类压榨、凌辱的弱小自然生命,写出了它们的含辛茹苦、血泪悲剧,从而呼唤现代人能够尊重生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他的《一个人的阅兵式》《瑟瑟发抖就是反抗》《庭审现场》等诗歌都是角度新颖、震撼人心的生态诗歌。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新世纪同样出现了不少生态意识鲜明、艺术风格独具的少数民族诗人,除了吉狄马加、倮伍拉且在此阶段继续创作了不少生态诗歌之外,还有藏族诗人列美平措、刚杰·索木东,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蒙古族诗人斯日古楞、斯琴朝克图,苗族诗人吴凌,白族诗人何永飞等。他们的不少生态诗歌都能够深入本民族传统文化中,面向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可怕现实,呼唤生态意识的觉醒,例如斯琴朝克图的《把地球留给孩子们》,鲁若迪基的《一个山民的话》,列美平措的《许多景致将要消失》等等。倮伍拉且致力于在诗歌中重塑大凉山的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书写彝族人的万物有灵论,抒发众生平等、万物一体的生态高峰体验,例如他的《常常有那样一个时刻》等生态诗歌形神兼备、意蕴深远。鲁若迪基则在生态诗歌中传达普米族的韩规文化,呈现小凉山的地域特性,他的《斯布炯神山》《果流》等诗歌不但表现出诗人浓郁的恋乡情结,而且呈现出生态诗歌鲜明的在地性。何永飞则对云南大理白族人生活展开了动人的生态审美书写,他的诗歌《海舌》写大理洱海的美及其面临的生态危机,《万物有灵》写白族人对万物有灵的信仰,《对神招供》写自然万物其实都是神的化身从而也表现出泛神论式的生态诗意。纵观新世纪头二十年的生态诗歌发展,当代生态诗歌的确出现了诗人荟萃、佳作迭出的繁荣景象。相对于此前的生态诗歌多处于不自觉的状态,此阶段的许多生态诗人不但从事生态诗歌创作,而且具有较为自觉的理论意识。例如华海曾的《关于生态诗歌的对话》《敞开绿色之门:生态诗歌——对自然的联接、体验和梦想》等文章对生态诗歌的定义、特性就曾做出较为明确的厘定,尤其是他把批判性、体验性和梦想性视为生态诗歌的核心特质,具有较大的创新性。至于吉狄马加的《青海湖诗歌宣言》则可以视为当代生态诗歌的理论觉醒的标志。此阶段的生态诗人也具有更为开阔的全球性生态视野,例如吉狄马加的《裂开的星球》就是典型例证。而与全球性生态视野并行不悖的是,此阶段生态诗人大多培育出鲜明的地方意识,例如雷平阳、沈河、华海、哨兵、徐俊国、津渡等无不如此。更为重要的是,雷平阳、李少君、华海、哨兵、津渡等生态诗人均有极为自觉的传统文化意识,他们的不少生态诗歌就好像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后现代复活,极大地提升了当代生态诗歌的本土性和艺术性。
结语
整体观照近四十余年的当代生态诗歌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生态诗歌经历了从最初的零星绽放到新世纪的大面积崛起的过程,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如果我们披览一下历届鲁迅文学奖中获奖诗集,我们可以发现生态诗歌在许多诗集中占比较高,获奖诗人具有较为自觉的生态意识。例如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中,李松涛的《拒绝末日》、李瑛的《生命是一片叶子》、韩作荣的《韩作荣自选集》、沈苇的《在瞬间逗留》;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于坚的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李琦的《李琦近作选》、雷平阳的《云南记》等诗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阎安的《整理石头》、李元胜的《无限事》等诗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张执浩的诗集《高原上的野花》等。这些诗集中,生态诗歌较多,而且艺术水平较高,许多诗人常常能够从人们习焉不察之处发现生态意识的盎然诗意。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当代生态诗歌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价值:
其一,当代生态诗歌为中国新诗重塑了生态维度。中国新诗长期以来多崇奉现代化的主流价值观,相信进步、发展、科技、民主等通约价值,但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对自然生命素来缺乏足够的思考和观照。而当代生态诗歌真正彻底地反思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立场,提出尊敬自然、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观,从而为中国新诗刷新了生态维度。
其二,当代生态诗歌为中国新诗重振了地方维度。中国新诗也曾一度丧失了地方维度,多被现代化、革命意识形态的时代大潮裹挟而去。但是当代生态诗歌却重回地方,呈现了特定地方的生态现状和理想,例如于坚、雷平阳对云南的诗意书写,吉狄马加、倮伍拉且对四川大凉山的深情描绘,鲁若迪基对小凉山的耐心抚摸,哑石对四川青城山的诗意品味,华海等诗人对广东清远的诗意构造,沈河对福建三明青印溪的精妙刻画,哨兵对湖北洪湖的详细踏勘,徐俊国对山东平度鹅塘村的耐心观察,津渡对杭州湾湿地的精美描绘,等等,都是当代生态诗人复活地方的重要努力,他们以生态诗歌有力地阻止了非地方化的异化泛滥。
其三,当代生态诗歌重新复活了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文学传统。古典山水田园诗歌虽然与当代生态诗歌存在着较为鲜明的差异,但是其中蕴含着亲近自然、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智慧如今在当代生态诗歌中得到较为完美的赓续。许多当代生态诗人都对传统山水田园诗人保持着高度的敬意,例如于坚之于李白、苏轼,雷平阳之于杜甫,李少君之于李白,哑石、华海之于王维,哨兵、徐俊国、津渡之于王维、孟浩然等。他们尽可能地复活了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宝贵遗产。
其四,当代生态诗歌极好地促进了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无论是当代生态诗人的生态批判,还是当代生态诗人对地方的关注、对传统生态智慧和西方生态伦理的诗意表达,都可以极好地促进读者重建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促使读者积极地反思现代文明,为生态文明的转型做出应有的文学贡献。
诗人于坚曾在《便条集·9》中写道:“把春天说成神庙把树说成神衹/只是一个非法的比喻/我只有比喻而已/也许会有人因此改变想法/收起斧子开始倾听”[8]。生态诗歌也是一种比喻,它试图改变的是现代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希望现代人放弃那种对待自然永无餍足的功利主义、敲骨吸髓式的利用、支配和征服,能够“收起斧子”,开始倾听大自然的声音,也倾听生态良知的声音,谨言慎行,节制欲望,物质简朴而精神丰盈,与自然万物和谐地诗意地生活在大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