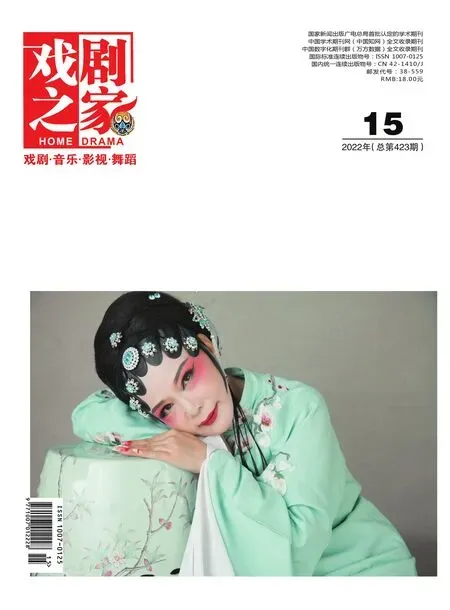一曲生命的挽歌
——浅析萧红《小城三月》中的女性意识
2022-11-12史晓红
史晓红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 郑州 450000)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称不上大家,但就性别而言,她是一位女作家,她将这种性别意识深深地嵌入她的作品,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因而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萧红在短暂而颠沛流离的一生中,受尽了人间的苦难,但她一直坚持以女性意识为基点进行创作,她的作品所展现的是对封建思想笼罩下女性苦难命运的思索与觉醒。女性意识贯穿于她创作的始终,从早期《王阿嫂的死》到后来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再到后期代表作《小城三月》,都是透过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揭露农村女性的苦难生存状态,这些作品寄托了她对男权社会下受压抑女性群体的终极审视与深切关怀。《小城三月》是萧红在病榻上留给世界的遗言,讲述了一个青春少女无法把握自己的爱情而最终走向毁灭的悲剧故事。
一、女性生存体验
相对于男性意识而言,女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更多地体现为女性作家以自己独特的性别视角对社会历史、女性生存状态以及女性内心世界的独特感受与把握,女性意识是女性作家自我意识的流露和体现。作为女性作家的萧红,正是凭借着女子的敏锐以及她所经历的人生苦难,在作品中不断思考中国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投射她对女性悲剧的自我体察与情感认同。
《小城三月》于1941 年发表于香港《时代文学》,是萧红的后期代表作,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封闭落后的北方小城的“我”的翠姨的爱情故事。小说一改萧红前期作品中的冷静与嘲讽口吻,而是洋溢着温情,像三月的春风一样轻抚着大地,只是,这春天过于短暂,美好过后,又留给世间无尽的凄凉。就在这部小说发表几个月后,这位有前途的作家与世长辞,留给后人无限的痛惜与感慨。读《小城三月》,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苦难而短命的女子萧红,在生命结束之时,依然在费尽所有力气去挖掘与寻找人世间的温情,渴望着爱与幸福。《小城三月》的主人公翠姨,是萧红小说中女性美的典型代表,“长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地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她伸手拿樱桃吃的时候,好像她的手指尖对樱桃十分可怜的样子,她怕把它触坏了似的轻轻地捏着。”不管是相貌还是性格,翠姨身上皆承载了东方传统女性之美,就是这样一位温柔恬静、端庄大方的女子,依然没有逃脱封建思想的毒害,成为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萧红笔下的翠姨,出生在旧式家庭,由于她母亲先前是寡妇,因此受到族人的歧视,这造就了翠姨感伤的气质。尽管翠姨出身的小城是落后的,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吹起的思想解放的春风,还是吹到小城的一些角落,召唤着一些黑暗中的人们走向觉醒。小城里有洋学堂,男子中学的学生是洋化的,他们穿着裤子,见了女性也不再像传统的书生那样会脸红。尤其是“我”成长于其中的大家庭,思想很开放,大家在家可以打网球、弹筝、吹箫,叔叔、哥哥们都去哈尔滨读书,有时回来甚至会谈论学校里男女自由恋爱的事,“一切都很随便,逛公园,正月十五看花灯,都是不分男女,一起去”。在“我”家的时光,翠姨无疑是快乐的,然而,这种自由轻松的环境也燃起了翠姨作为少女的梦,她悄悄地暗恋上了“我”的堂哥,但这种超越辈分和世俗的爱,翠姨只能将其苦苦地埋藏在心底。后来,翠姨与“一个长得又矮又小,穿一身蓝布棉袍子,黑马褂,头上戴一顶赶大车的人所戴的五耳帽子的年仅十七岁的陌生人”订了婚,刚开始,翠姨似乎没有任何反抗,但她内心那种对堂哥的爱慕却在日益膨胀,终于有一天,在婚期越来越近,无法改变事实的时候,她决定依从自己的心,勇敢地将对堂哥的爱同躯体一起带进坟墓。
萧红对翠姨出身的安排,寄托着她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感慨。通常,大家都喜欢回忆自己的童年,那里充满了无忧无虑的快乐,然而,对于出生在旧式家庭的萧红来说,苦难似乎从她出身的那一刻起便紧紧地跟随着她。她的童年记忆是重男轻女的母亲用石头砸她,祖母用针刺她的手指,继母虐待她,父亲辱骂她……长大对她而言又意味着,自己变成一件商品被贪婪的父亲拿去出卖。父亲为了攀附高门,把萧红许配给了呼兰驻军游击帮统领王廷兰的次子王恩甲,为了摆脱封建包办婚姻,她不得不大胆离家出走,开始了漂泊的一生。无论生活多么苦痛与凄惨,萧红都没有放弃过对真爱与世间温情的追求,直到最后,萧红在孤独中客死于香港,年仅31 岁。萧红和翠姨一样,都不满无爱的婚姻,终以寂寥的死来抗争。
二、男权下的女性命运
作为一位饱受封建父权势力和男权势力双重压迫的女性,萧红的人生是凄苦不幸的。作为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而觉醒的女性,这些凄苦的人生体验又激发了她鲜明独特的女性意识,影响了她的创作。萧红对女性命运的洞察是细致而深刻的,她的作品不仅是要唤醒人们对女性悲惨命运的认识,同时也是为了消解男权社会下的男性威望,呼唤男女平等。《小城三月》的主人公翠姨,出生在中国最北边的小城,这个小城是偏僻落后的,是被封建男权思想笼罩着的。这里的女性的思想长期处于一种被压制的扭曲状态,她们无法与社会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小说中,作者不惜笔墨描写翠姨在举止投足间所展现的温婉、娴静、矜持和端庄的大家闺秀气质,作者甚至用翠姨亲妹妹与翠姨作对比,诚然,翠姨可以像她的妹妹一样大说大笑、疯疯癫癫,但翠姨没有。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说过,“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成女人的。”在封建传统文化熏染下的翠姨,早已在心底形成一套审美标准和道德典范,并默默遵守。“假若有人在她的背后招呼她一声,她若是正在走路,就会停下;若是正在吃饭,就要把饭碗放下,而后把头向着自己的肩膀转过去,而全身并不大转,于是她自觉地闭合着嘴唇,像是有什么要说而一时说不出来似的……”,在小说中,作者通过讲述翠姨买绒绳鞋的故事,展现了翠姨内心深处强烈的宿命意识。在满城流行绒绳鞋的时候,翠姨的心里已经生起了对绒绳鞋的喜爱,只是她一直在压抑着自己的欲望。当这场流行风逝去的时候,翠姨还是忘不了对绒绳鞋的喜爱,邀“我”去逛街,逛了一家又一家,刚开始,“我”始终不知翠姨要买些什么,直到后来,翠姨悄悄告诉“我”要买绒绳鞋,“我”用孩子般的童真去安慰她一定能买到,并热情帮助她寻找,不错过任何一家店铺,可最终,我们也没有买到合乎翠姨心意的绒绳鞋,最后,翠姨发出的感慨是,她的命不会好的。其实,不仅是翠姨对绒绳鞋的喜爱,她对待任何东西的喜好,都是默默放在心底,不告诉任何一个人,也不争取,包括她对“我”堂哥的暗恋。
翠姨这一带有悲观宿命色彩的性格特点,实质上是“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封建思想钳制下中国底层女性的共性,她们的思想被禁锢、行为被规范,又无力反抗,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翠姨始终牢记着,自己是出嫁了的寡妇的女儿,这反映出她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将社会的、外在的压抑内化为自身的、自我的压抑。
三、挣扎与毁灭
萧红一生都在努力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争取女性自由思考与独立生存的空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春风为她提供了契机,她坚持用自己的写作、自己的话语引导女性觉醒,引领女性摆脱封建思想的枷锁,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然而,面对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文化,和男性主导的社会现实,女子的力量毕竟是微弱的,她只能用尽全力去挣扎与反抗,最后走向毁灭。《小城三月》对女性意识的展示,是萧红在生命的最后对女性觉醒和解放的思考。
翠姨的故事开始于阳春三月,三月的空气里充满着蛊惑与躁动。翠姨在“我”家开放自由的家庭氛围影响下,接受了一些新鲜的东西,穿高跟鞋、弹琴、打网球,和堂哥、叔叔们一起玩耍。在不知不觉中,翠姨内心深处尘封的爱情意识被唤醒,她悄悄地爱上了“我”在哈尔滨读书的堂哥。堂哥“很漂亮,很直的鼻子,很黑的眼睛,嘴也好看,头发也梳得好看,人很高,走路很爽快。大概在我们所有的家族中,没有这么漂亮的人物”,同时,堂哥还有学识,这一切都吸引着翠姨,因此,堂哥讲故事的时候,翠姨比大家更专注,凡是有堂哥参加的活动,翠姨定要更加精细地打扮自己。翠姨虽是客人,但她得到全家人的喜欢,享受着家庭的温暖。然而,对于翠姨来说,大家给她的关心与爱护只是带给了她表面的欢快,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她的内心,作者高明之处在于,把“我”安排为一个儿童,懵懵懂懂的“我”不明白大人世界的感情,更给予不了翠姨大胆追求内心真爱的鼓励和勇气。翠姨毕竟是一位背负沉重传统观念包袱的柔弱女子,她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自己是出嫁了的寡妇的女儿,自己的命是不会好的,她的爱只能在心底悄无声息地萌发,悄无声息地毁灭。她按照那个时代家长的安排,接受了和一个长得很丑的人的婚约,也接受了对方家的聘礼,并且用这些聘礼风光一时。但在婚礼一天天逼近时,翠姨才意识到这种生活的可怕,她再一次正视自己的内心,开始用置办嫁妆、读书等借口来拖延婚期。但她没有想到,哈尔滨置办嫁妆的所见所闻,更是让她对自己未婚夫生出前所未有的不满,但她又无力改变已经订婚的事实和自己的命运,她唯一的选择便是去糟蹋自己的身体,用死来表示自己对生的绝望。
四、结语
萧红对底层女性生命意识的探索,表现出作者自己独特的个性。在《小城三月》中,萧红以女性作家的眼光和审美视角,进入到充溢着梦幻与憧憬的家乡,小说在诗意中透露着生命的苍凉。三月的春风是温和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东北的这片土地,春去春又回,“年轻的姑娘们,她们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没有人曾注意到,载着翠姨的马车将永远消逝在这三月的春风里,萧红用翠姨的死来表达自己在生命意识觉醒后的反抗,企图唤起中国广大的麻木、愚昧的底层女性的女性意识、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