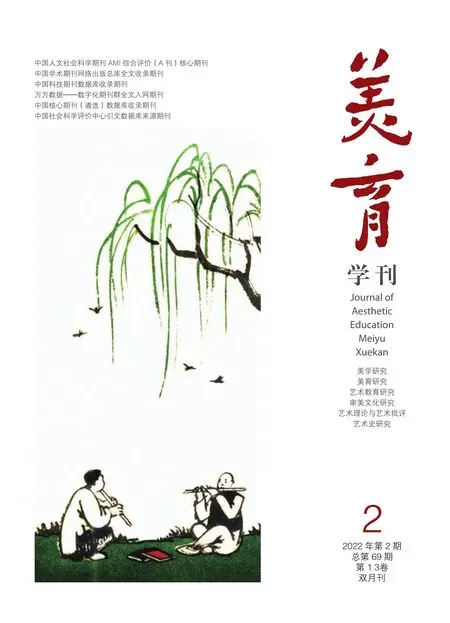陈世骧论“时间”新探
2022-11-11胡旻
胡 旻
(成功大学 中文系,台湾 台南 701301)
一、导言
诗人杨牧(1940—2020)曾说:“陈先生论古典文学,屡次探讨时间的意义,这方面的关注已经构成他的文学观之骨干。”作为陈世骧的弟子,杨牧正确地指出“时间”议题之于陈氏理论的重要价值。学界关于陈世骧之研究,多集中于“抒情传统”说,鲜少注意其论时间的相关论述。实际上,陈世骧在阐发中国文学“时间”主题上富有创见,值得探讨。
陈世骧论时间,最值得探讨与省思者有两处:其一,陈氏精心构建中国式悲剧观,视命运为时间空间无尽流转,以此发掘杜甫《八阵图》之悲剧精神。该理论雏形为1958年6月7日陈世骧在台湾大学文学院的第三次讲演辞,录为文字稿题为《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10年后终稿为英文版,题为“”(《〈八阵图〉圜论》),发表于台湾《清华学报》新7卷第1期(1968年)。其二,陈氏以“时间性”为轴心,绾和屈原《离骚》各要素,解读此诗的时间意识。见于其:’ü,(《论时:屈赋发微》),作为遗稿收录于台湾《清华学报》新第10卷第1期(1973年),后经古添洪中译,刊登在《幼狮月刊》第45卷第2-3期(1977年)。
在陈世骧所处年代,中西比较文学方兴未艾,探讨中国是否有悲剧等议题,颇受学界关注。不过,研究者无论观点几何,多囿于戏剧范围内做比较研究,并常以中西戏剧对举论证。陈世骧却独出机杼,不拘限于同一文类比较,主张中西文学皆有悲剧精神或意识,但二者表现方式有所差异,并藉由杜甫《八阵图》构建一套中国式悲剧理论,论命运与时间空间之关联,又引入比利时戏剧家梅特林克“静态悲剧”说,进一步阐发其特征。陈之说法,虽有舛误,但瑕不掩瑜,本文尝试梳理其中国式悲剧观之精义要点,修正讹误并重述中国命运观。
陈世骧论屈原《离骚》的时间意识,更是其晚年思想精华所在。时间主题本身即是中国文学研究之“大哉问”。陈氏以“时间性”概念切入《离骚》,提出新解,令人赞叹。不过《论时:屈赋发微》一文为身后遗作,亦有草就之处,尤其在引诗方面甚为简略。故本文论述在突出其精要基础之上,将辅以更多《离骚》诗例作为旁证补充。本文以整理陈世骧时间理论为契机,期待学界能重新关注其思考时间的路径及优点。中国诗人对时间敏感者,又何止屈子一人?当再论其他作家时,陈氏之所言所想,必值得借鉴与延伸。
二、中国式悲剧理论建构
(一)古希腊悲剧观概述
陈世骧构织中国式悲剧观,基本以古希腊悲剧为参照模型而加以修改。后者通常展现英雄受难经过,凸显人与命运之冲突,故常被视作命运悲剧。命运实为核心要素,指称一种外在或内在的必然性力量。其特征有二:其一,神秘晦涩,难以测度且超越理性与道德,故命运与惩恶赏善或因果报应无涉。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说:“上帝抚平其仆人的厄难;他补偿约伯遭受的折磨。然而凡有补偿和正义,则不是悲剧。”换言之,不必诉诸命运的公理正义与否,更无合理解释。其二,命运多与神祇有关,表现为具体神明或神谕(oracle)。如古希腊神话中命运化身为三女神:克洛托司职纺织命运之线,拉克西斯工于赋予与摆弄,而阿特罗波斯负责剪断。又如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主角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命运,是经宙斯的神谕道出。总之,古希腊悲剧中命运指涉一种神秘难解、超越理性道德的必然力量,常具神格化面貌。
在古希腊悲剧中,英雄之意志与命运常构成直接且戏剧冲突的关系,以显示人之动作(行动)与处境。英雄殒命的意义有二:其一,结局主人公必然败北且无救赎与补偿,展现人之脆弱有限。其二,由于主人公直面命运挑战,并与之抗争,表现人之高贵与尊严,可谓虽败犹荣。姚一苇说:“悲剧英雄即使在无可逃避的命运的摆布下,他也没有被压倒,敢于以自己的有限向无限挑战,作着悲壮的选择,以证实自己的品质的高贵和人性之不可侮。”悲剧展示主人公遭逢命运拨弄,蒙受苦难,旨在引起观众恐惧与怜悯之情,进而达到净化宣泄情感之目的。
(二)杜甫《八阵图》中的悲剧精神
西方悲剧理论固然精深复杂,但其要义不外以上所言。陈世骧为与西方悲剧理论相颉颃,精心构筑了一套中国式悲剧论述,并以此重读杜甫《八阵图》一诗,发掘其中的悲剧精神,本文从以下三点入手,详述命运定义及其与人之关系、省略动作特质与《八阵图》细读。
首先,论及中国文学里的命运,陈世骧认为:
不像希腊命运以三女神形象出现,对中国人来说,这个巨大无可抗拒且不可见的命运,我认为,经常以时间与空间的空白形象现身,看似无所作为,却无穷流转,改变万物。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思考命运的力量,称其为“命运”或“时运”即“注定的运动”或“时间的运动”。命运常具象化为巨大的节奏,无人格且不可抵抗地运转着,其无穷无尽远超单独个体范畴。
运即运动流转,中国式命运并无神(人)格化特征,常以无限流转的时间与空间形象现身。另外,英雄与命运之关系不依靠冲突,而是呈现“反映与对照”(reflection and contrast)。
其次,中国式悲剧里多省略动作书写,与西方传统悲剧强调动作相比,大异其趣。为阐发此特征,陈世骧援引比利时现代戏剧家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创立的“静态悲剧”(static tragedy)说,意在论证《八阵图》省略动作描写,与静态悲剧契合。因此处涉及面较广,陈氏亦仅一笔带过,未见详论,本文则接续探问,旨在论述中国式悲剧与静态悲剧之相契,并探讨《八阵图》省略动作特色与中国诗学传统的关联性。
梅特林克所谓“静态悲剧”有两个特征:其一为关注日常世俗生活,展现“日常平凡存在中的美、宏伟和庄严”。梅氏有此论调,主要针对西方悲剧传统着眼于不平凡的事件与人物:
但对于悲剧作家而言,如同仍执着于历史画卷的平庸画家,唯有暴力的轶事传闻才具吸引力,其作品的全部旨趣即在此。他以为,野蛮土著人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如谋杀、暴力、背叛,我们也会津津乐道。然而,我们大多数人早已远离流血、喊杀、剑刺,现今,人的眼泪是无声无形的,几乎是精神面向的……
梅氏认为现代生活平稳安定,早已远离暴烈事件,故悲剧作家不应再取材于奇情奇境。其实西方传统艺术,不限于悲剧,通常借鉴重大历史事件,人物多以英雄为主,反观西方现代主义则一反传统,关注日常生活及平凡人物。威廉·白瑞德(William Barrett)称之为“价值的削平”,即打破“伟大和粗鄙之间的严格分野”:
而这一切和西方艺术的传统大异其趣;西方艺术对伟大和鄙陋区分得一清二楚,并且规定最高尚的艺术应处理最伟大的题材。……画家应当描绘福音书里绝伦的景象、伟大的战役,或是高贵的人物。……时至今日,等级说法已经完全废弃。立体主义者追随塞尚,以普通的桌子、瓶子、杯子、吉他之类作为他们最伟大绘画作品的主题。
梅特林克的戏剧,包括之后契诃夫、贝克特等人的作品都可印证,现代主义确实更加关注现代人平凡庸常生活的书写。
“静态悲剧”第二个特征是减少动作、淡化冲突甚至削弱情节:“真正优美伟大的悲剧,其特出之处不在行动而在语言。”该主张意在反叛西方戏剧强调动作或行动(action)的传统。描绘英雄勉力搏斗是古希腊悲剧的要件之一,亚里士多德《诗学》对悲剧的典范式定义为:“悲剧是对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magnitude)之行动的模仿。”亚氏亦将行动视为悲剧之核心:“悲剧并非对人的模仿,而是对动作及生活的模仿(生活由行动构成),悲剧旨在呈现行动状况而非品质。性格(character)决定人的品质,而他们幸福与否则取决于行动……无行动则无悲剧,但无性格,仍不失为悲剧。”
陈世骧构建的中国式悲剧,基本与梅特林克“静态悲剧”说两特征相契合。相较于西方悲剧或史诗擅长书写英雄行动事迹宛如目前正在发生,《八阵图》则是诗人面对废墟有感而发,以哀歌方式,追忆诸葛亮,却减少动作描绘。玛丽·陈(Marie Chan)探讨唐代咏荆轲诗发现,《史记》特重荆轲刺秦王的动作展现,中国诗在书写同一段历史,却往往省略动作和戏剧冲突,选择易水离别场景,刻画一个失败的英雄形象。
陈世骧结合上述中国式悲剧模型,重读杜甫《八阵图》诗: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因文类(literary genre)皆有其成规定式,故陈氏先以此角度观察此诗。《八阵图》虽属五绝,但突破了既有文类窠臼,表现有二:其一,五绝通常书写人与自然之互动融合,重点落于自然界,而《八阵图》则反之,强调人世;其二,五绝风格多为优美,而《八阵图》则展现出悲壮情调即陈氏所谓的悲剧精神。
第一、二句极言事业功名之盛,但转入第三句:“八阵图”即诸葛亮创制的操练或作战垒石阵法,在江水冲击下变为残石遗迹,提示人世功业的短暂易逝,但重点不在于此,细味“江流石不转”,即江水流动,残石却屹然不为所动,强调残石之于江水的默然抵抗。陈氏认为,江流意象实为命运即无穷运转时空之象征,而残石则是诸葛亮赍志而没、遗留千古怅恨的化身,可得出两组对照关系:残石与江流、遗恨与命运。
因此,陈世骧关于《八阵图》的观点可归纳为:即便命运即时间之无尽运转,具有摧毁一切的能力,但英雄之无限怅恨,默然承受并超克命运的流转磨蚀,依旧挺立不坠,一如残石抗拒江流冲刷,始终岿然不动。读者因有德者之陨灭,产生恐惧,又因残石与江流、遗恨与命运之间永恒的映照对比萌发怜悯。古希腊悲剧善于表现英雄与命运的冲突张力,而《八阵图》则凸显英雄遗恨与命运之映照对比关系,表现诸葛亮之于厄难的被动隐忍、默然抵抗品格。
(三)中国命运观之再思:“命”与“时”
据前所论,庶几可将陈世骧中国式悲剧理论归纳为:命运常显现为无穷运转的时间与空间,超越个体且非人格化。一方面,人生功业和英雄事迹,与命运参照,均显得短暂易逝,但另一方面,即便是丰功伟业骤降至江流残石,亦留下无限怅恨,凸显英雄之于命运的隐忍与砥砺(非冲突关系,省略动作描绘),终达成悲剧精神。此观点提出后,引发不少质疑之声,如夏志清认为:
《八阵图》明明是一首lyric,硬把它和希腊悲剧一起相提并论,也有些不伦不类。……时间空间那种demolish人生功业的感觉,差不多是present in all lyrical poetry(莎翁sonnets, Landor, Rose Aylmer, Marvell, Coy Mistress),不一定是中国诗的特征,虽然中国诗人对这一点特别敏感。而这种“人”与“时”和“人”与“地”相对照的感觉,用Brooks的irony来说明已非常adequate,不必借用tragedy的大帽子。
夏氏的疑虑,颇值得思考。若依陈氏,命运即时间与空间的无穷流变,摧毁人生功业,西方同样存在大量类似主题之诗作,故如此定义命运,显然无法使其成为中国文学之特出观念。
要之,陈世骧对命运之定义,确有值得商榷与改进之处,不过,他试图构建中国式悲剧观之大方向并无不妥,故夏氏言“不必借用tragedy(悲剧)的大帽子”的讲法,恐又显极端。实际上,杜甫《八阵图》里展现的中国式命运,不妨视为“时”,解为时运或时机。一方面,“时”“命”二字并列搭配为“时命”,有先例可循,如汉代文人严忌作《哀时命》,旨在哀叹不遇于时代。另一方面,“时”或“命”,均可泛称外部条件或环境之总和。冯友兰说:“命意味宇宙间所有存在的条件与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成功,这些外部条件的配合总是必不可少,但其并非人力所能掌控。”所谓“时势造英雄”,即是说外部环境与英雄需配合得当,当二者不合之际,则有“时不我与”之慨,如项羽的自我辩护:“时不利兮骓不逝。”
因此,德才兼备之士,如诸葛亮,诚可谓不逢其时,尤其是刘备攻吴失利后的形势:“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伐与不伐,打或不打,败局均已注定。在此时运困境中,诸葛亮仍选择勇敢担当其命运:“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后出师表》)《八阵图》凸显的正是此种绝望奋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而结局则是:无论个体如何努力皆难以逆转颓势,最终殒命,如此失败英雄的形象,引发绵绵遗憾与喟叹,是为中国式悲剧精神,故杜甫诗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悲剧倾向于详细描绘英雄的动作,而中国诗却常常省略未提。
三、陈世骧论《离骚》的时间意识
在陈世骧看来,对《离骚》研究若只关注诗人生平与名物考证,易导致文本艺术价值的轻忽,故其论《离骚》由时间角度切入。陈氏以其深厚文献学功力,整理分析《诗经》《尚书》《论语》《孟子》《庄子》等典籍中“时”之意指,并勾勒出“时”字含义之变迁历史,探讨该字如何发展为指称抽象概念的时间。最终确认,屈原是首位将“时间”观念引入文学的诗人,故曰他始创“诗的时间”(poetic time)。
(一)发现“时间性”
陈世骧拈出“时间性”(temporality)概念以切入屈原《离骚》。要言之,存在于时间中即是“时间性”:“时间的本质是时间性,步入存有,获得生命,意味走入时间,获得时间性。”有意思的是,“temporality”亦有短暂易逝之意。首先是人之存有具有“时间性”,意味存在于时间中的人,是短暂易逝、有限且向死而生的,这无疑会引发焦虑与恐惧。诚如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诗云:“在我背后总能听见/时间如带翼马车急迫逼近。”
《离骚》开头自述出生与家族系谱,即描绘存有步入时间历程,获得“时间性”。接下来便是对主观生命短暂易逝的喟叹:“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以上所论,均不难理解,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曹丕《典论·论文》曰:“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对于衰老、湮灭、死亡的恐惧,人人皆有,无需赘述。吉川幸次郎谓此为“推移的悲哀”,即由时间带来的悲哀,并提出“意识到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悲哀”主题或情感,在之前文学中表露并不明显,直到汉末《古诗十九首》,才“表露得非常清楚而强烈”。此断言恐怕颇值得商榷,因《离骚》浓烈的时间感受早已有之。
(二)以“时间性”观照万物
陈氏前述“时间性”,尚局限于主观时间(subjective time)感受,不脱东坡所谓“哀吾生之须臾”,然其理论精华关键,绝不止步于探讨一种自我主观的时间意识。既然人之存有具“时间性”,同理可知,其他事物无不沾染“时间性”色彩。陈世骧说:“就人类基本需求而言,时间性道出人类的普遍命运。此诗最深广的魅力,在其中主观时间的敏锐意识,被投射于人类、自然与超自然领域,成为贯穿整体的感伤主调。”陈氏论时间,精彩之处便在于此:由主观时间意识,扩展至人类、自然乃至超自然领域,即万物皆在时间中,获得其“时间性”。换言之,《离骚》一诗主要元素,无不身处于时间,无不浸润“时间性”,无不显得短暂易逝,故时间成为贯穿全诗之匙。现据陈世骧所言,进一步分点详论之。
1.香草。芳草变易而腐化为萧艾:“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2.道德。德性衰微,唯有群小的丑恶贪婪:“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德性高尚之君王只存在于过去:“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3.求女(或美政的象征)。《离骚》描绘抒情者求女经历,发现宓妃、有娀、二姚等玉女徒有其表,德性有亏:“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
4.超自然界。当抒情者遨游神境天际,却仍遭受时间的威胁:“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当抒情者抵达天宫之门,帝阍的冷漠,让天国成为人间的映照,美善遮蔽衰变(“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此处亦出现表时间的语汇:“时暧暧其将罢,结幽兰而延伫。”时辰向晚,天色渐暗,亦象征时代溷蒙,诗人只能原地等待踟蹰。
清人贺贻孙《骚筏》提出“变与不变”是理解《离骚》的“通篇柱子”,再结合陈世骧的观点,便更易知晓,因万物身处时间中,则始终在“变”:芳草腐败、德性颓然、求女不得、仙境失落。而寻找“不变”之物,故为诗人所念兹在兹。
(三)抵抗时间
万物皆处于时间中而衰变湮灭,无论是香草、道德、美政还是超自然界,无一不使人失望难堪。《离骚》抛出其核心疑问:面对时间何以自处?此诗抒情者怀揣追逐不朽的愿望,不随波逐流,坚守与耕耘德性,展现直面失败与绝望的英雄式勇气,维系人之尊严与价值于不坠,抵抗时间之流,成为全诗最令人心神摇荡之处。陈世骧总结道:“于本文中清楚可见,从诗的开头,人物已被卷入时光之流,载沉载浮,被它带走或与之抗衡,以几近绝望的自我肯定,坚守其人类德性、本质与存在。”
这里屈原抵抗时间的处境,以里尔克的诗来概括再合适不过——“对迅疾的流水言:我在。”纵览全诗,其抵抗时间的主要途径正是修德,即“余独好修以为常”,锻炼修养品德以为“常”(即前述贺贻孙所谓“不变”),以抵抗“时间性”之“变”。固然在此之前,他亦尝试过其他选择,只不过皆未能顺遂人意,如施展政治抱负以建功立业:“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另外,需注意的是,“远游”即空间的旅行,也是《离骚》主人公企图摆脱时间的催迫力量。换言之,对时间的恐惧焦虑以象征化的空间漫游呈现,即“将往观乎四方”。在全诗尾声描绘一场盛大华丽的巡游过程,“抑志而弥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在仿佛超越日常时间以抵达极乐之境前,主角却意识到这不过是短暂的“假日”以偷乐,陈世骧将之解释为“借来的时间”(borrowed time),暗示之前设法跳脱时间掌控的幻觉破碎,因为现实再度袭来:“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踡局顾而不行。”仆人悲伤马匹停歇,迷失于空间。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为抵挡时间之流,修德则必为首选。该行动几乎贯穿全诗,多以象征方式出现,如以香草制衣做裳,以披挂穿戴装饰其身:“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又如栽植莳养香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美善品德与其他事物,亦会于时间中凋萎变质,故抒情者需时常耕耘、采摭、养护,方可抗拒时间之劫运。
此外,结尾处乱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或视彭咸为修德保名之隐士或长生不老者,均与抵抗时间之侵袭有关。更有论者言:“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两句中食菊行为,亦含蕴不死的欲念,正源自对时间的忧虑,其后中国文学将菊花与养生成仙关联,肇始者恰是屈原。
四、结语
陈世骧所在年代,中西比较文学方兴未艾,悲剧议题颇为学者津津乐道。为与古希腊悲剧相颉颃,陈氏主张中国虽无悲剧文类,但亦存悲剧精神,且表现方式与西方悲剧不尽相同,因此精心构织一套中国式悲剧观,并以此重读杜甫《八阵图》:即便命运即时间之无尽运转,具有摧毁一切的能力,但英雄漠然承受无限怅恨并超克命运的流转磨蚀,依旧挺立不坠,一如残石抗拒江流冲刷,始终岿然不动。本文主张,中国文学里的命运应为“时”,解为时运或时机,泛指外部环境或因素的总和,而《八阵图》真正的悲剧意识是:英雄处在“时不我与”的困境里,依然绝望奋斗,最终身死殒命。陈氏的讲法或许值得商榷,但他指出的省略动作描绘是中国诗的重要特征,并与梅特林克“静态悲剧”类比,实可为今后研究可资借鉴的重要论断。
陈世骧以“时间性”切入《离骚》,绾和各要素,提出该诗的时间意识:万物无不身处于“时间”,无不浸润“时间性”,无不显得短暂易逝,并视《离骚》为诗人与时间较量的英雄挽歌,总体而言可自圆其说。就其思路而言,仍不脱英美新批评为文本寻求统合连贯之核心的路子。从其后发展来看,陈氏好友吉川幸次郎将时间主题视为《古诗十九首》关键;吕正惠认为六朝“物色”论是一种观物感物方式,“是以‘叹逝’的角度去观察大自然,从而赋予大自然以一种变动不居、凄凉、萧索而感伤的色泽,并把这一自然‘本质化’、‘哲理化’,使渺小的个人在其中感悟到生命的真相,而欷歔不已”;许又方再论屈赋的时间问题,自述是承继陈世骧衣钵,“在陈文的启迪下对此论题做了进一步的推敲”。以上例证皆可证实陈世骧时间理论的独创与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