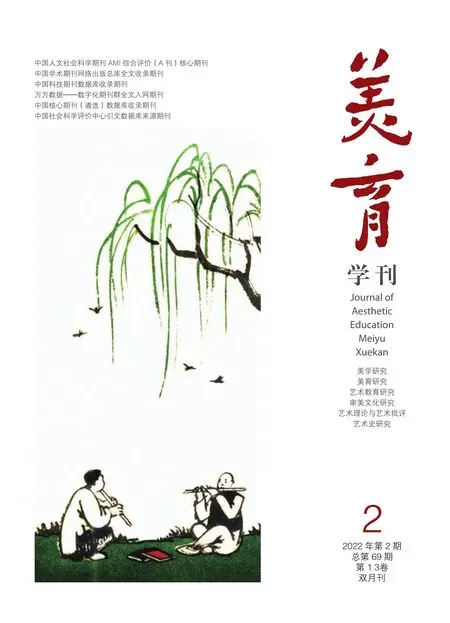比较学视域下古代艺术“南北”论及其风格范畴
2022-11-11张兰芳
张兰芳
(天津音乐学院 艺术管理系,天津 300171)
“南北”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批评中的重要论题,古人区分南北差异,起初基于地理环境的比较。在长期适应外界地理环境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不同地域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的影响制约,人类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气质性格、语音强调等方面产生很大差异,进而影响到人的审美情趣与艺术活动,也呈现出稳定而鲜明的地域特征。然而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演进,门类艺术的渐次发展成熟,不同时代理论家对艺术的认知理解、思想观念、审美情趣等都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在艺术发展至高度成熟的阶段,面对艺术实践领域异彩纷呈的风格事象,理论家不仅关注个体风格的独特性,而且更关注共性风格的相通性。从宏观层面审视艺术“南北”问题,成为理论批评的热点论题。考察历代艺术理论文献发现,古人区分南北差异,从南北艺术事象的描述到南北艺术审美特色的概括,最主要的着眼点在于风格,以简洁凝练的语词概括南北艺术整体风貌或审美特点,在艺术批评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对立性风格范畴。从整体来看,不同门类艺术“南北”论相关风格范畴,并非相互隔绝、互不干涉,而是彼此之间存在相通之处。鉴于此,从艺术学理论学科视角出发,借鉴比较学方法来探究艺术的南北差异,挖掘风格范畴的内在关联,非常重要而且必要。
一、艺术“南北”论的萌芽与事实存在
“南北”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对地理环境对人群自身及其活动的塑造作用,古人早有认知。孟子云:“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尽心上》)荀子也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儒效》)《淮南子·地形训》指出“土地各以其类生”,地理环境作为客观存在的物理空间,对生存其间的人群,不可避免地打上地域的印记,“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秏土人丑”。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南方之强”“北方之强”的对比
关于南北方的对比,最早见于《礼记·中庸》——“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在孔子看来,“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在南北方之间,缘何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呢?唐孔颖达注疏云,“南方,谓荆阳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性刚猛,恒好争斗”。宋庄绰也认为,“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这表明南北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及气候条件等客观因素对人的性格、精神具有强烈影响、塑造作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苏联学者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地理环境对早期人类活动的决定作用,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力部门的最初分布,不是取决于人的意志,也不是神的力量,而是决定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周围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性质”。地理环境为人类生存提供所需的物质资料,也影响着人类活动类别和气质品行。《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相对而言,艰苦恶劣的环境,容易培养出吃苦耐劳、勇于斗争的精神,而物资丰盈的环境,容易滋生出贪图享乐、骄奢淫逸的品性,诚如《国语·鲁语下》所云:“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响义,劳也。”从我国南北地域来看,北方高山苦寒、物资匮乏,南方丘陵平原、物资丰盈,造就了南北方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人群的精神气质,进而影响到文学艺术创作在审美趣味、风格特点上的显著差异。
(二)艺术“南北”差异的事实存在
古人区分南北差异,始于口头演唱的“南北音”比较。据《吕氏春秋·音初》载:
禹行动,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南音。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其中,“南音”大体产生于江淮流域,《诗经》中的周南、召南属于“南音”系统。而“北音”大体在河洛之间。虽然《音初》仅对不同方位人类口头演唱的早期形态做了描述,尚未采用标识风格的范畴语汇概括南北音的审美特色,但从其描述的事象差异,可推论南北方诗乐一定具有不同的风格特点。
“音”在古人眼里,具有强烈的反映功能,“音”是体现地域民俗风情、表达人的内心情感、洞察人的志趣德行、反映国家兴衰和政权统治、衡量君子小人的主要途径。“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吕氏春秋·音初》)孔子《论语·阳货》篇指出,诗可以“兴”“观”“群”“怨”,还可“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表明诗乐除了具有反映政权统治与风俗民情的社会功能,还具有认识自然环境的教育功能。因此,不同地域环境的诗歌(民歌),在风格上也必定迥然有别。
《诗经》与《楚辞》作为中国早期文学代表,具有鲜明的地域风格。《诗经》之国风大部分是北方歌曲,《楚辞》则有着浓郁的南方特色。然而一直以来,“人们尚未把南方文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系统,与北方文学分疆划派”。尤其是六朝之前,北方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人们对北方文学的关注度远高于南方。然而,自西晋以降,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分裂为南北朝,人们对南北方的认知愈加明晰,不仅限于地理环境,还有人文环境、哲学思想、审美趋向及文学艺术等方面。从六朝文论只言片语中,可以发现批评家对南北文风的认识与态度。南方刘宋文学辞藻华丽、精细柔美的文风,屡遭文论家的批评,刘勰推崇建安风骨,欣赏“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文风,力矫齐梁软媚诗风。颜之推对比南北(古今)之文,提出“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主张,正是基于对南北文风之弊的深刻反思。
就南北朝民歌来看,无论题材内容,还是情感表现、风格特色,南北差异非常明显。北方民歌多表现社会现实和男子般霸气豪情,风格粗犷豪放、刚健朴实;而南方民歌多表现男女爱情生活和游子的思乡别离志气,风格婉转清丽。南北差异之强烈,与地域环境影响下的民俗风情、审美情趣有关。及至后世形成戏曲这种综合性艺术,南北曲风差异依然与南北文风差异一脉相承。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六朝批评家尚未对南北文学(或民歌)从理论层面进行区分概括。唐以后,艺术的“南北”问题才逐渐进入理论视野。
二、“南北”论范式的初步确立
(一)“南北派”的滥觞
唐代关于“南北”的比较,率先在文论批评中展开,见于初唐形成的几部论著当中。《北史·文苑传序》云: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
此论以“清绮”与“气质”对比南北文学总体风貌和风格差异,“气质”侧重于“理”之内涵,“清绮”侧重于“文”之形式,二者各有所长,“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这里的“南北词人”既包含地域之南北,也包括历史之南北朝,特指南朝齐梁、北朝魏齐时代的南北文人。南朝文学注重音韵辞藻,文风清新绮丽,但存在“文过其意”的弊短,“一方面继承了魏晋以来文学的骈丽传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南朝文人在经济发达的社会基础上所产生的新的审美趣味”。北朝则由于战乱不断,生活条件艰苦,加之北方人性格豪爽尚实,因而文风朴实刚贞,重乎气质,但存在“理过其词”的弊短。唐人认识到南北文风差异和优劣,但更倡导“合其两长”,实现“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的艺术理想。
《隋书·文学传序》,所论与《北史》类似,论及北朝文学更为具体,列举一系列作家予以佐证,赞美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然而南朝梁大同之后,文风转向“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这种萎靡文风也波及北朝“词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直到隋唐方有改变,陈子昂疾呼“汉魏风骨”正是为了扭转齐梁以来的软媚文风。可以说,《北史》《隋书》等著述相关南北朝文学的概括总结,尤其是对各自优缺利弊的比较批评,拉开了“南北派”论文的序幕,对后世各门类艺术批评产生深远影响。
(二)“南北宗”的介入
除区分南北朝文学差异,唐人还借鉴禅学思想“南北宗”论文、论诗,为探讨“南北”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文论“南北宗”
王昌龄最早将禅学“南北宗”思想引入文论,《诗格·论文意》以“司马迁为北宗,贾生(谊)为南宗”,从评价贾谊的言论可获悉其分宗思想:“谊谪居长沙,遂不得志,风土既殊,迁逐怨上,属物比兴,少于《风》《雅》,复有骚人之作,皆有怨刺,失于本宗。”贾谊居于南方,所作辞赋与屈骚“怨刺”类似,文风失于“本宗”,即北方之“正风正雅”,遂将其作为“南宗”。王昌龄区分南北宗的依据为“风土”,属地域层面的区分。但王昌龄缘何要用南北宗论文,恐怕与唐代禅宗发展有关。佛教南北差异的起初意义基于地域差异:“世人尽传南能、北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禅师,于南荆府当阳县玉泉寺住持修行;慧能大师,于韶州城东三十五里漕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南能北秀分别在南北方弘法,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差异:中原神秀承继先祖,主张修行“渐悟”,过程烦琐,需经多年苦读苦悟,此为“北宗”;而岭南慧能未修禅学,但突然作偈,根于灵性,“顿悟”修行,方法简单高效,此为“南宗”。出于修行方式的繁简和领悟速度的快慢,区分出南北宗。当时佛教对文化艺术的影响很大,很多文士受佛教教义浸染,借用禅学南北宗论文亦在情理之中。王昌龄将“北宗”视为正宗,一方面与中国文化发源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这一事实有关,另一方面与佛教发展有关。禅门五祖弘忍之后的两位高足在南北各自形成法门,神秀在唐武后时被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作为官禅的北宗占据着佛门正统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因此王昌龄尊北宗为正宗,体现出官方正宗对文论批评的影响。
2.诗论“南北宗”
贾岛《二南密旨》“论南北二宗例古今正体”,指出“南宗一句含理,北宗二句显意”。并列举一系列诗人诗句予以佐证。相较王昌龄秉持正统,贾岛区分南北宗的标准则与句之多寡挂钩。从王、贾所处的历史时期来看,恰好反映出初盛唐和中晚唐诗风的演变。初盛唐追求浑融自然,不尚雕饰,“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练”;而中晚唐则追求清词丽句、字句雕琢、“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锤炼,更强调“一句见意”,以有限的语言表达无限的意蕴。加之中晚唐禅宗发展兴盛,安史之乱后南禅一跃成为禅门正宗,而北宗渐趋式微,直至销声匿迹。身处南宗禅占据上风时代的贾岛,对南宗禅十分偏好,不免会将南“顿”北“渐”思想与诗歌句法相结合,“这种以禅法喻句法,以繁与简作为北宗与南宗的精神”,巧妙勾连了诗学句法与禅学南北宗之间的相通性,“简练省净”与南宗直指心性的“顿悟”相关,“繁复细致”与北宗长期修炼的“渐悟”相关。
继贾岛后,僧虚中、徐夤亦以南北宗论诗。虚中谈及“诗有二宗”云:“第四句见题是南宗;第八句见题是北宗。”很明显,依循了贾岛“南北宗”论诗思想,由句法拓展为篇章;徐夤则将“南宗体”“北宗体”视为诗体之一,且在“叙句度”中直接承袭贾岛之说。
可以说,唐代以“南北宗”论文、论诗,固然与南北地域文风差异有关,但更与禅学南北宗发展演变有关。南北宗概念来自禅宗,但引入文学批评后,讨论内容逐渐从外部地理环境转向了文学自身。王昌龄时代的南北文风呈融合趋势,旨在树立大唐帝国刚健风骨、清新自然的文风气象,故以北宗为正宗;而中晚唐以来的社会转型、南宗禅占据主导,以律诗为主的诗歌创作追求字斟句酌、以少胜多的诗意表达,贾岛以南北宗论诗,正是时代诗风的反映。尽管唐代文诗南北宗论未以“风格”范畴彰显南北差异,但“南北宗”思想的介入,为探讨“南北”问题提出了一个新思路,建立了“南北宗”论艺的早期范式,对后世其他门类艺术批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三、艺术“南北”论的广泛普及
宋元以来文学艺术不断承传发展,衍生出词、曲体裁,书、画艺术成就斐然,创作实践成果为理论批评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理论批评总是滞后于实践发展,直至明清,“南北”问题才再次引起理论界关注。画、文、诗、词、曲、书多个批评领域承继唐代确立的南北理论范式,以“南北派”或“南北宗”论艺,结合门类艺术特殊性,提出诸多创见。不同于前代仅侧重于分派分宗,较少关注艺术自身的审美特色,明清艺术“南北”论最显著的特征是采用充满审美特色的“风格”范畴比较南北差异。
(一)画论“南北宗”“南北派”
绘画历经魏晋、唐、宋、元、明发展衍变,涌现出众多名家杰作,为探讨“南北”问题提供了丰厚的实践资源。明以后最具影响力的是画论“南北宗”,董其昌与同时期且相对较早的莫是龙相继总结山水画史,以禅喻画,提出画分“南北宗”说法:“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著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幹、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借鉴禅学南北宗论画,沟通了禅学与画学的内涵本质。从其言论发现,董、莫区分南北宗画派的依据并非地域,而是画法。以李思训父子为代表的北宗派,“著色山水”、浓墨重彩、精雕细琢,属于重在形似的工笔画;而以王维为代表的南宗派,“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追求神韵,重在写意。董氏对待南北宗画派的审美态度存在崇南抑北倾向,这也是其以南北宗论画的目的所在——标举“士气”、推崇“文人画”。文人画重天赋,与禅学“顿悟”之灵感相符,画风以“天趣”“自然”为旨归,非“渐修”苦练所能企及。画论“南北宗”独辟蹊径区分宗派,在明清各门类艺术批评领域引起很大反响,尤以画论批评最为突出。晚明沈灏《画尘·分宗》从审美角度区分南北宗画风,以“裁构淳秀,出韵幽澹”概括王摩诘及其流派风格,以“风骨奇峭,挥扫躁硬”概括李思训及其流派风格,这对范畴是对文人画与行家画的概括,其差异正缘自南北宗思想。明徐沁亦论南北宗,推崇山水画、贬斥体貌画,认为山水画“随所遇而发之,悠然会心”,追求“天趣”,而体貌画“殚心毕智以求形似”,拘泥于规矩,游心于尘世,同样体现出崇南抑北倾向,“天趣”与“形似”是对山水画与体貌画的区分,也是对南北宗思想的进一步强化。
清代画论批评十分注重笔法与南北宗派的联系。清华琳《南宗抉秘》强调“作画与作书相通”,指出北宗画用笔“遒劲”,虽“非出筋露骨”却“令人见而刺目”,呈现出“浑厚有力”之美;南宗画用笔“似柔非柔,不刚而刚”,有如“绵里藏针”,绝无“剑拔弩张”之态,呈现出“秀韵天成”之美。鉴此,华氏对效仿者不得用笔要领的做法予以批评,对绘画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无独有偶,郑绩亦从笔法区分南北画风,指出山水笔法有勾勒、皴擦两种,因用笔和腕力不同可分为南北两派,北派重勾勒,“笔笔见骨,其性主刚”,南派重皴擦,“笔笔有筋,其性主柔”,筋骨各有所长,“论骨其力大,论筋其气长”,并结合“十六家”笔法阐述筋骨对于绘画的重要性,其出发点并非将筋骨对立,而是倡导有筋有骨、相融相济的笔法,创作中“随意生变,欲筋则筋,爱骨则骨”,强调创作主体运用笔法的灵活性,彰显出总结时代画论家对“南北”问题的深刻认识。
当然,基于地理环境区分南北画派也颇受重视。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宗派》指出:“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佻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焉。”沈氏以“蕴藉而萦纡”与“奇杰而雄厚”概括南北山水,并对主体得南北“气”之正偏,以“温润和雅”“轻佻浮薄”和“刚健爽直”“粗厉强横”进行对比,既是对南北方人群审美趣味的区分,也是对南北画风差异的概括。除了南北画派的宏观概括,理论家还认识到地域画派的差异,清范玑强调“宗派各异,南北攸分”,由于不同环境地形地貌差异或人员流动,造成画派风格不同,“或因地变,或为人移。体貌不同,理则是一”。张庚也认同画分南北,但明代出现的浙派、松江派、金陵派等派别亦不可忽视,这是从微观层面对地域流派的认知与区分。
(二)文、诗、词论“南北派”与“南北宗”
结合文、诗、词发展实践,清人站在历史高度重新审视“南北”问题,力求从多元角度提出新见解。
1.文论“南北”
这方面主要是对南北派的区分。一方面溯源南北派肇始,强调南北差异的事实存在。况周颐指出“自六朝以还,文章有南北派之分”,意指六朝以来才有南北派区分,此处的“南北”,指南北朝文学,包含历史、政治上的区分,也有地域文风的不同。杨际昌则以“文”“质”区分南北诗风:“国朝诗,大江以南多尚文,大江以北多尚质,各有不可磨灭处,则视乎性情得正。”另一方面针对特定时代作家流派予以区分,张谦宜强调“古文有南北派”:“南派以八家为宗,自宋濂传方孝孺后,有王慎中、茅坤、唐顺之、归有光;北派以秦汉为主,李攀龙、王世贞倡之,李梦阳和之。”此论侧重分派,未以审美范畴标识两派文风,旨在凸显流派之间的对立,表达对拟古主义风潮的反对。
2.诗论“南北”
一是以“南北派”论诗,基于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影响。明徐学谟指出:“大江南北,其谣俗之不相为用……其发之为声诗,大都北主迅爽,而南人则诮其粗;南主婉丽,而北人则短其弱。”以“迅爽”“婉丽”区分南北诗风,以“粗”“柔”指摘南北之弊。清孔尚任论诗受画论影响,《古铁斋诗序》说:“画家分南北派,诗亦如之。北人诗隽而永,其失在夸;南人诗婉而风,其失在靡。”以“隽而永”“婉而风”彰显南北诗风特色,以“夸”“靡”指摘缺失。谢堃区分南北诗:“北方刚劲,多雄豪跌宕之词;南方柔弱,悉艳丽钟情之作。”同样采用对立性审美性范畴彰显南北诗风特色,指摘各自不足,渗透出较强的理性批评意识。
二是以“南北宗”论诗,汲取前人思想力求做出新阐释。清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将李、杜视为南北二宗:“以禅悟喻,谓太白顿而子美渐。”认为唐人“首推李、杜二公为大家”,且不能论其优劣,“其沉雄俊逸品之概”,各有“登峰造极之美”,区别在于“二公之诗,一以天分胜,一以学力胜”,这与禅宗南“顿”北“渐”思想相通。其论说是对宋严羽“李杜”诗评和“以禅喻诗”的进一步发挥。无独有偶,清王士祯亦以南北宗论诗,其“神韵”说推崇王、孟为南宗,深悟严羽“以禅喻诗”内涵,将王孟作为抒写兴致的理想代表,神韵诗追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空灵境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诗境与文人画意在画外的“逸品”相似。论及诗画关系,“画家之有董巨然犹禅家之有南宗;董巨后嫡派,元唯黄子久、倪元镇,明唯董思白耳。予问倪董以闲远为工,与沉着痛快之说何居?曰:闲远中沉着痛快,唯解人知之”。认为画理与诗文相通,将画之“闲远”与诗文之“沉着痛快”比肩,联通了禅理与诗画关系,也就建立了神韵诗与南宗画的联系。谈及“北宗”,王士祯以杜、韩为代表,其友宋犖《论画绝句》曰:“华原雪景特雄奇,笔底全将造化窥。韩碑杜句取相况,解道文人即画师。”认为华原作画师法造化,风格雄奇,与韩杜诗风类似。王士祯《跋论画绝句》予以附和,认同杜韩为北宗。但所列画家(华原、营丘、洪谷、河阳等)却指向北方画家,与董其昌“北宗”李思训画派不一致,似乎混淆了南北派和南北宗划分依据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王士祯论诗除褒赞南宗自然、闲远诗风,对北宗雄奇、沉着痛快诗风也持欣赏态度。
3.词论“南北”
词兴于两宋,但词论批评至清代才蔚为大观。南北派论词主要基于地理环境因素,况周颐总括“文分南北”的同时,具体针对词体展开分析“细审其词,南与北确乎有辨”,不同历史时期南北词风差异鲜明,“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梦窗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遁安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善读者抉择其精华,能知其并皆佳妙”。以“深致”“清劲”概括南北(宋金)词风,强调地理环境对南北词风的影响,指摘南之“绮靡”“雕文刻镂”,北之“荒率”“深裘大马”,对清晰认识南北词风具有指导意义。
以“南北宗”论词,主要受画论南北宗影响。清代浙西词派中期领袖厉鹗将画学“南宗胜北宗”思想用于词学,在《张今涪红螺词序》中说:“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南宗也。”厉鹗认同该派创始人朱彝尊“词至南宋始极其工”的观点,并为南北宗推选出了代表,北宗是以南宋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南宗是以北宋周邦彦、南宋姜夔为代表的清雅派,厉氏将周邦彦也视为南宗,其“婉约隐秀”“纡徐幽邃”的词风与南宗画风相通。结合厉鹗所处时代,乾隆年间“文人吟风弄月追求清雅风尚愈演愈盛”,将周、姜视为词之南宗,堪比南宗画派,是对时代精神需求的回应。
4.曲论“南北派”
戏曲成熟于元明,曲论批评于明清时期渐趋丰富,对“南北”问题相当重视。明徐渭《南词叙录》最早区分南北曲,从审美欣赏角度区分南北曲给人的听觉感受:“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从中可见北刚南柔的曲风差异。明王世贞以四字范畴高度概括南北曲,“大抵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并对戏曲自身问题展开多角度分析:“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此吾论曲三昧语。”对戏曲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曲论批评领域产生很大影响。明王骥德旁征博引从“辞”“地”“声”区分南北曲,并强调:“南、北二调,天若限之。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画地而知也。北人工篇章,南人工句字。工篇章,故以气骨胜;工句字,故以色泽胜。”“沉雄”“柔婉”是南北曲风,指出北曲重篇章,故“气骨”胜,南曲重句字,故“色泽”胜,分析颇为中肯切要。此外,基于表演实践论说南北曲也不乏精论,徐复祚《曲论》从歌唱入手,以“委宛清扬”和“硬挺直截”概括南北曲风;魏良辅从唱奏曲调入手,强调“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宛转为主,各有不同”,他十分重视“调”的核心作用,体现出一位改革者对戏曲音乐实践的独到见解。
清代曲论批评承袭明代,更重视对词曲自身特点的深层次、多角度分析。沈雄围绕词韵区分南北曲,以“重厚而沉雄”“轻浮而雌浅”范畴概括南北曲风,认为地域口音、音调、发音位置、音律不同,决定了南北声韵及其风格的不同。清李渔论曲侧重词曲发音吐字,《宾白·字分南北》云:“以北字近于粗豪,易入刚劲之口,南音悉多娇媚,便施窈窕之人。”“粗豪”“刚劲”和“娇媚”“窈窕”两对范畴见出南北方发音及曲风特色。清黄图珌从音调情感区分南北曲,指出“南有南调,北有北音,不可混杂。……北曲妙在雄劲悲激,南曲工于秀婉芳妍,不出词坛老手”。“雄劲悲激”“秀婉芳妍”鲜明体现出南北曲差异。清谢元淮论述“南北声音不同”,一方面区分南北特色,“以辞而论,南多艳婉,北杂羌戎”,“以声而论,南主清丽柔远,北主劲激沉雄”,“北宜和歌,南宜独奏”;一方面指摘不足,“及其敝也,北失之粗,南失之弱。此其大较也”。作为音乐文学的词是可以演唱的,辞之“艳婉—羌戎”,声之“清丽柔远—劲激沉雄”,表演之“和歌—独奏”是其艺术特色,但也存在南“弱”北“粗”的弊端。无独有偶,清王德晖、徐沅澄的《顾误录》沿袭王氏论说,专门针对戏曲实践诸多问题进行分析,唱法上以“遒劲”“圆湛”概括南北曲风,尤其对南北曲音韵、词情、调式、板式、衬字等的分析,可视为戏曲实践的指南。此外,清笠阁渔翁《笠阁批评旧戏目》、晚清刘熙载《曲概》亦谈及南北曲,虽创见不多,但也体现出对“南北”问题的关注。
5.书论“南北派”
自汉魏六朝,历经唐宋元明,书论批评内容丰富、宏论迭出,但关于书之“南北”问题,至清才引起理论家关注。受画论南北说影响,清冯班强调“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但画论侧重南北宗,书论却侧重南北派。清阮元著《南北书派论》回溯书法演变历程,指出汉末魏晋之间是正书、行草区分南北书派的分界点,书法从此分为南北两派各自发展,“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北派共同的源头是钟繇、卫瓘,南派自王羲之、北派自索靖,朝不同方向延伸。隋以后南北书派出现不平衡,北派势力壮大,而南派只有王氏七世孙智永一人。尽管唐李世民偏爱王书,但世间流传主要还是北派,“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直至“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南派自宋才成为书坛主流,尤其“元明书家,多为《阁帖》所囿”,书风转向南兴北衰格局。阮元认为“两派判若江河”是由于“南北世族不相通习”,“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阮元以“疏放妍妙”“拘谨拙陋”区分南北派,书风差异与媒介“启牍”和“碑榜”相关。从书法对物质媒介的利用来看,石刻记录在先,字帖流传在后,书法史上曾出现汉唐“碑版之法盛”、宋元“字帖之风盛”景象,由宋至明重帖轻碑的书学偏向,尤其是清康熙对董、赵婉转圆美书风的偏爱,引发书界对南北书派的思考。于汉人而言,异族入侵、改朝换代,加重了汉族文士追思故国的民族情怀,从故纸堆、残碑古迹中追寻历史印痕,促进了经史学、考据学、金石学走向繁荣。书学领域出现重碑轻帖倾向,书论批评强调崇北抑南,正是对特定时代复古主义文艺思潮的回应。
无独有偶,同样倡导碑书的还有包世臣、康有为。包世臣作《艺舟双楫》强调:“欲见古人面目,断不舍断碑而求汇帖已。”其对篆隶、北碑的研究颇为深入,“北朝隶书……然皆极意泼发,力求跌宕”,“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篆书之圆劲满足,以锋直行于画中也”等,进一步强化了碑书地位。其后,康有为作《广艺舟双楫》,扬碑抑帖观念更加强烈,指出“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习书者若要提高书学素养,与其寻师不如“购碑”,于是康氏开出一系列南北朝碑目供人选择。从习学对象来看,“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康氏更推崇碑书,提出五条理由表明习法碑书的必要性,并强调“古今之中,唯南碑和魏碑为可宗”,缘其“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并专设《宝南》《备魏》两个篇章品鉴碑书,“南碑数十种,只字片石,皆世稀有,既流传绝少”,如《封禅国山》之“浑劲无伦”,《天发神谶》之“奇伟惊世”,《谷朗》之“古厚”等;“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风格多种多样,如奇异的《石门铭》、古朴的《灵庙》《鞠彦云》、古茂的《晖福寺》等,有了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不可”,如此厚重的崇碑观念、强烈的崇北抑南倾向,亦是对当时书学风尚的反映。
当然,清人论南北书派还有一种“融通论”。刘熙载论书区分南北书差异,但也认识到二者互为包含的关系:“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南如袁宏之牛渚讽咏,北如斛律金之《剌勒歌》。然此只可拟一得之士,若母群物而腹众才者,风气固不足以限之。”以“温雅”“雄健”概括南北书风,强调北书以“骨”胜并兼有“韵”,南书以“韵”胜并兼有“骨”,骨韵偏胜表明二者互相融济特点。要成为一个孕育群物、容纳众才的人,不应受到南北书风格限制,而应刚柔相济、南北融通,这些观点对习书者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四、结语
综上,回顾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文献可以发现,乐、文、诗、词、书、画、曲等批评领域探讨“南北”问题相当广泛,从南北艺术事象的描述,到南北派的区分、南北宗的介入,理论家结合门类艺术的特殊性,从不同角度审视“南北”问题,对比南北差异,采用极具审美特性的对立性“风格”范畴彰显南北特色,指摘南北不足,体现出古人对“南北”问题的深刻认知和多元思考,对当前艺术理论探究“南北”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们理解“南北”,不能仅从地理环境角度比较南北差异,而应当结合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与门类艺术形态的差异性,尤其是艺术自身审美特性、宗法沿袭、媒介工具及文艺思潮等多方面因素来厘清艺术“南北”问题的复杂性,发掘古代艺术南北论的丰富内涵。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古人探讨艺术“南北”问题的角度不一,在“风格”范畴语汇运用上丰富多样、异彩纷呈,但我们发现“风格”范畴之间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整体上体现出:南“柔”北“刚”、南“宛”北“挺”、南“软”北“硬”、南“轻”北“重”、南“筋”北“骨”、南“秀”北“雄”、南“媚”北“劲”、南“圆”北“方”等审美特点,这与古代《易传》“阴阳刚柔”思想一脉相通。南北差异长期存在,彼此不可替代,但随着时代发展、南北交通便利,南北艺术之间不可避免会出现相互借鉴交融,从艺术审美角度来看,各居一端的南北艺术各自存在一定弊端,常受到理论家批评指摘,因此理论界亦倡导通过“刚柔兼济”“骨韵并存”等方式追寻完美和谐的艺术形态,体现中国艺术的“中和”之美。中国古人相关艺术“南北”论的阐发,基于历代文学艺术发展实践的长期积淀。一系列“风格”范畴的提出,是古人深刻认知“风格”本质的思想见解与理论精粹,也是当前构建中国特色艺术理论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