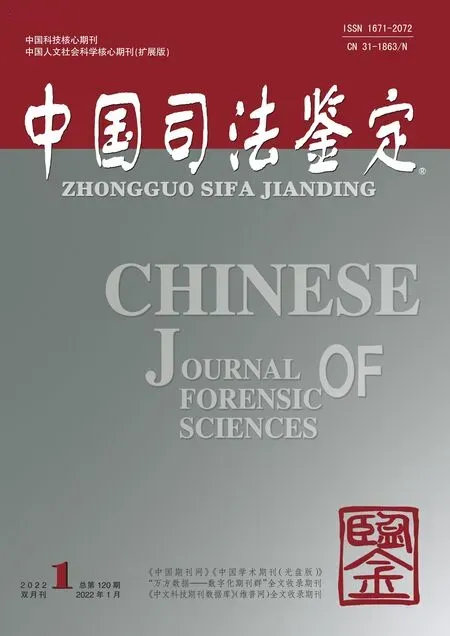医疗损害鉴定中因果关系分析理论及其应用
2022-11-08朱广友夏文涛
朱广友,夏文涛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上海市法医学重点实验室上海市司法鉴定专业技术服务平台司法部司法鉴定重点实验室,上海200063)
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形式决定了医疗过错在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通常情况下直接关系到医疗损害诉讼中医方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及应承担多大程度的赔偿责任。因此,因果关系分析是医疗损害鉴定的关键。 一般认为,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哲学上因果关系的一种类型,但又不同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两者之间是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关系。 虽然我国《民法通则》和《民法典》对因果关系的评判都未直接作出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因果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从未动摇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明确规定,鉴定意见可以按照导致患者损害的全部原因、主要原因、同等原因、次要原因、轻微原因或者与患者损害无因果关系,表述诊疗行为或者医疗产品等造成患者损害的原因力大小。 但是如何分析、 判定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类型,并根据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确定医疗过错的原因力大小,亦未作进一步阐述。 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讨论两大法系医疗损害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分析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并结合我国医疗损害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讨适用于我国医疗损害诉讼及其鉴定中因果关系分析的理论与方法,而关于原因力的判定将另文讨论。
1 英美法系因果关系分析基本理论与方法
1.1 必要条件理论/“若无”因果关系理论
“必要条件理论”(but for test),又称“若无”因果关系理论,是侵权法中因果关系分析最常用的理论,检验方法为:如果没有被告的过错行为,原告就不会受到损害。 法律的假设是:可以证明若不存在A 事件,就不会发生B 事件。 该假设的推论是:如果“若无”检验不能得到满足,因果关系就得不到证明,被告不论是否违反义务,均不承担责任。
“若无”因果关系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加以检验:一是剔除法,即剔除医疗过错(通常指临床诊疗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如果损害后果仍然发生,则医疗过错不是损害的原因;二是替代法,即用符合临床规范的诊疗行为替代医疗过错行为(通常指临床诊疗活动中的不作为),如果损害后果仍然会发生,则医疗过错就不是损害后果的原因,反之则是原因。 必要条件理论主要适用于“一因一果”的情形。 例如,交通事故致伤者闭合性腹部损伤,因入院时一般情况尚可,接诊医师未予特殊处理,而在留观过程中护理人员疏于观察,4 h 后发现伤者面色苍白、血压下降、心率快、心音弱,已经处于严重休克状态,经抢救无效死亡。 死后解剖证实死者因脾脏破裂,失血休克死亡。 此种情形下,采用替代法进行“若无”因果关系的证明,如假定医务人员能够认真观察伤者病情变化,及时发现休克征象,并在抗休克治疗的同时积极进行腹部超声等影像学检查,则完全有可能避免伤者死亡的发生,故应认定医师的过错行为和伤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1.2 合理医学确定性理论
“合理医学确定性理论”(resonable medical certainty)又可称为“合理的医学概率”(≥51% 的概率)或“可能性大于不可能性”(more likely than not)。 因为医疗因果关系一般超出非专业陪审员的一般知识范围,所以通常需要专家证词来满足这一举证责任。 当然,专家意见也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医学确定性的支持,否则就缺乏足够的证明力。 因此,尽管证明因果关系不需要绝对的确定性,但当专家就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作证时,“确定性”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统计学应用来看,“置信区间”反映了可预测特定结果的确定性程度。 例如,一名脊椎外伤的原告起诉主治医生没有给予其类固醇治疗,据称类固醇可有效缓解脊髓受压,避免功能障碍持续加重。 原告的医学专家援引了一项专门的医学研究结果,证明有“95%的确定度”表明:如果使用类固醇,伤者就不会发生脊髓功能完全丧失。 但被告的医学专家对原告的医学专家所引用的医学研究重新审查之后发现:根据95%统计学置信区间,类固醇对此类患者产生确定疗效的可能性仅为53%。 这表明,专家的证词在技术上是正确的,但结果是错误的,且具有高度的误导性。 假设专家作证认为,他或她有“99%的确定度”认为某种检查或治疗有75%的概率可以达到某种特定的效果,那么根据统计学原理,要获得99%统计学置信区间所需观测样本量至少需要1 875 例,如果他或她的证词是基于不到1 875 例样本量进行统计学分析的结果,那么该专家的证言就是不可信的。 由此可见,合理医学确定性依赖于统计学结果,换言之,应用该证明方法需要一定的条件,即所属领域具有大量的统计学资料可以利用。
1.3 累积因果关系理论
“累积因果关系理论”(cumulative causation)是指在两个以上加害因素累积的情况下共同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法院可选择性地认定被告负有责任,即如果认定这些因素累积在一起共同导致原告的损害,则被告的过错行为作为一个构成因素。 如果不是最低限度的(如果属于最低限度的,则应适用“实质性因素”理论),则可描述为“促成因素”(contributing factor)。
在医疗过错行为与自身疾病共同作用导致损害后果的情形下,如果判定两个因素单独存在时后果均不至于发生,应判定医疗过错与自身疾病在损害后果中的作用为共同作用,原因力大小为同等原因。 例如,伤者患有双下肢深动脉硬化闭塞症,交通事故致右下肢软组织挫伤,由于医方对于伤者右下肢血液循环障碍处理不及时,致使发展为右下肢缺血、坏死,并发感染难以控制,最终导致伤者右下肢截肢。 若判定患者自身没有深动脉硬化闭塞症,其截肢后果不会发生,而与此同时,如果医方能够及时发现伤者右下肢血液循环障碍并采取相应的诊疗措施,则伤者也不至于发生截肢后果。 此种情形可判定医疗过错与伤者自身疾病是导致患者截肢的共同原因,原因力大小可判定为同等原因。 再如,在一例急性心肌炎误诊误治的案例中,患者以“畏寒、发热,伴恶心、呕吐1 天”于下午19:30 去被告医院急诊。 医院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并予以相应的处理。第三天清晨5:00,患者因上述症状加重再次去被告医院急诊,急诊时体温高达40.5 ℃,心率70 次·min,7:45 心电图检查示心室性期前收缩,房室传导阻滞Ⅰ度,心室内传导阻滞,QT 间期延长,ST-T 段异常,怀疑右心室肥大。 WBC13.71×10·L,NE 73.3 % ,NE 10.04 ×10·L,RBC 4.23 ×10·L,HGB 130.00g·L,PLT 34×10·L,电解质无明显异常。急转ICU 进一步治疗,9:04 患者突发心跳骤停,急予心肺复苏心脏按压2 min 后患者复律成功。 医院初步诊断为“感染性休克、肠道感染可能、心脏骤停复苏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恶性心律失常、急性肾衰竭”,并予以抗感染、抗休克和扩容等对症支持治疗。 而后患者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死亡,死后病理诊断为“急性心肌炎”。 鉴定人认为,患者死亡既有起病隐匿、病情发展迅速和诊疗困难的因素,也有误诊误治的医疗过错因素,两者难分主次,在患者死亡后果中的原因力为同等原因。
同样,如果是两个医疗过错行为共同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且无法区分其中任何一个过错行为单独存在是否必然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那么可以判定为两个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都存在因果关系。 例如,伤者因颅脑损伤先后在甲、乙两家医院接受治疗,两家医院都违反了激素使用的相关规定,给伤者大剂量、长时程服用激素。 伤后1 年发现伤者双侧股骨头出现无菌性坏死。 此种情形,可判定两家医院均存在违规使用激素的医疗过错,两家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共同导致了伤者损害后果的发生,即两家医院的过错在伤者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为同等原因(在总体过错中承担基本相同大小的责任)。
1.4 实质性因素理论
“实质性因素”(substantial factor)指通常情况下,理性的人会认为被告的行为可能导致原告的损害,因此其应当承担法律上的责任。 “实质性因素”理论与“合理的医学确定性”理论在判定的理念方面存在较大的区别,其似乎根源于法律上的“救济理论”,法律依据为:向他人提供服务的人,应该意识到有必要保障他人的人身或财物安全,如未能给予合理注意,可增加造成此种伤害的风险。 而在诊疗过程中,当医方未能尽到合理注意而导致患者身体伤害时,显然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应用“实质性因素”须掌握以下5 个前提条件:第一,目前的科学知识状况使原告本身不可能确切证明其伤害是如何造成的;第二,医疗过错必须在理论上大幅增加对原告造成伤害的风险;第三,医疗过错应当可造成原告的伤害;第四,患者的损害与医疗过错所造成的风险具有关联性;第五,类似损害在相似的医疗机构和同样的情形下通常也会发生。 此外,应用“实质性因素”理论,还要求医疗过错引起损害后果的可能性须达到一定的程度,这种可能性程度在不同的法庭会有不同的要求,但最低要求一般应至少达到10%。 例如,有些癌症患者由于医疗过错未能获得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但由于延误诊断的时间并不长,依据一般经验判断未能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病疾的发展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但依据现有资料也无法证明医疗过错如何影响患者疾病的发展以及影响的程度。 “实质性因素”理论对此种情形进行分析,可以判定医疗过错行为与疾病进展存在实质性的因果关系,分析医疗过错在疾病进展中的原因力大小为次要或轻微原因。
1.5 机会丧失理论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均承认“机会丧失”(loss of chance)理论,该理论既是一种损害后果的证明方法,也是一种因果关系的证明方法。 为了证明“机会丧失”,原告必须用大量证据来证明医疗过错使原告获得更有利结果的可能性降低。 即原告必须用大量证据证明医疗过错事实上造成了原告的伤害,包括获得更有利的医疗结果的可能性降低。
在美国,早期对“机会丧失”的医疗诉讼存在以下3 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第一种方式作为传统的民事侵权方式而被少数法庭所采用。 根据这种方式,原告必须证明由于医务人员的过错行为剥夺了患者至少51%的康复或生存机会。 一旦原告能够完成举证责任,会获得治疗疾病的所有赔偿。 相反,如果患者的疾病即使得到适当的诊疗也仅有50%以下的康复或生存机会时,尽管医务人员存在过错行为并使得患者丧失了这种康复或者生存机会,原告依然得不到任何赔偿,这就是所谓的“全或无规则”(all or nothing rule)。第二种方式是对上述传统方式的改良,该方式降低了因果关系证明标准,原告只要证明被告的过错行为使患者丧失这种康复或者生存机会的可能性大于不可能性(笔者注:可能性≥51%),或者失去了获得康复或者生存机会的可能性(笔者注:可能性≤50%),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使患者的病情加重,或者危险因素增加,就能获得相应的赔偿(即按比例赔偿)。第三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相同,尽管患者获得康复的机会在50%以下,也可以获得赔偿,但不能获得包括自身疾病在内的全部赔偿,只能获得因丧失康复或生存机会所造成的那部分损害。 这种方式克服了上述“全或无规则”的不足,是大多数法庭采用的方式。
1998 年,JOSEPH 等讨论了“机会丧失”理论的发展,并建议将基于机会丧失利益损失的百分比折算为赔偿金,既可适用于机会丧失在51%以上的情形,也可适用50%以下的情形。 后来许多学者在其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有关“机会丧失”的具体计算方法,并在诉讼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例如,在 Plaintiff v. Friendly Medical Group 一案中,原告5 个月前因白带增多曾在被告医院就诊,诊断为阴道子宫囊肿并行手术切除,术后病理检验提示慢性炎症急性发作。 5 个月后在其他医院取活检后诊断为子宫颈高分化腺癌(IB3 期),并行剖腹全子宫切除+双附件切除+盆腔淋巴结清扫术+肠粘连松解术。 术后病理检验提示子宫颈高分化腺癌(IB3期),癌组织侵犯宫颈肌壁深部肌层,不久患者死亡。 鉴定人查阅文献发现,宫颈癌I 期患者的5 年生存率为81.6%,Ⅱ期为61.3%,Ⅲ期为36.7%,Ⅳ期仅为12.1%。 因此,分析认为,患者在被告医院就诊时医方存在应推定患者此时已患有宫颈癌的过错(误诊或漏诊),但属于I 期患者,此时5 年生存率为81.6%,而至5 个月后其属Ⅲ期患者,5 年生存率为36.7%,即被告医院的过错导致被鉴定人5 年生存率减少了约45%。
1.6 联合概率
“联合概率”(joint probability)实质是“机会丧失”理论应用的具体方法。 THOMAS 等认为,对专家证词进行严格的基础审查,是因为统计学分析结果对于确立因果关系往往显得至关重要,特别是在误诊、误治等多个过错行为共同导致原告损害时,统计相关事件的联合概率显得尤为重要。 在Patient v. Efficient Medical Group Suppose 一案中,原告指控被告如果能够在其患有癌症的初期及时作出诊断,其就会得到及时治疗并会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原告的专家作证认为,被告的医生如果遵循通常的注意标准,指示患者进行胸部X 线检查,有“可能”会作出明确诊断。 这一证词使得陪审团相信,如果给患者及时行胸部X 线检查患者获得早期(第一阶段)诊断的可能性达51%以上,但并不支持获得较好治疗效果的可能性可以达到相同的概率。原因是患者的专家作证时所说,如果患者在癌症处于第一阶段时接受了治疗,其大约有60%的机会活到5 年或更长时间。 因此,证据实际上只证明了由于被告的过错,患者失去了30.6%的生存机会(第一阶段获得诊断的几率51%乘以第一阶段开始治疗后取得更好结果的几率60%)。由此可见,应用统计相关事件的联合概率会导致损害赔偿数额大幅减少。
当因果链条中存在多个统计相关事件时,因果关系会变得更加难以证明。 在Plaintiff v. Friendly Medical Group 一案中,原告指控医生的过错延误了癌症诊断,以至患者无法及时获得治疗。 然而,本案中指称的因果关系链条甚至比上述案例更长。 原告称,医生的过错在于未能及时进行巴氏涂片检查,而此时可能已经表现为异常。 其还声称,异常的巴氏涂片检查结果可能会进行阴道镜检查,阴道镜检查可能会显示不正常并导致活检,而活检可能会明确癌症诊断。 如果活检作出诊断时,其还有65%的机会被治愈,但实际上原告已经死于癌症。 采用统计相关事件的理论来分析因果关系,原告如果作了巴氏涂片检查,其存活的几率是巴氏涂片作出诊断时的存活几率、后续阴道镜检查作出诊断时的存活几率和获得及时治疗情形下的存活几率的乘积,这是最终的存活几率。 而原告专家认为,“巴氏涂片可能是不正常的”,这只能证明51% 的巴氏涂片是不正常的,这种不正常的巴氏涂片“更有可能”会“不能令人满意”并需要进行活检,这实际上证明了在51% 的巴氏涂片不正常的情况下,需要进行活检的只有26% (51%×51%)。 假设在26%的所有病例中进行活检并能够给予明确诊断和治疗,那么26%的活检患者中会有65%的人能够存活下来。这意味着,在据称需要巴氏涂片检查的情况下,处于原告状况的患者存活几率只有17% (26%×65%)。换言之,原告的因果关系证据表明,类似于这种情况,49%的妇女会进行正常的巴氏涂片检查,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治疗。 此外,在巴氏涂片检查不正常的妇女中,有49%的人阴道镜检查结果并未发现异常。 最后,在接受活检和治疗的人中,仍有35% 的人已经死亡。简言之,根据原告的证据,有83%(即:49%+25%+9%) 的患者进行巴氏涂片检查不会改变患者的生存结果。 H.Thomas Watson 认为,随着医疗、保健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延迟诊断病例中的医疗因果关系问题变得更加普遍和复杂。
例如,原告指控1 年前曾因呼吸道感染在被告医院就诊时胸片已显示有微小的磨玻璃样结节,但医师未予重视,因未能得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现已发展至肺癌中晚期。 如果被告能够在1 年前诊断出肺癌,其就会得到及时治疗并能够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原告的专家认为:如果被告医师能够在发现病变的初期即对患者实施进一步检查,患者有可能获得早期诊断(即早期确诊的可能性超过51%)。如果患者1 年前得到诊断,癌症尚属早期,此时接受治疗,大约有60%的机会活到5 年或更长时间。根据联合概率理论,法庭认为,专家意见实际上只证明了由于被告的过错,患者失去了30.6%的生存机会(第一阶段获得诊断的几率51%乘以第一阶段开始治疗后取得更好结果的几率60%)。 这表明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生存机会丧失)存在因果关系,但显然只属于次要原因。
1.7 事实自证原则
“事实自证原则”既是医疗过错证明方法,也是因果关系证明方法,适用于原告无法举证证明医疗过错,但事实本身足以说明医方存在过错且该过错是造成患者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 本质上,该原则是一种通过逻辑推断的证明过程,需要满足以下3个条件:(1)如果没有医疗过错,患者的损害后果通常不会发生;(2)患者处于被告的监护之下,即被告有保护患者免受损害的法律义务;(3)患者本身不存在足以导致损害发生的过错。 例如,手术器械被遗留在患者体内,手术误切正常的组织或器官等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被告存在过错,该过错直接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其医疗过错在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应为全部原因。 一般说来,适用“事实自证原则”无需原告举证证明医疗过错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也无需专家提供帮助。 但在有些情况下,仍需专家从专业的角度进行分析判断。例如:甲状腺次全切除术通常不会引起术后甲状旁腺功能低下的并发症。 医师在手术过程中应熟悉局部组织解剖,精细操作,注意保护支配甲状旁腺的血管免受损伤,认真辨认甲状旁腺组织、对于切下的组织应详细检查以免甲状旁腺被误切等,但手术记录并无相关操作记录。 患者疾病本身并无导致甲状旁腺血管受损及被误切的风险,如血管变异、组织粘连致分离困难等。 此种情形,依据“事实自证原则”可以推定医师在手术中存在操作不规范、损伤甲状旁腺血供或误切甲状旁腺的过错,且该过错与损害后果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再如:通常情况下,产妇正常分娩不会发生新生儿锁骨骨折或臂丛神经损伤的情况。 助产人员有义务密切观察产程变化并适时采用规范的助产措施,帮助胎儿顺利分娩,并有义务保证母婴安全,但产程记录中并无异常情况或助产情况的相关记录,而患方亦不存在头盆不称或影响分娩的不利因素。 此种情形,适用“事实自证原则”可以推定助产人员在助产过程中存在助产方式不规范或对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如相对头盆不称等)处理方式不规范等医疗过错,且过错是造成新生儿产伤的直接原因。
2 大陆法系因果关系分析基本理论与方法[15]
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关于事实因果关系在大陆法系占主导地位的学说是经过改良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其基本含义是加害人必须对以他的不法行为为相当条件的损害负赔偿责任,但是对超出这一范围的损害后果不负民事责任。
相当因果关系说诞生于19 世纪80 年代,由德国富莱堡大学生理学家冯·克里斯首创,其认为可能性的判断就是一个运用概率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分析的过程,并且可用于因果关系判断。 理由非常简单:如果可能性的判断显示A 很有可能导致B的发生,而当存在A 的情况下确实有B 的发生,那么人们会比较有理由相信A 就是导致B 发生的原因。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冯·克里斯是从统计分析的方法出发来探讨因果关系判断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将可能性判断完全建立在数据的统计和分析的基础之上,而主要是依靠一个普通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学者应当拥有的经验和常识。 这是因为“依据相当性概念判断之结果,与普通人或经过训练而具有正义感的法律人,依据经验之启发及事件发生的正常过程,所为之判断,甚为相似”。 冯·克里斯认为,相当因果关系学说的应用必须符合两个要件:一是该事件为损害发生的不可欠缺的条件(条件性判断);二是该事件实质上增加了损害发生的客观可能性(可能性判断)。 换言之,在冯·克里斯看来,极大地增加损害发生可能性的必要条件就是损害后果的原因,行为人应对由此而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 因此,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首先应判断结果发生之条件是否为损害发生之不可欠缺的条件(条件关系之判断),亦即在认定确实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后,再判断相当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相当性之判断)。
相当因果关系学说以概率论之可能性理论为基础,其先天之缺陷甚为明显,但是在人类现有认知水平下,人们尚无法对事件之间的客观联系给出全面决定性的论断,因而一切所谓的客观判断也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判断”。 考虑到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民事审判对诉讼经济的内在需求,相当因果关系学说对于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判断无疑是一种比较成熟、也比较实用的方法。 时至今日,相当因果关系说在德国、希腊、奥地利和葡萄牙等国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3 我国医疗损害诉讼中的因果关系分析基本理论与方法
从目前我国医疗诉讼实践来看,我国医疗诉讼同时受到了域外国家两大法系因果关系理论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学界在讨论域外国家两大法系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因果关系理论时常将英美法系的“二分法”与大陆法系的“相当因果关系”相提并论,强调两大法系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因果关系分析理论的不同, 而忽略了两大法系因果关系理论的共同点。 所谓“二分法”是指英美侵权责任法将因果关系划分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两种不同的类型,前者是指某一加害行为是否符合某特定的侵权诉因的构成要件,后者则是指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 因此,“二分法”是因果关系的分类方法,“相当因果关系”是因果关系的判定方法,两者本身并不存在可比性。 如上所述,无论是英美法系的“因果关系理论/必要条件理论”“合理医学确定性理论”“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实质性因素理论”“机会丧失理论”“联合概率理论”等与大陆法系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在本质上均基于共同的理论基础——概率论,实际上都致力于解决同一个问题——判定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较之大陆法系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英美法系的“因果关系理论/必要条件理论”“合理医学确定性理论”“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实质性因素理论”“机会丧失理化”“联合概率理论”等则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因果之间的关联强度——概率,而这种概率弥补了相当因果关系分析时“可能性”的判断方法,往往难以获得明确结果的不足,从而更易于理解和实际运用。
鉴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在实际应用中难于把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医疗过失赔偿纠纷案件办案指南》中引入了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于“若无因果关系”)和复杂因果关系(相当于“累积因果关系”),并且强调医疗过错行为实质上增加了损害后果发生的客观可能性和不可欠缺的条件,系具有相当因果关系(相当于实质性因素理论)。 这种解释在某些方面虽然值得商榷,但却将两大法系相关因果关系分析理论统一起来,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此外,“机会丧失”理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逐渐获得认可。 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89 辑)中以指导案例的形式,主张在低治愈率患者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当患者依照传统因果关系理论难以证明其损害与医疗过错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获得赔偿的可能性极小时,为平衡医方和患方的利益, 可借鉴存活机会丧失理论,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代替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对医方和患方的举证责任重新进行合理分配,并将期待适当治疗利益作为赔偿对象,以比例因果关系原则为基础,由法官酌定赔偿数额。
比例因果关系用以确定致害因素与特定损害后果之间的可能性联系及其比值,具有推定性和评价性的特点,是解决此类侵权责任承担问题的技术工具和关键因素。 比例因果关系的确定需经过一般因果关系的确定和与个案具体情况的比对这两个步骤,其“比例”数额的确定是在综合考虑各种事实因素和酌定因素的基础上,参考有关数据进行的综合评价,用于恰当分配被告的责任。 首先所涉及者为频率判断,或谓之“统计学上的现实可能性”,即基于法官的经验或鉴定意见, 当特定事件A 发生时,B 可能发生的百分比;其次是标准问题,即法院对盖然性程度的认同与否,对此各国司法实践有不同的认识和要求,从51%到95%不等,我国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的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这一点与两大法系的情况基本相同,就所要求的具体数值而言,学者之间虽存在较多的争论,但多表述为51%。
由以上分析可知,目前我国医疗损害侵权诉讼中有关因果关系分析的认识和实践深受两大法系思想的影响,可谓兼收并蓄、各取所长。 在鉴定实践中,此种情形也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例如,在一例患儿因病毒性心肌炎死亡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两级医学会鉴定专家均认为,患儿所患疾病急骤,发展迅速,病情凶险,死亡率高,早期诊断有困难,导致难以极早采取有效救治措施。 因此,被告在诊疗过程中虽然存在一些过错,也未能及时确诊病因,但被告的过错行为与患儿死亡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但有学者在评论该案时认为,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基本思想是“一个可能性判断”。 如果根据一般见解,能够确定加害行为在客观上有可能导致损害后果,就可认定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不要求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而应强调此种加害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就本案而言,患儿并非完全失去救治的可能,医方的过错行为减少了患儿可能成功获救的机会,因此应认定医方的过错与患儿死亡后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并且建议医方的责任程度以10%~20%为宜。由此可见,此案应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分析的结果与应用“实质性因素理论”分析结果异曲同工。
由于我国法律尚未就医疗损害诉讼中的因果关系分析理论与判定方法作出明确规定,学界理论探讨不少,但实践中应用并不多。 因果关系分析涉及医学、法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需要充分理解因果关系分析的重要性,正确理解因果关系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提高医疗损害鉴定的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