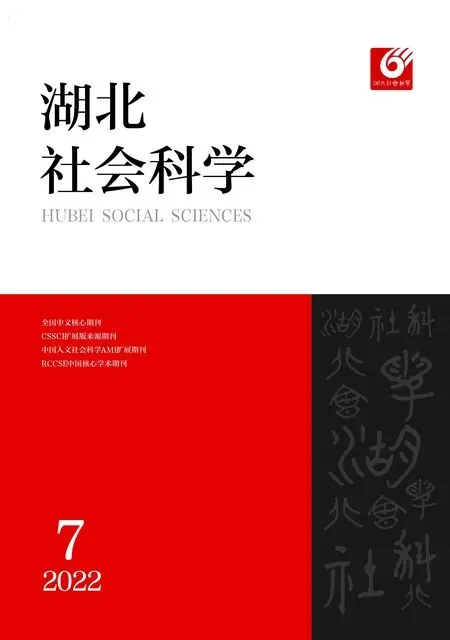“物”的解析:以黑格尔与王阳明为中心
2022-11-08张依萱
张依萱
现实世界中每个人都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物”或者“物体”“物质”,在日常生活中也常使用“事物”或“东西”一词来代替,物时常与“事”或“东西”相关联。比如我们逛街购物可以说去“买东西”,还有对不知道名称的物件,我们可以说“这是什么东西”等等。虽然我们在日常中时常使用“物体”“物质”“事物”等范畴,但它们的具体内涵却很少有学者去探究。鉴此,本文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中一窥“物”的观念史演变。
一、黑格尔之前的“物”论
“物”在英文里一般表达为“something”,而在德语里则为“das Ding”,在中文里更多地指向了“事物”。宽泛地说,“物”实际上指向了主体在日常生活中与之打交道的那些可感物。但哲学不是常识,日常我们以为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哲学当中却是异常重要的问题,正如海德格尔说“对物之物性的解释贯穿了西方思想的全过程”。
诚如海德格尔所言,早在哲学的起初阶段,希腊哲人就对此做了系列的讨论,如米利都学派泰勒斯所言的“水”,阿那克西曼德所提出的“无限”以及阿那克西美尼所谓的“气”等等。他们无不以自然界的具体物质来说明万事万物之本源,从而奠定后来亚里士多德等人自然哲学的基础。然而,思维的演进不是一以贯之的。与之不同的主张,我们可以在毕达哥拉斯学派中找到,他们认为“数”才是宇宙万物之本源,即便万物的原初之状是有具体形态的事物。进一步而言,该学派普遍地认为万物共同的、有定形的东西只有“数”这个范畴。这涉及事物的抽象本质,为后世形而上学的未来开启了基础。与此同时,爱非斯学派的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本源。火变动不居,具有以一否定多、以静止否定运动、以本质否定现象等等特征。除此之外,爱利亚学派主张万物的本源是“一”,比如克塞诺芬尼所说的“一”,以及后来巴门尼德所主张的“存在”等等。他们认为唯有“一”才是“神”,神就是唯一的。事实上,早期希腊哲学发展到顶峰的是“原子论”,恩培多克勒主张“四根”说、阿那克萨戈拉提倡“种子”论、德谟克利特持“原子”说等等。这些希腊先贤致力于寻找宇宙万有的本源,强调“物”作为宇宙万有的开端。
哲学之思发展到“希腊三贤”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中认为米利都学派、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等这些思想家“只认识到了质料因,最多在极个别的地方承认他们意识到了动力因……这只是以质料因在解释事物,而动力因只是辅助质料因解释事物何以有动变之用的”。实际上,在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以及巴门尼德等人的观念里,宇宙秩序和万物存在自身被当作主体表述了出来,它们的动静、善恶、有限与无限这一系列的观念现象背后,都在这个秩序之下,秩序与存在本身,使某物成为该“物”。进一步来说,这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二人所主张的“理念”或“形式”作为事物的决定性原因,作了良好的理论铺垫。详细地说,柏拉图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是对“理念”的分有或是模仿,然而所有的事物和理念都趋向于“善”的理念。与之相似,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宇宙万有的第一本体便是“物”,因为它指称“个别事物”。“物”只是“这一个”或“那一个”具体的可感事物。但是,“理念”作为事物的模仿对象,只能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而不能在事物之外独立存在。另外,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式”作为事物的外在表现样式,它指向的实际上不是肉眼所见的那个“外观”,而是心灵之眼所见到的那个样子。进一步而言,亚里士多德将“形式”纳入到了万物的“质料”之中。事实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物”是众多属性的集合者,“物”的实存不依赖于他者。以上哲人,他们思维世界中的“物”,只停留在物理学的构成上。在这个单一的维度里,他们没有继续追问物何以成其为“物”。
后来,在康德那里,“物自身”能成其为“物”,依靠主体的意识就可挺立的东西。如康德在他的《形而上学导论》中说道:“作为我们感官对象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物是已有的,只是这些物本身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它们的现象,也就是当它们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在我们之内的产生的表象。因此无论如何,我承认在我们之外有物体存在。”这里的“对象”,实际上就是客观世界中存在的物事,亦可说是主体的所思所行,它所指向的是客观事物。宽泛地说,物体本身的实际存在是无须怀疑的,但它自身的原貌是什么样子的,外界则难以知晓,因为它展露给我们的只是外在的现象而已。事实上,要想揭示“物”自身这一历史重任,有待黑格尔去完成。
二、“物的辩证法”:黑格尔的“物”论
对“物”的解析,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的第二章中有其严密的推理过程。在研究黑格尔的文本中,关于本书的重要性,莫过于马克思所认为的《精神现象学》乃是黑格尔及其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后来,美国的学者芬德莱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亦说:“黑格尔以后体系的每一个概念和原则,无不在《精神现象学》中可以找到,且常常是在更透彻、更有启发性的形式中找到。”进一步而言,从《精神现象学》的内容上说,它的第一章所讨论的是“感性确定性”。他认为曾经自诩是“一种最丰富的认识”“一种最真实的确定性”的感性确定性,而在现实上却是“一种最抽象、最贫乏的真理”。感性确定性的对象是不包含任何内容的“这一个”“这里”。但是感性确定性所能获得的也仅仅是一个“意谓”,亦即一种经过中介了的或是“普遍”的东西。当我们把“普遍者”“当做一个真相予以接纳,我不再是认知一个直接的事物,而是接纳真相,亦即进行这知觉活动”,由此便进入了《精神现象学》的第二章,即“知觉,或物与错觉”。
在黑格尔那里,“知觉”的对象既是一个“普遍者”,也是单纯的普遍者。然而,“这一个”现在作为认识对象不是直接的存在,这个对象仍然是“一个东西”,“但却不再像在感性确定性中那样是一个意谓中的个别事物,而是一个普遍者,或者说一个被规定为属性的东西”。不过,“属性”具有多种多样,其中任何一个属性都是对其他属性的否定。知觉的对象由感性中的“这一个”变为“这一个”的“无”,是对感性的直接否定,因此对象就成为了“感性的普遍者”。属性是“物”向我们的认识敞开的一扇门,然而属性依附于“普遍者”,当这些属性借助于它而表现时,众多属性就被设定在知觉的对象之中,但是它们就“仅仅与自己相关联,彼此之间漠不相关,每一个都是自为的,不依赖于其他的规定性”。由属性之间“自相关联”或“媒介”,进一步向前推进,我们就能得出“物性”的概念。实际上,“这一个”之中蕴含了众多的“属性”,“但是那个单纯的、自身一致的普遍性本身又不同于它的规定性,不受它们的束缚。它是纯粹的自身关联,或者说是一个媒介,所有规定性都包含在这个媒介或这个单纯的统一体之内”。实际上,这句话中所提及的“单纯的、自身一致的普遍性”即指向了“这一个”范畴。这里黑格尔把它称之为“物性”,正如黑格尔所言的“这个抽象的普遍媒介可以被称作一般意义上的物性或纯粹本质,它无非就是‘这里’和‘这时’,就像已经表明的那样是众多‘这里’和‘这时’的一个单纯集合”。从中可以看出,“这一个”为众多的属性提供了一个共同场所,而属性之间也不关涉他者。比如黑格尔所举的例子“这一块盐是单纯的‘这里’,同时也是多样化的;它是白的,并且是咸的,并且是一个立方体,并且有特定的重量,等等”,这里的“白”“咸”“立方体”“重量”都是自为的,彼此之间互不干扰,仅仅只是因“并且”才发生关联。故而,黑格尔进一步认为“这个‘并且’就是那个纯粹的普遍者或媒介,就是那个把众多属性如此这般聚集在一起的物性”。
“物性”不是“物”,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物性”只是“媒介”“普遍者”,如上面的例子,其中“并且”就是一个“物性”,而不是“物”。由“并且”这个“物性”把属性之间的“自相关联”揭示出来,从肯定的方面确知了“对象”。而在另一维度上,属性之所以被称为“属性”,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它含有否定性的维度。换言之,就是对他物进行否定从而确定自身。进而言之,黑格尔对之做进一步的“规定”,便可得到“物”的概念。
宽泛地说,客观“对象”不仅蕴含了诸般自身所具有的属性,而且还内藏了“他物”的维度。诸如,盐的属性有“白”“重量”“晶状”等。一方面,这些属性都与盐自身相关联着,不与他物相干;另一方面,“白”之所以是“白”,乃是因为它不是黑、紫或绿的。因此,“媒介不仅仅是一种‘并且’,一个漠不相关的统一体,而且也是一个单一体,一个排他的统一体。”换言之,对他物的关联使得对象成为一个单一体。黑格尔说,“单一体是一个环节,代表着否定,因为它以一种单纯的方式与自身关联,排斥他者,并因此把物性规定为物。”由“物性”发展到“物”只需要经历一个“否定”的过程,把“单一体”亦即“个体性”赋予“物性”,“物”的概念得以完成。但是,黑格尔认为,“单一性”和“多样性”,即与“他物关联”和“自身关联”这两个环节对“物”的概念形成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单一性”的“一”与“多样性”的“多”如何统一的问题,始终是黑格尔在“知觉”章中所思量的。这些作为“对象”时的“物”概念,是被“我们”给规定的,而当我们的意识去“知觉”对象时,作为客观存在的对象,与我们意识所认识到的“物”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
我们知道对象既是“一”也是“多”,亦即对象自身包含在差别中,是“一”与“多”的统一。但知觉的意识以“自身一致性”为标准,认为对象不能既是“一”,同时还是“多”;如果它是“一”就不能是“多”;如果是“多”就不能是“一”。所以,知觉的认识活动就难以摆脱自身的“谬误”。在《精神现象学》的第一章中,黑格尔要论证的就是“物的个别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并不能在一个连贯的知识中聚集起来。而在意识尝试着对其只是进行修正的时候,对象把握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换言之,黑格尔要寻求事物的统一性,与第一章中寻“感性确定性”,即简单地确定事物存在着有着本质的差异。当然,知觉在最后还是失败了,其中的关键性因素是“诸属性之间的关系不能在单个事物内部说清楚,也不能归之于人的五官之间的差异,更不能将重心交替放在意识与对象身上;任何属性都必然指向单个物之外,因为属性本就是普遍的,任何单个的物都不可独占某种属性,否则那种属性就是没意义的”。实际上,当主体的意识认识到这个失败后,意识会将认识到的对象进行融合,从而将“一”与“多”进行融会的分析,这样的话会过渡到“知性”领域。
三、“意之所在便是物”:王阳明“物”的概念
实际上,黑格尔一直在思辨的维度上讨论“物”范畴,换言之,他的“物”或者“物性”难以有现实性。换言之,黑格尔有将“物”规定为某种精神的产物之嫌。然而在黑格尔之后,列宁曾说过:“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这是唯物主义的典型观点,与唯心主义截然不同。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似乎两种看法都存续,在王阳明的哲思中两者兼立。
王阳明关于物的讨论,如下几处文献最能体现他的特性。先看王阳明与他的女婿徐爱之间的对话:“爱曰:‘爱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可无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这段对话最为核心的表达便是“意之所在便是物”。然而要想理解这句话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对“意”的解释。关于“意”王阳明曾在与一个学生的对话中解释过。正如“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与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个体的“意”乃是与主体之心相关联的。心之动可唤醒个体沉睡的“意”。进一步而言,意始终与对象相关涉。王阳明还说:“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在王阳明看来,个体的“意”不能无物。人之念虑的展开,就是物的开始。事实上,从刚才的几则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所谓的“物”具有两个层次。一方面,王阳明对“物”的解析,时常与主体之“意”相关涉;另一维度,王阳明以“事”来诠释“物”。
首先,这里先论事与物的关系。朱文正公曾经在《四书集注》中注释“格物”时,曾说道:“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在朱熹看来,从个体日常的生活经验中,我们熟知“‘物’一般表示具有空间性的现象存在,‘事’则一般表示具有时间性的现象存在”。宽泛地说,“事”与“物”之间的关联,常常被我们称作为“事物”,对二者的差异,一般人往往不加区别地使用。实际上,在宋明理学家那里,除了朱子以“事”来解“物”之外,还有伊川也曾认为:“物,则事也。”这亦倾向于以“事物”来指代一切现象,从而把个体实践活动之“事”包含在了“物”的范围内。然而,王阳明的哲思则与此不同。事实上,在王阳明那里,他用“事”来界定“物”,但却不把“事”归于“物”。换言之,在王阳明的思维世界里,“事”不仅归于“物”,且“事”自身即是“物”的全部。
其次,再来看下在王阳明那里“意”与“物”二者的关联。通过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对“物”的分析,时常与“意”相伴。“意”与“物”二者之间的关联,如上面的材料中有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这道出了“意”的属性。个体之心的发动便产生了“意”,这个意简单而言就是思维念虑。然而这个“意”总有一个外在对象与之相伴而生,这个伴随意产生二有的对象便是物。换言之,“意”有时候它既是心的作用和功能,有时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主体”。进一步而言,“物”是“意之所在”即是说物是主体的认识对象,意识的对象,其中体现了认识论中“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然而,“意之所在便是物”之言,容易导致“物”的内化或意识化。进而言之,还会使“物”的内涵推扩至一切意识对象,即凡是可以意识化的事物都属于物的范畴。简单地说,王阳明以事来规定物,是肯定了物的外在实存性即客观存在性,而“意之所在便是物”则是把物内化、意识化,从而扩大了物的维度。
综合以上分析,黑格尔“物的辩证法”与王阳明“意之所在便是物”似乎存在着逻辑上的相关性。黑格尔对物的认识,他始终认为对象的实在性亦即物的客观性,他在论述“物”时,指出物是“实存着的东西”,所谓“物”乃是“反映在他物内与反映在自身内不可分”,此为物的“根据”,物始终是“为他存在”与“自为存在”的统一。然而王阳明在论述“物”时,虽然他有把“物”的概念意识化的倾向,但是他还肯定与“事”相对的实在之“物”。正如我们常常引用他“山中观花”的例子。不论主体来不来山中观花,作为客观的物质存在,花始终在那里。换言之,作为客观的物质存在不以主体的意志转移。但是,山中花要想唤醒在主体中的地位就需要主体去观赏它。此时,作为与主体关涉的“花”就具有了价值上的维度,即主体见此花而一时高兴或失望起来。进一步而言,带有价值维度的山中之花离不开主体我而存在。换言之,王阳明对物的分辨,虽然强调了与“物”相对的“意”的重要性,但也没有否定作为客体而存在的自然之物。总之,王阳明所论之“物”所统摄的辖域远大于黑格尔的“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