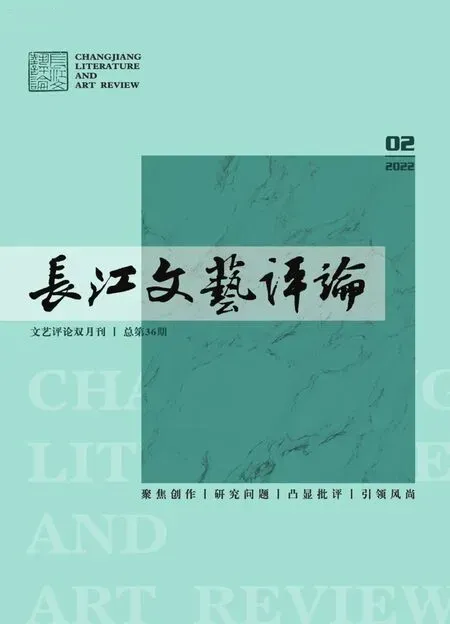不一样的《如果来日方长》
2022-11-07周新民
◆周新民
2020年寒春之际,武汉突然爆发了新冠疫情。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武汉这座城市一度陷入到“封”城境地。像其他武汉市民一样,作家刘醒龙也被禁足在家。作为一名有使命感、有担当的作家,刘醒龙以笔抗疫,写下了一部《如果来日方长》。2020年5月初,武汉开城不久,刘醒龙就带着笔者以及其他二三友人,来到梁子湖岛上,就《如果来日方长》展开了细致、深入的探讨。迄今三年,《如果来日方长》萦绕在心头,总觉得还有不少话可以说说。现就几点感想记述如下。
一、别样的“中国”故事
谈到书写疫情的文学作品,大家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两部作品:《鼠疫》和《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两部作品似乎成为横亘在人们眼前无法跨越的疫情书写的“高峰”。这两部作品虽然主题不同,但是,无法回避的是,这两部作品所采用的思想资源都是个人主义的哲学思想。《霍乱时期的爱情》对于霍乱疫情的书写,更多的是侧面,或者是,霍乱是作为背景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之中的。《鼠疫》是正面叙写疫情的作品,然而,一部《鼠疫》无法写尽武汉这座城市“封”城“战”疫的内蕴。正如刘醒龙自己所言:“不要说一部《鼠疫》,就是再用十部《鼠疫》也说不透武汉‘封城’的平常与特殊”。《如果来日方长》叙述武汉“封”城“战”疫这个重大事件,所采取的文化立场和西方文学如《鼠疫》是不一样的。这包含着刘醒龙对于中西文化的深刻认识:“欧美地区的文化基础,建立在‘原罪’上。一代又一代,只要有人出生,就无法避免产生贪婪、嫉妒、傲慢、仇恨等等‘原罪’。中华文化圈对人的理解,是以‘人之初,性本善’为出发点,信奉善对恶的包容改造。在2020年的新冠病毒面前,西方社会崇尚群体免疫,淘汰老弱病残,留下健康青壮人口,将人性的裸奔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东方,中国率先垂范,通过群体的巨大努力,自觉与不自觉地隔离封闭,动用一切财力、物力和人力,将新冠病毒传染链强行斩断,用科学和拼命使得人道的苦行具备更胜一筹的幸福感。”。刘醒龙对于武汉“战”疫的理解,是从中国文化传统出发来理解的。按照评论家孙郁的观点,刘醒龙的《如果来日方长》所采用的叙述疫情的观点,是中国文化的内视角观点。孙郁认为,这种中国文化内视角是鲁迅之后的中国作家叙述灾难、疫情的主要视角,和西方文学叙述灾难和疫情的叙述方式是不一样的。
刘醒龙对于疫情的理解,决定《如果来日方长》在叙述疫情上的独特性。他重点再现了武汉“战役”齐心协力的集体主义精神。《如果来日方长》对于“战”疫的叙述,焦点对准了武汉人自觉居家隔离的精神,也叙述了医护人员的拼命精神,其情节其细节无不令人动容。
武汉“战”疫,拼的是对人民群众生命的重视。《如果来日方长》有这样一个细节,非常令人感动:“(红窗帘)在武汉三镇最艰难的日子,一位女子发现邻居家的窗户从早到晚都无人来关上,任那红色窗帘在阵风中孤独飘荡。从二月,到三月,再到四月,红色窗帘的主人仍旧没有露面。数百万关注的网友,没有一个人往最坏的方面去想,没有一个人往最惨的方向去说,人人都对着红色窗帘留言,希望它的主人早点回家。一直到武汉解禁,让数百万人牵挂了接近三个月的邻居终于回来,那红窗帘从窗口轻轻消失的过程,见证了最不经意的陪伴。”
这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写尽了武汉人的团结和对生命的重视。这构成了武汉战胜疫情的重要保障。抵抗住了肆虐的疫情,武汉“封”城“战”疫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刘醒龙通过抗击疫情这一特殊战役,写出民族精神的升华:“在新冠病毒面前,一千多万人,全都是以黄继光为榜样的英雄儿女。我的医护朋友小葛医生和小谭护士长们,我的新闻主播朋友们和同事小陈们,我的患哮喘病的夫人和天真无邪的小孙女等家人们,以及我认识与不认识的武汉的人们,在战‘疫’时从未有过‘雄赳赳’,胜利了也不见半点‘气昂昂’,然而,过去、现在与将来,那些跨过鸭绿江的勇士留给中国人的大无畏精神,都会细水长流地传承下去。习总书记说得好:把中国人惹恼了,是不好办的。这句话对天地万物都是道理。”
虽然是书写疫情的作品,但是《如果来日方长》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特殊的精神气。我想,这股特殊的精神气就是刘醒龙通过“封”城“战”疫的书写,凝聚起来的自民间、传统文化的精神与气度。它也是刘醒龙要在作品中书写的一股民族气魄。这是《如果来日方长》最为打动人心之处。
二、日常生活的审美意义
刘醒龙是一位接地气、有温度的作家。这一特征从他走上文坛之初所创作的“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就能看出端倪。刘醒龙一出道,“大别山之谜”就引起广泛的反响。“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被认为和其时中国正盛行的先锋小说有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不过,系统阅读过“大别山之谜”的读者就会发现,“大别山之谜”和先锋文学随处可见的“弑父”情结完全不一样,刘醒龙对于“父”有着不一样的尊重乃至敬仰。其中,对于逝去的传统、美德,葆有深深痛惜的情感。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刘醒龙创作《凤凰琴》时,这种温情成为《凤凰琴》最为打动人的地方。乃至《分享艰难》这部有不同意见的作品,其中最为打动人的地方仍然是它弥漫着对民生的温情关注。从《凤凰琴》开始,刘醒龙开始回归到具体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之中,不再像“大别山之谜”一样,把生活场景置于特定的时空范围之中。《凤凰琴》所叙写的是民办教师的日常教学、生活,乃至争转正名额。但是,刘醒龙所描写的日常生活和自8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主义”不一样。“新写实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继承了先锋小说的遗产,对于人性美和人世间美好的品质、情绪更多的是披坚执锐的解构,以琐碎的欲望洞穿日常生活的底线。于是,我们在阅读“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时候,总难以有满足感的原因是这些小说所叙之事、所写之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也许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又很遗憾地发现,如果文学作品只是照相式地反映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我们还要文学干吗呢?难道我们阅读文学的目的就在于从文学作品中再次强化日常生活?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刘醒龙90年代以来的创作,我们就能理解刘醒龙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从90年代开始,刘醒龙的小说就走上了一条挽救日常生活审美意义的道路。他的小说创作无不一再强化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他的创作,让琐碎的日常生活具备了别具一格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点在《如果来日方长》里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如果来日方长》叙写的是武汉“封”城抗‘疫’的生活。他所写的都是“封”城之后的家庭琐事、个人所感,基本很少涉及到正面抗击疫情的场景。按照批评家们的观点,《如果来日方长》是一部叙写日常生活的作品。也的确如此,《如果来日方长》所叙述的事情是作者一家在封城期间的居家生活。其中有与老母亲的互动、与孙子的亲子活动、与妻子的日常交流等等。但是,刘醒龙在叙写这些日常生活的时候,并非仅仅就日常生活写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在“新写实小说”那里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也进入了作家叙述的视野,为曾被政治意识所遮蔽的日常生活赋予了审美意义。这自然是“新写实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但是,日常琐碎的生活的叙述在“新写实小说”以降,包括90年代“60后”作家所创作的小说那里,日常生活包括琐碎的欲望,都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和意义。原因在于,日常生活曾经具备解放意义,它把人被遮蔽的价值放在日常生活的尺度上进行衡量,赋予它以价值和意义。而90年代市场经济的崛起,日常生活的解放力量不复存在,相反,日常生活成为把“人”变为“物”的主要推动力。如何重建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和意义?这是《如果来日方长》带给我们的启示价值。
《如果来日方长》的第一章“今年水仙花不开”所叙的内容是围绕老母亲决定春节大家原地过年来展开。《如果来日方长》对于这一部分内容的叙述,无非是作为长子的“我”和老母亲之间的交流,也写到了大姐和“我”、家人之间的交流。但是,这种日常交流在《如果来日方长》中获得了特别的意义。这个意义不在于真的叙写老祖宗的英明神武,而是表明了亲情的精神力量。《如果来日方长》运用文学的手法,表达了这一观点:“‘封城’下,所有人的神经都极度敏感。连失聪者都恨不能听清楚对面楼栋昨夜一共响了多少声咳嗽。阳台上的水仙花,看得见,也听得清,她对气温变化无常的敏锐,检查阳台面对的近千户人家中每一个三十七度三以上的人体体温。人不知,花有觉。水仙不开花,她用开花所需要的精神物质,弥补灾难中人所表现的不足和不如意,将寒冬腊月对春暖花开的渴望凝成精灵,像家里没有贴在窗户上的福字那样,收起美丽,让省下来的春意,潜入更需要的人家!”普通人的日常情感在《如果来日方长》里得到了升华,自然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如果来日方长》还有一段写和家人过情人节的场景,写得很动人。情人节本是舶来品,现在已成为中国人表达爱情的重要节日。情人节的日常,无非是恋人、夫妻之间表达爱情。但是,2020年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正处在“封”城之时。情人节献花的仪式只能在室内进行。由于“封”城,鲜花市场没有开放,鲜花也只能“就地取材”。《如果来日方长》有这样一段描写:“我转身走向冰箱,打开最底下的冷藏柜。又从冷藏柜的最底下,翻出一只塑料袋,再从塑料袋里取出两根剩下来的洪山菜薹。昨晚清点冰箱的食物时,就曾发现它们。当时还忽闪一想,这东西得尽快炒了吃掉,不然会老得只剩下一层皮。洪山菜薹是‘封城’之前买回来的,原本打算大年初一开车去罗田县城给老母亲拜年,带去给老人家尝鲜。武汉突然‘封城’,原计划落空,只好留作战‘疫’物资。不知什么时候,剩下来的两根洪山菜薹被压在冷藏柜最底层。过了二十多天,菜薹根部已经空心化,那最清甜的营养都被输送到最顶端,用来开出几朵金黄色的小花。我背对着家人,将几朵凄美的小黄花拿在手里整理半天,也无法弄得像个模样,只好原样拿着,回过头来,当着孩子们的面,郑重地献给夫人。夫人灿烂地笑过后,眼睛里多出一层亮闪闪的东西。”
“我”找出洪山菜薹,把她作为鲜花,献给妻子。这样一些日常生活,在平时,也就是平常的行为,而在“封”城期间,这段献花仪式就具备了不同于一般日常生活的意义。它是武汉这座城市达观、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最为充分的表达。
《如果来日方长》虽然写的是“封”城“战”疫期间的日常生活,但是,这些普通人的生活描写,具备了不一样的特别意义。它不同于自“新写实小说”所开辟的描写日常生活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如果来日方长》拯救了日常生活的审美意义。
三、一种新的美学风格
一般说来,叙述疫情,包括抗击疫情的文字,一般呈现两种美学风格,一种是充满哀伤的美学格调。产生这种美学上的格调,也实属正常,毕竟疫情是一场大灾大乱。它不仅仅冲击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还给人们的情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损伤。因此,一般书写疫情的文学,往往会呈现疫情给人世间带来的伤害,叙述个人在疫情面前的无力感和挫伤感。这样的叙述文字,自然给人带来无边的哀伤,这是疫情文学正常的审美效应,它给人们的情感宣泄带来机缘。疫情文学的另一种审美风格,是人定胜天的豪迈的美学风格。这种审美风格的出现,主要表现人们战胜疫情的必胜信念和胜利最终来到的愉悦。这种审美风格也是疫情文学的一种重要价值,它带给人们的是战胜自然的信心和力量。这两种疫情文学的审美风格,都有其重要价值和意义。但是,人们也会不得不仔细思考,难道除此之外,疫情文学再也写不出另外一种审美上的风格么?
《如果来日方长》在美学风格上毫无疑问做出了一番探讨。它给我们呈现的是另外一种美学风格,我简单地归纳为“哀而不伤”的美学风格。客观地讲,书写疫情的文学作品难以回避作品中笼罩的哀伤氛围。即使是那些具有刚直力量、充满豪迈情感的抗击疫情的文学作品,也难免触及到哀伤的情感。起于哀伤而终于豪情,是豪迈美学风格的疫情文学的重要特征。而那些充满哀伤的疫情文学,也只不过是更多地书写到了哀伤罢了。但是,刘醒龙的《如果来日方长》不一样。作为一部书写武汉新冠疫情的文学作品,它难免触及武汉这座城市、中国这个国家在面临疫情时的慌乱和无法承受的压力。《如果来日方长》仔细盘点了整个武汉市收治新冠肺炎病患的床位情况:“陷入舆论风暴的市中心一医院,连个呼吸道传染病床位都没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只有十七家医院设有能够收治新冠肺炎病患的可怜兮兮的九百零八个呼吸道传染病床位。就是在这不足一千个呼吸道传染床位里,拥有更严格标准的负压病床位,除了金银潭医院有一部分,就只人民医院东院还有两个。其余像久负盛名的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等,连一个负压病床也没有。如此窘境,也是疫情爆发后,拥有众多大医院的偌大都市,难求一张病床的现实原因。”《如果来日方长》虽然没有直接写疫情期间武汉的悲惨景象,但是,通过这一组冷冰冰的数字,我们还是能感受到疫情突如其来的时候武汉的惨状。《如果来如方长》也的确通过一些文字,叙述了武汉封城期间生活的不便,也写到了人们对于不明疫情的恐惧和对武汉这座城市的担忧。这些是作为叙述疫情的文学作品难以回避的内容。自然,当触及到疫情的恐惧和惨状,这些文字流露出的悲哀情绪,是自然难以避免的。
然而,《如果来日方长》绝对不是为了宣泄哀伤。它在美学风格上是“哀而不伤”。在超越“哀”上,《如果来日方长》也没有陷入到豪迈的情感宣泄之中。虽然,《如果来日方长》所叙写的事件涵盖了疫情的发生、发展和结局的整个过程,但是,它没有沿用从疫情开始到疫情的发展再到疫情结束的自然事件来叙述事件。一般说,按照疫情的发生、发展和结束的自然事件来叙述疫情的发生和抗击疫情的整个过程,是最能体现人和自然的搏斗过程的,也最能体现人最终战胜自然的书写目的,这也是时下大多数疫情书写的最为常规的写法。但是,《如果来日方长》的叙述避免了这种线性的叙述。它在结构上没有采取这种结构方式,而是采取了一点多面的结构方式。从全书的整体内容来看,全书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今年水仙花不开”“你在南海游过泳”“问世间情为何物”“九七年的老白干”“情人节的菜薹花”“洪荒之力满江城”“冥冥中自有天理”等几个部分。这几个部分之间无事件线也无情感线。这种处理方式的目的就是不愿意把《如果来日方长》写成抗击疫情的豪迈之作。作品中每一个章节都写到了疫情和抗击疫情的事件以及在这其中所产生的情感。
每一章的内容首先写的是家庭的生活场景,表现的是日常化的普通人的情感。其次是写和“我”有关的人,以及相关的人和事情、情感。再向外扩展一层就是社会的生活场景,以及对很多问题的一种思考。这样的由己往外的洋葱式结构,使《如果来日方长》的书写回避了一般意义上抗击疫情的书写结构。那么,作为洋葱结构的《如果来日方长》的内核是什么?是什么使《如果来日方长》的各个层次的内容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这个内核就是“情义”。“今年水仙花不开”“情人节的菜薹花”这两节是写家人之间的“情义”,写的是亲情、爱情。“你在南海游过泳”则主要写的是朋友之间的“情义”。而其他三个部分主要是人间的“情义”。由“情义”统一起来了的《如果来日方长》,使它的各个部分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但是,《如果来日方长》又不是一般性的人世间的普通情义。人世间的普通情义自然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最终的落脚点是涉及民族兴旺发展的“义举”。在刘醒龙看来,“毫无疑问,武汉‘封城’战‘疫’是史诗级的义举。追溯起来,这样的苦痛惨烈正是中华文化最为看重的春秋大义。”正是基于对中华民族的“大义”的书写,《如果来日方长》所体现的美学风格,就不是简单的哀伤和豪迈所能概括的了,而是接地气的“哀”,是升腾出来的“大义”。所以,《如果来日方长》所体现出来的美学风格就不只是“哀而不伤”了。
《如果来日方长》作为一部书写疫情的文学作品,它具有具体特殊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同时,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如果来日方长》也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在庚子疫情过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重新阅读《如果来日方长》的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