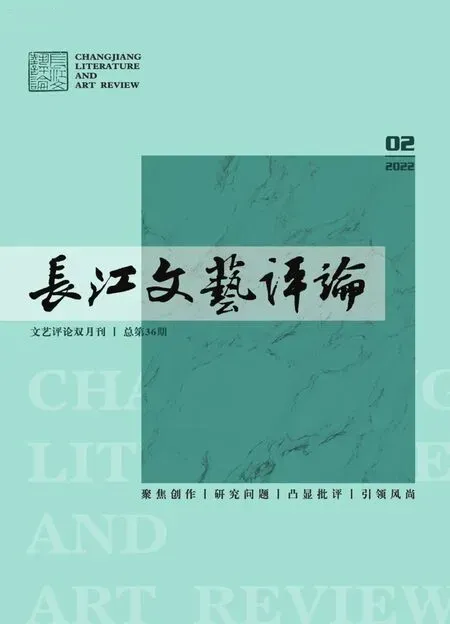革命者·偶像·“反英雄”
——试谈改革开放以来哪吒动画形象的时代嬗变
2022-11-07刘思彤
◆陶 冶 刘思彤
自改革开放以来,哪吒的神话故事先后经历了五部国产动画片的改编。这42年里,不仅中国从改革开放走到了新时代,国产动画也经历了从辉煌到低谷直至今天的“国漫崛起”。在这种时代变迁的背景下,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所处不同时期的动画文本中哪吒成长叙事的差异,全盘视为创作者主观的艺术观念所致,诚如饶曙光所言,动画创作“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对其的根本性解释需要从生产的时代语境中探索答案”。并且,动画作为凝结了大量劳动的文化产品,恐怕时代的集体意识对作品的创作有着更大的影响。
革命英雄的新时期斗争
1979年出品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其里程碑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是中国第一部宽银幕动画片,也是中国第一部在戛纳参展的华语动画电影,更为重要的是它身处刚刚结束“十年浩劫”,迎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新时期”。一方面根据神话改编而来的《哪吒闹海》成为反思“文革”期间“题材禁锢的媒介载体,积极回应着解放思想的时代方针”;另一方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创作者们又通过对《封神演义》中相关情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改编,彰显了这一时期中国动画创作者“破旧迎新”的创作理念。
创作者们对该片进行了全龄化观影的定位,《哪吒闹海》的导演兼编剧王树忱曾撰文回忆当初选择这个题材的初衷,就是因为“它是少有的以小孩为主角的神话,这段故事给小孩和大人都合适”。同时,对于哪吒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导演表示“要让人们感到他活着可爱,死了可惜,复活有理”,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兼具了正剧和悲剧的风格。这种新的艺术观念具体表现在对国产动画低龄受众定位的突破,并在与时代的互映中构建起了观众的情感认同。
(一)反帝反封建的斗士
1979年的《哪吒闹海》对明代《封神演义》中有关哪吒的故事情节较为显著的改编,便是将哪吒大闹东海的行为动机从顽皮惹祸改写为救人心切。影片中作为一方天官的龙王却要吃掉人间的童男童女,如此一来,影片中的正邪对抗其实是包裹了一些微妙的阶级对立意味,无形中承接了“十七年”革命电影中的叙事逻辑。它继续上演了“那些由无辜的受害者(陈塘关的百姓),勇敢的抗议者(革命者哪吒),清醒成熟的智者(支持哪吒复仇的太乙真人),与邪恶、非人的恶势力(腐败的权力专制龙王)之间的生死角逐”。当然,影片中与哪吒对立的是“旧”有的腐败专政,因而它可以被合理地质疑和批判,这也是作为“新”的上层机制所给予艺术家有限的话语权力。而个体的抗争总是要与国家的民族的解放连为一体,才能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凸显出意义,就像影片中的哪吒决心打败龙王并非为己,而是为了拯救整个陈塘关百姓,他的“革命行动”始终围绕着人民利益出发,继续实践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主流意识形态。
影片中所体现出的哪吒的革命意识也并非只是推翻专制的暴权,而是通过暗合在故事情节里的父子冲突,呈现出对封建落后文化一定的反思。影片中李靖身为哪吒的父亲非但没有肯定哪吒的救人之举,反倒对哪吒呵斥“你怎敢伤害天庭龙种”,进一步彰显了封建纲常伦理的愚昧性。而那个自己受了委屈还怕连累父亲的哪吒,如此写实地反映了长久以来被父权压迫的子一辈无奈的心理,因而哪吒选择以自刎完成了自己的“孝道”尤为令人痛心。当对抗龙王时威风凛凛的英雄哪吒,也因无法回避这种“父父子子”的情感纠缠而倒在血泊之时,反而将影片反强权反压迫的斗争精神推向了极致。诚如戴锦华在描述“新时期”涌现出的文化英雄那样,哪吒“作为一种体制的批判者,以燃烧自己的方式而照亮了前方黑暗,成为了当然的这一时期的引路人”。如此,《哪吒闹海》这一全龄化的成长故事,对于儿童来说,它无疑是再次讲述了一个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童话寓言,而对于经历文革伤痛,迎来思想解放的成年观众而言,显然它是蕴含了启蒙精神的典范。
(二)“大团圆”的人道主义
诚如王树忱导演的笔述,影片中的哪吒是饱含了悲剧色彩的英雄,出于解救小伙伴的正义之举却让他承受了生命的代价,而更显悲剧性的是,这一结果又是由哪吒的父亲间接导致的。在影片的高潮——“哪吒自刎”的情节点上,四海龙王以陈塘关百姓的性命相逼,而关键时刻哪吒的法宝又被父亲收缴,致使其无力对抗龙王。
在这个叙事段落中,导演以哪吒的视点快速衔接了一些百姓们受苦的近景和特写镜头,目睹了这一切的哪吒毅然决然地拿起了地上的刀剑。影片灰暗的色调将英雄赴死的悲壮氛围烘托到极致。而叼着法宝奔向哪吒的梅花鹿也未能实现“最后一分钟营救”,不甘屈服的哪吒就这样成为了旧恶势力压迫下的祭品。到了影片后半段的情节,哪吒复活的众望所归,以及哪吒歼灭妖龙的大快人心,将影片前期的悲剧基调陡转为“大团圆”结局,应验了革命的前途——“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胜利”神话预言。
全片最耐人寻味的是结局的那一幕,打倒了龙王的哪吒脚踩着风火轮,在小伙伴与疼爱他的管家的欢呼声中归来,作为英雄的他貌似又回到了人民群众中去。可是随即哪吒又骑着他的小鹿大步奔向了远方,他去了哪里我们不得而知,但正是如此,给予了观众足够多想象的空间。而且归来这一幕全然不见了曾经将他束缚住的父亲,是否也象征着哪吒已经摆脱父权的那层压迫?这种联想并非毫无根据,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新时期”,“解放思想”的政治方针也一同带来了70年代末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也使得艺术家们将创作的思考落在了如何反映“人”的价值和尊严这一点上。
影片中的哪吒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才得以重新回归,与遭受了十三年打压,在“新时期”涅槃重生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着几乎一致的境遇。换言之,创作者们将自己所处变革时代获得的直接经验,已经表露在了哪吒的“英雄旅程”里,而影片中的成长叙事,并非只是为了满足艺术家个性的宣泄,而是尽可能地映照出时代的其他景观。哪吒的成长之路唤起了部分创伤记忆,而其奔向自由的结尾则回应了人道主义思潮下,大众对新生活的向往。这不仅是一次对群体情感经验的总结,更是一次集体潜意识的流露。
少年英雄的新世纪蜕变
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却是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体身份的危机,不仅一种反思和质疑全球化的思想在国内蔓延,而且传统文化复兴的民族化思潮也进一步渗透到了文艺创作的实践中。在国产动画领域,神话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被再次唤醒和激活,“哪吒”作为家喻户晓的神话英雄也再一次呈现在了影视作品中。首先是2003年中央电视台所播出的52集电视动画片《哪吒传奇》,曾为当年的央视创下了7.06%的高收视记录。而2016年的《我是哪吒》更是打着“国内首部以哪吒为主角的3D动画电影”的名号与观众见面。相比于前作《哪吒闹海》,这两部动画片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对哪吒以更贴近现代儿童的形象进行塑造,其“英雄之旅”也更像是一场儿童世界的冒险探索,尽管影片也还是一如既往地以主人公打倒反派、拯救世界为结局,但其成长的重心是凸显身为“儿童”的主人公性格的蜕变和收获。动画片中哪吒的英雄蜕变更像是现代少年儿童成长生活的投射,换言之,这两部动画片中都有意将哪吒的“英雄之旅”与现代少儿的成长轨迹缝合,使得哪吒不仅被塑造为动画片中的少年英雄形象,也力图将其打造成为文本外部少儿观众的偶像。
(一)儿童教育的功能性期待
从哪吒的视觉形象上看,2003年《哪吒传奇》俨然是沿袭了《哪吒闹海》中刚出场时身着红肚兜的小娃娃形象,一方面《哪吒闹海》和《哪吒传奇》中主人公的视觉年龄都指向孩童,这固然是对神话里哪吒原型的还原,但在2003年《哪吒传奇》中哪吒的性格特征显然更贴近于现代少年儿童。哪吒传奇的导演曾坦言,在塑造哪吒这一人物时,是有意凸显哪吒的孩童特征,要将其视为一个正在成长的小英雄。如此来看,“小”和“英雄”正是导演对哪吒形象塑造的重要指导理念。
一方面对“小”的强调使得正在成长中的哪吒被允许暴露一定的缺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哪吒传奇》中那个起初有点骄傲自负的哪吒,那个因为贪玩弄丢了盘古石的哪吒。但“英雄”的所指,又强调对哪吒正面形象的塑造,并能通过电视机“合家欢”的效果达到教育青少年儿童的目的。换言之,创作者们实际上是以《小兵张嘎》的方式在塑造着哪吒的形象。另一方面,199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提出少儿文艺作品应当增强知识型和趣味性。这更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新世纪后动画片创作方向的调整,消解了上个世纪的小英雄天生的“正义凛然”,而是呈现一个更能被少儿观众所认同的,与自己一起成长的“朋友”。
在革命记忆日渐遥远的新世纪,时代的轻松氛围也使得英雄背负的使命不复上个世纪的沉重感。与《哪吒闹海》中那个需要反权威斗父权的哪吒相比,一种更无忧快乐的小英雄形象,呈现在了彼时的动画荧屏上。新世纪以后哪吒“英雄旅途”的重点也相应地不只是描写英雄如何历经磨难为世人带来正义与光明,而是强调其如何在冒险路上,长知识长本领,形成正确的道德品质。甚至在《哪吒传奇》每集大写的片头中,都会出现“信义无价”这样直接的“中心思想概括”。并且,“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等一些指向优秀品格的故事,也被杂糅到了《哪吒传奇》中演绎,这无外乎也是社会对新一代少年儿童的教育期待,使得少年英雄小哪吒可以被清楚地认定为是新世纪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二)少年英雄的全球化想象
作为中央电视台耗时三年,总投资上千万元人民币的力作,《哪吒传奇》的导演在其创作阐述中,曾谈到“我们长久以来渴望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民族气派的动画片,塑造出中国的卡通明星,让中国儿童欢喜,乃至受到世界儿童的喜欢。”话语背后是对国内动画市场长期以来被美日动画片所占领的一种文化焦虑。实际上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系列引进的外国动画片就受到了国内青少年儿童的极度喜爱,有调查显示,在90年代北京电视台播放的动画片中,迪斯尼出品的动画占到了百分之五十,美日动画加起来的占比远超国产动画。因而对哪吒以更贴近现代儿童的特征塑造形象,几乎已经上升到彼时国产动画与国外动画竞争中国儿童收视主导权的地步。
然而矛盾的是,当少年英雄小哪吒被视为是一种民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抵抗,并希冀他也能实现“文化走出去”之时,我们仍然能在《哪吒传奇》中看到不少迪斯尼动画的影子。尤其是该剧中作为哪吒成长道路上的伙伴“小浣熊”的加入,显然是在1999年迪斯尼动画《花木兰》在国内上映以后,国产动画中才出现这种主人公和他的动物小帮手设置。事实上,该片一方面希冀通过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挖掘,宣誓全球化下“自我”与“他者”的差异;而另一方面,又能在“自我”的身上不断找到“他者”的影子。这种断裂和矛盾,不只体现在新世纪以后国产电视动画片的创作领域,在动画电影的创作中也比比皆是。2011年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兔侠传奇》中兔二的“英雄之旅”,和2008年美国梦工厂出品《功夫熊猫》中阿宝如出一辙,无一例外都是平民英雄历险归来、实现梦想的故事。
再看2016年动画电影《我是哪吒》中小主人公离开家实现梦想,进而拯救世界,最终重回家庭收获爱的情节,其实也并没有跳脱20世纪90年代以来,迪斯尼动画奉行的“儿童冒险+温情路线”的叙事模型。诚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言:“人们只有分享共同的东西,才能在差异中彼此共存”,显然,在全球化浪潮中,多元文化的碰撞之后的互相融合不可避免,对于国产动画创作亦是如此。
另类英雄的新时代自信
在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主题的新时代,大国崛起所带来的文化自信,也在2015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下简称《大圣归来》)的市场逆袭之后涌入动画电影的创作领域,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今日所谓之“国漫崛起”。
《大圣归来》的标志性意义,还在于国产动画的创作终于可以呈现出一种由低幼化逐渐转变为面向全年段受众的趋势。而其塑造的另类英雄孙悟空的形象,是与传统英雄完全相悖的“反英雄”。显然,这种“反英雄”的塑造到了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魔童降世》)及2021年《新封神榜:哪吒重生》(以下简称《哪吒重生》)仍在延续。《魔童降世》的导演饺子在接受采访中多次表明是《大圣归来》给他带来的信心,甚至在该片以50亿票房荣登中国电影史第三位的当日,其官方微博还主动提及《大圣归来》并予以致谢。而《哪吒重生》的导演创作之初就是想要以年轻一代的情感召唤一个全新的哪吒。这两部作品与《大圣归来》有着一致的内在叙事逻辑——讲述一个现代人的成长故事。
(一)英雄自反与观众镜像
2019年《魔童降世》中一个烟熏妆的丑哪吒,极大地颠覆了观众对哪吒的既有印象;而2021年《哪吒重生》中的哪吒更是化身为骑着摩托车的热血青年。他们对于哪吒不仅只是颠覆前作中哪吒的视觉形象,而且在主人公身上还赋予了明显的“反英雄”特征。
《魔童降世》中的哪吒被设定为魔丸出世,当面临他人的误会时,他并不会选择忍气吞声,甚至会如反派般予以暴力相向;而《哪吒重生》中的主人公李云祥,尽管是迫于生计,但其确实一直从事着非法走私的活动。这两部影片中的英雄主角形象所体现的复杂性恰恰就是成人世界灰色地带的缩影,从而使之有别于传统英雄故事里善恶分明的设定——显然这种灰色的人物设定,就表明了影片创作之始便不打算面向低龄化群体。
两位主人公身上所体现的不止于要褪去了英雄完美的外衣,暴露出一定的性格缺点,而是他们发出了一种共同的困惑——“我”是谁?这是在前三部哪吒神话改编动画片中均未呈现的。显然,这种“我是谁”的困惑恰恰也投射了银幕前的观众对自我的追问——以80后和90后为主要消费群体的目标观众,恰恰是中国计划生育背景下独生子女的一代。有学者曾经这样描述过这个群体的心理特征是:“因为缺乏兄弟姐妹,总是会显得孤独,又因为一直是家庭的中心,使得他们更关注于自我”。因此他们一开始就能够体会到影片中主人公的孤独和自我怀疑,对于人性暧昧不清的理解,对人与群体之间的隔阂,正是这部分群体共有的精神困境。
从角色认同的角度看,他们更能与影片中“反英雄”特征的主人公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而影片的“英雄之旅”所完成的根本上说恰恰是个体对于“我是谁”的解答过程。毫无疑问,几乎所有的艺术作品本身都会存有艺术家个人的情感投射,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魔童降世》和《哪吒重生》的导演都是80后,影片打动的也恰恰是银幕前的80后观影群体。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为,在一个缺乏自我认同的时代,电影银幕就成为了一面镜子,银幕中的与观众产生共鸣的“反英雄”,投射出的恰恰是观众自我认同的镜像。
(二)个人情感与集体理想
“反英雄”并不是代表着反对英雄,只是淡化了先天的英雄主义,让英雄从神性中回到普通人的身份上来。英雄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心灵符号,无论在何种时代和社会语境下,它都能被有效地召唤出来。有学者认为,在当代社会,急剧的社会变迁会带来人们对“英雄功能”的质疑。但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却呈现出一种积极的辩证法:“一方面是个体心理空间的扩大的同时也会带来公共服务意识的生长”,个人往往还是会归属到集体中,找到自我的价值。
正如《魔童降世》中,哪吒是因为想改变他人的看法,所以开始跟着太乙真人学习了法术,欲通过降妖除魔来寻找自我价值,而他最后返回陈塘关,也是因为他被父亲李靖愿意以命换命所感动,但影片最后呈现的还是哪吒拯救了陈塘关。影片的大结局是以一个全景镜头交代了陈塘关百姓对于哪吒的感谢和认可,而看到这一幕的哪吒也深受感动。可以说,哪吒拯救陈塘关所以他成为了英雄,同时回到集体中的他,也获得了改变。
在《哪吒重生》中,李云祥打败了东海龙王,实现了个人复仇,但同时他也阻止了海啸的来临,拯救了东海市的百姓们。这也是中国的英雄大片与好莱坞大片所呈现的完全个人英雄主义最大的不同。尽管新时代以来的国产动画电影更多地彰显了人性与情感的主体地位,但归根结底,中国式的英雄叙事并不会凸显个人与集体的二元对立,而是将个人与外部世界力量融合在一起。这是能继续响应新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体系,同时又能让观众产生认同型互动的英雄。
事实上,从2015年暑期的《大圣归来》开始,近几年涌现出来的头部动画电影中,都非常注重对个体微观经验的阐述,将高高举起的英雄主义回归到日常平淡的叙事中。“反英雄”人物塑造的有效性,其实是将个体的话语表达与现实生活中的景观实现深度的套嵌,从而建构起观众对人物的情感认同。此时,英雄的深刻性得以彰显———他/她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群体的镜子,他/她最终仍然会回到主流价值的话语中,从而在集体认同中获得“我是谁”的自我认同。
结语
从1979年的《哪吒闹海》开始,国产动画片中哪吒“英雄之旅”变迁的叙事逻辑,恰恰是从中国迈入改革开放以来,国产动画创作与不断更替的社会文化和市场环境的融合。而“哪吒”从革命英雄到少年英雄再到“反英雄”的变换,一方面体现了国产动画创作努力探求与时代同步的文化自觉,另外一方面也带来了今日国产动画的创作实践应该思考的现实问题,即夹杂在与好莱坞动画和日漫竞争中的国产动画,如何以传统文化为根,同时又能适应当代受众的文化心理。正如那些已经取得票房佳绩的现象级国产动画,既重拾了对中国悠久神话故事的改编,唤醒了国产动画电影的传统文化因子,同时又以对英雄情怀的当代性书写被盛赞为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
首先,国产动画英雄叙事的核心应落脚在对社会共同情感的表达上。《哪吒闹海》中的革命英雄曾经呼应了新时期启蒙思想和后革命下的“人性”反思,而《魔童降世》中“反英雄”叙事的成功,也是因为瞄准了新一代年轻观众对自我的关注,与银幕中有着“缺失”的英雄的情感共鸣。
其次,国产动画的创作在承接了美国迪斯尼、好莱坞超级英雄故事的叙事传统后,一种新的本土动画英雄叙事也正在生长出来。曾几何时,当国产动画电影使用好莱坞式的语法展开叙事,不免让人质疑这是对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文化霸权的默认。《魔童降世》后观众对“神话宇宙”的想象,也是国人对本土超级英雄电影的呼唤。
实际上,自2015年《大圣归来》以来,国产动画电影发展至今已经有足够的技术自信,而新一轮的国产动画创作中的“反英雄”将个体主义和集体诉求的融合叙事,更体现了将民族文化内涵与“他者”的成功叙事经验有效融合之后建立起来的文化自信。那么“哪吒”之后,国产动画的发展又该去往何处?大热期待之下的《姜子牙》并未取得如期的票房,或许已经说明了,国产动画才刚刚踏上自己的“英雄之旅”。
注释:
[1]饶曙光,常伶俐:《挑战与机遇:当代国产动画电影的现象反思》,《长江文艺评论》,2018年第2期。
[2]褚亚男:《传统文化资源与动画创新策略研究——以20世纪80年代中国动画电影为例》,《当代动画》,2019年第2期。
[3][4][8]王树忱:《〈哪吒闹海〉的剧本改编和银幕体现》,《电影通讯》,1979年第4期。
[5]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6]褚亚男:《传统文化资源与动画创新策略研究——以20世纪80年代中国动画电影为例》,《当代动画》,2019年第2期。
[7]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9]朱洁:《中国电影中人道主义思潮的流变——兼论新生代电影中的人道主义》,《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0][12]蔡志军:《中国卡通明星——谈〈哪吒传奇〉中哪吒的人物塑造》,《电视研究》,2003年第10期。
[1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新华每日电讯》,1997年5月23日头版。
[13]杨利慧:《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民间传统的重构——以大型国产动画片〈哪吒传奇〉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4]【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郭忠华、何莉君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5]史春景:《不英雄的英雄孤独的反英雄——〈局外人〉中莫尔索形象再次解读》,《文学界(理论版)》,2012年第7期。
[16]白惠元:《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1页。
[17]沈杰:《志愿精神在中国社会的兴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