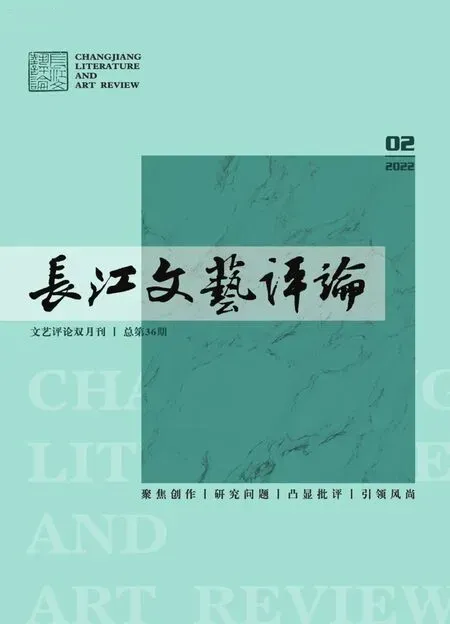19岁到21岁,韩少功汨罗经验的细节性呈现
——对《长岭记》的还原性阅读
2022-11-07◆黄灯
◆黄 灯
2021年3月,《芙蓉》第二期刊出了韩少功插队期间的日记《长岭记》,涉及的时间将近两年,从1972年3月到1974年12月。整体来看,韩少功汨罗的插队时光分为三个阶段:其一,1968年12月到1972年3月,主要在天井茶场劳作。1968年12月,韩少功响应国家号召,成为一名知青,落户到湖南汨罗天井公社,多年来,“韩少功的天井茶场”,已沉淀为汨罗人的一种共同记忆和集体意识。其二,1972年4月到1974年12月,转点到长岭大队。在茶场待了三年多后,1972年3月21日,韩少功因写作能力强,转点到长岭大队,除了日常的农业劳动,得以有机会不定期参与一些文化宣传工作,这段时光持续到1974年年底。其三,1974年12月到1977年12月。1974年12月31日,韩少功被汨罗文化馆招录,正式结束了知青的时光,成为了一名有干部身份的人,严格说来,这段时光已经和知青身份没有太多关系,但依然是他汨罗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意思的是,在对韩少功下放阶段的汨罗经验进行盘点时,涉及最多的是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天井茶场”和“写作《任弼时》”,构成了其中的关键场景和典型事件,而第二阶段,则鲜少有人提及,事实上,1972年到1974年底,是韩少功从懵懂少年向成熟青年转变的重要过渡时期,这三年的人生经历对他极为重要,《长岭记》以非虚构的日记体还原了这段时光,让人从岁月的烟尘中走向了历史现场,感受到了韩少功青春时代汨罗经验的各类细节,丰富呈现了这段时光对韩少功一生的重要价值。具体说来,韩少功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日常生活,诸如劳作、文化、文娱活动等;也记下了他写作的初步尝试,更对知青命运的变迁以及个人命运的走向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下面将从以上几个方面,通过对《长岭记》的还原性阅读,勾勒韩少功19岁到21岁汨罗经验的细节呈现。
一、日常生活的肌理
《长岭记》以个人的视角,详细记载了韩少功本人的日常生活。从文本提供的信息,可以看出韩少功1972年3月到1974年12月,从事的工作主要与以下方面相关:一、各类农业劳动,这构成了他生活的主体部分,这其中既包括种田、作地这些传统的农活,也包括农村的一些日常杂务,诸如建筑、搬运等。传统农活如下:下禾种(1972年3月26日)、保秧苗(1972年3月30日)、插秧(1972年4月20日)、薅禾(1972年5月3日)、车水(1972年7月7日)、收割踩打谷机(1972年7月19日)、学犁田(1974年9月6日)等;日常杂务则包括挖茶坑(1972年4月2日)、挑竹子(1972年4月12日)、建猪场,去弄石头(1972年5月28日)、做泥砖(1972年8月7日)、育杉秧造林(1973年2月27日)、对付地震(1973年10月8日)、拖石灰(1973年11月25日)、去戴家里借秧(1974年4月27日,救两个被雷击的人)、挖红薯(1974年10月15日)等。二、各类文化、政治活动,主要侧重写材料、编刊物和参加文艺汇演及汇报开会,如,参加(汨罗县)文化馆歌曲创作班(1972年4月6日)、办油印刊物《革命文艺》(1972年5月5日)、跟随罗玉堂书记画地图(1972年7月5日)、到公社帮忙写材料写标语(1972年9月29日)、挑送放映机和发电机到黄市(1972年10月9日)、写一个学哲学救猪娃的先进典型材料(1972年10月24日)、刻蜡纸赶编《革命文艺》(1972年11月9日)、参与岳阳地区文化工作会的全体代表检查工作的汇报演出(1972年12月15日)、寻访杨沫故居(1972年12月16日)、去县里报到写剧本,迎接全省的文艺会演(1973年4月4日)、去弼时公社采访(1973年 4月 10、11、13、15号)、参加公社老师联欢会演(1973年8月7日)、在张家坊开会半天(1974年10月12日)等。三、娱乐活动,1972年6月20日,韩少功记载了知青加盟打篮球,晚上文艺汇演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些事情算得上这个年龄段少有,但因为时代的特殊带来的经历,诸如1973年4月28日,在玉池公社卫生院,与程大安解剖尸体;1974年4月27日,去戴家里借秧,遇上雷击,在路上救两个被雷击的人。1973年5月11日,去新华书店买查封的书。
从这些生活细节可以看出,知青的生活经历非常复杂,从他日记内容看,劳作和参与各类文化活动,构成了韩少功知青生活的主体,其中,对他影响最深,记忆最深的是各类劳动。尽管所从事的农活特别庞杂,但繁重的体力劳动,给一个出生城市的年轻人带来的冲击,还是让人印象深刻,韩少功在1972年7月19日的日记中,较为具体地记载了踩打谷机时,给自己带来的体力挑战,“我是踩(打谷)机子的主力,呜呵呜呵地踩上一天,滚筒越来越重,带泥、带须、带水越来越多,根本踩不动,累得人吐涎水。最怕中午收工,烈日暴晒,还要送谷去晒谷坪。两箩水淋淋的谷,足有两百来斤。路面本来已经很烫,加上担子一压,脚皮紧紧贴地,就像爆烧肉皮。这时候的跳脚只是心理想象,因为双脚根本不听使唤。”“到晚上,路面没那么烫了,但蚊子扑面而来,吃几口饭都要连连打腿,打得两腿血迹斑斑,都是蚊子血”。“摸回家,一倒床就可以呼呼大睡,腿上的泥可能都来不及洗。”
换一个视角观照,韩少功从1972年3月到1974年12月,从天井茶场转点到长岭大队后,实际上处于组织随叫随到的状态,由此也可以推断出韩少功知青年代通过参与多项工作,和当地生活的深度融合状态。对笔者而言,这段极富时代特色的日记,不但激活了我的记忆,也纠正了我的一些认知偏差。先说韩少功日记对我童年记忆的一种激活,1973年12月15日,《长岭记》提到,“在嵩华(大队)的冬修水利工地上挑泥,晚上编印简报。这里同漉湖工地一样,吃饭有窍门:第一碗不能装太满,以便很快吃完,抢到先机便能吃上第二碗;否则,吃第一碗太费时间,一不小心饭桶空了,第二碗就吃不上了。当然,谁也别指望第三碗,因此第二碗要尽量装,往死里压满、压实、压紧,压他个心狠手辣气壮山河”。“这叫一碗快,二碗胀,三碗四碗叮咚咣。”有两个细节,其一,是漉湖当年兴修水库,我童年因为住在外婆家,当年小舅舅还没有结婚,我记得他也经常要去修漉湖,从韩少功1973年记载的修漉湖,持续到我记忆中的1978年,可以说,修漉湖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二,在乡村,从小就被告知,一定要吃饭快,而且第一碗不要太满,以方便盛第二碗,原以为这个习惯是自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从韩少功日记推断,这个已被内化为当地村民的一种习惯,其实来源大集体时代的义务劳动,《长岭记》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我的印象。再说对我的一些认知偏差的纠正。韩少功和别的知青不一样,尽管在离开汨罗前,他仅仅只是展示了会写东西,毛笔字写得好的优势,并未完全展现他的文学才能和成就,但当地村民对他知青年代的生活留有深刻印象,并且将这种根深蒂固的记忆和天井茶场联系在一起,“天井茶场”构成了想象韩少功知青生活的固定场域,以致遮蔽掉了他更为丰富和全面的知青生活。但从《长岭记》可以看出,韩少功干过的活非常多,绝不仅仅是人们印象中的茶叶种植。从这个角度而言,1972年3月到1974年12月的日常生活细节,对补充韩少功知青岁月的具体情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长岭记》的价值由此进一步凸显。
二、写作的尝试
除了还原日常生活的基本脉络,《长岭记》同样还原了韩少功作为一个作家知青年代的阅读、思考及创作历程的基本情况。从阅读情况看,韩少功具有那个年代青年的共同特点,喜欢政治类书籍,诸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新阶级》,但同时,他也阅读一些传统的经典作品,在1972年10月10日,他勉励自己背完《岳阳楼记》,“打算从今天起,向黄新心看齐,挑五十篇古文背下来,打一点底子。”自然,那个年代的作品《艳阳天》和连环画《山乡巨变》(1972年12月21日)也构成了他阅读的关注点。“读(浩然的)《艳阳天》,闹粮一场写得高潮迭起,好看!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一样,作者也是乡土语言高手。贺牛带来的一套《山乡巨变》连环画也让人百看不厌,画得好。画家贺友直,据说是他爸的朋友,又是本家人。”由此可以判断,韩少功的阅读视域并未被框定在一个单一范围内,尽管因为特殊的时代氛围,他会更多地接触到政治色彩浓厚的书籍,但他也已认识到中国传统经典的价值,并将此视为“打一点底子”。需要留意的是,在阅读这些作品的同时,韩少功已经开始阅读《契诃夫的戏剧创作》,并深有感触,“契诃夫多次强调剧本的‘潜流’,展开来,可能包括情绪、生活、世界观等所有一切,很多没说出来的东西”。这种广泛的阅读向度,也暗示了韩少功创作资源的多样性,为后来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的精神资源、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中国革命实践的左翼资源等多重资源的萌芽奠定了基础。
与阅读相对应的,是韩少功此时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这从他和二姐韩刚的交往中可以看出。1972年5月17日,韩少功回长沙,“见(俞)巴立、二姐(韩刚)、(孙)二毛,姚(国庆)宝、喻红等。大家讨论《实践论》,议论阿连德,分手前由巴立倡议,轻声合唱《国际歌》”。也正是这一次回家,韩少功讨论了什么是“社会帝国主义”?几天后,他从长沙回到下放地,在1972年5月21日这一天,又同义妹子争论,“世上有没有鬼?”韩少功从现实出发,以三个问题,逻辑性较强地进行了回应,被当地人说成“你们知青只是‘火焰’高,‘火头子’高,因此就看不见鬼了。”“火焰”一词由此进入韩少功的视域。1972年8月5日,给刘(杰英)寄信和书,主要讨论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我强调兼听则明,不要简单地用信条指导行动,要用事实说话,根据实情办事。”1972年9月11日,接二姐信,讨论“工人阶级算不上‘精神贵族’?”韩少功在回信中,显示了成熟理智的一面,“我回信提出:一、‘精神贵族’的说法可能不妥。工人确实有既得利益,有户口、国家粮等,依附于国家体制,但他们也是劳动者,同官僚主义阶级有天然冲突。二、国家也有合理性的一面,可能无更好的组织形态可以取代。无政府主义是空想。马克思批‘国家’,应该是指资产阶级国家。”这些讨论的问题,极其形象地还原了韩少功知青年代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也还原了他关注的兴趣点和对现实的关注热情。和日常生活相对应,这种对讨论问题的记载,同样有助于我们今天回到他的思想和思维现场,回到他当时的精神世界。
事实上,除了阅读和讨论问题,韩少功在下放期间即已开始写作。他妻子梁预立眼中的第一篇习作《路》,韩少功在1972年5月2日有明确记载:
花了一天时间,第一篇小说《路》大功告成,兴奋不已。小克说,元贵这个人物很有味。印象深的细节,是他家吃红锅子菜(无油的),灶台上挂一块肉皮,炒菜前拿来在锅里划两圈,就算是下油,因此那一块肉皮可挂上个把月。他去供销社买火柴,买盐,买布,也要讨价还价的。其实兆矮子就是这样的人。
小克说,正面人物还立不起来。可生活中,哪有他说的那种高大形象?哪有那些惊心动魄的感人故事?但小克认为,应该是我们的观察不到家,是我们的世界观还改造得不够。这话说得我不服也得服。
除此以外,韩少功还曾模仿当年流行的政治抒情诗,“写完《十月的旗》,也来一回阶梯体,178行”(1972年 7 月 13 日);“写船工,写到鸡叫,也不觉得累”(1972年9月10日);也提到投完稿后的退稿经历,“先后收到退稿信两封。老蓝写的样板戏创作经验,一二三,大道理,好是好,但不解近渴。只是抄文件三大页,也费他心了”(1972年8月6日)。与自发的写作一起萌发的,是韩少功自觉对艺术的思考,在1972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韩少功提到他写了一篇和守林员有关的小说,虽然没有留下小说的名字,但留下了他对小说文体的宝贵思考,“什么样的小说才能成功?什么样的人物才算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共产主义新人形象?《戏剧及电影的技巧》一书说,戏剧是一种‘危机’的艺术,又说戏剧其实都是从最后一幕写起,意思是先要设计高潮,再在前面铺垫。”当然,如果我们将日记也当作创作,韩少功下放期间的日记,都可算得上自觉的创作,尽管根据他的自述,写日记是应一位老师的要求得到认可后所养成的习惯,但韩少功在很年轻的时候,显然就已意识到日记对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日记还是有必要写下去。一是训练语文,把笔头子写活;二是留下记忆,弥补脑记的不足。有些东西,自己以为忘不了,其实很快就忘了,只有日记才可长久保存下来,至少可保存一些线索”。现在看来,当年的日记,现在的《长岭记》,确确实实现了“保存一些线索”的重要功能,至少通过这些线索,在四十多年后,我们能轻易地勾勒出韩少功知青期间的创作、思考路径。
三、知青的命运变迁
韩少功1968年12月落户到湖南汨罗时,和他同时下乡的有“100多位知青(以长沙第七中学的学生为主)”,作为坚守到最后的知青,韩少功亲眼目睹了知青的日常生活和命运变迁,作为见证者,《长岭记》恰好提供了宝贵记录。尽管户口已经落到农村,从现实身份而言,知青算得上农村人,但因为是政治的潮汐,将这群城市孩子送到乡间,对他们而言,如何处理乡村和城市的关系,如何融入农村的生活,始终是一个现实的挑战和问题。尽管韩少功能较好地融入乡间生活,但他始终关注同伴的生存境况和命运变迁,这些内容构成了他日记的重要部分,从《长岭记》提供的信息看,知青的境况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岗位在乡间的变动;其二,以各种方式返城、回城;其三,在当地结婚生子。
韩少功是1972年3月从天井茶场转队到长岭大队的,《长岭记》因此构成了一段相对独立的记载。这其中暗含的一个转折,恰恰来自韩少功岗位的变动,在天井茶场,他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在三年茶场生活中,韩少功面对的是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和清苦的饮食。从日出到日落,一天十几个小时连续不断地干活,开荒垦殖、挖沟挑土”。以韩少功自己的话说,这段岁月是“连钢铁都在迅速消融的一段岁月,但皮肉比钢铁更经久耐用。耙头挖伤的,锄头扎伤的,茅草割伤的,石片划伤的,毒虫咬伤的……每个人的腿上都有各种血色,老伤叠上新伤”。而1972年转到长岭大队后,其主要任务是“带动那里的农村文艺宣传活动,使之成为地、县两级的基层文化工作典型。”也许因为自己工作的变动,韩少功从1972年开始,在日记中记载了更多同伴的工作变动,诸如陆莉莉被调去学校教书(1972年3月21日)、志宝也去学校当民办老师,(大部队)又空出一张床(1973年2月13日),当然还有她(指梁预立,韩少功在长岭大队认识的知青,后来恋爱结婚)也被派到学校当老师。对体力劳动繁重的知青而言,当老师算得上一个解脱,“我鼓励她(去当老师)。去就去,怕什么呢?记全劳力的工分,是个好差事。”
当然,知青内部岗位的调整,只是局部减轻了体力劳动的程度,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身份和出路问题。从1971年开始,国家政策有所调整。1971年2月19日,全国计划会议结束,“会议确定1971年计划招收固定工144—155万人。招工对象包括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知青。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知青群体产生分化。”这种大环境的变化,为知青回城提供了政策保障,也导致了知青群体内部的真正瓦解。在韩少功日记中,记载了不少知青的回城情况:沈白薇撤退回城(1972年3月23日),“沈瓜皮(沈白薇)不安心,说一声对不起,终于打背包走了。她说这里电也没有,就三两盏油灯,晚上打得鬼死,太吓人。她那一天失足,差一点掉进厕所粪坑,更坚定了撤退的决心”。为了回城,知青们想尽各种办法,在1972年10月22日的记载中,韩少功来回步行八十里,到智峰公社去寻访同伴,发现“那里的知青点也冷落了,很多人也在办病退、困退、各自找回城的门路。据说有的吃麻黄素,在测血压时,佯坐实蹲,全身绷紧用力,可憋出血压上升。还有的,尿检时夹带调包,也能混到一个假证明。再不行,有人就狠狠心,折断自己一两根指头,反正那也不妨碍吃饭。”他原本想和往常一样,和同伴去讨论文学,但看到的场景却是,“他们的猪都快喂成‘野猪’了,凶得很,要咬人,动不动就成了跨‘栏’冠军,跑到山上去了。肯定是饿成了这样。”而和同伴见面后,“才发现已说不起来,大家有点无精打采。”更荒谬的是,当年知青面对地震的强烈愿望就是,“要震,最好就大震,第一要震掉公安局,第二要震掉知青办,震得户口都没有了,大家就可以回城了”。1972年12月28日,韩少功送走了伟伢子,“阴雨天,挑行李送伟伢子到(公社)茶场,赶明早的班车。他终于如愿以偿,被株洲县文工团点名招走,得抢在年底报到”。因为是年尾的缘故,距离韩少功20岁生日只有两天,这次送别对他的情感冲击特别强,“深夜回来,寒风刺骨,油灯飘忽,窗子的塑料膜哗哗响,孤单感油然而生。再也不会有人去后山吊嗓子了,再也不会有‘我爱大草原——’那种美声抒情,气得大家撑着锄头,在一大片刨不完的野草前欲哭无泪”。这种状况持续一年以后,到1973年4月17日,“放学之后,整个学校已空荡荡。只剩下我和黄伟民两人”,到9月6日,知青点“已溃不成军”,甚至连排演一台节目都无法完成,“小潘从县里来,代表文化馆领导,又要求排演一台节目,配合十大的宣传。但伟伢子、豆豉等都走了,志宝也回城跑病退去了,锣齐鼓不齐”。当然,那些回城的知青,同样处于挣扎和自寻出路中,韩少功1974年3月30日提到,肖鹏夫,下放江永的老知青,病退回城当了泥瓦工,其实和乡村的生活并无太大差异;1974年11月8日,回城知青虾子(鲍晓明)跑供销,路过天井,和韩少功住了一晚,在招工无望后,开始搞了一个社队企业,做化工产品,倒是让人看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至于知青出路的第三种情况,在当地结婚生子,并不多见,在《长岭记》中仅仅记载了一次,1972年9月10日,“到(天井)中学,祝贺范菊华当妈妈,全公社第二个‘小知青’诞生了。”从韩少功对知青命运变迁的关注来看,尽管他对乡下的生活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但从个人而言,内心也一直处于煎熬和挣扎之中,对个人命运的思考事实上成为他知青生活的内在线索。
四、个人命运的变迁
因为日记的遗失,《长岭记》并未将韩少功知青岁月的全貌记录下来,从1972—1974年提供的信息看,伴随对其他知青命运的关注,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人生和出路,在记录他人命运变迁的同时,也同时记下了自己的命运变迁。
1972年是韩少功极为挣扎、也极为忧心的一年,也许是知青群体的分化,引起了他强烈的情绪波动,在沈白薇调走后的第二天,韩少功在1972年3月25日的日记里,以热血般的自信表达了真实的担忧,“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生活是浑浊的激流,我们是逆流而上的水手。不要依恋过去,也不要空想未来。未来就在你的脚下的每一步!”确实,这段话在青春的激情里,貌似更多的是给自己鼓励,实际上难掩真正的落寞。随着知青队伍的瓦解和变化,一切都不一样了,1972年4月1日,韩少功回到茶场后,发现当下的情形和三年前初来时,形成了鲜明对比,情绪上的波动可想而知,“一直阴雨,心情也沉沉的。回到(公社)茶场,发现已有陌生感。本地农民换了不少新面孔。新来的汨罗知青年龄小,也不认识我们老一辈”。“想当初大家刚来时,恍惚就在昨天,大雪纷飞,天地白茫茫,知青们赖在被窝里不起床,只是一个劲地唱歌。俄国的、朝鲜的、蒙古的唱了个遍,还隔着墙互相拉歌。那样的欢乐日子一去不返。眼下不再有小提琴和口琴的声音,更没有夜深人静之时,杠铃重重砸在地上的咣当巨响。”农村环境固然美好,“满天星光,一片蛙鸣,几乎无声的小溪流水。如此良辰美景有何用”(1972年4月16日)?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一直企图通过精神的力量来化解肉体上的煎熬,“插完秧,这几天车水,车水,车水……生活就是顶住、扛住、咬住不放!劳动固然可恶和可畏,却能使人思想开朗而不空虚、意志坚定而不萎靡、身体强健而不虚弱……正如阿·托尔斯泰所言,一个强大的人,必须‘在清水里洗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在盐水里腌三次’”(1972年8月8日)。可以说,1972年,韩少功面对现实,总是试图通过理想主义的牵引和自我磨砺的顽强意志来对抗具体生活的挑战,由此也可以感知到他当年内心的困惑和挣扎。
到1973年,韩少功的命运仿佛出现了转机,5月15日,他得到和高考相关的消息,“听报上说,大学要恢复招生了,采用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录取方式。新心劝我还是回公社争取机会为好,他可以帮我找课本,复习资料”。接下来的时间,韩少功开始复习功课,准备高考,“自我感觉还不错,但也得做面对最坏结果的准备”(1973年6月28日),但事情并没有按预想中的发展,1973年8月4日,他去公社文(教)办打探消息,“看来果真如新心信中说的,我们肯定都是家庭政审不过关,‘高考未遂’,白忙了。”
从1968年年初萌生“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奉献青春”的热望,到1968年年底落户汨罗成为知青,经过天井茶场三年的劳作和长岭大队三年的历练,尽管相比其他知青,韩少功更能坚守理想主义的信念,但直面现实,面对曾经战友的溃散,韩少功对未来的迷茫也变得真实而无从掩饰。1974年末,韩少功回长沙,和母亲有过一次直接的对话:
平时离家出门,妈妈从不远送。但昨天妈妈执意要送,说赶火车还来得及,于是在越来越暗的黄昏里,陪我走过一个公交站,又走过一个公交站。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就说:“我不会怪爸爸的”。
她没说话。
我又说:“我现在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
她看我一眼,还是没说话,大概好多话不知该如何说。
在韩少功后来的写作中,他几乎很少涉及个人隐私,这次日记中透露出的和母亲的对话,可以窥视到韩少功内心的担忧和倔强。
值得一提的是,在展现个人命运变迁的同时,《长岭记》隐藏了另一条重要的线索,尽管前面提到,在韩少功的创作中,他很少涉及私人情感,但日记作为一种真实、在场性强的文体,往往会对私人感情有着原初的记录,《长岭记》不经意中展现了他知青年代收获的宝贵恋情。韩少功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到恋人梁预立是1972年4月2日,离他从天井茶场转到长岭大队不到两周,在一次劳作中,韩少功记录,“天转晴。挖茶坑。每人四十个洞的任务,长、宽、深都得有一尺五。这全看运气,碰上松土,半天干完,还收早工。碰上铁硬的‘巨咬子土’,就喊天吧,耙头下去常常就会弹跳回来。”正是在这次挖茶坑的劳动中,韩少功首次提到了梁预立,“志宝帮豆豉(两人好像已分手)。我帮她”。1972年5月13日,19岁的韩少功确认了青春恋情,和任何一个青春期的男孩一样,他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恋爱的心跳,“这就是爱情吧?这就是爱情吗?也就是看一眼,心里莫名地跳。”在同一天,韩少功记录了一件事,和知青陆莉莉、志宝一样,“她”获得了一个当民办教师的机会,“今天,大老胡一来就大喊,说公社来电话了,决定让‘鸭婆子’顶替‘豆豉’,去当民办老师,而且明天就得去,不能拖延!”从日记内容看,两人的交往极为克制,梁预立去当老师后,约定和韩少功一个星期只能见一次,“她又对我提要求,说她真去了,往后肯定忙,希望我少去找她。这个我同意,向毛主席保证,顶多一周一次。”同时,梁预立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经常给韩少功提供学习上的方便和资料,1972年7月24日,韩少功记录,“她下午送来竹垫和薄被子、一瓶墨水、三本《译文》杂志。”经过一年多的交往,目睹同伴们通过各种途径离开乡村,韩少功和梁预立几乎成为最后的留守者,两人在孤寂的乡间成了彼此最重要的精神支撑。1974年8月5日,在志宝成功病退、小克获推荐去岳阳师专念书后,韩少功成了大队部“最后一个知青”,此种情况下,大队觉得往常的摊派方式已失去意义,让韩少功出自由工,而为了照顾“她”,他选择了靠近学校的地方,两人开始了更多的日常交往,也真正触及了最为普通的琐碎生活,尽管也有平静中的温暖,但内心依然忐忑不安,“我白天打禾,晚上住林老师那间房,就在她隔壁,给她壮壮胆。每次收工回来,我们一起去地上摘菜,然后她淘米,我打水,她炒菜,我烧火,她洗碗,我扫地,她洗衣,我泼水降温……俨然‘老夫老妻’的日子,过出了小温暖,但也让人略感不安——就这样过下去吗?永远就在这破山冲里过下去了?”
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致梁预立家里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她爸做了最坏的打算,说万一她没机会回城了,以家里的全部积蓄,每个月五元或十元,也能补贴她二三十年。”直到1974年12月28日,事情才出现转机,“事情来得很突然。新心(被)招工了。去长沙第三医院报到。几乎是同一时刻,她也撞上大运,被长沙二轻局医药公司录用,手续很快办完,连(学校的)欢送会都来不及开”。
两天后,1974年12月30日,韩少功获得消息,29号那天“我也被县商业局录用了——其实是县里怕几个知青笔杆子都被挖走,就让文化馆借了商业局一个指标,赶紧把我截住”。到12月底,韩少功顺利到县文化馆报到,暂住在客房里,结束了六年的知青生活。三年后,韩少功参加高考,离开汨罗文化馆,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征程。《长岭记》以细致的记录,为读者了解他知青经历中1972年到1974年的具体生活,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注释:
[1][2][4][5][6][7][9][10][11][12][14][15][16][17][18][19][25][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6][47][48][49][50][51][52][53][54][55]韩少功:《长岭记》,《芙蓉》,2021年第2期。
[3]韩少功下放的知青点有一大片茶场,叫天井茶场,这片茶场留存至今,我上高中时,每次从湖南汨罗三江镇坐县际班车去往县城,必然经过这片茶场,在上小学以前就被告知,天井茶场是韩少功下放的地方。
[8]“你看见的鬼穿衣没有?你见的鬼多不多?那些鬼只讲本地话吗?”
[13]梁预立在《诱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60页)的《跋》中提到:“我记得,又送走一批伙伴招工回城后,他写了第一篇小说习作《路》,就是在队长家的堂屋里写成的。那时他在我们知识青年中算是能写点什么的了,出黑板报,或是为文艺宣传队编点什么说唱剧、对口词、三句半等等。他不满足,就写小说。《路》的第一个读者是我,好像也就是唯一的读者。那是写乡下修筑一条机耕路的故事,他自觉写得很幼稚,也就没拿给别人看。”
[20][22][24][26][45]武新军,王松锋:《韩少功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第15页,第17页,第15页,第11页。
[21]韩少功:《长岭记》,《芙蓉》,2021年第 2期。1974年12月29日记载,“没错,我已成为(长岭)最后一个知青了,可能就是同命运顶上了。但我不会说孤单,不会说痛苦,不会说绝望,不会说我想哭。我横下一条心决不!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这里就是罗得岛,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23]韩少功:《山居心情》,《天涯》,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