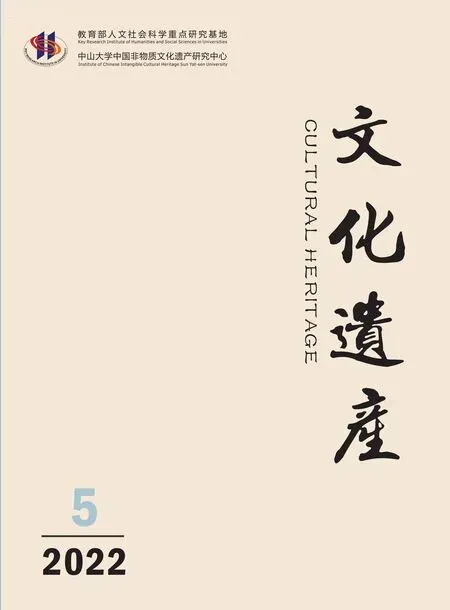《琵琶记》版本研究述略*
2022-11-05罗欢
罗 欢
高则诚《琵琶记》问世于元末,以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获得人们喜爱,不仅在舞台上不断搬演,长盛不衰,而且在明代被大量刊刻,广为流传。或出于舞台演出的需要,或出于案头阅读的需要,其文本在刊刻时被或多或少的改动,故而产生了系统不同、面貌各异的版本。
现存《琵琶记》明代版本,可分为四类:一是全本流传的版本,二是戏曲选集中的折子戏和曲子,三是保存在曲谱中的佚曲,四是前人提及但已亡佚的版本。这些版本又可分为接近作者原貌的古本系统和受过明人较大修订的通行本系统。
明刊《琵琶记》版本的研究,对于中国古典戏曲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可为《琵琶记》版本流变梳理出清晰的脉络;其次是有助于推断《琵琶记》的元代旧貌;再者可以从特定的视角审视中国戏曲发展的历程。
进入20世纪后,学者们在《琵琶记》版本的搜集、影印、校点、注释与研究等方面付出了艰辛劳动,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郑振铎、钱南扬等先生对《琵琶记》的版本研究做了不少奠基性的工作,黄仕忠、俞为民、孙崇涛等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琵琶记》版本研究方面贡献尤多。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对《琵琶记》版本的研究学术史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加评述,以期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
《琵琶记》产生于元末,流行于明清两代,在此过程中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进而成为经典剧目。不断的演出和刊刻过程中,《琵琶记》产生了数目众多的演出本、案头阅读本。据研究者统计,《琵琶记》现存版本中以全本流传的有四十余种。对这些本子的认识乃是洞察《琵琶记》流变和接受的一个重要方面,可借此探究中国戏曲发展的历程以及戏曲观念之变迁。
明嘉靖年间,河间长君最早注意到《琵琶记》有多种本子,他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所作《琵琶记序》中提到当时所见《琵琶记》本子就有四十余种之多,提到名字的有写本、京本、吴本、浙本、徽本、闽本等。
到了明万历年间,《琵琶记》的版本数量就更多了,玩虎轩主人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琵琶记序》中提到的版本达七十余种。“不断的演出、刊刻,就会有不断的修正、补充,把自己的认识、审美评价、时代思想贯注入作品中。”人们利用当时所见的本子,作了或校订、或删改、或评点的处理。如万历间凌濛初刻《琵琶记》(简称“凌刻本”),在《凡例》中提到《荆钗》《拜月》在当时被大加改窜的情形之后,称独此曲偶获臞仙藏本,据以校订,“亟以公诸人,毫发毕遵,有疑必阕,以见恪守”,着力于寻求“原貌”;在校订中提到有“元本”“古本”“时本”“昆本”“徽本”等。而明末槃薖硕人的《词坛清玩〈伯皆(喈)定本〉》,对此剧作了新修订,还在批注中对当时流行的版本作了说明,所提及的版本,有“元本”“古本”“俗本”“近本”“吴本”“京本”“徽本”“浙本”“闽本”等。明末清初钮少雅在《九宫正始》的批注中,也提及“古本”“时本”“昆山顾本”“昆山俞本”“坊本”等,并且注意到昆本有顾、俞两家。
清初陆贻典在所抄录的《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简称“陆抄本”)后,提及以往“刻者无虑千百家,几于一本一稿”。这些版本的差异所具有的戏曲史价值,并不在于确认何者为“原貌”,而在于可以通过这些变动来窥知戏曲的接受历程。
二
兹将学界关注的问题评述如下:
(一)高则诚《琵琶记》的原貌问题
《琵琶记》的版本问题中,研究者集中关注的是其原貌问题。
清黄丕烈士礼居藏有“元刻巾箱本”,即《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简称“巾箱本”),黄氏在跋中称此本为“元刻”。20世纪初,冒广生在《戏言》、吴梅在《霜崖曲跋》中都提到这部“元刻巾箱本”,刘世珩将这个版本与通行的明刊本相比较,撰成《琵琶记剳记》。其后武进董康诵芬室将巾箱本用珂罗版影印出版,并以“元本”为号召。赵景深、青木正儿等也认为巾箱本比较接近元代旧貌。
董康影印巾箱本附有精美的插图。因未加说明,使人误以为原刻本即有此图。郑振铎在获得凌刻本后,发现董氏影印本的插图是据凌刻本移录;经过他的比勘,认定巾箱本并非“元本”,而是明代嘉靖间的刻本。他在《重刊河间长君校本琵琶记》一文中说:“武进某氏影印之琵琶记,号为元刊本,与《荆钗》为双璧,均传奇最古刊本。原本曾藏士礼居,后归暖红室。今则在适园。然实亦嘉靖间刊本,非元本也。”
1954年,郑先生编纂出版《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收入陆抄本。据陆抄本所附“旧题校本琵琶记后”和“手录元本琵琶记题后”,其底本出自钱遵王所藏明刊本,与巾箱本属同一系统。黄仕忠据陆抄本上卷末所记“元本”的刻工姓名,考证其底本当为弘治七年(1505)所刻;即陆抄本之底本是《琵琶记》各传本之中能够考知刻印时限的最早刊本。
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圣劳伦佐图书馆藏《风月锦囊》,其中收录了《新刊摘汇传奇妙戏式全家锦囊伯皆(喈)》(简称“锦囊本”)。《风月锦囊》为重刊于明嘉靖癸丑年(1553)的一部戏曲选集,锦囊本为《琵琶记》今存最早的刻本;以渊源论,则仅晚于陆抄本之底本,故其价值尤引人注目。
1958年,广东揭阳出土嘉靖抄本《蔡伯皆(喈)》(简称“揭阳出土本”),刘念兹将揭阳出土本与陆抄本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等早期南戏进行比对,认为其与陆抄本具备说唱并重的艺术特色,是“继陆抄‘元本’和巾箱本之后的最新发现的第三种‘元本’《琵琶记》”;不仅如此,“从文字的正误方面来看,嘉靖写本比陆抄‘元本’更近原著些,更优越些,也更准确些”。黄仕忠则通过更为详细的考证,认为揭阳出土本的生本从内容上说比总本更接近陆抄本,但也留有曾据通行本系统传本订正字句的痕迹。
此外,钱南扬注意到《九宫正始》从元人曲谱里引用了《琵琶记》的曲文,称之为“元谱本”;彭飞、朱建明则从元谱的出现时间,否定高明(则诚)的著作权。但经黄仕忠考证,所谓的“元谱本”实际上是产生于明初接近《琵琶记》原貌的古本系统的本子。
《琵琶记》迄今尚未发现元代的本子。而元谱本、陆抄本底本、巾箱本、锦囊本、揭阳出土本、凌刻本等,也都是明代的本子,所以“元本”目前是不存在的。其实,“所谓的‘元本’,有二种意义。一是指元刻本,一是指‘原本’”。“元”“原”音同义通。现存《琵琶记》版本或其底本都是明代刊刻的,所以取“原本”之意比较合理。
总的来说,学界目前公认陆抄本最接近《琵琶记》原貌,与巾箱本、锦囊本、揭阳出土本、凌刻本同属古本系统,改动相对较少,通行本系统的版本则改动较多。
(二)版本编目与著录
20世纪前半叶,许多学者致力于搜集《琵琶记》版本,其中尤以郑振铎贡献为多。他购藏有万历陈大来继志斋刊本《重校琵琶记》(简称“继志斋本”)、明末刊本《新刻魏仲雪先生评点琵琶记》(简称“魏仲雪评本”),明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简称“李卓吾评本”)、凌刻本等。周越然则收藏有李卓吾评本、凌刻本、《六十种曲》本等,其《〈琵琶记〉之版本》(1933)一文有详细介绍。
傅惜华、庄一拂、侯百朋、李修生、金宁芬、张棣华等学者都对《琵琶记》作过著录。张棣华《善本剧曲经眼录》著录了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组所收明清《琵琶记》刻本,对其版式特征、主要内容等作了记录;侯百朋《〈琵琶记〉版本知见录》,共著录39种版本,但其中涉及的日本藏本,藏处多误;黄仕忠在《〈琵琶记〉研究》一书所附《主要参考书目》里,列有明清重要版本25种,均经目验;金英淑《〈琵琶记〉版本流变研究》分四类列明清42种全本、29种折子戏和曲子、6种南曲曲谱佚曲、4种有记载但失传的版本,由于一部分版本未寓目原书,故存有一种多录等讹误。
日本的《琵琶记》版本,黄仕忠有《日本所见〈琵琶记〉版本叙录》,共著录32种,其中有1种为西村天囚译本。此后,其所著《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著录37种,即增添了5种;所著《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对其中4种作了解题。
以上编目或著录多为专书中所附内容,为《琵琶记》版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线索。
(三)版本的重印、影印和校注
影印、重印方面,董康诵芬室影印了巾箱本;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奇》第二种即为《琵琶记》,其中收《新安汪氏玩虎轩绘镌琵琶记全图》《陈眉公先生批评琵琶记》(简称“陈眉公评本”)《陈眉公先生琵琶记释义》,并附梅溪钓徒(刘世珩)的《琵琶记剳记》;罗氏蟫隐庐影印了凌刻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了陆抄本、李卓吾评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影印出版《明本潮州戏文五种》,收入揭阳出土本。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影印收入锦囊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影印出版玩虎轩本《琵琶记》(简称“玩虎轩本”),孙崇涛主编《古本琵琶记汇编》影印收入锦囊本、揭阳出土本、巾箱本、凌刻本、陆抄本五种并附有校录。
海外藏《琵琶记》版本的搜集出版,主要见黄仕忠《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一辑)》,收入《袁了凡先生释义〈琵琶记〉》《重校〈琵琶记〉附重校〈北西厢记〉》《硃订〈琵琶记〉》。
标点整理工作,20世纪30年代起学者即已开始。如何铭标点《琵琶记》、胡协寅校勘《琵琶记》、朱益明标点《琵琶记》。这些整理本多以明代评本为底本,采取新式标点,保留原有评语。
在诸多校注本中,学界多推钱南扬先生校注本为最善。他以陆抄本为底本,参照巾箱本、李卓吾评本、陈眉公评本以及凌刻本,校注出版《琵琶记》,后来又详加注释,撰成《元本琵琶记校注》。此外还有王季思先生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以《六十种曲》本为底本,以“李卓吾评本和陈眉公评本以及钱南扬根据元刊本校注的本子参校”;黄仕忠有《琵琶记导读》,亦以陆抄本为底本作校勘,详加注释,每出附评,书前有长篇“导读”。
(四)版本的介绍与考证
赵景深、钱南扬、傅惜华、戴不凡、张棣华、郑骞、罗锦堂、刘念兹、金宁芬、孙崇涛、俞为民、黄仕忠等人均对《琵琶记》的版本有过研讨。
罗锦堂在《大陆杂志》上连续发表了《风月锦囊(上、下):流落于西班牙文献之一》以及《全家锦囊琵琶记——流落于西班牙文献之二》等几篇介绍《风月锦囊》的文章,其中就包括锦囊本,由此引起了学界对《风月锦囊》的极高关注。
1958年揭阳出土本面世后,赵景深、刘念兹等人对其作了介绍和评价。
俞为民《南戏〈琵琶记〉的版本流变及其主题考论》,系统介绍了《琵琶记》版本的整体状况,将《琵琶记》的版本分为四种类型。黄仕忠《〈琵琶记〉研究》,在“版本篇”里初次梳理清楚《琵琶记》的版本系统,并且对版本的衍生情况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此后学者对于版本的讨论,大多是在该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
韩国学者金英淑的《〈琵琶记〉版本流变研究》,在黄仕忠和俞为民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再作深化,也分四类列明清各种版本,将之分为古本、通行本、选本三个系统,选取古本系统和通行本系统中有代表性的版本进行分析和考察,分专题讨论《琵琶记》版本流变情况。但此书所见版本有限,对于众多的通行本系统万历时期传本缺少深入研究,且没有对毛声山评本做出评述,使清代以降《琵琶记》流传的情况,缺失了一个重要环节,且间或还有考订结论的失当。
(五)异文与评点研究
朱万曙的《明代戏曲评点研究》参照侯百朋的介绍和《中国善本书目·集部》的著录,统计了明代《琵琶记》的评点本,将之分为李卓吾评本、凌濛初考评本、徐奋鹏改评本三个系统,列表对所涉四十出评语和总评对照分析,认为李卓吾评本对陈眉公评本、魏仲雪评本和《三先生合评元本琵琶记》(简称“三先生合评本”)都产生了影响,各评本中的批语有着重要的价值,可借此了解明代批评家对这部作品的接受心态;而徐奋鹏改评本对原作主题的集中和突出、对人物形象和性格特点的加工、对全剧结构的紧缩以及在批语中所表达的创作思想,都值得充分肯定。
童雯霞的《〈琵琶记〉丛考》中有专门一节《孙鑛评本〈硃订琵琶记〉研究》,认为孙鑛评本是明天启年后书商之伪托,其评语是杂糅李卓吾评本、陈眉公评本而成,其拼凑手法有张冠李戴、移花接木、错误迭出等,在李卓吾评本、陈眉公评本俱出评的情况下,多从李卓吾评本。
曹竞华的《明刊〈琵琶记〉评本研究》结合明代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对16种明刊《琵琶记》评本进行了解题,并重点介绍了有代表性的评点本,在勾勒《琵琶记》明代评点史的基础上,将其分为学术型和鉴赏型评点,不仅为了解《琵琶记》在明代的接受情况提供了佐证,也可从中窥见明代戏曲理论的样貌和演进。
结 语
纵观《琵琶记》的版本研究史,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经打开了一个较广阔的空间,使研究者发觉可做、需做的事情更多。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利用。新资料的刊布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有些版本还未知藏处;也有的虽知其藏处但无法轻易获取,如上海图书馆曾藏《重订元本评林点板琵琶记》;还有则是稀见版本有待影印出版。
二是具体版本的进一步研究。相较于《琵琶记》数量众多的版本而言,目前对具体版本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必要,而且有些结论尚需修正和进一步完善。
三是从多个维度对《琵琶记》版本开展研究。随着学术研究视野的进一步开阔,在扎实的文献学研究基础上,从多个维度对《琵琶记》版本开展研究,从而拓展出《琵琶记》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尤为重要。比如通过《琵琶记》不同时期的版本,来探讨当时的戏曲观念、时代风尚和审美意识,还有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戏曲的发展历史,并不单纯是文本创作和舞台表演两者的事情,更要探寻戏曲与政治、阶层、文化以及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如此,戏曲研究可获得更为广阔的新视野,发掘更多的新史料,生发出新的学术生长点。”再如在当下数字化时代,如何将古籍数字化从而建立版本数据库,利用计算机代替人工来进行版本比对,利用大数据来开展研究,就是一个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