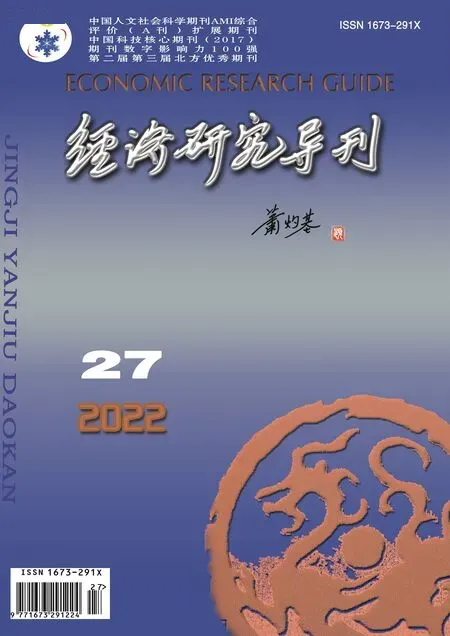数字经济领域互联网平台不兼容行为的竞争法思考
2022-11-05倪佩佩
倪佩佩
(浙江理工大学 法政学院,杭州 310018)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平台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激烈的竞争,一方面给数字经济市场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实现互联网平台的优胜劣汰;另一方面,平台为了能在相关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利用技术手段实施不兼容行为的几率也随之增加。一旦不兼容成为互联网平台竞争的惯用手段,或愈演愈烈成为互联网行业的常态,无疑是互联网发展创新的首要阻碍,彼时,互联网又如何能称之为互“联”网?
频发的互联网不兼容行为,引发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 条(以下简称为“互联网专条”)第二款第三项(以下简称为“恶意不兼容条款”)对恶意不兼容行为的定义:“经营者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恶意对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实施不兼容”的行为。因此,恶意不兼容条款设立之初便将行为的判定标准集中于经营者的主观恶意之上,但这一判断标准是否合理、是否适用于现实案例仍有待考究。
一、互联网不兼容行为的定性分析
互联网不兼容行为本质是一个技术问题,表现在互联网平台的不兼容行为多为封禁、屏蔽链接、二选一等。从技术角度出发,根据诱发原因、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类型化分析,并对现有行为进行梳理分析,互联网不兼容行为的类型主要可分为:平台之间的二选一、不予直链、平台的降维与自我优化、封闭的API 政策。这些不同的类型虽有不同的诱发原因、表现形式,但都是互联网平台实施竞争的技术手段,而技术手段在施于特定目的前并不存在优劣之分。
从不兼容的词源分析,不兼容行为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汇,其中“兼容”一词是指一个产品、系统或组件交换信息和/或实现其所需功能的程度,并同时共享相同的硬件或软件环境,而不兼容则是产品实现其功能但不能共享相同的硬件或软件环境。互联网产品或服务之间的不兼容,主要指不同互联网产品或服务之间发生冲突,以致不能同时使用或者一方对另一方的使用施加了较多限制的情况。从不兼容的技术来源、产生之初来看,互联网不兼容源于技术问题,因此本身是一个中性的行为。
在互联网快速崛起、平台类型数量大爆发的阶段,不同的互联网平台之间因所采用的技术不同,开发阶段未曾发现的技术问题,可能会在运行过程中发现互不兼容的情况。例如,在猎豹浏览器过滤优酷视频广告案中,优酷通过“广告+免费视频”的商业模式支撑其经营,这也是当时视频网站乃至整个互联网内容服务行业采用最多的经营模式。而猎豹根据行业惯例、优化用户体验,默认开启浏览器软件的广告过滤功能,过滤了优酷网的视频广告。优酷“广告+免费视频”是其合法提供的网络服务,猎豹因涉及的经营领域不同,开发指向不同,所以在运行过程中产生互不兼容的情形。法院认为,这一案件中,猎豹并不存在恶意,对于经营者并非恶意造成的软件冲突,不应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案例肯定了互联网不兼容行为的中立性,不兼容本身是平台的技术问题。
不兼容本身中立,却不代表其实施者完全中立。在频发的不兼容案例中可以发现,不兼容易被经营者所利用,成为互联网平台的竞争工具。2010 年3Q 大战、2013 年淘宝关闭从微信跳转至淘宝商品和店铺的通道、2014 年 3B 大战、2020 年微信关闭飞书的 API 接口等事件,反映的都是互联网平台在市场竞争中,为了扩大相关市场份额,利用技术手段实施不兼容行为而进一步实现其商业目的。此时,平台不能再借助技术中立为由,为各自所实施的不兼容行为开脱。
二、互联网不兼容行为的竞争影响
不兼容并非互联网产业的限定行为,在传统产业中也存在不兼容。只是与传统企业相比,互联网平台中的不兼容行为天然的具有更为严重的影响。因为,互联网产业又是一个“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产业,天然的容易造成“赢家通吃”。互联网平台形成固定的用户群、拥有市场影响力后,会对竞争对手产生进入壁垒,不兼容行为的影响则加剧壁垒的形成。
一方面,互联网平台的不兼容行为会损害竞争对手的权益,损害竞争秩序。首先,对经营者而言,追求的是低成本高效率的经营模式,但不兼容会直接导致平台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无法正常稳定地运行,间接提高经营者的运营成本,不利于平台在相应市场中生存发展。互联网平台在察觉到这一影响后,便利用不兼容来打压竞争对手,竞争对手的生存环境恶化,则意味着实施平台获得更多生存空间,有利于其巩固或扩大市场份额,进而形成超级平台。其次,虽然互联网平台是私主体,但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平台已经是一种具有独立的组织架构和自己独特的权力机制的新型市场主体,是市场的组织者与管理者,因此其作为私主体享有服务供给者与市场监督者的双重属性。互联网平台的双重属性使不兼容的影响范围也从竞争对手扩散到市场竞争秩序。最后,互联网平台在相关市场的支配地位可以利用垄断杠杆传导市场力量,即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利用在某一市场的市场力量来提升或享有其在另一个市场的地位,因而不兼容对市场竞争秩序的影响需要“有形的手”来加以约束。
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一旦实施不兼容行为,损害的不仅是竞争对手的利益,还有在其中的用户权益。这部分用户权益可以大致分为平台使用的自由和平台选择的自由。首先,使用平台的自由是指用户在使用互联网平台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时,享有法律、平台服务规则限度内的自由,但不兼容却会对这种使用自由形成限制。具体对互联网平台屏蔽其他经营者链接行为的正当性探讨,可以区分分享链接行为是否由用户自主、自愿发起,还是基于外部因素诱导、误导甚或迫使用户非自愿地分享予以区别考察。如果是基于外部因素诱导或用户非自愿分享,这类链接往往不属于“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便无须讨论不兼容的损害结果;对于用户自愿分享的链接,且该链接合法合规的,则属于用户使用平台的自由。平台单方屏蔽用户分享的外部链接或单方关闭API 接口,是直接针对用户实施的,损害了用户的使用平台的自由。其次,平台选择的自由是指用户在使用互联网时享有选择何款产品的自由,但平台实施不兼容、打压竞争对手,则屏蔽了用户的信息来源,会影响用户的自主选择权。互联网平台实施恶意不兼容对用户造成的是间接抽象的损害,因此很难将其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专设恶意不兼容条款,正是在频发的案件中看到了不兼容给竞争者、竞争秩序和用户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的规制难点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恶意不兼容条款对恶意不兼容行为设置了三个构成因素:经营者的恶意、对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不兼容。在这三项因素中,最为关键的便是经营者的恶意。恶意是经营者的主观意识形态,在互联网平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竞争行为的动机能够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因而成为判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重要考察因素。因此,恶意不兼容条款规制互联网不兼容行为的前提是证明互联网平台具有不正当的竞争动机,表明只有那些恶意的不兼容行为才应规制。
这一判断标准适用到执法司法中,很难利用现有的客观证据来认定经营者的恶意。因为,竞争是市场的应有之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便是通过竞争实现资源流动,从而达到市场效率最优化。经营者利用自身条件为自己创设有利的竞争条件本无可厚非,而竞争同样会诱发经营者为谋取非法利益而采取不正当手段进行竞争。考量平台实施不兼容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时,通常以互联网行业公认的商业道德为标准进行评判,这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商业道德标准并非成文化文件,非固定化的标准不确定性强、证明力弱,在实践中以此证明平台具有不正当目的较为困难。
同时,仅考虑互联网平台是否恶意和行为的表现形式,而不考虑客观的竞争影响,对平台的处罚则如无根之木缺乏事实依据。考虑客观的竞争影响或许不影响行为性质的认定,但可以作为恶意判定过程的影响因素。恶意与非恶意的不兼容行为会造成不同的损害结果,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及实施程度也会形成不同的竞争影响,因此不考虑客观的损害结果、竞争影响,而仅关注平台是否具有恶意,在恶意无法判定时,难道任由严重扰乱竞争秩序的不兼容行为逍遥法外吗?
四、《反垄断法》视野下的规制路径
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都属于竞争法体系,但在具体价值目标上,前者在于规制不正当、违反商业道德的竞争行为,后者在于规制排除竞争、限制竞争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指向不利于自由竞争的方向。分析不兼容的行为表现便能发现这是互联网平台利用自身市场影响力对竞争对手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的竞争行为。
同时,考虑到互联网平台具有“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特性,平台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后,对其他竞争者形成进入壁垒;高用户黏性还会锁定用户群,使用户对其形成高度依赖性;市场影响力较大的还能使其他经营者对其形成交易依赖性。因此,综合考量经营者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竞争状况、经营者控制市场的能力、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等因素,可以认定平台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对应实施的不兼容行为就构成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表现形式多样,通过分析恶意不兼容的行为表现,发现不兼容行为与拒绝交易、差别待遇的行为表现具有更高的相似性。
就不兼容行为而言,互联网平台实施的这种有限制或有条件的兼容与不兼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当前互联网市场发展和竞争过程中被频繁运用的一种商业策略,当平台将这种策略选择性地施加在不同的竞争平台之上,在法律层面往往体现为“拒绝交易行为”。例如在腾讯拒绝与抖音实现兼容互通的案件中,这种不兼容从表面上来看不涉及任何交易关系,但是从互联网行业的整体发展模式来看,腾讯旗下所涉及的市场不仅是微信和QQ 所在的即时通讯市场,还包括短视频等多个市场,可以肯定其与抖音存在竞争关系。其次,两大平台从外在表现上看不存在直接的交易关系,但互联网平台的内在联系千丝万缕,两大平台之间或者旗下其他平台间存在或多或少的利益交换,在抖音开放向微信和QQ 平台分享的前提下,而腾讯拒绝兼容抖音短视频链接,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拒绝交易。
除了拒绝交易之外,平台之间的这种不兼容行为也有可能涉及差别待遇。“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的行为便是差别待遇。表现在互联网不兼容行为之上,平台对相同类型的产品或者服务,依据不同的标准实行差别化的兼容或是不兼容。例如,腾讯对抖音实施不兼容行为,但是却兼容同为短视频平台的微视,而微视正是腾讯旗下产品。腾讯为了支撑自身旗下产品的发展,运用在即时通讯领域的影响力,给抖音和微视设置不同的交易条件,其实质便是一种差别待遇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两者都是保护竞争的法律,只是针对不同程度的损害行为的规制,但在个案中应当认定为垄断行为还是不正当竞争行为,需要结合平台的市场份额、损害结果、平台是否恶意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通常占有市场份额较大、具有强大市场力量的互联网平台,实施的不兼容行为也更容易给其他经营者和市场的竞争秩序带来严重的损害,这种情况适用反垄断法且更为有效,惩罚力度也能与损害结果相匹配。
恶意不兼容条款对不兼容行为的规制,是法律迈入其中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即使有了恶意不兼容条款,也需要结合互联网平台灵活性强的特点,在个案中结合不同的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综合选择。避免现有的法条、条款落入被架空的境地,在恶意不兼容条款的基础上,结合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相关规定,从主观和客观层面、行为构成和损害结果方面,相互联系,准确判定个案性质,最后确定适用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