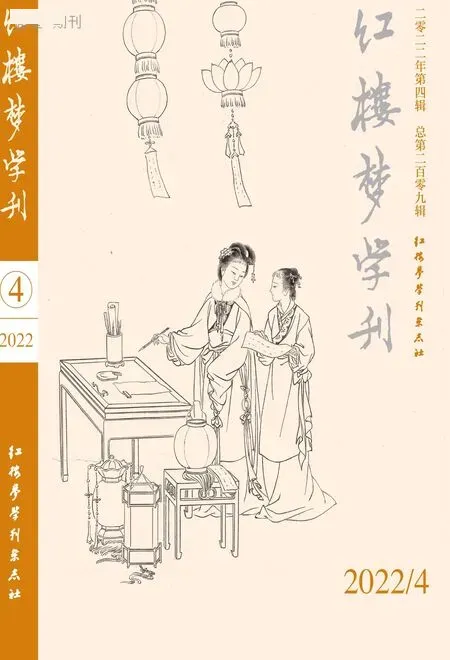一篇不该被遗忘的红学文献
——读俞平伯《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
2022-11-04苗怀明
苗怀明
内容提要:《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是一篇俞平伯早年所写与蔡元培商榷的红学文章,因《俞平伯论红楼梦》《俞平伯全集》及其他论著、论文集皆未收录,知者甚少,成为一篇被遗忘的红学文献。俞平伯写作此文的目的在支持胡适《红楼梦考证》中的观点,反对蔡元培的红学观点及研究方法,对其辩解提出反驳。这是俞平伯早年一篇较为重要的红学论文,也是新红学创建时期的一篇重要文献,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为方便学界同仁研读,将其重新整理刊布。
新红学是在批判旧红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今这已经成为一个学术常识,其标志是胡适与蔡元培围绕红学研究进行的论争。尽管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已有很多,但仍有一些问题未得到解决。比如在蔡胡论争的过程中,俞平伯也写过一篇与蔡元培商榷的文章,其后虽然有一些研究者提到,但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如何,提出了哪些观点,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语焉不详。更为奇怪的是,俞平伯本人对自己的这篇文章似乎也视而不见,在其收录红学文章最全的《俞平伯论红楼梦》一书中未予收录。俞平伯去世后,收录其著述最全的《俞平伯全集》一书也未予收录,此外也未见其他专书或论文集转载或引用过。这篇文章刊发在1922年3月7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专栏上,一百年间,一篇在新红学建立过程中十分重要的红学文章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长期以来,人们了解俞平伯的这篇文章,主要是通过胡适1922年3月13日的日记。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谈到了顾颉刚和俞平伯两人对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意见,其中对顾颉刚的观点较为赞同:“颉刚来书,有一段论《红楼梦》事,甚有理。……颉刚此论最痛快。”并在其后回应蔡元培的文章《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中引用了其中的两个观点。但对俞平伯《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一文则提出了批评意见:“平伯的驳论不很好;中有误点,如云‘宝玉逢魔乃后四十回内的事’(实乃二十五回中事),内中只有一段可取。”
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只有一段可取”,可见胡适对俞平伯的这篇文章是相当不满意的。虽然这只是日记中的话,但以胡适当时与顾颉刚、俞平伯关系之密切,俞平伯对他的意见应该是知道的。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俞平伯后来在自己的文集收录早年的各类文章时,都不收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到底都写了什么?为何让胡适不满意?以下稍作分析。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胡适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中有误点,如云‘宝玉逢魔乃后四十四回内的事’(实乃二十五回中事)”,这句话是针对文章的这一部分而发的:“他又以第二法,因宝玉逢魔而推为允礽,他却不知道宝玉逢魔乃后四十回内的事,不特康熙年间人未曾梦见,即曹雪芹也未尝梦见(因依蔡先生的话,《红楼梦》是康熙年间的书)。蔡先生何得以此来推求呢?”俞平伯此说又是针对蔡元培的这段话而发的:“以宝玉曾逢魔魇而推为允礽,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国柱,用第二法也。”
《红楼梦》第二十五回写贾宝玉、王熙凤被马道婆施法“逢魔魇”,这件事确实不是在后四十回,胡适的批评是对的。俞平伯在写这篇文章之前,1920年1、2月间曾在去英国留学的船上熟读《红楼梦》,并和傅斯年细谈,1921年4—7月间,又和顾颉刚多次通信,讨论红学问题,准备校勘《红楼梦》,也写了《石头记底风格与作者底态度》等文章,按说对《红楼梦》的内容是相当熟悉的,不该犯这种错误,也许他将“宝玉逢魔”理解为贾宝玉失玉之后的疯癫了,这倒是后四十回里的内容。但不管怎么说,商榷文章里出现硬伤,这是大忌,最起码这一部分的反驳是无效的。胡适的不满意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除了这一处问题,文章还写了些什么?是否真如胡适所说的“只有一段可取”呢?
俞平伯的这篇文章是对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一文的商榷,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蔡元培的文章又是对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的回应。蔡元培不认可胡适对自己红学研究是猜笨谜的批评,归纳了自己研究的三种方法,即“品性相类”“轶事有征”“姓名相关”,认为自己的态度是“审慎之至”。随后从四个方面进行反驳,其核心观点如下:一是考证作者、时代、版本固然重要,但考证作品的情节也是有价值的。二是索隐人名“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等作品都是可以这样研究的。三是自己对情节的索隐“有下落者记之,未有者姑阕之”,胡适文章对《红楼梦》人物、情节的考证也只是涉及作品的一部分,并没有解决书中的所有问题。四是根据甄贾宝玉、曹頫经历、作品措辞分寸、许三礼奏参徐乾学等例证说明《红楼梦》并非全写曹家之事。
文章最后重申“《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徐、余、姜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相比《石头记索隐》,蔡元培在第六版的自序中吸收了胡适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认可曹雪芹的作者权,但承认作品经过曹雪芹增删,也承认作品“插入曹家故事”的可能性。
俞平伯此前读过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一书,早在前一年与顾颉刚讨论红学问题时已表达了反对意见:“我想我们比那些红学家高明的地方,不是我们较聪明些,是我们较坦白老实些。他们所以迷了正路底缘故有两种:(1)先存了偏见然后去读《红楼梦》。(如蔡先生自己持民族主义,而谓雪芹亦持之甚挚。其实曹家是汉军旗,而强迫他去排满惜明,真是笑话。)……”
他这篇文章主要针对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的自序而发,其结构与蔡元培一文基本相同,对其观点逐条进行反驳。他首先指出蔡元培归纳的索隐三法存在问题,其得出的结论“都可以算作偶合的事情,不能当作铁证”,这是因为“他自己先有了成见,才能一个一个的比附上去”,并从正面提出研究《红楼梦》的三条途径,即“同时人的旁证”“作者底生平事迹及其性格”和“本书底叙言”。
随后针对蔡元培为自己辩解的四个方面,俞平伯逐一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肯定《红楼梦》的情节具有考证价值,但“考证情节未必定须附会,但《石头记索隐》确是用附会的方法来考证情节的”,随后接连提出几个反问,指出蔡元培对情节考证的认识是错误的,是自相矛盾的。对这一部分,胡适是比较满意的,他所说的“只有一段可取”即是指这一部分,并在日记中将其剪贴保存。
第二,针对蔡元培列举一系列小说作品例证为自己辩护,他认为蔡元培列举的索隐例证就是笨谜,如“非举出铁证,不足服反对者底心,这样的东扯西拉,是没有用的”。
第三,他认为蔡元培的态度虽然比较审慎,但“逐事比附,实在是‘可怜无益费精神’的事”,不过是牵强附会。
第四,针对蔡元培否定《红楼梦》写曹家家事的几个例证,他认为“‘真事隐’不过是改头换面,隐去姓名”,“甄宝玉是虚设以形容贾宝玉的,仿佛画中的背景,并非真是另有一人,甄家与贾家亦并非真是两家”,“曹頫底生平未能考定”,他做曹頫的影子还是有可能的。作者说话没有分寸的情况也有,但这只是书中的一小部分,“当从大体立论,不得以一语之征而概其全体”,至于许三礼奏参徐乾学之文,“蔡先生必须另有证据,方可自圆其说,仅仅东一鳞西一爪的比附,断断不能成为定论”。
对文章结尾蔡元培对《红楼梦》“康熙朝政治小说”的定性,俞平伯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这是“架空之谈”,指出蔡元培“既否认此书是雪芹做的,且又指不出究竟是谁做的”,这是自相矛盾的。他根据作品第一回的相关内容,重申胡适《红楼梦考证》中曹雪芹是作者的观点,认为作品之所以有“增删五次”之语,是因为“遮遮掩掩是中国文人底故态,雪芹亦未能免俗耳”。对蔡元培提出作品“插入曹家故事”的说法,他认为这不合情理:“在一部政治小说上,平空加入自己家内底事,曹雪芹莫非是个精神病者吗?不然,虽妄人也不至如此。”
总的来看,俞平伯写作此文的目的在维护胡适《红楼梦考证》中的观点,不认同蔡元培的红学观点及研究方法,对其辩解提出反驳。如果从辩论的角度来看,该文只是针对蔡元培的观点表达反对意见,同时提出自己的正面见解,基本上是点到为止,并没有进行论证,而且对蔡元培的研究也有一定程度的认可,比如承认其研究“十分审慎”等。这样要说服蔡元培是很难的,大概也是胡适不满意的地方。胡适之所以对顾颉刚的两点反驳意见比较欣赏,主要是因为他提出了新的思路,抓住了蔡元培观点的不合理之处,反驳较为有力。
不管胡适、俞平伯怎么评价这篇文章,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该文是新红学建立过程中的一篇重要文献,这是无可否认的,虽然未能收到《俞平伯论红楼梦》《俞平伯全集》中,但对研究者来说,则不能不注意,任其湮没。
就笔者的理解,该文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这是俞平伯早年一篇较为重要的红学论文,反映了他对《红楼梦》一些问题的认识,如作者、研究方法等,这在同一时期他写的《红楼梦辨》等其他著述中是没有的,通过该文可以较为全面的考察俞平伯的红学观。
值得一提的是,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1921年4月至10月间,俞平伯与顾颉刚书信往来谈论红学,其间俞平伯产生校勘《红楼梦》、创刊《红楼梦》研究刊物等设想。其后随着新学期开学,大家各忙各的事情,这些设想也都搁置下来。直到1922年2月,俞平伯看到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一文,又恢复了对《红楼梦》的兴趣,先是写了商榷文章,随即根据与顾颉刚的书信,写成《红楼梦辨》一书。对此,顾颉刚在该书序言中有明确的介绍:“去年二月,蔡子民先生发表他对于《红楼梦考证》的答辨。最奇怪的,这个答辨竟引不起红学的重兴,反而影响到平伯身上,使得他立刻回复以前的兴致,做成这部书。当时平伯看见了这篇,就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一篇回驳的文字。同时,他又寄我一信,告我一点大概;并希望我和他合做《红楼梦》的辨证,就把当时的通信整理成为一部书,使得社会上对于《红楼梦》可以有正当的了解和想象。我三月中南旋,平伯就于四月中从杭州来看我。我因为自己太忙,而他在去国之前尚有些空闲,劝他独力将这事担任了。他答应我回去后立刻起草,果然他再到苏州时,已经做成一半了。夏初,平伯到美国去,在上海候船,我去送他,那时他的全稿已完成了。”
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红楼梦辨》的序曲,如果不是由写作该文引发的学术兴趣,也许就没有《红楼梦辨》这部专著,最起码出版的时间要推迟,这样其在红学史上的地位可能就不一样。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这篇文章对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
其次,这是新红学建立时期的一篇重要文献。新红学的建立是多位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除了胡适,还有顾颉刚、俞平伯等。顾颉刚主要隐在幕后提供资料、观点,俞平伯则是站在前面摇旗呐喊,这篇文章就是很好的证明,他与蔡元培的论争可以看作是蔡胡红学论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这篇文章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新红学的建立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学术的新变,其中所体现的学术风气是值得后人学习借鉴的。俞平伯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写作这篇文章时,是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以这种身份对校长蔡元培的文章进行批评,而且言语犀利,毫不客气,这是需要学术勇气的。作为被批判方的蔡元培以平常心对待,这在当时无疑具有示范效应,代表着中国现代学术的良好开端。遗憾的是,这种学术精神后来未能得到很好的传承,即便在一个世纪后的当下,这样的论争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俞平伯《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一文刊发于1922年3月7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专栏,署名为“平”,距今已整整一百年,现在颇不容易看到。为方便学界同仁阅读研究,笔者根据报纸原件照片及扫描件进行整理,附录于后。在整理过程中,得到高树伟兄的资料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① 比如孙玉蓉在《俞平伯年谱》(简编)中有如下介绍:“二月,读了蔡孑民发表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一文后,受到触动,又产生了讨论《红楼梦》的兴致。于是,作了《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发表在本年三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署名‘平’。”内容如何,并未介绍。见《俞平伯全集》卷十,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47页。
②④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9、580—581页。
③ 该文刊于《努力周报》第2期(1922年5月14日)。
⑤ 俞平伯《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1922年3月7日《时事新报》学灯专栏。以下所引该文,出处皆同,不再一一出注。
⑥⑦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⑧ 俞平伯1921年7月23日致顾颉刚函,载《俞平伯全集》第五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⑨ 顾颉刚《红楼梦辨》序,载《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65页。
(本文作者:南京大学文学院,邮编:210023)
附录:
俞平伯
蔡孑民先生最近有关于讨论《红楼梦》的文章发表(见二月二十八日《时事新报》学灯栏)。他虽自己做了一种辩解,但使我不能无疑,谨以下列的论议各点,质之读者。
他在第一节引言里,提出他所用以推求的三法,且自以为审慎之至,但依我看来,所谓“品性相类”“轶事有征”“姓名相关”,都可以算作偶合的事情,不能当作铁证。这都因为他自己先有了成见,才能一个一个的比附上去。譬如他说:“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但古来豪放之士甚多,何以陈其年独与史湘云有关?他又以第二法,因宝玉逢魔而推为允礽,他却不知道宝玉逢魔乃后四十回内的事,不特康熙年间人未曾梦见,即曹雪芹也未尝梦见(因依蔡先生的话,《红楼梦》是康熙年间的书)。蔡先生何得以此来推求呢?至于后四十回是高君续作,这证据甚多,这里不赘及了(蔡先生在本文里,亦承认这个)。
他底三法,依我看来,并无一法可以凭依的,所以蔡先生虽然十分审慎,也不免走错了道路。胡适之先生底《红楼梦考证》,虽然所获不多,但所取的路径却极为正当,我并不说胡先生那文的断语,就是定论,但可信的程度,必定比《石头记索隐》要多得几倍。我终认定研究《红楼梦》,只有下列的三个途径,不知比他的三法如何?(1)同时人的旁证,(2)作者底生平事迹及其性格,(3)本书底叙言。如这些不可信,蔡先生底三法,岂不是更不可信了?我以为除掉这三条途径,我们更无从去窥测这书底本意。解释虽是欠圆满,但古人不可起于九原,这纯是无可奈何的事实。
这序底本文共分四节。第一节底大意是说著作底内容有考证底价值,这我极为同意。但我却不懂这一点与所辨论的何干?考证情节底有无价值是一件事,用附会的方法来考证情节是否有价值又是一件事,万不能并为一谈。考证情节未必定须附会,但《石头记索隐》确是用附会的方法来考证情节的。我始终不懂,为什么《红楼梦》底情节定须解成如此支离破碎?又为什么不如此便算不得情节底考证?为什么以《红楼梦》影射人物是考证情节,以《红楼梦》为自传,便不是考证情节?况且托尔斯泰底小说,后人说他是自传,蔡先生便不反对;而对于胡适之底话,便云“不能强我以承认”,则又何说?至于说《离骚》有寓意,但这亦并不与《红楼梦》相干。屈平是如此,曹雪芹并不因屈平如此而他也须如此,这其间无丝毫之因果关系,不成正当的推论。
在第二节文里,他举了许许多多的古人例证来为自己解嘲,而否认笨谜这个雅号。但古人这些事例,安见得便不是笨谜;虽不定是笨,总是可笑而无聊的。难道他以为侯石公影袁子才,纪献唐影年羹尧,是狠高明而有文学上的价值的吗?他说:“自胡先生视之,非皆笨谜乎?”我说:“以我观之,实是笨谜也!”至于胡先生底意思如何,则我却不敢知。他在此节之末又用《儒林外史》来推测《红楼梦》,则与上边引王逸解《离骚》之事,一样的说不过去。他说:“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且用之,安见汉军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我并不是以为做了汉军第一大文豪便不许影射人物,我说的是,在实际上汉军第一大文豪并没有影射人物,若蔡先生以为不然,请问他又有什么证据呢?他非举出铁证,不足服反对者底心,这样的东扯西拉,是没有用的。
第三节,他说明索隐从不知盖阙的例,是他底审慎。这我也承认的。但他这样八十两、二十两的逐事比附,实在是“可怜无益费精神”的事!即使那一百两头有了下落,也依然是“很牵强的附会”。蔡先生又将何以自解?第四节所辩论有好几点。(1)他因真事隐去,故说不得以书中所叙的事为真,我姑且不辩,“真事隐”应如何解释。试问此书第一回所谓“亲见亲闻”“按迹寻踪”应如何说法?怕还可以作“非真”解释吗?若不能作如此解释,则与蔡先生的释“真事隐”,是否有矛盾呢?我底意思,“真事隐”不过是改头换面,隐去姓名,作者所谓“假语村言”“荒唐言”便是。至于关于真事隐的解释底孰是孰非原无定论,我并不想强人以必信啊!
(2)他论甄贾之辨,以为何必有甄贾两个宝玉?《红楼梦》设甄宝玉以形贾宝玉实在是个缺憾,前人如江顺怡君已有论及。但这层意思却并不难猜。作者不过为世俗心中的“真宝玉”写照,而自居于“假宝玉”。其实呢,真是假的,而假反是真的。作者不过借此写胸中底愤慨,并非定以两宝玉影自己一人。他又何屑把如此的俗子来做自己底影!但甄宝玉是虚设以形容贾宝玉的,仿佛画中的背景,并非真是另有一人,甄家与贾家亦并非真是两家。此意见本书第五回中贾宝玉到太虚幻境所看见的对联,有假作真时真亦假之语。
(3)他以曹頫未闻放学差,不足为贾政之影。但曹頫底生平未能考定,他究竟放了学差与否,我们并无从知道,又何尝有证据说明曹頫一生没有放过学差呢?我们所不知道的,应该安于不知道。不能因我底不知道而断言人底不如此。贾政有何不可以做曹頫底影子?
(4)他因作者说话没有分寸,而因此推测不是自述其生平,这实在是冤枉了。综观全书,只有蔡先生所说的两点,是稍为愤激一点的,这正是羯鼓的稀之意,故慷慨斥之不为留余地。至于以外叙述,则多过厚蕴藉之词(如不明明说秦氏是缢死的,而专用暗笔侧笔,便是此意)。我们批评一书当从大体立论,不得以一语之征而概其全体。《红楼梦》是自述的文章,正因为他有蕴藉的风格。
(5)他举许三礼奏参徐乾学之文,以明此书确是指高徐金姜诸人而作的。这也因为他有主观上的偏见,所以方附会得上去。说他是影射果然可以,说他是偶合,又何尝不可。总之,蔡先生必须另有证据,方可自圆其说,仅仅东一鳞西一爪的比附,断断不能成为定论。
(6)全文最使人怀疑的是末一节。他以为《石头记》是康熙朝政治小说,经雪芹增删,而插入曹家故事的,这样看来,他既否认此书是雪芹做的,且又指不出究竟是谁做的。这话如何能说得通。慢说曹雪芹做《红楼梦》,前人已有明说,他岂能一齐抹倒。且抹倒之后,他并说不出所以然来。所谓《石头记》是康熙时的政治小说全是架空之谈,何足以破胡适之底推断。况且他又何以知道经雪芹增删插入曹家故事?他所谓“或亦许”,正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话。八十回的《红楼梦》,是一气呵成的,稍有文学眼光的读者忽然感到。蔡先生能指出那几节是插入的吗?他能告诉我们怎样插法吗?
况且,若不说雪芹是《红楼梦》底作者,则此书与雪芹何干?蔡先生因本书有增删五次的话,而依字面直解,以为《石头记》是经雪芹增删的,而非他做的,其实这又未免太呆看了。本书第一回既云:“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悼红轩与怡红院当然是一而非二),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阅到了十载之久,增删到了五次之多,目录章回都是他一手添的,那么老实说一句,便是他做的了,何必客气呢?作者不肯直说,这书是我底笔墨,故托辞是由他增删而成。蔡先生何必如此“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呢?譬如高鹗说后四十回是他从鼓担上搜求来的,但他底同时人张船山便老实不客气,说是足下底大笔。可见遮遮掩掩是中国文人底故态,雪芹亦未能免俗耳。
若照他说,在今本之外,另有一本经增删的本。我们试想,这本既无目录,又无章回,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虽尽我们想像,也颇不容易得一概念,这浑沦不名的原本,被曹先生,又增又删到了五次,删的是什么,书缺简脱,二百年之后,无从仿佛了。增的是什么,大约便是曹先生所谓“曹家故事”了。在一部政治小说上,平空加入自己家内底事,曹雪芹莫非是个精神病者吗?不然,虽妄人也不至如此。这么一部杂碎的小说,公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底文艺界,公然占了首座,这不是文艺同人底耻辱吗?像蔡先生这般的审慎,实在太审慎了。
蔡先生此文是对于他底北大同事胡适之先生来求商榷的。我非胡先生,却无端来岔嘴,实在是冒昧啊!故我此文,只曰“批评”,不曰“质疑”,胡先生想必另有意见,做他自己底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