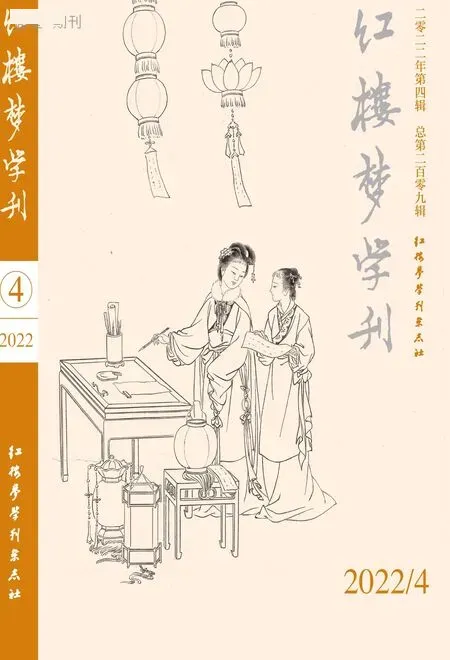英国汉学家包腊的《红楼梦》韵文翻译研究*
2022-11-04王璐瑾
王 燕 王璐瑾
内容提要:1868年,英国汉学家包腊将《红楼梦》前八回译为英文,连载于英文期刊《中国杂志》。在翻译《红楼梦》中的匾额对联、诗词歌赋等韵文时,包腊继承了德庇时、梅辉立等人“以诗译诗”的翻译策略,以淹雅弘通的汉学功底和卓绝精妙的翻译技巧,再现了《红楼梦》诗化文本的艺术风貌,同时,为了揭示韵文的隐喻手法添加了丰富的注释,由此使译文兼具诗人的气韵和学者的审慎。自从包腊译作问世以来,《红楼梦》翻译从马礼逊、罗伯聃等早期译者重视开发其语言学习功能,转向了关注其文学性、艺术性与审美性,包腊译作由此成为《红楼梦》英译史上的一大转捩点。
包腊(Edward Charles MacIntosh Bowra,1841—1874),英国汉学家,1863年来到中国,供职于大清帝国海关,是最早进入海关的英国职员之一,深受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重用,在1866年斌椿使团出访欧洲、1873年代表清廷参加维也纳博览会等外交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海关职责、外交事务,包腊对中国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饶有兴趣,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员,他最重要的汉学贡献就是翻译了《红楼梦》。
在包腊之前,《红楼梦》纤巧别致的谶语诗词、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从没被如此大规模认真译解过,他天生的诗人气质、广博的汉学功底、精妙的翻译技巧、丰富的文化注释,凸显了《红楼梦》自身的典雅与丰厚。自包腊译本问世以来,《红楼梦》的文学性、艺术性与审美性开始走入了西方人的视野,《红楼梦》英译由此出现了重大转向。
包腊译文是《红楼梦》早期英译史上的重要译作,也是篇幅最长的报刊连载《红楼梦》节译本。包腊所译《红楼梦》共八回,1868年开始连载于《中国杂志》(The China Magazine),题名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副标题括注Hung Low Meng。据任显楷考释,包腊译文所用底本出自王希廉评点本系统,这一系统现存有《双清仙馆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可与包腊译作对照研究。
《红楼梦》中存在大量匾额对联与诗词歌赋,较之叙述性文本,不妨将这类内容看作是广义的韵文,这些韵文对早期西方译者而言形成了不小的挑战。《红楼梦》的首位英译者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就曾在《中国一览》(AView of China)中评价《红楼梦》说:“对于初学汉语的人来说,每部分开头的诗歌阅读起来相当困难。所有关于人物服饰、居所的描写,以及门上、房间里题写的‘匾额’也很困难。如果缺乏中国典籍知识,那些被称为‘对子’或‘对联’的句子,也同样莫名其妙。它们经常暗指某些人物、地方或事情,除非熟悉相关典故,否则会令人费解。”对于《红楼梦》中的叙述性内容,包腊多采用逐字直译的方式,严格依照原文进行翻译;而对于匾额对联、诗词歌赋等韵文类内容,包腊则大多采用“以诗译诗”的翻译策略,在保留原文信息的基础上,再现了《红楼梦》诗化文本的艺术风貌。本文密切结合包腊译作,研究其“以诗译诗”的翻译特点。
一、匾额对联
对于《红楼梦》中的匾额对联与诗词歌赋,在英译文版式设计上,包腊做了明确的区分。原著中处于叙述之中、带有诗歌韵味的句子,例如“说不尽的光摇朱户金铺地,雪照琼窗玉作宫”“真是琼浆满泛玻璃盏,玉液浓斟琥珀杯”,包腊将之仍旧置于行文中。而对于原著中单起一行、句前空格的对联与诗歌,包腊则在格式上明确地将其与叙述部分区分开来:居中排版,前后各空一行,篇首的第一个单词大写并使用花体。
中国的匾额与对联是文学与空间艺术结合的产物。匾额悬挂于门户上方,作为装饰;对联也叫楹联,多悬挂于厅堂中或门户两侧,上下联语意平仄相对,是一种文学色彩浓郁且具有装饰性功能的应用性文体,以短小精悍的艺术语言点醒居室主人的文化品格、风度气韵。《红楼梦》中的匾额对联宏衍典丽、艺术精巧,对于环境渲染和情节提示都有重要作用。将这样一种特殊文学形式形神兼备地译为英语,无疑是对译者的挑战。
对于《红楼梦》中的匾额,包腊大多采取了直译的方法。如将“太虚幻境”译为The Region of the Supernal Void(超然的虚空之境),“孽海情天”译为The Sea of Calamity the Heaven of Passion(灾难之海,激情之天),将匾额中的信息无所遗漏地呈现出来。
对于《红楼梦》中的对联,包腊采用了几种不同的翻译方法。第一种是译作句式相近的两句,尽量还原对联上下句式整齐、文意相对的特征,这种译法最接近对联的本来面貌。例如:
原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Thorough comprehension of the affairs of the world,this is learning;
Experience of,and complete acquaintance with the passions of mankind;this is literature.
回译:对世界事务的透彻理解,这是学问;
对人类情感的体验和通晓,这是文章。
原文: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
The gentle cold which wraps in dreams,is the coldness of the spring.
The breath of fragrant plants which envelopes the persons,is the perfume of wine.
回译:封锁在梦中的温和的寒冷,是春天的寒意。
包裹着人的植物的芬芳气息,是酒的香气。
翻译对联时,要想在充分阐发文字意蕴的同时做到词汇数量与句式结构的完全一致非常困难。不难看出,包腊在此采用了逐字对译的方法,虽然他的这种译法容易拉长句式,但是却努力协调上下句之间的结构整饬,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对联”之“对”的形式之美。
第二种为译成诗歌。由于包腊翻译对联时追求逐字直译,比如他将“幽微灵秀地”译作“A place of mystery,seclusion,spirituality and elegance”,将“神秘”“幽静”“灵性”“优雅”尽数翻译了出来。然而,这种逐字直译的翻译方法在面对富含“春恨秋悲”“花容月貌”等密集意象的对联时,就很难将之压缩在两句之内了,因此,他不得不把短小的对联改写为多行的诗句。
在包腊的《红楼梦》前八回译文中,凡是翻译为诗歌的基本都翻译成了格律诗,体现了译者深厚的文学素养和高超的翻译水平。英语格律诗讲求节奏(rhythm)与押韵(rhyme),富于和谐性与音乐美。节奏的基本单位是音步(foot),由轻重音的交替构成。常用的音步有四种,抑扬格(the iambus,or iamb)、抑抑扬格(the anapaest)、扬抑格(the trochee)与扬抑抑格(the dactyl)。押韵可押头韵(又译作“双声”)、腹韵、韵脚,有多种押韵形式。包腊译诗所采用的押韵形式,有ABAB式(警幻之曲、元春判词)、AABB式(“无才可去补苍天”、香菱判词、王熙凤判词)、ABCB式(湘云判词、惜春判词、李纨判词)等。
在包腊之前,英国汉学家梅辉立(M.F.Mayers)就曾经以诗体翻译《红楼梦》中的对联,将“孽海情天”联译为一首ABAB式四行的英诗。包腊继承了梅辉立的对联翻译方式,将“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翻译为:
REGRETSwill dull the budding spring,
And griefs the days of Autumn bring,
These are by man himself provoked
And mostly by his faults evoked.
A face like flowers of beauty rare
A countenance like moonbeams fair!
Alas!that grace with bloom combined
Oft fail a fitting mate to find.
这首诗为AABB式八行,每个诗行有八个音节,分为四个音步,每个音步中有两个音节,前者轻,后者重,节奏规整,音律谐和,是一首非常完美的抑扬格四音步诗。这种译法的优点是可以充分传达出对联的文学内涵,但同时也改变了对联原本的艺术形态,从而容易使西方读者对这一特殊的文类产生根本上的误解。
二、诗词歌赋
包腊在翻译《红楼梦》前八回中的诗词歌赋时,采用了“以诗译诗”的翻译策略,即用英文格律诗翻译中文诗歌,这是其译文的一大特色。布拉格学派翻译理论家罗曼·雅科布逊(Roman Jakobson)曾于1959年发表著名论文《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在谈到诗歌翻译时指出,“文字游戏”(paronomasia)是诗歌艺术的主宰,诗歌从定义上来说是不可翻译的,只能进行创造性转换(creative transposition)。包腊翻译《红楼梦》诗歌时,也做了种种调适与转换。
包腊译诗的成功案例,有任显楷此前分析的《〈好了歌〉注解》,他指出这是一首抑扬格五音步、双行联韵的“英雄联韵体”,为18世纪最盛行的英诗体式。与此相类,包腊翻译的“春梦随云散”是一首押韵格式为ABAB、抑扬格五音步的四行诗。抑扬格五音步被称为“英雄诗行”,这种诗体被称为“英雄四行套韵体”(the heroic quatrain),由于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用这一体裁写下了著名的《墓园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故又名“挽歌四行套韵体”(the elegiac quatrain)。此外,包腊翻译的巧姐的判词,在双行联韵体后接续了一个较长的诗行,押韵格式为AABAAB,属于一种尾韵诗节(the tall-rhyme stanza)。
包腊与其目标读者生活在19世纪后期,以传统英诗来翻译《红楼梦》中的诗词,努力在形式上贴近西方传统的文学体式,不仅保留了原著诗文交织的艺术风貌,而且还以风流倜傥的古风流韵给西方读者带来了直观的艺术感受,从根本上提高了包腊译文的文学性与审美性。
为适应英诗格律,包腊对原文语序和句式做了相应调整,这是其译文的第二大特色。比如,巧姐的判词翻译如下:
THE grandeur fled,
The household dead,
Of rank and kindred speak again no more;
The dame the maid
Once chanced to aid
Repays the benefits conferred before.
包腊将原文的“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拆解开来,“势败”“家亡”各为一个短句,“休云贵”与“莫论亲”合为一个长句;又将“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的主语由王熙凤改为刘姥姥,意思也相应调整为“刘氏曾经偶然得到了帮助,回报之前所给予的好处”。在排列句式时,同样拆分为两短一长的三句,形成一种简练谐和的交错之美。
类似的转换同样出现在包腊翻译的《警幻仙子赋》中。在原著中,为了与前文音律和婉的楚辞体长句形成鲜明对比,曹雪芹以四字句设问作答,所谓“其素若何?春梅绽雪;其洁若何?秋蕙披霜”,句式短促,铿锵有力。包腊将之译作:“Her face,fair as snow on the plum bud in Spring time.Transparent as flowers touched with hoar-frost in fall.”他对四字句的翻译,与前文之楚辞体长句并无差别,虽然没有设问的警醒,却也与前文勾连,达到了一种意脉连绵的艺术效果。
包腊译作的第三大特色是在诗歌中补充人称,这也是中英诗歌显著差别之一。有论者指出,“中文诗常常可以省略主语,容许诗人不让自己的个性侵扰诗境,诗中没有表明的主语可以很容易地被设想为任何人,这使得中国诗常具有一种非个人的普遍的性质。”而英诗句法一般要求主语的在场,故而诗歌中人称代词往往不可或缺。
《红楼梦》第五回的诗歌虽然大多具有明确的描述对象,但诗歌本身缺乏确定的人称视角。包腊在翻译时补充了相关人称视角,以《红楼梦曲》为例,包腊除了引子“开辟鸿蒙”采用了第一人称之外,绝大多数以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的视角来称呼诗中所描述的对象。例如,他将巧姐《留馀庆》中的“休似俺那爱银钱忘骨肉的狠舅奸兄”译为“And not like this young maiden’s kin”,由第一人称“俺”改为了第三人称“this young maiden”,这样的翻译方法强调了《红楼梦曲》“仙子演唱”的抒写方式,明确了“由仙子向贾宝玉讲述十二钗故事”的情节结构。
在一些诗歌中,包腊通过转换人称,改换了原诗所指对象。例如,包腊将《警幻仙子赋》中的“宜嗔宜喜”翻译为“Lost in wonder I gaze,half in awe I admire”,在将其意思改写为“茫然瞋视,且敬且慕”的同时,还把相关主体由警幻仙子变成了“我”,由此而为译文补充了一个处于文本之中对警幻仙子进行观看、描述并作出情绪反应的阐发主体。又如探春判词中的“千里东风一梦遥”,包腊的译文如下:
And then their sad farewells they say
To one whom ne’er again will they
Revisit save in midnight dream.
原著中“千里东风一梦遥”所指对象为探春,意指探春回望家乡而远隔千里。包腊将此句对象置换为送别探春之人,语意为“从此以后,只有在梦中他们才能见到探春”,由探春怀念家乡改换为家乡的人怀念探春。然而这样一种处理并未损害原诗的意境,反而平添了中国古典诗歌中“对写”手法的意味。
包腊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原有结构,重写为传统的英诗形式,形式上的归化部分地冲淡了东方色彩的名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带来的陌生感,从而减少了《红楼梦》中大量的诗歌在文学接受上的障碍。这样的做法既适应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习惯,又保留了原著诗歌的丰富意蕴,转换巧妙而意味隽永。
三、寓意隐喻
《红楼梦》中的诗歌大多有丰富的意旨,与人物性格、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翻译诗歌时,多数情况下,包腊没有采用逐字对译的常见译法,而是时常将一句扩为数句,将原诗隐晦的意象转化为直白的陈述,甚至添加原文没有的内容作为解释和补充,更多地追求意韵的连贯而非字句的精准。例如,他对湘云判词“展眼吊斜晖”的译作:“Her sun of life too soon declines.Its brightness overcast.”中国诗歌重视意象的塑造,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自然风物与人物情感往往浑然不分、水乳与融,读者依靠文化语境和艺术想象,完成意义空间的扩展,但是,这样的表达方式,未必有利于西方读者的解码。或许是为了破除这种文化理解上的障碍,在此,包腊完全删除了湘云“展眼”的动作,将远望落日这样一个落寞萧索的场景,转化为对人物命运的直白描述,将“斜晖”直解为“消逝的生命之光”,直接替西方读者把诗歌隐含的涵义解读了出来。
在探春的判词中,“消逝的生命之光”的语义转换与原文的意境大体一致,但包腊所做的类似尝试并非总能成功。例如,袭人判词中的“空云似桂如兰”被译作“夏天最美丽的花朵”,似乎就不够恰切,没能自然传达出“似桂如兰”的温柔气韵。元春和迎春判词中的“虎兔相逢大梦归”“一载赴黄粱”,原指生命消逝,“虎兔相逢”和“一载”提示了元春和迎春死亡的明确节点,译者将两者均翻译为“从梦中醒来”,虽赋予诗歌一种恍然醒悟的意味,却没能表述出原文隐含的预言性。
当英译诗歌难以直接且全面转换或揭示原著富含的隐语时,包腊就通过添加注释的方式解说和补充诗歌的内涵。包腊所译《红楼梦》前八回共有九十七条注释,其中六十七条集中出现在诗词歌赋密集的第五回,或许正是第五回的翻译使包腊充分意识到了注释的重要性。
第五回的诗歌多是谶语,作为全书之文眼,利用双关、隐喻、拆字、典故等修辞手法,顷刻间点明人物名称,提示人物命运,暗示情节发展。在原著中,面对晦涩难懂的金陵判词与《红楼梦曲》,神游其中的宝玉尚且觉得“散漫无稽”、不能领悟其中意旨。其中的谶语,若纯以意译,将双关与拆字所指向的隐喻直接在正文中揭示出来,则必然会令宝玉的茫然无知、仙子的唯恐泄露天机失去根据。后世注家围绕第五回诗词,更是聚讼纷纭,平生出不少公案。
诗歌的双重乃至多重含义对译者提出了挑战,一方面,译文需要留存诗歌的表层文意;另一方面,译文还需揭示出诗歌隐含的寓意。通常情况下,包腊在正文中直译词句字面含义,在注释中对其可能具有的内涵做出解释和补充,通过注释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文的隐含寓意和多重意指,尽可能搭建和重构诗词谶语的完整意义空间,由此贴近与还原原著的本来面貌和文化语境。
在《红楼梦》第五回中,每一首金陵判词都有一幅附画,例如袭人判词的附画是“一簇鲜花、一床破席”,附画中的图像又以谐音、双关等修辞手法喻指出袭人名字中的“花”与“席”(袭)之意。包腊对袭人判词和附画的隐喻性了然于心,在注释中说:“这些诗句中的每一句都是一个谜语。每幅画的主题都与诗句中所提到的人名有一些隐秘的暗示,诗句本身预示着其命运。”
包腊在给英莲判词所做的注解说:“莲,一种睡莲,该字是本诗涉及的少女的名字中的一个字。”又为“孤木”添加注释说:“这首诗的第三行晦涩难懂,译者只能大胆猜测其意思。某些字组合起来,就会形成薛蟠之妻的名字‘桂’字,正如在续作中所写的那样,她的嫉妒害苦了英莲。”包腊不仅通过注释点明了“莲”和“桂”的关联,还揭示了英莲后来被夏金桂百般折磨的不幸命运。
在翻译钗黛判词时,包腊在相关注释中说:“两个‘木’字构成一个‘林’字,‘林’字是‘黛玉’名字的第一个字,而‘黛玉’之名则完全由‘玉带’转换而来。下面那个雪(薛)中的金钗,当然指的是薛宝钗。”包腊明白无误地揭示了“玉带林”与“金簪”“雪”的意义关联,并且还在括号内标注了“雪”与“薛”的谐音相关。
包腊对于大多数判词的解释都是正确的,但仍有遗漏和错译。同样是拆字游戏,“凡鸟偏从末世来”中的“凡鸟”合为“凤”被注出,“子系中山狼”中的“子系”合为“孙”则被完全忽略了。“一从二令三人木”是一个红学悬案,此句甲戌本批注“拆字法”,认可这一观点的学者多将“人木”合为“休”。包腊的解释为:“对于译者和他请教过的几位博学多识的中国人来说,本诗的第三行逐字读来均不可解。来旺曾两次加速了这个家族的衰败,来旺名字的第一个字是‘来’字,或许只有把‘三人木’理解为‘来’字,方能解决这一问题。”由此可见,包腊不仅自己琢磨与研究人物判词的隐指含义,并且还曾就不解问题请教过中国人,他的翻译与注解体现着一个学者的严谨与审慎。
除了谶语,诗中还涉及到大量典故,包腊同样不厌其烦地在注释中加以说明。比如,他指出钗黛判词中的“停机德”与“咏絮才”,用了孟母与谢道韫之典故;《终身误》中的“山中高士晶莹雪”,用了汉代袁安之典故,同时引用明代高启《咏梅》中的“雪满山中高士卧”来解读其语意;《虚花悟》中的“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引用唐代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郞》中的“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
《红楼梦》的谶语与典故历来聚讼纷纭,因而无须过多讨论包腊的注解是否足够坚实与合理。但可以见得,包腊对于《红楼梦》随处可见的文字游戏格外敏感,对于谶语、典故的知识性和《红楼梦》的寓言性充满警觉,他在这部小说纤巧的诗意中努力寻绎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走向。若非英年早逝,假以时日,包腊或许有兴趣和能力将《红楼梦》全部翻译出来。
四、以诗译诗
在《红楼梦》早期英译史上,遵循原著节译《红楼梦》故事片段的两位早期译者是马礼逊和罗伯聃(Robert Thom),马礼逊翻译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出自第四回,罗伯聃翻译的“刘老老一进荣国府”出自第六回。遗憾的是,两人都没有将第四回和第六回完整翻译出来,而包腊则尝试着完整翻译了前八回,篇幅之长,较之前人有了明显变化。
同时,包腊的译文通俗流畅、文辞雅驯,“以诗译诗”的翻译策略凸显了《红楼梦》的文学性,为诗词歌赋添加的注释丰富多样,诗人的气韵和学者的审慎使他的译作为展示这部经典之作的文学性提供了可能。可以说,包腊译文问世以来,《红楼梦》英译史发生了根本转向,从马礼逊、罗伯聃等早期译者重视开发其语言学习功能,转向了关注这部作品的艺术性与审美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腊的译作可谓意义非凡。
包腊之所以采用“以诗译诗”的翻译策略,大致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
第一,包腊本人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的诗歌创作天分与热情。他年轻时进入伦敦城市学院(City of London College)就读,为英法文学以及德语、法语等多语言能力的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青年包腊就有诗歌创作热情与经验。其子包罗(Cecil Bowra)在家庭回忆录中透露,他收藏有父亲创作的三首诗歌,这些诗歌粘贴在1865、1866年间广东常见的一本书中。笔者按图索骥,找到了这三首诗歌,分别是《播种与收获》(Seedtime and Harvest)、《沮丧的话》(A Word with Despondency)和《手的使命》(What the Hand findeth to do),1860年2月18日、1860年10月13日、1861年4月6日先后首刊于《钱伯斯杂志》(Chambers’s Journal),此后还在其他刊物得到转载。
此外,从收藏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SOAS Library,University of London)的包腊日记等文献来看,他青年时期即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良好的写作习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生活的有趣瞬间,诉诸笔端,用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在他的笔下,传奇将军加里波第、“常胜将军”戈登、凶悍的开罗臭虫、静谧的黄浦江村庄等人物、景象纷至沓来。包腊本人的诗歌创作天赋和写作技巧,使他能够灵活自如地转化和翻译《红楼梦》中的韵文。在包腊之后,乔利(H.Bencraft Joly)、霍克思(David Hawkes)等人在翻译《红楼梦》时,都在一定程度上承续了“以诗译诗”的翻译方法。
第二,包腊“以诗译诗”的翻译方法,受到了先行者的启发与影响。在包腊之前,已有汉学家对《红楼梦》中的诗词翻译做过尝试。《红楼梦》的首位英译者马礼逊翻译了第四回,尽管他意识到“护官符”是一首诗歌,却并未采用韵文来翻译。1829年,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的英译诗集《汉文诗解》首刊于《皇家亚洲学会会刊》(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其后以单行本重刊。《汉文诗解》中选译了《红楼梦》第三回描述贾宝玉的两首《西江月》,德庇时将其翻译成了英语格律诗。1867年,梅辉立在《中日释疑》(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第12期的《中国小说作品》(Chinese Works of Fiction)中介绍了《红楼梦》,并选译了部分诗词。
包腊所译《红楼梦》第三回中的《西江月》,完全采用了德庇时的译文,并在注释中做了说明。包腊翻译的“孽海情天”联、晴雯判词与袭人判词都是承继梅辉立所译而来,并在注释中盛赞梅辉立的译文精确优雅、气势磅礴。包腊对德庇时与梅辉立的译诗近于原样照搬,仅对个别词汇与标点做了改动。有趣的是,德庇时所采用的“文畬堂藏板”《红楼梦》中的《西江月》原文为“似俊如狂”,而在包腊所采用的王希廉底本系统中,此句为“似傻如狂”。从上下文来看,“似傻如狂”更加符合文意,但包腊并未对德庇时的底本与译文进行辨析,而是直接抄录进了自己的译文中,由此可见他对前人的诗歌翻译相当服膺,几乎达到了盲目追随的地步。
第三,《红楼梦》一向被誉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王希廉曾评价说:“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扁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译者熟悉并解说《红楼梦》中的诸多艺术形式、历史典故与文化知识,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其中的诗词歌赋至关重要。
除了汉学家,包腊还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博物学家,这是他在翻译《红楼梦》时能够为诗词歌赋添加丰富注释的主要原因。1872年,包腊曾为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的《英华萃林韵府》(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编撰《植物学索引》(Index Plantarum),将中国的植物名称翻译成拉丁文,同时将中国植物纳入西方植物学体系;1873年,在赫德的组织下,他还曾代表清廷搜集中国特产参加维也纳国际展,并撰写了《适合英国市场的中国产品报告》(Report on the Objects of Chinese Manufacture suited to English Markets,exhibited at the Vienna Exhibition)。博物学家的知识视野和“中国通”的广闻博见为他理解《红楼梦》提供了可能。
包腊是一位博览群书、热情洋溢的汉学家,也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对中英历史与文学都满怀敬意与热爱。包腊去世后,他的好友、在香港行政部门任职的利斯特(Alfred Lister)评价说:“包腊才华横溢、非比寻常,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学中有价值的东西、高贵的东西都心怀敬意,乃至热情昂扬,同时,他又很清楚英国在文学界、艺术界的崇高地位,对英国历史和文学的喜爱丝毫不减。”这是他敢于面对《红楼梦》这一鸿篇巨制,又能够以其流畅的诗笔翻译、注释前八回的重要原因。
整体看来,包腊译文诗意盎然、注释丰富,自问世以来,西方汉学界开始关注《红楼梦》的文学性、艺术性与审美性,该译作由此成为《红楼梦》英译史上的一大转捩点。
① [英]查尔斯·德雷格著,潘一宁、戴宁译《龙廷洋大臣:海关税务司包腊父子与近代中国(1863—192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② 任显楷《包腊〈红楼梦〉前八回英译本考释》,《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6辑。
③ 王燕《马礼逊英译〈红楼梦〉手稿研究》,《文学遗产》2021年第3期。
④ 曹雪芹、高鹗著,王希廉评《双清仙馆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本文所引《红楼梦》原著均出自这一版本,此后不再逐一注释。
⑤ E.C.Bowra,“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Hung Low Meng)”,The China Magazine(The Christmas Volume),1868,pp.1—17;pp.33—43;pp.65—79;pp.97—106;pp.129—152.E.C.Bowra,“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Hung Low Meng)”,The China Magazine(The Third Volume),1869,pp.1—11;pp.33—45;pp.65—75.本文所引包腊译文均出自这一版本,此后不再逐一注释。
⑥⑨ 吴翔林《英诗格律及自由诗》,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145页。
⑦ R.Jakobson,“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On transl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232—239。
⑧ 任显楷《包腊〈红楼梦〉前八回英译本诗词翻译管窥》,《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3期。
⑩ 詹杭伦《刘若愚融合中西诗学之路》,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11] 王燕《德庇时英译〈红楼梦〉研究——从约翰·巴罗书评谈起》,《红楼梦学刊》2018年第5辑。
[12] 王金波、王燕《〈红楼梦〉早期英译补遗之二——梅辉立对〈红楼梦〉的译介》,《红楼梦学刊》2014年第2辑。
[13] 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三)》,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