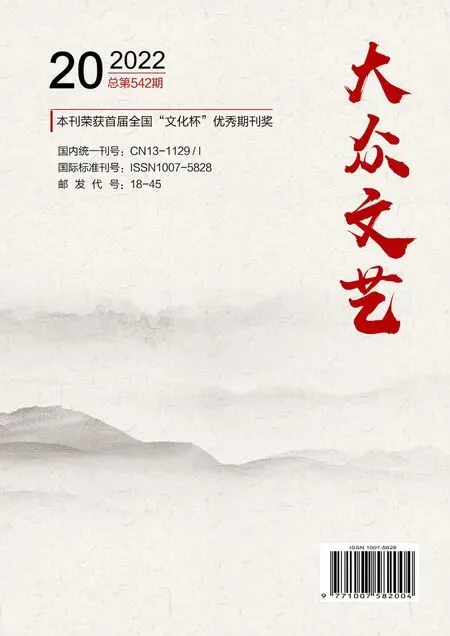由“仪式思维”再观梅特林克的早期独幕剧与哲学观念
2022-11-04高灵毓
高灵毓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雷曼在梳理后戏剧剧场前史时曾指出,礼俗仪式性的剧场艺术存在一条从日本能剧经由梅特林克、马拉美而至威尔森的发展弧线,且将梅特林克的作品对于礼俗的关注与其命运主题联系在一起。然而,国内现有的梅特林克研究大多着眼于象征主义风格、静态戏剧原则与死亡主题,尚未有论文对雷曼的这一观点展开讨论。基于此,本文拟从这一话题入手,探询梅特林克的早期独幕剧(即创作于1891-1895年的《无形的来客》《盲人》《七公主》《室内》)、理论思想与仪式之间的联系。
一、仪式思维与前理性思维
戏剧与仪式存在密切关联早已是共识性的观点,理查·谢克纳甚至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剧场艺术与仪式并无内在区别,“对二者进行区分应该看其‘效用’(仪式的目的)与‘娱乐’(艺术的作用)的参数”。因此,从仪式视角讨论梅特林克戏剧,当然不可局限于宏观层面上的戏剧与仪式的关系,而需强调这些作品异于同时期、前人剧作与后戏剧剧场艺术的独有特征——“仪式思维”便提供了一条独特且有效的路径。
在专著《过渡》中,意大利学者马里奥·佩尔尼奥拉以特洛伊比武(指记载于《埃涅阿斯纪》中的古罗马仪式,兼具丧葬、城市破土奠基与成人仪式三种功能)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仪式思维”这一概念。
与其他前逻辑思维相仿,这种没有神话的仪式也与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思维相对立,不强调行动的功用性、目的性。然而,与其他印欧语系仪式不同的是,这种仪式并不具备统一的、不可更改的意义——类似于对神物原型的大量忠实仿造反而挑战了前者的独尊地位,古罗马仪式在一丝不苟的重复中斩断了仪式与神话的联系,恰恰因为对原型的完美复制而消灭了原型。但与此同时,仪式并未彻底走向世俗化,而是在神圣与所谓亵渎之间建立了中介地带。
更为特别的是,这种仪式思维展现出了一种新的死亡观念。佩尔尼奥拉指出,基督教把死亡视作通向永恒的通道;人文主义思想将死亡完全排除在生命之外,对其刻意躲避;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观念坚定地面对死亡的确定性,从而令此在获得真实性——罗马仪式思维下的死亡观念则与这几种观点都存在差异。罗马宗教所认为的死亡是行尸走肉完全顺应神的旨意、听任环境的驱使行进,也就是说,“它的最大特征不是对于死亡的焦虑,或者对于仪式重生的喜悦,而是对于未来的犹豫不决,以及对于现在的神圣本质的深信不疑”。
这种仪式思维与梅特林克创作理念最为浅表层面的相似之处,显然表现为它们同现代理性的对立。梅特林克在哲学随笔集《智慧与命运》的多个篇章中对理性做出了价值评判,他将智慧与理性区分开来,认为前者远高于后者,理性应向爱与灵魂的本能屈服,人类灵魂中最完美的一切会首先发现于还不清晰的思想之中。这种价值判断与梅特林克对宇宙本体的认知紧密相关,在他看来,宇宙由四大经验主体(看得见的世界、看不见的世界、看得见的人、心灵)所维系,看得见的世界与人唯有预示了看不见的部分,才能获得实在性。
在这种神秘主义哲学观的统摄下,梅特林克的早期戏剧作品常有意识地显露理性思维的有限、无力。《无形的来客》中,父亲与叔父多次感叹失明的外祖父不服从理性、有种种奇怪的想法,然而,在护士宣告母亲死亡前,拥有所谓正常视力与理智的五个人都始终处于被蒙蔽的状态,唯有外祖父接收到了种种奇异响动传递的预兆。相似的,当《七公主》中的王后断定公主死亡且因此哭泣时,国王同样要求她理性一些,但他冷静理智的认知在剧末被宣告错误——众人无论如何摇动门窗都无法唤醒毫无生气的奥塞拉。
当然,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层面,将完全无法察觉梅特林克具有开创性的早期独幕剧作品、理论与这种古罗马思维模式存在的诸多深层关联。因此,下文将从“通过死亡赋予当下以神圣性”与“尊奉命运或其他形而上存在的统治力量”的角度出发,详细论述梅特林克早期戏剧及思想中的仪式思维特征。
二、神圣性与死亡母题
佩尔尼奥拉指出,罗马仪式“趋向于强调现在每一天,一切言谈举止、一切行为模式都处在一种流动之中”,并且强调此刻的神圣本质。梅特林克的日常悲剧理论亦是如此,它尊奉当下的神圣性,建立了神圣与世俗的中介地带。
谈及梅特林克早期独幕剧与传统悲剧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便不可不提这些作品中情节、行动的缺位——斯丛狄将这一点概括为“用情境的范畴来替代情节的范畴”;亦常有研究者将他的作品与《等待戈多》等荒诞派剧作并提,甚至认为“梅特林克的象征主义静态戏剧就是等待戏剧”。在《日常生活的悲剧性》一文中,梅特林克本人也旗帜鲜明地反对由奇闻轶事构成的悲剧,希望用几乎静止的日常生活情境取而代之。在他看来,静止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世俗与神圣的交界地带,当狂暴的动作与欲望都被摒除在外、人类安静地与世界对视时,当下便被赋予了神圣感。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种当下的神圣性究竟是如何与梅特林克早期独幕剧常涉及的死亡母题建立联系的呢?在罗马仪式中,当下的神圣感是由死亡与生命的融合所赋予的,佩尔尼奥拉称之为仪式思维中的“模拟死亡”——这是一种物获得了人的特征、人失去感觉成为行尸走肉的状态,处于此种中间地带的生命完全顺从环境的要求与神的意志。这种状态在梅特林克的早期独幕剧作品中并不鲜见:七位脸色灰白、紧闭双眼的公主躺在大堂中,其中熟睡的六人与已经死去的奥塞拉没有任何分别,直至被墓石与铰链的摩擦声惊醒,也依旧沉默、呆滞(《七公主》);老祭司坐在盲人之中,脸色蜡黑、一动不动,在狗引导盲人确认他冻僵的尸体以前,他对于观众而言似乎处于生与死的中介地带(《盲人》)。
在这些作品中,与上述角色相伴存在的,是他们的旁观者。无论旁观者是察觉到了征兆、还是茫然无知,都只能观望、等待,既无意躲避,也无力反抗。《室内》中知晓女孩溺亡消息的老人在窗外旁观着她不知情的家人,房屋的边界与他对这家人如常行动的叙述仿佛在舞台中隔绝出了一个自足空间,然而“世界是不会在房屋门外终止的”,老人自己亦不会因为能够读解预兆就享有自主权,因为“带来不幸的人们再也不能扼制不幸……不幸也是他们的主宰,他们必须为它效劳……不幸有自己的目标,走自己的道路”。在这层意义上,知晓真相的旁观者类似于佩尔尼奥拉所描述的罗马教士,享有聆听、顺应神的旨意的能力与责任。
文集《谦卑者的财富》再度证明了梅特林克的此类创作并非下意识的,而是受到了清晰创作观念的指引。在《日常生活的悲剧性》一文中,梅特林克以《建筑师》等戏剧为例指出,具有伟大悲剧性的作品中的角色无论如何躲避,都最终会与命运遭遇;而在某些时刻,我们作为旁观者,可以预知命运将如何行事——这样一来,一种难以名状的力量便主宰了梦游般的戏剧。在《命中注定》中,梅特林克将死亡的意义阐述为向导和生活唯一目的,认为恰恰是死亡塑造了人们的特征,只有死者才能在一个片刻中揭示自己的真正面貌。由此可见,在梅特林克看来,死亡并非生存的对立面或重生的开始,而是让人在某种形而上力量的统摄下严肃地靠近不可见的、真正的生活,如此赋予当下以神圣感——这种观念与仪式思维颇为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研究者易将梅特林克的前后期创作截然分开,认为只有后期显示了人的主观意志的意义,然而《星》等散文篇章证明事实也许并非如此。此外,在是否呈现死亡焦虑这一问题上,梅特林克的思想观念与仪式思维存在差异——这两点将在下文中继续展开论述。
三、死亡焦虑与自主意志
提起戏剧中的仪式特征,人们极易联想到欧洲中世纪宗教剧及其源头——教堂仪式剧。加之梅特林克曾就读于教会学校与天主教大学,此类联系也许显得更加顺理成章。然而,据《梅特林克及其戏剧创作》等相关生平经历介绍,少年、青年时代的学习经历反而使梅特林克对教会学院的阴森氛围与神父们的专制摧残感到反感。此外,教堂仪式剧与中世纪宗教剧多围绕上帝的绝对力量、原罪与赎罪、现世与来世、恶念与善行展开,它们蕴含的死亡情节与神的荣耀、人的罪责紧密相关,指向忏悔与灵魂得救。然而,梅特林克的早期独幕剧既没有将神秘统治力量的来源明确命名为上帝,也从未安置有效的忏悔、审判与救赎,直至结尾,人物都只是在焦虑中获悉真相或依旧被蒙蔽、陷入惊慌。甚至《盲人》中祭司的死亡与众盲人的无措还常被研究者解读为民众在宗教价值失落的时代茫然惶惑而寻不到方向。如此看来,仪式思维也许远比天主教仪式接近梅特林克早期独幕剧的思想内核。
不过,梅特林克早期独幕剧中的死亡观念也并非与仪式思维毫无二致,它们在死亡焦虑的呈现问题上存在分歧——罗马宗教用对此刻神圣本质的笃信消解了死亡焦虑,但在梅特林克的剧作中,日常生活的悲剧性必须以死亡焦虑为依托。以《无形的来客》中的台词为例:
外祖父:有些事我已经发现了!……我可以断定我的女儿一定发生不幸……
叔父:你在做梦吗?
外祖父:你们不想告诉我!……我清清楚楚看见有些事情了……
……
长女:那里没有人呵,外公。
父亲:我们告诉你那里没有人呀!
外祖父:你们都看不见,你们任何一个都看不见!
在《后戏剧剧场》中,雷曼将伯勒尔关于绘画艺术的“骇怖美学”分析拓展至戏剧领域,认为如同美杜莎空虚的目光引发了骇怖,剧场中的骇怖也是不依附于故事等客体而存在的,观众是为了惊骇本身而惊骇。“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对什么东西并不知情、不拥有,且这种不拥有、不知情作为一种空无突然进入了我们的体验范畴。在这个时刻,骇怖发生了”。类似的,在梅特林克早期独幕剧中,一方面,能够读解征兆的旁观者不断用台词预告死亡必然降临;另一方面,观众意识到自己和其他角色都对这种神秘力量无法充分认知、觉察,于是恐怖情境得以成功地搭建起来。
在戏剧形式上,这种情境的成立有赖于重复的、几乎是自说自话的对白,斯丛狄也因此认为梅特林克的早期剧作体现了戏剧的危机:斯丛狄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视作戏剧的中心,认为戏剧的主要表现形式应该是对话而非针对观众的讲述。这样一来,梅特林克早期独幕剧中那些没有对话功能、有时还带有叙事性质的台词自然就不符合要求。而且,与后戏剧剧场中的独白不同,这些台词也并非直接面向观众席的、存在于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交流,它们更接近于交流的彻底断绝,角色被抛在由神秘力量统摄的日常生活时刻之中,独自于世俗与神圣的交界处被死亡焦虑缠住。
顺着这一话题向下论述,我们有必要提及第二部分保留的另一个问题:虽然研究者常将梅特林克的前后期创作截然分开,但在他的早期散文《星》中,人的主观意志的意义其实并没有完全遭到否定,而这一点与死亡焦虑亦有关联。在该文中,梅特林克指出,不同于古希腊时期无人敢过问与探询命运居高临下的统治力量,新戏剧时期的人们应乐于了解灾难的本质与规律,即使这并不有助于抵抗或逃离命运的摆布,也会使人在放大自身意识的过程中接近看不见的、更为本质的世界,故而“增强地球上的意识也许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此看来,尽管梅特林克早期的戏剧与散文作品都毫不掩饰对于人无力躲避命运的悲观,但人物在行动层面上不充分享有主体性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认知层面上也是如此。诚然,增强认知的敏锐性也意味着将放大所需经受的悲哀,可“尽管威胁我们的悲哀还是威胁野蛮人的同样的悲哀”,“当我们的灵魂得到升华,它会净化命运”。认知的拓展同样在对抗着既定命运的狭窄,虽然其结果并不体现在看得见的世界与看得见的人身上。在这层意义上,承受死亡焦虑便不完全是一种客体性的行为。
结语
虽然从梅特林克的散文随笔中难以找到直接证据证明他的哲学思想与创作理念受到了古罗马仪式思维的影响,但在“同现代理性对立”“通过死亡赋予当下以神圣性”与“尊奉命运或其他形而上存在的统治力量”等方面,梅特林克的早期独幕剧及哲学思想确实呈现出了与仪式思维的深层关联。更重要的是,通过仪式思维这条路径,我们能有效地分析出他的早期独幕剧与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悲剧以及中世纪宗教剧的内在区别究竟落在何处。此外,若向后梳理,后戏剧剧场中虽然亦常出现用仪式取代情节的现象,但同样与梅特林克早期独幕剧有着显著分别:在后戏剧剧场中,仪式的膜拜指涉含义被取消,“着重于身体与存现”,“过程结构是音乐性的、节奏性的,或是视觉性的、建筑性的”;梅特林克早期独幕剧则同时保留着神话世界的前理性思维与严肃性,且台词仍对于戏剧情境地搭建起着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