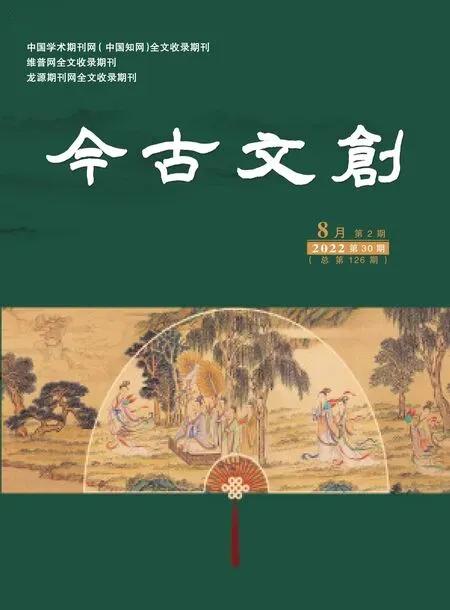论巴金《寒夜》中的“无物之阵”
2022-11-01侯梓妍
◎侯梓妍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56)
《寒夜》被称为平民的史诗,它叙述了在抗战胜利前一年的重庆,知识分子汪文宣与母亲汪母、妻子曾树生三人的家庭生活如何在重压下走向破裂的故事,揭示出底层平民的真实生活状态,蕴含着人性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深层思索。它以现实主义的深度、思想意蕴的丰富性、艺术手法的圆熟成为巴金创作风格转向的界碑。
一、“无物之阵”在文本中的内涵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物之阵”这个术语最初出现在鲁迅笔下《这样的战士》中,“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鲁迅以“无物之阵”来描写敌人的阴险、虚伪,写出战士面对这样的境遇时永无胜利可能性的绝望状态。这个富有意味的隐喻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阐释兴趣。
钱理群在《心灵的探寻》中通俗易懂地解释了“无物之阵”的含义:“分明有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当然就分不清友和仇,也形不成明确的战线;随时碰见各式各样的‘壁’,却又‘无形’ ——这就是‘无物之阵’。”
“无物之阵”更深层次的理解可以是指一个人被一种势力、习惯所深深包围却总也走不出来的那种无力焦灼又害怕的心灵困境状态,布下这个“阵”的人也不再局限于敌对方,有时恰恰来自至亲至爱之人。鲁迅对此曾有过同感:“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
在巴金的《寒夜》中,曾树生与汪文宣两情相悦,通过自由恋爱结合在一起,并非没有感情基础,汪母对独生儿子的爱更是不言而喻。然而正是汪文宣的这两个最无法割舍且深深爱着他的女人为他布下了一个“无物之阵”,使得他如困兽般挣扎于其中,遍体鳞伤仍无力反抗、无法逃离,只能自己默默忍受,最终在“无物之阵”中倒下,以死亡的悲剧收场。这个隐含在叙事背后的“无物之阵”正如小说题目“寒夜”一样,是一个虽未直接出现但能时刻掌控人物命运的笼罩性意象,这既是战争时期时恐怖压抑的氛围,也是巴金构建的最亲密人之间的隔膜。
二、“无物之阵”形成的原因
(一)汪母与曾树生:婆媳之间的双向冲突
自古以来婆媳关系就是家庭结构中难以调和、微妙复杂的情感,也是社会历史中最广泛的冲突之一。《寒夜》中大篇幅写到了汪母与曾树生之间的婆媳冲突,在曾树生离开家后,汪母不仅丝毫不关心,甚至连称呼都是“那个女人”;听说儿子主动去找树生,她冷笑着说:“她永远不会跟着你吃苦的。”而面对婆婆一次次的咄咄逼人、恶语中伤,曾树生也绝不逆来顺受,她年轻且富于生命力的身体爆发出反抗婆婆压迫的能量,明确表示“我也受不了她的气”。这种模式已不再像以往如《孔雀东南飞》里的恶婆婆焦母对柔弱儿媳刘兰芝的单向逼迫,她们之间属于互相伤害,具有从经济到思想再到情感上的多重矛盾。
婚姻、家庭生活的琐碎而又无休无止的冲突之中,受到最大伤害的人实则是最不希望发生冲突的汪文宣。汪文宣为儿为夫的身份让他在两个女人之间既焦急又尴尬,不管他选择帮助谁,都会对另一方造成伤害。然而无论哪一方造成伤害都是他最不愿看到的结果。两个女人每吵一次架都相当于架构起一面无形的墙壁,给汪文宣以重击,死死包围住了他,让他能自由思索、活动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婆媳双向冲突所带来的双倍痛苦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地纠缠着汪文宣的灵魂,使得本就脆弱、忧郁、神经质的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手足无措,最后导致他对母亲和妻子的吵架由无可奈何变成了置之不理,而他的态度会无形中致使冲突的再一次发生……婆媳之间的双向冲突给汪文宣筑成了一座喘不过气、使不出力的“无物之阵”。
(二)汪文宣:孤子、独子与知识分子身份的“弱质”性
作为家中的唯一的男子(小宣在学校并不和他们住在一起),汪文宣本该承担起顶梁柱的作用,在这个水深火热的外部战争环境下尽力维持好小家的安稳和谐,但是他没能做到,反倒在无尽的苦楚中越陷越深。这样的悲剧与他身为一个孤子、独子和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弱质”性密不可分。
汪文宣是一个早年丧父的孤子,父亲角色的缺失便理所应当由母亲填补,而汪母只有这唯一的儿子,她必须牢牢控制住对独子一切的管理权,事无巨细地为他操持一切。于是在母亲面前,即使已经人到中年的汪文宣仍旧活得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无法离开母亲的庇护去真正独立生存。小说中汪文宣不止一次地在内心独白中说“究竟还是自己的母亲好”的话, 当敌人打来大家惊慌失措时,他的第一反应竟是“我找妈去”,他的孝顺、懂事的背后也明显折射出潜意识中的“恋母情结”以及性格里不可独当一面的“幼儿心态”。
汪文宣虽然受过高等教育,在新思想的潮流中追求过个性的解放和自由, 但作为一个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其内心依然出于本能地背负着传统文化的重负。传统文化的特色是“阴柔”,缺乏阳刚之气,传统的儒家文化人格也正是顺从、容忍、中庸之道。“人类的原始情结演化为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并呈现为汪文宣们的行动。在汪文宣们的行动中埋藏着一种出于本能的集体无意识,这是人类的悲剧。”
在汪文宣身上,传统文化负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工作中的懦弱无能、处理婆媳矛盾中的暧昧心态以及在治疗自己疾病时瑟缩不前。归结起来即汪文宣信奉一种“忍让主义”,这与《家》中高觉新的“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如出一辙,是他们这类既接受现代性启蒙而传统旧思想又根深蒂固的知识分子所共通的“弱质”性。实际上,汪文宣已经丧失了一个男子汉起码的决断力,他羸弱的身体与萎靡的精神如一沟绝望的死水,面对问题时总是一副“痛苦”“惭愧”“泪眼斑驳”的模样,给自己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自身尚且需要人关心和照顾,哪里还会集中更多的精力来调节婆媳之间的矛盾。的确,人不能爱己,则无以爱人;不能自助,则无以助人。汪文宣这样一个丧失了血性生命力的人是无法在“无物之阵”中劈出一个出逃的缺口的,相反只会自掘坟墓,加速这个阵的形成、生长,使之越变越厚、愈演愈烈,最终彻底将他吞噬。巴金塑造这个人物未尝不是对腐朽生锈了的封建传统文化与民族痼疾的深刻反思。
(三)三个人物之间关于爱的占有的普遍矛盾
深深困扰汪文宣并使他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的“无物之阵”的形成原因,还在于《寒夜》中三个人物之间关于爱的占有的普遍矛盾,这个矛盾又纠结着人性深处的情感问题。曾树生明确地认识到汪母仇视自己的一个原因在于“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而她自己不是也一样不高兴婆婆分去她丈夫的爱吗?作为女人,为了争夺同一个男人的爱,她们费尽心机。他想对母亲说“既然你爱我,为什么不也爱她呢?你知道我多么离不开她!”这句话的潜在含义也包括对树生说“既然你也爱我,为什么不能再体谅一下我年迈的母亲呢”。
汪母年轻时丧夫,和儿子相依为命,她身上具有典型的“寡母心态”,“长期寡居的非正常生活,使她母性中的爱子情感发生了错位和扭曲。”外化为对汪文宣极端的爱和占有欲,甚至会在无意中流露出畸形的恋子倾向;相对应地,正如前文所述,汪文宣也有着弗洛伊德学说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深度依恋着自己的母亲。此外,他又多次明确表示他无法离开妻子曾树生,不能失去这个挚爱的伴侣。亲情与爱情双重的爱拧结在一起,密密麻麻分割不开,让汪文宣在母亲与妻子中间左右为难。
汪文宣既爱母亲,也爱妻子,出于对两个女人的爱,然而实际上却是无效帮助,结果不仅使母亲失望, 而且让妻子不满。母亲和妻子也都深爱着他,于是一个忙于家中各种琐事,即使年事已高还辛苦操劳、为儿子悉心打点好一切;另一个忙于工作和应酬,补贴家用负担小宣的学费。但她们婆媳的针锋相对又精准地刺痛着汪文宣的心,让他从身到心都疲惫不堪、备受压抑与折磨。三个人物之间关于爱的占有使得他们三者的精神负累都极为沉重。爱制造着仇恨,也制造着负担。某种程度上,汪文宣、曾树生和汪母与法国哲学家萨特《间隔》中的“他人即地狱”的人物关系具有某种相似性。人与人之间互相占有爱与自由,又彼此隔膜,无意间造成了他人的痛苦和自我的孤独。爱本身是没有错的,但霸权的爱就会变成沉重的枷锁,劈杀人的性命。正如鲁迅所说的“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的确,过量的、用错方式的爱是有毒的,反而比彻头彻尾的坏与恨来得更让人措手不及。汪文宣正是处于这样以爱为名的恐怖氛围中,渐渐演变为一种“无物之阵”的遭遇。身处其中的他面对的不是十恶不赦的敌人,而是至爱之人,于是他可悲地永远说不出对错,亦永远无法逃脱,像既定的宿命一般,除了默默忍受直至死去,别无他法。
三、“举起投枪”——打破无物之阵的方式
那么这个坚不可摧的“无物之阵”是否真的不能被打破呢?鲁迅在《这样的战士》中其实给出了他的答案。那个在阵中的勇敢猛士虽然战胜不了“无物之物”,但是他一次次举起了投枪。面对杀人不见血的残酷局势,他宁可力战而死,绝不缴械投降。在鲁迅看来,这就是更为神圣的一种胜利,打破宿命的束缚不在于结果成败与否,而在于为之奋斗的过程。
(一)汪文宣个人性格重建
老好人汪文宣打不破他的“无物之阵”,就在于他面对困境的无所作为、一味忍受,企图通过时间来自然而然地替他解决、处理好一切。每当妻子问到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或是局势会不会好一点之时,汪文宣的回答除了消极的一句不知道,便是含糊其词地说“总有一天会的”。其实曾树生并不是需要丈夫确切的答案,她只想得到丈夫语言、心灵上的支持与鼓励,并借此成为能够继续在黑暗狭小的生存空间里、在婆婆的百般刁难下苦熬下去的慰藉,可惜汪文宣连这点愿望都无法满足。他并非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恰恰对自己有很清醒的认知,“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但是他只停留在纸上谈兵这一步,反思得太多却没有勇气去实际行动,连抗议自始至终都是无声无息的内心独角戏。
对时局、工作、家庭,汪文宣均没有反抗。如前所述,他不是学不会反抗,而是从心底里害怕、抗拒反抗。因而如果他不重建自我性格,等待他的只能是悲剧。有的观点认为是病态的社会和战争损毁了汪文宣,但与他同处一个环境之下的曾树生却活得比他积极向上,在这个女人身上能看到健康、鲜活的生命状态与原始野性魅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巴金为何对曾抛弃家庭、跟随陈经理远走兰州的行为没有做出道德上的批判。沈从文曾说,“现代文明烛照下的都市人血液中缺乏了点野蛮的东西,因此显得过于病弱了。”这是“汪文宣们”的致命通病。拒绝怨天尤人的自我堕落,用尽全力去搏击命运带来的苦难,给死气沉沉的脉搏里注入希望,是巴金给予汪文宣打破“无物之阵”的方法。巴金为汪文宣安排的死亡结局代表了古老弱质性格的解体,而随着他身体消亡的另一个场景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这正是原始生命强力的象征,更是巴金对老态龙钟的传统民族性格重建的期盼。
(二)回归正常的爱——爱需要真诚、沟通、理解
其实不难发现,缠绕在汪文宣家中的始终是一些关乎日常琐事的矛盾,汪母和曾树生之间虽然各不相让,但又并非达到绝对意义上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程度。况且巴金一再强调他所塑造的三个人物都绝非恶人,况且他们是有“爱”来作为枢纽的。若三人之间能回归正常的爱,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沟通、交流,那么“无物之阵”便会迎刃而解。
汪母和曾树生没有血缘关系,缺少了母女的天然亲情以及共同生活所形成的相互理解和宽容的氛围。同样的一件事情如果放在母女之间便可轻易解决,然而若是婆媳之间就会产生隔阂,因为她们只是偶然相遇,相互之间更多的是不适或因传统的伦理规范所造成的对立,于是更需要相互的真诚理解。在战乱年代、困乏时期的背景之下,一家人更应该同进退、共患难,报团取暖,而不是分崩离析。汪文宣扮演好妻子与母亲沟通中的良好中介角色,用向上、积极的态度去解决她们之间存在的矛盾;两位女人能彼此做到爱屋及乌而不是因爱生恨,不再用所谓“无事的悲剧”来磨损、刺伤她们共同深爱着的汪文宣,多为他的处境着想,也能互相体谅各自生活中的不易。用最好、最健康状态的爱去打破“无物之阵”,营造和谐幸福的家庭环境。
《寒夜》作为巴金后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围绕“寒夜”这象征性的氛围展开,它不仅仅是物理时间,更是社会环境的“寒夜”和心灵体验的“寒夜”,使得人很自然联想到当时那个黑暗冷酷的社会和关于人性困境的话题。正如蓝棣之教授所言,“巴金在创作中所要探讨的问题,自始至终,都是人与现实的关系,探索人世间合理的生活,以自己的方式和体验提出人生里一些根本的问题。”历来的研究者都立足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笔者将《寒夜》的家中人隔膜与爱的占有的普遍矛盾与鲁迅作品中提出的“无物之阵”的引申义结合在一起阐释,并逐一分析此“无物之阵”的形成原因与解决方式,具有一定的创见性。对于其中关乎复杂人性问题的探寻也使得文本超越了一般的战争视角,而兼具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双重意义,从而更丰富了作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