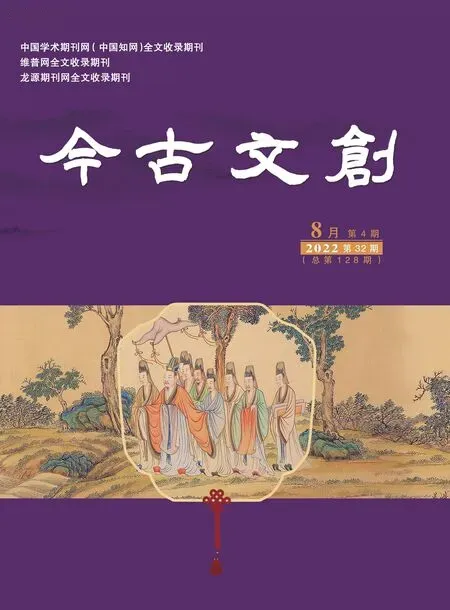关于“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的意义 ” 的一些思考
——以福柯、 怀特和詹金斯为切入点
2022-11-01刘森嘉
◎刘森嘉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4)
古今中外围绕历史学的哲学论辩都必然涉及关于“历史的意义”(包括历史对人的意义、对社会的意义和对其自身的意义)的问题,分析这一问题的概念框架和逻辑体系受到特定时空定位中历史的本质、性质、叙述模式、研究方法和解释策略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与之前的希腊人文主义、奥古斯丁主义、启蒙理性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的看法一样,都是基于特定时空定位中的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下形成的特定的文化逻辑。人类个体通过记忆建构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判断,而人类集体通过历史建构群体认同,这种认同是所有文明存在的意识形态根基。基于历史记忆和历史解释而形成的“思想气候”潜移默化的影响个体、群体甚至人类整体的当下生活方式和未来发展方向。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意义的讨论是在主客观条件剧烈变动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约1960年以后的西方社会)中对民族集体记忆、人的社会认同感和人类文明发展目标的重新思考和界定,这些观点的提出基于对旧有价值体系崩溃后的虚无主义的社会环境的分析和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走向的尝试性预判。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通过历史研究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层次的批判,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提出历史叙述不可能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基思·詹金斯(Keith Jenkins)从前期的支持后现代史学发展到后期的否定历史的意义。本文将以上述三个代表性的后现代历史哲学家为切入点,提出一些关于历史的意义的看法。
一、米歇尔·福柯:用“知识考古学”解构理性主义的社会秩序
基于高尚与低俗、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中心与边缘等二元对立逻辑框架的历史话语体系巩固了现代社会的思维秩序和权力关系。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通过解构主流历史观念进而攻击理性主义的社会秩序,他考察了“疯癫”与“理性”逐渐走向对立的历史过程,透过社会边缘群体被压制的人性和话语,揭露并批判上层统治者通过无形的真理和知识与有形的体制和机构不断强化意识形态控制的行为。福柯创建并运用“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的方法论(即从话语和陈述的维度重构历史的观念),分析历史进程中“权力”的运作机制,考察在不知不觉中被权力塑造的人性(包括人的思维、道德、情感、知觉、体验甚至潜意识等)和知识(在历史层面表现为历史整体论、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等),进而攻击被权力操控得更为广阔和深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和尼采分别从生产关系和伦理道德的层面对现代西方文明发起攻击,而福柯则通过考察人性进而攻击社会秩序。可见福柯延续了前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批判,但他的历史哲学是断裂性、碎片性且方向不定的,这使得他没有提出类似“五德终始”“永恒回归”或“阶级斗争”这样从宏观上概括历史规律的理论,也没有提出类似“上帝之城”“绝对精神”和“共产主义”这样指向性明确的概念范畴(无论是经验、先验还是超验层面)。事实上,这些宏大叙事或历史目的论恰恰是福柯和许多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激烈反对的,他们把这些理论看作是压迫性社会结构形成的思想根源。
由于拒斥系统的宏观理论建构,福柯透过历史的隐蔽面对社会结构进行的断裂性和碎片性的批判的力量是分散而不集中的,无法真正瓦解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根基。只有结论一致、体系完整且导向性明确的历史话语能够巩固秩序或引发革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真理永恒性、宏大叙事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后现代史学理论的社会影响力弱,事实上,其影响力并不亚于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历史哲学思想,只是这些影响并没有表现为某种指引人类的统一的强大力量。以福柯从1960年至1980年之间出版的一系列历史研究著作为例,它们的社会影响力在众多读者和研究者根据他们自身的不同的“视界”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解释和重新解释中不断扩大,却没有衍生出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凝聚成某种用以从根本上突破现代性危机的动力进而引发革命。
二、海登·怀特:历史叙述不可能避免的“意识形态”意义
1970年以后,客观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影响力不断扩大,但历史哲学却发生了后现代转向(即叙述历史哲学的出现)。在1973年的著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怀特通过研究黑格尔、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的著作,提出了历史叙事具备深层的文学性质和隐藏的哲学根基的看法。基于综合了哲学理论、文学理论和史学理论而形成的“元史学”概念框架,怀特认为历史文本的思想内核通过叙事语言中的情节设置、修辞技巧、论证方式、指涉对象、语言转义和意识形态等要素得以体现。
在《形式的内容》(The Content of the Form, 1987)中,怀特认为叙事既是“形式(form)”,又是“内容(content)”,形式和内容虽有所差异,但不可能完全区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立场就隐藏在形式与内容中。在《叙事的虚构性》(The fiction of narrative,2010)中,怀特认为历史叙事中包含的人的意志使得重构或再现历史的实践本质上是建构历史,“过去”被置入由历史书写者创造的情节化的历史叙事中。作者的情感、意志和立场在历史文本生成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文本完成后即独立于作者而存在,而读者用自身的情感、意志和立场对文本进行解读,最终在社会层面广为流通的历史话语及其包含的意识形态要素是在不断地“视界融合”中形成的。怀特从哲学层面对客观实证主义史学的攻击让人们意识到,在历史研究方法和历史学科定位上模仿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是不可能也不合理的。
在人类历史意识发展的初期,反映“过去”的著作(如《工作与时日》《荷马史诗》和《希波战争史》)往往具备一定的文学性、艺术性或神话性。但随着人类历史意识不断发展成熟,西方史学在哲学和逻辑学的影响下具备了思辨性的特质,才进一步对历史的本质、历史的规律、历史的目的和历史是否可知等问题展开深度讨论,历史著作的意识形态立场逐渐加强。中国古代的史书时常承担善恶评判、社会整合和伦理建构等任务,作为这些史书的理论指导的孔孟之道、黄老之学、阴阳五行或程朱理学等思想体系即是建构社会秩序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意识形态根基。因此,只要人类对“过去”还有了解的兴趣或需要,“历史”就永远不可能仅仅为了其自身而存在,历史著作的文化底蕴对人类精神的塑造及其哲学根基对社会存在的影响都将永不停止。
三、基思·詹金斯:否定“历史的意义”
詹金斯对历史相关问题的思考、论证和判断受到已经发展成熟的“后现代主义传统”中的福柯、鲍德里亚、德里达、利奥塔、怀特和罗蒂等人影响,属于综合性的晚期后现代主义。在《再思历史》(Re-Thinking History,1991)中,詹金斯认为西方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逐渐被基于不同的文化、利益和认同的各种亚群体并存的局面替代,而反映这些群体的过去的历史话语层出不穷,导致了“同一段过去被多种不同的叙述再现”的局面。詹金斯认为历史总是为了某种目的(通常表现为服务于某个群体)而被创造,因此客观主义的历史真相论已经瓦解,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成了主流。从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微观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史和环境史蓬勃发展并挑战制度史、贵族史、战争史和外交史的影响力的局面看,詹金斯的判断是正确的,社会结构的亚群体化导致了社会历史意识的多元化。
然而在《再思历史》出版后,詹金斯对历史的态度逐渐消极。在《为什么是历史?》(Why History,1999)中,詹金斯分析了历史与伦理的关系,认为关于已经消失的过去的知识是不可靠的,不可能为人类提供坚实的伦理根基,人类应该生活在时间之内,而在历史之外;生活在道德之中,而在伦理之外。在《论“历史是什么?”》(On'What is history?',1995)中,詹金斯主张“划清过去(past)与历史(history)的界限”,“大写历史(History)”和“小写历史(history)”都已经不合时宜。在《位于历史的极限》(At the limits of history,2009)中,詹金斯总结了他对历史问题的一些看法:历史认识论在哲学层面崩溃;历史不可能具备坚固的方法论;历史不可能回避权力和意识形态;历史学已经丧失社会影响力;历史不是人类进行深度思考的必要媒介;历史记忆是人类的负担。基于以上这些原因,詹金斯认为历史学已经变成无意义的伪科学,摆脱历史的束缚更有利于人类探索全新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并迈向最终的“解放(emancipation)”,除了过去之外我们不会失去什么,人类面对的是卸下了历史的重负的充满希望的未来。
在信息爆炸的当代,各种历史话语依然层出不穷,“过去”被强行赋予的异质性的描述、解释和意义越来越多,无论这些不断涌现的历史话语的初始动机是什么,它们在流通过程中必然被反复的利用、误用、滥用、误解、解释和再解释,而解释则由于解释者的不断改变而永远不会停止,这些新的异质性的解释又会衍生出新的话语。历史的社会影响力在这些话语和解释的无限扩散、不断再生和异化分裂中不可回避且难以把握。詹金斯看到了过多的历史话语给人带来的迷惑和负担,他的预想发展到了之前的历史学家从来没有到达过的极端,即完全否定历史学存在的意义。詹金斯不断地强调历史的各种负面影响,这些看法毫无疑问的有助于大家辩证地看待历史的意义(因为大部分历史学家更多的是强调历史的积极意义),但是他的乌托邦式的生活在历史之外的预想就目前来看没有办法通过实证进行检验,无论人类主观上是否希望,都必然生活在由各种各样的历史话语所构成的“意义空间”当中。
四、结论:不断发展中的“历史的意义”
本文以福柯、怀特和詹金斯为切入点,基于以上这三个部分的讨论,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是对客观实证主义史学的强烈批判和解构,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意义”的看法也是因人而异且不断变化的,这些批判、解构和变化在人类知识和社会的后现代状况下产生而又受其制约。然而发展方向多元、宏观把控困难且未来难以预测的21世纪已经无法用“后现代”甚至“后后现代”来定义——话语权力在国家之间和一国之内重新分配;人工智能有可能引发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文化在融合中打破了时空和风格的壁垒;多元化的大众意识冲击各国的传统意识形态;科技与信息革命进程加快并改变社会生活模式。在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各种排他性绝对主义意识形态都无法超出特定群体而广泛传播,也不可能真正全面或接近全面地反映世界形势,这些意识形态只能通过体制、机构和媒体的潜移默化的诱导而在部分人的头脑中相对稳定的存在。因此,后现代主义也只是多元意识形态中的一种视角,如果将其视为真理,那么后现代主义就会沦为一种新的排他性绝对主义而陷入自相矛盾。
在职业历史学方面,一些历史学家积极的关注人工智能、信息技术、认知科学、生物工程和量子力学等前沿领域的研究成果,从而打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壁垒,对人类心理演化、科技发展方向、生态环境变迁、社会政治运动、国际关系危机和全球经济运转等当今世界的重要议题展开全方位的深度讨论。而大众史学则通过通俗化、个性化、幽默化或网络化的叙述让历史和社会现实接轨,使其成为不断变化中的大众意识的重要载体。因此,无论从职业历史学还是大众史学的角度看,历史对人类的意义逐渐下降是不可能的,历史意识和社会秩序依然互为对方生成和变化的重要动因。职业历史学、大众史学和历史哲学的发展既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又在一些方面超越了后现代历史哲学讨论的范畴。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逻辑是后现代社会的产物,而到了无法再用“后现代”进行定义的时代,这些历史逻辑势必将成为传统观念,但只要人性没有改变,就无法完全否定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曾经显赫一时的众多历史逻辑中的某一种的合理性,因此尽管时代变迁,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唯一的不变就是变,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人类对历史的思考和历史对社会的影响都将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