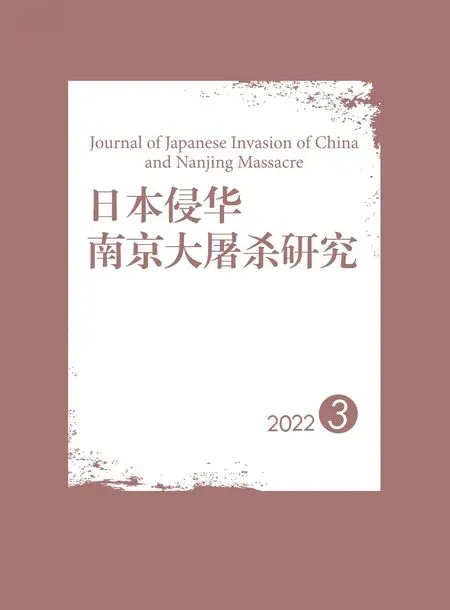基层视野下苏北民众的战时心态与选择(1937—1940)
——以《黄体润日记》为中心
2022-11-01郭丹
郭 丹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大片国土沦陷。苏北地处华北、华中两大区域交界处,又是津浦、陇海铁路的交汇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为打通华北与华中两个战场,确保铁路通畅,不断“扫荡”苏北运河线上的中国军队,并南北夹击徐州。面对日军的进攻,苏北国民党地方政权陆续迁移。镇江沦陷后,韩德勤亦率部退居苏北。由于日军在苏北的兵力较为薄弱,韩德勤即在苏北建立敌后根据地,以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这一时期,新四军则挺进苏南,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斗争。
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当局的扶植下,伪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下辖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在伪江苏省政府辖区内,各地又设立了伪县公署,以统治地方,同时还协助日军镇压各地的抗日运动。5月19日,徐州沦陷,时任江苏丰县代理县长的黄体润在其1937—1940年的日记中记载了从淞沪会战到丰县沦陷的详细过程,包括日军对苏北沦陷区民众实施的暴行和“宣抚”政策、国共合作及摩擦,以及战时民众的苦难生活和复杂心态。
本文拟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战时苏北沦陷区民众的心态与选择进行分析,并运用《黄体润日记》、台湾大陆同乡会文献数据库收录的《丰县文献》刊载的回忆文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辅以地方志、文史资料等,从基层视角考察全面抗战初期国、共、日、伪多方共存的苏北地区的社会状况,以还原战时民众复杂的心路历程及在个人利益与民族大义之间的现实考量。
一、危难面前的退缩与担当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12月,首都南京沦陷。此后,日军继续向苏北、皖北进犯,矛头直指徐州,一时间战火四起。相较于在炮火中惊慌失措的下层民众,国民党基层官员在与上层互动中能够及时获得战争信息,因而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准备。黄体润作为国民党基层官员,也积极备战。1937年,黄体润代表丰县赴庐山第二期军官训练团接受训练,其间,他学习了国防建设、战略战术等军事知识,接受了陈诚、戴季陶、汪精卫及蒋介石等人的抗战动员。他在日记中写道:
以前只知当一党员公务人员,应努力国家社会事业,但如何努力,及先后缓急之序,率多抉择不当,浪费心力。自经此次受训后,知救国建国之工作,莫先于抗日。抗日尤须统一意志,集中力量,有决心,有计划,有准备,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去努力,去牺牲。
随着战事的临近,一些殷实之家纷纷撤离丰县,从而加速了人口的流动,其中的主导者就是那些意识到战事紧迫的基层官员。这一时期,离职之基层官员和脱党的国民党员不在少数。武汉会战后,国民党清理党籍,要求全体党员重新登记,结果各地注册党员人数仅及全面抗战前的一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河南等省党员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
为了约束公务员的离职避难行为,1937年9月,江苏省政府颁发《战时公务员服务规律》,规定:“全省公务员,各应站在原有地位,尽忠职责,充分表现大无畏精神”,“除重病不能工作者外,一律不准请假,并不得托故辞职”。然而,当战事临近,生命受到威胁时,辞职避难是兼顾个人与身家性命的快捷途径,因此,即使有政府规定也收效甚微,辞职避难现象并未缓解。以丰县为例,“县府所有客籍职员,以时局紧张,均辞职他去”;“三区区长彭继亨,辞职照准”;“第二区区长卜宪章,一再呈请辞职,与县长商定,拟准其请”;“第四区区长夏慎言辞职照准”;“第一中队长李旭晨(辰)坚决辞职,未便再留”;“大队附韩野农,忽告病辞职”等等。1939年底军事委员会视察员关于苏北视察报告称:“苏北各县党务部,其稍洽舆望之人,大都避居内地……年少血气之徒,激于一偏之见,遂以为本党无望,因而投身于共产组织”。黄体润在日记中也称:“自时局紧张,吾县公务人员逃往外方及乡下者,几占十分之七八”。这些记述是当时丰县及苏北的真实写照。
与辞职人员相比,丰县原县长成应举无疑是“幸运”之人。1937年12月,江苏省政府任命董玉珏为丰县县长。董玉珏虽坚辞不就,然未获允准。成应举则“以重任得卸,快慰异常,催董局长(董玉珏)迅速接事,以便离丰他去”。
不论是为了留守抗敌,还是出于其他原因未能顺利撤离,许多留驻当地的人临危受命,黄体润即为其中之一。他将妻儿、兄弟姊妹送往内地投靠亲友觅职或读书,自己则坚持留在丰县。其妹黄体芬及岳父多次写信劝他撤离丰县,但黄始终没有离开。他在日记中表露了当时的心态:
一般知识届〔界〕恐日心理太甚,认为到处无安乐土,殊为笑话。余决不作后方流亡生活,已积极准备,万一乡土沦亡,即率领军警作游击队,作义勇军,抗战守土,以尽大中华民族一份子之义务。
在日记中,黄体润或许有自我标榜的成分,但他在全面抗战伊始便积极组织训练县义勇壮丁队以守卫县城,丰县沦陷后又组织常备队发起反攻夺回县城;在抵御外敌的同时,坚持消除匪患、惩处汉奸,几至丧命;在战争爆发、县长去向不明的情况下,临危受命任丰县代理县长,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政府非至万不得已不退出县城,即退出县城,亦决不离开县境”。时人回忆称:“县长董公玉珏率领撤出来的军警,在城东南的草庙附近,被向西撤退的中央大军冲散,一时下落不明(数月后由省府回县主政),秘书黄公体润毅然挺身而出,号召党政军警各级干部和热血青年,起来抗战救亡,重组地方武力,成立县常备大队,提示抗日除奸剿匪保乡的口号和任务,重新规复县政”。
黄体润虽然只是个例,但他代表的是敌后战场浴血奋战的特殊群体。在时人回忆中,提到了数百位坚持抗日、为国牺牲的国民党官兵,包括高级、中队和分队级干部和士兵,以及为抗日御侮满门忠烈者、亲兄弟共同殉难者。
相对于以维持生计为主要目的底层民众而言,受过民族主义教育的地方官员有更多权衡国家利益与自身安危的机会,虽然他们对国势、战事有较高的敏锐性,但从不同的选择来看,在这些地方官员身上依然体现出作为普通人的现实考量。国民政府内部虽然存在战斗力不强、抗战信念不够坚定等问题,但其抗战信念及家国意识并非荡然无存,亦不乏坚持抗战的爱国者。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定是个人的权利,苛责战争环境中每个人都须为国家牺牲,实则是一种理想化的认识。
二、暴力下的恐日与抗日
淞沪会战爆发后,苏北下层民众开始意识到上海的战事或将波及自身,由此产生了焦虑情绪,并通过地方官员和身边的知识分子以进一步获取与战争相关的信息。为缓解民众的忧虑,宣传爱国抗战思想,地方官员也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晚间村邻人等,因关怀国事,群来询问,告以国家已有准备,全国上下已精诚团结,将来胜利必属诸我国。”
此外,地方报刊对于这一阶段战局的报道也比较乐观,使得民众在一定时间内对战争获胜的信心增加,保持着相对积极乐观的心态。黄体润在日记中记载:
阅《丰报》,知前、昨两日,我空军在京沪杭镇一带应战胜利,两日统计击落敌机三十余架。上海我陆军夺回敌军司令部;南口我陆军毙敌五千余人,并克复商都。阅后,欣慰不已!邑人无不额手称庆也!
然而这样的欣慰并未持续太久,很快,上海、南京先后失陷。随着日军华中派遣军沿津浦铁路向北进犯,华北方面军也沿津浦铁路南下,战事逐渐逼近徐州。未待日军的飞机大炮惊醒苏北民众,逃难至此的难民对日军暴行的恸诉已在人群中造成巨大恐慌。黄体润日记记载:“据各方面观察,军人多贪财怕死;一般国民,人怀苟且,准备日奴来时好作顺民;知识份子,志气消沉者多,积极有抗日思想者少。”
有关日军的各种传言笼罩着苏北大地,恐日情绪迅速蔓延。听闻丰县县城岌岌可危,民众更是人心惶惶、草木皆兵。“晚间因有飞机声,一般民众疑为汽车声,一时谣传聂洼住有敌军,老幼妇孺,遂冒雨于黑夜间外逃”。一些年富力强的人为保全身家性命远走他乡或投靠土匪,而无处投奔的民众,只能以“你来我走,你走我回”的“跑反”方式躲避。他们听闻敌军将至,即简单收拾行李,逃往邻近村落,露宿一二日待情势稳定后再回家中。腿脚不便、安土重迁的老人听闻日军不能进入教堂,便纷纷躲进教堂,以致人满为患。也有一些人为了抵御土匪,家中藏有枪支,但听闻日军看到民众家中藏有武器易起戒心,遂扔枪弃弹,或将武器埋藏地下,更有村民为免遭日军袭扰,“偷做太阳旗备用”,以获得日军的“信任”。此外,有关日军性暴行的消息还引发各地民众的“结婚潮”:
在鬼子没来以前,早有人传说,鬼子不管到那里,第一件事就是找花姑娘,于是很早就掀起一阵赶快结婚的热潮。每个大小村庄上都增加了好几对新人……有很多在逃难中赶快结婚,一切从简,有的快到从议婚到嫁娶,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成了……还有好几对新人,都是坐在麦田里挽上头发,男女对着家长磕个头,就领起来逃难走了……仍有一些找不到对象结婚的女孩,而且多属大家闺秀,怎么办呢?干脆先把头发挽起来再说,所以拖着大辫子的女孩,几乎一个也看不到了。
丰县华山镇尹长庄村的尹联甲在回忆自己结婚经过时也说,丰县沦陷时由于地方沦陷、秩序混乱,定下娃娃亲的女方父母时刻担心女儿的安危,所以女儿在19岁时就嫁入尹家。当时尹联甲年仅15岁,还不懂事,羞惭生疏之余内心还有些害怕。面对日军抓“花姑娘”强奸的消息不断传来,民众产生恐惧心理,结婚不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为了免受日军性暴行的影响。
由此可见,虽然起初地方官员在进行抗战宣传动员时注意提升民众的信心,使民众保持乐观情绪,致使普通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轻视日军的实力,认为抗战并非难事。但随着战事不断迫近,各地难民纷纷逃难,同时日军暴行造成的恐日情绪愈加浓烈,民众对战争的体认也随之更加深刻,开始尝试采取各种方式自保。有条件的人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逃难,而一些走投无路的民众则显露出与敌“合作”以保全身家性命的倾向。
随着日军战线不断扩大,民众的抗战心态再度发生变化。投敌合作者的悲惨结局让人们开始重新看待做顺民、当汉奸的下场。在感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伤痛后,大家认识到妥协并不能保全自身,也不可能制止日军的暴行。黄体润在日记中记述:
有自滕县来者,云“敌兵未至曲阜时,有多数人谓日人尊孔,对圣人居必不骚扰,因往避难者,络绎不绝。及日兵进占曲阜,奉祀官孔德成之叔父孔某,即组织维持会,欢迎日军。讵知日军到后,首向孔等索青年妇女二百,供其奸污。孔等无以应令,各分返家中躲避,一入门,兽兵多人,正轮奸孔某之媳女,孔目睛日军兽行,遂羞愤自缢于客室中而死。”
现实的巨大落差使得与敌合作者仅存的幻想破灭,奋勇抗敌之民族情感在外部的冲击下再度萌生。黄体润在日记中记述:“济宁敌军残酷异常,闻已无人忍作汉奸,红枪会无极道亦变作义勇军。吾丰因迫近战区,见闻较切,亦无人存作顺民之想,与月前情形迥乎不同矣。”
对于生活在底层的民众而言,家庭、土地成为生活的中心,也是其个人抉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战事突然临近及日军暴行对苏北民众造成极大冲击,他们未及抚平心灵创伤,就不得不接受现实,在战争的夹缝中寻觅生存的空间。其实结婚并不能阻止日军的性暴行,在家中悬挂日本旗也无法完全获得日军的信任,当汉奸更不能对保护自身起决定性作用。在全面抗战初期,底层部分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尚不强烈,谁能保证他们的利益,谁就能获得他们的支持。虽然一些民众在战争初期自信于自身的抵抗力量,出于自保曾奋起抗争,但是在目睹悬殊的实力差距及日军的残暴后,发现抗争似乎不仅不能保证自身的利益,甚至对身家性命造成极大威胁。抗争未果,则开始寻求与敌相处的“平衡之道”,即通过“配合”来保全自身利益。这些生活在基层的民众没有意识到,无论是逃避、合作,还是抵抗,实际上都很难改变日军的战略。同时日军也没有意识到中国底层民众的这种心态,而是以武力震慑沦陷区的民众,使其服从日伪当局的统治。然而日军这种武力征服沦陷区民众的方式,使许多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油然而生,并进行殊死抵抗。
三、日军“宣抚”政策与民众轮转的抗战态度
丰县沦陷后,民众的生存境况发生巨变,其复杂心态也体现得更为明显。1938年5月14日拂晓,日军进攻丰县县城,中国守军与日军在城内展开激烈巷战。战斗中中国军队被冲散,随后从城南撤退。17日,丰城失陷,据当时东街参与埋尸的胡景瑞统计,城乡居民惨死者达300余人,其中以西关、南关、北关最多。日军进城后,大肆屠杀、纵火,城内尸体堆积,臭气冲天。黄体润在日记中亦记载了其率众反攻回城后所见情景:“房屋半被焚烧,商民绝迹,到处臭气熏人。亡国惨状,令人触目惊心矣!”
丰县沦陷后的当月下旬,日军便扶持成立了伪丰县治安维持会。伪维持会在征得国民党丰县政府同意后,同时为日军当局和国民党县政府服务。6月10日,日军撤出丰县县城,而7月10日又返回县城。为缓和民众的仇日情绪,日军“行为较前和善,无以前残杀奸淫焚烧之暴行”。此外,日军四处寻找城内的亲日者,以充当伪丰县治安维持会成员,扩大伪治安维持会的职能;成立宣抚班,并在公路沿线各村设置“爱路村”,散发“一人护路,万民享福”等传单;大肆宣传“打倒李贞乾百姓得过安然年,打倒冯子固人人都有安身处,打倒董玉珏良民太平皆欢乐,打倒黄体润除了万民恨,打倒卜昭贵人人都开同乐会”等反对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口号。
日军在实行残暴统治的同时,还对沦陷区民众开展所谓“宣抚”,采取怀柔政策,以达到以华制华、长期统治的目的。黄体润在日记中说:“城内之敌,尚有二三百人,欲积极建立汉奸政权,并向民众表示好感,怀柔政策,较毒辣手段为可怕也。”
随着苏北沦陷区的扩大,日军陆续在各地扶植伪政权。1939年,伪苏北行政专员公署成立,其下设的情报宣传部创办了伪《苏北公报》《兴亚月刊》等刊物,积极鼓吹其统治政策,如“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经济提携”“共同防共”等。伪《苏北公报》刊载文章称:
汪先生的和平主张是代表我们全国民意的,是替我们全国人民发表的声明,是建设新中国的基础,是东亚和平的政策。我们苏北民众决〔绝〕对的拥护汪先生的和平主张,誓灭匪共,誓除蒋贼,永久和日本善邻友好,保东亚和平,复兴中国,建设东亚新秩序。
日伪在“宣抚”过程中,矛头直指共产党和国民党,并试图利用中国农民靠天吃饭、依附于土地的现实进行宣传。伪《苏北公报》刊文称:
全国各地铲除旱魃蒋、共之声浪弥漫天地,上应天心,下顺民意。最近三日内京津沪汉各地已降甘霖,人人称庆。旱魃蒋贼早死一日则中国永免灾害,愿我同胞继续反共灭蒋。
日伪不仅攻击国共两党,还注重对基层民众的“思想改造”和“教育”。如在沦陷区创办学校,开设日语必修课,鼓吹“中日亲善、同文同种、共存共荣”“亚洲兄弟,联盟乃强,惠我新民,顺天者昌”等思想,试图将其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丰县人王献臣即受到日伪的宣传和影响,转而致力于丰县伪政权。王本为丰县旧军人,曾任福建军阀李厚基的第三师师长,北伐后退伍还乡。1929年王公玙任丰县县长时,王献臣的家产曾一度被查封,后虽发还,但与地方党政机关负责人的矛盾却未能缓解。1938年4月,王献臣被第九区行政专员兼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任命为游击总指挥部第四支队长。黄体润在1938年8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王献臣充当汉奸已证实,彼受委为伪苏北警防司令。”1939年6月,以王献臣为首的丰县伪县公署成立,8月1日,王献臣就任伪丰县县长职。然而不到月余,即有传言说王献臣因受日军压迫侮辱,牢骚不断,深感当汉奸之不易,有请地方士绅孙绍祖、王又参、李凤山、潘蓝生等代其向国民政府表达投诚之意向。由此可见,在日军“宣抚”政策下,部分乡绅的抗战立场摇摆不定。黄体润在日记中记述:
五楼乡乡长张小兰,久随王献臣,并在王部中颇有力量。近以王汉奸行为显著,颇有脱离意。今午约之晤谈,相见后,彼表示决不随之当汉奸,但亦不愿与之翻脸,仍愿率其武力,保持城东两乡治安。一般地主士绅,态度大抵如此。
地方士绅的选择,往往基于自身的利益。王献臣虽曾供职于国民政府,但因为利益纠葛无法真正认同国民党政权,故在得知日军扶植建立伪政权后,即选择脱离国民政府,投身伪政权。然而日军的压迫又使他倍感失望,试图再投向国民政府。张小兰亦是如此,其跟随王献臣能获得武装,以保卫身家性命,但又不愿背负汉奸之名,也不愿与各方势力作对,于是一面寻求王献臣的支持,一面又希冀获得国民政府方面的理解,并表明爱国之心。
《河北、江苏沦陷区视察报告及补救办法》曾概述了日军“宣抚”策略下江苏沦陷区的状况:
一、毒品、烟土、赌博遍地皆是。各沦陷区皆入无政府状态,一般流氓地痞任所欲为,红丸、白面、鸦片、吗啡、牌九、押宝、麻将、娼妓到处都有,而安分之徒则劫略之余难以为生。人民日趋堕落腐化之一途。
二、民众游击之实况。敌寇势力不及之地莫不有游击队之出现,组成份子不外流氓地痞,及当地土劣假借名义缴勒民枪,私增税款,甚至劫略财物、架人勒索、奸淫妇女、贩运毒品,种种罪恶罄竹难书,凡有枪一二十枝者即可称雄乡里,小民侧目寝馈不宁。且各游击队间因利害冲突或扩张势力时有火并之事发生。
三、沦陷区内之散漫武装无抗敌情绪。沦陷区内各散漫武装之活动不但实力不充,无抗敌能力,抑且无抗敌情绪。但扩充私人势力之心则甚炽。于是种种罪恶乃与流氓地痞之假借名义者无异。所谓扰民有余、抗敌不足,甚至有与敌暗通声气者。此种武力将来恐有被敌利用之危险。
四、各地民众之武装,既为不肖者所把持而为扰民之工具。在目前民众仇敌心里〔理〕尚炽,暂时可为若辈掩护,一旦民情因怨愤而离开则或被收买,或被歼弑者,属可能殊为可虑。
五、敌区优秀爱国份子所在多有,然不愿与坏人为伍,故不能发挥其报国精神。若不加以鼓励则在此环境之下意志易于消沉,或则迁避他处,则地方上所余者只汉奸地痞土棍愚民,加之敌人大量倾销毒品,毒化民众,不但抗战时得不到失地民众之助力,即失地收复后善后之处理亦将增加极大困难,民众生存之基础更受莫大之损失。
六、因此之故敌人乃乘机为收买人心之计,在江阴、无锡等地施行保护耕牛,散发蚕种等诱惑民众之工作。行之既久,则既有之仇敌心里〔理〕恐将日趋单薄而变为顺民。
七、沦陷区域民众与地方政府失去联系,长期以往亦足以消去人民对政府之信念或竟感失望。
测试结果表明:对于同一阶stokes光,温度越高,即ΔT越大,stokes光相对于BP的波长偏移量越大;对于相同的ΔT,阶数越高的stokes光的波长偏移量也越高。因此,理论上温度对高阶stokes光的输出特性影响更显著。
虽然各地情况不一,但有此情形者不在少数。沦陷区普通民众的生存选择十分有限,但不论如何选择,对大多数人来说,维护自身利益是其根本出发点。不具备反抗能力的普通民众,往往选择与敌“合作”,以保护身家性命和财产,而具有一定反抗能力的人,诸如地方乡绅富户,往往以保卫乡梓为由集合一些民间武装,组成所谓民众游击队。但此类游击队从本质上看还是服务于个人,没有组织纪律性,缺乏明确的行动目标,且对于游击队成员缺乏强制约束力。在成员之间利益不一致时,民众游击队更易分崩离析,甚至步入一条与组建初衷背道而驰之路。特别是很多人在意识到拿枪反抗将导致自己一无所有甚至失去性命,而顺从不但可以自保,还可能在伪政权中名利双收时,这些自发的武装自卫团体或由于缺乏反抗实力而选择归顺伪政权,或枪口转向自己的邻人,借机扩大自身实力,以攫取更大利益,成为独立于国、共、日、伪之外的地方武装势力。
起初,民众的“顺从”大多是由于认识到自身力量不足以抵御外敌后产生了恐惧心理,继而下意识地萌生了妥协自保的想法。不过日军占领之初的残暴行径不但打碎了民众对其仅存的幻想,还刺激了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很多人开始尝试反抗。但是沦陷之后,日伪当局推行的“宣抚”政策,再一次使部分民众的心态发生变化,其反抗决心受到动摇,对日伪的态度也从起初无意识的“配合”,转而成为有意识的“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在日伪“宣抚”的同时,国共两党的外围组织也在沦陷区积极进行抗战动员。在多方影响下,这种有意识的“合作”时常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长达7年的沦陷期间,丰县下层民众的心态与选择,随着战局及日军统治策略的转变而变化,不断在“妥协合作”与坚持抗战间轮转。从抗战全过程看,部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从觉醒到坚定并非朝夕之事,而是经历了数次从坚定到动摇,再到坚定的曲折过程。
四、国共合作及竞争中的民众选择
苏北沦陷后,国民党政权部分基层官员坚持在苏北动员民众,坚持敌后抗战。全面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在地方抗敌与剿匪的现实需求中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苏北地区国共两党军事合作的顺利开展,增强了民众的抗战信心,民众对抗战的态度也渐改以往的畏敌退缩,转而积极投身抗战。时人回忆称:
县政府秘书黄体润先生,基于义愤,决心联络同仁号召全县乡绅及热血青年,组军抗战,一年有成,建军五千。县立中学校长李贞乾先生,另树一帜,组成人民抗日义勇军,共与日寇周旋,黄、李交谊笃厚,一时传为佳话。
黄体润在日记中也说:“凤昌老板庄两亭,虽系商人,但对于国家观念极重,平时发表言论,多系劝人勿作汉奸,极力爱国,因以挽回沉迷之人心不少。”
有学者通过考察华北地区国共两党的军事合作,发现许多地方“国共两党这时上层将领关系不错,也影响到一些地区两党军政人员间关系不差……他们当时在地方政权、农民合理负担、武装民众、红枪会、军事配合以及除奸等许多实际问题,都能互相协商与沟通”。国共两党在丰县的合作也同样如此,双方在丰县地方政权建设、农民负担、民众动员、军事配合以及剿匪除奸等问题上联系密切,并组织了两支抗日武装,国民党方面为黄体润率领的丰县义勇常备大队,共产党方面为李贞乾率领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第二总队,同时两党亦共同组织成立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以动员和训练民众,坚持敌后抗战。在丰县保卫战中,两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协同作战。丰县沦陷后,两党武装又积极配合发起反攻,并在之后的剿匪除奸中密切配合。
在动员民众过程中,中共关心下层民众的利益,因而获得劳苦大众的支持。在宣传动员时,中共强调贫苦民众的革命性、批判富人的落后性,在经济政策和措施上,往往也造成地主、富农一定的经济损失,故在战时民众募捐、物资征集问题上,难免与富户产生矛盾。此时,国民党基层官员积极协助中共解决此类矛盾,以完成战争动员和物资征集。黄体润在日记中记述:
八路军向三四区富户募捐,因数目过钜,且多寡亦不公允,富户颇起恐慌,纷来找县长及我,请说公道话。因约同贞乾及县长,往八路军支队部,请彭支队长及吴政委,变更办法:1.富户捐款数目,由地方政府酌定;2.催收款由八路军直接;3.全县募捐数目,苏鲁支队二万元,挺进支队五千元。彭吴均采纳余等意见。
1937年底,苏北地区的共产党人及爱国人士组建了人民抗日义勇队,并兴办学校,对青年进行抗战教育。同时,丰县国民党基层官员也积极组织和动员民众坚持抗战。国民党丰县政府组织训练防护团、开办干部训练班,辅以深入民众、普及大众的宣传等活动,以加强抗战动员。1937年12月29日,在丰县县长董玉珏的组织下,国共两党成立了丰县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除人员构成由国共两党共同参与外,在舆论宣传方面两党亦相互配合。据李宗元回忆:
随着国共两党的合作由军事等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双方有了更大空间以发挥各自的作用。在合作过程中,国共两党有效整合资源,缓解了人力、物力、财力匮乏的矛盾,为地方抗战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增强了民众的抗战信心。
然而1938年后,国共两党各自在一些地方建立了基层政权,两党冲突时有发生,摩擦日益加剧。虽然两党对于抗战动员的目标尚属一致,但是合作已逐渐减少,并在宣传中强调各自的特点。同时,国共两党在对抗日军的“宣抚”政策,以争取民众方面的竞争逐步形成。
为了争取民众,1938年夏,国民党中央要求各地“密切联络人民,宣扬政府的意志,制止假借名义之扰民行动,并防止人民被敌寇之麻醉;抗敌方面不断的破坏敌人交通路线,略其辎重粮秣,刺探敌人动态,编造情报,并为收复失地总决战时之响应”,号召沦陷区民众“1.不买卖敌人货物;2.不供给敌人粮食及原料品;3.不使用伪币伪钞;4.不接受伪政府一切法令;5.不接受敌伪所施之教育;6.不接受敌伪之赈济;7.不为敌人工作;8.不与汉奸家庭往来”。从1939年起,国民党开始大量吸收党员,青年学生为争取的重点。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要求各县积极推进县党部的社会服务处工作,组织青年服务队、妇女服务队等,推进各项社会运动,加强抗战力量。
共产党则创办印刷厂,并于1939年发行《团结日报》(后更名为《湖西日报》)等,在湖西地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湖西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以增强民众的抗战信念。此外,共产党还深入民间,创办学校,广泛动员民众尤其是青年,宣传抗战,“讲解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党的方针政策及国内外的斗争形势……还编讲些红军长征故事和歌颂军民一条心、边区好风光等新的诗歌教材。……假期中,师生搞些抗日宣传活动,在各村大唱革命歌曲如‘抗日十大主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并在各村写墙报和爱国公约,把村里的抗日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显然,共产党在大力宣传抗日的同时也积极争取民众,这不可避免地与国民党在争取民众方面产生竞争和矛盾。
共产党内的“湖西肃托”事件,也成为苏北地区国共关系出现裂痕的催化剂,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的认知与态度。1939年,在中共苏鲁豫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干校青训班毕业分配时,学员间产生了“要不要服从组织分配,到自己不愿去的地方或单位工作”的热议,引起了中共湖边地委的重视。时任中共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调查后认为,学员产生不服从分配的情绪是由于干校中存在“托派”活动。这一认识得到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队政委王凤鸣(又名王鸿鸣)和中共苏鲁豫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认可。随之,肃清“托派”由干校开始并迅速扩大,使该党委大部分成员和全区区级以上党政军干部数百人先后被捕。曾与国民党地方官员合作抗日剿匪的多位共产党人,如王文彬、陈筹、李贞乾等也在被捕之列。此事从国民党基层官员的角度看来,曾同仇敌忾的故友的抗敌意志受到了所属上级组织的怀疑,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不免为其感到冤屈,对中共的信任也因之产生动摇。黄体润在日记中记述:
八路军后方办事处,前六七日间,在三区之于王庄,枪毙其干部陈雪楼、康文彬、孟宪真等四十余人,昨日闻又将王文彬枪决,并贞乾有被扣之说。查被枪决者,完全为丰沛萧单铜鱼各县之共产党干部。年来抗日,不无微劳,今竟借口脱匪罪名,施以毒手,使一般青年闻之,不无寒心之处。
李贞乾原为国民党员,曾是黄体润同事,两人在工作中因为性情相投,逐渐成为挚友。全面抗战期间,李因受共产党人的影响,认同共产党的纲领和宗旨,遂脱离国民党并加入共产党,以实现抗日御侮、保家卫国的志向。因李贞乾的缘故,黄体润对共产党一直抱有好感,并对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性颇为赞赏。在保卫乡梓的共同目标下,黄、李积极推动两党地方武装的合作,两人之间的友谊也在战争中不断升华。然而“湖西肃托”事件中李贞乾受到了极大伤害,黄体润等国民党基层官员对此难以释怀,对其遭遇愤懑不已:
贞乾自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联络青年,抗战以来,行将二载,心力交瘁。陈庄一役,两弟殉难,全家被掳,房屋焚烧净尽。其父母妻子,后虽脱险,然各处流离,几乎无以糊口。世人方以满门忠义称之,不料奸人竟以勾结日寇,拟用托匪二字冤杀之!公理正义之谓何?!令人不胜愤懑矣!
“湖西肃托”事件随即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介入调查后及时制止,并最终确定为冤案。包括李贞乾在内的诸多被定为“托派分子”的共产党员得到平反。但此事在地方的影响较大,中共湖西抗日根据地的一些区域或伪化,或为国民党抢占;地方各级干部不同程度受到冲及,致使一些地方的党组织一度陷入瘫痪;中共形象受到冲击,国共合作关系受到影响,抗战动员和宣传也受到一定的阻碍。
“湖西肃托”事件结束后,中共地方党组织努力修复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数次主动提出与黄体润等面晤。然而随着国民党高层调整了对共产党的政策,导致国共摩擦不断升级,国共两党在基层的合作再难维系,转而走向对立和摩擦。国民党利用中共“肃托”事件,进一步宣传其主张,与共产党争夺民众,在民众中散布共产党的负面信息及中共内部斗争的民谣,并动员各团体“防共”。同时,国民党还在党内以演讲、训话的方式抹黑共产党。国民党还阻止民众加入共产党并为民众“广开出路”,策动农会组织农民自卫队,并创办训练班,对农民、工人、商人,尤其是青年和妇女进行训练。在争夺青年方面,国民党除大力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外,还救济从沦陷区逃出的青年,吸收青年加入国民党,并选送优秀青年培训,以避免青年为其他党派所吸纳,藉以发展自身力量。
在丰县,由于国民党的一系列举措在民众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加上国民党利用“湖西肃托”事件丑化共产党,使其在争取民众的过程中取得暂时优势。但中共很快摆脱了“肃托”的消极影响,并积极争取民众,使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一些共产党人也努力维护党的形象。李贞乾获得平反后曾写信给黄体润:“我自己曾当众宣布我是托匪,但我的意思,宁肯冤抑而死,不愿使大多数人怀疑八路军,不满意共产党。”
虽然国民党在战时组织和动员民众方面曾做过努力,但共产党人以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和对信仰的坚守,以及持久抗战的信念,不断赢得民众的信任,并最终取得胜利。与此同时,由上也可以看出,苏北沦陷区一些地方经常呈现多方力量混杂的状况,不同力量在不同阶段往往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状态,而民众的选择也随之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
结 语
从基层视角考察战时地方社会时不难发现,抗战背景下生活在沦陷区的民众,其生活与心理并不完全围绕抗战,而是复杂得多。
作为地方官员,所能接受的战争教育及外界信息比基层民众更为广泛。这些人在面对战争时有比底层民众更为充足的时间思考战争和未来。坚持抗战者,临危受命、守护桑梓,而畏惧退缩者,亲日投敌,余下的人部分选择辞职,携家逃往内地或跑反。
沦陷区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选择往往是被动的,其心态和选择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对底层农民而言,家庭、土地是其生活的根本,也是生活的中心,他们无力远逃,部分人还缺乏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面对战争常会出现一定的短视和盲目,加上对自身抵抗力量认识的不足,往往成为战争中的被动群体,在各方势力此消彼长中摇摆。只要有合适的生存条件,部分民众会在生活压力下忍受外侮,寻求与日伪“合作”,成为沦陷区中的“灰色地带”。
全面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军事和民众动员方面的合作,为基层抗战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提高了民众的抗战信心。随着国民党加紧反共,两党裂隙扩大和摩擦频发,在这样的环境下,沦陷区民众由于缺乏统一领导,思想容易产生混乱。与此同时,日伪的“宣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沦陷区部分民众的抗日热情。就丰县来说,以现有资料看,国共双方在动员民众的方式方法上有相似之处,而双方争取民众的结果却较为复杂。当地部分民众的心态是在朴素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对和平生活的期待。
苏北地区多方力量的交融和碰撞,在全面抗战初期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复杂态势。不论是情感联系、利益牵绊还是政治导向,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苏北民众的社会生活及心态。审视全面抗战期间沦陷区基层社会时,应实事求是地对经历战争的苦难民众给予更多的理解。当给这些战争的亲历者足够的关怀,才能更深刻地体悟到为国家、为民族牺牲者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