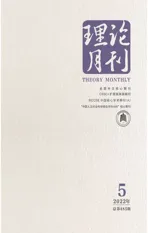明代丛书编纂者及其编刊类型选择释论
2022-10-31王玉超
□王玉超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明代丛书编纂群体庞大,既有身居要位的朝廷显官,也有隐居、从商的平民布衣,复杂的编纂群体使明代丛书内容庞杂,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明代立国之初至末年,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以及文学风尚差异较大,丛书编纂者受时代风尚的影响,编纂的丛书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不同地域的文化风尚和传统也不相同,使明代丛书编纂带有明显的地方文化烙印。丛书编纂者的身份差异使其在选择丛书子目、确立编刊方式和编纂体例等方面都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丛书编纂理念和丛书编刊质量。
一、明代丛书编纂者的时代分布与编刊初衷
据目前可知的明代丛书来看,明代丛书编纂存在比较明显的时段性。明初至弘治年间是丛书编纂的寂寥期,编刊数量不多,参与丛书编纂的文人学士极为有限,大多站在文化道统的立场进行编纂;正德、嘉靖时期丛书编刊兴起,各种丛书均在此时出现,丛书类型多样,丛书作用渐受重视,丛书编纂群体也愈发庞大,士夫文人、坊贾布衣都参与到丛书编刊当中;隆庆、万历以至明末可谓丛书编纂的繁盛时期,一方面,正、嘉时期编纂丛书的风气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坊贾主持编刊的丛书迅速增多,丛书的商业性、实用性成为此时的标识。
迄今可知生平或主要生活时期的明代丛书编纂者共计379 人,其中,明初至弘治年间有44 人。这一时期的丛书编纂初衷多具有强烈的道统性,都意在确立文化道统的地位,维护儒家思想的道统尊严,并借道统确立朱明王室的权威政治,这成为明初丛书编纂者的主流意识。
明代建立之初,军事上不断平定各种势力,政治上加强专制统治,制定礼乐典章,思想上提倡儒家道统,明初朝臣士人既有有志于用世、参与朝政者,也有退隐自保、著书耕读者,他们著书立说、编纂典籍都颇具明初的时代特征。明初丛书编纂者朱升、李质、胡广、刘定之、郑若曾、徐节、徐绅、张瑄、叶盛、游潜等,无不在儒家道统的意识之下编纂丛书。李质精通经史,编纂的《三苏文抄》多选史论和政论文章;张瑄,正统七年进士及第,授刑部主事,《明史》载其“有能声”,历职期间,发廪振贷、陈抚流民、上疏献策,颇有政声;朱升曾拜江敏求、金斋谕、陈栎以及理学家黄楚望门下,为池州学正时,整治儒学,后隐居讲学,其曾建议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后为翰林院学士兼东阁学士,与儒臣修《女诫》,以防后宫干政,制定明朝礼乐制度,注《周家仪礼》《礼记》《小学》等儒家经典。明初丛书编纂者汇集儒家经典和各种注本,借以推行儒经道统,他们继承了儒经学术的发展,也呼应了明朝得国最正的新朝格局。朱升编纂《小四书》,序称:“此四书者,四字成言,童幼所便精熟,融会宇宙在胸中矣。然后循序乎六籍之学,归趣乎孔孟之教,究极乎濂洛之说。”这部丛书适于初学之用,其编纂意在作为研习程朱理学的途径,从政统的角度来看,朱升提倡道德治国,此书也明显地呈现了崇儒和遵理的思想。
明初丛书编纂者崇儒遵理的思想决定了丛书编纂的道统意识,道统意识维护了明代的政治统治。明初丛书编纂者具有强烈的文化道统思想,注重丛书编纂的功用性,他们的政治功用意识主导着丛书的编纂,使丛书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显得颇为密切。明初胡广被称为“学究五经,古今术艺皆毕览之”,他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奉敕纂修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魏裔介认为:“后之欲窥圣人之道,非《集注》何由进?非《大全》,则《集注》之微言奥义亦几不明。”高攀龙称:“二百余年以来,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于是。”三部“大全”选辑了儒家经典的重要传注,确立了儒经阐释的标准,更重要的是规范了明代科举考试的内容。这类丛书的编纂符合明代科举制度的推行,关系到明初立国之本务,明太祖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借科举以得能臣,凭儒经以养贤德,明代很多丛书的编纂都与之相应,明初的“四书”“五经”注本丛书多属此类,如徐节编纂的《五经集注》、张瑄的《研朱集五经总类》等,都有借儒经丛书确立道统,进而巩固政统之意。具有实际功用的丛书备受关注,很多具有军事才能、政治作为的朝臣也开始参与了丛书编纂,一些文集类的丛书同样以道统和政统为核心,譬如明初的奏议类丛书有叶盛的《叶文庄公奏议》、徐绅编刊的《秦汉书疏》,重在借奏议的功用性实现百官文人的治平之道。
目前可知的主要生活在正德、嘉靖年间的丛书编纂者约125人。此时的丛书编纂者身份复杂,朝臣仕宦、学者文人、藏书家、书坊主都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丛书编刊,其中具有多种身份的编纂者也大有人在。正、嘉时期复杂的编纂群体使丛书呈现了多样性,经、史、子、集各部典籍的汇编层出不穷,丛书编纂的主观目的较为明确,或为宣传文学主张,或为传播地方文化,或为保存文献典籍。
经过唐代古文运动和宋代诗文革新运动,明人对待文学的态度颇为严正,尤其正、嘉时期,丛书编纂者多有自己的文学主张和所属的文学流派,他们似乎随时可以将道统、政治、喜好与文学建立起关联,因此,这一时期的集部丛书编刊特别盛行。丛书编纂者在明代的复古声中开始了集部丛书的编纂,其编纂意图较为明确,集部丛书大都带有宣传文学主张、扩大文化影响的初衷,编纂者在各自的文学流派和主张下,或汇辑秦汉文集,或编刊唐宋诗文,借以提倡效法前朝文学,恢复古代文学的精神。秦汉派、唐宋派大力推行“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宗法唐宋八大家,于是,总集类丛书如《李杜全集》《唐李杜诗集》《李杜诗选》《韩柳文》《十家唐诗》等相继问世。郭正域编刊《韩文杜律》,“欲矫七子摹拟之弊,遂动以肥浊为诟病。是公安之骖乘,而竟陵之先鞭也”。郭正域博通载籍,自守介然,不满七子派的摹拟,借集部丛书转变文风、确立主张成为他编纂丛书的主要动力。这部丛书具有较大的影响,在流传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一定的功用,清代四库馆臣认为明代公安派、竟陵派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韩文杜律》的影响,接受了郭正域的主张,所谓“骖乘”“先鞭”是也。其他如方弘静的诗风接近王、孟,编纂了《十家唐诗》。李齐芳学诗于李攀龙,一尊李攀龙为“后七子”的领袖地位,应和王世贞的复古倡导,赞同二者继“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继续推行文主秦汉、诗宗盛唐的主张。李齐芳“学诗于李于麟,尽得其学”,并在李攀龙的影响之下编纂了《李杜诗合刻》。正、嘉以来,唐宋八大家的文集类丛书迅速风行。八大家文章选本篇幅有限,似不能全面反映唐宋古文的精神和气韵,相较而言,总集类丛书便具有一定的优势。其中,通代总集类的八大家丛书尤多,如《历代文选》《顾太史评阅唐宋四大家文选》《八大家文选》《文纪》《重刻韩柳欧苏文抄》等相继编刊问世,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明代末年,不断有八大家文集类丛书编纂。
明代总集类丛书成为文学主张和观念传播的重要方式,也是古籍文献保存的方式之一。在明代刊刻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明人很快意识到丛书保存文献的强大功用,这成为此时文人学者编纂丛书的主要目的。嘉靖时梅鼎祚编纂了一系列的丛书,《八代诗乘》《历代文纪》等均卷帙浩繁,其《历代文纪》包括《西汉文纪》《东汉文纪》等,清代四库馆臣评其“捃摭不遗,其采辑亦云勤矣”。其他如袁褧的《金声玉振集》、范钦的《范氏奇书》《天一阁奇书》、吴琯的《古今逸史》等都有意借丛书保存典籍。吴琯《古今逸史·自叙》(万历年间刻本)云:“(《古今逸史》)即古之作者,典历纪略、匠构不同,志录纪书,标目各异。要其旨归,未有不捃摭缥缃,总会丘索者也。”《金声玉振集》包括明代史料四十余种,学术论著十余种,保存了很多明代初年的边疆、水利、海运等资料,对明初相关史料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万历朝至明末可以说是明代丛书编纂的繁盛期,不仅丛书数量多,类型也最为全面,各种类型的丛书均在此时大量编刊。这一时期的丛书编纂群体发生了较大变化,各层文人与书坊商人的联系更加紧密,各种丛书呈现了有别正统、通俗广识的特征,明代后期的文化和文学下移,使丛书编纂开始考虑接受群体,丛书编纂者具有一定的知识普及意识。
明代一直推行的科举制度,以及科举考试中的大量落第者,使明代下层文人群体比重增大,学术和文学呈现出明显下移的趋势。明代后期的图籍纂刻多有考虑接受群体,迎合士人大众的编撰和纂刻意识较为强烈,譬如明人李诩曾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今(隆庆、万历年间)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李诩所言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明代万历以来坊贾编纂、刊刻典籍的情况颇为常见;二是明代后期编刊典籍往往考虑接受群体的需求,明代后期丛书编纂即与之相同。明代后期丛书编纂具有大众接受的知识普及意识,受心学末流、李贽“童心说”等思想的影响,经学呈现出异于程朱学说的阐释内容,私人修史的现象和杂史杂传著作不断出现,自抒性灵的文学主张、轻俊灵巧的晚明小品流行于当时。其中,儒经类丛书多用于指导举业应考,如《经言枝指》《学庸正说》等;杂史类丛书具有逸闻性质,如《逊国逸书》《名臣宁攘要编》《皇明史概》等;戏曲类丛书发展尤其繁荣,如《阳春六集》《白雪楼二种》《元曲选》《古杂剧》等,戏曲类丛书大兴足以表明,明代后期戏曲文学兴盛,引领一时新的文学风尚,呈现出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学化趋势。总体来看,明代后期丛书编纂大多力求在趣味与知识、奇闻与学问之间找到契合点,最大限度地扩大其普适性。
二、明代丛书编纂者的地理分布与编刊类型
明代丛书编纂者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其地理分布与明代各地经济的发展正相关,与各地文化风尚相呼应。据目前可知籍贯的明代丛书编纂者统计,各地数量居首的是浙江,有100人,其次是江苏、安徽和上海,分别有80人、30人、17人,长江
①明代丛书编纂者的籍贯按今天地理行省划分名称。下游吴、越两地的人数,约占明代丛书编纂者的大部分;再其次是江西和福建两省,分别有42 人、25人;北方又居其次,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京和陕西,共计63人;两湖、两广、云贵川和海南等地数量较少,共有39 人。明代丛书编纂者的地理分布符合明代刻书的地域性,明人胡应麟曾言及:“凡刻之地有三,吴地、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稀)。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可自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明代刻书本身就存在明显的地域性,明人对此多有总结,各地刻书或多、或精、或“直重”“直轻”,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地的文化风尚。明代丛书编纂者的统计数字表明,江浙是明清时期的富庶之地,文化兴盛,丛书编纂也领先他省;北方诸省文人多秉持儒学传统,丛书编纂的类型以经史居多。各地思想文化、文学风尚差异较大,丛书编刊也呈现出一定的倾向。
明代江浙一带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江浙文人群体扩大,江浙文化的繁盛可以说是这两地丛书编刊大兴的主要原因。就科举乡试贡额而言,洪武朝时,“直隶贡额百人”,后“洪武十七年诏不拘额数,从实充贡。洪熙元年始有定额,其后渐增。至正统间,南北直隶定以百名……庆、历、启、祯间,两直隶益增至一百三十余名,他省渐增无出百名者”。南直隶科举乡试贡额始终多于他省,进士及第人数也居明代首位。浙江亦复如是,明初洪武年间首次开科取士,浙江士人即占1/4,《万历野获编》记载:
洪武四年辛亥,始开科取士,时自畿辅外加行中书省,凡十有一列,中式者一百二十名,而吾浙得三十一人,盖居四分之一。而会元俞友仁,复为浙西之仁和人。首藩首科,盛事如此。是时,刘基、宋濂、章溢、王祎辈,俱浙人,一时同为开创名臣,宜其声气之相感也。累朝教育,遂以科第甲海内,信非偶然。是科独湖广一省无一人中式,而高丽国中一人。
明代江浙科举及第人数众多,整体的文化风尚浓厚,文学素养较高,明代丛书编纂者多为江浙或寓居、游历于江浙之人。
江浙文人群体呈现出多层次性,决定了江浙文化的多元化,经学儒术发达、文学形式多样,丛书编纂的类型也较他省更为复杂。自宋代刻印业发展以来,古籍繁盛、撰著颇丰,时至明代,江浙一带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藏书家,纷纷兴建藏书楼,清人俞樾在《书丁竹舟武林藏书录后》中称:“武林山水甲神州,文物东南莫与俦。缃帙缥囊富藏弆,香梨文梓竞雕锼。”藏书家、刻印商的身份使他们更易编刊综合类丛书,昆山叶盛、吴县都穆、金陵焦竑、华亭陈继儒、钱塘胡文焕等,都是享誉一时的藏书家,他们也编纂、刊刻了大量的综合类丛书,丰富的藏书为他们编刊丛书提供了有力保证。缪咏禾认为:
杭州地区藏书家特多,在丰富的藏书支撑下,出现了大量聚零为整的丛书,著名的有《格致丛书》《唐宋丛书》《汉魏丛书》《古杂剧》《重订欣赏编》《稗海》等。杭嘉湖一带因此被称为“丛书之乡”。
其他类型的丛书也是形式各异,譬如传统史钞、诸史考订类之外,像《逊国逸书》《名臣宁攘要编》《皇明史概》等杂史类丛书也颇多编纂;传统诗文集之外,戏曲类丛书也成为当时人热衷编刊的内容,譬如《鞠通乐府》,即在昆山腔发展的基础上编纂而成。
明代江浙丛书编纂的多元化充分体现在文学流派和主张的突破上。从明代初年的吴中四才子,到明末兴起的小品文,如果从文学流派的角度上讲,似乎在文学史上主导一时的前后七子、唐宋派都不是以江浙文人群体作为主体,但江浙文人的个性却最为鲜明,其中既有诸种文学流派的响应者,也有不拘一格的独立者,文人融通诸家、汇聚各派的主张和观点,提倡文学的多样性、不宗主一家一派的意识尤为明显,《词坛合璧》《八大家文钞》《明四家文选》《十六名家小品》等各种通代类集部丛书相继问世。总体而言,明代江浙文人编纂集部丛书往往不限于某一文学流派,不拘于影响较大的复古派,不排斥魏晋文学的骈辞俪句,不薄当世的明人著作,明代江浙文人具有兼容的文学意识,为文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文化环境与丛书编刊相互关联,呈现出明代江浙文学风尚的多样化。
明代江西和福建的丛书编纂者人数仅次于江浙,在目前可考的编纂者中,江西有42 人,福建有25人。总体而言,在江西学术的影响下,丛书编刊带有明显的理学色彩;福建书坊参与刊刻较多,丛书编刊呈现鲜明的市民特征。
江西自宋代以来文化鼎盛,人才辈出,官学发达,书院林立,至明代仍呈现一派繁荣气象。朱国桢记吉安“讲会”时述及:“江西讲会,莫多于吉安,在郡有青原、白鹭之会,安福有复古、复真、复礼、道东之会,庐陵有宣化、永福、二卿之会,吉水有龙华、玄谭之会,泰和有粹和之会,万安有云兴之会,永丰有一峰书院之会,又有智度、敬业诸小会,时时举行。”明代江西科举及第人数多,官至公卿宰辅者甚众。至明中叶以来,江西文人流派蜂起,台阁、江右、临川等文学流派纷纷引领一代的文学风尚。《明史·儒林传》载录了大量的江西籍人物,理学家尤其多见,阳明学理论在江西得到广泛影响和传播,不同的学术思想都包容于此,譬如吴与弼(江西崇仁人)开创了“崇仁学派”;胡居仁(江西余干人)师从吴与弼,尊崇程朱理学,主张居敬教化思想;罗钦顺(江西泰和人)继承并改造程朱理学,主张“理气为一物”;胡广、张吉、陈凤吾、刘元卿、杨时乔等都有编纂丛书,诸如《篆文六经》《五经集注》《周易古今文全书》等,这些丛书或汇辑程朱、陆王的理学著作,或综合经注、儒理论说各种内容形式,与北方的传统儒学不同,江西呈现出尊程朱、崇阳明的理学特征。明代江西丛书编纂者多具有较为强烈的传道意识,汇辑各家思想著述的编纂初衷较为显著。
福建的丛书编纂者数量虽不及江西,但由于福建自宋代以来刊刻业就十分发达,有明一代的丛书编刊也较为繁盛。《八闽通志》载:“建阳县麻沙、崇化二坊,旧俱产书,号为图书之府。麻沙书坊元季毁,今书籍之行四方者,皆崇化书坊所刻者也。”万历《建阳县志》记载:“崇化里书坊街……每月俱以一、六日集。……书坊书籍比屋为之,天下诸商皆集。”福建刻书广布天下,尤其建阳、麻沙、崇化各地都有闻名于时的著名书坊,熊氏、余氏刻印闻名天下,尤其万历年间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刻书繁盛,这几乎成为明代福建刊刻的标识。更值得关注的是,市民阶层是重要的接受和阅读群体,这成为福建书坊编纂、刊刻图籍的重要动因,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福建的丛书编刊。福建丛书编刊以营利为目的,日常实用性得到了充分体现,一方面指导举业的儒经注本较多,譬如陈琛的《重刊补订四书浅说》、余象斗的《刻九我李太史十三经纂注》都有指导举业的作用,陈琛乃明代理学大家,发展了朱熹学说,《四书浅说》重在儒理阐释,至万历年间重刊补订时,《四书浅说》作为举业用书的性质取代了儒经注疏性质。明代福建丛书编纂、刊刻的另一特点是医书药典、家居日用之书较多,譬如吴琯编刊的《薛氏医按》、余象斗刊刻的《必用医学须知》、萧京的《轩歧救正论》等,这些医药丛书不仅意在汇辑各种医案、药典,更在于切于日常实用。
明代北方总体的图籍编纂和刊刻不能与江浙相比,编纂的丛书数量也比较有限,因此,笔者将黄河流域诸省均归为北方区域进行整体考察,包括今天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北京各地。就目前已知籍贯的明代丛书编纂者统计,山东有18人,河南18人,河北11人,陕西8人,山西7人,北京1人。明代北方各地的丛书编纂者以官员居多,丛书内容以经史和独撰类为主,丛书类型相对单一。明代程朱理学作为科举选才的唯一思想,大有一统学术之势,阳明心学兴起后,其影响遍及全国南北,但总体来看,秉持程朱理学或以程朱为核心的学术风尚更为明显。明代永乐年间薛瑄(山西运城人)创始的河东学派,传承朱子之学,“究心洛、闽渊源,至忘寝食”“日探性理诸书,学益进”,引领了北方的学术风尚;王廷相秉承张载的气一元论,对宋代以来的理学、心学均有研判。明代北方的学术传统往往成为典籍撰著的根本属性,丛书编纂也带有传统儒理的功用性,诸如张瑄的《研朱集五经总类》、吕柟的《吕泾野五经说》《宋四子抄释》、白璧的《经史音义字考》、朱鸿谟的《五经旁训》、曹珖的《大树堂说经》、宋廷训的《六经正义》《校刻五经四书正文》等,大致形成了经史为主、类型单一的丛书编刊特征。王安舜在《刻〈五经旁训〉小引》中说:“又可以会圣人之心于羹墙梦寐之先,即正、即旁、即文、即训、不增、不减,其取精也多矣,读者得之。”强烈的治平思想和传统的儒学理念,使明代北方士人颇多关注经史儒术,且大多在这一范畴内编刊丛书。
三、明代丛书编纂者的身份差异与编刊风格
明代丛书的类型、体例、质量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纂者的身份和旨趣。身居高位者注重丛书编纂的事功性,优游林下者汇编闲赏游戏著述;有志治学者注重丛书的经史学术性,倾心文学者则拣选诗文审美著述;典藏图籍者注重丛书的文献性,纂刻贩书者则编刊畅销盛行的著述。其实,各种类型的编纂者其身份标识并不完全界限明确,身居显位者有志于治学,有志于治学者也喜好典藏图籍,只是从他们的思想和身份意识上来看,占据主导的思想在编纂丛书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古代文人具有强烈的身份意识,丛书编纂也不例外,同样带有编纂者的身份标识。查考明代丛书可以发现,科举及第并居官者编纂丛书往往注重事功性,有益致用是编纂和衡量丛书优劣的重要标准,对于山林优游者而言,闲情雅趣则可以作为丛书编纂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明代相当一部分丛书编纂者具有科名和职官身份,有益致用的事功性是其编纂丛书的主要动因,儒经治致、史料政书类丛书多出于这类编纂群体之手。他们编纂丛书、选择子目与其居官任职恰好相应,完全能够呈现其身份特征,诸如翰林编修陈仁锡编纂了《五经旁注》;国子监祭酒吕本、王锡爵、朱国桢分别有《皇明宝训》《春秋左传释义评苑》和《皇明史概》;内阁首辅高拱编纂了《边略》,军事家郑若曾有《郑开阳杂著》,两部丛书都与舆地有关,关系着国家军事和治理。其他官居六部侍郎、主事之职的编纂者也有相关丛书,如刑部侍郎张昺有《小史集雅》,礼部仪制主事沈节甫编纂了《纪录汇编》,太常寺少卿陈与郊有《檀弓考工记辑注》等,丛书编纂内容与职官身份于无形之间存在着关联。沈节甫编纂的《纪录汇编》史料性极强,其中涉及英宗被俘之事具有重要的补史作用,意在借“参正史以垂一代之典谟”,这与他任职务本、遵礼守约的为官治化之道相契合。陈仁锡于天启二年殿试第三,授翰林编修,署国子司业事,再直经筵,《明史》记载:“仁锡讲求经济,有志天下事”,他编纂《五经旁注》正是出于注儒经、讲经筵之用。在这类丛书编纂群体中,他们编纂的丛书或为经注,或为史集,科名官职的身份意识成为编纂丛书的直接动因,决定了丛书的功用性。
优游林下的编纂群体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有的是去官隐退,有的是科举未第,闲居优游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更愿意编纂赏闲一类的丛书,江山之助、文人雅趣都成为他们编纂丛书的动因。诸如名满吴会的王穉登编纂了《风光十种》,华淑有《清睡阁书二十七种》,张如兰的《闲中八种》,项元汴的《蕉窗九录》等,这些清闲、艺术类丛书颇有随性编纂之意。茅一相的《茶谱后序》可谓清赏宣言,称:
大石山人顾元庆,不知何许人也。久之,知为吾郡王天雨社中友。王固博雅好古士也,其所交尽当世贤豪,非其人虽轩冕黼黻,不欲挂眉睫间。天雨至晚岁,益厌弃市俗,乃筑室于阳山之阴,日惟与顾、岳二山人结泉石之盟。顾即元庆,岳名岱,别号漳余,尤善绘事,而书法颇出入米南宫,吴之隐君子也。三人者吾知其二,可以卜其一矣。今观所述茶谱,苟非泥淖一世者必不能勉强措一词。吾读其书,亦可以想见其为人矣。用置案头,以备嘉赏。
茅一相的序言基本勾勒出明代优游林下的雅士生活图景。他们彼此之间交往甚多,不慕势利、不恋世官,厌弃世俗、雅好结社。顾元庆与茅一相等人结为“泉石之盟”,优游山林之中,隐居闲适,寄情于书画、茶饮,茅一相编刊的《欣赏续编》即优游之作。晚明以来,以山林之客的身份参与到丛书编刊十分流行,陈继儒、屠隆、周履靖、赵宦光等无不以山人雅趣标示着他们的隐士身份,清闲玩赏、小品艺术等丛书纷纷编纂而成。其实,对于很多去官隐退者而言,居官理想未得实现,满腹的失望无以释怀,优游林下、清闲谈艺或许成为他们弥补和掩饰伤痕的最好方式。
明代丛书编纂者的学术喜好决定着丛书子目著述的选择,大多有志于治学的编纂者倾向汇辑经史著述,重视校勘,编刊的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倾心文学的编纂者则往往汇编带有审美性质的著作,其丛书编刊的文学意义值得关注。
明代丛书是在宋代综合类丛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早在东汉颁布熹平石经之时,带有丛书性质的著述就已出现,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明代相当一部分丛书编纂者具有学者的身份,有志经史、精研学问,他们往往出于学术资料汇编的目的编纂丛书,邓元锡、刘元卿、曹端、舒芬、杨时乔、穆文熙、薛应旂等都是声名卓著的大儒学者,他们编纂的丛书在明清学术发展史中颇受重视。明代刘元卿是著名的理学家,与邓元锡、吴与弼、章潢合称“江右四君子”,他创办书院,复礼研经,悉心讲学,“务以求道为事”;薛应旂归居后,专事著述;穆文熙精通史略,史籍记载“少颖悟,经籍无所不窥,尤尚节义……浩然而归,所居有逍遥园,坐起一编,文藻蔚然,为一代名家”。这些编纂者无不悉心经史、精研学术,他们以经史学问为终身事业,既重修身也重事功,诚如《先秦诸子合编序》中所云:“诸子之言皆所以载道,惜乎后人弗能知也;诸子之术皆足以致治,惜乎后人弗能用也。读《合编》者,尚其有经世之思哉!”可谓言行著述不悖学术精神。邓元锡“研精性命,卓有领会而不为玄谭眇论、高自标榜”,其学问研究精深,为人谦逊,编纂的丛书《五经绎》“其思深,其识正,其指远,其词文,出入今古,贯穿百氏,不主一说,不执一见,而卒自成一家言”。邓元锡编纂丛书的学术性与其人品、学识一样,都备受赞誉。丛书编纂与学者的学问见解相一致,如杨时乔不喜阳明之学,辟之甚力,尤恶罗汝芳,曾上疏斥罗汝芳称:
佛氏之学,初不溷于儒。乃汝芳假圣贤仁义心性之言,倡为见性成佛之教,谓吾学直捷,不假修为。于是以传注为支离,以经书为糟粕,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逾闲荡检,反道乱德,莫此为甚。望敕所司明禁,用彰风教。
其学术见解不同于阳明学,认为罗汝芳杂入佛氏之学,有碍风教。杨时乔编纂丛书《周易古今文全书》即汇辑诸家理学传注,其序中言及“四圣五儒合而功重全《易》矣”。杨时乔汇辑理学诸家注本,重在阐明《易》义,反映了他的治学方向,与他的学术主张一脉相承。这些丛书内容选择精良、重视文本校勘,多为明清学者所器重。
明代集部丛书数量居各类丛书之首,通代及历代总集、家集、戏曲类丛书都有大量编纂,这得益于明代庞大的文人群体。明代文人兼有居官、隐逸、治学、优游等各种类型,但他们总体倾心于文学,有着自己的文学主张和思想、文学审美与批评意识,因此,文人群体编纂的丛书大多呈现着明代不同流派的文学面貌和发展进程。查考明代丛书的文人编纂群体,几乎各个文学流派的主将都编纂过丛书,如后七子的王世贞编纂了《宋四大家外记》,唐宋派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选》,竟陵派钟惺的《钟伯敬评秘书十八种》,小品文代表黄汝亨编纂了《合诸家真评先秦十五种》等。归有光编纂的丛书即围绕唐宋派主张,文集去取悉从其文学主旨,《顾太史评阅唐宋四大家文选》《唐宋八大家文选》等无不是唐宋派的文学范式。钟惺以编选和评点经史、诗文选本著称,其中丛书编刊数量甚多,《钟伯敬评秘书十八种》《合刻五家言》《诗归》等相继纂刻。至明末复社文人张溥在文学上再次力主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倡导文章务为有用,“解经论文”“砥行博闻”,并编纂了《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文学选本能够反映不同时期选家的文学观念,明代文人群体编纂的丛书也具有考察文学发展演变的功用。
明代文人多在一定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思想下编纂丛书,尽管在底本、校勘等文献方面达不到清代学者的要求,但对于明代文学的发展和研究而言,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在明代刊刻业十分发达的条件下,丛书作为文人群体推行文学主张的重要方式,也在无形之中记录了他们的心路历程,承载了文学发展的重任和记忆。
明代刊刻业迅速发展,图籍编撰、刊刻和发行较前朝都相对容易得多,图籍典藏随之兴起,藏书之风在文人群体中甚为流行,很多具有职官、学者和各层文人身份的丛书编纂者,也同时兼有藏书家的身份。由藏书到刊刻,明代文人具有了藏书家和书坊主的双重特征,但究其本质又与商业书坊主不同。明代藏书家所指的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图籍典藏为主,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图书收藏和纂刻者;书坊主则指以营利为根本目的的收藏、编纂、刊刻和发行图书者。由于这两类群体图籍经营方式不同,他们编刊的丛书便存在内容、质量、形式等方面的差异。
明代藏书家与书坊主的身份界限其实难以划分得非常明确。明人多有藏书喜好,譬如袁褧屡试不第,以藏书、刻书著称,家中筑有藏书楼,所刻图书镌“嘉趣堂”“石磐斋”等,在《六家文选》中自称:“余家藏书百年,见购鬻宋刻本《昭明文选》,有五臣、六臣、李善本、巾箱本、白文、小字、大字,殆数十种。家有此本,甚称精善。”袁褧家族藏书百年有余,多鬻购收藏精本、善本,叶德辉称其“明人刻书之精品”。沈节甫居官自正,喜好藏书,建“玩易楼”,自称“余性迂拙,无他嗜好,独甚爱书。每遇货书者,惟恐不余售,既售且去,惟恐其不复来也。顾力不足,不能多致,又不能得善本,往往取其直之廉者而已,即有残阙,必手自订补,以成完帙”。且不论沈节甫藏书版本优劣,他藏书、订补、编次书目,足见其保存文献之功。祁承爜喜抄书、藏书,曾记述“手录古今四部,取其切近举业者,汇为一书,卷以千计,十指为裂”,祁承爜同样抄藏图籍数量甚多,自称“如十余年来所抄录之书,约以二千余本,每本只约用二食,纸张二三钱,亦便是五六白金矣。又况大半非坊间书,即有银亦无可买处”。据此可见,祁氏藏书中抄本图书更具价值。其他如叶盛潜心著述,朱彝尊在《菉竹堂书目跋》中称:“文庄中外敭历不遑宁居,而见一异书,虽残编蠧简,必依格缮写,储藏之目,为卷止二万余,然奇秘者多亚于册府。”叶盛藏书亦多精本、秘本。明代文人多喜藏书,筑藏书楼、抄校图籍已司空见惯,借藏书之便刊刻图籍也不足为奇。顾元庆藏书万卷,刊刻图籍质量颇高,就其编刊的丛书《顾氏文房小说》来看,版本价值极高,鲁迅先生编纂《唐宋传奇集》时多采录其中作品,或者用顾氏本进行校勘。享誉一时的毛晋,尤喜藏书、刻书,兼有藏书家和书坊主的身份,毛晋藏书有文人雅好特征,注重版本,多藏精善,同时他也刻书销售,刊刻的诗文选本、戏曲丛书等都深受市民大众的欢迎,但是不同于专门的书商坊贾,藏书家身份使其刊刻图书质量颇精。由于藏书家的典藏之故,从藏书到刊刻,很多藏书家也拥有了自己的书坊,如范氏天一阁、毛氏汲古阁等,于是部分文人的图书从家刻逐渐成为坊刻。明代书坊林立,书商蜂起,很多坊贾形成了自己的刊刻特色,如闵氏、凌氏的朱墨套印,凌氏套印本图书流行海内,陈继儒称:“自冯道、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版,布衣毕昇再变而为活板,闵氏三变而为朱评。”但是,更多的书商坊贾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诸如胡文焕、熊大木等以书坊经营为生,纂刻图籍更多考虑的是阅读和接受群体,编刊的丛书也符合市民大众的需求,譬如《寿养丛书》《格致丛书》等。
就明代藏书家和书商坊贾的丛书编刊来看,藏书家编刊丛书往往基于自家的图籍典藏,注重所录子目著述的底本、校勘及其内容的完整性。譬如袁褧编刊《金声玉振集》,共61卷,收录子目著述50种,各种著述均内容完全,未经删减。沈节甫编纂《纪录汇编》,共计216 卷,收录子目著述123种,其中包括摘选收录的子目著述,对于摘选的著述内容,他均在著述题名中一一注明,如《古穰杂录摘抄》《震泽长语摘抄》等,这与明人随意增删、另立书名的情况截然不同。沈节甫编纂丛书的态度十分严正,对文献保存的准确性也非常负责。以毛晋为代表的兼有藏书家和书坊主身份的丛书编刊群体,既注重文献保存,也考虑阅读群体的接受,胡震亨在《津逮秘书·题辞》中说:“余以虞山子晋毛君,读书成癖,其好以书行,令人得共读亦成癖。”毛晋编刊丛书多有以飨同好之意。毛晋编刊丛书带有书坊主的特点,但更多仍是藏书家的文人特征,《藏书纪事诗》引钱受之《隐湖毛君墓志铭》称毛晋:“通明好古,强记博览,壮从余游,益深知学问之指意。”正因“深知学问之指意”,汲古阁刻本图书才多为精本、善本,毛晋编刊图书往往自撰题跋,交代版本源流、编纂成书,并进行学术评价,编刊的丛书多校勘精良,收录足本,序跋不遗,文献价值较高,与书坊以营利为目的的编纂和刊刻不可同日而语。查考大多书商坊贾的丛书编刊以部头大、卷数多为主要特征,譬如《重辑说郛》《说郛续》《广百川学海》等,但删减割裂、伪托讹误随处可见,令人无法卒读。
明代丛书编纂群体呈现明显的时代性、地域性和身份特征,明代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风尚影响了丛书的编纂初衷,尊崇儒理、务实政教的功用和主张以及文献保存和文化传播功能,成为明初丛书编纂者的主流意识,也成为他们编刊丛书的重要动力。江浙、闽赣和北方的学术传统、文学流派和市民文化,使丛书编纂带有明显的地方文化烙印。同时,明代丛书编纂者具有明显的身份意识,丛书编刊理念和质量、编刊内容和方式的选择,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身份定位。明代丛书的编纂群体较为繁杂,尤其明代后期出于坊贾之手的丛书,编刊粗率、错讹百出,使明代丛书颇受非议,查考明代丛书编纂者的时代、地域和身份特征,并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探讨编纂者与明代丛书质量良莠不齐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必要,这实际也是客观评价明代丛书、充分利用丛书文献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