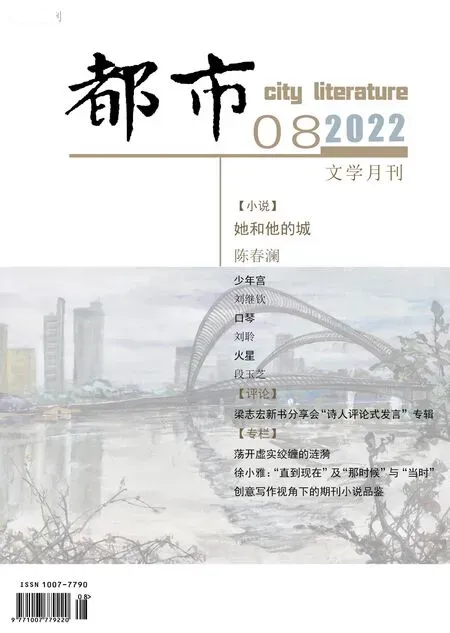食羊闲话
2022-10-22文张扬
文 张 扬
烟火万重,风味万千,羊肉不可方物,以其独有的肌理与滋味占得食界一席,又如鲜花灼灼,粉蝶自来。
故里湖鲜河鲜池鲜已少尝得,于是客居地的羊鲜便成为后来居上者。初食羊肉时,懵懵然而不知其味,因老家以往鲜有养羊者,市面上也几无羊肉可售。从长江之畔移居淝水之滨,对于羊肉渐由被动接纳转向主动寻食。淮南淮北一带养山羊和黄牛居多,饭桌上的羊肉、牛肉若非盆装,便是用海碗、大盘盛放,热气腾腾之状匹配着主人好客的蓬勃热情与豪爽劲头。某一年冬夜,在北方,人已入睡,却被当地的朋友叫醒,上了车身体仍打着哆嗦,车子忽左忽右转几圈,停在一个油乎乎的馆子门前,入店后坐不多久,伙计费劲地端上两大搪瓷盆红汤羊骨头,羊骨头香气滂沱,友人不顾吃相一通啃食。红烧的羊骨头用搪瓷盆装盛,应和了其时环境与氛围。若用精致的青花盆来装,当小心手脚,似也不宜高言大语。
见过生猛的北方汉子,一双手不知洗净没有,直接抓起生羊肉片,稍一仰脖,肉入口中,腮帮略鼓动几下便吞咽了,其时,他手里还攥了一把蒜子,吃肉的间隙,他一粒一粒剥去蒜衣,跟吃花生米似的往嘴里送。生吃鲜肉活物于我断断不敢。有一次在山中,当地人捉了一条菜花蛇,要取蛇胆,说可以明目,我连连后退,不敢触碰。恐有寄生虫藏身,诸如醉虾、生三文鱼片我都不大敢吃,就是牛排也需煎得全熟。如此,自然少些口福。
昔有怪力乱神,身着黑袍的人念念有词,忽地张口,狠狠咬断一只冠红毛亮的公鸡脖子,惹了满嘴的血与毛。在多个戏说版本里,四阿哥尚未称帝为雍正前,一次狩猎途中饮了鹿血,顿时浑身上下奇热难耐,情急中与一名宫女行了男女之事。男人饮鹿血之状未有亲见,鹿茸酒倒是浅尝过几口,不觉有何异样。若吃什么补什么,人欲强身健体自然简便。
风和草绿,羊撒欢吃草,吃草的羊会反刍,反刍是羊的常态。食物链上,羊是主动者,也是弱弱的被动者,为人宰杀或被虎狼捕食。吃了羊的人或有“反刍”,羊肉是我“反刍”食养之一,于我,“反刍”可算作一种回溯,回溯个体食物图谱,对阳光风雨乃至万物都心存感恩,愈加爱物惜物。人为刀俎,鸡鸭牛羊变成一道道菜品,进入腹腔、四肢与血脉,化为一股股浊气、清气与力量。荤素穿肠,不过是物质与能量兜兜转转。换言之,滋养人的每种食物,都有了和光同尘的献身精神。
云白天高,坡上的羊似油画家的笔在画布上游走。高寒山区的羊以自然放养居多,放养前被标上记号,即便羊群留宿山上,也不大担心走丢。与黑色沾边的吃物自有其独特内蕴,乌鸡、乌鱼、黑米、黑芝麻、黑木耳、黑猪肉等,向来为人所看重,山区放养的黑山羊也显得出挑,其肉质细腻,用来做羊肉锅,当称得上“一锅鲜”。云南师宗的朋友说,每至火把节,当地家家户户提早起灶烧水,宰羊炖羊,吃杀羊饭比吃杀猪饭还欢腾。数次去往云南,都未吃上杀羊饭,算是缺了一份食缘。对于地道的草原上的羊肉,可用清水煮熟,不蘸酱也不撒孜然粉,寡口吃都会齿颊留香。出自草原的绵羊肉质较肥厚,膻味可淡到忽略不计。常见的山羊肉质紧实,膻味较大,宜烧烤、做汤。我的一个长辈清炖或红烧泥鳅,从不剖肚掏肠,而是直接将满身黏液的泥鳅放入锅里,他若活到满街飘着羊肉气息的今天,说不定也会专拣膻味重的羊肉店光顾。
曾吃过一家羊肉店,里外装潢近似文艺场所,入店可见明厨亮灶,供食客挑选的有羊肉种种,食客们吃得嗨了,如在苍蝇馆子,顾不得斯文,只管扯起嗓门,叫老板再来一盘羊肉。与同窗年年有聚,同窗是乡友,也是故人,甚或胜似亲人,聚餐时常点涮羊肉或手抓羊蝎子,羊肉的热力助推着人的情绪发酵,人在少年,梦中不觉;人至中年,滔滔不绝。滔滔不绝正是眼饧耳热之际,听一曲《似是故人来》较为恰切,词句里有人生况味,这况味非男女之情可解,亦非同窗之谊、手足之情能一言蔽之。
吃烤全羊时,众人团团围坐,起先都戴着一次性手套,吃到兴起,手套被扯乱,个个腮边见油光,屋子里的喧哗声趋向高分贝。一年深秋,在天山脚下,胡杨绚烂如幻,我们白天飞奔数百公里,晚间尝到紧实而喷香的馕坑肉,奈何我不擅酒,不敢抓着大块羊肉畅怀开饮。
寻常时日,喝一碗羊肉汤就可温胃提神。遇有食欲不振,来一份酸汤肥羊也能刺激味蕾。羊肉近似面食,吃法多样,烤羊头、烤羊腿、红烧羊蹄、白切羊肉、爆炒羊羔肉,色泽诱人,而牛肉、猪肉、鸡肉等,连吃几顿,可能就会口舌生厌。
姑苏之地的藏书羊肉有其清香味,皖北萧县的丁里羊肉似较厚实。丁里镇地处皖苏鲁豫交界,好办伏羊节,伏天吃伏羊,饕客趋之若鹜。早些年到萧县,县城饭店一律面食当家,一个南方人在异地整天吃不到米饭未免愁肠百结,幸赖当地羊肉花样百出,借此挡一挡饮食惯性。
涡河是老子、庄子都曾涉足过的一条河流,位于涡河之南的涡阳有座小山,名叫嵇山,山上残存着一个墓穴,当地人称之为嵇康墓。十多年前走上嵇山,但见山体特别瘦小,采石的人在忙个不停,山坡一丛意杨树里拴着几只山羊,羊毛无不脏兮兮的。阴云密布的天空下,山羊们东张西望,有一只羊眼里水汪汪的,似噙泪花。这一幕顽固地留存于大脑皮层,消减了行程中面对香气四溢的羊肉时的惯常食欲。
羊在山上健走,也在人的身体里低吟。楚楚动人的羊,如人一样通情,会感念哺乳之恩。元季赵子昂平生爱画马,曾破例为友人作过一幅《二羊图》,清帝弘历极爱此画,并于画上题诗,中有二句:“跪乳畜中独,伊人寓意长。”郎世宁采用中国人“三阳开泰”的说法,绘过《开泰图》,画中一只小羊低头食草,另一只小羊半跪,忘我地吸吮母羊乳汁。北宋苏汉臣也画过《开泰图》,骑羊的童子与古松梅花下嬉戏的群羊一派花团锦簇,富贵气逼人。个人尤喜陈居中所作的《四羊图》,羊的观望之悠闲与茫然、打斗之俏皮与灵巧,让人如在画中笑看,又或化身为当中一只,在野坡溜溜达达。画中的羊、石刻的羊、陶制的羊、玉雕的羊,有着插翅的奇妙构图,也有精细的写实塑造。在江南一个博物馆里,我看过陈列的青瓷羊尊,这件三国乱世中的瓷器,做工上并非随便拿捏,羊的整体造型圆润饱满,四足贴地而跪,抬首张口,似咩咩而叫。
舌尖上的滋味是一种即时性体验,而人生起伏冷暖自知。原本与教育打交道的朋友,去年转行到外地做生意,不久又归乡承包了一片果园与水塘。在他的水塘里,鱼们浮潜游戏,懒懒散散的一群羊走在岸边的草地上。尘土满面他也不顾,一心期待果实挂枝。将近年关时,他宰羊捕鱼待客,屋子里弥漫着混合的气息,有腥味和乡土气,也有浓郁的香气与喜气。
另一位玩石头的中年人,隔三岔五招饮,石头行情降温后,其攒局热情逐年消减,近年连打照面都少了。且说那些年的聚餐,他选的多是北方人开的饭店,有一家做的羊肉食过难舍。间隔一段时间未去,再次寻味,却见招牌已换作别个。后来,在一个会场遇到那位羊肉馆的老板,知悉他的店面只是搬至别处,着实一阵惊喜,似收藏人寻寻觅觅,于街巷深处的铺子里重拾旧珍。
天南地北的食物风一样流转,蒲公英般散落。陕西臊子面、云南米线、东北饺子、徽州刀板香、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山西晋家门的烤羊排、六安的风干羊肉锅之类,纷纷传入我所居住的城市。大别山里,六安人家招待客人好以七八个锅子摆满一桌,其中多半不缺风干羊肉锅,这锅子以手工千张丝铺底,放风干羊肉及切成段的葱蒜、干辣椒,一锅香辣的风干羊肉嚼劲十足,齿间难免不沾羊肉丝。腊月里的阳光晒到头顶上,颇似裹身的棉袄暖烘烘的,三两同好边走边谈,随机进到一家土菜馆,把菜单翻来覆去,目光落在一锅羊肉上,烧热的羊肉锅白气袅袅如雾,各人吃得额头沁汗,把肚子都撑得隆起。正所谓店无须大,人不必多,菜不一定丰盛,对味就好。
独自外出觅食时,我喜欢到专门做羊肉汤的餐馆里去吃一碗羊肉面,外加一两个蒙城烧饼或泡馍就能管饱。梁实秋说,用大蒜黄瓜佐烧羊肉面,美不可言。我尚未尝试过梁氏所言的吃法,只在吃羊肉粉丝时配过凉拌黄瓜,店家于一盘黄瓜中撒入芫荽,淋了辣椒油,蒜及醋放得多了,吃起来满嘴不清爽,不如自家的凉拌黄瓜入口。
上夜班的那些年里,每逢夏夜,时常会就着啤酒,嚼几根羊肉串,啃几块羊排或羊蝎子。犹记那时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同事,爱吃热炒羊杂,每回还要上一份羊㞗。其滋补几何,恐难说得明白。《儒林外史》中,金东崖在杜少卿面前卖弄学问,说羊枣即羊肾,曾晳虽嗜好羊枣,其子曾参不忍食羊枣,在于他爱惜羊的性命。杜少卿笑话他这般解释属于穿凿附会,而且是“太不伦了”。羊枣实为一种小小的圆形果实,形如羊矢,也称为羊矢枣。曾子吃羊枣未免会想起逝去的父亲,故而不忍再吃。
爱逛菜市的汪曾祺深有体会,认为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就会感到生之喜悦。热热乎乎的一碗羊肉汤,足可令人心花怒放,个中三昧,大体在于所蕴含的入世之心与朴素的生存之道。推而广之,羊肉之类美食就是平常人家的星辰大海。
食物的味道是物质的,也是精神层面的,并有哲学上的道理。吃菜喝汤间隙,可旁观同一时段、同一地点就餐的他人模样,亦可借机反观自我,一点点咀嚼、消化、回味现实境遇里的沉郁、纠葛或欢喜。
平日来不及做饭或懒得洗手下厨,要么就近吃碗兰州拉面、淮南牛肉粉丝,或者点一份羊肉千张粉丝。在家里做羊肉火锅多选周末或节假日,火急火燎有负羊肉之鲜。我所住的小区附近,数年前沿街百米内即有三家羊肉馆,四季食客不断。当中有一家内设较清洁,白汤羊肉火锅做得尤其拿手。那紫铜锅甫一端上桌,就见细碎的蒜叶、芫荽隐现在白汤里,待到白汤翻腾,羊肉片、白菜俱已滚熟,拿勺子舀一碗,一小口一小口嘬下,满口生香而腹中温润。碗筷叮叮当,足足喝下三四碗后,续些白汤再吃,只觉得脚底生热,浑身舒泰。去岁,住所旁又新添一家羊肉馆,一天到晚兼做烧烤,以致烧烤的香气与焦味充塞整个小区。这真是让人纠结,日日美味横陈眼前,也日日担心着入肺的空气质量。
随遇所安,有肉吃肉,无肉剔骨也香。苏轼有一副宽大心肠,贬到哪里就在哪里寻食觅物,生火煮釜。谪居惠州期间,一次他路过卖羊肉的摊位,见摊主将羊脊骨丢弃喂狗,当即求了些,带回洗净、煮熟,继而撒盐炙烤,吃起来以为如食蟹螯,还不忘写信调侃弟弟苏辙,说他整日饱餐公家饭菜却不知羊脊骨多么好吃。与苏东坡交好的韩宗儒同样喜食羊肉,某一日急吼吼差人送信给苏轼,苏大学士却未提笔回信,仅让来人转告韩宗儒,说“今日断荤”。苏轼当真是幽他一默。这韩宗儒一旦得到苏轼手迹,即刻去换羊肉,图个口腹快活。今日谁能易字解馋?怕是少有。
师长石楠先生赠我一帧扇面,钤了一方吉语闲章,曰“吉羊”,“吉羊”通“吉祥”,青铜古器上就有这般铭文。与羊相关的字,含有物态人情民风,投入吉利祝愿与美好寄托,如“为君洗手作羹汤”的羹,如“东舍捉鹅鸭,西舍烹豚羔”的羔,如“姜是老的辣”的姜,如“鱼鲜饭细酒香浓”的鲜,如“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羞,如“井花水养石菖蒲”的养,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美,如“上善若水”的善,如“吉事有祥”的祥。羊脂玉,世间尤物,和田玉中的极品,物稀而市价高;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肤白而温润,如凝固的羊脂油。家中冰箱常年放有羊脂油,做饭烧菜时如不慎烫伤,取出羊脂油敷上,可减轻皮肤疼痛感与受伤程度。
有人问我笔名“羊咬鱼”何意,亦有人喊作“鱼咬羊”,不知是打趣还是一时拗不过口。坊间有一道菜品,名为“鱼咬羊”,做法并不复杂,将切碎的羊肉装入鱼肚子,封口即可烹饪。关于“鱼咬羊”有一则传说,清代徽州一位山民赶着几只羊,要过新安江支流练江,所搭乘的船较小,一只成年公羊被挤落舱外,扑腾几下随即没入深水。山民无可奈何,心疼地过江而去。羊沉水后引来鱼族,群鱼争食羊肉,水中动静不小。摇着渔船经过的渔民见状,立马撒网捕鱼。回到家,渔民拿刀剖开一条鱼肚,只见鱼腹内装满羊肉,连剖几条都是如此,便乐滋滋将鱼洗净、封好刀口,连同鱼腹内的碎羊肉一同红烧。起锅后,鱼酥肉烂,不腥不膻,汤味尤其鲜美。消息传出,效仿的人有增无减。在徽州,吃过石鸡、毛豆腐、火腿肉、臭鳜鱼、一品锅、腌笃鲜,羊肉却极少吃得,遑论“鱼咬羊”这道菜。萧县也有人做“鱼咬羊”,只是这道菜有另一个故事版本,说的是孔子领着弟子周游到了萧县这里,饥肠辘辘时,弟子为他讨来小块羊肉和几条小鱼,急急忙忙一锅烩了,未想到羊鱼合烹的味道几乎鲜掉舌头,这一做法就此流传开来。这两则故事里,鱼羊同锅为菜,均是巧而又巧。
“鲜”由鱼与羊两字组成,一为水中精灵,一为陆上生物;鱼饮水,羊吃草,各有气味,气味源自的本体亦即气味所依托的肉身,莫名地被混搭在一起。宁愿相信这是一种巧合,巧合中藏着天机妙趣,一如酒的来源。人世间玫瑰带刺,神话中狐仙伴有妖气,“鱼咬羊”可谓腥与膻的强强对垒,经由阴阳相克相生,化为餐桌上的郁郁芬芳。造字的先人大概尝得个中滋味,才有神来之笔。
老子出口更妙,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古时祭祀先人,奉以鱼腊鲜兽,今已倡导鲜花寄思。鲜及酸甜苦涩麻辣咸香臭,各对应一种滋味定性。设若滋味至今混沌一团未有分解,人间生活将会多么寡趣!界定滋味的人有如天才,但非坐井观天之人,也非桃花源中人。羊肉之鲜,河豚之鲜,菌菇之鲜,芳草之鲜,雨水之鲜,有同有殊。鲜而又鲜,鲜到极致,人人所求。
写有古老文字的羊皮卷隐遁于历史深处,唯有羊肉的气息仍在尘世间的锅碗瓢盆上萦绕,在一代代人的经络中纠缠。饮食如风,风从四面八方来,又向四面八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