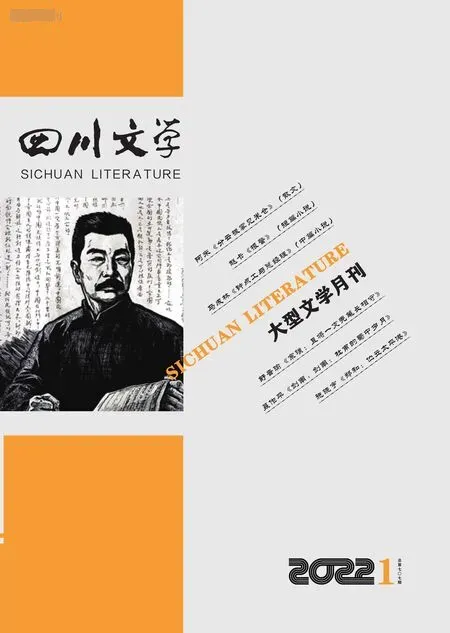槐花香
2022-10-21钱静
□文/钱静
1
院门右边的路上,站着一个人,眼睛看着我们这边,细看,是郑小泉。村里的人背地里说,他神经有问题。他呆呆傻傻的,几乎不说话,你跟他说,他只会笑。听说,他五年前去了十多公里外的天坑,才变成这个样子。有人说,他被天坑里的怪物吓傻了,有的说,他中了坑里的毒气。人们问他,进天坑看见什么、闻到什么,他笑而不答。
矮处手臂粗的枝干锯掉了。以前,我只能爬三米高,今天到五米就不能再上去了。杨海能爬,在我六七米高的上面,当然,我们是交错着的,他东我西,或他南我北,这样避免树枝掉下来砸到我。
我和杨海相处有五六年了,把我和他拉近的是一件事。一天下午我去田里看秧苗,走上一个小斜坡,看到一条沟渠里一双脚成V形一张一合,像把要剪破天空的剪刀,然后又像作揖,上下摆动。我走近看,是杨海,他肚皮朝上,双肩夹在沟渠里,手无法动弹,舞动脚也不能让他起身,像一只石板上肚皮朝天的乌龟。我忍着笑,像摇一截树桩,花了五六分钟才把他拽出来。他说挣扎十多分钟了,因为怕招来很多人而丢脸,一直没有喊,只用脚来求救,还好碰到我。
“昨天体检,你的也是脑血液不稳定?”杨海说完,手上锯断了一根树丫,树丫掉到地上,槐树下的杜春把它拖到一边。
昨天县疾控中心来村里体检,检查心脑血管,女的外加妇科。检查心脑血管的时候,脑袋上套一个头盔一样的东西,上面两根线,连到一个收音机大的显示器上。显示器有两个表盘,上面有一些刻度,刻度每隔一段标着数字,一根红指针在上面摆来摆去,像根拒绝的手指,看不出什么意思,只有医生才看得懂。我问看显示器白白胖胖的男医生,我的脑血管有没有问题,他说没什么大问题,只是脑供血有些不稳定,脑子里的影像不清晰。我站在一旁,见他对好几个人都这样说。那指针,还真是根否定的手指。我们问要不要医治,他说不用。
“是啊。”我说,顿了两秒,又说,“难道全村人都一样?”
杨海扒开脸上的一条树枝说:“有两个不一样,喏,一个是正在看我们的郑小泉。”他拱着嘴向远处的郑小泉指一下,“另一个是傅永会。”
傅永会住在村北边,七十多岁,听说是北京来的知青,回不了城,在我们这里娶妻生子,跟女婿女儿生活在村里,大儿子在市医院工作。土地承包到户时候他当过两年村主任,好土地分给自己,粮食年年丰收。从村主任位上下来,村里好多人都恨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画起画来,有一年还拿到市里展览,成了画家。我没见过他的画,见过的说,他画的都是些破房子、枯树、光屁股女人。
人们都说,他为什么不画村里的洋楼、白花朵朵的大槐树和穿衣服的姑娘,这分明是要砸我们“文明村”的牌子,有人说他老不正经。这几年,他对村里人也不大来往,几乎没有朋友,路上见了,一副冷冷的态度。我们都认为他傲气十足,对他慢慢由不喜欢,变成讨厌。男人们见他,向地上吐口水,女人见他,远远地让开,巷子里实在让不开,贴墙站着,等他过去了才走。
“这两个人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杜春仰头问杨海。
“这两个人脑子影像清晰,连小问题都没有,正常得不得了。”杨海笑嘻嘻地说,一片树叶挡住他的鼻子,让他的表情残缺不全。
“你听哪个说的?”杜春又问。
“医生刚要上车,我问了,看仪表盘的医生说的,就是白白胖胖那个。”
“一个精神病,一个老不正经,真是怪了。”我说。
“难道我们也要变成精神病和不正经,血管和影像才正常?”杜春自语似的说,手里提着一根树丫砍削着,他的话我们还是听见了。
杜春是我奶奶堂妹的孙子,和我是表兄弟,我们常聚在一起喝酒闲聊。杜春七年前大学毕业,在城里做了两年的快递员,辛苦且工资不高,回来了,在自家山林围下一片地做养鸡场,父母帮照看,他说现在有两百多只鸡。有时我家里要用鸡,去他那儿,他都是便宜价给我。他喜欢吃动物肠子,猪肠、羊肠、鸡肠、鱼肠,就连菜叶的茎须也不放过。他吃过所有能吃的肠后,觉得还是鸡肠更入口,他说:“鸡肠的那股香和嚼劲,有种说不出的好。”我有时想,他是否因为喜欢吃鸡肠才养鸡。
阳光穿过树梢,来到身上,像一件轻薄衬衫,不轻不重。每经过这里,我都会停下脚步,仰头看树一眼,随后,目光下移,停留在它根旁的土地上。
风呼呼吹,几片橙黄的树叶斜斜地飞,像受伤的蝴蝶,有的落到西边菜地,有的落到东边晒场。风并不甘心,仍不倦地翻动着树叶,像要把它们叫醒,让它们重回枝头。
槐树根离晒场边一米多,在矮处,晒场比它高七八十公分。槐树比我岁数还大,大很多,也就是说,它所看到的人事比我看到的还多。树根一抱还围不过来,两米以上枝丫分开,向四周伸展,高达二十多米,每到春夏季,枝叶繁茂,阳光落下来,大半个晒场被它遮挡。蜜蜂在白色的花蕊上停留、飞舞,热热闹闹,仿佛是它们的露天会场。我前面八九十米远,就是我家院门,站在院门口能闻到飘散而来的槐花香,有许多蜜蜂飞过头顶,奔向槐树。
杨海曾对我说:“是该修理修理了,我那块菜一到秋冬季落得到处是树叶。”
树叶落到地里倒是小事,主要是这几年烧柴贵了,砍下一些枝丫,也算减少点开支。厨房里虽然用上了电,但也有不方便的时候,比如请客吃饭,可以多烧两个炉子。
这棵树第一次修枝,是在五年前,那一次是杨海上树,我没有上去。这一次,我应该上来,人一辈子总不能三米高都突破不了吧。不过,头是真的晕,我的左手紧紧抱着树干。
该砍的几乎都掉落地上,整棵槐树稀疏了些,地上堆满了枝干和树叶。我和杨海从树上下来。
槐树下是家里的菜地,听父亲说,爷爷死在地里后,奶奶没有再种菜,在上面栽了三棵槐树,一棵两个月后枯死了,一棵长得慢,两三年不见长一截,最后也干枯而死,只有这棵,倔强昂扬,长势良好。父亲说,这棵树脚正是我爷爷侧躺的地方,“他嘴和鼻子都流血,可能是你爷爷的血滋养了这棵槐树,才让它长这么高。”如果真是这样,每朵花、每片树叶都有他血的养分。看着地上砍下的枝丫,身上的肌肉一下收紧。转念想,不可能吧,它早被五十多年的岁月冲走了。
爷爷生前,上过初中,在村里是唯一的高学历,时常跟人讲古论今,言语直率,说这人不是,那人不是,得罪了村里好多人,人们看不惯他夸夸其谈的样子,同时对他的不留情面报以怨恨。五十二年前,村长听信一个神汉的话,让每家每户从分到的粮食里匀出一碗,或大豆,或玉米,聚拢来烧成灰,撒到田地里,边撒边念几句词,这样可以增加粮食收成。如果谁没贡献一碗粮食,生产队便以破坏生产之罪,给予惩罚,来年粮食少分三斤。爷爷不仅不贡献一碗玉米,还在村里的墙上贴了大字报,上面写着:粮食增收,靠的是粪肥、勤快,不是靠巫婆神汉,献出一碗米,全家少吃一天粮。王良才。村长认为,爷爷不仅想让群众饿肚子,而且还煽动人们反对增产增收,不能轻饶,便撤下墙上的大字报,来到家中找爷爷,奶奶在做晚饭。奶奶以为他只想批评爷爷几句,便没放在心上,告诉他爷爷在菜地里浇水。村长从家里出去,进了几户人家,叫上几个人,一起去菜地,边走边说爷爷居心不良,敢写反动大字报,简直翻天了。村里好多人早就对爷爷卖弄学问的样子见不惯,听了他的话,恨得牙痒痒。
爷爷提着水桶准备回家,村长把大字报展开在他面前,问是不是他写的,他说是。村长给他脸上一巴掌,其他人蜂拥而上。他被打倒在地,五六个人拳打脚踢长达二十分钟。他口鼻流血,最后被一个男人踢下晒场,滚到地里,蜷缩着。村长见他不动,怕闹出人命,才叫身边的人回去。奶奶赶到,把他背回家,午夜时死在床上。两天后,奶奶疯了,半年后跳了崖。
杨海跟杜春一起削带叶子的枝丫。我回家骑来那辆破摩托,把削下的枝丫捆到后座上,一趟趟运回院子里。
我第三趟回到晒场上,有三男两女五个小孩在晒场边摘树叶玩,其中一个是我女儿小双,八岁,上小学二年级,另一个男孩是杨海儿子,跟我女儿同岁,其他三个我不认识。村里一百多户人家,这些年,我很少走门串户,小孩一茬茬出生,八九岁以下的小孩,我多分不清谁是谁家的。杨海站在树根旁,一只脚搭在晒场边,嬉笑着问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你祖祖还画不画不穿衣裳的人呢?”小男孩手里捏着一片树叶,低着头,把脸侧向一边,不回答他。他还在追问:“说啊,他还画不画?”杜春提着一根枝干砍削,脸上微笑着。
孩子低头站了一会儿走开了。另一个比他大一两岁的男孩手里捏一根枝条,走近杨海,眨着一双大眼睛说:“他刚才跟我们说,他祖祖说了,昨天医生检查,好多人的脑子里有许多小人,就他祖祖跟那个疯子没有。”
“他真这样说?”杨海脸上的笑消失了,扭头看向晒场边低头折树叶的小男孩,杜春手里停下来,看着杨海面前的男孩。
“不信你问他。”男孩手指一下远处的小男孩。离男孩两米远的杨海儿子对杨海说:“他真说过。”
2
“老头说我们脑子里生娃娃,这不是侮辱人吗?”杨海刚坐到饭桌边就说,他好像相信了孩子的话。天色已黄昏,院子里风噗噗地吹动墙边的槐树枝,刘梅把一碗猪排烧土豆端上桌,浅笑着看杨海一眼,走出去了。小双和杨海儿子把菜扒到饭碗里,坐在门外吃,边吃边叽叽咕咕说话。
“他说我们都是女人呢,脑子里有小孩做窝。”杜春双手拄在大腿上,咧嘴笑。我对傅永会没什么接触,即使路上碰见,也不打招呼。他好像对谁都看不惯,我们也看不惯他对人冷冰冰的样子,能画几幅画有什么了不起啊。说实在的,我对画画也不懂,在村里画光屁股女人,终究是伤风败俗。他把我们都说成女人,真是过分。
“饭吃完,我们去问问他,到底我们脑子里有没有小人。”杨海喝下一口酒说。
我说:“你俩去就行了。”
“怕什么,拿出你以前的狠劲儿,在他脸上吐一泡口水。”杨海又接着说,“我还记得,前年,你提着砍刀把阿三撵得满村跑,想不到你平时温温和和的,那次倒是把我吓着了。”他呵呵笑着。
我用筷子指指饭桌说:“往事不提了,吃菜。”傅永会没对我怎么样,我怎么会朝他脸上吐口水,杨海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我说:“别乱来,好好跟他说。”
“当然,我咋会乱来,不过,人要对得起我们村,他一个外地人,来到我们村,不能砸了我们‘文明村’的牌子,这是良心,他咋就不懂呢?”杨海把一块瘦肉塞进嘴里,筷子摆到碗上,腮帮勤奋地磨动着。他的热心肠在村里相当耀眼,十多年前的一天傍晚,他在一个山崖下翻地,一辆拖拉机飞下对面三四十米高的山崖,眼睁睁看着拖拉机落在斜坡上,车斗里的五个人被扔出来,在斜坡上木头一样滚。他赶忙丢下锄头跑上斜坡,一个个察看,最后背起一个满脸血污的女人往镇上走,路上不管碰到谁都说赶快去救人。后来有人笑话他,只会救女人,他咧嘴笑,“莫乱说,她都不会哼叫了,救人先救重。”幸运的是,那五个受伤的男女,医院里住了三四个月,最后都陆续出院。
刘梅坐到我身边,端着一碗饭,默默吃菜。刘梅不是话多的人,我们男人说话,她一般不会开口。
我给杨海和杜春添了一回酒,杜春没有接,我自己的酒杯添了一点。我喝酒少,不想醉酒后身体难受。我原来就交代过的,能喝多少是多少,谁劝酒,谁他妈滚蛋,这俩家伙还算有点耳性,我交代后,没劝过酒。
杜春端起酒杯向杨海敬酒,说他是他婶婶的救命恩人,很感谢。杜春婶婶就是出车祸时杨海背到镇医院的女人。杜春说:“有你这样的好心人,是村里的福气。”杨海笑得脸上褶子乱爬,摆摆手说:“一村人,应该的,应该的。”说完跟他碰了杯。
杜春端着酒杯转向我:“杨海夹在水沟里,你救了他,是我恩人的恩人,也是好人。”我笑着说:“救人一命胜过喝酒吃肉。”跟他碰了杯。杨海尴尬地笑笑也向我敬酒。
杨海像要摆脱水沟事件,把话题转到傅永会上。“傅永会以前为什么留在村里不回城?”他脸上似乎有答案,只是问我们是否知道。他脸没有红,但醉意横行。
我摇摇头。“为什么?”杜春反问他。
“没结婚,他媳妇肚子就现形了,哪回得了城。”他喝一口酒说。刘梅白了他一眼,对刘梅的白眼他没放在心上,呵呵笑着。这个我倒没听说过,也许是真的,城里人谁会平白无故留下来。
“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杜春说。
恨不恨,只有他心里知道,我没法判断。杜春沉默几秒说:“有一次在娱乐场上,他跟我大叔聊天,我站在旁边,他一个人叨叨个不停,说他儿子小时候如何如何懂事,在医院里研究的项目如何如何高端,还有,他一张画别人给了几千的价,我大叔只顾点头,他整个话傲气十足,显得自己多了不起,好像别人渣渣都不是,我听了想吐,转身走开了。”
这个我没法说,因为我几乎没见过他跟谁在一起聊天。
3
杨海和杜春离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小双在屋里看动画片,我和刘梅就着院里的灯光,把院墙下的槐树枝码放整齐。“还有一股清香味。”刘梅说。我没有闻到,可能是我喝了酒,身上的酒味把它冲散了。
“脑子里咋会有小人,这不是乱说吗?”她手提一根树丫说。我不知怎么回应她,只是默默做着手上的活。也许是她看我动作慢,让我到一边去。刘梅做活是一把好手,行动起来,风风火火,像一头刚习惯鞍辔的骡子。
我进堂屋,提起电视机旁的暖壶,轻的。我去厨房烧水。在等水开的时候,我进堂屋打开电视,新闻、综艺节目、电视剧,一路往下调,都是清汤寡水,不疼不痒。也得承认,这些年,我的电视口味,连我也搞不清是什么。我丢开遥控板,走出屋门,院门口进来一个人,是杨海。
“我去问傅永会,是不是我们脑子里有小人。”杨海坐到沙发上开口说。
“水开了。”刘梅在院子里喊。我赶忙去厨房,提了烧壶回堂屋泡了两杯茶水。他看一眼面前直冒热气的茶水,转向我说:“他说,‘是有好多人’。这话说得稀奇古怪,我问他咋晓得,他说那仪器是他儿子和两个医学专家刚研制出来的新产品,白白胖胖的医生跟他儿子是高中时候的同学,他认识,那医生告诉他的。我说仪器上只有红色指针,医生咋看出我们脑子里有小人?他说上面还有一个瓶盖大的小屏幕,我们没注意,注意也看不出什么,还说刚研制出来,只是悄悄试用。我问他为什么我们有好多人,唯独他和郑小泉没有?傅永会说晓不得。”杨海看向我,“你说那仪器是不是真能看出我们脑子里有好多人?”他说完,抓起水杯喝一口茶,咽水时,嗓子叽咕叽咕叫两声,像吞到一只拼命挣扎的青蛙。
我说不知道,随即又说:“现在的科技也许能研制出来,你想想,能研究出下围棋的机器人,还让世界水平最高的人成为手下败将,能研究出看见人脑子是否有小人的仪器,应该也正常。”科研方面的信息我常看,所以知道一些当下最前沿的科技,比如,能把死去千年的人脸复原出来,机器人能写诗、写小说,科技发明超乎人的想象。
“下围棋的机器人,我好像听哪个说过。嗯,那我们咋整,总不能让那些脑子里的人跑来跑去吧?”他笑了一下。如果真是这样,确实是个问题,他这一问,把我问住了。
刘梅走进来,问怎么了,目光在我和杨海脸上晃,杨海把去找傅永会的事说了一遍。她一脸不解,但没说什么,倒了一杯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小双坐在她身边。
我对杨海说:“你跟傅永会没吵吧?”
杨海说:“吵了几句。我说不要乱讲,人脑子里咋会有好多人,他说你不信的东西多着呢,我说如果你危害我们村,我对你不客气,他返身进屋,不理我,我就出来了。”小双看他一眼,目光又回到电视上。他端杯喝一大口水,嗓子又叽咕叫了一下,嘴上粘着一片茶叶,低头噗地吐到地上,动作粗鲁,像吐出一只死蝴蝶。“听你一说,脑子里有好多人的事可能是真的。”他说。他东一句西一句说了一会儿,喝了两杯水,走了。
我和刘梅看会儿电视,喝下去的酒在身上慢慢消散,洗个脚,睡了。一时没有睡着,想到杨海的话。那些人在我脑子里,也没影响我的生活,没有那些人,郑小泉反而傻乎乎的,傅永会还不是让人讨厌?他俩才不正常。可是,有人跑来跑去,脑子像个运动场,终究有些不痛快,又不晓得怎样把他们赶出去。我有一点不明白,他知道我们讨厌他,为什么还要跟杨海说这个,可能是即使告诉他,他也不会相信,或者不在乎。
4
第二天起床时,太阳还没有出来,没有风,天气有点凉,我喝了一杯茶。院墙脚,槐树干码一堆,枝叶码一堆,虽然经过一夜风吹,但还能闻到清香味。树干上还有一些没砍削干净的枝叶,在微风里轻轻招摇,我提了砍刀一根根削干净。
削了八九根,太阳照到院墙上,身上热起来,把外衣脱了挂在屋檐下。身上的汗水越来越密集,两边的腮帮上有它们爬动。我喜欢流汗的感觉,它们让我全身舒畅,也喜欢被大雨浇淋,如果地里干活,碰到大雨,我不会去躲,雨越大,身上越有力气。不管是流汗还是被雨淋,我喜欢的其实是畅快淋漓,有了这个,我才觉得生活是有意思的。
手机铃声从堂屋传来,我拿起沙发扶手上的手机,是杨海。他说杜春刚打电话给他,说村外路上碰到傅永会,杜春问他,脑子里有人有什么影响,他说,影响要说大就大,要说小也小,问他有多大,他不肯说。“你说有什么大的影响?”他问,我说不知道。
挂了电话,我又接着削树干上的小枝。有什么大的影响呢?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吗,可我的身体好好的,没有感到哪里不舒服,脑子也不疼不晕。我始终想不清楚有什么影响。
那些人,是谁?怎么会跑到脑子里来?什么时候进去的?傅永会和郑小泉脑子里怎么没有?这些问题像一群马在脑袋里跑来跑去,踩得脑子生疼,砍玉米秆时它们吵闹,吃饭时它们也在吵闹。见我呆呆傻傻的,刘梅问怎么了?我说没怎么。我不是把心事都说出来的人,即使是自己妻子。
那么多人挤在脑子里,我自己那个呢,很难看到。我的脑子被他们霸占,就像房子被人占了,我只能在野外风餐露宿。这样的事不能继续下去。可是,要怎样才能把它们赶出去?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傅永会的脑子里为什么没有别的人,他是用什么方法?我跟他没有任何来往,路上碰到,也没打过招呼,在我心里,他就是个爱画裸体女人的老不正经,但在村里,没见过也没听说他跟哪个女人乱来。他会跟我说吗?试试吧,不试怎么知道结果。
晚饭后,我出了院门,向傅永会家走去。
5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屋檐下亮着灯,刘梅在扫地。她问我去哪儿了,我说去傅永会家。她问去干什么?“问问他脑子里有好多人是咋回事,他也说不清楚,只是建议我下天坑一次。这是什么话,分明是要让我去送命,不送命也得跟郑小泉一样成精神病。”我说。她站直身体,手握扫把,一脸不解。我补充一句:“他下过天坑。”
“你去问他干什么,脑子里有人又不疼,不会死人,下天坑才会死人呢。”她说。
那个天坑,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个恐怖之地。听村里老人说,我还没出生前,前后有两个男人下去,最后都没有上来。在我十岁的时候,镇上一个年轻小伙子下去,绳子往下一百多米后,变轻了,拉上来,人不在上面,绳头断了,不知是在岩石上磨断还是被动物咬断。十年前,省外两个野外探险者下去过,听说在坑底也只停留了二十多分钟就上来了。就我所知道的,下去的人不超过十个,傅永会和郑小泉能安全上来已不容易。我曾经到过它旁边,我向来怕高,离悬崖边十来米就不敢往前走了,坑底是什么样子,我看不到。
我问过傅永会,为什么下天坑能消除脑子里的人,他说,说不清,但绝对能。他跟我说话,一直都是平静温和,从他神色语气,我看不出有想害人的意思。去天坑,只是他的建议,并没有必须去的强烈要求。他说,他在三十多岁时,懂点草药,肚子疼、发烧感冒、跌伤之类的他能治好。他常到山上挖药,一天来到天坑边上,看到里面有树林、河水、成片的各色野花,他被吸引住了。但太高了,有四五百米深,而且四面都是悬崖,仅靠双手双脚是下不去的。他回来后常常想到它,夜里也会梦见自己进到天坑里,有时会被天坑里出现的怪物吓醒。最后好奇心战胜了恐惧,他和妻子带着轮盘和绳子去了。他说,坑里有许多地面上没有的动物和植物,叫不出名字。老虎豹子没看见,也许是他运气好,没碰到。他在坑底待了十多分钟,汹涌的恐惧还是把他赶了上来。他说,那是个神奇的地方,也是个凶险的地方。回来后,他脑子像被换了似的,清清朗朗。我问他,郑小泉也下去了,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个样子,他说他不知道。
郑小泉几乎是被他哥哥用绳子吊上来的,回到顶上,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没站起来,眼看天坑,面无表情,手脚被岩石擦破了,还微微颤抖。他哥问他咋成这样,他缓缓说,回去再说。待他慢慢恢复体力才回家,一路上都没有说话。回到家,躺到床上,晚饭也不吃。迷迷糊糊睡了两天才起床,他哥问他在天坑里看见什么或听见什么,他说没有,问他怎么会这样,他说我也不晓得。他没下去之前,爱说爱笑,胆子大,敢手抓竹叶青,捏着脖子绕到手臂上,凑近脸,蛇信快舔到他的脸还笑嘻嘻的。他身体灵巧,不怕高,爬树像踩了楼梯似的,晒场边上的那棵槐树,噌噌噌爬到十八九米高。如今像换了一个人,站在哪儿,像截木桩,脸色忧伤,目光定在哪儿,像生了根,拔都拔不出来。
同样的一个坑,两种不同的结果,难道是天坑发生了变化?这个有可能,毕竟两人下去的时间相距三十年,三十年里,什么都在变化,天坑没理由不变。
天上星星稀少,一个月牙从东边房顶升起,耳房、柿子树成了黑影。
那个仪器是不是真的很准,事实是不是像傅永会说的一样?仪器的检测结果他俩正常,而他俩去过天坑,应该是准确的。不过,郑小泉现在的样子,就是他自己应该具有的样子吗?也许吧,我说不清。那些人悄悄住进脑子,已经几十年,我吃的饭、喝的水都是提供给他们,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仆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我怕高,相当怕,要下去那么高的地方,会被吓死,不死也可能成为郑小泉的样子。不过,很多事是可以改变的,只要去做。就像阿三,他的水牛吃了我的秧苗,跟他说要看好牛,他说牛会听人话就不叫牛了。他这样说当然是蛮不讲理,我不想跟他一般见识,自己去补上秧苗。他八岁的儿子烧了我的稻草垛,我问他儿子为什么要去烧,他说:“肯定是图好玩,要不,我赔一碗饭给你?”我不想跟他吵,转身走了。他用锯子锯晒场边那棵槐树枝,我说是我奶奶种的树,他说:“上面有你奶奶的名字吗,还是它长成你奶奶的样子?”我不是喜欢抬刀弄斧的人,那次我提了砍刀向他走去,他见了刀就转身跑,我紧追不放。他绕了半个村子,我也追了半个村子,他最后跑到镇上亲戚家躲了两天。后来,他拉牛从田边走过,死死拉着牛鼻绳,从晒场经过,眼睛不再看槐树,低头走路。
决心是个好东西,比金条还贵。
6
晒场上还有掉落的树叶,它们已经干了,被鞋子踩到,嚓嚓响,像呼喊。西边一块地,重新翻过,一条浅沟横过,地被分成平整的两块,可能撒了种子。种子?我想起傅永会讲的一件事,因为那件事,四十多年前他才留在这个村子。
包里的手机响了,是杜春,他说去他二叔的鱼塘钓了两条鱼,晚上喝一口。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走进他的院子。三间正房,玻璃钢窗,厦台铺着瓷砖,厨房在南边,他在厨房门口的水龙头下杀鱼,正翻洗鱼肠,脸颊上溅了两个血点,地上一堆鱼鳞内脏。我对鱼肠没有兴趣,都是丢了的。他说,我见你早上骑摩托出村子,去哪儿?我说去加点油。加油是一个,主要是去天坑边上,但我不想告诉他。
“听说没有?傅永会跟阿三说,他想在村里的墙上画几幅画,让村子好看一点,感受点美,分文不收,阿三说各家的墙让不让画得跟主人说,他没法下命令,傅永会问了几家,都不同意,谁愿意他那烂画粘在墙上?”世事在变,阿三也不例外,当了村主任后,体壮脸肥,性情沉稳了好多,以前的无赖样无影无踪。我说听说了。他说:“傅永会也问到我,我不同意,几张烂画,有多稀奇,还脏了我的墙呢。”他把鱼肠拿到龙头下冲洗,水四处溅,赶忙放低。他叫我去堂屋喝水,然后端着瓷盆进了厨房。
院墙几个土罐,里面栽菊花、月季、剑兰,泥土板结,没有肥土,杜春好像不常浇水、施肥,都瘦小干萎。
杨海从院门口进来,见我,笑笑说:“听说杜春钓了几条鱼。这两天做什么?”我说庄稼都收了,暂时闲几天。
吃饭在厨房里,南墙有一道门,外面是个菜园,有青菜、辣椒、西红柿。虽然有两道门的光亮进来,杜春还是拉亮了灯。主菜是鱼,一大盆,摆在桌子正中,另外还有一个煮青菜,一盘瘦肉炒青椒。杜春每人倒了一杯酒,杨海好像喜欢吃鱼尾,第一筷下去就夹到盆边上的鱼尾巴,在蘸水里裹一下,一嘴咬着鱼肉,尾巴在嘴外像挣扎似的抖动。杜春用筷子在盆里翻了翻,找到蜷着的鱼肠,夹进自己碗里,他等杨海把鱼尾骨放到桌上,才端起酒杯抿一口。
杨海说:“这鱼味道好。”
杜春说:“在水塘里养两三年了,我二叔什么也不喂。”他顿了一下说,“昨天我就去了,看见水塘边坐着傅永会,抬个画夹子在画,我不想跟他坐在水塘边,回来了。”
“听说他一幅画能卖几千呢。”杨海说。
“能卖几千他早在城里买房住着了,别听他瞎吹,现在什么人都想冒充专家。”杜春又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听过很多专家的课,他们理论一套一套的,根本不实用,不实用的理论就是放屁,实用才是硬道理。”我没有他那样的好命能上大学,高中毕业在城里做过几年电器销售,觉得没意思,回来了。他说到自己养鸡上,如何防病、如何治病。我觉得他不应该去读公共管理专业,而是该上技校。
鱼吃了半盆的时候,天黑下来,杜春给杨海添了酒,要给我添时,我挡住了。杜春提着酒壶硬往我酒杯上凑,我说喝够就行。他不听,我说你再添,我就走了。我这样说,主要是反感他说傅永会冒充专家。那晚我跟傅永会谈话后,我觉得他有专家的气质,待人温和,说话有分寸,他的画有没有到专家水平,我不清楚。另外,傅永会还说:“你爷爷死得冤枉。”我爷爷死的时候,他才二十岁。在村里,他是第一个对我说这样话的人。我不知道杜春为什么对他有那么大的意见,难道是讨厌画,连带画画的人也讨厌?
杜春说:“你原则性怎么这样强。”他放下酒壶。杨海看着我们笑笑,说:“下午,我儿子回来,他跟我说,傅永会在晒场边画那棵砍了枝丫的槐树。我儿子和四五个小孩看他画,后来跟着他回去看他的画,我跟他说,以后少去。”
他俩越喝越醉,说话重复,我的头也是晕得够呛。
7
天气越来越凉,村里村外的树叶纷纷落下,仿佛是冬天雪花的预演。
天亮,太阳还没有出来,我骑上那辆破摩托,刘梅跨上来,我们出了家门。上了柏油公路,绕了几座小山,走了八九公里,离开主路,岔进一条沙土路,摩托车微微颠簸。身上冷起来,刘梅也感觉到冷,身子贴着我的背,把我的腰勒得紧紧的,好像有意逗我。我很不舒服,影响到驾驶,便说,手松一点,她的手放松下来。刘梅身后的货架上捆着两个蛇皮袋,它们装着两根尼龙绳,每根四百多米,还有两个滑轮。我们要到天坑去。
两周前,我跟刘梅说:“我想去天坑看看,十多年没去了。”她睁大眼睛,“有什么可看的,那么高,别去了。”我说就只看看。她说:“你是相信那老头子的话了?”我说我怎么会信他的话。她见我去意坚决,不再阻拦,一再嘱咐我不要走到边上去。那天清晨,太阳还没有在山顶露头,我带上一根二十米长的绳子,骑上摩托上路了。十多年前,我跟刘梅恋爱时,就曾用摩托带着她到过那里,当然,那辆摩托早已几经转手,进了熔炉,成了新机器的零件。那时,我们都只远远地看,不敢靠近。
我把车子停在树林边,从车上拿下绳子。这根绳子我是趁刘梅进屋后,悄悄带上的。我不能让她担心。
从停车的地方到天坑边沿比较平整,没有树木,我的绳子太短。我试着向边沿走去,相距十多米就不敢再靠近,我担心酒醉似的眼花缭乱,控制不住,把自己撂下悬崖。我退回来,沿着树林边走,寻找到比较靠近坑边的树木。我走过去,把绳子一头拴到一棵腿粗的树干上,另一头拴在我的腰上。我带来的尼龙绳是新买的,足以承受我可能会失控的身体。我向前走,离坑边十米远,心跳加快,眼睛有些花,脚步也不稳,我只好双腿跪下,两手着地,往前爬,晕眩减轻不少。这个样子,一定像过去的江边纤夫。
离边沿约三米的时候,整个身体趴在地上,匍匐向前。是的,我就是这样怂,怂得让我意外。坑底慢慢出现在面前,那里树木青绿,两块隔得较远的花五颜六色,一片春天景象。离边沿还有一米多,我停下来,脑袋有点晕,我担心身下的这片土突然塌方,赶忙往后退,回到拴绳子的树下。
我在树下坐了十多分钟,第二次向坑沿靠近,仍是刚才一样,先走,后跪,最后是爬。如此靠近五次,终究没有爬过那一米。
回到家,刘梅看到我衣裤上没拍干净的灰土,问我咋了,我如实告诉。她说:“你真是不要命了。”我笑着说:“有绳子保护着呢。”她知道我打算下坑,这是准备阶段。“你还把那老不正经的话当真了。”她说。
“事实是他跟郑小泉都下过坑,而且脑子里没有别的人影。”我说。
“那你就不害怕会成郑小泉的样子?”
“我有办法,不可能变成他的样子。”我的话没有让她放心下来,她很气愤,脸色铁青,最后说:“那就随你。”转身走开,脚步咚咚响。
第二天我带着绳子又去天坑边,刘梅终究不放心,跟我去了。她怕得紧紧拉着绳子。我说绳子拴在树上很稳,但她还是拉着,一点一点给我放绳子。三次后,我克服了最后一米的距离。第三天,她放心了,没有跟我再去。我去的目的是巩固那一米取得的成果。到第六天,我可以站着走到边沿,并停留两三分钟,脑袋不再晕眩。有点小兴奋,恐高被我摁住了,不再控制我,也许是我的决心把它压下去的,就像我决心抬起砍刀去追阿三。
8
刘梅又夹紧我的腰,我再次提醒她松开一些,我怀疑她是对我过于固执的恨。
我们骑着摩托沿着树林边慢慢行驶,穿过凹凸不平的土包、洼地,来到先前选定的树林边,这里崖壁笔直,如果下滑,很少会碰到岩石,能减少绳子与岩石的摩擦。我解下两个蛇皮袋,掏出新买的两捆尼龙绳和滑轮。四个滑轮,每两个为一组,一组固定在两棵腿粗的松树间,一组固定在悬崖边,刘梅只需绞动两棵松树间的滑轮手柄即可。尼龙绳拴到滑轮上后,我和刘梅用力扯了两次,都很结实。两根绳子,一头拴到滑轮上,另一头拴带着手掌宽的皮带,皮带分别套在我的腰上和屁股上。皮带连着拇指粗的铁链,铁链系在绳子上,在家里试过,皮带和铁链都很牢靠。为防坑底瘴气,我吃了四五天薏仁,戴了两个口罩,都喷了酒精。
套好身上的皮带,我拉着绳子,面对崖壁,从崖边下去,脚蹬岩石。心里不紧张是不可能的,出现任何意外都会带来危险。当然,也有兴奋,这个曾经从不敢想象能靠近的坑底,将踩在我的脚下。站在悬崖边,我对自己说,今天将是我一生最耀眼的一天,它的光芒将闪耀在我今后的日子里,把我平庸的生活打扮得花枝招展。
太阳已经升起很高,并不很热,但身上有汗,也许是紧张带来的。往下十米、二十米、五十米。我听到坑底悦耳的鸟鸣声,空气清凉,带着潮湿味。每下滑几米,我都扭头看看两边和身后。坑底的树林这里一片,那里一片,翠绿挺拔。左边好像是一片泥沼地,各种颜色的高秆野花开得鲜艳,细看,连黑色的花也有,这在坑外是难以见到的。鸟声啾啾,清脆悦耳,像清凉的水。
抬头往上看,崖顶离我很远,天空被边沿切掉一大块。目光回到身边崖壁,右边两米外,一只我从没见过的猪仔大的动物趴在一个洞口,无毛,鲜红的肉色,脑门上左右各长一对角,细细的,一拃长,眼珠凸出,一红一绿,恶狠狠地看着我,前爪慢慢撑起,脖子伸开,像要扑向我,好像我是个怪模怪样的侵入者。我吓得能听到脑神经唧唧叫,可下降的速度由刘梅控制着,我无法加快。在我下降中,它的前爪慢慢放松,脖子缩回一些,我一直盯着它,它也一直盯着我,我们相互提防着,直到离它六七米,脑子里的唧唧声才停止。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还在下降,脚下的树林越来越近,八十米、七十米、五十米,降到相距二十米的时候,我掏出哨子,扒下口罩,悠长地吹一声,绳子停止下降。我和刘梅说好,吹一声哨子,停下,吹两声,继续,吹三声,绳子上升。
盲目落地是一种冒险,因为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等着我。这个坑的大,超出了崖顶上看到的,可以说是广阔,直径一公里多,对面悬崖下的树林,遥远得像一团绿雾;深度不少于四百米,这样的深度,是我这一生从未到过的。我为来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而兴奋,又担心无力爬出这个深洞而恐惧,两种情绪在心里此起彼伏。
既然下来了,恐惧于事无补,这样一想,身体慢慢放松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前面五六十米远的弯曲树梢上,蹲着一个怪物,有一只公鸡那么大,全身浅黄绒毛,脑袋拳头大,长鼻子遮住了嘴,大眼睛,耳朵上面手掌宽的东西平展开,像一对翅膀。手掌宽的东西抖动了一下,泥蒿,是它在说话吗?周围看不到别的动物,声音是从它那儿传过来的,好像在说“你好”。我马上反应过来,我回了一声“你好”。听到回应,它快速窜下树梢,在密林中消失不见。把它拍下来多好,我马上想到身上带着手机。我掏出手机拍照,近处的树林、崖壁,远处的河流、草地都拍。正拍照时,一只比山羊大全身洁白的动物,从树林里跳跃着,闯进镜头,我啪地摁下按钮,它已不见。我刚把手机放回袋子,远处河流上出现一个黑色东西,露出一半在水面,像脑袋,顶上一条条的东西像蛇一样扭动着,从脑门上射出两道光,对着我这边,即使是青天白日,那光仍然强烈耀眼。如果是夜间,一定像远远射来的探照灯。它也许发现了我,我吓得心脏怦怦跳。慌忙掏手机想把它拍下来,也许是太过紧张,手机从我的手里滑落,撞到崖壁上凸起的一个岩石,岩石把它弹出六七米远,落进一片树林,在树丫上弹了两次,跌进树脚的一条窄窄的水流里。那水平缓,没有声音,一定很深。我不敢去捞,即使捞上来,是否能用也说不准。那可是我一千多块买来的手机,最可惜的是刚照的几张相片。当我抬头看远处河流时,那个射出强光的怪物不见了,水面平静,仿佛那东西从没出现过。我的脑袋嗡嗡响,像一群飞机在远处轰鸣。
太阳已到头顶,但我感觉不到热,可能是潮湿削去了阳光的热量。我犹豫着是否该到地面上,想到刚才看到的那些从没见过的东西,我害怕了,再说,我跟这个陌生的世界已经近距离接触过,也算粗浅地认识了它。我拿出哨子,用力吹了三声,十秒钟后,绳子缓缓上移,身体像增加了重量,我担心绳子承受不了,身体紧缩着,好像这样能为它减轻负担。
也许是用了三十分钟,也许是四十分钟,我到了崖顶。回到地面的时候,不知是麻木,还是惊吓过度,我的双脚难以站稳,只能慢慢挪动。刘梅还在树下站着,脸上是我安全后的放松。她没有上前拉我一把。她从来就不敢到崖边,刚才河流里出现的怪物,自然没有看到。
我来到松树下,坐到地上,脑子还有隐约的嗡嗡声。我给刘梅讲下面看到的东西,讲述凌乱,不知道她听明白没有。她睁大眼睛,一脸的不可思议。手机落到水里我也告诉她。她说:“来一次,损失了一千多块的手机,值得吗?”我说:“值得。”这个话我是冲口而出的,没有任何犹豫。
大约休息了二十多分钟,身上有了活力,脑袋里的嗡嗡声消失了。我起身收绳子和滑轮,把它们塞进蛇皮袋,捆在摩托后座上,做这些时,脑子里总晃动着坑底看到的景象,仿佛它们已经在我脑子里安居下来,挥之不去。那是一个广阔神秘的世界,也是一个时刻骚动的世界。车子在路上行驶,脑子里还是难以控制地会想到它们,为了不冲出路边,我只能放慢车速。
我想到傅永会和郑小泉,还有那棵奶奶栽下的槐树,我好像闻到一股槐花香,但又好像不是,似有若无。我突然感觉,砍下槐树枝是一个错误。今后我不会再砍,任凭它枝繁叶茂,而且,院子里还要栽两棵,让槐花香遍布院子。回去后,我想去见见傅永会,跟他说我到坑底看到的景象,还有别的话也想跟他说一说。我想起他讲的那件事,两百年前,应该是清朝中期,一个布政使路过我们村。村中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秀才,拦下他,递上减轻百姓税款的文书。布政使看后发怒,便上报更大的官,他们认为他扰乱民心,把他给砍了,家人受到株连,也都被杀。傅永会看到我们村竟然能出这样的秀才,想必这村一定风水好,便留下了,至于杜春说的未婚先孕,他倒没说。
脑袋好像轻了许多,眼睛看什么都很清晰,我能感觉得到刘梅身后的蛇皮袋一颤一颤的,以及它的愉快情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刘梅的手机响了,她对着手机说:“华贵的手机掉了没找着……咋这样呢,我们马上就到家。”她挂了手机,我问什么事,她说:“杨海用他媳妇的手机打来的,他说小双跟杨海家的儿子、杜春家的喜翠,还有三四个小孩去傅永会家看他的画,傅永会把女人不穿衣服的画拿给他们看,简直是在教坏小孩。傅永会说没有给他们看,是他们翻出来的。他在晒场上画槐树,杨海和杜春,还有四五个男的正往晒场去,要打傅永会一顿,叫我们也去收拾一下他。”她顿了一下又说,“傅永会还跟小孩说,练练胆子,长大了可以去天坑看看。”
我加快车速,并说:“给杨海媳妇手机打电话,叫他们停手,马上停下来。”刘梅说为什么,我停下车,我说给我手机。她犹豫着掏手机,我一把抢过来,翻到刚才打来的号码,拨过去,对方手机已关机。真是怪了,回拨就关机。也许没电了。
我跨上摩托,刘梅一直看着我,呆了似的站着,我说:“上车啊。”她赶忙跨上来。我启动车,快速行驶。西边的太阳看不到,已被大片黑云遮挡,风呼呼在耳边吹,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