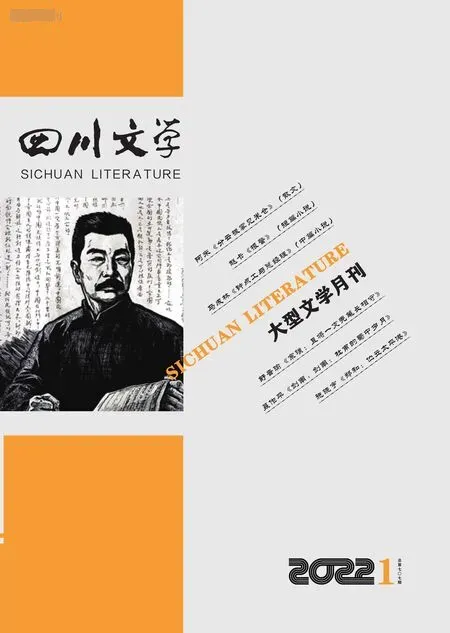通往自知之明
——论陈希我
2022-10-21曾念长
□文/曾念长
一
陈希我刚获得关注那几年,常被归入先锋小说家行列。那是在世纪之交,似乎快要过气的“先锋”一词,由于新潮媒体兴起,新奇之风盛行,因而又变得流行了。大家对先锋小说都有心照不宣的理解,就是讲故事不走正路子,不再正面强攻现实,而是变着花样调戏现实。当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路径朝向死胡同时,小说家借助先锋叙事通向一个新世界,其诗学意义自不待言。但凡有一顶先锋帽子抛过来,许多作家还是愿意接住的。希我却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先锋作家。他说,如果先锋只是玩耍叙事圈套,他就不应该被安放在先锋作家阵列。他又补充道,如何写,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在过去特定时期固然有其先锋意义,但在当下,作家必须重新回来思考写什么的问题。我理解希我这话的意思——作家不该再对现实躲躲闪闪了。希我还真的对现实生活保持了正面关注。补肾、减肥、网聊、养老、移民……这些极富时代色彩的元素时常出现在其小说中,想必都是希我从现实生活中采撷来的。不过希我处理这些元素的方法并不总是稳定的。在少数情况下,他会把这些元素当作一个小说题材来处理,再将其演绎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长篇小说《移民》就属于这种情况。在多数作品中,他只是以现实元素为引子,让小说里的人物出来说话,滔滔不绝地说,直到最后淹没了可能展开的故事,也颠覆了我们对小说的常规认知。我们已然接受了一种观念——小说是一门叙事艺术。参照西摩·查特曼的说法,一个完整的叙事单元由故事和话语两种要素构成。故事是内容(写什么),包含人物、背景、行动和事件。话语是表达内容的方式,回到小说创作中来,也就是解决如何写的问题。是否可以想象,一个小说没有故事,或是故事容量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只剩下大篇幅的话语呢?其实这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一篇没有故事只有话语的小说。希我的多数小说,是话语大于故事。由此得到启示,可以将小说区分为两种,一是故事小说,一是话语小说。话语小说以言说替代行动,以语义变化替代情节演进,最终吞噬了故事的生长空间。这是希我小说给我的直观印象。无须深入探究内在精神构造,仅仅是在可见的形式层面,就可以把希我的小说和其他作家的小说区隔开来了。这时候会发现,希我在小说叙事上也是做形式探索的。他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子。就这一点来看,称陈希我是一个先锋小说家,似乎也无不妥。只不过,很难将他与其他先锋小说家相提并论罢了。
二
在中短篇小说里,希我极少给人物取名字。究其原因,或许是在于,希我将小说人物的关系世界化约到极简状态,要么是“我”和“你”,要么是“你”和“他”(她),要么是“我”和“他”(她)。如果还有多余的人物,就可以从“我、你、他”这三个主体延伸出来。我的妻子,你的丈夫,他的同学……但不可能无限延伸。再看希我的长篇小说,由于故事容量在扩大,人物关系在扩张,许多有名字的人物就出来了。但是我们仔细体会一下,这些有名字的人物依然是在“我、你、他”的基本关系之中生成的。这时候就会发现,希我的小说里其实只有“我、你、他”三个人。在这个由三人组成的小说世界里,“我”是叙事逻辑的第一起点。“我”无处不在。由“我”出发,“你”和“他”获得了有效指认。《抓痒》以第二人称视角来叙述,讲述“你”和“她”的故事。但在“你”和“她”的背后,有一个隐藏起来的“我”,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话语的传递者。《心!》的主体结构以第三人称视角来叙述,但在主体结构内部,有一个时不时跳将出来的“我”。这个“我”是旁观者,也是倾听者,还是评判者。还有许多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小说,“我”是行动者,也是言说者。由“我”的主观视角统摄的三人关系,在希我的小说里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世界。当然,例外的情形总是有的。比如长篇小说《移民》,以第三人称视角讲述一个人的移民故事,“我”的视角完全缺席了。还有少数几个中短篇,也是这种情形。不过,正是这种例外,帮助我们有效识别了真正属于希我风格的小说。当“我”的主观视角缺席时,希我特有的小说味道开始削弱,甚至消失了。理解这一点,或许要回到前头提到的话语小说。话语小说与故事小说的分水岭,就在主客观之间。故事是客观的,但如何讲故事却是主观的。传统现实主义往往以全知视角叙事,就是要赋予故事客观性。一旦希我放弃“我”的主观视角,代之以全知视角,故事的客观性就得到加强,话语的主观性也就随之减弱了。反之,只要希我启用了“我”的主观视角,话语的力量就会被放大,从而大大压缩故事的客观性空间。在希我的已有作品中,将“我”的主观视角发挥到极致的,当属《心!》。仔细体会,你会发现,这部小说里不止一个“我”。每一个向“我”转述故事的人,都是另一个“我”。每一个“我”面对同一个故事,却输出了不同的说法。这个说法,就是话语。话语爆破时,人心被照亮。《心!》的叙述模式,显然是受到了芥川龙之介《竹林中》的影响。这个小说讲述一个武士在竹林中被海盗杀害的故事,就故事本身而言,容量极其有限,但是不同讲述者赋予这个故事不同说法,引爆了巨大的话语空间。据我所知,芥川龙之介是希我推崇的日本作家之一。从《竹林中》到《心!》,我们可以看到相似的文学方法论,而希我对话语小说的探索,又走得更远了。
三
我不止一次想过,希我的小说有可能改编成影视作品吗?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产生,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们已然身处在一个影视为王的时代,一部小说若是成功改编成影视作品,极有可能改变一个作家的生存处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可能性的探讨,从另一个角度来确认希我小说的特征和属性。事实上,在一些场合,我也听希我谈到这个问题。他自然是有自知之明的,不敢对这种设想抱有希望。其中的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影视作品依赖故事性,而希我的话语小说,恰恰是反故事性的。当然,这么说似乎不太准确。从纯技术角度来看,没有谁规定,影视作品一定要讲故事。如果将小说区分为故事和话语两种,影视作品也是可以的。数月前我观看了一部探讨艺术创作和人性真实的电影,叫《马尔科姆与玛丽》。这是一部完全由话语支撑起来的电影,没有行动,没有事件,只有两个人在一套居室里不停地言说,对峙灵魂,坠入深渊。看完电影,我首先想到了希我,立马向他推荐,跟他说,这部电影与他的小说在风格上高度匹配。但我并没有因此天真起来,以为希我的小说就多出了改编成电影的希望。事实上,我们几乎看不到类似的国产电影。生产能力是个问题,消费需求也是一个问题。故事娱情,话语烧脑。没钱赚的电影谁愿意拍呢?就当不切实际好了。我们只需在务虚层面讨论这种可能性。其实,希我的小说不仅可能改编成电影,也适合改编成话剧。我对话剧有一个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以话语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剧种。这又与希我小说的特性不谋而合。不仅如此,话剧表现空间的封闭性和虚拟性,恰恰也是希我小说里常有的空间特征。希我对小说人物的活动空间几乎没什么要求,只要可以说话就行了。《抓痒》写一对夫妻网聊,人物活动没有超出隔着一堵墙的两个房间。《又见小芳》写一个肥胖症富婆的自我救赎,主要场景发生在一座别墅的运动器械房里。就说《心!》这部长篇吧,似乎有着一个波澜壮阔的史诗背景,其实把一个个话语场景拆开来看,都发生在封闭空间里。不仅是封闭性的,而且是虚拟性的。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些空间只是作者的一种假设。假设就发生在这个空间里。这个假设的空间,也可以移置于舞台,成为话剧演员的活动空间。这让我想到了台湾作家王文兴的《家变》,也是一部弱故事而强话语的小说,人物活动空间也带有封闭性和虚拟性特征。这部小说后来改编成了话剧,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二度叙事形式。其实这也是希我的小说该有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希我对话语小说的坚持,是相当彻底的。他对话语内部冲突的表达,距离话剧的表现形式,不到半步之遥。
四
于是问题来了——希我的话语小说是如何发生的。它是反故事性的。它是主观的。它是封闭性的和虚拟性的。所有这些特征,都会层层加重我们的疑问——希我小说的物质性基础是什么?物质决定意识。我相信这一点。故事小说的物质性基础是故事。这个没有什么疑问。故事是对现实生活的模拟,由人物、背景、行动和事件构成,这些元素样样都带有物质属性。话语小说却试图颠覆这种物质性基础,用话语洪流摧毁它们,就像大水冲走龙王庙。但我要提醒大家,希我的小说也是建立在某种物质性基础之上的——即身体。希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小说,往往聚焦于身体,却又不止于身体。《我的补肾生活》和《抓痒》写夫妻双方相互麻木的身体。《我爱我妈》写天生小儿麻痹症的身体。《又见小芳》写一个女人的肥胖不可抑制的身体。就是《心!》,也是以身体自残行动来铺垫冲突叙事。身体是希我小说的物质性基础,是一切话语展开叙述的逻辑起点。由此,我们自然会想到二十年前开始流行起来的身体写作。希我也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亮相文坛的。他赶了一趟时髦吗?从文学内部看,身体写作是对文以载道的一种反驳。道是一种遮蔽物,就像衣服,以安全、伦理和美学的名义掩饰身体的第一存在,抑制其野性动能。从这个角度看,身体写作便具有了某种反遮蔽诉求。然而从文学外部看,当年消费社会在中国蓬勃兴起,呼唤身体感官全面开放,于是身体写作兴起,呼应了时代潮流。回过头来看希我的小说,很难说与当年潮流没有一丁点儿关系。他主张反遮蔽。他也反复写到消费场景。但是最后,我们发现他却是走在潮流对立面。消费社会对身体写作的推动,背后有快乐哲学在作祟。因为消费,所以快乐。消费其实是另一种遮蔽物,就像鸦片,可以帮助我们屏蔽苦痛,制造快乐幻觉。如果没有了这种遮蔽物呢?希我开始抬杠。他指出一个生理学上的常识,人体内有一种阿片类物质,如果这种东西失效了,我们会感受到血液在突奔,神经如闪电。这当然是一种极端情况。希我就是这么极端。于是他成了极少数的反对派。他不写快乐,而是写痛苦。他回到痛苦的物质性根源——肉体疼痛。于是,我们阅读希我的小说,可以从《我疼》开始。这是直接以肉体疼痛为主题的一个作品。还有更多作品,不是以肉体疼痛为主题,但是如果把肉体疼痛这部分内容抽走,我们就会发现,小说的叙事逻辑轰然倒塌,或难以为继,或难以结局。所以,肉体疼痛是希我小说的基础神经元。于是可以对前面的一个说法做一个修正——准确一点说,希我小说的叙事逻辑的起点,不是身体,而是肉体疼痛。
五
或许希我不会同意我这般看待他的小说。他更愿意将自己的写作归结为一种宿命,而不是什么物质决定意识。他甚至认为,文学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自己都说不明白。因为从根儿上讲,文学作品无法换算成一种逻辑语言提供给别人重新理解。他人更是说不明白。就像一个捕蜻蜓的人,无法明白蜻蜓飞翔的感受。然而这种说不明白的文学观,其逻辑起点也是与肉体疼痛相通的。肉体疼痛具有内向性质。我痛了,我醒了,只有我自己体会得到,实难为外人道,更别指望获得他人同情。即便有同情,也仅是一种伦理学意义上的反应,或知识学上的推理,却永远无法有效抵达别人的肉体疼痛。我们到医院就诊,医生问我们如何痛。我们实在说不清楚的,也无法将这种疼痛编成一段程序发送到医生的身体上,让他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感同身受。我们只好说酸痛,或刺痛,或隐痛。其实词不达意。医生接收到的,也不是疼痛本身,而是关于疼痛的某个概念。而他对病人肉体疼痛的理解和反应,不过是建立在知识和逻辑之上的一种推理罢了。然而正是这种不明觉厉的肉体疼痛,让我们意识到有一种黑暗存在,无法被人类的理性之光照亮。这种黑暗存在只能自己照亮自己,正如我们只能以疼痛的方式获得对疼痛的真切感知。一旦希我将肉体疼痛作为小说叙事的逻辑起点,他就进入了一种黑暗写作,开启了“我”对“我”的探索。“我”无法照亮他人,也不能被他人照亮。但“我”通往自知之明。“我”由此获得了一种方法论。“我”确认了一种自作自受的疼痛诗学。由此,我们又回到了希我小说的发生学问题。希我不向外求。他没有将小说的内在叙事逻辑建立在广阔的现实生活之上,这是他与其他现实主义作家的根本不同。尽管他的小说从来不缺乏现实生活素材,但仅仅是素材而已。他拒绝将这些素材当作题材来处理。当一个作家试图在现实生活中确立写作题材时,他是在理解别人,理解一个广阔的外部世界,就像医生理解患者和疾病一样。这种写作方法固然也是一种类型,然而在科学理性如此发达的今天,倘若文学认知世界的方法与科学并无不同,是不是意味着它们可以合并同类项了呢?至少在希我这里,文学是不会被合并的。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它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太过现实了,太过物质了,太过客观了。希我也在理解现实,但他绝不依赖现实。他说,文学躲在现实题材里,作家就浅薄化了。又说,文学面对虚无,面对深渊。这种虚无和深渊,就是一种从“我”的肉体疼痛中抽象出来的黑暗存在。没有故事,只有话语。没有角色,只有不停分裂的“我”。没有背景,黑暗就是它的背景。
六
我意识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故事与叙事。没有故事,何来叙事?或者说,没有现实,何来文学?面对希我的小说,李敬泽提出一个问题:“精神叙事何以可能。”这是一个触及文学本质的问题。请留意关键词——“精神叙事”。叙事不是文学的专利。历史学家在叙事。人类学家在叙事。摇篮边的妈妈也在叙事。只有叙事向内转,穿过物质事件,抵达精神事件,才算是文学叙事。但是一个作家如何抵达精神事件?这是文学的内在难题。对希我来说,这同样也是一个难题。他喜欢引用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的一个说法——除非受到刺痛,否则我们从来不曾注意我们拥有一颗灵魂。但是注意到灵魂之后,该怎么办呢?这是一颗因痛而苏醒的灵魂,作家该如何面对它?如果肉体神经没有麻醉,痛就会清醒,就会自明。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揭示痛,比如用舌尖去试探牙疼,或用手指去触碰伤疤。灵魂没有了麻醉药,也开始自明。与其说是自明,不如说是自我审判。这样,就看到了希我小说的另一种情形——不涉及肉体疼痛,直接展开灵魂审判。中篇小说《父》刚发表时,一度广受关注,可能是希我小说中最受公众认可的一部作品。个中原因或许在于,读者看到了家庭伦理题材,看到了当前社会热点。其实这是一种误读。希我写的依然是灵魂审判。父亲出走了,四个儿子开始商量着寻父。但他们没有行动起来,而是在商量中展开灵魂辩诘。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客观现实被虚化了,主观现实凸显出来,类似于摄影里的变焦手法。所谓变焦,就是歪曲客观,变现主观。我们把希我的作品按创作时间摆开来,可以看到主观色彩逐步增强的渐次变化——从肉体疼痛叙事走向纯粹灵魂审判的精神叙事。主观色彩越浓,叙事手法就更趋简明——将数个虚拟人物放在一个虚拟空间里,让他们展开虚拟对话,类似于审讯室里的场景。审讯室是一种类虚拟存在。一个人被推进审讯室,意味着部分人生现实已暂时清零,或者说,已转化成灵魂现实。希我将人物推进完全虚拟的灵魂审讯室,但是往往不安排审讯官,而是让他们自话自说。希我也不是审判官。每个人都在自我审判。其实我发现,用审判一词也是不准确的。审判是正义对非正义的矫正。但在希我这里,对与错,真与假,最后都瓦解了,灵魂不过是回到一种疼痛的自明状态。这就是希我的精神叙事。
七
再说一部作品——《普罗米修斯已松绑》。“我”接到学院交给的一个任务,为即将到来的百年校庆导演一部舞台剧。本子是学院一个学生提供的,但“我”不满意,先是修改,不行,干脆自己重新创作。但是新本子触怒了学院领导。为了保住前程,“我”只好妥协,请求父亲为“我”说情。这是《普罗米修斯已松绑》的主要内容,围绕一个剧本展开,大部分篇幅用在了对重新创作的剧本内容的陈述上。这个小说是希我在创作长篇《心!》的过程中,临时起意挥就的一个中篇。因此我们可以读出两个作品在同一种思想状态中的某种天然联系。然而就表达有效性而言,《普罗米修斯已松绑》或许更胜一筹。首先是形式有效性——陈述一个剧本,必须借助密集的话语流,这是对希我小说特质的一次发挥。其次是内容有效性,充分体现在那个新剧本内容的构思上——几户城里人家在城郊山上一个山庄里度假,与强索保护费的村霸发生冲突,在高校从事美术专业的李老师将一个村霸打伤了,村民封锁道路,要求山庄里的人交出打人者。被困山庄的城里人展开了激烈的话语交锋。起初大家欢呼胜利,拥护李老师。接着大家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和李老师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将李老师交出去,他们才能为自己松绑,于是他们在言说中相互拉扯和平衡,最终供出了李老师。众人下山之后,动用关系资源解救李老师,但是李老师不肯接受他们的解救,也不愿与村霸讲和。新剧本编到这里就被打断了,重写剧本的“我”也不知道该如何结尾。作为读者,我们可以看到,剧本里的每个人都从现实逻辑出发,以无可置疑的话语维护着各自的正当性。但是这种正当性被李老师否定了。李老师以知识分子身上残存的一点血性、冲动和执拗否定了他们。这似乎是对微弱之光的礼赞。但是,希我接着写道,学院领导对这个新剧本非常不满,多次沟通失败之后,将“我”驱逐出门。对未来导演生涯充满了想象的“我”,感觉像是被逐出天国,在惶恐中寻求父亲的帮助。父亲是学科带头人,在学院里说话一言九鼎。但是父亲劈头盖脸将“我”训了一顿,说剧本中那个李老师不负责任,以无所谓有的一点小原则,绑架了众人的现实利益。父亲的训词同样是无可辩驳的,残存的那点微弱之光也覆灭了,“我”感觉整个世界在直线崩塌。现在,让我们从这个小说里走出来,回到希我个人境况中,你就会明白这个小说是一部元小说,是希我对自己的写作理想和处境的一种隐喻式书写。表面上看,李老师有知识分子的理性,其实他是非理性的。他最先拒交保护费,乃至把大家从被勒索的处境中解放出来,靠的是一点血性、一点冲动。当大家认为事态可以得到妥善处理时,他却不肯妥协和讲和,又是因为他非理性的认死理。相反,山庄里的其他人,还有学院里的领导,也包括他的父亲,都是高度理性的,他们识大体,他们顾大局,他们懂得两全其美,他们用理性文明之光照亮世俗生活里的天国。在这个天国里,非理性的李老师成了一种有害的存在,而那个在剧本中虚构了李老师的“我”,也被逐出了天国。为了强化这种隐喻性表达效果,希我植入普罗米修斯的意义符号。我们理解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可以先参考一下弗洛伊德的观点——每一种人类文明在其发端之初,都有一个或数个受难者形象出现,其发生机制是人类的神圣性冲动在起作用。从普罗米修斯的神圣性冲动,到李老师的血性冲动,再到希我的黑暗写作,都是一种在黑暗中找光的行动,却又走到了光的对立面,或被强光吞噬。普罗米修斯已松绑,意味着人类神话的终结,意味着神圣性冲动的溃败。而希我的黑暗写作,或许也无法被理解和接纳。它依然只是一种自知之明。
八
突然间想到了另外一个闽人——明代思想家李贽。李贽,字卓吾。希我与卓吾,字面意思何其相似。只要对着这两个名字稍做凝视,便能嗅出一种自命不凡的味道。这种味道是危险的。一个人视己不群,又一意孤行,必将众叛亲离。似乎是冥冥天意,他们果真应验了这种命运的自我安排。起初,李卓吾将自己放逐,远离闽南故土和族群。他相信,他乡必有知音,可以日夜切磋,可以尽情嬉游。后来他发现,身边朋友所剩无几,讨伐他的人却日益增多。明白这一点时,李卓吾已入晚境,亦陷入了绝境。那么,希我也走向绝境了吗?许多年前,李敬泽始读希我小说,一度以为希我的写作已到尽头。许多年后,他惊讶地发现,希我还在写作的路上继续前行,而且是走在一条伸向黑漆漆夜空的路。这么说来,希我还没有把写作的路走死。但在这条路上,他冷暖自知,其心境终究难被外人证实。在多数人看来,他走得更像是一条绝路。想必希我也时时有身陷绝境的感觉吧。当他茫然四顾时,猛然发现路上就他孤身一人了。他的朋友越来越少,其情形与晚年李卓吾几无二致。事实上,他要比李卓吾更艰难一些。李卓吾至少在早些年有不少交心朋友,即便在进退维谷的至暗时刻,也有一些不离不弃的追随者。而希我自始就是一人独行。尽管一路走来也收获不少喝彩,不过喝彩的人极有可能是路旁看客,也有可能只是给予精神支援的加油者。三十多年前,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希我还在读大学时写了一篇小说,获得其师孙绍振的赞赏。他惊异于希我竟有一颗如此黑暗的心。他固然包容了这种黑暗。但他终究不同于希我。他更像是手持理性之光的精神导师。然而希我的那颗黑暗之心还是被鼓动起来了,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希我有了一些追随者。这一点又与李卓吾相似了。但这些追随者是同行者吗?希我固然也享受被拥趸的满足,但很快又清醒了过来。他说自己走不通的路,也不该让别人跟着走。这何尝不是一种自知之明?我猜想希我的内心是反复纠结的。他也渴望被认同,但是这种认同一旦顺畅起来,他的黑暗之心就会变得暖和、变得光明,希我也就不是希我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自绝于群。他终究克制住了,没有让自己成为一个前呼后拥的精神导师或文化英雄。事实上他也做不了。在这个时代,除了利益捆绑,还有谁会更关心谁呢?我们都活在自顾不暇的心境中,一个沉沦的人看不到另一个人的沉沦。而我阅读希我的小说,一直以来也是流于表面的。虽然我也早早领会了希我的勇气,惊叹于他的彻底和决绝,但我也只是看客而已。只是随着年龄渐长,我又慢慢在希我的小说里读出了许多隐秘的真切经验。这让我惶恐。我怀疑,我连面对希我作品的勇气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