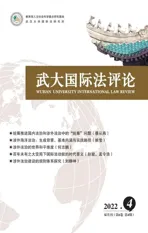我国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适用困境与完善建议
2022-10-20王伟峰
王伟峰
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6月17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一揽子协议是各成员方为应对当今以及将来世界面临的挑战所做努力的集合,其中包括对知识产权相关规定的共识,针对疫苗等医疗用品的供需分配难题而重申《TRIPS协定》第31条所规定的灵活性安排,要求适当放宽该条款的适用条件,如不管适格成员(eligible Member)国内法中是否含有强制许可制度的法律规定,该成员都可以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如行政令、紧急法令、政府使用授权以及司法或行政命令)利用《TRIPS协定》第31条规定的专利且无须征得专利权人的同意,从而以最大可能保障相关用品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①See WTO,WT/MIN(22)/30.
之所以“重申且重置”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适用,不仅仅因为南非、印度等一众国家提议临时豁免《TRIPS协定》的相关义务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根本原因还在于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对紧急危机确有应对之效。
众所周知,《TRIPS协定》重要的目标之一是确认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并加以保护,以促进技术创新、减少贸易障碍。因此,就专利而言,除非获得专利权人的同意,否则其他人不得使用该专利。但成员方也意识到只有“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①[德]E.博登海默:《法理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27页。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对私权的保护并非绝对,私权保护之外还有公共目标需要实现。《TRIPS协定》第31条以及31条之二所规定的强制许可制度便是为践行该协定的公共目标而设置的灵活性安排。
具体而言,专利强制许可是指,在一定情况下国家依法授权第三人无须经专利权人的许可即可使用受专利保护的技术,包括生产、销售、进口有关专利产品等,同时,要向专利权人支付一定的使用费。②参见林秀芹:《TRIPs体制下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其灵活性体现为不经专利权人同意即可使用专利技术。这一灵活性安排对于实现某些公共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举例来说,当某成员方出现公共健康危机,而相关专利药品又不具有充分可及性时,政府可基于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授权适格第三方利用该专利技术生产药品以解决药品供应不足等问题,从而保障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当然,强制许可的专利对象并非仅限于药品领域,但医药领域是体现生命健康与私人财产权冲突最为直观的领域。需要注意的是,灵活性指的是《TRIPS协定》所具有的特征,即同时涵盖私权保护和公共利益保障的制度安排。虽然两者同样重要,但在社会现实中却呈现为私权保护的“一般性”和公益保障的“例外性”,毕竟公共健康危机出现的情况总是较少的。
然而,作为《TRIPS协定》灵活性安排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在其自身的适用上可能并不灵活。一方面,为避免该制度滥用而损害专利权人的利益,《TRIPS协定》为该制度的适用规定了较多程序上的限制,如拟使用主体须事前与专利权人协商以做出相当条件下获取专利的努力等;另一方面,在已将该制度引入国内法的成员方立法中又不可避免存在规定上的出入,有的照搬《TRIPS协定》的规定,有的对该制度的适用程序施加更重的负担。由此,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上的双层“赋重”,加上部分专利强国反对、专利所有人抵制等,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可适用性大幅降低。因此,南非、印度等成员提出了《TRIPS临时豁免提案》,理由之一便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具有“个案性”(一事一议)和“低效性”,无法及时、充分地应对目前大范围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③See WTO,IP/C/W/672,pp.4,20.进而催生了前述WTO部长级会议上对相关规定的共识。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专利强制许可这一制度在整体上囿于各种程序和非程序的限制而无法充分发挥其作为灵活性安排的效用,但是其所包含的专利政府使用制度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程序冗杂的缺陷。专利政府使用往往与专利强制许可一同被提及但却经常被忽视。专利政府使用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特殊类型,两者是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专利强制许可有不同的适用事由,其国际法渊源《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5条A(2)款和《TRIPS协定》第31条均未对专利强制许可的适用事由做出详细规定,①《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5条A(2)款规定:本联盟各国都有权采取立法措施规定授予强制许可,以防止由于行使专利所赋予的专有权而可能产生的滥用,例如:不实施。但《TRIPS协定》第31条(b)款对特殊程序的规定中提及三个具体的适用事由,即“在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或在其他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或在公共非商业性使用情况下”,其中,“公共非商业性使用”又称为“政府使用”(government use)。②See WTO,Obligations and Exceptions,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rips_e/factsheet_pharm02_e.htm#compulsorylicensing,visited on 18 September 2021.
专利政府使用作为一种特殊的专利强制许可类型具有政府主导、程序便捷等优势。例如,前述WTO部长级会议所达成的共识提到要有选择性地放宽相关成员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限制,其中包括豁免前置协商程序。前置协商程序是指专利拟使用主体要在此种使用之前按合理商业条款和条件努力从权利持有人处获得授权。但专利政府使用制度本身即已获得对此种程序要求的豁免。因此,专利政府使用相较于一般专利强制许可类型具有程序上的优势,是应对紧急、严重危机的重要工具。但目前这一工具在我国缺乏详尽的配套立法,实施程序规定不清,参与主体职权不明,甚至学界对于该制度在我国是否存在仍存在争议。③参见刘义胜、田侃:《根据〈专利法〉第49条研究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可执行性》,《中国新药杂志》2016年第22期,第2584页;王丽华:《从WTO有关强制许可的规定看我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第63-64页;王江、李佳欣:《我国绿色技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实施的多重障碍及破解》,《环境保护》2021年第1期,第49页;刘宇晖:《论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兼评〈专利法〉第三次修订的相关条款》,《河北法学》2010年第4期,第110页;林秀芹:《TRIPs体制下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38-440页。此外,虽然基于前述WTO部长级会议决定,有选择性地放宽相关成员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限制,如不以立法为实施前提、实施类型可多样化、免除国内市场限制要求以及豁免前置协商程序等,但该共识具有时限要求,即适格成员应在5年期内适用该决定(虽然总理事会可以视情况延长该期限),但是,完善国内相关立法才是根本应对之策,而非仅在危机情况下依赖国际层面的共识。为此,本文将分析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比较优势,梳理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相关实践,并在剖析我国专利政府使用制度适用困境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
二、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比较优势及镜鉴
(一)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比较优势:政府主导、程序简捷
专利政府使用制度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以“不经专利权人同意而使用相关专利”为根本,以“政府自己”是专利拟使用主体为特殊,故名为专利政府使用。
实践中可以基于不同的事由适用专利强制许可,如滥用专利、专利发明未得到实施或未得到充分实施、反竞争行为和/或不公平竞争、紧急情况或极端紧迫情况、公共利益、公共非商业性使用、未能以合理的条款满足市场需求、公众的合理要求未能得到满足,为制造和向制药部门制造能力不足或没有制造能力的国家出口而授予专利制药产品的强制许可以及在植物品种与专利发明相互依存的情况下授予专利强制交叉许可等。其中,“公共非商业性使用”这一事由下的专利强制许可一般被解读为专利政府使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的专利法常设委员会在其起草的《关于强制许可例外的参考文件草案》(以下称《草案》)中指出,“一般而言,公共非商业性使用是指由(或用于)政府为让公众受益的使用,其性质为非商业性,即使专利是由行政相对人使用也是如此。通常,这类使用称为‘政府使用’”。①WIPO,SCP/30/3,pp.20-35.
从上述概念来看,专利政府使用制度适用需要满足公共性、政府主导性。首先,专利政府使用的适用事由具有公共性。专利政府使用是为让公众受益的使用,具有“非商业性”。一般来说,“如国家安全、营养、健康或国家经济其他重要部门的发展有此需要的,或者,如果政府使用适当地矫正了专利权人或其被许可方从事的反竞争行为,则允许政府使用”。②See WIPO,SCP/30/3,para.167.专利政府使用的适用事由较为广泛,这使其与一般类型的专利强制许可的某些适用事由存在交叉性。例如,公共利益、国家紧急状态等情况既可引发专利政府使用的适用,也可引发专利强制许可的适用,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仅在不同的解释中存在细微的实质性差别。③See WIPO,SCP/30/3,para.152.其次,专利政府使用制度下专利拟使用主体具有专门性,即“政府自己”,因而具有政府主导性的特点。专利政府使用制度中目标专利的拟使用主体是政府部门或者政府拥有的机构、政府指定的能够代表政府的自然人或者法人等相关机构。一般情况下,商业实体可作为承包商(contractor)成为专利政府使用的适格使用人。①See Carlos M.Correa,Guide for the Granting of Compulsory License and Government Use of PharmaceuticalPatents,https://www.southcentre.int/wp-content/uploads/2020/04/RP-107.pdf,visitedon2May2021.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其他代表政府的自然人或法人,其最终均表现为由(或用于)政府的使用。
专利政府使用作为一种特殊的专利强制许可类型,相较于其他一般类型下的专利强制许可,还具有程序简捷的比较优势。
为使私权与公益之间的价值保护达致平衡,《TRIPS协定》中引入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但专利强制许可对私权“侵害”的可能性也促使《TRIPS协定》成员方为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设置了较多程序上的限制,因而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制度实际效用的发挥。②参见林秀芹:《TRIPs体制下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9-104页。根据《TRIPS协定》第31条,要想适用专利强制许可制度,需要遵循的程序要求有12项之多,如个案审查、事前协商、司法审查等。相较而言,专利政府使用却得以豁免事前协商的程序要求。不仅如此,由于专利政府使用的专利拟使用主体是“政府自己”且不经过事前协商程序,在具体的启动等程序上也存在特殊性。不同于专利强制许可程序是经第三人申请启动,专利政府使用程序是政府部门依职权(ex officio)直接启动。③See Carlos M.Correa,Guide for the Granting of Compulsory License and Government Use of Pharmaceutical Patents,https://www.southcentre.int/wp-content/uploads/2020/04/RP-107.pdf,visited on 2 May 2021.当政府部门在判定出现需要适用该制度的情形时,其可以不经与专利权人的协商而依职权直接授予“政府自己”使用相关专利的许可。无论是决策还是实施,程序均由政府控制,这样的程序设置使政府能够更迅速有效地对紧急情况做出反应,充分体现出政府主导的特点。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政府同时作为程序的决策和实施主体,免去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调程序,如一般专利强制许可类型下的申请、决定等程序,但若要保证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实际效果,还有赖于各国具体立法保障专利政府使用程序设置的行政效率。因为,即使是“政府自己”同时作为专利政府使用程序的决策、启用以及实施主体,也可能由于政府部门或机构的多样化导致因涉及多部门而效率低下,从而丧失该制度程序优势。
(二)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实践及经验借鉴
对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考察一般可以分为两部分,即立法和实施。《TRIPS协定》各成员方在引入专利政府使用制度时基于不同的考虑会有不同的立法和实践。
1.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立法考察
WIPO专利法常设委员会在“专利权的例外和限制”这一议题下专门对专利政府使用的国内立法情况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调查并形成了相应的参考文件草案。①WIPO专利法常设委员会在2014年第20届会议上同意就“专利权的例外和限制”这一议题展开讨论,就“强制许可和/或政府使用”这一问题,为使信息更易理解,秘书处将之区分为专利强制许可和专利政府使用两个文件(SCP/21/4 Rev.和SCP/21/5 Rev.),并最终针对专利强制许可和专利政府使用形成了一个综合参考文件草案(SCP/30/3),https://www.wipo.int/patents/en/topics/exceptions_limitations.html,2022年7月15日访问。从WIPO专利法常设委员会秘书处专门对专利政府使用编写的文件(SCP/21/5 Rev.)来看,其调查主要涉及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目标以及具体事由,国内法依据,决策及实施主体,专利权人得以被通知、获得报酬等权利以及该制度的实施障碍等方面。
就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基本目标而言,各国普遍以实现公共政策为目的。公共政策的具体内涵又有不同,例如,紧急情况,营养、健康或国民经济其他重要部门的发展有此需要,或者如果这种使用能充分弥补专利权人或其被许可人的反竞争行为等。甚至有立法做出极广泛设定,认为专利政府使用是“没有限制”的。②See Chapter XVII and Section 47 of the Patents Act of India.
在国内法层面,一般可分为两种立法模式,即单独立法模式和混合立法模式。单独立法模式是指,国内立法中针对专利政府使用没有单独条款规定,其形式或者名称往往不同,如“专利的征用”“国家对专利的获取”等;而混合立法模式则指的是将专利政府使用的规定囊括于专利强制许可条款中,类似《TRIPS协定》第31条,将之作为专利强制许可的一个特殊类型加以规定。就前者而言,单独立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加清晰且实操性强的优势。单独立法模式往往会对专利政府使用制度进行更为详细的规定,典型代表如英国1977年专利法中明确将专利强制许可与专利政府使用分别进行规定。专利政府使用在英国专利法中名为“为王室服务使用专利发明”(use of patented inventions for services of the crown),该部分包含6条规定,而专利强制许可则在前一部分“权利许可和强制许可”(licences of right and compulsory licences)中以10条规范加以规定。在“为王室服务使用专利发明”这一部分,除基本规定外,还包括对王室使用(crown use)规定的解释、第三方的权利、与王室使用有关争议的建议以及紧急情况下王室使用的特别规定等。③See The Patents Act 1977,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50221/consolidated-patents-act-1977.pdf,visited on 26 July 2022.可见,在此模式下,详尽的立法规范无疑会从法律依据层面极大保障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可实施性。除英国外,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专利法也采用这一立法模式,且澳大利亚在其立法中专门对“专利药品发明强制许可”(patented pharmaceutical invention compulsory licences)进行了规定。①See German Patent Act 1980(Federal Law Gazette 1981),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patg/englisch_patg.html;Australian Patents Act 1990,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9C0-0088,visited on 26 July 2022.相反,法国、中国等成员方则采用的是混合立法模式。以法国为例,真正体现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条款是在专利强制许可诸多事由中的国防目的下,依职权获得专利使用许可,无论这种使用是由自己进行还是由其代表进行。由于仅有此一条规范,相对来说,其具体实施时的可参照性较弱。
对于决策和实施主体来说,前者一般是政府有关部门,如“部长”“国家行政部门”“国家”“国王”“主管当局”等,尽管名称各异,但其具有相同的特征,即都能代表政府,而各国对实施主体的规定则相对较为统一,大多规定为“政府”“政府机构”或者“政府指定的第三方”。在专利权人被通知和获得报酬的权利方面,由于《TRIPS协定》第31条中有硬性规定,因此各国对此均有相应的义务规定,不同的是,各国对通知的时间或者报酬的计算方式有一定区别。此外,各国在其自由裁量的范围内还对专利政府使用的期限、范围等其他方面加以限制,例如“使用的范围和期限应限于授权使用的目的”等。②See WIPO,SCP/21/5 Rev.,pp.6-8.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实施方面,绝大部分成员方认为其国内现有的法律框架能够满足现实需要,不构成适用上的障碍,只有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少数国家表示其国内关于专利政府使用的法律规定仍不充分。除此之外,还有的国家(如乌干达)表示,技术问题才是阻碍专利政府使用制度具体落实的主要障碍。③See WIPO,SCP/21/5 Rev.,pp.9-10.
虽然绝大部分成员认为其关于专利政府使用的立法框架不会阻碍该制度的具体落实,且仅有摩洛哥、不丹、卡塔尔等少数国家表明有修订立法的意愿,但事实上,专利政府使用基于现有国内立法真的不具有实施障碍吗?答案似乎并不像TRIPS成员所言。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在2020年3月25日颁布《新冠疫情紧急应对法案》(Covid-19 Emergency Response Act),该法案第12部分对加拿大专利法“政府对专利的使用”部分做了修订,其主要修订是在原第19.3条后增加第19.4条。新增加的第19.4条内容主要有三个亮点:一是将专利政府使用的申请主体扩展至卫生部长,而原来仅限于“加拿大政府或某省政府”;二是将专利拟使用主体扩展至私人,即“政府和申请中指定的任何人”,而原条文仅限于政府;三是通知结束授权,即授权结束的方式包括卫生部长通知专员不再需要该授权,而原来是需要经专利权人申请、专员审查确认才会终止授权。从上述修订内容来看,专利政府使用制度在应对紧急且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时需要更为完善的程序和主体规定。就程序方面而言,快捷迅速落实该制度以应对紧急情况,需要授权最熟悉现状的有关主体推动该制度的实施,在遭遇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况下,卫生部长无疑是最了解情况的,因此授权卫生部长启动该程序,并授权卫生部长“通知”终结程序,使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整套程序运行最大程度掌控在最了解现实情况的主体手中,有利于充分保障程序运行的有效性,发挥该制度的功用。就主体方面而言,除前述将程序的控制权授予最了解情况的卫生部长外,还扩展了专利拟使用主体的范围,不仅包括原有规定的政府主体,还包括卫生部长指定的私人主体,该举措虽然是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应有之义,但事实上加拿大通过本次修订才将政府指定的私主体纳入专利拟使用主体之列。专利政府使用制度中程序和主体设置问题并非仅体现于加拿大此次的修法实践中,在早期涉及专利政府使用的具体案件中早已有所展露。
2.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实践考察
中国台湾地区在2005年为应对全球性禽流感疫情颁发强制授权案中因程序问题而引发争议,最终导致“专利法”修订。①中国台湾地区“专利法”将《TRIPS协定》中“未经权利人授权的其他使用”制度称为强制授权,其含义与本文中的专利强制许可相同。当时“智慧财产局”依据原“专利法”规定的因应紧急情况而颁布强制授权,但由于原“专利法”中规定了给予专利权人3个月的答辩期限,而此次授权又未履行该期限的规定,因此引发专利权人的程序质疑。②参见朱怀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258页。根据《TRIPS协定》第31条的规定,处于紧急状态或其他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或在公共非商业性使用的情况,这三种特殊情况的实施程序应当更具有便捷性。换言之,依据不同事由启动的专利强制许可在程序上是有不同要求的,前述三种情况下的实施程序理应区别于其他一般专利强制许可类型的实施程序,应减少对其程序上的限制条件以更迅速地应对紧急、严重情况。但中国台湾地区“专利法”并没有给予紧急情况下的强制授权以“优待”,而是适用一般的强制授权程序,从而产生上述争议。
为弥补上述缺漏,中国台湾地区在2011年修正的“专利法”中完善了对强制授权的规定。新修正的“专利法”对强制授权分类实施,即区分不同的强制授权启动事由,进行不同的程序设置。其第87条第1款规定:“为因应‘国家’紧急危难或其他重大紧急情况,专利专责机关应依紧急命令或‘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之通知,强制授权所需专利权,并尽速通知专利权人。”第89条规定:“依第八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强制授权者,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无强制授权之必要时,专利专责机关应依其通知废止强制授权。”①参见中国台湾地区“专利法”第87-89条,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lp-677-101-xCat-01.html,2021年3月12日访问。这一程序设置不同于其他(如为增进公益之非营利实施、依赖性以及限制竞争或不公平竞争等)情况,无前置程序、无专利权人限期答辩等程序性要求。同时,其终止程序不同于其他情况下“特许实施之原因消灭时,专利专责机关得依申请废止其特许实施”,而修改为专利专责机关依照“‘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通知废止强制授权。
综上,无论是从各法域的自我评估还是具体实践来看,除技术等客观原因外,法律框架的完善与否都是影响专利政府使用制度具体落实的关键因素。具体到法律规定,专利政府使用的参与主体和程序设置又是影响其功用的重要因素。
三、我国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现状及适用困境
(一)我国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相关规定
专利政府使用一直被学者呼吁引入我国《专利法》中。②参见刘义胜、田侃:《根据〈专利法〉第49条研究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可执行性》,《中国新药杂志》2016年第22期,第2584页;王丽华:《从WTO有关强制许可的规定看我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第63-64页;王江、李佳欣:《我国绿色技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实施的多重障碍及破解》,《环境保护》2021年第1期,第49页;刘宇晖:《论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兼评〈专利法〉第三次修订的相关条款》,《河北法学》2010年第4期,第110页;林秀芹:《TRIPs体制下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38-440页。但我国《专利法》中是否确无专利政府使用的规定呢?事实上,WIPO专利法常设委员会在2014年报告中所列国内法律规定包含专利政府使用的国家中即含有中国。③See WIPO,SCP/21/5 Rev.,para.4.我国《专利法》④本文采用2008年《专利法》版本。因为2020年新修正的《专利法》对原第49条(现第53条)未做修改,且现行有效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中有关规定对应的是原2008年《专利法》版本,因此,为方便起见采用旧版本《专利法》规定。第49条应为专利政府使用的主要国内法渊源。该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第6、12、18、21条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以下称《意见》)中的第12项规定。①《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第6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专利法》第49条的规定,建议国家知识产权局给予其指定的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强制许可。第12条规定: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根据《专利法》第49条建议给予强制许可的,应当指明下列各项:(1)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目的需要给予强制许可;(2)建议给予强制许可的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名称、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以及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3)建议给予强制许可的期限;(4)指定的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名称、地址、邮政编码、联系人及电话;(5)其他需要注明的事项。第18条第1款规定:请求人或者专利权人要求听证的,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听证。第18条第6款规定:根据《专利法》第49条或者第50条的规定建议或者请求给予强制许可的,不适用听证程序。第21条第2款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专利法》第49条作出给予强制许可的决定前,应当通知专利权人拟作出的决定及其理由。《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规定:明确药品专利实施强制许可路径。依法分类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提高药品可及性。鼓励专利权人实施自愿许可。具备实施强制许可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依法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强制许可请求。在国家出现重特大传染病疫情及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防治重特大疾病药品出现短缺,对公共卫生安全或公共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等非常情况时,为了维护公共健康,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进行评估论证,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实施强制许可的建议,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作出给予实施强制许可或驳回的决定。
上述六款规定共同构成了我国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法律基础。
首先,就专利拟使用主体来说,涵盖范围较广,包括政府以及其他适格主体。《专利法》第49条仅规定“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可以给予……强制许可”,但对如何给予、给予何人等都未做具体规定。而《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第6条对此进行补充规定。其中,“指定的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即为专利拟使用主体。可见,实施主体除了应当“具备实施条件”之外,并无其他资格限制。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自然人或者法人,只要“具备实施条件”都可作为实施主体,充分体现了专利政府使用制度下专利拟使用主体的广泛性。当然,我国的这种规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为与一般强制许可中专利拟使用主体用语相同,即都采用“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而一般来说,《TRIPS协定》的成员方大多将之规定为“政府”“政府机构”或者“政府授权的第三方”,采用这种用语更能体现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特性。
其次,就启动程序来说,无须专利拟使用主体进行申请,政府一方依职权可直接启动。这符合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政府主导和程序简捷的要求。从《TRIPS协定》第31条的规定来看,专利政府使用这一特殊的专利强制许可形式简化了事前协商程序,以便应对紧急情况或实现公共目标。除此之外,《TRIPS协定》第31条对程序的启动方式、启动主体等其他事项未做特殊规定。考虑到该制度下的专利拟使用主体是政府一方(包括政府授权的第三方),该制度的启动程序一般是由政府直接依职权启动而不需要与专利权人进行协商。②See Carlos M.Correa,Guide for the Granting of Compulsory License and Government Use of Pharmaceutical Patents,https://www.southcentre.int/wp-content/uploads/2020/04/RP-107.pdf,visited on 2 May 2021.我国专利政府使用制度是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以提出建议的方式启动程序,是一种依职权的启动方式,符合国际层面上对该制度的规定模式。另外,为与国际层面要求同步,《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第18、21条免除了政府使用的听证程序要求并明确知识产权局对专利权人的通知义务。
最后,在适用事由方面,我国《专利法》第49条明确规定了“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三种事由。从表述来看,该规定与《TRIPS协定》第31条(b)项规定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即使不论及事由所具备的紧急性或者公共目的性,单从规范表述上看,我国《专利法》第49条也与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国际法渊源如出一辙。
可见,专利政府使用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确有存在,且1992年《专利法》修正即引入该制度。①我国《专利法》最初颁布于1984年,在该版本中还未规定专利政府使用制度。1992年《专利法》引入该制度,1992年《专利法》第52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专利局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在法律修订过程中,后续版本除将“专利局”修订为“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之外,未做其他修订。但是,可能现实中较少出现启用该制度之情形,至今该制度在我国实践中并不多见。囿于我国实践上的匮乏以及认识上的不足,我国关于专利政府使用的立法尚有诸多不足之处,影响了该制度的可实施性。
(二)我国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适用困境
1.欠缺详尽的配套立法导致可实施性不强
我国现行立法对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规定仅限于《专利法》《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以及《意见》。而作为《专利法》配套实施立法的《专利法实施细则》并未对此进行规定。
《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第6、12、18、21条作为《专利法》第49条的配套实施立法,仍然较为粗略,不足以指导具体实践。其中,《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第6条明确了在《专利法》第49条所列法定情况下,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强制许可的具体方式,即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建议的方式启动专利政府使用程序。第12条则进一步明确了“建议”中应列明的具体事项,如具体事由,专利的具体名称、专利号、申请日、授权公告日,专利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具体的期限以及具体所指定的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的相关信息等。《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第18、21条则分别在最后一款中规定了专利政府使用制度不适用听证程序以及对专利权人的通知义务。从规定来看,《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中的四个条款仅补充了“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建议权”。但是,对具体实施程序并未作详尽规定,如该建议权的效力如何,“国家有关主管机关”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之间的职权如何分配等。
此外,虽然《意见》专门对药品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做出规定,细化且明确了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的具体事由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即“在国家出现重特大传染病疫情及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防治重特大疾病药品出现短缺,对公共卫生安全或公共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等非常情况时,为了维护公共健康,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进行评估论证,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实施专利强制许可的建议”,但这一规定仍存在立法位阶较低、范围局限等问题,不足以支撑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具体适用。换言之,《意见》仅仅是一项规范性文件,而且仅针对药品这一对象,辐射范围有限,指导性不强。
2.实施程序未做分类易加剧实施上的混乱
专利政府使用作为一种特殊的专利强制许可类型,具有程序简捷的特殊优势。而这一优势最直接的体现方式就是与其他一般专利强制许可类型的程序相区分,正如《TRIPS协定》第31条中免除专利政府使用制度下的事前协商程序一样,我国立法中同样遵循了《TRIPS协定》第31条的程序设置模式。但存在的问题是,专利政府使用制度实施程序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前置程序的豁免,还应包括特殊的启动和终止程序。
根据我国《专利法》的规定,专利政府使用的具体实施程序包括启动、审查、授予、公示、费用确定以及终止等六个环节。其中,与其他类型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程序相比,除启动程序不同(依靠“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以提出建议的方式启动该程序)之外,其他五个程序基本相同,并未对专利政府使用的具体程序做特殊规定(见表1)。专利政府使用的政府主导性应当是一以贯之的,由其决定开始也应由其决定结束,否则会因程序参与主体过多而导致混乱无序。根据现行立法,我国专利政府使用的终止方式包括两种:到期自动终止以及理由消失且专利权人提出申请后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后终止。这两种方式并未体现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尤其是后一终止方式与专利政府使用的程序安排明显不相匹配。根据《意见》中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具体的实施指导,导致需要利用专利政府使用的具体情况是由“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进行评估论证,然后由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建议从而启动程序。换言之,“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是对具体情况最了解的主体,理应由其监督问题的进展以及专利政府使用的具体情况并决定是否做出程序终止的决定。而我国相关规定却规定由并不了解具体情况的专利权人申请结束,明显缺乏合理性。

表1 专利政府使用与其他一般专利强制许可类型的具体实施程序比较
3.参与主体职权不明且决策程序设置不当
根据现行立法,我国专利政府使用中的决策主体包括“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即先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建议,再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做出决定。国务院在《意见》中对相关专利强制许可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做了进一步明确:“为了维护公共健康,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进行评估论证,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实施强制许可的建议,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作出给予实施强制许可或驳回的决定。”从这一表述来看,专利政府使用程序是先由相关主体进行评估论证,进而提出建议,最后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做出决定。根据《意见》,最先的评估论证阶段,国家知识产权局是不参与其中的。然而,这样的程序安排明显不合理,因为,国家知识产权局明显不是最了解情况的主体,即使通过后续建议程序获知具体情况,也无谓造成程序上的冗杂。另外,由于“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这样的表述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因而如果将国家知识产权局解释为“评估论证”的参与成员之一,那么就会使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建议权主体向自己提出建议,这样的安排恐怕也不妥当。因此,就当前的制度安排来说,无论是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主体地位作何种解释都具有不合理性。
四、我国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完善配套实施立法保障可实施性
无论是在主体方面还是在程序方面,专利政府使用制度均需要进一步的详细立法加以补充完善。《专利法》作为一般性立法,需要其他配套实施立法的辅助。具体来说,由于现行《专利法》于2020年修订、2021年生效,对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修正在短期内不宜通过修订《专利法》进行,而应在《专利法实施细则》或者《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中加以细化规定。新版《专利法》生效后,《专利法实施细则》正处修订之际。同时,由于《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运行时间较久需要根据立法及实践进行更新,而且新版《专利法》中原来第六章“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已被现在的“专利实施的特别许可”替代,因此,现行《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或废或改都存在可能,但无论如何都要有所改变。
为了增强我国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可实施性,本文认为,应在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现行国内法渊源——2020年《专利法》第54条的指导下,在《专利法实施细则》中明确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基本规则,并在保留《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的前提下对该制度的具体实施步骤予以系统规定,以此构建一个完善的专利政府使用规则体系。
从目前《专利法实施细则》和《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的具体规定来看,前者对专利强制许可的规定主要涉及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中相关概念(如“未充分实施其专利”)的解释以及专利强制许可请求和使用费率裁定请求。因此,在其修订过程中,也可继续遵循这一思路,对专利政府使用及其相关概念予以解释的同时对其基本实施程序,如实施事由、责任主体以及启动方式等做出基本规定。此外,虽然新版《专利法》按其新内容已将第六章标题“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修改为“专利实施的特别许可”,看似原先独立成章的专利强制许可的重要性因其成为专章之一部分而降低,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当前其对公共健康危机的应对来看,其重要性实际上不减反增。因此,《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不仅仍有保留之必要,且应当对其进行补充完善。从其现有规定来看,该规章仅涉及专利强制许可请求、使用费裁决请求以及终止专利强制许可请求等方面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在该实施办法中对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具体问题,如具体事由的非完全性解释、依职权的启动程序和终止程序、具体责任主体的职能划分、使用费和使用期限以及范围等相关问题予以细化补充。另外,还需要注意在修订过程中应整合先前《意见》中的有关指导性规定,将其纳入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之列,提升其法律位阶。
(二)分类设置具体实施程序保障程序效率性
专利政府使用的程序效率优势需要通过参与主体和实施程序的特殊性设置予以保障,其特殊性是相对于其他一般专利强制许可类型而言的。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主要应用场景在于实现某些公共政策目标,尤其是在应对公共危机方面。公共性事由为减少其程序限制提供了基本的正当性。因此,应用于其他一般专利强制许可类型的程序限制不应加之于专利政府使用制度之上。
此外,在专利政府使用制度下,决策主体从程序启动到结束应一以贯之,保持前后一致性。因为最可能启用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情况就是对一些紧急危机的应对,而无论哪种危机类型,其严重程度以及应对之策都应交由最了解情况的政府部门进行评估决定,且从危机开始到危机结束均应由相同的部门进行监测和评估。因此,与其他依适格主体申请启动的一般专利强制许可类型不同,依职权启动的专利政府使用应在决策主体方面作特殊设置。
(三)明确参与主体的职能划分保障决策科学性
根据我国专利政府使用制度的相关规定,专利政府使用制度中参与主体的职责分工主要存在于“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两个主体之间。
首先,为保障决策的科学性,应当调整前期评估论证主体的范围,即“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应尽可能全面的包含相关部门。在公共健康卫生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医疗保障局、科技部以及商务部等都应涵盖在内,尤其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参与其中,而不应将其设置为后续的审查决定主体。这种制度安排可见于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专利政府使用实践中。泰国在提出专利政府使用建议之前,先是任命了一个小组委员会对相关情况进行认定,该小组委员会的成员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国家卫生安全局、公共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部以及健康和消费者保护团体的代表,如医院医生、艾滋病和癌症患者、法律协会等。①See Suwit Wibulpolprasert,et al.,Government Use Licenses in Thailand:The Power of Evidence,Civi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7 Global Health 4(2011);Jiraporn Limpananont & Kannikar Kijtiwatchakul,TRIPS Flexibilities in Thailand:Between Laws and Politics,in Gaëlle Krikorian &Amy Kapczynski(eds.),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Ag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439(Zone Books 2010).马来西亚同样要求在决定做出之前明确“政策目标”,相关参与主体包括卫生部,贸易、知识产权、公共卫生专家,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国内贸易和消费者事务部以及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官员等。②See Chee Yoke Ling,Malaysia:Government Use Route to Importing Generic Medicines,9 Third World Resurgence(2006).可见,广泛的评估参与主体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保障。此外,参与部门众多就容易产生众口难调的困境,阻碍程序的推进过程。因此,为保障专利政府使用程序的效率性要求,可以设置联合决策机制,如建立国务院联席工作机制,直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相关单位协同运作。专利政府使用或者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实施始终是对于专利的使用,因此,在危机发生时,相关国家部门的协调工作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予以统筹较为适宜。
其次,应当将专利政府使用的决定权直接赋予“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且其实际上通过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牵头的国务院联席工作机制做出实质有效决定。我国专利政府使用决定的做出需要经历“建议+审查”两步走程序,即“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建议,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审查。一定程度上,这种设置与一般专利强制许可类型的启动程序——“申请+审查”相似,无法保障其效率优势。鉴于国务院联席工作机制的建立,在保障专利政府使用决策科学性的前提下,应当将我国专利政府使用的实质决定权赋予“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而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专利政府使用中应仅对相关文件等进行形式审查。事实上,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守门员”作用并未被剥夺,而是将其提前至于国务院联席工作机制中行使而已。此外,对于终止程序,除到期自动终止外,应由前期的评估论证主体——“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在适用事由消失的情况下通知国家知识产权局,并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依照通知做出决定。之所以不再适用“由专利权人申请”,是因为“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才是对适用专利政府使用制度之具体情形最为了解的主体。
结语
我国作为专利政府使用制度实践不多的国家,应对我国专利政府使用制度进行审视。从域外实践来看,专利政府使用制度在应对危机方面的优势体现为程序简捷和政府主导,可迅速有效推进程序以应对危机。其中,关键之处在于主体和程序方面的具体立法安排。因此,亟须在将来修法中明确我国专利政府使用制度参与主体的职权,并将其实施程序与其他一般专利强制许可类型进行分类设置,以为应对危机情形做必要且充分的制度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