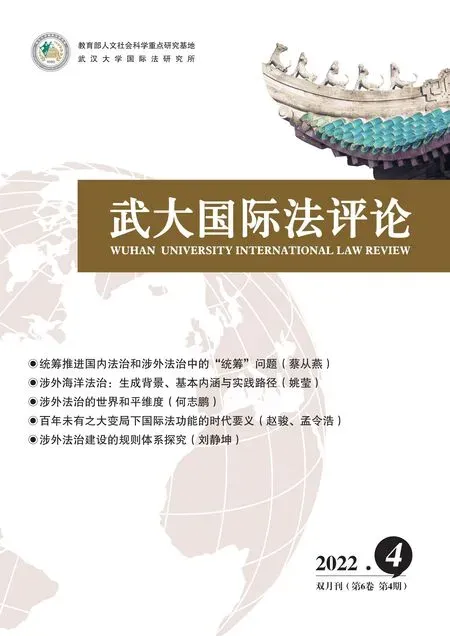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中的“统筹”问题
2022-01-01蔡从燕
蔡从燕
一、导言
2020年11月16—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强调:“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综合利用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开展斗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8日,第1版。这是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法治方略而做出的新决策。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使得涉外法治成为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对于中国法治化的整体进程以及深化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法律秩序都可能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众所周知,“统筹”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的一种工作方法论。毛泽东指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①《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毛泽东生动地用“弹钢琴”描述如何统筹。毛泽东指出:“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不仅强调国内治理中的统筹,而且日益强调国内与国际的统筹。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2014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特别要指出的是,“统筹”一词始终贯穿于202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③《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开宗明义指出,制定该文件是为了“统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各项工作”。尽管如此,由于统筹并非一种新的方法论,能否妥当地统筹,取决于人们是否深刻地理解统筹所处的背景、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所针对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有效的统筹方法。
针对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我国学者已经进行了不少有益的阐述。④尤其参见黄进、鲁洋:《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际法治意涵》,《政法论坛》2021年第3期,第8页;何志鹏:《涉外法治:开放发展的规范导向》,《政法论坛》2021年第5期,第182-183页;马怀德:《迈向“规划”时代的法治中国建设》,《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第33-34页。不过,关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中“统筹”问题的专项研究暂付阙如。有鉴于此,本文讨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背景(第二部分)、目标(第三部分)、内容(第四部分)以及方法论(第五部分)。
二、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背景
我国对国内与国际间的统筹的大力强调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此之前,这种统筹主要着眼于经济事务,旨在推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据此,在强调激发国内市场活力的同时,中国大力吸引国外资本,学习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为此,中国政府以国内为立足点,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近年来,中国所处的国内与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准确理解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所处的新的时代背景,对于中国合理确定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目标和内容,进而寻找妥当的统筹方法而言,是一项前提性工作。
(一)法律在全球范围内被公认是最主要的治理方式
众所周知,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治理方式从来都是多样化的,包括法律、政治、道德等。然而,法律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被公认是最主要的治理方式。法治是人们认为法律应当具备的良好的品格,尽管人们对法治的含义迄今为止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参加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的各国领导确认:国内层面与国际层面的善治与法治,对于稳定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以及消除贫困与饥饿是至关重要的。①See UNGA,A/RES/60/1,24 October 2005,para.11.联合国大会、秘书处等通过了大量关于如何促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文件,比如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②See e.g.,UNGA,A/RES/67/1,30 November 2012.虽然这些联合国文件并没有法律拘束力,但它们表明法治在国际社会中已被确认为最主要的治理方式。
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199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据此,我国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步伐。2008年3月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③《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syxw/2008-03/09/content_1410051.htm,2022年5月13日访问。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指出,涉外法律工作在当前被赋予更丰富的含义,这表明我国进一步深化了对法治的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提出:“适应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促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强化涉外法律服务,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依法维护海外侨胞权益。深化司法领域国际合作,完善我国司法协助体制,扩大国际司法协助覆盖面。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积极参与执法安全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贩毒走私、跨国有组织犯罪。”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所指的涉外法律工作具有两个突出的新特点:第一,更加强调维护中国国家和私人的权益,提高中国在国际法律秩序中的地位;第二,更多地涉及在中国境外的人或事项,因而要更多地利用国际机制。
在国际关系方面,20世纪70年代,亨金提出了一个耳熟能详的观点:在国家间关系方面,文明的进步可以被看做“从武力迈向外交,从外交迈向法律”。①See Louis Henkin,How Nations Behave 1(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亨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达了一种期待,并不当然反映国家间关系的事实。但是,人们不能否认,“二战”后国际法律体系不断扩大、管辖事项日益增多、拘束力不断增强、实施机制不断完善,由此,国际法在规范国际关系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国际法自身还不完善,国际法并不当然始终被善意地运用,它也可能被滥用,甚至被抛弃。因此,《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倡导的国际法治还远未实现。②See e.g.,Machiko Kanetake,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A Framework Paper,in Machiko Kanetake &AndréNollkaemper(eds.),The Rule of Law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18-22(Hart 2016).在2014年举行的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对此做了精辟阐述。习近平指出:“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没有只适用他人、不适用自己的法律,也没有只适用自己、不适用他人的法律。适用法律不能有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③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第2版。
总之,虽然法律并不当然被善意地制定与实施,各国对于法治也并不当然具有相同的理解,但法律确实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认为是最主要的治理方式;相应地,法治也拥有了普遍价值。在此背景下,即便在国际关系中拥有强大国家实力,拥有更多治理手段的大国,也不得不更多地重视法律的作用,运用(善意地或恶意地)法律手段处理各种事务。
(二)全球化背景下国内事务与对外事务高度互动
关于“对外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称《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九)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虽然《宪法》并未进一步规定“对外事务”的含义与范围,但提及“对外事务”,即从逻辑上蕴含着“国内事务”和“对外事务”的两分法思维。但是,关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政策文件既没有“国内事务”和“对外事务”的两分法表述,也没有“国内事务”与“涉外事务”的两分法表述。不过,从这些政策文件针对“涉外法律”或“涉外法治”的内容所做的表述看,①参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第七部分之(七)、《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第八部分。涉外法治的对象较之《宪法》所指的“对外事务”宽泛得多。诚然,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似乎都没有明确地规定“对外事务”的含义,但它似乎被普遍理解为涉及国家间的事务,比如缔约条约。笔者拟从国内事务与对外事务的关系角度,理解涉外法治以及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新背景。
自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从法律上说,一国的国内事务与对外事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分离的。换言之,一国的国内治理纯粹是本国的内部事务,不会对他国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类似地,一国的对外事务不会明显地影响一国的国内治理。比如,虽然划界条约会影响缔约国的利益,但它不会影响缔约国的特定国家治理实践。正因为此,“二战”以前的国际法被认为是“共存国际法”,即国际法主要规定国家的不作为义务,②See Wolfgang Friedman,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 60(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而《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更是明确规定了不干涉内政原则。然而,“二战”后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尤其是日益兴起的国际经济交流使得各国逐渐开展合作,以保障国际经济交流的顺畅进行。早在20世纪60年代,弗雷德曼就提出了“共同国际法”迈向“合作国际法”的范式转换。③See Wolfgang Friedman,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 61-67(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较之20世纪60年代有了巨大发展,其中,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尤其迅猛,它不仅影响国家间实力的此消彼长,还影响到一国国内的所得与分配;不仅表现为对国内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表现为一国的国内治理可能产生重要的正面或负面的外部溢出效应。在2015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各方应该特别注意加强彼此政策的沟通和协调,防止负面外溢效应。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大国,则更需要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充分考虑对他国的影响,提高透明度。”④习近平:《创新增长路径共享发展成果——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6日,第2版。以国内治理为规范对象是“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法发展的一个主要特点与趋势。换言之,当代国际法是一个以规制为主要导向的法律体系与法律过程,它深刻地影响了主权的观念与实践。⑤亚布拉姆·蔡斯和安东尼娅·汉德勒·蔡斯正是以“规制性协定”(regulatory agreements)为对象阐述新的主权理论,尤其是国际法遵守理论。See Abram Chayes&Antonia Handler Chayes,New Sovereignty:Compliance with Regulatory Agreemen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就中国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快了缔结涉及投资、贸易的规制性条约,涉及领域不断扩大,承诺水平不断提高,从而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国内治理,包括法治化进程。⑥参见廖诗评:《经由国际法的国内法改革——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内法制建设的另类路径观察》,《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5期,第145-153页。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国内事务和对外事务高度互动,不仅分别构成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背景,而且二者还相互促进,产生叠加效应。以中国对外事务为例,外交部指出,随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步伐加快和民众法治意识提高以及民众对外交工作的关注度上升,外交部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面面临的任务日益繁重,依申请公开案件内容更加多元。①参见《外交部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http://www.gov.cn/gzdt/2013-03/28/content_2364373.htm,2022年5月13日访问。关于中国对外事务透明度的详细分析,参见Congyan Cai&Yifei Wang,Transparency and Transparency-related Litigation in Chinese Foreign Affairs,10 Chine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2022).这生动地表明,国内事务与对外事务的高度互动不仅是事实驱动的,也是观念驱动的。
(三)全球化进程进入新一轮规则重塑与创设期
当前的国际法律秩序基本上是“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在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下建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然而,由于南北国家实力悬殊等原因,这些努力未能有效地改变国际法律秩序,发达国家仍以其惬意的自由化方式持续推进全球化进程。②参见徐崇利:《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潮落与中国的立场》,《国际经济法学刊》2008年第5期;蔡从燕:《国际经济新秩序与中国的选择:变与不变》,《国际经济法学刊》2009年第3期。
晚近,全球化进入新一轮的规则重塑与创设期,涉及的领域较之以往更加广泛。一方面,西方国家以维护与促进其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构建的国际法律秩序产生了某种“反身性”效果,导致在重塑某些领域的国际规则方面形成了更多的国际共识。以投资条约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缔结投资条约时普遍要求东道国放松管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高水平的投资待遇与保护标准,却几乎没有想过它们自身的规制权会遭到外国投资者的挑战。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频频被外国投资者诉诸国际仲裁,这导致它们纷纷修改国内法与投资协定。以美国为例,2002年,美国通过《两党贸易促进授权法》。虽然该法并未改变投资条约的自由化传统,但强调外国投资者不得获得比本国投资者更好的待遇,并且应当通过改革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维护美国的规制权。③See Bipartisan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Act,19 USCS§3802(b)(3).美国也与加拿大、墨西哥一道敦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所属自由贸易委员会(Free Trade Commission,FTC)澄清NAFTA中的一些规则,例如最低待遇标准④See NAFTA Free Trade Commission,Notes of Interpretation of Certain Chapter 11 Provisions,http://www.naftaclaims.com/files/NAFTA_Comm_1105_Transparency.pdf,visited on 13 May 2022.以及争端解决过程中非争端当事方的第三方参与。⑤See NAFTA Free Trade Commission,Statement of the Non-disputing Party Participation,http://www.naftaclaims.com/Papers/Nondisputing-en.pdf,visited on 13 May 2022.美国还更新了双边投资条约范本,融入了FTC所做的澄清。①See 2004 US Model BIT,http://ita.law.uvic.ca/investmenttreaties.htm,visited on 13 May 2022.作为国际投资仲裁主要被告方的发展中国家更具有改革投资条约的强烈愿望。②See Congyan Cai&Huiping Chen(eds.),The BRICS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on Investment:Reformers or Disruptors 233-237(Brill 2020).当前,各国普遍认为应当重塑传统的国际投资规则,尤其应当维护东道国的规制权。比如,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虽然强调投资政策应当为外国投资提供法律确定性和有力的保护,但也指出应当确保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不被滥用,并且维护东道国的规制权力。③参见《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http://top.chinadaily.com.cn/2016-07/18/content_26133785.htm,2022年5月13日访问。
另一方面,晚近全球化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要素或内容,但现行国际法未能有效地规范这些要素或内容,因此产生了针对这些内容创设新的国际规则的要求。在这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数字经济的兴起是一个突出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但它也给传统的国际贸易法律制度造成了极大挑战,还滋生了网络犯罪、国家安全等其他问题。近年来,围绕信息技术进行国际造法已经成为国家间的一个竞争“高地”。④参见《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http://www.xinhuanet.com/2017-03/01//c_1120552767.htm,2022年5月13日访问。应该强调的是,围绕着晚近全球化中新的要素或内容进行的国际造法往往广泛地涉及一国的国内治理。据此,一国的国内法实践不仅是完善国内治理所需要的,而且有助于强化一国在国际造法过程中的主张,提高其在国际造法过程中的影响力。
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中未能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鲜有参加多边法律秩序——虽然中国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才逐步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申请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创始缔约方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加速融入国际秩序。
中国意识到晚近全球化出现的一系列新发展意味着国际规则进入新一轮重塑与创设期,由此应当寻求在参与重塑与创设国际规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要“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在解读《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涉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容时,汪洋阐述了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方面的地位以及中国对于国际规则制定的新认知。汪洋指出:“规则和标准的竞争是最高层次的竞争。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进入了重大经贸问题谈判的核心圈,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作为现行国际经贸规则适应者、遵循者的角色没有根本改变。《决定》提出,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国际经贸新议题谈判,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就是要以更加积极、自信、负责的姿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和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全球性问题治理,增强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共同利益。”①汪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2日,第6版。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家实力快速提高,中国逐步成为国际规则重塑与创设中的关键性国家。这不仅指中国追求成为重塑与创设国际规则的关键性国家,也指中国成为重塑与创设国际规则的主要针对对象。
如前所述,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事务与对外事务高度互动。这表明,与以往不同的是,新一轮的国际规则重塑和创设与国内法治实践的联系更加密切。
(四)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笔者看来,尽管其他国家可能没有使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表述,但前述美国更新BIT范本并据此缔结投资条约等实践表明,许多国家事实上都在开展实质意义上的“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实践。较之其他许多国家,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一个特殊背景。对于中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来说,这一特殊背景也许更为重要。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身份使中国面临着日益突出的、如何使国内治理与国际秩序相互包容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不断借鉴其他国家先进治理经验的同时,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制度与道路。中国始终主张不得以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为由阻挠国际合作,更不能以此为由干涉他国内政。②参见《中国的民主》,http://www.gov.cn/zhengce/2021-12/04/content_5655823.htm,2022年5月13日访问。然而,无须否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日益强大在国际社会引发了一些误解,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恶意攻击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通过炮制所谓的“市场经济”议题和“民主”议题等,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竭力打压中国发展。③See e.g.,China’s Trade-Disruptive Economic Model,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WT/GC/W/745,16 July 2018,pp.2-3.因此,客观上说,如何实现国际秩序的普遍性与包容性之间的平衡是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的一个日益重要而迫切的议程。④参见蔡从燕:《国际法的普遍性:过去、现在与未来》,《现代法学》2021年第1期。可以认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实现国际秩序的普遍性与包容性的一条重要路径。
其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得中国实施国内治理与开展对外事务的方法体系不仅具有国内层面的重要性,而且具有国际层面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大国在处理公共事务,尤其是对外事务方面拥有更多的手段。由于拥有强大的国家实力,一些大国倾向于利用有利于其发挥强大国家实力的政治手段处理对外事务。然而,这往往容易导致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始终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坚持大小国家应该平等,并且这一政策不因中国日益强大而发生改变。我国将更多强调利用法律处理对外事务,而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则有助于通过更好地协调国内法与国际法,构建更加完善的方法体系。这对于避免把中国私人与其他国家发生的法律争端演化成政治争端,甚至是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政治争端,具有重要意义。①对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蔡从燕:《公私关系认识论重建与国际法的新发展》,《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第204-205页。特别是考虑到参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强化以法律的方式处理各种分歧或争端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近年来,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加大打压中国发展的力度。WTO争端解决机构早在1999年实质上已经裁定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节采取的贸易措施违反WTO协定,但美国政府无视这一裁定,仍然根据该法对中国发起国际贸易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制裁。②参见蔡从燕:《重大国际争端中的“法律战”:一个分析框架》,《中国国际法年刊》(2018年卷),第85-86、93-96页。为此,中国必须采取包括法律在内的措施,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此后,中国陆续制定《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以下称《阻断办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以下称《反外国制裁法》)等。
总之,中国提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不仅具有中国面临的特殊背景,而且也具有其他国家同样面临的相同或类似背景。这意味着,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过程中,我国不仅要大胆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实践,也要充分考虑、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律实践。
三、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目标
完整地理解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目标,既要基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等文件的表述,也要结合中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背景。不仅如此,这些目标的内在关系也值得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目标主要包括:(1)建设中国图景中的法治中国与世界图景中的法治中国;(2)实现对内事务与对外事务的全面法治;(3)综合考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需求;(4)平衡中国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
(一)建设中国图景中的法治中国与世界图景中的法治中国
诚然,法治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但是,由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各国的法治实践并不完全一致。中国的法治实践也理应立足中国国情。我们不妨把中国的法治化进程称为建设中国图景中的法治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最大国情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坚持党的领导。同时,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要积极考虑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①参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第一部分。总之,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绝不能照搬外国的法治理念和模式。
虽然各国的法治认知有所不同,各国的法治实践也各具特色,但各国在涉及法治的许多方面已经形成(或者说应该具有)共同或类似的认知与实践。这是法治具有普遍价值的根本原因,也是各国可以彼此借鉴法治实践的重要基础。中国也认为建设法治中国应当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②参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第一部分、《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第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妨把中国的法治化进程称为建设世界图景中的法治中国。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先进法治经验,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西方国家倡导的法治观念。③See Randall Peerenboom,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Rule of Law 56-62,20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Jianfu Chen,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aw:From Formal to Substance,37 Hong Kong Law Journal 736-737(2007);Randall Peerenboom,Soci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Living Constitution,in Tom Ginsburg(ed.),Comparative Constitution Design 138,159-160,16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背景下,确立建设中国图景中的法治中国与世界图景中的法治中国的目标,并且准确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更好地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及建立中国与国际社会更为和谐的关系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以往,中国对外关系倾向于融入国际体系,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不断更新观念,履行国际义务,借鉴国际惯例。中国法治实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内场域。现在,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的国内法治实践必然会产生溢出效应。尤其是,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从逻辑上蕴含着把国内法治贯穿于涉外领域的可能;而且,不断强化的涉外法治实践更具有对外指向性,因而更可能产生溢出效应。针对这些溢出效应,外部世界会有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国家应当重新思考其基于所谓的自由主义框架建立的法治理论,建立能够容纳中国法治实践的法治理论;西方国家应该思考“东方法律主义”(oriental legalism)取代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法律东方主义”(legal orientalism)的可能。中国的法治实践可能具有普遍性意义。①See Teemu Ruskola,Legal Orientalism: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Modern Law 232,23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法治实践以及中国的崛起将破坏西方主导确立的法治观念乃至西方秩序。②See BjÖrn Ahl,The Rise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37 Human Rights Quarterly 659-661(2015).尤其是,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和实体加大了抹黑、攻击中国国家制度的力度。这理所应当地受到中国的坚决反驳。③参见《中国的民主》,http://www.gov.cn/zhengce/2021-12/04/content_5655823.htm,2022年5月13日访问;《美国民主情况》,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202112/t20211205_10462534.shtml,2022年5月13日访问。然而,这些复杂的反应表明,中国不仅要立足中国图景,更要放眼世界图景。
(二)实现对内事务与对外事务的全面法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既涉及对内事务,也涉及对外事务。但总体而言,国内法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中国法治实践的主要方面。比如,早在1978年,中国就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律政策。与此相比,对外事务的法治实践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
在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法治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观念上都会在对外事务领域产生影响,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指立法、执法、司法等诸环节的法治,也包括对内事务与对外事务两个领域的法治。据此,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应当有助于实现对内事务和对外事务的全面法治。
(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我国历来强调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在2020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应当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是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基本目标。
应当注意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对此,不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以下称《国家安全法》)为例进行说明。《国家安全法》的首要立法宗旨与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④《国家安全法》第1条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但是,由于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各国在界定国家安全时往往会根据特定情形做出更具灵活性的解释,而晚近,国家安全概念更是出现被泛化的趋势,比如把经济问题安全化。①See Congyan Cai,Enforcing a National Security?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International Law,10 Journal of East Asia and International Law 67-77(2017).就我国而言,一方面,随着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具备了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强大能力;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发展问题仍然是中国的首要问题,因此,维护发展利益不宜被理解为只针对近年来美国等一些国家肆意采取旨在阻挠中国发展的行为,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应当避免不适当地解释国家安全的含义,以免对我国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虽然经济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构成要素,②参见《国家安全法》第3、19条。但也应当避免将所有经济问题归入国家安全范畴,以免损害我国的发展利益。
(四)平衡中国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不仅要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而且旨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兼顾中国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
诚然,国际社会仍然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但是,主权国家的利益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并不当然是完全一致的。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实都表明,有些大国并不当然会善意地运用其拥有的强大的国家实力。尤其是,近年来美国恣意奉行单边主义,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利益之上。与此不同,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主张改革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主张合作共赢,倡议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③参见《中国的和平发展》,http://www.scio.gov.cn/tt/Document/1011394/1011394.htm,2022年5月13日访问。
四、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内容
从法律实践的角度看,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被倾向于从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进行理解。④参见黄进、鲁洋:《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际法治意涵》,《政法论坛》2021年第3期,第8-10页。与此不同,本部分试图从制度、行为体、机制以及场所等角度讨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涉及的内容,期待从类型化的角度理解在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过程中需要统筹什么。
(一)制度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指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但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虽然以往人们侧重于关注国内法治的不足,但就当下而言,涉外领域存在的问题也许更为突出。主要原因是,国际法律秩序的发展、中国发展的自身条件以及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以审慎参与国际法律体系以及作为国际法律规则接受者和遵循者为基本特征的涉外法治思路,越来越不能适应更高水平地参与国际法律体系,提高中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以及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需要。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指出,为了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工作要求,中国要“完善涉外法律和规则体系”,特别要“补齐短板”。这突出地体现为我国要构建某些重要的涉外法律制度,或者业已存在的法律制度亟须进一步完善。在这方面,一个引发广泛讨论的例子是适用于中国境外的法律制度的建构问题。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强涉外领域立法,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人民日报》2021年12月8日,第1版。
全面讨论中国在涉外领域需要构建哪些新的法律制度显然超越了本文的研究任务。②参见廖诗评:《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现状、问题与完善》,《中国法学》2019年第6期,第23页。从本文旨在讨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角度出发,不妨以域外适用之国内法与其他国内法的统筹为例予以说明。根据《阻断办法》第9条第2款的规定,根据被中国主管部门认定构成不当域外适用的外国法律所做出的判决或裁定致使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遭受损失的,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在该判决、裁定中获益的当事人赔偿损失。不难发现,我国公民或组织在提起诉讼时可能会面临特殊的问题,比如如何认定“受益人”,如何认定相关“受益”和“损失”,以及如何认定相关“受益”与相关判决或裁定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如果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对此做出特别安排,《阻断办法》第9条第2款可能无法发挥预期的规范作用。
与此同时,采取妥当的法律制度形态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我们不妨以国内法域外适用进行说明。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是指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还是指在相关法律中增加域外适用规范,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显然,不同形态的法律制度建设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我国有必要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背景下审慎思考。
(二)行为体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充分运用立法、执法和司法手段。这意味着,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是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基本行为体。由于对外事务在各国主要是行政机关开展的,所以行政机关在涉外法治方面可能更为积极。以条约批准为例,有中国学者认为,不少条约从重要性的角度看应该属于《缔结条约程序法》第3条第2款所指的“重要协定”,因而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但在实践中往往直接由国务院核准。①参见张乃根:《论条约批准的宪法程序修改》,《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1期,第17-18页。不过,近年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涉外法治领域明显日益活跃。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1年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最高人民法院以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等。尤其是,2018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设立国际商事法庭,采取有别于一般国内诉讼的某些特殊规则。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第2款、第9条第2款等。未来,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有必要进一步创新涉外法治的方式。④关于中国法院创新性实践的初步考察,参见蔡从燕:《中国崛起、对外关系法与法院的功能再造》,《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30页;蔡从燕、王一斐:《大国崛起中的跨国司法对话——中国司法如何促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法研究》2022年第1期,第21页。
由于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私行为体在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中成为日益重要的行为体,私行为体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中的合作也值得重视。以往,跨国公司往往被视为被规制的对象,为此,各国通过缔结条约或制定国内法规范跨国公司的活动。事实上,跨国公司通过内部治理机制的变革可以成为重要的规制主体,从而在推动涉外法治中发挥能动作用。中国也日益重视跨国公司在涉外法治中的主体性地位。《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指出,中国主管部门要“引导对外经贸合作企业加强合规管理,提高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三)机制
在日益深化的全球化背景下,对外事务日益复杂。通过构建好的机制以便进行统筹,对于妥当地发挥不同行为体的作用,据此制定良好的制度并使之获得良好的实施,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不同的行为体之间或者不同的制度之间可能相互冲突,或者彼此脱节,导致未能发挥预期的效果。
在相关制度缺失或不完善的情况下,行为体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机制补充或纠正机制方面的不足。考虑到对外事务往往涉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涉外法治的发达程度不如国内法治,因此我国更加重视机制的作用。在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与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处理涉外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规定》)。《规定》注意到现实中可能出现涉及以外国政府为当事人的争端,比如中国公民对外国政府提起诉讼。由于我国尚未制定外国国家豁免法,因此《规定》明确,在处理包括此类案件在内的涉外案件时必须遵循密切配合、互相协调的基本原则,必须严格执行“请求报告、征求意见和通报情况等制度”。尤其是,法院在审理重大涉外案件时应当征求外交部及地方外事部门的意见。
随着参与国际法律秩序的程度不断深入,中国显然意识到机制统筹问题变得日益重要。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称《若干意见》)。《若干意见》要求我国“建立国际经贸谈判新机制。抓紧建立依法有序、科学高效、协调有力、执行有效的谈判机制。统筹谈判资源和筹码,科学决策谈判方案,优化谈判进程。加强谈判方案执行、监督和谈判绩效评价,提高对外谈判力度和有效性。充分发挥有关议事协调机制的积极作用,完善国际经贸谈判授权和批准制度。”从2017年国务院《缔结条约程序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称《征求意见稿》)的内容来看,中国有意强化外交部在缔结条约方面的统筹作用。①《缔结条约程序法》第3条第4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国务院领导下管理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的具体事务。”在此基础上,《征求意见稿》第4条进一步规定:外交部在国务院领导下管理缔结条约的具体事务,指导、督促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法定程序办理缔结条约工作。参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1705/20170502569554.shtml,2022年5月13日访问。
特别要指出的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在统筹涉外法治机制建设方面可以发挥独特作用,这是中国国家治理优势的重要体现。中国始终重视执政党在涉外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尤其是,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上升到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决定》要求:“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全面贯彻党中央外交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深入推进涉外体制机制建设,统筹协调党、人大、政府、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加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格局。”在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前的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据此,此前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被改组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这进一步强化了在对外关系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以及督促落实。
总之,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过程中,中国有必要全面检视相关机制存在的问题,不断强化机制统筹。
(四)场所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必然要依托特定的场所。合理的场所选择对于有效地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特定的场所可能更有助于特定制度的设计与实施;另一方面,特定的场所可能更有助于特定行为体和机制发挥作用。能否恰当地进行场所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能否准确地理解特定涉外法治实践所处的背景以及所追求的目标。
就国内场所而言,我们不妨以近年来上海自贸区建设为例。根据《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上海自贸区肩负着我国在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第1条规定,上海自贸区旨在充分发挥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试验田”的作用。第3条进而规定,上海自贸区将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2019年7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该方案指出,设立临港新片区是彰显我国主动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制度性开放是当前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特点,它意味着诸如金融监管等国内治理制度与机制要受到更大的考验。显然,作为经济体量巨大、商业活动活跃且复杂以及国内法治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上海是中国率先针对高水平开放开展压力测试、从而决定是否以及如何接受相关国际法律规则的场所之一。换言之,上海是中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一个先行示范场所。
就国际场所而言,除了继续充分利用诸如WTO等位于其他国家的国际组织平台外,近年来中国显然致力于建立更多的基础设施以设立中国的国际场所。我们不妨把此类国际场所称为“在地化的国际场所”。在这方面,2020年10月成立的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该机构由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联合有关国家商(协)会、法律服务机构等在中国共同发起设立。作为非政府间、非营利性、国际性社会团体,该机构致力于吸收借鉴现有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先进经验,为商事主体提供从争端预防到解决的全方位服务,为贸易畅通与投资便利化搭建新平台,为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提供新选项。对于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来说,此类在地化的国际场所可能会发挥特殊的作用:一方面,经由此类机构,中国既可以吸收国际先进法治经验,促进我国国内法治的发展,也可以展示、贡献法治实践的“中国智慧”或“中国方案”;另一方面,其他国家行为体甚至国际行为体的参与,有助于增强中国涉外法治实践的国际参与性、吸引力与竞争力。
五、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方法论:在“正常化”与“例外主义”之间
从本质上说,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提出意味着,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中国与国际法律秩序互动日益密切以及中国法治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不同领域的法治实践被有意识地强化彼此间的联系。在笔者看来,诸如“彼此互动”“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等貌似公允的表述无法解决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进程中在方法论方面面临的挑战,即涉外法治与国内法治是否遵循同样的法律逻辑?换言之,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中的两个“法治”是否应当遵循同样的标准?
对此,我们不妨先简要考察美国对外关系法中有关“正常化”(normalization)与“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的争论。①关于“例外主义”与“正常化”的新近争论,参见Ganesh Sitaraman&Ingrid Wuerth,The Normalization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128 Harvard Law Review 1897(2015);Curtis A.Bradley,Foreign Relations Law and the Purposed Shift Away from the“Exceptionalism”,128 Harvard Law Review Forum 294(2015);Carlos M.Vázquez,The Abiding Exceptionalism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128 Harvard Law Review Forum 305(2015)。虽然美国语境中“对外关系法”的范围小于中国语境中的“涉外法治”,但二者仍然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缔约实践既是美国对外关系法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语境中的涉外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关于“对外关系法”与“涉外法治”关系的简要讨论,参见蔡从燕:《中国对外关系法:一项新议程》,《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1期,第25页。因此,这一考察对于理解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方法论是有益的。
按照“例外主义”理论,美国学者认为对外事务领域与国内事务没有也不应该遵循相同的法治逻辑。也即较之国内事务领域,在对外事务领域,法治化程度相对较低。其主要原因是,对外事务往往涉及国家间关系。由于国际社会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构成单位的体系,并且,实力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往往较之法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洛克提出的处理对外事务的基本原则,尤其是行政部门在对外事务领域应该被赋予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议会不应该介入对外事务领域,以及国际法对于一国处理对外事务只具有软约束作用等,③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1-93页。深刻地影响了各国处理对外事务的实践。④See Campbell McLachlan,Foreign Relations Law 3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尽管如此,随着国际法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且日益涉及国内治理,对外事务日益以一种法治化的形式开展,比如私人更多地参与对外事务过程,以维护自身权利,法院也更多地参与对外事务过程,以审查行政部门的行为。⑤参见蔡从燕:《中国崛起、对外关系法与法院的功能再造》,《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32页。据此,有学者认为国内事务遵循的法治原则应该适用于对外事务领域;甚至有学者认为,对外事务的法治实践应当并且已经实现了“正常化”,即遵循与国内事务相同的法治逻辑。⑥See Ganesh Sitaraman & Ingrid Wuerth,The Normalization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128 Harvard Law Review(2015).不过,多数学者认为,对外事务领域应该维护某种“例外主义”,并且事实上并未实现“正常化”。①See Curtis A.Bradley,Foreign Relations Law and the Purposed Shift Away from the“Exceptionalism”,128 Harvard Law Review Forum(2015).有学者认为,“例外主义”其实是各国对外事务法律实践的共同特征。②See Eric A.Posner & Cass R.Sunstein,Chevronizing Foreign Relations Law,116 The Yale Law Journal(2007).换言之,在对外事务领域可以降低相对于国内事务的法治化水平。
如上所述,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所处的社会基础与所针对的对象均有所不同。据此,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不应当或者至少并不当然要遵循相同的逻辑。换言之,我国的涉外法治可以遵循“例外主义”逻辑。然而,在中国涉外法治实践的语境中,“例外主义”的含义应当被重新予以解释。申言之,“例外主义”不仅意味着某些涉外法治实践可以并且应当遵循较之国内法治较“低”的标准,也意味着某些涉外法治实践可以并且应当遵循较“高”的标准。
具体来说,对于那些明确或者实质上涉及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涉外法治实践,即美国学者所说的对外关系法实践,我国可以并且应当遵循较之国内法治较“低”的标准。这不仅是各国普遍的做法,而且,当前国际环境极为复杂,尤其是在一些西方国家肆意采取各种措施,企图打压中国发展的情况下,赋予我国相关部门足够的自由裁量权,以便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更是必要的。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第7条规定,国务院相关部门针对反制裁事项做出的决定为最终决定。换言之,即使此类决定显然构成《行政诉讼法》第2条所指的“行政行为”,但它们不得被诉诸法院。据此,国务院相关部门可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决定采取反制裁措施的时间与方式。③参见《反外国制裁法》第4、6、8条。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并不明确涉及或者实质上并不涉及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涉外法治,中国在某些情形下可以考虑采取较之国内法治较“高”水平的实践。这种做法非但不会损害反而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换言之,针对某些涉外法治实践,可以以一种与传统理解相反的方式来适用“例外主义”。对此,我们不妨以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官任职为例。根据我国《法官法》第9条规定,不具有中国国籍的人不能担任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官。作为应对,有学者建议,中国可以吸收中国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官担任人民陪审员,或者选任中国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官担任“任期法官”,但不宜引进外籍法官担任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官。④参见何其生课题组:《当代国际商事法院的发展》,《经贸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第75-76页。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国际商事法院的实践,通过修改《法官法》等法律,引进外国法官。⑤参见蔡伟:《国际商事法庭:制度比较、规则冲突与构建路径》,《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5期,第187页。从实践方面看,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设立了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其中包含着少数外国退休法官,①参见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简历,http://cicc.court.gov.cn/htm/1/218/226/234/index.html,2022年5月13日访问。以弥补外籍法官无法担任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法官的不足。然而,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员终究不能以法官的身份做出裁判。事实上,修改《法官法》第9条,让某些外国法律专业人士在特定情况下担任中国法官,比如,在国际商事法庭担任法官,这从法律技术上来说并非不可能。由于国际商事法庭审理的是涉外民商事案件,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外国法律专业人士担任法官,并不必然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相反,它可能有利于增强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吸引力。
六、结论
2020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提出的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使得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成为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对于中国法治化的整体进程以及深化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法律秩序都可能产生长远、深刻的影响。
提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有着深刻的一般背景和特殊背景。首先,法律在全球范围内被公认为最主要的治理方式。这意味着中国在各个领域中有必要更多地运用法律,尊重法治原则。全球化背景下国内事务与对外事务高度互动。这意味着传统上法治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涉外领域应当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全球化进程进入新一轮的规则重塑与创设期。这意味着中国在提高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方面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如何妥当地处理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与国际法律秩序的关系问题变得愈加迫切。中国不仅应当追求建设中国图景中的法治中国,也要追求建设世界图景中的法治中国。其次,鉴于国内事务与对外事务犬牙交错以及中国不断深化参与国际法律秩序,中国应当实现国内事务与对外事务的全面法治。再次,鉴于中国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仍然面临繁重的发展任务,中国应当统筹实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目标。最后,中国应当兼顾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从而在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承担大国责任,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内容方面看,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主要涉及制度、行为体、机制以及场所等方面。关于制度,中国有必要增强不同制度间的衔接,避免出现冲突或脱节,促使相关制度积极发挥预期作用。同时,中国有必要准确理解制度的表现形态。关于行为体,中国有必要全面发挥立法、行政与司法机关的作用,尤其更要努力探索创新性的实践。同时,诸如跨国公司等私行为体不应只被视为对象,而应进一步被视为主体,以便发挥私行为体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中的能动性作用。关于机制,鉴于涉外法治与国内法治的联系日益密切,以及涉外法治的不同构成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有力的机制建设至关重要。尤其是,有力的机制可以弥补制度方面存在的不足。关于场所,中国有必要根据特定涉外法治实践所处的背景、所追求的目标以及特定场所的优势,选择恰当的、示范性的国内场所,实现涉外法治实践与特定场所的良好匹配。同时,中国有必要积极利用、创设国际场所,尤其是基础设施位于中国的国际场所,即在地化的国际场所。此类在地化的国际场所有利于中国吸收国际先进法治经验,促进我国国内法治的发展,也可以展示、贡献法治实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由于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所处的社会基础与所针对的对象都有所差别,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不应当或者至少并不当然要遵循相同的方法论。中国的涉外法治可以遵循“例外主义”逻辑。不过,这种“例外主义”有别于美国对外关系法中所指的“例外主义”。中国涉外法治实践语境中的“例外主义”不仅意味着某些涉外法治实践可以并且应当遵循较之国内法治较“低”的标准,也意味着某些涉外法治实践可以并且应当遵循较“高”的标准。两种形式的“例外主义”对于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提高中国的法治形象和国家竞争力,应当是适当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