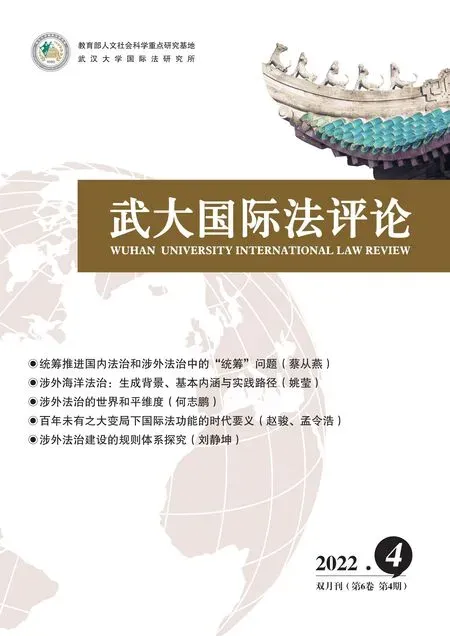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法功能的时代要义
2022-01-01赵骏孟令浩
赵骏 孟令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称“百年变局”)下,有效实现并完善国际法的功能是国际法理论与实践面临的基础命题。通常而言,国际法致力于维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平等相处以及促进实现各国所认同的共同利益。①参见[美]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张乃根、马忠法、罗国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48页。国际法作为国际社会的法律规范,其产生与发展均受到国际关系现实的高度影响,处于国际秩序演进与国际社会结构动态变化之中的国际法必然呈现出不同的功能状态。国际法并不是顺应民族国家出现的自然产物,而是国际关系的参与主体依据各自知识体系主动建构出来并在国际交往中加以实践的。①参见邓正来:《王铁崖与中国国际法学的建构——读〈王铁崖学术文化随笔〉》,《中国法学》1997年第6期,第110页。在以国家共存为基础性目标的时代,国际法的主要功能在于调整和维持独立国家之间及国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国家间独立共存的根本需要造就了国际法调整独立国家之间战争与和平关系的基本功能。②See Myers S.McDougal,et al.,Theories about International Law:Prologue to a Configurative Jurisprudence,8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0-191(1968).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际关系经历了“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的系列演变,③参见何志鹏:《国际法的现代性:理论呈示》,《清华法学》2020年第5期,第156页。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上的变革使得国际交往的广度与深度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国际法所要调整和规范的国际关系日趋复杂,国际法逐渐具备了更为丰富的功能构成,以更好地回应治理需求和时代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作为国际法的新领域产生,使得国际法被进一步赋予了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人文功能”,更多地表现为国际法功能的人本化倾向。国际法不仅代表着国际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组织国际关系的制度形式,而且肩负着构建并维护国际秩序的法治保障使命。④参见曾令良:《论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法的交互影响和作用》,《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第111页。国际法处于不断变化发展当中,这种动态性源自国际关系演进所产生的变局。⑤参见王铁崖:《国际法当今的动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第17页。国际法唯有适应国际社会结构的变化,才能始终作为调整国际关系的法律规范而发挥其应有的时代功能。
百年变局是国际法功能调整的客观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⑥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39页。这一论断准确揭示出当下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动趋势以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风险。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及其规范辐射发生深刻变化,全球风险触发的潜在治理需求持续扩张,国际法功能面临本体性与主体性两个层面的动态倾向:一方面,在本体性层面,国际法理论与制度形式面临实践形态异动所带来的调适需求,文明冲突、大国博弈、多边主义危机、气候变化、全球性流行病、人工智能等议题不断对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造成威胁和挑战,全球治理充斥着历史积累的信任损耗、规则滞后和效率欠缺。世界之变,最终将以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变化的状态体现出来。在国际社会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关键时刻,国际法功能如何有效适应并应对国际社会结构变动带来的全球风险与秩序挑战,是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亟待回应的基础命题。另一方面,在主体性层面,作为发展和变革国际法的核心力量,大国以其广泛利益和国际政策触发国际法功能的适应性变更,国际法是崛起大国的制度重器,妥善地利用国际法,充分发挥国际法的功能,有助于抵御国际社会的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有效处理、参与和引领国际事务。①参见何志鹏:《国际法在新时代中国的重要性探究》,《清华法学》2018年第1期,第9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②《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人民报》2020年11月18日,第1版。这要求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发挥国际法功能,开拓运用国际法的新维度,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国际法功能的一般理论与基本内容
本质上,国际法也是法,因而,国际法功能符合法的功能的一般原理。③参见[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10页。国际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接受。④See Onuma Yasuaki,International Law in and with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Func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14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22(2003).各国均承认国际法的法律性质并按照国际法交往和发展关系。国际法作为法的性质决定了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法的一般功能。法的功能是对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或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实践表征。法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制度,国际社会亦无例外。⑤参见贾兵兵:《国际公法:和平时期的解释与适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普遍的理论认为,法是一种具有很强约束力的社会规范,能够起到调整社会生活中各种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作用。⑥参见[美]凯尔森:《纯粹法学》,刘燕谷译,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31页。古罗马法学家莫迪斯努斯认为,法的功能主要包括禁止、命令、允许、惩罚等要素。⑦参见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96-300页。法的一般功能构成国际法功能的基础和来源,从法的一般功能出发,国际法具有不同程度上的指引、预测、评价等规范功能。
国际法的功能除了与法的功能一脉相承之外,还受到国际法自身特点的影响,即国际法根植于政治力量和国家利益的均势状态,形成于国家意志的相互协调,⑧参见赵骏:《国际法的守正与创新——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规范需求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29页。这些特点对于国际法功能产生塑造作用。在主要由独立国家作为核心主体,并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轴的国际关系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国际法仍是与国内法相区别且具备特殊功能的特殊体系。①参见古祖雪:《国际法:作为法律的存在和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透视历史可以发现,在国际社会面临的数次危机状态中,国际法都发挥着减缓冲突维护和平、定分止争促进合作、稳定秩序实现共同利益的重要作用。
(一)维护和平状态,防止非法诉诸武力
国际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国家之间和平共存并高度依赖的结构状态。国际法可以引导国家的行为,预防和避免争端发生。虽然国际法受到权力政治的影响,呈现出一种软约束的状态,但是并不能因此否认国际法的规范作用。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以及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等关系到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问题上,国际法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战”后,国际法更好地发挥了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使命。一方面,战争非法性的基本原则得到确立,国家不再合法地拥有诉诸战争的权利。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一项强行法规则,任何国际法主体都不得违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另一方面,国际法允许特定条件下的自卫行为,并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机制,②See Hans Kelsen,Collective Security and Collective Self-Defense under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42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83-796(1948).有力促进了国际社会长期的和平稳定。自联合国成立至今,虽然局部的战争与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至今没有改变,这背后离不开现代国际法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二)促进国际合作,构建政策协调机制
国际法为各类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和协商谈判的平台,为国际法主体确立起明确的行为规范③参见曾令良:《论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法的交互影响和作用》,《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第111页。,从而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基本的实体与形式保障。国际法框定了国际合作的正确方向与基本底线,任何国家都被禁止使用胁迫、欺诈等手段进行国际交往,也不能就违反国际强行法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事项达成协议。因此,国际法为国际合作的合意基础、正当方式和结果分配提供了基本的规范要求,促进重要治理领域的政策协调,这有助于国家之间发展经济交往与友好合作。④See Jack L.Goldsmith & Eric A.Posner,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Law 13(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在国际法的规范功能之下,国际合作才能始终处于法治的轨道之上。国际合作原则已经被确立为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其中,国际法在促进各国经济合作方面的功能较为凸显。例如,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规则体系为主要代表的国际贸易法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进程,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和互惠关税减让原则有力地促进了贸易自由化。①参见曹建明、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1-93页。国际投资法也通过规定投资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不断提高投资自由度和保障投资利益。②参见赵骏:《体用兼具:国际经济法的重要性释义》,《清华法学》2018年第1期,第55-56页。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国际法具有发展经济和促进合作的重要功能。③See Joel P.Trachtman,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Global Government 22-3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三)促进共同体认同,实现共同体利益
国际法功能体现了国家参与国际交往的基本期待和国际社会的现实状态。晚近,国际法的新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越来越多地着眼于维护全人类的利益和应对威胁全人类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体现出更加明显的时代特征。国际法首先服务于构建国际关系的稳定状态,确立各国追求和实现各自国家利益的合法基础,这也是构建国际社会共同体利益的秩序保证。④参见曾令良:《论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法的交互影响和作用》,《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第111页。在国际社会中,高度依存的国家之间必须通过合作协调才能有所作为,而缔结条约和创设国际制度成为各国交往与合作的重要方式。作为主要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和规范,国际法明确宣示和规定国际法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促进各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以共同面对和解决风险,促进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与可持续发展。⑤参见何志鹏:《国际法在新时代中国的重要性探究》,《清华法学》2018年第1期,第20页。
“二战”之后,国际社会反思战争中基本人权受到践踏、人类惨遭浩劫的悲惨境况,推进人权的国际保护,为各国施加了保护和促进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国际法义务,凸显出对人类尊严的维护和保障。⑥《联合国宪章》将尊重全体人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作为联合国的宗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通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构成国际人权法的核心内容。在经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复杂的利益斗争与妥协平衡之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明确任何“区域”开发与利用活动都应当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彰显出一种不同于单个国家的“海洋安全利益”与“海洋自由利益”的共同利益导向。此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保障机制、能力建设机制、履约监督机制等,推动世界各国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威胁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气候变化问题。上述实例都充分表明,国际法在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与人类尊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百年变局下国际社会的主要时代特征
国际秩序的振荡和重塑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这背后包含着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也包含着价值和观念的发展和重塑。从整体上看,国际法受到特定历史条件下国际实力增减和国际力量对比关系变化的影响,①参见赵理海:《国际法基本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国际关系变化中的因素和特征必然反映在国际法上。百年变局下,世界秩序振荡重构,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态势强劲,传统西方大国的实力已经不足以支撑其在国际社会所具有的政治地位和所掌握的合法性权力,国际社会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时代特征。
(一)国际社会的结构趋向多元化
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占据国际秩序核心地位,主导国际治理话语权,决定国际关系发展方向。②参见徐光春:《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红旗文稿》2021年第6期,第8页。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日渐式微,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③参见杨洁勉:《当前国际大格局的变化、影响和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3期,第2页。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决定国际治理和秩序安排的合法性权力呈现减弱趋势,世界多元化趋势向纵深发展。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快速增长,经济总量与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与此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日渐缩小。④See World Economics,Contribution to Global Growth,https://worldeconomics.com/Indicator-Data/Economic-Growth/Contribution-to-Global-Growth.aspx#:~:text=The%20table%20above%20shows%20the%20extraordinary% 20contribution% 20made,and% 20highlights% 20the% 20importance% 20of% 20China%20and%20India,visited on 29 June 2022.世界经济的中心日渐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世界经济的活力也逐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际社会的秩序和治理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向,国际权力的分布进一步分散和均衡,新兴发展中国家与区域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日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出广泛的影响力,为全球治理不断贡献出自身力量。与此同时,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扮演着更为突出的角色。因而,单个或少数国家逐步失去了在特定治理领域的垄断治理权力以及主导治理过程的特殊地位,各类行为体以自身偏好、利益和诉求为基点竞相塑造国际体系。⑤Se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40:A More Contested World,https://www.dni.gov/index.php/gt2040-home/emerging-dynamics/international-dynamics,visited on 29 June 2022.
国际社会多元化趋向要求国际法具备更为包容和多样化的功能。第一,全球层面的治理共识变得更加难以达成,多元主体之间的分歧使得国际法用于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功能不断得到重视。第二,区域层面的治理安排可能会变得更加灵活、多样,国际法更多地发挥着为双边、区域层面的治理提供保障的功能。第三,全球治理中的理念思维必将更为丰富,多元主体不同的治理模式、发展道路、体制机制等主张,亟待通过国际法的形式加以表达和固定。
(二)国际社会的治理需求趋向复杂化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与百年变局背景交织叠加,给国际秩序稳定造成严峻考验,导致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后疫情时代,国际社会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风险,这些风险不仅与中国未来发展息息相关,而且关系到国际秩序的走向和全人类的共同命运。百年变局催生具有时代性的国际法功能需求,国际社会期待通过国际法的创新性发展填补功能欠缺,缓和危机,增强信任,推进治理。
1.多边贸易体制的变革需求。当前,多边贸易体制仍处于危机之中,WTO上诉机构停摆导致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完整发挥作用,决策机制改革也面临着很大挑战。①参见周頔:《对话张向晨:要客观评估MC12成果,WTO改革仍面临挑战》,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626597,2022年8月15日访问。随着百年变局下发达国家的主导能力下降,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问题展开激烈博弈。②参见李计广、郑育礼:《多边贸易体制改革:背景、性质及中国方略》,《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5期,第76页。美、欧、日等正在推动制定有关市场经济、产业补贴、国有企业的特殊规则,欲借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改革之机,为中国戴上制度枷锁。③参见孔庆江:《美欧对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设想与中国方案比较》,《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3期,第38-56页;陈凤英、孙立鹏:《WTO改革:美国的角色》,《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2期,第71-77页;屠新泉:《中美贸易摩擦与WTO改革:分进合击的美国对华贸易策略》,《求索》2019年第6期,第46-54页。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将深刻影响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国际经贸环境,对中国中长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对现有多边贸易体制提出了变革要求,然而,WTO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谈判陷入迟滞,导致多边贸易规则无法有效回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治理需求。其实,早在1998年部长级会议上,WTO便通过了《全球电子商务宣言》④See WTO,Electronic Commerce,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minist_e/mc11_e/briefing_notes_e/bfecom_e.htm#:~:text=The% 20Declaration% 20on% 20Global% 20Electronic% 20Commerce%20adopted% 20by,all% 20trade-related% 20issues% 20arising% 20from% 20global% 20e-commerce% 20%28WT%2FL%2F274%29,visited on 29 June 2022.,但之后WTO框架下电子商务谈判进展缓慢,至今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试图重新制定“21世纪新贸易规则”以实现约束中国的战略意图。①Se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of Ambassador Katherine Tai Outlining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ew Approach to the U.S.-China Trade Relationship,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speeches-and-remarks/2021/october/remarks-prepared-delivery-ambassador-katherine-tai-outlining-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ew,visited on 29 June 2022.
2.国际公共卫生合作需求。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对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各国经济发展都造成了极大冲击。作为国际社会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文件,以《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国际卫生条例》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暴露出约束力不足、责任分配不公、争端解决机制虚置、执行制度不力等诸多缺陷。后疫情时代,国际社会更加迫切地需要完善国际卫生法律体系。例如,2021年12月,在世界卫生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同意制定一项新的国际大流行病公约,以预防并应对大流行病。②Se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orld Health Assembly Agrees to Launch Process to Develop Historic Global Accord on Pandemic Prevention,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https://www.who.int/news/item/01-12-2021-world-health-assembly-agrees-to-launch-process-to-develop-historic-global-accord-on-pandemicprevention-preparedness-and-response,visited on 29 June 2022.变革国际卫生法律体系、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进一步加强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积极解决现有国际法制度在设计理念和实施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完善国际公共卫生领域的责任分配制度,努力修复和提升国际卫生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成为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合作的重点方向。
3.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需求。气候变化给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带来系统性冲击。为此,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成为全球治理的优先事项。③参见赵骏、孟令浩:《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规则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基于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互动的视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21页。气候变化具有生态环境问题的属性,但归根结底属于发展问题。④参见黄惠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69页。全球气候治理不可避免地会对贸易、投资、金融、能源、安全等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气候变化形势越来越严峻的背景下,国际层面围绕气候变化议题的主导权争夺和外交斗争愈发激烈,广大发展中国家承受着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承受着减排义务所造成的重大经济和社会压力。在中美两国进行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尽管气候变化问题被美国视为同中国进行合作的重要领域,并且中美先后达成了《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和《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但合作仍充满风险。美国试图为中国施加超出发展阶段和能力的减排义务,从而达到迟滞中国发展的目的。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弱化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基石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破坏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良好基础。⑤参见薄燕:《全球气候治理机制适用“共区原则”方式的变化》,《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21年第2期,第98页。
4.新兴科学技术法律治理需求。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和治理方式。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仅将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和国家竞争力造成深远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到国际力量的对比和国际秩序的变革,构成百年变局的重要推动力量。①参见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第10页。同时,新的科技也为各国带来了新的挑战与风险。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催生新型治理问题。②参见赵骏、李婉贞:《人工智能对国际法的挑战及其应对》,《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9页。无人机、无人潜航器等人工智能武器的发展,正在改变国家之间的战争手段与形态,从根本上打破原有国家间的实力平衡状态。此外,数据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国家敏感数据、商业机密数据和个人隐私数据极易被泄露,从而产生操控政治、干预舆论和颠覆政权等风险。新兴科学技术带来社会生产力和全球供应链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会通过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对国际社会结构产生间接影响,而且也会直接促动国际社会结构的改变。③参见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第128-156页。
(三)国际社会的法律关系处于动荡状态
1.具有制度性影响的意识形态对立。意识形态已成为美国与中国进行竞争甚至对抗的重要领域。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④See 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visited on 29 June 2022.打压中国或迟滞中国的发展,已经上升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导向。⑤参见杨楠:《“布林肯演讲”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态势》,《世界知识》2022年第13期,第59-61页。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意识形态因素已经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美国对华关系的各项议题之中,美国政府开始单方面地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准来界定和处理中美关系。⑥参见节大磊:《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97页。美国频繁鼓吹建立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民主国家同盟”,在国际法层面挑起并强化意识形态纷争。⑦参见黄惠康:《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变革和国际法治贡献中国智慧——纪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国际法学刊》2021年第3期,第19页。国际社会面临意识形态对立扩大化的秩序风险。一方面,意识形态融入多边国际体制,这迫使国家根据意识形态而非共同利益“选边站队”,最终将导致国际社会分裂为相互独立的竞争阵营。另一方面,这也导致意识形态对立在更多的新兴议题上以间接和隐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最终损害国际社会为弥合全球治理赤字而开展的国际合作。①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公开表示,担心世界分裂成“两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阵营。参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世界面临形成两大独立竞争体系风险》,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09/1042102,2022年6月29日访问。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指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矛盾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使得解决“巨大的经济和发展挑战”变得不可能。See United Nations,Restore Trust and Inspire Hope,UN Chief Says in Message to UNGA 76,https://news.un.org/en/story/2021/09/1100452,visited on 29 June 2022.
2.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时代碰撞。在百年变局下,全球性问题和风险需要各国通过国际合作加以共同应对,而有些国家却奉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企图瓦解甚至替代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②参见韩立余:《当代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碰撞及其发展前景》,《国际经济法学刊》2018年第4期,第23-41页;孙南翔:《美国经贸单边主义:形式、动因与法律应对》,《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179-192页;张乃根:《国际法上的多边主义及其当代涵义》,《国际法研究》2021年第3期,第3-19页;沈伟:《美式小多边主义与美国重塑全球经贸体系》,《国际论坛》2022年第1期,第3-24页。单边主义主要体现为出于本国利益至上的考虑,依靠本国国内法而不是国际法处理国际事务,同时不断干扰、阻挠甚至退出现有多边安排。近年来,美国频繁诉诸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一方面积极推行“退出外交”,接连退出或威胁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重要多边机制,阻挠WTO上诉机构成员遴选致使其陷入停摆;另一方面凭借强大综合实力频繁滥用长臂管辖权,极力扩张本国立法和司法效力,这不仅危害国际法治和国际秩序的稳定,还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中国的企业及重点关键产业极易受到美国长臂管辖权的打击,持续面临被美国巨额罚款及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的处境。美国滥用长臂管辖权的根本意图在于将美国国内法置于超越和优于国际法的地位,依美国国内法院和美国国内法来调整国际关系以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这一行为严重破坏国际法治的运行环境。③参见肖永平:《“长臂管辖权”的法理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法学》2019年第6期,第58页。
3.地缘政治角力所形成的法律冲突。中美之间目前处于高位运行之中的战略博弈将会进一步激发法律斗争与冲突。现实中,美国已经在印太地区加大了对中国外交和军事上的遏制和施压力度,中美之间在南海、台海、东海地区面临激烈的地缘政治角逐。其一,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南海问题将可能进一步呈现出被动国际化与滥用国际司法的趋势。除建设基地、贴近部署或侦察、滥用航行权等手段之外,美国还在寻求推动新技术与新模式之下的海上力量博弈。④参见吴士存:《2022年南海作为继续“稳”字当先》,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6SaeQZ ZLDV,2022年6月29日访问。其二,美国频繁介入台湾问题,表现出强烈的言行不一。①参见信强:《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嬗变与困境》,《台湾研究》2022年第3期,第1-11页。其三,日本政治上右倾倾向有所发展,东北亚的半岛局势仍严峻复杂。②参见吕耀东:《日本必须深刻汲取历史教训》,《人民日报》2022年8月16日,第17版。此外,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与分裂主义对中国的潜在威胁依然存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使中国在地缘政治上面对来自多方因素造成的安全风险与挑战。
三、百年变局下国际法功能的时代定位
国际关系的复杂程度受到百年变局影响而日益加剧,基于国际关系一般状态对国际法功能的总结和提炼可能已经无法适应国家实践的新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存或共进状态③参见易显河:《向共进国际法迈步》,《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55页。属于一种整体秩序状态的描述,百年变局下国际关系中的局部竞争、斗争、敌对等非常规状态更为显著。为此,有必要在分析当前国际社会及其成员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与风险的基础上,从法律调整的不同维度出发,对国际法功能重新进行发掘、定位与解读,以更好地发挥国际法功能,为国际关系提供更为精准的理论概括和规范指引。
(一)国际法是建构国家身份的重要载体
百年变局下,促进共同体认同和实现共同利益固然重要,但是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仍然是国家追求的优先目标。在国际关系中,国家时刻处于同其所处的周围环境互动的状态之中,这种互动既存在于少数国家之间,也存在于众多国家之间。归根结底,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同状态是由这些互动的性质所决定的。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方面,国家身份与角色可以对国际交往、国家政策的走向、公众认知等产生重要影响。④See Kenneth E.Boulding,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3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20-131(1959).对国家的身份建构与角色塑造不仅能够提升内部的凝聚力与自信心,还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支持并促进国际合作的实现。因此,面对更加多元的国际社会主体、更加复杂的治理需求和更加不确定的国际局势,国家必须积极建构适应时代要求的国家身份。
国家身份与角色的塑造离不开国际法的作用,这对百年变局下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具体而言,积极参与国际法发展并贡献智慧能够强化国际社会对本国身份与角色的认知。反过来,国际法的发展又会进一步确认和固化国家的身份与角色。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家身份经历了一个由国际事务的“一般参与者”到“重点建设者”再到“负责任大国”的演变。①参见吴瑛、史磊、阮光册:《国家身份的建构与认同: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分析与反思》,《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30页。“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②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2版。与之相对应,中国的国家身份和角色也需要借助国际法加以强化和彰显。例如,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设计和国际公共产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也为推动国际法运用和创新发展提供了契机,这将有助于中国从主要为既有国际规则的采纳者和追随者,逐步成长为创新型规则的共同制定者和重塑推动者。③参见石静霞:《“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法——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视角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第179页。
(二)国际法是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压舱石
国际法是维护多边、开放和稳定之国际秩序的压舱石。稳定的国际秩序是对基本和平的国际秩序的深化。相应地,国际法促进国际秩序动态平衡的功能也是对维持和平功能的深化贯彻。从状态上看,“和平”通常是指国际社会处于一种没有战争的状态,本质上是一种消极和平。这意味着,尽管国际社会总体上没有发生战争,但是仍然存在国家间的潜在或隐性的政治或法律冲突,只不过这些冲突并没有导致战争而已。消极和平并不代表国际社会处于一种稳定状态。相反,消极和平反而包含更大的不确定性。④参见周丕启、张晓明:《国际关系中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2期,第49页。百年变局下,虽然和平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流趋势,但是由国际力量对比关系改变而引发的摩擦和冲突不断增多,国际法对于消极和平的维护作用依然重要,而且对于国际秩序稳定的维护已经成为国际法新的功能侧重。
提供秩序稳定的规范期望是法所具有的核心功能。⑤参见[德]卢曼:《社会的法律》(上册),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国际法是预防并应对风险、化解和解决利益冲突的规范工具,稳定秩序是其基础性功能。一方面,国际法起到预防风险的作用,使国家之间对相关行为或事件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在任何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国际法都可以为国际社会提供一定的行为指引和稳定预期,即使是在缺乏相关规定或先例的情况下,基于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以及国际合作等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关系仍旧可以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下。另一方面,国际法为各国提供了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能够最大程度上确保争端始终处于法律框架之下而不至于失控。有学者甚至乐观地表示:“所有国际争端,无论其严重性如何,都是法律性质的争端,因为只要法治得到承认,它们就能够通过适用法律规则得到解决。”①Hersch Lauterpacht,The Func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166(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例如,晚近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实证研究表明,国际司法程序明显改变了潜在诉讼国家之间的涉海谈判,促使其就海洋诉求和争端解决展开磋商或合作性努力。②See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Andrew P.Owsiak,Judicialization of the Sea: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UNCLOS,115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2021).这充分表明,在当前全球治理失灵、各国之间存在严重信任赤字的时代背景下,国际法在维护多边主义、稳定国际秩序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压舱石作用。
(三)国际法是全球治理赤字的填补器
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着严重的治理、信任、和平、发展和正义赤字,全球治理的广度与深度都亟须拓展。国际法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开放的规则和话语体系。国际法具有相对固定的术语和表达,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共享国际法概念、规范、系统,运用相同的法律推理和论证以及思维逻辑。国际法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话语平台,不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都可以运用国际法进行交流,这为国际关系的法律调整提供了基础,进而促进了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的有效应对。③See Martti Koskenniemi,From Apology to Utopia 1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国际法可以通过促进国际合作来填补各种赤字,推动形成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在此过程中,国际法为全球“善治”提供了制度保障,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强行法的国际规则等构筑了全球治理走向“善治”的法律基础。
当前,国际法通过稳定现有治理体系、增设治理规则、创新治理机制供给等方式,填补当前的治理赤字。例如,针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问题,国际治理规则和机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相关区域海洋法律关系面临不确定性,因此,联合国一直在主导推动制定相关国际协定,以努力完善当前的国际海洋治理体系。④参见孟令浩:《BBNJ国际造法中的“一揽子交易”:作用与局限》,《中国海商法研究》2022年第1期,第50页。又如,针对网络攻击、网络干涉和网络犯罪等问题,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也正在联合国的主导下稳步推进。⑤参见黄志雄:《2020年上半年联合国信息安全工作组进程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博弈》,《中国信息安全》2020年第7期,第68-71页。在国际竞争和摩擦不断上升,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受到侵蚀的情况下,国际法成为各国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媒介,并且为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稳定的规范预期和保障,这无疑有助于弥合国际社会中的信任赤字。全球治理所依托的国际法治既从形式上对国际法规则的可预期性、普遍性和有效解决纠纷等提出功能性标准,①参见黄文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治——以形式法治概念为基准的考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22页。也为实质上追求目标设定良好、价值导向合理、治理效果有效的“良法善治”状态。②参见何志鹏:《国际法治:一个概念的界定》,《政法论坛》2009年第4期,第77页。
(四)国际法是开展国际法律斗争的重要媒介
国际法是法律斗争的重要媒介。国际法伴随国家意志的实证表达而产生,并随着国际关系结构演变而变化。③参见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国际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4页。从国际法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国际法的斗争功能始终受到国家的重视并不断被实践。国家之间不仅可以达成合作关系,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斗争关系。全球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法律化,使法律成为参与跨国斗争的主要语言。④See David Kennedy,A World of Struggle:How Power,Law and Expertise Shap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171(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国际法经常被作为进行国际法律竞争的媒介以及开展国际法律斗争的基础性工具。“话语即权力。”国际法话语背后实际上还蕴含着权力因素,如福柯的话语理论所指,话语并非仅为记录,亦是话语存在和话语运用所形成的权力状态,“话语乃是必须控制的力量”。⑤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话语的秩序》,肖涛译,载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随着国际法规范的日渐增多和使用的日益频繁,国际法可以被任何个体用来判断和评价某项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个体熟练运用国际法话语体系有助于占领国际事务的道德与法律制高点,否则便可能由于丧失话语权而变得处境艰难。⑥参见车丕照:《国际法的话语价值》,《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36页。
从国际法的斗争功能来看,国际法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反殖民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反击以实力出发的不平等对待、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规范基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通过国际法进行沟通、评判和分配责任,进而在国际造法、司法层面展开国际法律斗争来维护自身权益。小岛屿国家在气候谈判中坚持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以内的目标和毛里求斯推动针对英国的查戈斯群岛咨询意见案,⑦参见曹亚斌:《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小岛屿国家联盟》,《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第39-43页;黄影:《联合国框架下非殖民化问题的最新进展——国际法院“查戈斯群岛咨询意见案”述评》,《国际法研究》2019年第6期,第28-40页。都是充分体现国际法斗争功能的典型例证。相比于战争和暴力手段,国家间在国际法的范围内所进行的言语交锋和论辩显然更为平和。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角色走向世界,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发挥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以及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斗争功能。
总体来看,百年变局下,维护和平、促进合作和实现共同利益等国际法功能面临新的时代背景和使命,全球治理和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使国际法功能产生了动态变化的需求。在特定情况下,国际法之所以没有发挥出令人满意的作用,原因在于国家利益的制度凝滞和对待国际法态度的历史惯性。从实然的角度来看,第一,国际法维护和平的功能正在朝着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的方向深化。第二,国际法促进合作功能的重心正在转为填补全球治理赤字。第三,国际法实现共同利益的功能有所减弱,但助力国家身份与角色的塑造功能有所增强。第四,国际法的斗争功能得到不断强化,国际法将愈加呈现出斗争性的一面。
四、百年变局下国际法功能的有效发挥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时空背景下,国际法呈现出不同的功能状态。①See Onuma Yasuaki,International Law in and with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Func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14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7(2003).从国际社会整体来看,国际法是用以调整国际关系和建立国际秩序的法律手段。但是,从单个国家的视角来看,掌握在不同国家手中的国际法所起到的作用各异。②参见朱奇武:《谈谈国际法的作用》,《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45页。例如,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国际法功能而达到一定的社会效果,如承载国际社会的结构和制度、实现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等。③See Philip Allot,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Law,in Michael Byers(ed.),The Ro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69(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国家在运用国际法时,需要辩证地对待其功能,结合自身的综合国力、角色定位、价值目标等,扬长避短,科学促进国际法功能的更好发挥。
(一)协调运用国际法的内容和方式
1.强化国际法的稳定和预期功能。国际法并非调整国际关系的唯一工具,除法律手段外,国际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手段都具有积极的反映和促进作用,甚至在很多治理领域,是政治而非法律主要发挥着调整国际关系的作用。④参见万霞:《论国际法的性质与作用》,《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79页。在看待国际法的功能问题上,不仅要反对国际法“虚无论”,也要反对国际法“万能论”。国际法与政治、政策或道德手段相比,在调整手段灵活性、差异性方面相对较弱,并不能总是及时回应不断变动中的现实世界,存在覆盖面与适应程度的短板。尽管国际法的空白或灰色地带不可避免,但是,相比于政治与道德,国际法却明显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基础性,具有维系国际社会基本秩序的重要作用。不论百年变局包含何种变量因素和变化趋势,都应当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应当不断筑牢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功能,强化国际法的运用,合理选择运用国际法规则和制度调整国际关系,促进国际法稳定和预期功能的发挥,反对以少数国家的“自定规则”取代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反对以少数国家主导的“霸权秩序”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
2.选择运用国际法的适当形式。除了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条约、国际习惯法以外,国际法还包含虽没有法律拘束力但却具有一定法律效果的“软法”。①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国际“软法”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事物的出现和“硬法”制定的滞后。晚近,国际“软法”率先在国际环境法领域兴起,其原因是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贸然制定强行法无力适应客观条件的变化,客观上各国也难以迅速达成普遍的共识。②参见赵骏:《“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的发展图景与法治路径》,《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2期,第53页。“软法”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对于主权国家的约束性较小,谈判的成本较低,更加容易促成各方的共识,在推进国际合作与弥合分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国际“软法”具有不可忽视的法律效果,其不仅可以发挥促进条约的达成、解释、实施与发展等对既有国际法渊源的塑造作用,还可以在国际治理进程中发挥凝聚共识、触发行动的重要作用。③参见何志鹏:《逆全球化潮流与国际软法的趋势》,《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59页。另一方面,以国际条约为代表的“硬法”意味着相对较强的拘束力,可以在有力地约束各国行为的同时,增强国际关系法律调整的可预期性与稳定性,促进全球治理理想模式的形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应当充分发挥“软法”与“硬法”的不同优势与功能,灵活选择不同的国际法形式,在“软法”与“硬法”有机结合与相互配合的基础上,运用国际法服务于本国利益和推动全球治理秩序的构建。
3.选择运用国际法的合适时机。在国际关系不同阶段,国际法的功能存在不同的阶段策略和效果区分。在国际关系的危机与挑战时刻,恰当地运用国际法可以产生预期效果,而错失良机之后,国际法功能便会大打折扣。例如,为阻止全球臭氧层空洞的进一步扩大,各国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该项条约有力扭转臭氧层空洞并使臭氧层逐渐恢复,收获了“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国际条约”的美誉,成为国际社会在适当的时机下运用国际法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的典范。④See United Nations,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Ozone Layer,https://www.un.org/en/observances/ozone-day,visited on 29 June 2022.从国家视角来看,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不同阶段的功能也会呈现出一定的侧重。例如,在国家间政治与经济合作关系处于良好状态时,国际法更多地体现出国际合作的促进功能,而在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低谷时,国际法通常被作为防范、限制、反制或斗争的工具。这也充分表明,国际法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运用的时机,如果时机不当,则国际法可能会难以发挥预期的效果。在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都面临着诸多的风险与挑战,只有善于在特定时机下将国际局势演变与国际法运用巧妙结合,才能更好地利用国际法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使自己的意见更好地被国际社会所倾听和接受。历史上的英国、美国等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均借助国际法营造出了更加有利于自身发展成长的国际环境。①参见蔡从燕:《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190-193页。
(二)促进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交互支撑
理论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存在“一元论”“二元论”等主要观点,前者强调国际法和国内法属于统一法律体系的不同构成部分;后者则强调国际法和国内法本质上独立且互不隶属,国际法必须经由转化或并入等过程方可在国内法中产生效力。②See Antonio Cassese,Towards a Moderate Monism:Could International Rules Eventually Acquire the Force to Invalidate Inconsistent National Laws?in Antonio Cassese(ed.),Realizing Utopia: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 188(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但无论如何,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存在功能性的关联关系,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渗透并内在互动,二者统一于国际关系对于法治状态的客观需求。③See James Crawford,Chance,Order,Change:The Course of International Law 143-165(Martinus Nijhoff 2014).法治互动过程持续且双向、循环往复,这种互动状态构成了国际法功能产生、发挥并产生现实效力的基本状态。④参见赵骏:《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第83页。
一方面,国际法能够借助国内法实现其规范功能。国际法可以通过影响各国国内法,促进协同有效地处理全球性问题。英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都规定国际条约须经过转化为国内立法的方式,⑤参见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页。才能在国内得到实施和适用。中国加入WTO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国内法清理与修订,主要以转化立法的方式确保国内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规则对接国际经贸规则。⑥参见《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32334/1632334.htm,2022年6月29日访问。同样地,中国在批准《京都议定书》之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⑦参见吕忠梅、吴一冉:《中国环境法治七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5期,第108页。此外,为了有效落实和衔接国际法中的先进规则,中国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并逐年更新,进一步推动了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
另一方面,国内法能够提供国际法功能的操作性要素,这主要体现在国内法的原则、规则或制度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而被纳入到国际法中。实践中,许多广为接受的国际规则都是由国内法发展而来的。例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最先在美国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中出现,随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该制度逐渐被国际组织的决议、宣言所引入而成为国际环境法的重要制度。①参见林灿铃:《环境问题的国际法律调整》,《政法论坛》2001年第5期,第127页。诸多国际条约也规定了该制度。②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埃斯波公约》《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等都对此进行了规定。又如,中国海南自由贸易港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在补贴、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形成了能够实现国际法功能的中国方案。③参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19942.htm,2022年6月29日访问。
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互动过程中,大国在维护国际法权威、保障国际法实施和构建国际秩序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们是国际法发挥规范效力、展示规范效果以解决全球危机的重要力量。不论是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还是完善国内规则,中国都需要努力推动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的良性互动和交互支撑,避免二者的冲突与掣肘。
(三)探索弥补国际法功能的局限
国际法承载着政治格局的规范化设定、政治选择的规范化指引、政治行为的规范化约束、政治纷争的规范化解决等理想层面的功能,④参见何志鹏:《硬实力的软约束与软实力的硬支撑——国际法功能重思》,《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05页。同时,其也存在着功能上的局限性。国际法在制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权力政治的影响,在执行过程中也受到国家同意原则的严格制约,这使得国际法的内容本身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为此,应当通过如下途径探索弥补国际法功能的局限。
首先,强化对国际法功能局限的规律性认识。作为调整国际关系的工具,国际法存在的功能局限是对国际法形成、适用和解释过程的一般规律性反映。国际法的功能局限不仅受到法律自身局限的影响,而且也深受国际社会结构特点的影响。任何事物都具有不断螺旋式发展的一面,通过国家实践不断致力于探索和推进国际法功能局限的弥补,依然充满可能。国家不仅是国际造法的核心主体,也是国际法规则遵行的主体,这一双面形象使得国家在塑造国际社会认可的法律规范与体现本国国家意志上达成了平衡状态,二者在不断彼此影响的状态下推动国际法以良法的形式不断完善。
其次,强化规范形成阶段国际法功能的塑造。国家双边和多边的约定、明示和默示的认可是国际法生成的基本方式。作为国际社会的法律规范,国际法规范的形成基于国家自身的允诺和有效的同意。①See John Westlake,International law 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4).国际法的力量来自国家认同与社会认可,只有国家普遍地持有认可和支持态度,国际法才具有权威和信用。②参见何志鹏:《以诺为则:现代性国际法的渊源特质》,《当代法学》2019年第6期,第146-157页。实践中,国际法功能也必须围绕主体意志及其有效协调展开。各国的立场与利益关切是否真正得到体现,相关国际法规则本身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法能否被有效地认可和实施。在规范形成阶段就应当重视对国际法功能缺陷的弥补与完善,这需要每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平衡他国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也需要通过合理的程序设定限制大国强权的影响和增进参与规则制定的普遍性与实质性,以形成普遍认可、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弱化国际法限于国家之间允诺而缺乏外在强制性的缺陷。③参见蔡从燕:《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188-206页。
最后,强化国际法规范的正当性。国际法体现出高度模糊化和碎片化的特点,因为国际法是国家间的协调意志,这使得国际法为了增强规则的适应性,以相对模糊的文本容纳政治妥协,缺乏具备充足权威的普遍性状态。“建设性模糊”的规则状态刻意回避准确性维度要求,极大地影响了法律文本的完整性与执行性,放大了现行国际法欠缺规定或有规定但无法适用的局限性。④参见马雁、史志钦:《国际法模糊性建构体系中的全球治理规范秩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67-189页。同时,国际法的模糊性可能会进一步引发司法造法问题,相关国家的法律利益也会面临不确定性的风险。为此,进一步设定和更新国际法的理念价值和伦理标准,建构国际法的公正地位,提升国际法的形式理性,不断完善国际法规范本身的正当性就显得十分必要。因此,倡导国际法律秩序的价值,提高国际法规范本身的正当性与可预期性,将有助于增强国际法的权威性和不断提升国际关系的合法性。⑤参见何志鹏:《硬实力的软约束与软实力的硬支撑——国际法功能重思》,《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12页。
(四)正确处理国际法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国际法兼具保守与开放特征,具有在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动态过程中回应和解决全球问题的潜力。随着百年变局下国际格局的演变,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及其规则的不合理性愈发凸显,国际法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发展势在必行,这是国际法能够有效发挥其应有功能的重要前提。推进国际法的创新需要妥善处理好守正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守正意味着坚持遵从国际法的现代性,崇尚国际法的价值性和遵循国际法的规律性,而创新则要求国际法适应和满足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国际法的守正和创新处于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就国际法功能而言,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①参见赵骏:《国际法的守正与创新——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规范需求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29页。面对危机,国际法需要发挥稳定秩序的功能,并审视和反思既有制度,酝酿更加公正、合理与高效的制度改革。因此,筛选、总结国际法制度改革发展的国际实践,进而进行理论层面的提炼和升华尤其重要。
第一,国际法创新应当兼顾维护国家利益与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国际关系状态的变化要求国际法由原来主要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律逐步发展成为应对全球性危机与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规范,由共存国际法向合作国际法进行转变。国际法不仅要继续发挥维护国家利益与稳定国际秩序的作用,还应当在此基础上更加顾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此,国际法创新应当重点关注如何实现国际法在维护国家利益与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之间的平衡,以及如何使国际法更好地促进人类共同发展。
第二,国际法创新应当体现国际社会结构与国际关系的变革发展,特别是顺应中国与世界局势的新变化。百年变局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力量上升,国际社会的结构正在从西方中心朝着东西方平衡的方向演进,国际法创新应当对国际社会的新变化进行回应。在国际法的形成阶段,国际法创新必须积极吸取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理念主张和规则方案,反映这些国家的主要利益和时代需求。在国际法的运用阶段,国际法创新要求对国际法的解释和适用也应当顺应上述发展变化。
第三,国际法创新应当尊重各国的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有必要在相互交流和扩大理解的基础上增进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平等互鉴和包容互惠。因此,国际法创新应当体现多元文明共存的客观事实,“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5版。,进而构建起包容互鉴、尊重多元、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
五、结语
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百年变局背景下,从发展和创新的角度思考国际法功能的时代要义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理论凝练、思维启示和方法指引。充分发挥并逐步发展国际法功能对中国有效应对各种挑战与风险,深度参与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具有重大意义。大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定鼎格局和主导方向的重要作用。面对百年变局,中国担负着促进国际法治和维护国际秩序的时代使命,这要求中国应当实现从“会用”国际法到“善用”国际法的重要转变,在国际关系中熟练运用国际法以达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基本目的。为了促进国际法功能的妥善发挥,中国不仅要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比较优势,尽量规避国际法的局限,也要在规范形式、时机成本等方面做好选择衡量。更重要的是,国际法功能应当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客观需求契合同步,综合考量新旧规则衔接的历史维度、国内外法治互动的内外维度以及往今机制考察的现实维度,有效地变革和完善国际法功能。这些是中国在运用国际法时必须深入探讨的关键因素。国际法功能的充分发挥,无疑将有助于化解国际社会的普遍性风险和调控不同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促进中国方案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