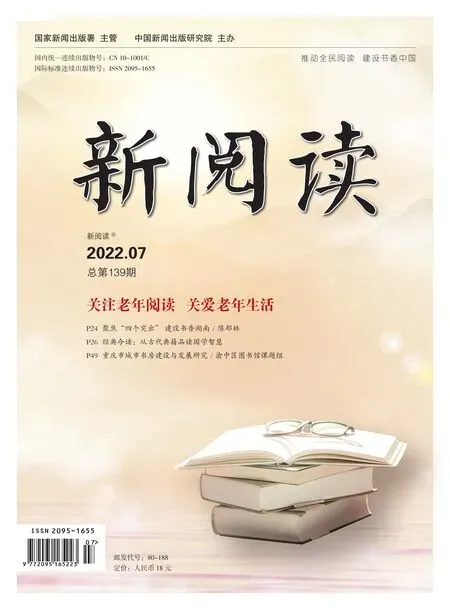一个法国汉学家的“中国共情”
——《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新的社会革命》评介
2022-10-16龚伟亮吕安娜
在“汉学家”这个群体中,不乏熟悉中国语言和文化、长期专注于中国问题研究、在学术研究和公共传播中持续发出知华友华和声援中国的声音者,但是如法国汉学家、知名媒体评论家、前外交官魏柳南(Lionel Vairon)这样,在历史认知、理论思考和表述方式上都体现出对中国“高度共情”的,仍然并不多见。
《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新的社会革命》(池宗华译,党建读物出版社2021年8月版,以下简称《时代之问》)一书的书题(同时也是贯穿性的总体意向或“问题意识”),来自于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该书总结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国大党”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的新的时代命题,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取得的成就。从执政理念、政府改革、中国智造、司法改革、基层治理、城乡平衡、公平教育、精准扶贫、生态文明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全面而富有“现场感”地揭示了在这场新的伟大社会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面对“时代之问”(Question of the Times)交出的新答卷。
内外合一:根植于作者内心与观念中的认同感
“大国大党,正道沧桑”的中国主题奏鸣,在这位来自遥远国度的汉学家的头脑和笔下,得到了同频共振的回响。这种回响既带有基于历史梳理和现实观察的客观性与实践性,又体现了作者一种难能可贵的对于“人民性”理念的高度认同。如果说前者为整本书之所以能体现高度的“中国共情”提供了材料和论据,后者则是这种“共情”的智力/智识上的基础。
作者对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理念的认同,敷演于内,则有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国战略和中国行动的深度认可;敷演于外,则体现为一名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前外交官对于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担当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心口合一,理念和逻辑合一,内容和修辞合一的。
中国共情:贯穿于理念与逻辑中的认同感
多年来,魏柳南不仅作为一个关注中国、研究中国的冷静和审慎的学者发言著述,而且在个人历史和文化实践层面对于中国也有着强烈的代入感。他曾经面对媒体坦诚自己的中国情缘:“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005年,去的是上海,被它的现代化水平惊呆了。”“我已经来华60多次了,每3个月来一次,这里都会出现新事物,变化非常快。我的妻子是半个中国人,我的儿子在中国银行巴黎分行工作,我的女儿在美国获得中文和中国文化学位……”
魏柳南的这种“中国共情”不仅体现为一种清晰和确凿的理念认同,而且体现为对于理念背后的政治逻辑和历史逻辑的把握。书中对诸如浙江“最多跑一次”的政务服务改革、“裁判文书透明化、审判现场可参与、司法服务便捷化”的司法制度改革、“精准扶贫+互联网电商”的可持续扶贫机制等案例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知道中国这些年发生了什么,而且清楚地认知到发生这一切背后的政治历史逻辑。全书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改革依靠人民,改革为了人民”的底层逻辑构成作者所着力描摹的“中国行动”的指针。“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工人阶级为基础,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近年来进行了多次卓有成效的改革。”魏柳南对当代中国改革逻辑的这一认知,是清晰无误和鞭辟入里的。
这种理念世界和生活世界的交融,可以看作支撑他在很多时候带有对华歧见的欧美社会中一以贯之地发出理性和友好声音的内在基础。他以中国为镜鉴,多次以公开方式发出对欧美世界的批评。例如,他在专著《中国的威胁?》一书中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驳斥了在欧洲盛行的“中国威胁论”;又如,他在演讲中呼吁,“西方国家应逐渐放下‘优越感’,把西方文明放到和其他文明平等的位置,一同构建崭新的、带给人类和平与福祉的‘全球化’”。
综上所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麻醉科在住院医师气道管理培训中探索性引进了“CBL”的教学方法,同时在我们进行的国家级气道培训项目和地区级手拉手培训项目中均已实施多年,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充分调动麻醉住院医师学习的积极性,通过培训可以迅速掌握具体临床实践思路和技术,切实地提高了气道管理的知识和技能。
“心口合一”“理念和逻辑合一”,也水到渠成地导致和表现为“内容和修辞合一”。综观全书,作者对中国语境中的政治、历史话语和修辞的熟稔程度是惊人的,总让人恍惚之间几乎忘记了正在阅读的《时代之问》是一本来自法语世界的译著。这一点,我们只用看一眼他的各个章节标题——比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协商治理:释放‘人民当家作主’的活力”“平衡也是硬道理”“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就会如沐春风、会心一笑了。
如魏柳南在书中所说,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的社会革命的理念和实践的关注,乃是基于“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全球治理困局凸显,地区冲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甚嚣尘上。世界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这样一个全球性的严峻背景,在这种自觉的国际视野之下,魏柳南在书中展开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的社会革命这一伟大实践的观察论述,在其本身的能指所指之外,始终具有着一种微妙但清晰的“意在沛公”的弦外之音。在此意义上,笔者宁愿把这本讲述当代中国改革的著作看作是一位外国观察者基于其自身社会环境(或曰困境),对于“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一个婉转回答。而事实上,后疫情时代,中国为回应时代之问所提出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和中国愿景,也的确无一不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在历史逻辑方面,作者对中国的理念认同也奠基于其对中国革命和改革历史的了然于胸。《时代之问》的书名,除了前述的体现一种鲜明的现实感之外,其实也精准地踩中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窑洞之问”和“进京赶考”的历史节拍,“新的社会革命”也吻合着“历史周期律”之辩的历史韵脚。他在做客CGTN法语频道《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节目时曾评论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实现民族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中华民族焕发出蓬勃生机。”他认为“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显然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实现快速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政治发展的范例。”这都体现了作者深厚“中国共情”的历史基础。
以叙代论:蕴藏在话语和修辞中的认同感
话语和修辞的认同与理念和逻辑的认同互为表里,体现出魏柳南这种“中国共情”的深度是卓然不群的。这种共情和认同既远超一个“中国通”的层面,也超过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心智表现。更何况,《时代之问》的论述里还增加了魏柳南作为一名来自法国的国际关系学者的国际视野和理论深度。
对灌区进行现代化管理,建立现代化的管理机制。充分调动相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相关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促进灌区朝着现代化灌区建设发展。
考虑经济性与可靠性的大小水电短期协调消纳模型//苗树敏,罗彬,刘本希,申建建,程春田//(8):101
其次,在线下传统课堂上用作业或测验的方法检验学生线上学习的学习情况,对学生线上自主学习起到监督作用,而不是学生想的线上微课视频留下的问题老师是置之不理。课堂上有组员一起协作完成一个项目,让同学们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了实践中,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动手编程能力和团队协作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4]。
作为一个汉学家的理论深度,不仅体现为对于诸如“半床棉被”这样的经典红色故事的熟知和引用(这种对细致材料的占有当然体现了一名当代汉学家的“自我修养”),更重要的是,在书中时常可见的带有浓厚理论色彩的信息增量。比如,在论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出现“美好生活”一词时,他将亚里士多德对于“美好生活”论述与成书于汉代的《礼记·礼运》篇熔为一炉;再比如,他在阐释群众路线时讲到:“中共不同于其他政党,它既反对精英主义,又反对大众主义”,“中共要在精英主义和大众主义之间寻找平衡,既不能脱离群众,又不能唯群众马首是瞻,而是要来自群众,又领导群众”,就鲜明地带有一位来自西方世界思想者的理论新意。
综合而言,本书带有公众普及和舆论纠偏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有在欧美社会面向国外读者为中国发声的积极进步意义。作者在书中很多时候是以一位面向公众侃侃而谈的描述者的姿态出现,在述论结合上往往产生“以叙代论”的遗憾,在更高层次上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一种更高级人类文明的存在的意旨还较少有深刻揭示和体念。
斯人已逝(魏柳南先生于2020年12月23日圣诞前夕因癌症不幸离世),对于他的这一份真诚和努力,我们仍要报以一份温情与敬意。